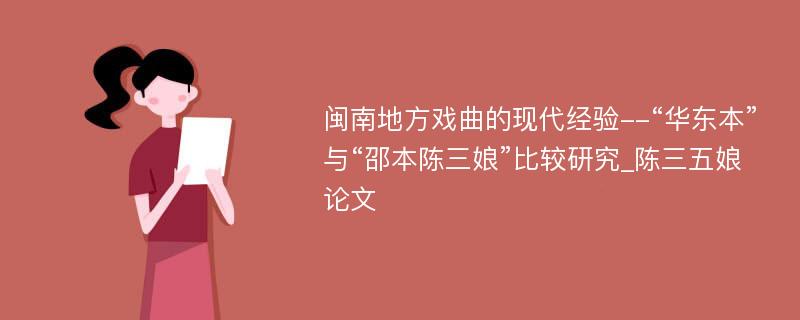
闽南地方传统戏曲的现代性经验——华东本与邵氏本《陈三五娘》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闽南论文,戏曲论文,邵氏论文,性经验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缘起 笔者与黄科安教授在2013年5月台湾成功大学举办的“台闽民间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以戏改语境中的荔镜情缘(即《陈三五娘》)的故事重述为例,专门探讨精品生产到经典命名过程中的选择性遗忘机制。我们认为,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探勘戏文经典的形成机制与潜在裂隙,“不难得知所谓戏文正典的标志确认,并不在于其于一时一地之风头无两的流行喧嚣,也不在于各式各样、琳琅满目之戏曲奖项的锦上添花,更不在于籍籍无名之草根戏迷的口耳相传、街谈巷议;而在于被拥有话语权力的文学史大家、戏曲史名家,将之纳入具有官方背景、影响面大的全国统编戏曲文学史教材,在这一版面有限的编撰框架中,辟有一节以上之独立篇幅而予以讲述。如此这般,方使之成为一代又一代戏文专业学生(作为戏曲艺术的历史传承者与当下发展者),所反复涵咏、用心揣摩的学习对象;以及一批又一批学科建制内的戏曲学人(作为艺文正典的阐释者与捍卫者),运用层出不穷、花样百出之理论工具进行循环理解、更新诠释的理论演练场。”[1]实而言之,现代性语境中戏曲经典的生产与再生产,既关乎审美又是来自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传媒场等多个“场域”之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博弈结果。 具体到本文论域,本已沉沦的梨园戏《陈三五娘》,经由戏曲改革这一传统地方戏曲现代性转换的重要路径,得以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在东亚大陆想象戏曲现代性的关键时刻,极具症候意味地超越文化地域的天然隔阂与语言分殊的现实藩篱,骤然暴得“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不虞之誉。其在六十年前“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中,出人意料而又合乎情理地一举斩获“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乐师将、舞美奖和四个演员一等奖”[2]等六项最高奖项,并旋即改编为电影而热透闽南、远销南洋,成为闽南戏曲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与艺能界挥之不去的情结。时至今日,仍然热度未减、高烧不退。无论深处“闽南戏曲文化圈”核心地带的戏曲史家,如郑国权、吴捷秋、庄长江等;还是位居次核心区的台湾地区学者,如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及其座下得意门生;抑或大洋彼岸声誉卓著、著作等身的西方汉学家,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等,从时代知识状况、思想主旨意涵、艺术表演特色、现实作用影响等诸多维面,跨学科、全方位对之进行深度剖析与全面解读,遑论批量涌现之常见常新的印象式戏评与绵延不绝的学术化论文,足见其影响早已溢出舞台的表演“场域”,积淀为这一文化圈中庶民阶层的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 吊诡的是,倘若穿透彼时闽地“戏改”所建构之构狭隘局促、画地为牢的现代戏曲地理,即龙溪地区(今漳州市)赋予重点发展“芗剧”(即闽南歌仔戏)的时代使命,晋江地区(今泉州市)则倾力建设梨园戏与高甲戏,而从“闽南戏曲文化圈”的广阔视阈对两个重要改写版本进行必要而全面的检视,令人不胜唏嘘地发现,出自“芗剧祖师爷”邵江海手笔的《陈三五娘》(1937年初稿,1961年修订),成为潜隐于历史深处之“被遗忘的文献”。进而言之,检索海峡两岸现今出版的多部区域文学史论著,即便是在“全球本土化”之大势下的新编戏文史与歌仔戏的剧种史,如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原厦门台湾艺术研究所所长陈耕先生的《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海峡悲歌:风雨沧桑歌仔戏》,厦门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陈世雄教授和曾永义教授联合主编的《闽南戏剧》,知名芗剧编剧陈志亮先生的《漳州芗剧与台湾歌仔戏》,均未对邵氏改编本加以正面论述,顶多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 那么识者不禁要问,为何华东本梨园戏《陈三五娘》,越界成为闽南与潮汕地区妇孺皆知,甚或台湾与南洋等地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而邵氏版歌仔戏《陈三五娘》即使是在其核心区厦漳两地也芳踪难觅、难见经传,毕竟同为地方化知识生产的现代性产物,两者命运却有云泥之别?有鉴于此,偏向编导演等具体舞台实践的剧坛名家与侧重演绎思辨、学理探究的学院精英,基于各自不同的阐释视域,对这一牵涉戏曲地景与文化记忆的戏曲史之问,纷纷提供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多元理解。考虑到“才子佳人的老套模式,其在具体时空中的各式表述,本身就构成饶有趣味的永恒议题”[3],笔者尝试在“现代性如何建构爱情神话”的阐释框架下探讨爱情传奇这一古老戏文类型的当代境遇,进而“将之纳入关系主义、建构主义的参照视野之中,视之为一种面向日常审美生活的文化实践,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示无限可能的跨界行动”[4]。 二、经典建构的时代规驯 首先就有论者基于“个人是历史的人质”的述史秩序意味深长地指出,剧作改编者在世俗社会与戏曲“场域”的权力结构身份位置与话语权力资源掌控,促使华东会演本在经典命名之没有硝烟的竞逐之战中,一举压倒包括邵氏本在内的众多改编本,进入史册、影响后世。若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工具重新观照华东本《陈三五娘》的来龙去脉及其所映现之新文艺工作者的自我镜像,不难发现许书纪、林任生等兼具现代性视野又熟稔民俗曲艺的新文化人,在这一已然描述为“抢救”之改编事件中所起作用的暧昧多义。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能在“改人、改戏、改制”之自上而下、如火如荼的改革实践中,享有不容置喙的主导地位与真理在握的心理优势,并不在其对闽南庶民戏剧的感情多寡有无和具体编导演经验的深浅与否,而在于其作为上级部门派驻地方、深入基层的戏改干部,被主流话语塑造为掌握先进思想武器与现代戏剧理论的理性改造者。缘此,唯其方能深入把握剧种历史嬗变规律与戏曲未来走向,真正自觉领会专属“新社会”、“新时代”、“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戏”应该“怎样演”与“为什么要演”。由此不难理解身为晋江县文化馆首任馆长许书纪,何以能够审时度势的凭一人之力,瞬间颠覆梨园戏数百年来三派分立、相互设防的剧种格局,石破天惊地“开创了混合三派于一出戏的梨园大融合”[5]。与新文艺工作者(主流观念形态话语之合法化的具象代言者)相互映衬的是,无论是梨园戏《陈三》的口述者蔡尤本,还是歌仔戏的改良者邵江海(杨路冰先生在1995年2月厦门举办的“歌仔戏艺术研讨会”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邵江海与新文艺工作者颇有摩擦而格格不入”[6]),缺乏前者拥有丰沛的政治资本与潜在的经济资本,其特有或曰残存的文化资本乃是,“中国古老的戏剧行业百千年来所形成的、为艺人们熟稔的那一套行业规范”[7],只是天然自发地懵懂知道“戏”从艺术传统的审美角度如何演而已。质而言之,现实身份不过是腹内有戏、需要改造的民间艺师,其作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严重匮乏与时代对话的思想资源,陷入身份迷茫、认同焦虑的现代性焦灼之中,因此能量有限、话语低微。 另有不少学者将论述顺势引申到中华戏曲架构的剧种坐标中来。从剧种起源时间上看,梨园戏历史悠远、出身高贵,其轻柔曼妙、韵味悠长的“十八科母步”,无愧于“宋元南戏活化石”的隆重声誉。与之相应成趣的是,歌仔戏作为与“新剧”几近同时出场的“旧戏”,其可考历史不过短短百年,起身微末、发自草根,表演程式、身段舞步、搬演剧目,都是挪用自其他剧种而来,在文化积淀与血统纯正方面无法望其项背。事实上,作为老歌仔戏“四大柱”之一的《陈三五娘》,即为梨园戏中小梨园“七子班”的传统保留剧目。从地理空间上看,如果说梨园戏通过勘定溯源,千方百计地与地位显赫的“南戏”(已然被戏曲教科书刻画为华夏戏曲之正宗源流)构建联结,进而与占据大中华戏曲版图之主流剧种建立想象性的脉络关联,而摆脱地方剧种的身份焦虑与合法性危机;那么坎坷波折、命运多舛的歌仔戏,则无法循此路径而获象征资本,始终难以进入戏曲圈层的核心地带以配合文化中心的共同体想象。其前身“歌仔”据说诞生于东南边陲的九龙江畔,后传入宝岛台湾而在日据时代渐次演化为“大戏”形态,再借助闽台民间交往辗转回传到故土原乡。显然,歌仔戏从诞生伊始到繁衍至今,长期地处远距中原(政治中枢)与游离江浙(文化中心)的边缘区域,被主体视为“他者”而将之放逐。其典型例证,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统治大陆(亦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内地延展主义”等酷烈文化殖民政策)之时,“说它是‘亡国调’,对‘歌仔戏’艺人的侮辱和迫害,无所不至。到抗战爆发,更是凶狠地下令禁演,甚至扬言凡是唱‘台湾戏’的抓到就要杀头,并已搜查汉奸为名,逮捕‘歌仔戏’艺人游街”[8]。据此歌仔戏本身被“污名化”的现实境遇,其代表剧目《陈三五娘》珠玉蒙尘也就顺理成章。应该承认,上述论述的确有助于今人理解《陈三五娘》乃至歌仔戏这一剧种的历史定位与时代坐标,以小观大、由点到面,管窥蠡测地方传统戏文在东亚现代性想象中的命运问题。但进而思之,这一着眼于地缘要素、政治光谱及其所支配文化策略的宏大修辞,或许过分耽溺于族群结构与权力分配宰制剧种疆界的表象层面。其实暂且不论在华夏戏曲甚至东亚戏剧的讲述图谱,中心主流/地方边缘、历史正统/现代晚发、精英阶层/庶民群体的二元划分,一贯就是界域开放的动态游移,而非静态凝滞的一成不变。历经反复研磨、精心改良的地方曲目(诸如华东本《陈三五娘》之类),在风云际会的历史机缘下,鲤跃龙门、反客为主而进入正史、跻身主部数不胜数。姑且就说,邵江海为后人缅怀的功绩之一,便是其创作“改良调”,使得“疑神疑鬼的地方当局,因闻不出改良调和改良戏有任何‘亡国之音’、‘伤风败俗’的气味而网开一面”[9],让歌仔戏在闽地“禁戏”的喧嚣声浪中获得生存空间。职是之故,笔者以为,不仅要重返历史语境而将问题重新语境化,更要直面文本本身的艺术质素。 三、戏文经典的美学伦理 有道是,“爱情故事永远被人们重述,而一个被巧妙重述的爱情故事又永远是迷人的”[10]。去粗取精、反复提纯的华东本与市井味浓、异质性强的邵氏本,各擅胜场、互有短长,但前者更为符合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需要,典型表征主流话语对民间资源的征用询唤。耐人寻味的是,在叙述内容的取舍方面,二者都具有大刀阔斧、删繁就简的“腰斩”勇气,所不同的是邵江海大笔一挥是前半部分,而华东本则屏蔽了后半部分。显然问题的枢轴,并不在于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在于“为什么”和“如何讲”这个故事。毋庸置疑,许书纪等新文艺工作者壮士断腕,力排众议、忍痛割掉《荔镜记》的大半篇幅(当中包含着“美视美听”的《大闷》),让这部戏在第13出《私奔》的高潮时刻戛然而止,绝非临时起意的突发奇想,亦非有效压缩戏曲演出时间至三个钟头的单纯技术考量,而是有着“闽南族群想象现代性”[11]的文宣用意。具体来说,在“一脉相承五百年”的古老戏文中,官宦子弟陈三之所以能够战胜土豪恶霸林大而抱得美人归,并不是感天动地、浓情蜜意却是凌空高蹈、虚无缥缈的真爱力量;恰恰相反,其所凭借的是其位居广南运史的兄长(在彼时红火的革命伦理中乃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所带来之炙手可热、无以伦比的官位权势。若重回文本“叙境”及其支撑逻辑,原来最终成就“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大团圆结局,就表象而论是封建高官源自血缘纽带、亲情关系的出手相助,就实质而言是“不在场的在场”的世俗权力。毫不夸张地说,这无疑意味着决绝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故事主人公,还是为温情脉脉之旧有制度宽宥包容、收编整合,亦指涉陈三与五娘这些疏离体制、想干就干的他异个体,其惊世骇俗的叛逆举止与可歌可泣的爱恋行为,仅仅是青春荷尔蒙的一时冲动与适度越轨,终究还是要心悦诚服地臣服父权体制与复归宗法制度,轰轰烈烈的斗争出逃带来的是更深的陷落禁锢。为了避免叙述逻辑困窘、构筑新的“常识”,契合“爱情是婚姻之合法基础”的启蒙现代性神话,建立戏文思想主旨与新婚姻法精神耦合关系的社会现代性论述,华东本别出心裁抑或别无选择地扬弃传统戏文关于“公子受陷落难、佳人无助哀怜”的解决方式,藏匿陈三兄长(父权的符号、体制的象征)这一完成终极逆转之关键人物的出场,以前途未卜的大胆私奔(开放式结尾),置换苦尽甘来的一家团圆(闭合式结局),深刻隐喻“被启蒙者”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于道统之外。细而言之,其将重心投向戏文的前半部分,浓墨重彩地渲染《睇灯》、《投荔》、《留伞》等相关节目,借重“婚姻由己”的同义反复,以绘制两情相悦、相知相惜的传奇爱情;同时强化《训女》、《出奔》等有关戏码的戏剧性碰撞,极力将戏文呈现之发生在私人领域的个体事件(如林大逼婚的情感冲突与父女之间难以调和的代际矛盾),刻意引向公共空间的热点议题(如时尚新颖的阶级表述与方兴未艾的斗争话语),从而满足“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的戏曲美学与诗性伦理。若说华东本以“去尾”避免所谓的画蛇添足,邵氏本则体现另一思路“掐头”彰显画龙点睛。其在潜意识层面,未曾有过挑战升斗小民之审美期待视野与群体情感逻辑的冲动,在自觉意识层面,始终与现代性主潮保持审慎的审美距离。具体来讲,满肚子戏、用心良苦的邵江海,为了让“哭腔”(歌仔戏最感人肺腑也最富有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拥有更大的驰骋空间与用武之地,不仅将前面交待男女主人公“上元赏灯的一见钟情、再见倾心的投荔相许”[12]的华彩段落统统删去,还将细腻展现二人“由慕色到慕才,由情欲到精神”的叙述章节一笔抹消,从而把整部戏的叙述重心放在男主人公被捉之后的感伤悲苦。缘此,在华东本删除殆尽、不见踪影的大段唱段(如五娘在心上人被官府缉捕归案、发配充军之后愁肠百结地“哭五更”,即梨园戏明清刊本中的《大闷》一出),在“江海师”手中不仅得以存留,而且大大强化以至于远远超过华东本的母本蔡尤本的口述本全本。例如,在邵氏本《中集》开篇伊始,五娘便在婢女益春捧水进屋之前,未曾消歇地从一更唱到五更(连唱八十多句),之后又用长达十六句的冗长唱段以表达肝肠寸断的相思之苦。平心而论,这种用抒情僭越叙事的剧本处理方式,的确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演员的唱念功力,让戏曲观众郁结于胸、铭心刻骨的复杂情感恣意抒发,压抑已久、热闹翻滚的炙热欲望彻底宣泄,无处安放、疲惫感伤的心灵驻留栖息,有效增强歌仔戏的舞台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但其结构情节的叙事技巧上实在不甚高明,无限延宕的反复吟咏、一唱三叹的过度煽情,不仅有“戏不足、哭来凑”的“做戏”嫌疑;而且与剧情发展的内在逻辑严重不符,毕竟五娘此时早已对陈三压倒竞争对手的显赫之家世了然于心,何须终日以泪洗面、哭天抢地地自寻烦恼。总而言之,一个平淡无奇、司空见惯之富家子弟的猎艳故事,被华东本翻新为人本主义的爱情颂诗与反抗男权的反封赞歌,被邵江海包装成生命欲求的身体狂欢与感怀身世的海峡悲歌。前者在现代性“元话语”模式下,不仅将“超秩序”与非理性的恋人絮语,统合为秩序化的理性存在,而且因为“去尾”的言语归并而让故事主线分明、不蔓不枝,令性格坚定的戏曲人物作为行动的发出者,形象饱满、光彩照人,适合担任昂扬向上、破旧立新之时代精神的生动象喻;后者由于“掐头”让情节出现跳跃、过渡不甚自然,毫无主张、优柔寡断的女主人公,仿佛只是为哭而哭的男性附庸与窥视对象,孟浪轻浮、风流自适的男主人公,似乎只由利比多驱使而招蜂引蝶,其浅斟低唱的顾影自怜,喃喃独语的兀自徘徊,难以汇入慷慨激越、雄浑豪迈的时代合唱,只是一个逝去年代的一阕文化挽歌。 值得一提的是,若从戏曲语言的审美角度而论,华东版《陈三五娘》较之邵氏版本更有利于其他剧种的横向移植与市场推广,也便于普罗大众的欣赏接受与情感投射,因而影响面大、传唱者众。如前所述,作为闽南方言大师的邵江海,为了彰显歌仔戏剧种声腔的张力特点,用力过猛、过犹不及。其笃信“自己的,自己宝,别人的,生虱目”,其文本充斥大量貌似生动、实则晦涩的俚语方音、俗语民谚,这令一般民众(也包括念兹在兹的闽南方言区内的戏曲观者)在面对这些本应耳熟能详、形象风趣的粗粝言辞,反而悖谬式地感到不知所谓的佶屈聱牙。这一“近邻变远亲、熟悉变陌生”的背叛现象,其发生根由在于,“方言中的许多词,找不到恰当的汉字来表达,只好用谐音字,或者音义结合,自创新字”[13],使得方言剧本存有“许多互相矛盾的、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考本字”更成为一个专业性强、难以破解的语言难题,有待方言专家的悉心考辨与戏曲学者的上下求索。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剧团班社在特定公共观演空间演绎华东本《陈三五娘》之时,或许会因时因地制宜使用风情万种、缠绵呻吟的闽南方言,但其所据文本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并加以转译为典雅优美、朗朗上口的共同语。由是观之,华东本文白夹杂、雅俗兼具,借助所指与能指的符号滑动与象征游移,让地方化俗语与共同性语言珠联璧合、浑然一体,在既互相托举又相互矛盾的编码系统之中精心结构戏曲文本的意义网络,悄然塑就荔镜情缘声色交辉、辞曲并骊的声腔魅力,令戏曲的阅听者(无论是否谙熟闽南方言)回味无穷、浮想翩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