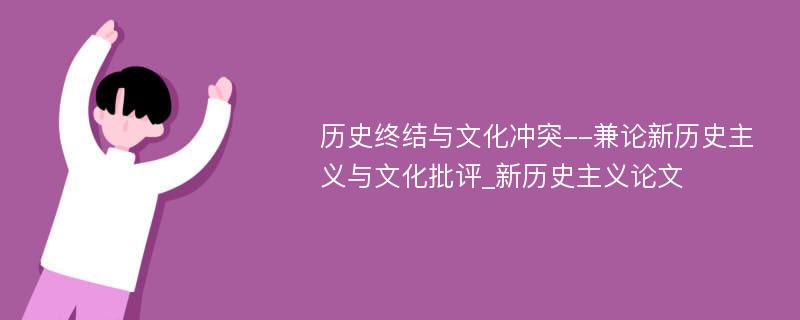
历史的终结和文化的冲突——兼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文化论文,冲突论文,批评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此世纪之交,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以及其他各门各类的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顾后瞻前,纵横捭阖,高谈阔论,各陈己见。在众多的论著中,有两篇文章尤为触目,引起了颇为热烈的反响。其一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iory?”)。该文最初发表在1989年夏的《国民利益》季刊(“National Interest”)上,后来作者又把文章扩展成专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于1992年出版。作者福山是日裔美籍学者,1955年出生,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副主任,也是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人员。据说,他的文章是根据他在芝加哥大学奥林研究中心作的一个课题报告写就的。其二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此文发表于1993年夏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此文乃是该所《变化中的安全环境和美国的国家利益》(“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两篇文章有许多相似的情况,不仅都出自于同一个人命名的研究机构,均以四字短语,后加问号为英文题目,而且两文都以历史、文化为切入点,论述人类的命运与前途,一个终结,一个起始,前后衔接,相互呼应。对于这两篇文章,已有不少人从国际关系、政治、历史、社会和哲学等方面作了评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本文只准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两篇文章中关于“历史”和“文化”的概念,联系文论中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批评作些探讨。
1989年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表之后,一些朋友推荐我看了这篇文章。但我当时未对福山文章中关于“历史”的定义和“终结”的意义进行更多的思考和质疑。
最近几年,我担任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课程,接触到了诸如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批评等文论,重新引起了我对福山文章的兴趣,后来又读到亨廷顿的文章,发现两文有前面提到的不少相似之处,因此便开始考虑能不能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它们作一些分析研究,因为这些统称为文化批评的文论都强调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的联系。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形式的话语,如法律、神学、道德学、文学、艺术……等,极少是独立自主的,通过对某个文化范畴内相互渗透的不同话语的研究,学者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控制该文化所有话语的思想法规”(“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ed.by Martin Coyle et al p.793)。《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的主编、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则是更明确地指出:“文学理论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有关话语的论述,它必然要对历史话语进行分析,因此,文学理论既是文学的理论也是历史的理论。”他还进一步引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话来加强他的这一观点:“现代文学理论必然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历史意识的理论、历史话语的理论、历史写作的理论。”(第12页)怀特把古往今来主张文史相通、文史互济的论述加以系统化、理论化。这样,我们把福山和亨廷顿的文章用文学理论来考察是否可看作当前文化批评的一种实践,还算顺理成章。
20世纪被称为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发生大爆炸、大裂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学理论的各种思潮与流派纷呈,不同的批评方法各显神通,令人眼花缭乱。如果说在过去一种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从形成到成熟,由鼎盛到衰微,长则要经历几个世纪,短则也要一个半个世纪,可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一种文学理论的生命周期愈来愈短,大多在二、三十年左右,有的更短,昙花一现。就以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和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来说,1982年,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ratt)首先将他以及与他志同道合者从事的批评笼统地概括为“新历史主义”以后,它就曾在80年代大行其道,但时到如今,不足20年的时间,就已成颓势,因为它的理论中存在着一个难以走出的“死角”。但是,新历史主义像“新批评”、解构主义等文学理论一样,在它完成其生命周期的过程中,总会留下一些闪光的亮点,比如在关于历史和文化这两个概念上,它提供了不少可供人们思考的材料,福山与亨廷顿这两篇具有轰动效应的文章恰好出现在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风靡西方学术界的时期,我们不妨寻找和探索一下这两篇文章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之间的联系(affinities),从而帮助我们认识西方文化研究的态势及其影响。
历史和文化二者都是非常难于界定的名词,据说,“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英国著名文论家雷蒙·威廉姆斯曾说过:“‘文化’一词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二、三个词之一。”文化一般分为两大类:人类文化(anthropological culture)和学术文化(academic culture),又称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或称小写c文化(small c culture)和大写C文化(large C culture)。“历史”的定义有多少种,笔者尚未见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估计也不会少于几百种;无独有偶,它也有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和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之分。当然,大小写的“历史”与大小写的“文化”是不同的。小写的、复数的“历史”,用新历史主义的解释,被称为是一种“历史叙述”、“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历史文本”。
那么,《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对历史是如何界定的呢?为什么说历史结束了呢?
《当代文学理论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的作者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认为,六、七十年代后结构主义引起的思想革命向传统的历史主义提出了挑战,对历史、历史时期、历史研究以及历史与文化和历史与文学等提出了一整套新的看法。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一词含有两个意义:一是过去的事件,二是“对过去事件的叙述”。后结构主义明确地表明历史是一种语言,一种叙述,它永远是被叙述的。因此,决不存在纯粹形式的过去,存在的只能是对过去的“叙述”,故而历史的第一个含义是站不住的。
现在,我们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下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的历史观和终结观。福山在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对“历史”与“终结”作了说明。他说:“我们或许看到的不只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战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消逝,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的终结:那就是,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达到了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作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普遍实行。”他接着又说,尽管今后物质世界仍然会发生重大的事件,尽管自由民主制度在现实世界里并非十全十美,但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这个理想将最终(in the long run)会统治物质世界。要了解为何如此这般,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有关历史变化性质的某些理论问题”。由此可见,福山使用“历史”一词有别于我们上面讨论的定义,他实际上更多地把“历史”一词作为“演进”、“进步”、“变化”等的同义词,而他的“终结”实际上是“最终”的意思。我想我们是否可以把福山文章的标题和他自己的解释,作为一种文化的,至少语言的“接受”和“变形”的例子。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福山说的那样,这里还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福山说他的“历史终结”的概念不是一个独创的新概念。他凿凿有声地说:“这个概念的最著名的传播者是卡尔·马克思,并说,把历史作为一个有开始、中间和结束的辩证过程的概念则是马克思从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那里借过来的。”他甚至断言,这是黑格尔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现在很多人对黑格尔的了解主要通过马克思,而不是直接研究黑格尔的著作。有趣的是,他在文章里对黑格尔关于历史终结的阐述仍然借助于他人。他十分赞赏30年代在法国巴黎讲学的俄裔法籍哲学家亚历山大·科杰夫(Alexandre Kojeve),让他来阐述黑格尔学说。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这位出生在俄国,后来移居法国的学者比之黑格尔的同胞对黑格尔的原著理解得更深刻更正确些呢?
根据科杰夫对黑格尔的解释,黑格尔早在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击败普鲁士君主政体时就已经看到了法国革命理想的胜利,并预言自由平等的原则会很快得到普遍的实现。他们承认,尽管在1806年以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不可能改进的了。他们把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与随之而产生的革命和政治变动说成只是在空间上扩大了这些原则,故而把人类文明的许多方面带到了更先进的水平;同时也迫使处于文明前列的欧洲与北美社会更充分地实行自由主义的原则。
福山认为,科杰夫不仅正确地理解了黑格尔的学说,而且还身体力行,指导自己的生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辞去了哲学教授的工作,因为他认为哲学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谋得了一个职位,工作至1968年病逝。福山几乎用了两个章节(全文共5个章节)来讨论黑格尔关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但是在理论阐述结束前,他谦逊地说道:“我既没有篇幅,而且坦率地说,我也没有能力深入地替黑格尔激进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辩护。”但是,他还是肯定地说:“现在的问题不是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他的观点是否揭露了我们视为当然的,实际上却成问题的许多唯物主义解释的本质。”我没有福山的那种谦逊和自信来批判唯心主义和捍卫唯物主义。不过,恩格斯早就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保守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它反映了黑格尔哲学系统和方法的矛盾。另外,科杰夫和福山论证问题的方法也使人想起了美国新历史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他的论证方法。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的作者盛宁在论述新历史主义时,曾对他的批评方法作过很精辟的评述:“按照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典型操作程序,批评家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到某一被人忽略的佚事或看法,然后将这一佚事或看法与待读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提供了怎样的新意。”福山从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找到了“历史终结”的这一看法,然后把它与世界政治舞台或意识形态范围里展开的斗争联系起来,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发出了惊人之语。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终结”之说,不少学者指出,并无多少新意。有人说得好:生活中总有一种诱惑,令人们不能抗拒,这就是寻找终结。历史上,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总会有一些预言家要大胆断言:这是最后一次!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就充满信心地预言:拿破仑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场战争。事实并非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预言。但是,那次大战的硝烟未散,美国总统威尔逊却又信誓旦旦地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a war that would end all wars)。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诸如丹尼尔·贝尔、李普塞特等思想家、理论家高谈“意识形态的终结”。在美国文学史上也不断有人出来宣布什么“文学的死亡”、“小说的死亡”、“现实主义的终结”等等。英国批评家弗兰克·克尔莫德(Frank Kermode)对于人们追求终结做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他认为:人以外的全部客观存在(时间和空间),是无始无终的一片浑沌,全然无规律可寻。在这样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上,人们……只好仰仗形形式式不断变化的虚构,以获得对外部世界和对生活的理解。虽然客观存在既无起始、又无终结,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但是,人总要人为地裁定一个起始、中间和终结,总要发挥自己的想象,设法编出一个首尾相连的格局,为生活赋予一定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p.24,参见《20世纪美国文论》第142—143页)。我想这段话对于人们追求终结,产生终结意识的原因,做了很有启迪的解释。
有终结必然有起始,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则可以说是人们追求起始,富有起始意识的一种表现。尽管亨廷顿把包括福山在内的种种终结理论称为“结束主义”(endism),但实际上历史并未结束。即令福山本人在其文章最后还表露出一种“眷恋”、“伤感”的怀旧怀疑。他无限感慨地说:“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时刻。争取承认的斗争,为了一个纯粹抽象的目标而甘愿献出生命的精神。要求勇敢无畏和想象力的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理想主义等将代之以经济的算计、没完没了的给技术问题寻找解答、对生态环境的关心以及如何满足消费者要求的考虑等等。”他还说在后历史时期将没有艺术和哲学。他思想上十分矛盾,一方面承认历史的终结不可避免,但又十分留恋1945年以来在欧洲、北美以及亚洲所创造的文化。他最后说:“也许在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历史的终结的厌倦会使历史重新开始。”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出现了新的格局,许多学者都在努力寻找所谓“范式”(paradigm)或理论模型来描绘世界地图,新的世界矛盾以及冲突的根源和性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提出的众多范式之一。对于这篇据说被称为1993年度国际政治领域内最有影响的文章,引起的反响似乎超过福山一文,评论众多,我国已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我也必须坦率地承认我没有能力对此文作出全面的评述,没有那个“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宽大的历史视野”,在此只想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发表一点议论。
亨廷顿强调文明或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让人们也不禁想到了新老历史主义之间的一个区别。早先的历史主义强调文化的统一的作用,即使在一个允许多种文化存在的境域里,历史批评家会最终把不同的精神(Geist)消解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文明或一个种族的单一的精神;或者用更实际的、实证的历史方法,把它们消解为在范围上较狭窄,但仍为一致的政治或社会的事件、行动或利益集团等;在文学领域里,就成为一个时期的统一的或主导的流派或风格。按美国批评家萨克温·伯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的说法,这种倾向在美国文化历史学者中尤为突出,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长期战略,即把开展多种解释作为吸收或同化不同意见的手段。与老历史主义相对比,新历史主义最感兴趣的则是不同种类的话语相互间如何交叉、矛盾、颠覆、取消和改变(Don E.Wayne,Encyclopedia of Lit.& Criticism,p.795)。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时期不是统一的实体。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历史”,有的只是许多不连贯的、矛盾的“历史”。所谓和谐一致的文化只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宣扬和强加在历史身上的一个神话而已。亨廷顿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
另外,亨廷顿在研究文明史和文化冲突时,正如福山在研究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演变时一样,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或“欧美中心论”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等一些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所表现的倾向是十分相同的。亨廷顿不仅把从17世纪开始到冷战结束为止的现代世界文明史归结为“主要是西方文明的冲突”,是“西方内战”,而且在观察与预测当前和未来世界的冲突时,他断言冲突的中心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有人尖锐地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反映,该理论并不是从学术角度考察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着意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上,进而为西方国家出谋划策(见徐国琦:《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3页)。无怪乎,他被人们叫做“学政复合体成员”(academic-political complex)。
1996年冬,也就是《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两年以后,文章引起的轰动效应尘埃徐降,亨廷顿写了题为《西方文明:独特,而不普世》(The West:Unique,Not Univesal,载美国《外交》季刊,1996年11/12号)一文,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质疑作了反批评与析疑,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做了必要的补充和调度。他再次强调世界并非朝向西化的方向发展,指出那种把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认为非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可能照抄西方。他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帝国主义是西方文化普遍适用论的必然结果”;叹息“西方已不再具有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社会所需要的那种经济上的和人口方面的活力”。为此,这位美国的“学政复合体成员”给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开了一贴“回春灵药”,要求西方加强团结,保持活力,促进凝聚力。
显然,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悖论,一方面他承认文明的多元化,惊骇他所谓的非西方文明的复兴和发展,似乎不得不收敛起西方中心论;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西方文化影响的削弱,出谋划策,竭力维护西方对世界的控制权,为可口可乐殖民化理论与现代化论辩护,为西方中心主义招魂。
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当前社会上正在开展的清除殖民文化心理的讨论。有的地方已经付诸行动了。譬如,有一些城市已清理了一批明显带有殖民和封建意识的商店招牌和广告等。对于外国文学工作者来说,加强对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在更深的层次上清理殖民文化心理是义不容辞的。虽然福山和亨廷顿的文章在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文学的范围,但是许多美国文学选读本早已把文学的典律扩大了,将历史、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些经典著作囊括进去,诸如杰弗逊的《独立宣言》、林肯的《就职演说》,以及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等。因此,用文论这个“武器”来评论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政论文章或许并非是一种无益的尝试。
标签:新历史主义论文; 亨廷顿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终结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弗朗西斯·福山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塞缪尔·亨廷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