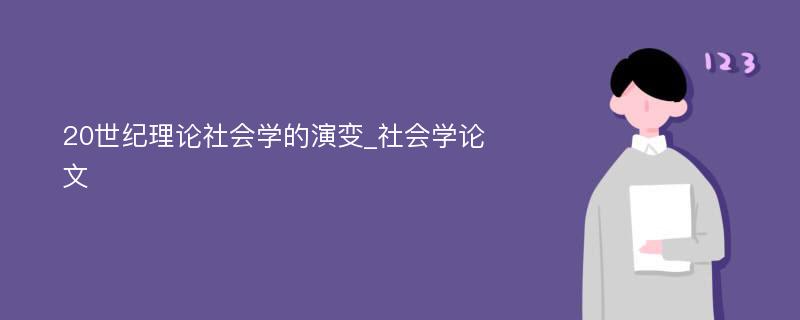
二十世纪理论社会学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观点的出发点是:当代能决定社会学命运的两次“巨大”的危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尚未引起重视。危机向理论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第一次危机早在上世纪末就已开始,在本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第二次危机的高潮形成于60至70年代,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了10年。
如果从一般观点来分析,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危机,其深刻内容都在于:暴露出“社会学唯实论”和“社会学唯名论”相互关系中根本意义上的二律背反。它们共存于以独特的“妥协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学理论稳定化的时期。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这种妥协以唯名论思潮占上峰为标志,贯穿其间,而在康德和马克思时代则相反,它的标志是唯实论思潮明显占优势,一直到临近上世纪末,唯名论才有所加强。人们追求唯实主义程度的加深,导致两者方法论目标相互间的平衡被破坏,而即便这种情况没有,平衡也并非稳定。
两次危机不单单是所持续时间相吻合,而且与某种世界观危机有着“选择性相似”之处。世界观危机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以60年代“反文化”形式反复表现。这两次所指的情况已不是社会学里某种“科学性”概念上的危机,而是关于对世界理解的危机。在世界观危机第一次“爆发”的时代,它的临床病症和代表思想,一是尼采哲学和他的“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观”;二是已聚集起力量的、雅斯贝尔斯称之为当代三种“反理性”思想之一的种族主义。在这种具有原始意义上极右色彩的危机进入尾声时,又产生出了极左思潮,这正是危机意识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年轻的卢卡奇和追随他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把种族主义“反理性”思想与另两种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正是它们和种族主义一起组成雅斯贝尔斯的三段式)相对立。尽管它在第一次“世界观危机”的氛围中产生,但要起推波助澜的决定性作用还太早,要到第二次危机期间才行。此时,新马克思主义的队列中不仅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还有左派存在主义者,其中包括萨特,他被以存在主义为方向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梅洛—庞蒂称之为“极端布尔什维克”,他自己也这样自称。法兰克福派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在极其矛盾的相互作用下,其组合已经进入定型阶段。这种组合,除了可用“社会学激进主义”来定义外,别无选择。这种激进主义从一开始就表露出要把社会学提高到哲理高度的倾向,由此确定了第二次全面危机的理论方法学内容。
第二次社会学理论堪称总的或全面的巨大危机,很大程度要比第一次大得多(因为无法指出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在这方面早就落后的美国,他们对社会学中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在进步过程中的分解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还认为基础是稳固的)。如此规模,注定使这一学术领域“稳定意识”的前景黯淡。
从19世纪下半叶起,社会科学分为以稳定和危机为内容的两派,它们相互对立,对立程度到了从一方面看符合科学,而从另一方面看则不符合科学的地步。再说,处于发展初期的新马克思主义本身拒绝谋求“资产阶级”的学术地位,把自己看作以揭露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其中社会学组成部分为宗旨的“批判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不管怎么说,它们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内,从同一枝干上长出对社会认识的两个分枝,它们都以符合“绝对真实性”自居,相互对立。只是在理论社会学第二次共同危机到来期间,当用极左社会学武装起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还在为自己争得社会学一席之地时,它和经典社会理论已是平起平坐了。顺便提一下,由此证明,经典社会学发生重大变化已是在70年代末了。
应该指出,当我们谈及理论社会学时,如不考虑从深层次哲学世界观出发,用社会学方法区分产生分裂和危机的根源,我们就会一无所知。甚至当社会学家,那些认真保守自己出身“家世秘密”或按弗洛伊德说法不肯去揭“祖上疮疤”的理论家无所顾忌时,也不能加以忽略。共同世界观作为先决条件的逻辑奠定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如果它的确是理论,而非相互对立主张的罗列),这不取决于我们记住或忘记它们事实上存在着的根源。
在任何情况下,“危机意识”的内部根源与新黑格尔主义有关。这一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由20世纪社会学史学家所指出的新马克思主义宏大的反实证主义特点。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只不过是用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物主义的言词和各种“自然主义”的复旧来加以掩饰,其实质仍然还是包括在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之中。这种唯心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合题的尝试。这一“秘密”说明了法兰克福学派反实证主义的内在联系。法兰克福学派已发展到了置任何事实以及他们革命主义于不顾的地步。如果在黑格尔(和新黑格尔)精神中把任何客体化和异化视为相同,而异化又被视为“资产阶级”现象,则宏大的反实证主义将会提出这一要求:与这一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世界分手。
理论社会学的各种思潮、派别、趋势的相互对抗,我们习以为常。如果我们把“唯名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意向的对立也归结到所有司空见惯的分裂和分歧中去,则完全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集中”和“合并”都不能不引起(正如20世纪所发生的那样)社会学理论共同危机的效果,而且每一次的危机在社会学家团体范围内都引发要去克服它的意愿。这种危机不能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决定着理论社会学的命运,直到这种命运掌握在致力于社会学理论稳定化的学者们自己手里为止,而最主要的是能够给稳定事业作出必要贡献的人。
以上便是本世纪理论社会学进化的动态过程。该动态还由另一个20世纪理论社会学很有特点的发展现象所决定。它是指各种社会学理论,确切地说,由这类理论的“复兴”所决定。这类“复兴”的共同基础,如果指“危机意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诸如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的“复兴”,第二次危机则显得格外深刻、极端和有害。因此,在第一次危机时(特别是在产生社会学稳定化意向之前的背景下)所表现出的破坏性观点到了第二次危机时,开始显露建设性的一面,大有某种类似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展。
在本世纪临近结束之际,历史理论研究正成为理论社会学的发展形式。我们有足够的理论论证一种新的综合,即历史和普通社会学的综合。
杨伟民摘自俄《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