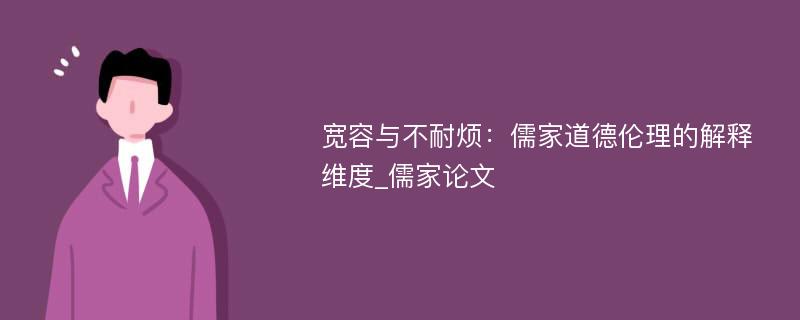
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德性论文,伦理论文,不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60-06
鲜见以忍或不忍作为对象的专题论文。把它们作为哲学范畴,从一般西学的立场看更无可能。即使是中国传统的德性伦理学,也更乐于谈论仁、智、勇之类范畴。忍与不忍与“惑”之类现象一样,若隐若现,难以界定,而且还不能简单加以推崇或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可有可无。以人格完善为论学宗旨的儒家,早就触及这一问题。孔子面对季氏违礼,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经典表达;孟子则更是把“不忍人之心”作为人性的根本予以褒扬。因此,探究这一问题的内在意义,对理解儒家人格修养的理念、深化儒家德性伦理的研究,有着颇为独特的价值。
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现象,即人对自身心理冲动的克制。这种冲动可能只是萌生于内心的欲望或意愿,也可能是开始着手而未曾完成的行动,所以,忍有否定性的意向。
不忍不是忍不住。在实际使用中,两者并非是逻辑层次上的对立。从意向上讲,忍与不忍可以都指向否定,但忍着眼于克制自身,不忍则是因不能接受而企图阻止某些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外部情况,包括可能因自己原初冲动所导致的情况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情况。就前者而言,忍与不忍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不忍于自己的作为所导致的后果,就得克服或中止自己原先的冲动,那就是要忍。而如果不忍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则这种要求制止的冲动就与忍无关。当然,涉及情感问题的任何抽象说法,都需要结合具体的经验予以分析。
先说忍。由于忍涉及欲望或意愿,而意欲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只能在特定的分类上分析。大致可以把忍分为四个方面: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之忍与忍人之忍。
人类有无限多的意欲,而最基本的是生理需要,所谓“食色性也”。较高端的,则有权力与名誉的追求。物有尽而欲无穷,为了共同生存或者均衡发展,社会文明发展出各种有形无形的规则,针对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方面进行各种意欲的限制。要遵守这些规则,就要不同程度作忍的功夫。这种忍可能是因害怕惩罚而作的选择,更包括从内心认可这些规则后对自己的克制,后者就是修养之忍。依孔子之见,一个人通过“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能成仁。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要靠长年累月的修身功夫。一旦功夫到家,便“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望与克制的紧张也就消解了。
有些忍并非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意欲,而是在实力不足或计划未周的时候,为更有效的行为或更长远的利益而进行的临时妥协。这往往需要装,装傻甚至装孙子。被灭国的勾践要卧薪尝胆,未得势的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就是典型的例子。楚汉相争中,刘邦就比项羽更善忍,所以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故孔子会讥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这种忍是手段而非目标,因此,其意义取决于目标的价值:为了高尚的理想,忍是智慧的表现;若怀有卑劣的欲望,那就是使阴招。上上若水,大智若愚,中国古代的道家、兵家、纵横家皆精通此道。
还有一种是被欺凌的弱者面对困境无可奈何的忍。《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父女,面对恶霸的横暴忍气吞声。《苏菲的选择》中,母亲被迫选择让一个孩子生存,意味着变相让另一个孩子送死,无反抗的余地。这种忍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被迫的承受。
所谓忍人之忍,则是已脱离了人性可接受限度的忍。鲁迅曾经描写过一种“看客”。那些人面对同胞受辱被害的场面,无动于衷,如同在看今日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这种对他人受难的容忍,用孟子的话就叫“忍人”,其已失去为同类甚至同胞解脱痛苦的冲动,是麻木不仁、心性不健全的表现。在文明社会中,正常人即使是对虐杀动物也不能熟视无睹。忍人的程度深浅不一,最严重的不只是放任无辜者受难,而是亲自加害于人。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比赛杀人的恶魔,以残害他人为业甚至从中找乐,这是残忍,此为有正义感、有血性的人所不能容忍。
忍的四个类型也可以被看作四个层次。类型可以是并列的,层次则有递进的关系。从自觉的程度看,修养之忍层次最高,因为它追求的是原则;手段之忍随条件或需要的不同而变化,故次之;无奈之忍本身就是无奈的,是基于自保的本能;而忍人之忍则是正常心性的丧失。换一个角度,从价值的角度看,修养之忍最可取,是美德的表现;手段之忍则由其服务的目标所决定,是否可取是有条件的;无奈之忍,可以被同情,但无法推崇;忍人则只有负面价值,是儒家所强烈谴责的态度与行为。所以,儒家不仅提倡节制自己私欲的忍,同时还呼唤与“忍人”对立的不忍,或叫不忍人之心。其主要论述者是孟子。
孔子学说以“仁”为宗旨。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事业,其心性说为先秦儒家仁学提供了形而上基础,而“不忍”之说则是孟子整个心性论的核心。《孟子》七篇,涉及“不忍”主要有两处,其说理的方式均从具体例子入手:一是以羊易牛,一是见孺子将入于井。
第一处是答齐宣王问王政。孟子为了鼓励齐宣王行王政,通过对齐宣王一个普通行为的分析,来唤起他的良知,强化其信心:
(齐宣王)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齐宣王因不忍心见牛临死前恐惧的样子,决定以羊易牛当牺牲,放牛一条生路。凡是观看过宰牛的人,见其临刑前暗淡的眼神、发抖的腿以及绝望的悲鸣,很容易理解这种“不忍”之情。但是,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人命被视如草芥,又有多少人真能对牛的生命动不忍之情?对战国时代离开暴力就几乎保不住权力的君王而言,有这样心肠,尤为可贵。孟子从中看到人性的光辉:“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忍动物主受害,即是把它当作同类,对其生死感同身受。对动物如此,对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由此启发齐宣王通过反思,把不忍之心从对动物推至对人,那就是行仁术。
第二例,则是被反复引证的经典论断: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这里,“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已把对动物的不忍提到对人的不忍上来,无疑更有感染力。任何正常人意识到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濒危时,担心、难过的心情是自然而发的。① 孟子的这番论说包括两层很重要的意义:其一,把“不忍人之心”即对他人受难的不忍之情,概括为恻隐之心和“仁之端”,即人性善中仁、义、礼、智四德目之首。这样,其“不忍”之说就成为性善论的中心。人之所以有道德或人之所以为人,从根本上讲,就是内心深处有对他人(甚至他物)苦难的同情。其二,孟子在对人性的信任与维护的基础之上推出的儒家政治理想——仁政(孔子叫德治),其焦点正是对弱者的同情,对孤苦无告者命运的担心。这是极其伟大的政治信条和社会理想。
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正是对孟子这一相关思想的继承与发挥。王阳明的《大学问》如是说: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唯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悌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都也,是故谓之“明德”。②
阳明的发挥思路清晰且成系统,其中不乏对宋儒观点的综合,但其“不忍之心”的思想渊源应上溯至孟子是无疑的。摘引上述从孟子到阳明的若干语录,不是要作相关的思想史叙述,而是要凸显这一问题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的关键地位。③
联系第一节的分类,不忍的对立面便是忍人之忍(或残忍的忍)。而不忍与修养之忍,则不但不对立,而且相辅相成。修养之忍,是对自己欲望的克制,是自律;不忍则是对他人受难的同情,是爱人。一个人知道自己欲望的界限,便是懂得忍,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关心、体恤他人的存在。他人和他物都不是异己的对象,而是与我心气相通、血脉相连的同类。故忍己与不忍人,本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但忍己还只是独善其身,不忍人则能兼济天下。
忍与不忍的情感培养,对人格形成关系很大。从伦理学角度来研究,它不属规范伦理学,而属德性伦理的范畴。但在德性伦理中,它与评价性的善恶范畴不一样,而是有点类似于好恶或忌妒、羞耻(或羡慕)等心理状态或意识活动。正是这些心理活动直接导致了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才有善恶是非的评价。所谓人格修养,主要体现为这个层次上的自我修炼,也就是宋明儒者常说的功夫。功夫是一个实践而非论说的问题:知道一个道理,与将这个道理内化为信念(甚至是直觉反应)不是一回事。只有到了“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境地,才是真功夫。然而,修身或下工夫有一个方向问题,即需要是非优劣的评估,因而又离不开义理的帮助,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所以,知行合一成为儒门的一项宗旨。
从孟子到王阳明,都以人性善为修养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修养就没有基础或方向。但性善只是一个善端,即苗头而已,故需要培养,包括祛除后天所蒙蔽上的不良因素。由于人性本善,故大多数人都有感受和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但由于自觉不够,意志薄弱,导致常人的心思不能持续向善,行为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与在特殊情况下不一样、人前人后不一样、对关系亲疏不同的人不一样,因此需要修身,变化气质,使之一致。而关于忍与不忍的训练,则是最基本的功夫之一。
先说忍,内容大致有两方面。一类是有社会规范的限制。你不能越轨行事,而是要明白界线的存在,要克制住犯规的欲望。不过,害怕被惩罚的忍,有点像无奈之忍,不是自觉的,因此它不是修身的目的所在。孔子要求以礼为行为的规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勿”就是要求你要忍。季氏忍不住,“八佾舞于庭”,孔子就忍无可忍。这类的自我克制,从大范围说,是戒色、戒利、戒权、戒名。戒就要忍。另一类不是公共规范,而是君子(即追求人格高尚者)的自我要求。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非规范的自我警惕:“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天天自我提示,天天做功课,是修身之忍,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违”就是忍不住,无违需要心中时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他老人家赞扬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就是因为他经得起诱惑。到这种情形,已经不必忍,对私心杂念有了自动屏蔽能力,内心的紧张消除了,便能如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知耻近乎勇”,则表明要克制自己不体面的言行甚至念头,也是需要勇气的。每个人境遇不一样,欲望不一样,故忍的内容与程度也不一样。很多界限是模糊的,靠的是在实践中调节。
相对而言,不忍的内容较为明了。在孟子那里,不忍既对物,也对人,而且重点是对人。宋儒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试图把对两者的不忍统一起来。依照王阳明,不忍从待人到接物是个分层次推演的过程。不忍以爱为前提。在儒家实践中,它是从点拨、培养亲子之爱开始的。父(母)慈子(女)孝,这是所有人类感情中最自然的。不过,两者相较,后者更被重视,因为在经验中,父母养育子女比子女赡养父母更自觉。对孝的培养是一个过程。对此儒门经验丰富,《论语》中有大量孔子答弟子问孝的语录。有讲大纲的,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公冶长》)也有些堪称细致入微:“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公冶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由此可见,孔子论孝,关心的不只是行为,更有情感。“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这种忧是情感的牵动。以亲子之爱为基础,则“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从孝到悌,再到爱众,合乎推己及人的心理逻辑,这样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另一方面,儒家还爱屋及乌,要把爱扩展到天地万物。早期儒家这方面的意识并不是很自觉,甚至比不上庄子,但他们对生命的死亡有本能的悲悯,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以羊易牛的所谓仁术也与之相类似。以羊易牛,目的不在动物,而是启发对人的同情心。至少从张载《西铭》的所谓“民胞物与”的说法开始,这一思路越来越清晰且自觉。这也就是所谓亲亲、仁民、爱物。从此,爱物本身就是目的,同时,爱物反过来又更促进对人的爱。所以,讲孝道只是爱的基础,修养的功夫还得扩展到物上。宋明儒者有许多观花树、赏鱼虫、叹风月的趣事,都是事关对宇宙人生态度的大问题。程颐《养鱼记》说:
鱼乎!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于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于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尔于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心将奈何?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④
悲悯之情,跃然纸上。可见,在儒家那里,玩物未必丧志,它也可以是修养的功夫。
功夫的问题极为复杂,我们不仅不可能把宋明儒者修身的经验全部复原出来,即使能够,也未必能应付每个具体的人所面对的具体的道德境遇。同时,功夫与学问不同,行与知有别。学问或知通常是把握规则性或原则性内容,而行则千差万别。道德践履中总有许多矛盾或困惑的体验。对有些问题,前贤也作了思考,如人与物的生存在根本上有冲突时,应当怎么办。⑤ 还有更多的问题每个人得自己掂量。例如,是不是在利益面前都得忍让?对那些利用别人的忍让而获取非分之利的人,这种忍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一个事事以忍为先的人,固然是对人无伤害的人,但是否会形成懦弱的性格,从而也是不能承担公共责任的人?此外,如果对弱者、失利者都怀着不忍之心而施以援手,会不会是不智的表现,成为传统所说的“妇人之仁”?有时不但被骗,甚至会被反咬一口,如《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情形。还有,一个处处以忍为处世原则的人,会不会很容易从忍己转成忍人?一个更尖锐的例子是,面对安乐死的选择,对立意见的双方都以不忍为理由:支持者不忍垂危者备受折磨;反对者不忍一个生命被放弃。在理论不清楚或原则无用的时候,只有实践者自己选择。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取向,而这种性格特征又可能正是人格发展的结果,包括自觉的修养或环境的熏陶。
德性伦理中的任何修养范畴,在实践中都不是孤立起作用的。儒家讲君子应有三达德:仁、智、勇,可见不同德性有互相补充。套用孟子的四端说,不忍是仁,忍是义。如果羞恶之心是义之端,那么羞就是忍己,恶则是不容许其他人忍人,是正义感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勇,则即使有不忍之心,也没有匡时济世的豪情,不敢救民于倒悬之中。智也是如此:对恶人的容忍是不智,只会暴虎冯河;但是不懂忍,不计代价也是不智。离开智,则决疑解惑,排忧解难都办不到,但如果只有智和勇而没有仁,那就可能会大奸大恶。因此,修养是不同德性的均衡发展。理论只是观念的指引,功夫才是把美德内化为人格的途径。德性伦理不能离开修身行为。
忍与不忍在道德修养上有重要意义。不论及实践功夫,德性伦理学就会苍白无力。一种有生命力的观念,在从传统转化的过程中,总会伴随新的经验而被充实或调节。仁爱的观念就可以延伸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孟子把“不忍人之心”作为恻隐之心的表现,并认为恻隐之心为仁之端。仁是孔子的思想贡献,虽然仁的含义复杂,界定也并非很精确,但“仁者爱人”则无疑标示出其非常重要的内涵。《论语·乡党》有一个可供回味的情节:“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在孔子的心目中,人比物的命运更需要关切。《论语》用孔子“不问马”作为对比加以强调,潜台词是孔子的这种态度不同寻常。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是什么人,物是什么物。在春秋时代,马不是等闲之物。“千乘之国”与“万乘之国”的说法,意味着马是计算国家实力的基本尺度之一。而马厩失火时可能危及的人,不是马夫就是其他奴仆,多半不是马的主人。这可证明孔子首先关切的,就是地位卑微的人的命运,而非贵族的财产。不管赵纪彬如何从字源上证明人与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⑥,但在孔子时代,“人”泛指普通人则是无疑的。因此,可以相信孔子的“爱人”是不分地位贵贱的。在关心人是否被伤的意义上,这种爱与孟子的“不忍人”是一致的。当然,这也显示了孔子尚未有后来宋明儒家所强调的那种泽及万物的爱。
现在的问题是,不忍人或仁,是否是爱的全部?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样的爱?前一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可通过对比来分析:一个人爱热恋中的情人,宗教共同体爱他们的精神导师,民众爱民族英雄或爱政治领袖,甚至“粉丝”爱偶像等等,都并非是基于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反之,看见一个陌生路人忍饥挨饿,或看见动物受伤挣扎,如果你有怜悯之情,那也并非是热爱此人或此动物。如果他或它不受难的话,你可能对之毫无兴趣。回到前面以羊易牛的例子。齐宣王说:“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他既非爱财物,更非特爱这头牛。退一步说,即使在仁民爱物意义上讲爱物,也与一般爱宠物不一样。程子养鱼是因为“心之戚戚者”;庄子爱鱼,是见“儵鱼出游从容”,从中感受到“鱼之乐也”。至少,我们可以把爱分为热爱(或喜爱)与怜爱两类(当然这不意味着爱只能分成这两类)。热爱是渴望实现某种价值,是价值的拥有或扩大。怜爱则不然,它是对固有价值的珍惜、维护,是不忍心其受损害。热爱与快乐相联系,而怜爱则与悲情相伴随。西方人讲的爱欲或者浪漫主义的爱,大致都可归入热爱的范畴;而儒家褒扬的不忍人之心或佛教讲究的慈悲为怀,当然都是体现为怜爱之情。这种爱不必热烈,更不会狂热,它可以是冷静的,却有着更为动人的道德力量。
不过,儒家的不忍人之心更多地是对外人或陌生人的态度,并不能概括为亲子之爱。亲子之爱是天伦之乐,显然与快乐相联系,因而同上述的热爱相一致。而儒家讲孝则不仅诉诸自然感情,同时还把它作为道德义务来强调。在这种强调中,热爱与怜爱又是可以转化的。在亲情中,热情可以转化为温情而持续下去。在热爱的范畴中,儒家的亲情同现代人讲求的爱情也很不一样,因为亲情所依赖的关系是天然的,天伦之乐意味着它已与血缘相关联,它不是爱者自己创造的。而男女之恋,除了《诗经》上少量的诗句外,儒家很少正面肯定。即使是夫妇之情,基本上也是亲情,而非罗曼蒂克的激情,因为这种关系是由婚姻而非爱恋造成的。爱欲—激情—创造,这种浪漫主义的生命理想,并不是儒家的追求。由亲亲、仁民而爱物的思想路径,是通过点化自然情感,导出道德责任,从而拓展生命情怀。儒家把责任放在每个人身上,与其对人的命运的忧虑有深刻的关联。
儒家对不忍的诉求,凸显了其在整个道德心理中的基础位置。与不忍总体上具有正面价值不一样,忍本是中性的概念,因为该忍与不该忍,都需要另外的标准来决定。但是,由于儒家人格修养的目标是成君子,而君子则以谦让为主要的性格特征,因此忍成为儒家经常性的要求。讨论这两者的道德意义,必须区分目标与手段的不同:不忍是人性光辉的体现、修身的根本;忍则依情形而论,有时候忍不住有所作为,恰恰可能是不忍的某种情景的出现。
注释:
①关于恻隐之心的道德价值的讨论,参见何怀宏:《良心论》,第1章,第56—10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②《王阳明全集》(下),第9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有改动。
③参见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④《二程集》(上),第5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⑤陈立胜在论王阳明时,对宋儒关于“恶与牺牲结构”的议论非常有意思。
⑥参见赵纪彬:《释人民》,见《论语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