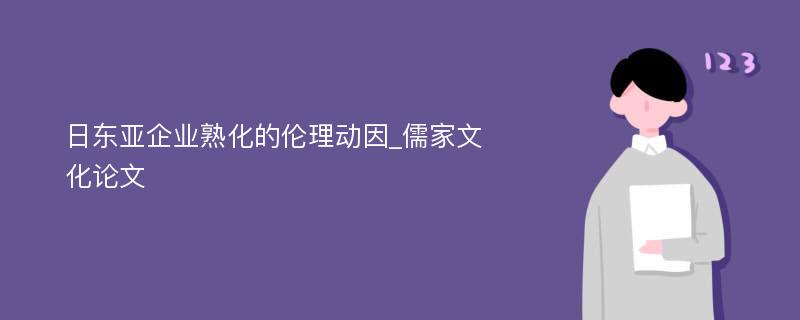
日本、东亚企业家族化的伦理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动因论文,日本论文,伦理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东亚企业家族化的伦理动因,是当前伦理学界、经济学界等多学科跨领域关心、讨论“儒家伦理与日本、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拟从日本、东亚企业家族化的伦理动因及辨析谈点自己肤浅的看法。
一、企业家族化的伦理动因
日本、东亚企业的家族化,是毋庸置疑的。日本、东亚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家族化?这涉及社会动因说。依据社会动因说的看法:“社会动因”是一个系统,分为不同的层次。有起主要作用的;有起次要作用的。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伦理道德诸内容。从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角度探讨社会动因,始于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著名的新教伦理观点,构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方模式的理论体系。以后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有的人选取了像马克斯·韦伯一样从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角度去探讨社会经济动因,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伦理动因说”。这一方法论原则,同样适合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基础的企业的伦理动因认识上。
在探讨“日本、东亚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时,由于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对作为整体的日本、东亚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之描述,也同样适合作为其部分的“企业家族化的伦理动因”之描述。日本、东亚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是什么?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还是有的人提出的“新儒家文化”、“儒家理想”呢?
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而不是“新儒家伦理”。其大意:新教伦理使人们意识到人生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又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为了取得上帝的恩典,为上帝争光,贫穷并不能为善行增添光彩,它只能是对上帝荣誉的贬损。以此为出发点,新教伦理把入世苦行和积极劳作看作是神的召唤和教徒们的天职,认为教徒们如果不去抓住自我完善的机会就会白白浪费上帝所赐予的礼物,由此“新教伦理”使人们在一种天职的观念中诚勉地劳作和禁欲节俭,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伦理。而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有别的儒家伦理,则是把现实视为安身立命之地,既没有超越或救赎的位格神,也不讲彼世的超验领地,宗教意识淡薄,形而上学的观念极少。不像新教伦理那样以理性态度改变世俗、驾驭自然,不能引发出改变世俗的社会力量,而是用一套伦理规范去维系既定社会的和谐秩序,崇尚的是适应现实社会的价值取向,这必然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入世信念,从而妨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因此,韦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伦理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东方印度宗教、中国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东方的儒家伦理却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1]
其他学者认为,儒家伦理是日本、东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新教伦理”。美国学者卡恩是最早用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之迷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认为,日本等“四小龙”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大多数成员皆受儒家传统的熏陶而具有一些共同伦理。“新儒家文化”在面临着公平和组织效率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胜过“新教伦理”。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格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布:韦伯的命题错了。尤其是英国学者雷丁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海外华人企业家族化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为对象,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与研究方法,得出了令学界瞩目的看法——家族企业“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产物”;“儒家理想,尤其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的儒家信念至今还深深地扎根于绝大部分海外华人的心中,用‘儒教’这一单词去表达主宰海外华人大部分社会行为的价值观是比较恰当的”。[2]从认识的方法论看,雷丁用实证方法得出的企业家族化与儒家家族主义关系的结论,尽管对象是旅居东亚的海外华人企业,但既然日本、东亚同处儒家文化圈,在企业家族化与儒家家族主义关系这一点上应该是相通的。可见,以卡恩、彼得·伯格和雷丁为代表的外国学者,在“企业家族化与儒家家族主义”或“日本、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伦理”上,对“企业家族化的伦理动因”或“东亚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
孰优孰劣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首先,韦伯的基本命题。韦伯提出了“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而东方的儒家伦理却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命题。就其中的“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命题而言,是韦伯从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角度研究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洞察了从16至18世纪欧洲的历史状况及欧洲人在那个时期的心理历程而提出的,是实证的理论概括而不是所谓的“文化设计”;就其中“东方的儒家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而言,是韦伯在1864—1920年生活期间,以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有眼光”,探讨了东方印度的宗教、中国的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而提出的。由于缺乏东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实证(日本、东亚经济发展是本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事),他关于日本、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伦理关系的论断,只能是一种所谓的“文化设计”,并不适合日本、东亚经济发展的实际。
其次,卡恩等的看法。卡恩、彼得·伯格和雷丁等提出了儒家伦理是日本东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究竟是“根本原因”,还是“一般原因”或“伦理动因”值得商榷。但至少他们看到了儒家伦理与日本、东亚经济发展有关,是助力而不是阻力。并且从他们撰文(书)阐明看,卡恩是1979年,雷丁是1990年,彼得·伯格是1993年,均是在70年代末日本经济腾飞、东亚经济崛起之后对日本、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伦理关系实证基础上而作的理论升华、概括,不是所谓的“文化设计”。如果把这种探讨拿来与韦伯的基本命题相比较,更有其合理性。
因此,从日本、东亚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之争不难看到,日本、东亚企业家族化存在伦理动因,并且这个伦理动因是儒家文化而不是“新教伦理”。
二、企业家族化伦理动因之辨析
在对企业家族化伦理动因探讨时,在分析了“企业家族化伦理的动因”之后,还受到“内部因素制约”和“外部环境影响”之困绕。从“内部因素制约”看,必然涉及本文题目中所包含的“动因”、“伦理动因”和“企业家族化”诸内容,本文在前部分作了探讨。然而这个探讨是基于“企业家族化伦理动因”之认识上,并未对“伦理道德观念是企业家族化的动因吗”?“对企业家族化给予影响的儒家文化,是‘传统型’还是经过‘转型的’”?“企业家族化是日本、东亚经营所采取的普遍形式,而普遍形式能否认定是最好的形式是否涉及超越”?“以王安为代表的华人家族企业的式微或破产,是企业家族化所导制的必然结果,还是另外的原因”……等等。面对这些本文题目所包含的内容且是应当给予说明的,如不能给予适当之回答,反过来势必又影响对前部分所作的探讨。这一任务的完成只好放在“二”部分加以说明。从“外部环境影响”看,“本世纪90年代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能否归结为伦理动因,而对儒家文化给予经济或企业的影响持否定态度”?“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人的个性、创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家族化有无超越”……等等。这是当前认识日本、东亚经济发展,企业活力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内部因素制约”还是“外部因素影响”,都表明对企业家族化伦理动因辨析之必要。
1.“动因”与“伦理动因”
企业家族化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普选基础上的代议民主制再加上儒教伦理温情‘三合一’的结果”。[3]即以制度因素作用为主、传统文化因素作用为辅,且两者又是互动的。从伦理动因探讨日本、东亚经济发展或从伦理动因探讨企业家族化,仅涉及动因关系的文化层面,而未涉及经济、政治制度层面。因此象马克斯·韦伯把“新教伦理”归结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因,象卡恩、彼得·伯格和雷丁把儒家伦理观念归结为日本、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因,都夸大了道德的社会作用而忽略了对决定道德形成、发展的经济、政治制度的作用,因而是欠妥的。
2.成为企业家族化伦理动因的儒家文化,是传统型还是“转型”的
在以儒家文化为视角认识日本、东亚经济发展时,有时让人感到困惑。日本、东亚经济的发展,从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角度看儒家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企业家族化就是其典型。但是,同样隶属儒家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有的至今仍未经济崛起。尤其是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五·四”运动以前一直把它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最后的也是最顽固的堡垒,要通过提倡民主和科学给予批判。甚至在当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怎样看这两个问题?对于前者,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即使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也需要与所在地区或国家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并“组合”为能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的“文化转型”;对后者,涉及儒家文化本身体系的认识。在学术界,有人提出儒家文化有其内部结构,可以把儒家学说区分为孔孟之儒和汉代之儒。认为孔孟之儒是非政治化的,而汉代之儒则是政治化的。其中政治化的儒家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阻碍中国近代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的正是政治化的儒家文化。对日本、东亚经济发展起作用的是非政治化的儒家文化,它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当与所在地区或国家传统文化融合,依据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之需加以“改造”,使儒家文化焕发出青春即所谓“文化转型”,成为这些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这样的认识应该是有道理的,至少在方法论上给人以启迪。让人认识到:以后在探讨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之影响时,既要对内部结构加以分析,又要注意其在不同的时期所起的不同作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企业家族化的局限性
企业家族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或不足的一面。其中消极的一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封闭性。企业家族化,当以“集团意识”和“忠诚意识”形式出现时,对企业来说群体的价值趋于增大,对于企业成员来说能自觉地维护其和谐,因而整个群体构成一个封闭的集团,呈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特征。反映在企业的活动上易使企业对外部群体采取敌视或排斥态度。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不合作”态度显然是不利于企业自身的进步。
第二,压抑性。当企业家族化仍以“集团意识”和“忠诚意识”出现时,由于集团意识强调协调,个体的行为必须随大多数成员的行为方式。这样以来,那些特异而不随大流的个体往往视为“神经不健全”,“狂”和“不合群”而受到歧视。无疑,这样把“协调”极端化的结果会压抑个人创造性的发挥。因而在企业内部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是疲软的,即使是出类拔萃的个人,也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这恐怕可以用作解释日本企业为什么跳槽少,为什么在实行年功序列工资制强调纵向的上下关系时,可能出现“能力平等观”的原因。因此,企业家族化的现状向人们提出了对企业家族主义应持辩证的态度。对其积极因素应当发扬,对于其消极因素又应当克服。
4.怎样看待以王安公司为代表的华人家族企业的式微或破产
企业家族化的特征,除了有的学者提出的“集团意识”、“忠诚意识”、“参与意识”、“封闭性”和压抑性“三意识”、“二性”以外,在华人企业中还有“血缘亲情”。据有关资料介绍,正是由于按“血缘亲情”规则来经营导致了众多海外华人企业的失败,著名的王安电脑公司、印尼的谢建隆的阿斯特拉集团的破产就是典型的例子。对此,曾任台湾经建会主任的赵耀东明确指出:中国的家庭制度已变成发展工业一大障碍。[4]据此,能否推演出以王安公司为代表的华人家族企业的破产就意味着企业家族化的破产呢?如果我们用它来与日本企业家族化相比较,就会发现这样的推论是轻率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家族“血缘亲情”之企业经营模式与日本企业家族化之经营模式相比较,以往过多地注意到它们都是企业的家族化,都是同处儒家文化圈等相似之处,而不太注意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是以“孝”为核心,而日本传统的家族伦理则是以“忠”为核心。由于在这一认识层面上的疏忽,就不能认识到日本的家族企业在选择接任者时,首先考虑的是继承人的“发展家族势力,增加家族财富”的能力,而不是看重血缘关系。甚至未有姻亲关系,以“养子”的身份也能担任继承者。其前提仍是以“发展家族势力,增加财富”为选择之标准。
比如松下幸之助就是将公司交给其女婿,而不是儿子。这在中国家族企业之中,是很难想象的。又如王安电脑公司,因恪守传子不传女的传统观念而导致公司经营每况愈下最后倒闭。这种传子不传女的传统观念不止是王安公司。在台湾最大的家族企业中99%的总裁都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作接班者。可见,虽然中国与日本都是家族式企业经营,但两国的企业文化有许多不同之处。
5.亚洲金融风暴给亚洲经济、企业所造成的灾难性损失,能否归结为“伦理动因”
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的经济、企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有的人认为与其文化背景,即儒家文化不无关系。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决不是亚洲价值(即偏重于整体的价值取向,它是一个经济现象,因而其原因也必然是经济的,而不是文化的、哲学的。其内因在于东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过度投资导致信贷膨胀与泡沫经济;国内投资比例失调,结构不合理,造成呆帐死帐大量增加;银行过量投资于证券业抬高了资本市场价格,为投机者的炒卖提供了可乘之机;过早推行金融自由化,大量举借外债,短期债务过多,外资结构及流向不合理,而国家又未能及时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督管理体系及危机防范机制等。可见,亚洲金融危机与作为亚洲价值核心的儒家文化及企业家族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6.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家族化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社会发展以深刻影响。它需要有个性、有创造性的个体。而在以往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上,东西方各有优劣。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伦理动因的西方模式,在价值取向上重个体本位,强调个体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倡导从个体利益出发去开发、征服和驾驭自然。这正是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但个体本位虽然对建立充满活力的个体是有利和有效的,却容易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金钱万能;容易给“公平和组织效率”带来负面影响。以儒家文化为资本主义发展伦理动因的东方模式,在价值取向上重社会本位,强调社会和谐,个体去适应社会整体,倡导个体性服从社会整体性。这容易导致个体的主体性、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丧失。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
企业家族化在价值取向上属于“东方模式”。必然具有东方模式的优劣。对此,已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一点。雷丁在对华人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优缺点从“纵向合作、横向合作、控制、适应性”等四个参量上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家族企业既是高效的、又是失败的根源。[5]在日本企业也有类似的看法。“日本一些高层的经理们越来越感觉到,虽然社团精神、合作和谐的气氛历来倍受盛赞,但是企业管理人员缺乏冒险性、挑战性、开拓性、缺乏管理名星的头脑,想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能是纸上谈兵”。[6]
鉴于此,日本有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企业家族化可能使企业丧失原创力,职工失去开拓性,因而制定一些制度来弥补不足。比如禀议制或建议制,都不失为一种发挥职工主体性的好方法。又如丰田汽车公司通过教育的方式去调动每一位员工的干劲。而“这种‘干劲’,一是发掘独创力,二是养成积极进取精神,三是提高员工作为企业一员的自觉性”。[7]再如“本田”开发新产品的体制,是“采取广大职工和专业队伍相结合的方针。鼓励职工从事自由思考,甚至鼓励并支持他们从事异想天开的遐想和计划”。[8]
众多的海外华人企业也开始意识到企业家族化可能使企业丧失原创力,职工失去开拓性,因而也提出了一些对策以弥补不足。“以血缘+能力的规则取代单纯的血缘亲情规则;以家长式+咨询民主式的决策来代替家长主观武断式决策;在报酬支付中用能力绩效规则取代宗亲地位规则”等。[9]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人的个性、创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企业的家族化来说,的确存在着怎样解决企业发展的原创力问题,存在着企业家族化的超越。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怎样保持企业家族化的优点,进一步地克服其不足是值得重视的。
标签:儒家文化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家族企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