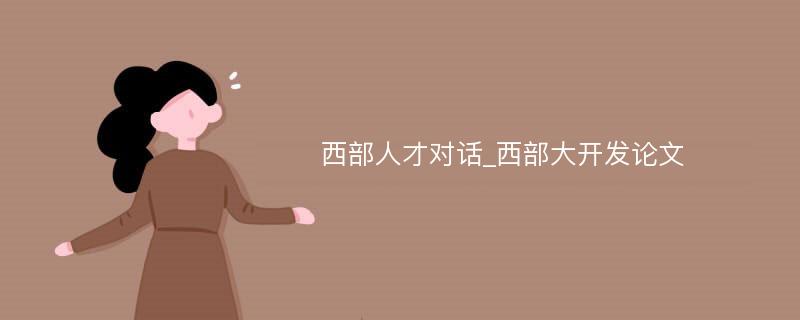
西部人才问题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乔根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乔:西部大开发需要多方面的投入,如政策方面的倾斜,资金、项目、科技的投入,人才的支持等等。在这各种要素中,你认为什么最重要?
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才。西部大开发,首先需要的是人才,人才工程是西部大开发中的首要工程。人才在经济发展中或在各方面的事务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五次赴江苏春兰考察,我问春兰集团的领导和普通职工:“春兰为什么能超常规发展,十年增长一百多倍?”大家一致回答是因为有陶建幸总经理这样的带头人。东部的发展是如此,西部大开发也是如此。
乔:西部大开发的人才工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邹:清朝诗人龚自珍有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西部大开发需要的人才应该是不拘一格,多种多样。人才工程的结构是多层次、多样化的。西部大开发需要资金和项目,谁能搞到资金和项目就是人才;西部大开发需要有好的思路、好的举措,谁能提出好思路、好举措就是人才;西部大开发需要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谁能搞好山川秀美谁就是人才;西部大开发需要形成和发展大量的企业,谁是优秀企业家谁就是人才;西部大开发需要开拓、高效、强有力的领导,谁是这样的领导,谁就是人才。总的来说,西部大开发最需要的人才主要分三个层次:一是专业型人才;二是领导型人才;三是战略企业家。
乔:据我了解,西部也并不缺少这些人才,而为什么西部经济总是搞不上去呢?
邹:关键在于这些人才能不能有效地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生力军,从而使人才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优势。为此,必须使才有所识,才有所用,才有所得。
乔:在五、六十年代,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工人放弃了较优越的生活条件,挺进大西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但是,近年来许多人,特别是土生土长的西部人却离开了西部,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局面。您怎样看待这种反差呢?
邹:过去人们是把自己的理想同社会价值的实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意识在增强,个人利益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们更多地追求个人价值,把社会价值孕育在个人价值之中,于是一些人才开始往收入高的地方、职位高的地方、生活条件优越的地方流动。这是人才流动的客观规律,无可厚非。除去东部沿海地区资本雄厚、机会多以外,主要是那里的收入高、待遇好。因此,西部目前必须提高人才的待遇水平。
乔:有很多籍贯或出生地是西部的,或曾在西部工作过的人,想回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并不一定是看重工资的高低和待遇的好坏。但常因为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最后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离开了。
邹:我看到一篇文章《西部儿子:我为什么不回家》(载2000 年3月27日《中国青年报》),是说一位非常关爱西部故乡的青年,几次回到西部故乡,想为家乡的发展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家乡的一些人并不怎么欢迎,而且人为地折腾和设置障碍,使想为家乡做的好事流产泡汤。这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产生了“我爱家乡,家乡并不需要我”的感受,再也无心回家乡,无心为家乡做好事了。
乔: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需要人才,但为什么却会出现上述相反的事例呢?
邹:从理论上和一般的常识来说,确实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需要人才。然而,现实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反而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排斥人才。所谓“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并不都是要逃避贫穷落后,不愿为西部经济发展做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当地人文环境的恶劣,不堪忍受对人才的排斥,不堪忍受抱负的失落和才华的空废,带着一腔遗憾、惆怅和怨气,不情愿地被迫“南飞”和“东流”的。比如说,你想干事,但不干事的让你干不成事,而且比你混得更好。比如你有一个很好的设想方案需经政府审批,但众多低效、扯皮的行政环节,使你的设想和方案石沉大海、成为泡影。这些都会使你热血变凉、变麻木。你误不起人生啊!
乔:那么,是不是说,在西部某些地方,故意要排斥、打击人才,故意要为西部经济发展制造障碍呢?
邹: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但极少。绝大部分并不是坏人坏心坏意干出来的,恰恰相反,不少是好人好心好意,或者说自觉不自觉地干出来的。由于种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长期催生出了一种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发展不太匹配、吻合的思想观念,这就是比较保守、比较守旧。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体制,从更深层次上看,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而西部地区的不少地方,在经济观、财富观、幸福观、人才观、竞争观、分配观、风险观等许多方面,是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宗法经济、封闭经济中孕育起来的,平均主义、红眼病、墨守成规、看不惯创新、害怕风险等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都比较严重,而且这不是个别人、个别单位、个别地方的现象,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群体性的文化氛围。这种群体性的文化氛围,就像一张无形的网一样,网住了人们的思想,网住了人们的眼光,网住了人们的手脚,形成一种对现代体制、现代经济、现代人才、现代思维和行为不相容的排斥力,或者不亲和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西部特色”,而是世界上贫穷落后国家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正因为如此,世界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概念,即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因素,不仅有“正式制度”:成文的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也有“非正式制度”:社会上自发存在的陈旧观念、习惯、风俗、思想意识形态等。显然,在西部落后地区存在的群体性的守旧、保守问题,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围。
乔:对于落后的“正式制度”比较好办,就是改革。那么,对于落后的“非正式制度”采取什么办法呢?
邹:与对落后的“正式制度”一样,也是改革。但这种改革不同于去摧毁、替代一种体制,而是要推进和提倡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对“非正式制度”改革的深邃思考。在西部大开发中,就要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变革观念。我在80年代就提出,解放思想、观念变革,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环节。从90年代初开始,就反复倡导“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
乔:话题回到前面,《西部儿子:我为什么不回家》一文的观点是不是可取的?
邹:我认为,《西部儿子:我为什么不回家》一文反映的那种遇到“冷漠”、“障碍”就不再回到西部故乡,不再爱西部的态度和观点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因而是不可取的。我认为,我们西部出来的同志要有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和思想境界,要容忍我们故乡的缺点,就好像容忍我们的母亲有缺点一样。不要去逃避甚至怀恨西部故乡的缺点,而要以积极的态度去感染它、改革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步去影响它,要以无怨无悔的精神为西部大开发做出自己的贡献。
乔:您所讲的宽容,我理解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西部工作的同志要宽容西部的缺点,同时,我们西部的父老乡亲也要采取宽容的态度,给外来人创造一个宽松的创业、工作环境,让他们能安心地工作。
邹:是的,宽容应当是相互的。无论什么人才,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完人,都会有缺点。因而,我也提倡我们的西部故土宽容人才的缺点,就好像母亲宽容儿子的缺点一样。中组部提出西部要做到“三个留人”:以感情留人,以事业留人,以较优厚的待遇留人。我认为,以感情留人,就包括对人才缺点的宽容态度。
乔:我同意你的观点,要制定出好的政策来,吸引大量的人才到西部工作。
邹:你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在制定人才政策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顺序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重视人才首先要重视当地人才,激发当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些地区在制定人才优惠政策时,往往只注意到外地人才,伤害了当地人才的感情。要知道,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本地人才的成本是比较低的,用活用好当地人才是第一步,其次才是吸引外部人才。
乔:实际上,我们过去曾经制定过很多吸引人才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明显,人才吸引不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邹:建立吸引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机制,不是说想办法把人才死死地留在西部,就像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一样,那是死用人才、用死人才。现在我们则活用人才、用活人才。比如,现在北京人去西藏,官升一级、双份工资,3年后可以自由回来,迁不迁户口自愿, 这一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很多人排队报名。正是因为可以自由地离开,那才有人愿意来,如果人来了后就不让走,那后面的人就不敢再来了。
乔:对于西部大开发,我们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呼吁呢?
邹:我们呼吁每一个西部儿子,每一个华夏子孙,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西部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