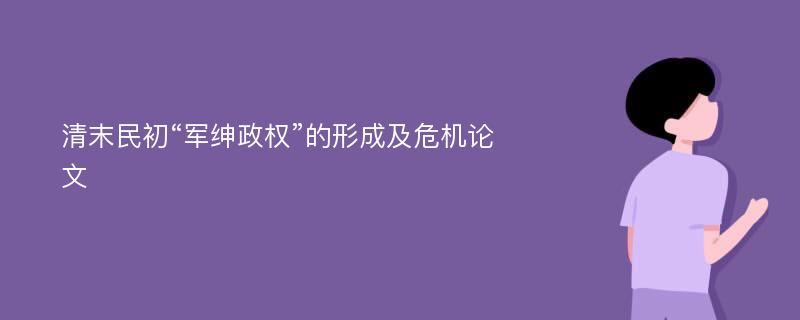
传统与现代
清末民初“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危机
曹瑞涛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清末民初中国政坛出现了武夫当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从前把持权力的传统士绅集团不得不屈从于新兴的职业军人集团。新式职业军人集团之所以能够顺利把持政权,并非传统士绅阶层的实力因社会动荡而遭到削弱。相反,士绅手中的权力在时局动荡中不断加强,但士绅权力的急剧扩大却最终导致了武夫的上台。这种颠覆性的结局是传统中国社会和新时代各种新旧因素复合的产物。然而,军绅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完成救亡图存、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反而使国家和民族深陷到更大的危机之中。
关键词: 军绅政权;士绅阶层;军阀;清末民初
陈志让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时提出了“军—绅政权”的概念。中外虽有不少学者对近代中国军阀政治进行了多方位研究,但在陈先生前后,从“军—绅政权”的角度进一步研究的却并不多,“知网”上相关的文章只有5篇,且多以介绍为主。再者,由于陈先生研究重心放在军阀一边,对“军—绅”双向交互模式也没有展开研究。因此,笔者不揣冒昧,从“军—绅”互动模式入手,对近代军阀政治的特性进行一番初步考查。
一、从“绅军政权”到“军绅政权”
1911年10月29日山西省咨议局的会议厅里气氛诡异,表面上喜气洋洋的与会各方你推我让、一团和气,可越是临近会议的正题,会场中的紧张情绪就越浓重。就在这天凌晨,山西继湖北、湖南和江西之后,成为全国树起反清大旗宣布光复的第四个起义省份。随着太原城中忠于前清政权的巡防营和新满营的迅速崩溃,这场仓促间起事的革命进展之顺利,令起义领导人来不及欢呼胜利,便得为添补清廷势力骤然退却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而展开新的争斗。
在酸奶、Mozzarella干酪的发酵过程中、混合菌株间的共生作用让蛋白水解以促进菌株的生长;由图2可知:试验采用传统发酵菌嗜热链球菌、瑞士乳杆菌及筛选的高产抗氧化肽菌株副干酪按不同比例进行复配,发现1∶1∶2的比率能有效促进山羊乳蛋白水解且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力。
当会议进行到选举山西都督一项时,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拿出一叠早已准备好的选票,“亲自散发,一副民意代表的样子,似有自我推荐之意”。突然,同盟会会员“张树帜一个箭步登上主席台,把主持会议的梁善济挤到一边。然后,抽出乌黑锃亮的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大声说:‘选都督还要什么选票,举手好了。大家应当推选阎标统为都督,同意的举手’”。一时,同盟会员群起响应,呼声不断,“众议员面对张树帜黑洞洞的枪口和不可逆转的局势,于惊愕相顾之中,一个个战战兢兢举起了右手,‘一致’通过了选阎锡山做都督的提议”。面对此情此景,“议长梁善济自知大势已去,悄然从后门退出会场”。[1]
清末民初武夫当国局面之形成,在山西的这场选督闹剧中得到了极具戏剧化的展现。对这种武人掌权的政权形式,陈志让称之为“军—绅政权”,它和传统社会中的“绅—军政权”正相反,特别是在1912年后,“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军人在政治上首要的领导地位已经奠下了基础。军人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不再是驯服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2](P.20)
这些能够进入咨议局选举阵营的士绅,主要是地方性的、在野的、最上层的士绅,是当时中国社会精英中的精英。1908年清廷公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后,由这些人选举而成的咨议局,从原本“仅是地方督抚采撷舆论的咨议机关”,实力急剧扩充到除有权“议决本省庶政之兴革,监督本省财政,参与立法、评断下级自治会纷争、接受人民请愿等事项外”,还拥有对本省督抚大员的监察纠弹权,同时咨议局议员还拥有言论免责权。一时咨议局权力之大,如美国人吉包尔奈在其《中国观》一文中所云:“督抚司道,虽仍由中央政府选派,而司法行政之权,省人民均得参与其间。”[3](PP.10-11)
受自然和人类工程活动的综合作用,乐山市境内地质灾害种类发育较齐全、数量多,但分布不均,且具突发性及不可预见性。地质灾害种类以滑坡、崩塌(危岩)为主,其次为潜在不稳定斜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裂缝)。其中滑坡约占50%,崩塌约占30%,潜在不稳定斜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约占20%。
金川集团公司利用二氧化硫生产硫酸的能力已由“九五”末的每年22万吨提高到目前的每年220万吨,96%的工业烟气得到回收转化。金川集团中水利用量由“十五”末的78万吨提高到2017年的1 332.7万吨,提高了近17倍;工业废水处理率达100%,重复利用率达93.6%;尾矿、水淬渣及粉煤灰、粗骨料等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63.47万吨;处理白烟灰5 750吨、黑铜渣2 780吨、铜炉渣77万吨;硫酸、亚硫酸钠生产能力分别达到252万吨和15万吨,成为国内利用二氧化硫烟气生产硫酸的最大企业之一。二氧化硫一度是金昌环境污染的元凶,现在变成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工业污染持续下降。
对清末民初时“绅”较为狭义的理解,则要与清末咨议局联系起来。为缓和国人对立宪的要求,清廷于1907年“命令各省督抚筹设谘议局,以便选出‘公正明达官绅’来‘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3](P.9)至1909年,各省咨议局次第成立。咨议局议员的选举资格十分苛刻,“排除了一般人民普通选举而采取一种条件极多的限制选举,把财产、资望、学识、名望、出身、年龄,定为选举权与初选举权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能当选者绝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士绅阶级”。[3](P.11)
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小的、全部男性绅士上流阶层,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按立宪运动研究专家“张朋园估算,选民仅占人口总数的0.42%。湖南和湖北略低于这个平均数,分别为0.36%和0.38%”。[4](P.117)据1909年广东咨议员选举记载,“广东全省入册的选民,仅约占总人口的0.43%”。[5]陈志让也认同这一数据,他认为绅士阶级在清末“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2%”[2](P.12),而这些人中“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0.42%”[2](P.11)。
由于“军—绅政权”是在对“绅”的反动中产生的,故而对其性质的解析,须首先从“绅”(1) “绅”、“绅士”和“士绅”在本文中意义相同。 开始。广义上讲,“绅”大抵可理解为自前清以来中上层地主阶级和内生或依附其上的传统知识分子,以及由这些知识分子进阶而成的文职官僚集团。进而,在清末特殊社会状态中,历来遭贬斥的“商”由于和“绅”相互交通渗透的程度逐渐加深,“绅”的队伍中又出现了“绅商”等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身影。组成“绅”的这些人虽然在清末民初成分变得复杂起来,但他们与传统的权力体系都有着密切联系,只是有些“在朝”,有些“在野”。
然而,在清末敢与中央叫板,地位如日中天的这些狭义上的士绅们,以及由其带领的更为广义的士绅群体,一入民国便被他们明里暗里参与、鼓动、支持的革命风暴吹倒在地,面对武人的强势逆袭,其反应大都如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般无可奈何地悄然退出。这一局面,就像突然到来的辛亥革命一般,莫说当事人,就是旁观者也感到不可思议。
2.部分邮政企业党组织对党员教育管理不到位。一方面,对党员教育缺乏有效的措施,部分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放松对党员的教育,而且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缺乏针对性和创新性,在党员教育制度上缺乏长效机制,影响了教育的实效性,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对党员监督管理不严,首先“进口”把关不严,使一些尚不够具备条件的人混进党员队伍;其次“出口”不畅,对不合格党员处置不严;再其次,管理不够严格,党员管理的基本制度执行不严,落实不够。
2)扩孔钻头的横向不平衡系数对钻头扩孔钻进的影响较大,通过自平衡原理设置切削齿将钻头的不平衡系数控制在0.05以内,能提高钻头的稳定性,减少钻头异常失效现象。
各阈值函数方法处理后信号如图3所示,使用新调节阈值处理公式方法去噪后波形f明显比b、e要好.去噪后波形c在信号开始具有抖动现象,而f的波形一直都光滑.分析表1:带噪信号经过新阈值函数处理后, Rs,n提升2.09倍,Er,m,s由未处理时31.471 6减少到5.283 7.结合图3和表1可以得出使用新的可调节阈值函数去噪质量优于图3中的其它方法.
二、两大强力集团的形成
清末民初武人崛起之端倪在清中期就已出现。清代督抚之职袭于明代,原系中央临时派遣到地方的行官,时日迁延,便演化为地方正式长官。“到雍正、乾隆、嘉庆以后,各省总督或巡抚,又因向例兼兵部尚书或侍郎头衔的关系,均取得过问辖区内兵权之事。至是督抚控制地方之权力,又形扩大一步。”[3](P.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末武人上位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就开始标志着中国在军事指挥方面有才能的人逐渐地掌握了朝廷中的重要地位”。[6](P.12)不过当时的湘军、淮军,“还是由文人(绅士)行政长官所领导的军队,指挥和管理系统相当统一。军队的粮饷,装备仍然由行政长官负责,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免,中央政府还不是由军人操纵的政府”。[2](P.4)
民国之初,武人终于向着权位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里,虽然许多文人投笔从戎,但归根到底也没把武职看成官场上真正的归宿,毋宁说,他们在走一条由武转文的曲线捷径。可民初的军阀则不然,如袁世凯麾下的诸多干将,“身为职业军官,他们拥有特殊技能,因此有别于传统官员。……后来都出任北洋政府的官职,他们却不把军事生涯看作是转作文职的踏脚石。受到军校教育经验的影响,从军对他们来说是生涯的职业”。[7](P.277)
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时,王亚南发现历代统治者无不以轻徭薄赋相标榜,然而,中国农民依然困苦,“与其说是由于正规租赋课担太重,毋宁说是由于额外的、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多、繁多”。[12](P.129)实际上,“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统治,……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响的”。[12](P.122)
可明廷对于豪强地主扩张的失控,破坏了这些地方中小地主重建乡村的努力,最终导致了明朝内部崩溃的进程。这一历史教训为清朝统治者所吸取,通过一系列改革,到康雍年间,“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9]继而,“摊丁入亩”政策得到全面深入实施,这“意味着清统治者放弃了一直延续到明代的一君万民原理,即全体人民都由皇帝统治的原理”,也就是说皇权正式“承认地主的土地私有权与地主在私有土地上对农民的统治”。 [10]
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士绅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在庚子之役中,“发起东南互保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因为他得到了上海和两江地区地方士绅之强烈支持”。[3](P.5)清末立宪运动中,虽然“根据清廷颁布之谘议局章程,各省谘议局职掌,均限于讨论本省内部之事项,但日后却仍然演变成为反中央势力的一大温床。特别是清廷之中央集权措施与省督抚之地方分权主张冲突时,督抚们常常与各省谘议局互为声援,沆瀣一气地与中央朝廷相对抗”。[3](P.13)
因而,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内部同时存在两个强大集团,一个是相对于中央皇权的地方士绅阶层,另一个则是打着“新军”旗号、贯彻着“中体西用”精神的职业军人群体。当清廷在“新政”改革中日趋独裁和封闭时,这两大集团于反对清廷上形成某种默契,而随着表面强大的敌人迅速土崩瓦解,默契旋即变成勾斗,不过勾斗却没有升级成大规模火拼。现实是如张树帜一般的武人仅仅把乌黑锃亮的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各路议员就都集体齐刷刷地缴械了,强大的士绅集团犹如刚散架的大清帝国般不堪一击。
众多地方中上层士绅因此变成脱离农村、脱离农业经营,而成了不能算作真正工商业资本家的城市高级游民。城里的买卖竞争不过西洋、东洋的公司,城里的开销又远大于农村,只能不断加大对农村的压榨——这种不断加码的压榨已不再受中央皇权的限制。而离土离乡的状态,又促使“他们透过私下和下层士绅组成联盟,在乡村中找到了一批干部、经理人,替他们征收赋税与租金”,可是“这些小地主、土财主们并不以乡绅自居,他们的地位比起农民高不到哪里去,但是却厚颜无耻地在乡村肆行压榨,加深阶级之间的仇恨”。[7](PP.304-305)
三、外强中干的士绅集团
地方士绅在自述其志的文章中,往往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情怀和故乡责任感,这当中自然不全为虚构,比如北宋熙宁九年(1076),陕西汲郡的儒士吕和叔(吕大钧)就在其家乡蓝田推行过一种县以下村落进行自治的乡约制度。吕和叔“给乡约厘定的四大条款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四大条款就描写了乡约制度的主要功能,它是绅士以领导者的身份,作为教育与组织人民的工具,冀以形成为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11](P.108)
可惜,这套满含善意的乡村自治计划只实行了五年半就夭折了,究其原因,一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和皇权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根本上是冲突的,甚至还会遭到打压。再者,“这一套儒家的做人标准,一套繁文缛节,只是能有知书识礼的闲暇的绅士所能讲究的规矩,并不足成为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准则”。[11](P.108)此外,地方士绅虽然掌控着书写表达之权,并把自己描绘成贤良君子,但这个阶层中,如吕和叔这等人物的其实只是少数。
而在士绅(尤其地方士绅)一方,其影响力于晚明时分便开始加强。当时,自命清流与阉党势不两立,而在更深层上,这种对抗“可以说是里甲式专制体制下旧与新的斗争,换言之,就是顽固坚持旧有的皇帝一元化专制体制的皇帝宦官派和与之相对抗的东林派等追求新体制的一派人员之间的对立”。[8](P.31)与皇权紧密相连的特权式大地主(豪强)相对立的政治势力,东林党人“从整体上说,他们是通过对里甲制的改编、补充加强甚至通过里甲制的实质性解体,谋求重组和强化乡村秩序的所谓乡绅阶层即乡村中的领袖”。[8](P.33)
“绅权和民权是两件事,绅权和官权则是一件事。”[11](P.37) “绅”与“官”紧密相连,所有的“绅”(无论豪强还是地方一般士绅)本质上都是特权性的,区别只在量上。所以,以君子自命的东林党人一面与拥有皇权支持的豪强地主斗争,“另一方面,同样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他们对反抗大乡绅暴行的民变采取了抑制压迫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奴变,他们采取了彻底镇压的立场”。[8](P.103)当然,地方士绅阶层与皇权支持下的豪强还是有所不同,比之豪强的纯破坏性,地方士绅很多时候还起着维系统治平衡的“转换器”的作用。
这台“转换器”若能正常运转,一方面,当地方士绅与中央皇权讨价还价以维护自身利益时,往往打出“民意”的旗帜,携百姓以抗君权,顺带着保护了一些百姓的利益。另一方面,士绅终非从皇帝那里得到供养,而要靠压榨百姓获得,可中国士绅又缺乏西方封建领主的独立武装力量,所以还得回过头来寻求中央皇权的支持。于是,这台精明的“转换器”在权力上通下达的过程中既疏解了矛盾,又捞到了油水。
到辛亥革命时期,“转换器”出了大故障!由于清廷吸取了晚明之鉴,其统治者一直对豪强地主有所抑制,同时也限制了地方中上层士绅的发展。因而,周锡瑞评价辛亥革命时特别指出其“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作攻击的目标。但是,那个独裁专制不但限制着中国人民的自由和主动首创精神,也妨碍着地方上流阶层过分地压迫人民。辛亥革命成功地结束了中央政权对于地方上流阶层权力的掣肘”。[4](P.9)
教师可采取课后辅导和小组定期轮流发言相结合,教师要做好后进生的思想工作,课后进行谈心和辅导跟踪,了解并弄清楚后进生的学习状态,多多进行积极鼓励和前途励志教育。此外教师要落实学习小组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且定期轮流发言,并对表现好的学生及时进行课堂大力表扬和加分或赠送一些称号,另外教师务必多多巡视课堂提醒后进生参与小组合作讨论。
清中后期,农业、工商业及城市的发展都超出旧制度所能承受的临界,西方强势文明入侵又极有力地推进了这些社会变革。清廷推行“新政”后,上层士绅在城市文明的磁力吸引下,纷纷走出乡村,定居城镇。“通过参与兴办工业企业,新的上流阶层中的某些成员已经变为‘资产阶级’。但是,为了把绅士阶层转化为资产阶级,当时的工业化确是过于软弱无力了。结果,就整体而言,新的上流阶层没有充分和绅士渊源决裂,没有充分地承担起发展工业、兴办自由企业以及实现经济的合理性这些资产阶级的意图。”[4](P.84)
医院感染高发科室在于泌尿外科,尤其是经手术治疗后患者,具有较高的感染风险,不仅可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且还会带来较为强烈的应激反应,因此在临床上实施护理干预措施尤为重要,对降低院内感染发生率具有积极作用[1]我院为了探究泌尿外科应用护理干预对防治医院感染的临床作用,选取2016年11月14日至2018年03月03日收治的研究对象为88例例泌尿外科患者,见正文描述:
从表象上看,士绅集团屈于下位是因为手里没枪,可搞几条枪、拉支队伍出来,对有钱有势的士绅集团算得上什么难事呢?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士绅阶层却安于武人统治之下,并没有急于恢复文官统治的努力。或许吊诡之处就在于,由“绅—军”向“军—绅”的转化,关键性因素恰恰在于士绅阶层自晚明以来不断自我强化的进程。
本篇故事貌似客观描写了家族历史,实际上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极其幽默而带有讽刺意味地展现了家族历史上的士兵们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的样子,我们通过陈译本的翻译来感受一下其中的幽默感:
最终,作为有资格进入咨议局选举的那0.42%的大清国精英中的精英,其强大表皮下裹着的,实在是不堪一击的筋骨,在城里他们是幼稚、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乡村,他们培养出一大批低层次的土豪劣绅扰乱乡里。以前,这些“人上人”可以携民意以抗君权,倚君权以压百姓;现在,在阶级矛盾日益升级威胁下的他们,看到张树帜拍在桌上的那把乌黑锃亮的手枪,与其说是来自武人的威胁,还不如说是武人抛来的一颗救命稻草。
四、新式职业军人集团的崛起
士绅屈从于武人,以求乱世中保障财产、生命安全,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几乎每逢改朝换代之际都会重演一遍,可清末民初的“军—绅政权”却有着全新的性质。旧时军阀虽然威加于士绅之上,马上得来的天下终究还要靠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套路来治理,可作为“政治斗争主角”的民初军阀,此时却具有了古代军阀所没有的新性质,这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愿意、也难于退回到为传统士绅阶层所支配的那套统治模式之中。
首先,清末民初,社会上尚武之风流行,为武人上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种风气与传统中国社会中隐性存在的暴戾因素间虽有联系却又不同。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显性性状上看,它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在谴责暴力行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共存确立为道德规范方面,要比许多其他文化传统积极得多”。 [13]可又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14]这股杀伐戾气广布于社会阴暗处,一遇动荡就展现出来,甚至精研理学的曾文正公,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给其弟曾国荃、曾国葆的家书中亦写道:“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15](P.737)当曾国荃攻打安庆时,曾国藩又特别写信叮嘱:“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15](P.726)当然,主流“尚文”文化始终坚守“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16]的观念,这使“尚武”观念总与这股杀伐戾气脱不了干系,从而在传统社会中一直伸展不开。
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敲开大清帝国封闭已久的国门,华夏文明遭遇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连蕞尔小国日本也欺负到头上来了,保国、保教、保种成为刻不容缓之急务。在民间,郑观应于《盛世危言》中大声疾呼:“中国积弱之病在重文而轻武。”[17]朝堂上,张之洞亦没了旧文人的遮遮掩掩,直言曰:“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18](P.11)作为学者的严复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更是选择性忽略掉“伦理学”部分,而突出“进化论”的部分,故以《天演论》为书名,赫胥黎本意在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却在《天演论》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19](P.75)。虽然“严复对国家富强的关注与赫胥黎的关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19](P.68),但这种选择性误读却在那个时代取得了普遍共鸣。
通过这些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的作品,又配之以西方舶来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流行,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尚武之风中被填充进“进化”“自强”“爱国”等新观念,它们不仅冲淡了旧式尚武中的“三国气”和“水浒气”,还塑造出新式尚武的核心精神。于是,这种新式尚武之风渐为主流所接纳,到了“新政”时期更为官方所提倡。“1906年4月的一道上谕列举了关于公共教育的各项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后主要由绅士文人组成的大多数教育团体,也都提倡尚武精神。”[20](P.535)进而,朝野风气为之一变,“在此之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还甘心‘埋首书城,磨穿铁砚’,接受科举制度的愚弄;而在此之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已经弥漫全国了”。[21]
在瓷面上“打玻璃白”也是一项讲究的工艺活,玻璃白是水溶性颜料,而彩瓷是先要用油性颜料钩线和画底色,这个过程必然会使瓷面沾上油,这样水溶性的玻璃白就无法打在含油的瓷面上。这就需要用到“锅灰”锅灰具有吸油作用。在需要上玻璃白的位置先抹上少许锅灰,然后再把锅灰轻轻扫除,这样玻璃白就可以打在瓷面上。
其次,在新型尚武之风中成长起来的新式军官亦非旧时武将可比,其综合素质不仅远高于传统文官,甚至高于同时期受西式教育成长起来的新式文官。
与“虚文”相比,“武”是可以被立刻实证的,义和团般的“武”摆到洋枪洋炮面前,高下立判!故而,张之洞直言“盖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18](P.129),怕是再顽固的腐儒也不得不认。因此,尚武、习武能以较为开放的姿态接受西式教育。到了新政时期,各地纷纷建立武备学堂,高薪聘请洋教习,派送优秀毕业生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
清末民初职业军人的崛起乃至“军—绅政权”的建立,既是传统士绅阶层无力维系其统治的结果,也是接受了更多西方“器用之术”教育的新式军人实力急骤扩张的结果。故而,士绅失了权,虽有些无可奈何,但其中也绝非没有主动“予”的意思;武人夺了权,表面上气势汹汹,可接下来又不能失去士绅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支持,对士绅们也不能得罪太深,反而会多加维护。
而在国内,“新建的军阶体制,它使军人得到了同文职官僚一样的官衔和薪俸”。通过这些措施,新军中的“军官——即便是最低级军官——的素质和教育水平及其对科学技术的了解,都远远超过旧式军队的同僚,与文职官员的平庸无能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军队已经超过了文职官吏:西化的军官比从事外交的文官升迁更快”。[20](PP.534-535)
再次,新式军队中的军官成分、军官品质以至普通军人的品质也出现了新变化。
清末社会新型尚武之风流行,但在一个有着长久尚文传统的社会里,即便废了科举,在士绅阶层眼里从军不仅是危险的行当,也没有出国买张文科文凭回来就能升官发财来得稳妥。说到底,从军的还是些穷苦人家的孩子,所以新军大门敞开,放进来的是少年丧父,“剩下孤儿寡妇,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的吴佩孚;[23](P.5)是卖布为生,“肩挑手提,走遍大街小巷,博取蝇头小利”的曹锟;[23](P.92)是跟着父亲卖鱼糊口的李纯,作粮店学徒的陈光远,看着母亲活活饿死的王占元等。
不过,除了这些挣扎在最底层苦难深重的贫民之子,新军还放进来另外一些人。1905年废科举之后,新式教育明显比传统教育昂贵,八股取士虽弊端百出,毕竟给寒门学子留了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现在这点希望也没了,眼前除了师范院校就是新式军队,结果,“凡知识分子,见科举已停,贫士无进身之阶,遂相属投军”。[4](P.186)大量小知识分子投军改变了军队的成分,也改变了传统军人的气质,这些在新旧思想冲击下苦恼、茫然又激动的失意知识分子无形中使新军军营变成了一所大学校,利用新军引进西方技术时推开的对外窗口,不仅改造着自己,也教育着身边的普通军人。
再次,为了实现医院发展就应当发挥人才作用,提高人才素质。目前医院应当成立专门绩效考核部门,对于医院的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通过科学以及有效培训,提升员工的综合能力以及素质,与此同时,还是需要加强临床知识的教授,从而促使人员临床知识水平全面提升。绩效管理工作过程当中,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对于奖金进行核算,而且需要绩效管理人员发挥更多作用。绩效管理人员素质是绩效管理工作质量以及效率基础,只有绩效管理人员素质高,才能保障绩效管理职能得到正常有效发挥。为了提升人员素质就要加强培训,还需要加强人员指导,建立合适管理制度,保障医院绩效管理水平以及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在这种特殊的教育环境下,新式军人具有了比传统乱世投军吃粮的亡命者更为复杂的人格结构。一方面,他们虽不能深刻理解民主宪政为何物,但国家、民族主义的观念已极大地挤压了推翻了皇帝当皇帝的传统打江山思想,他们多少都分有着蔡锷的壮志,即“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24];另一方面,如魏斐德分析黄浦早期生源时所说:“他们这种小知识分子意识和由于自己地位卑微而受压抑的壮志结合起来,使他们对实现权力的向往更加炽烈。加上他们并不是摇笔杆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比起大学教授这类高级知识分子来就更加愿意采用搞革命组织或军事训练等其他方式来表达个人志愿。” [25]
总之,以浸染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等西方观念的尚武精神为背景,经过系统的西式军事教育,又配之以寒门乃至社会最底层的悲愤交集和勃勃生机,新崛起的武人阶层在清末民初天下大乱的时局中横空出世。当传统士绅在新危机面前手忙脚乱、无所适从时,这些活力四射的武人却勇气益振,毫不客气地从士绅手中夺过政权,充满自信地从兵营走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
五、“军绅政权”引发的危机
习武留学者皆为公派,且多是军中佼佼者,与当时蜻蜓点水、急功近利的习文留学生不同,他们更刻苦,所受教育和训练更深入、更系统。日本军事当局最初授权成城学校为中国学生开设军事预科教育,1903年日本军事参谋本部又成立振武学校,专门初步培训中国军事留学生。“1900—1911年间,690名成城和振武的毕业生考入士官学校,其中647人完成了全部训练课程。”[22](P.153)这些军事留学生中名人辈出,如蔡锷、孙传芳、阎锡山、李烈钧、蒋百里等。
清末两大实力集团通过主次结构的调整,建立起新的联合。进入民国后,面对列强进逼,其首要任务为——重建统一高效的中央政权。当时,“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政治组织如果敢于违背这个全国一致赞同的信念,它就别想得到人民对其权威的承认”。[6](P.160)可“军—绅政权”非但没有担负起拯救国家、民族的历史重任,反而加剧了国家分裂的局面,带给人民巨大的苦难。
之所以会如此,根本还在于“绅”的特点,王亚南认为中国两千年封建制的特征在于“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了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把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封建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封建形态。封建的形态是改变了,其本质还存在着”。[12](P.45)所以当前清官僚体系崩溃后,就暴露出士绅地主阶层天然的分散性、地方性,而少数士绅新增的资本家身份又根本无力承担起建立国家统一大市场的任务,倒是颇欲固守地方一隅市场以求自保。军人不事生产,他们的存在模式只能取决于供养他们的阶层的存在模式。
“军—绅政权”因而自然地趋向割据模式,以至于连各省督军都“很少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管辖领地。有许多小军阀、师长、地区驻军司令,甚至旅长,都急于争夺地盘。这些势力较小的军人不管有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都是独立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6](P.17)分裂的现实和统一理念间的矛盾,使所有军阀的存在都失去合法性依据,谁也不敢把“地方自保”升格为“地方建国”。这又造成军阀间总处于战争状态,只有打出“统一”的旗帜彼此攻击,才能确保自己不站到分裂国家的全民公敌的位置上,才能苟延自己不合法的存在。
与此同时,士绅阶层侧身于军人权威的保护之下,以期维系他们在农村岌岌可危的特权,并获得在城市发展工商业时不可或缺的超经济庇护。军人确也给予了士绅这样的特别关照,可结果却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得以在农村继续存在,而民族产业又开启了新一轮洋务运动时官商勾结的扭曲发展历程,士绅阶层无法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又导致其在西方势力强力竞争面前整体持续衰落。士绅越衰落,就越要依附于军人,这在表面上更加强化了军人掌权的必要性。
尽管志愿服务最先起源于西方国家,但其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相契合。“奉献”强调甘于付出,不求回报;“友爱”强调与人为善,平等尊重;“互助”强调互相帮助,助人自助;“进步”强调自己进步,社会进步。志愿服务倡导维护社会的稳定、公平和公正;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倡导追求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充分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和谐、社会进步、公民友善的基本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表现。“志愿服务”直白、浅显的表述便于老百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理解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品评小组5位成员对每一个因素进行逐个评判,统计每一个因素的各个评语的人次,4个因素的5个评语共有20人次。然后将品评员对每一因素的品评分值转化为评语域各等级得票数,得到猕猴桃酒感官评定结果,见表2。
但军队毕竟是消耗性集团,尤其军阀间战争不断,衰落的士绅阶层终会支撑不起庞大的军费开支。到那时,军阀们要么以出卖国家核心利益为担保,大肆向列强广借外债;要么在国内滥发公债、操纵通货,置国家金融安全于不顾;要么征缴各类苛捐杂税,乃至减少粮食作物面积以种植鸦片,鼓励毒品贸易。等这些几近自杀的招数都用尽了,甚至纵容士兵劫掠百姓。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多次毁灭性饥荒,“美国红十字会当时拒绝参与在中国的饥荒救济,认为中国的饥荒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26](PP.311-312)
“军—绅政权”在思想观念层面也是漏洞百出。严复说起支持其理论的斯宾塞之思想,称其著作“数十万言……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而“他认为急需译的是一些能把达尔文的主要原理以吸引人的方式概述出来,而且其文章又易于驾驭的小册子”。[19](P.66)故而在当时,连大部分知识分子乃至社会上层人物,也不过是以游记、小册子、报刊文章等方式,浮光掠影地了解西方——或了解他们想接触的西方。
文化快餐虽然营养不足,但还不至有毒,可“不幸的是这时候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渐渐为人放弃,西方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在欧战之后,西方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抱严厉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比较安静恬适的文化传统有向往之意”。[2](P.143)一时新文化运动变得徘徊不前,知识界出现保守主义的反动,比如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4年间连印8次,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学者艾恺对此认为,梁氏的成功“说明了在比庞大的沿海城市更庞大、却少有发言权的中产阶级社会中,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影响确实是有限的。梁著似乎的确是以这种感情结构在有文化却默不作声的中层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27]
尽管梁氏在其著作中明确声明,对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而言,“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28]但大多数“有文化却默不作声的中层知识分子”有意无意间还是忽略了这份提醒,陶醉于“东方不败”的预言中。新式军阀中的不少人恰属于这类知识分子,因而在知识界出现文化反转时,“一般不很了解西方文化的旧学者,旧官僚,军阀,受了这些趋向的影响,深深了解儒家学说与军—绅政权的关系,于是以卫道君子的身份,由卫孔子来卫军—绅政权”。[2](P.144)
一时间全副西式装备的大小军阀们又成了儒教的信徒,连被称为“狗肉将军”的山东督军张宗昌都印行了一版《十三经》。在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军阀们除了在故纸堆搞出些玄而又玄的说教,以期人民谦卑恭顺地忍受他们的统治外,提不出系统的、全面的、真正有建设性的建国方略。可以说,在现实中他们还凭着那“乌黑锃亮的枪口”苟延着,但在观念的层面上,他们早被世界大势所抛弃,“军—绅政权”的前景一片漆黑。
六、结 语
古典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士绅阶层总高居于武人之上,只在天下大乱时武人才翻过身来欺负一下士绅。可到了这番境地,遇着兵的秀才仍不失对兵的心理优越感,兵们虽然气势汹汹,内心深处仍气短三分。随着清末民初“军—绅政权”建立,形势陡变,新型职业军人不仅不以“兵”的身份为憾,反而具有了傲视传统士绅的心理优势!此时,传统士绅阶层已没有能力有效限制武人,尤其那些固守乡村的旧士绅,面对现代化大潮,除了复古尊孔的老套路,提不出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方略,被他们忽悠了的军阀尝到点儿苦头,基本上都将他们高高挂起,不真当回事了。
至于开明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提出的方案看上去多么迷人,却都应了胡素珊尖锐却不失正确的评论,即也许他们最大的悲剧是“智力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自身游离于现实之外这个事实”[29]。所以,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开明士绅力图以各省立宪的方式来约束军阀,他们的那通忙活也只是“建立在民间士绅、学者和醉心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之间。其中虽也有一部分军阀,曾为之效力,但是一旦时过境迁利用价值不在时,军阀们就会抛弃之如糟糠”。[3](P.248)
这些雄心勃勃的当国武夫们,虽然手里有枪杆子,却没有装备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在千年未遇的大变局面前越来越无能为力,他们不仅没有给苦难的中国带来实质性改善,反而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民族的危机。“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绝不能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基础。”[26](P.313)
参考文献:
[1] 雒春普:《阎锡山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3]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4]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 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6]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7] 魏斐德:《大清帝国的衰亡》,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8] 沟口雄三:《中国的历史脉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9]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
[11]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3] 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4]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1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16] 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7] 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18] 张之洞:《劝学篇》,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19]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20]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1]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
[22]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章君谷:《吴佩孚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
[24] 蔡锷辑录:《曾胡治兵语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5] 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6]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7] 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2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9] 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
The Emergence of “Military -gentry Regimes ”and the Crisis during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AO Rui-t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there emerged warlord regimes in China. Consequently, the traditional gentry was forced to succumb to the rising warlords. The reason why the warlords could take power so smoothly is somewhat mysterious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gentry was never weakened by the social turmoil. On the contrary, the gentry became more and more powerful in the social turmoil, result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litary-gentry regimes whose government was composed of warlords and gentry. This dramatic situation could be contributed to a variety of factors conflicting with each other, among which there were both the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ose of the new era. However, the military-gentry regimes could not save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e its survival, nor did they fulfil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advancing modernization. Due to the malfunction of military-gentry regimes, China was caught in a more severe crisis.
Key words: Military-gentry regimes; gentry; warlords;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9)05-0039-08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9.05.004
收稿日期: 2019-05-10
作者简介: 曹瑞涛,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中国史研究。
标签:军绅政权论文; 士绅阶层论文; 军阀论文; 清末民初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