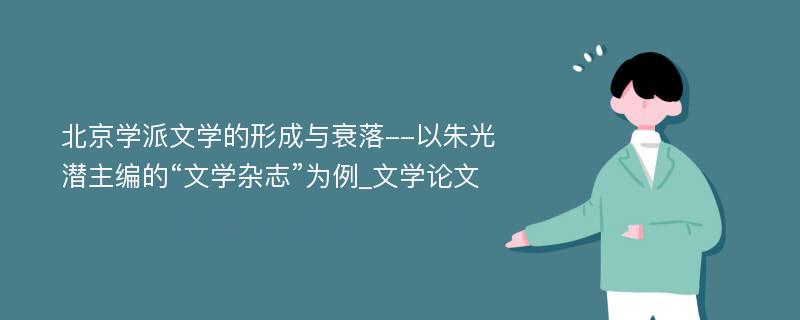
京派文学的守成与式微——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文学论文,个案论文,杂志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34(2004)02-0066-05
《文学杂志》是抗战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大型文学刊物,是后期京派的文艺阵地。迄今虽有不少学者对它给予关注,其中1995年12月出版的《朱光潜研究丛书》对它进行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与它实际价值相比,仍显得不够,并且有些研究还与事实出入较大,如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中,对它创刊的时间,出版的期数就不准确。另外,在有些工具书如《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中根本就没有收入。因此,对该刊物重新做些整理与评述,对该刊物的科学定位,透析京派文学艺术特征以及京派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有不可藐视的价值和意义。
短暂而曲折的历程
《文学杂志》一个纯文学刊物,1937年5月1日创刊,编辑部设在北平后门内慈慧殿三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每月1日出版,上海及各地印书馆发行。朱光潜任主编,胡适、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冯至、朱光潜和常风共十人为该刊的核心成员。[1](p118)1937年8月1日出版第一卷第四期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处于蓬勃之势的《文学杂志》因战争的到来而不复存在。1946年冬,朱光潜回到北京大学,经过半年的筹备,1947年6月1日《文学杂志》复刊出版第二卷第一期,编辑部设在北平沙滩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附六号,从第三期开始改为每月初出版,直到1948年11月初出版第三卷第六期后,因各种原因停刊,前后两个时期共出版了三卷二十二期。
《文学杂志》以“在自由发展中培养纯正文艺风气”为目标。在北方文坛主将沈从文1935年8月15日《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可窥见创办《文学杂志》的端倪,经过两年的筹备,1937年5月1日,《〈文学杂志〉创刊号》终于面世。任何一种刊物都有它办刊宗旨和指导思想,《文学杂志》也一样。朱光潜在题为《我对于本刊的希望》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并指出“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端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应该“集合全国作家”在“自由发展个性”中“开发新文艺”,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2]十年后,在该刊的《复刊卷头语》中又说道:“我们的目标在原刊第一期已表明过,就是采取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综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培养成一个较合理的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的纯正底文学风气”[3]。由此可见,“培养健康纯正的文艺风气”始终是《文学杂志》办刊的宗旨和指导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才使该刊前后两个时期保持了严谨而超脱的大致统一的风格和较高的文学品位。
《文学杂志》作为京派作家的文艺园地,一个大型的纯文学刊物,在以朱光潜为主的京派作家周密筹划、精心耕作、苦心经营下呈现出它特有的个性与风采。首先,内容齐全,作家阵容庞大。诚如商务印书馆在为《文学杂志》写的介绍词所说:“《文学杂志》的内容包含着诗、小说、戏剧、散文各体的创作,以及论文书评。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宇宙风》第43期)[4](p120)这样门类齐全的栏目设置,必然吸引了大量知名学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目光。统观三卷二十二期《文学杂志》,共有123作家发表不同类型的作品,这些作者大都是北方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地道的学者型文人,从而使《文学杂志》显示出较高文学水准和学术品位。其次,理论与创作并重。当时一般的文学刊物只重创作,不顾评论,而朱光潜在编配时参考了欧洲几种著名的文艺刊物的编配方法,以五分之三的篇幅登创作,五分之二的篇幅登“论文与书评”。并且在编排上,以“论文”打头,以“书评”殿后,加重理论的力度,让读者在读刊物时,“不仅要读,还要谈,要想”[5]。第三,注重对外国文艺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译介。在《文学杂志》中,几乎每一期都介绍国外新近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来打开国人的文学视野,从而树立《文学杂志》的现代文化品格。
可见,《文学杂志》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近两年时间,可在这短暂而艰难的历程中,显示出了它独特的文学品位和魅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京派“纯文艺”观的倡导和实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学“乌托邦”的建构与推进
在“文学革命”已向“革命文学”转变的三十年代,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流派各以自己独特的文学景观,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竞相争流的壮观局面。作为京派文学阵地的《文学杂志》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建构与推进京派文学理念的重任。
1.以“振作京派”为契机
京派是一个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在三十年代宏大的阶级叙事潮流中,京派文学显然有着几分不合时宜的味道。同时,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前期京派在文化立场和美学原则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位移”,呈现出“趣味主义”的倾向,致使以沈从文为主的京派后起之秀对此表示鄙夷和批判,并决心“以一种负载使命的真正‘严肃’的文学来拯救自由派文学的颓势”[6](p150)。因此,为了进一步壮大京派文学的影响力,加重与其它文学流派竞争的砝码,京派主将们迫切需要创办“较为合理”的“纯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底文学风气。”[3]于是,《文学杂志》应运而生了。正如朱光潜在《自传》中所说:“我回国的时候,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7](p284)由此可见,《文学杂志》是以“振作京派”作为创刊背景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文学杂志》才成为后期京派文学一个主要的文艺阵地,担当起推进“纯正文艺”的重任。
2.阐扬京派文艺观念为己任
京派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商品化的功利主义倾向,主张文艺家应该采取“中立”、“超然”的态度,推崇“纯正文学”,强调文学要表现人性和“和平静穆”的美,显现出纯文艺的审美趣味。那么作为京派文学阵地的《文学杂志》必然会大力提倡和阐扬这一文艺思想和文学观念。在《文学杂志》所发表的80余篇论文中,特别是第一卷的11篇论文,几乎都传达和表述了京派的文艺思想。朱光潜的《我对于本刊的希望》(第1卷1期),可以说既是《文学杂志》的办刊宗旨,也是京派的理论纲领。在文中他大力提倡走自由发展的“纯文学”道路,他指出,“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的“文以载道”说是条“窄路”,提倡“多探险,多尝试”,“让不同的学派思想在骚动发展甚至冲突斗争”中“自由发展”,用“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在读者群众中培养‘纯正文艺’的风气”。显然,这些观点与京派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沈从文作为京派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再谈差不多》(第1卷4期)中,提倡“诚心写作”、“自由发展”;反对“追随风气”,而丢掉“风格”、“个性”和“独立见识”。叶公超的《论新诗》(第1卷1期)和陆志韦的《论节奏》(第1卷3期)从新诗的“形式”、“格律”、“节奏”契入,用比较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节奏,文字意象诸多问题,来探索新诗创作的路径。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第1卷4期)介绍我国固有的“人化文评”,宣传“移情说”。周作人的《谈俳文》和《再谈俳文》(第1卷1、3期)对中日俳文进行比较,得出徘文由“替政治或宗教办差”转向“游戏”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些论文或隐或现地凸现了京派的文艺观念和文学思想。此外,在书评和《编辑后记》中都承载着京派的文艺思想,对小说、诗、散文、戏剧等方面的创作和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3.以京派作家、作品为重镇
《文学杂志》作为京派文学的园地,作者大都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院派”式地道文人,他们以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表达着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念,使《文学杂志》呈现出浓郁的纯文学气息。虽然时不时有些非京派作家登台亮相,但京派作家却是地道的中坚主力。特别是前期的四期中,像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林徽因、芦焚、凌叔华、废名、萧乾等等京派作家频繁地在刊物中泼墨挥毫、激扬文字,而其它流派的作家仅仅只是修饰点缀而已,而这一点缀却恰好体现了京派所倡导的宽容态度与“君子风度”。即使十年之后,京派作家仍然是复刊后《文学杂志》主要的撰稿人。正是这些诚朴治学、地道的学者型作家的加盟,大大提高了《文学杂志》的文学趣味和艺术品位,也正是这些作家以丰硕的创作实绩丰实了《文学杂志》的审美蕴味,从而扩大了京派文学的影响。
在创作上,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戏剧,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就诗歌而言,废名的《宇宙的衣裳》(第1卷2期)、卞之琳的《半岛》(第1卷1期)、冯至的《给几个死去的朋友》(第1卷3期)、林徽因《去春》(第1卷4期)、穆旦的《荒村》、《三十诞辰有感》(第2卷3、4期)、袁可嘉的《进城》、《难民》(第2卷3期、第3卷2期)等等,都是代表作家创作水准的得力之作。小说方面,沈从文抒写湘西世界对自然人性、自然生命形态怀念追忆忧思的《贵生》(第1卷2期)、《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第2卷1、6期);杨振声描写山东沿海野蛮原始风俗的《抛锚》(第1卷1期);萧乾那烘托北方乡村沉闷气息的《破车上》(第1卷2期);以及凌叔华用儿童视角叙写成人世界的《八月节》(第1卷4期)等等都是现代短篇小说,特别是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力作。散文的名篇尤其多,钱钟书的《谈交友》(第1卷1期)、沈从文的《神之再现》(第1卷3期)、朱自清的《房东太太》(第1卷2期)、俞平伯的《无题》(第1卷3期)、朱光潜的《生命》(第2卷3期)等等,或用幽默风趣的文笔提示精辟的人生哲理;或抒写“素朴、单纯的人性”和“牧歌情调的边陲之地”;或以简练、亲切口吻道家常琐细;或笑谈“人生”的无常和灵魂的优美;真是色彩纷呈、风格各异、绚烂多姿。
可见,《文学杂志》在朱光潜等人的热诚关切和悉心经营下,呈现出蓬勃之势,以致朱光潜在第1卷3期的《编辑后记》中写道:“为设法充实内容多登来稿,决定把原定的八万字的编排扩充到九万至十万字”,并且在《复刊卷头语》中又说:“当时每期销行都在两万份以上”,从这些可看出当时《文学杂志》影响之大。勿庸置疑,《文学杂志》确实起到了“振作京派”和构筑京派文学的积极作用。
文学“乌托邦”的无奈和宿命
《文学杂志》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维护并推进了京派文学的发展,展示了京派文学的艺术风范与实力。但历史的车轮没有给它进一步表现的机会,抗战的爆发使得劲头正足的《文学杂志》随着京派在炮火硝烟中风流云散而搁止停刊了。十年后,复刊的《文学杂志》虽然继续贯彻原刊办刊的指导思想,风格上大致统一;但时代的变迁、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使以建构“纯正文艺”为宗旨的《文学杂志》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带着几许无奈走向终刊停办的宿命。
1.以反映现实、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为主调
尽管朱光潜在《复刊卷头语》一再重申办刊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办成一个较合理的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底文学风气”。[3]但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急遽变化,使得作家们身不由己不得不面对现实,面对生活做出恰当的答复。正如朱光潜所说:“《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7](P284)。诚然,复刊后的《文学杂志》不仅有左派倾向的作家出现在刊物上,而且即使京派作家的作品也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性与时代感。
抗日的烽火使作家们更加贴近血肉的生活,随着思想情感的变化作品的风格也有所转换。在诗歌、小说、散文、游记等专栏的作品大都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废名的小说《莫须有赶坐飞机以后》在《文学杂志》上连载,就改变其晦涩风格,生动地记录了战时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现状,写出了苛政猛于虎,“内忧”重于“外患”的残酷现实。徐盈的游记《煤区纪行》(第2卷1期)展现了1947年前后北平的黑暗、混浊与恐怖。邢楚均的散文《壶水曲》(第2卷1期),叙写了抗战胜利后邪恶、压抑、愚昧的现实和知识分子幻灭、失望的悲凉。而最具有时代特色的要数诗歌,废名的《鸡鸣》、《人类》、《真理》(第2卷12期)写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于反动派的痛恨与愤慨;林徽因的《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第二卷12期)用极其悲痛的笔调写出于失亲丧弟的痛苦与祖国深沉的灾难;以及方敬的《战时作》(第2卷12期),穆旦的《荒村》、《三十诞辰有感》、《饥饿的中国》(第2卷2、4、8期),袁可嘉的《进城》(第2卷3期)、《难民》(第3卷2期)等诗作无不显示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忧患意识。可见,《文学杂志》的基调已由构筑“田园牧歌”转向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同时,刊登作品的质量也大不如前,缺乏精品意识,李健吾的《阿史那》和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连载的两部重头作品,但无论其思想还是艺术成就都不高,影响也不大。此外,复刊后的《文学杂志》不再仅局限于文学,每期还刊载一些讨论文化、思想的文章,以显示其丰富多样,如吴之椿的《明日世界与中国文化》(第2卷2期)等。从以上这些变化可见,复刊后的《文学杂志》已经与京派文学所倡导的“纯正文学”的理想有了一段距离,这也正表明“不合时宜”的文学“乌托邦”已日薄西山,走向衰落。
2.版本编排、设计的随意与尴尬
前期的《文学杂志》在版本的编排、设计上非常考究,为二十四开本,二百页左右。内容上设有论文、诗、小说、戏剧、散文、书评六个栏目,以论文打头、书评殿后,并且每期都有编者精心撰写的《编辑后记》,引导读者去阅读和欣赏;每期的目录设计也很特别,用充满生机、富有诗意的图画作背景,显得精致、典雅、大方。此外,书中起首、结尾几页以及封面都有介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书籍广告,提供给读者各种书籍信息。每期字数八万到十万字左右,价格低廉,定价二角,每月1日出版。
而复刊后的《文学杂志》就显得不够严谨、精致。版本改为三十二开本,栏目的设置随意性大,增加了“游记”,原来的“书评”改为“作家作品”,每期除了论文、诗、小说是固定栏目外,其它栏目不一定都出现;另外,还出了“诗歌”、“纪念朱自清”两期专刊。到第二卷第八期,因奉政府节约纸张的命令,由原来的二百页左右减少为六十四页,同时字体也由原来的大四号字改为小五号字;第三卷第一期开始又由六十四页扩充为九十二页,定价从第二卷第十二期改为国币六元,第三卷第六期又改为金元四角五分;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改为每月初出版。另外,每期的目录也不再用图画作背景,末尾也没有编者的《编辑后记》;除了封面之外,也没有专门的用于作广告的页码。可见,前期编辑的那种执着的激情不见了,编排、设计的技巧亦大为逊色,正如朱光潜所说:“抗战胜利后复刊,出了几期就日渐衰落了”。[7](P248)
3.历史的宿命
朱光潜先生在《复刊卷头语》中说:“《文学杂志》目前复刊是处在一个很不顺利底环境。”[3]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战时刻,政治上是不会有“中立”,“中间路线”的,因而以“中立”、“超然”的姿态出现的京派作家,必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显得格格不入。与此同时,遭受空前大灾难后的中国,时局混乱、经济萧条、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致使“从事文学的人们生活不安定”。再加上一些“低级趣味底刊物”粉墨登场,使得复刊后的《文学杂志》处在难以维持的尴尬境地。
如果说,提倡“纯正文艺”的“自由发展”的京派文学在30年代是与左翼文学运动相抗衡的话;那么在40年代末就是与“文艺为民主运动、为人民解放战争服务”的文艺思想相抵触。因而,在1948年间,文艺思想界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路线展开了严厉批评和猛烈抨击。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萧乾所进行的政治性的诋毁和批评,直接宣告了“在两种强势政治力量争雄的罅隙中”获得“一席滋生与繁衍空间”的京派作家们在现代文化中历史命运的终结。同时,在京派作家内部,文艺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1948年11月“方向社”举行的座谈会上,“文学应否载道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并且带有浓厚政治化意向的新诗创作已成为他们新的文学追求,这无疑是对以“纯正文学”为宗旨的京派文学的致命的一击。由此可见,种种不顺利的环境和复杂的因素,使得作为京派文学文艺阵地的《文学杂志》随同京派文学厄运的到来而走向“停办”的历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