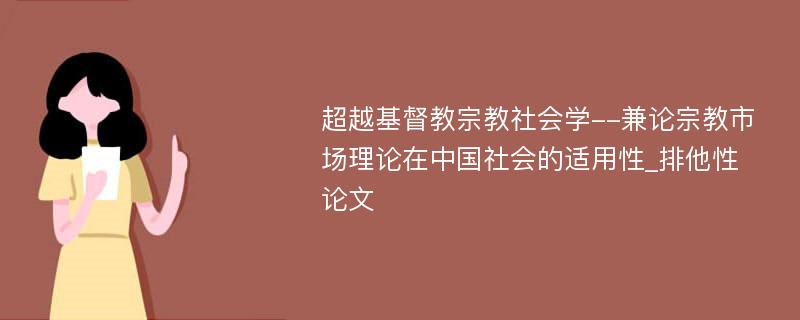
超越基督宗教社会学——兼论宗教市场理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宗教论文,社会学论文,性问题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过去20年里,宗教社会学经历了“范式的转换”(Warner,1993)。世俗化理论受到宗教市场理论(religious economy model)的挑战。通常情况下范式的转换源于人的自然更替:旧范式拥护者的凋零之时也即新范式的确立之日,大师们很少会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有误,但这次我们遇到了例外。1997年,世俗化理论的旗手彼得·伯格承认:
我想我和大多数其他宗教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世俗化所写的东西是个错误。我们的潜在论述是说世俗化和现代性携手并行。越现代化就越世俗化。它并不是个荒诞的理论,有些支持的证据。但是我想它基本上是错误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确实是富有宗教色彩而不是世俗化的。(Berger,1997:974)
这段话基本上宣告世俗化理论已经走进历史(Warner,1997)。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在这轮范式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斯达克在学生时代便已崭露头角,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宗教性的雄文。1971年从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立即被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聘为终身任职的正教授。从那时起,斯达克致力于构造一套有关宗教的演绎理论,也即是宗教市场理论。该理论在宏观层次的论述与世俗化理论相冲突,论战由此展开。也就是说,范式的转换不过是一个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副产品(Stark,1997)。在《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文版的序言中,作者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Roger Finke)写道:
如果一个宗教社会学只能适用于西方国家,就像一个只能应用于美国的物理学,或者一个只适用于韩国的生物学,那同样都是愚蠢可笑的。在这部理论著作中我们试图系统阐述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命题——就跟它们足以解释加拿大的宗教行为一样,它们足以解释中国的宗教行为。(斯达克、芬克,2004:1)
很显然,他们试图建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但是宗教市场理论的适用性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该理论的数据支持大部分来自基督教社会,尤其是美国,因此很难用于解释其他社会中的宗教现象(Warner,1993;Sharot,2002)。鉴于这样的质疑,近年来宗教市场论者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北美以外的宗教。他们把目光投向西欧(Stark & Iannaccone,1994)、东欧(Froese,2004;Froese & Pfaff,2001)、南美(Gill,1998)、日本(Miller,1995)、香港(Lang & Ragvald,1993)、台湾(Lu,2008;Lu & Lang,2006;Lu et al.,2008)和中国大陆(Lu,2005;Yang,2006)。
笔者十分认同斯达克构造可证伪的演绎理论的努力,也曾运用宗教市场理论分析华人社会中的宗教现象,但这不妨碍我们思考该理论在华人社会中的适用性。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在运用宗教市场理论解释中国宗教现象时应该注意哪些陷阱;第二,研究华人宗教对宗教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有何帮助。文章先陈述宗教市场理论的基本假设和主要脉络,然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层次分析该理论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及其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同时指出未来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些可能议题,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二、风险与宗教形态:排他性宗教vs.非排他性宗教
宗教市场理论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之上,它接受“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追求收益(rewards)是人的天性,但是,有些收益在人世间很难获得或根本不存在,比如救赎和不朽,这些“彼岸的收益”(otherworldly rewards)就是宗教所经营的独特商品(斯达克、芬克,2004)。很显然,宗教所承诺的收益具有很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这些许诺是否能在死后真正兑现(Iannaccone,1997)。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减少产品风险的方式有两种策略:分散和集中。在金融投资时,人们往往建立一个投资组合(portfolio),而不是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典型的风险分散策略;心脏病人则会固定光顾同一个医生,这体现了风险集中策略。在宗教领域,处理风险方式的不同则会导致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分殊。遵循分散风险策略的信众会逢庙就拜,比如在传统中国,人们相信“没有拜错的,只有拜漏的”。这很好理解。可是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一神教呢?宗教市场理论的回答是,宗教堂会(religious congregation)是用来降低宗教风险的重要机制(Iannaccone,1997)。
让我们还是从世俗的商品说起。当你要购买高风险产品比如二手车时,你会尽量从有信誉的商家那里购买,也会请懂车的熟人去帮助鉴定。总之,你会去积极搜寻有关产品的信息以防被骗。同样,人们在信仰宗教时也会去寻找各种可靠的信息来做出判断,最好是这些提供信息的人没有盈利动机,于是就有了各种见证。当人们聚到一起来分享见证时,堂会就产生了。“堂会指在一个宗教组织中最小的、相对自治的会员单位”(斯达克、芬克,2004:191)。堂会的参与者大都相互熟识,他们在一起做礼拜,一同参与社区的慈善和义务活动。堂会主要依靠兼职人员或志愿者来服务,因为这些人的收入与宗教无关,所以他们更可信赖;频繁的集体活动让参与者能充分且持续地展现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由于堂会的同修(fellow)彼此熟识甚至是亲人,所以他们的见证更加可信。凡此种种均能有效降低宗教的风险(Iannaccone,1997:35)。
堂会型宗教(congregational religion)强调宗教委身(religious commitment),在资源动员上具有优势,因此他们将在竞争中取得统治地位,比如古希腊的多神信仰最终让位于基督教(Stark,2006)。从历史上来看,堂会型宗教大多是排他性的(exclusive)一神教。宗教市场论者据此断言:“当一个社会的历史越悠久,地域越辽阔,构成越复杂,其人民信仰的神灵的数量越少,神灵所管辖的范围就越广”(Stark & Bainbridge,1987:86)。随着神灵数量的减少,排他性的宗教最终出现。在宗教市场论看来,排他性的宗教指的是崇拜“一个特定的神(以及所认可的次级神,比如天使)”的宗教(斯达克、芬克,2004:123)。他们认为排他性的一神教最终会打败非排他性的(non-exclusive)多神教(Stark,2001)。考虑到“所有非排他性的组织都与生俱来地软弱”,斯达克、芬克在构建其理论时明确表示他们只关注排他性的宗教(斯达克、芬克,2004:176),非排他性的宗教则被忽略。
本文的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斯达克对排他性宗教的定义和论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中心主义和进化论的色彩,但历史并非线性进化,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不是所有的一神教在宗教认同上都完全排他,比如台湾及东南亚的天主教会也容忍祖先崇拜。同样,中国文明可称得上是最长和最复杂的文明之一,但中国的宗教市场并没有进化出占统治地位的排他性宗教,主宰中国宗教市场的都是非排他性宗教。
许里和曾这样描绘中国的宗教构成:在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的基座上,耸立着三座山峰:儒教、道教和佛教(Zurcher,1980)。这四个宗教传统没有一个是排他性的宗教。多神信仰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固有特征。儒道佛从未声称自己垄断一切真理,即使彼此偶有攻击也不会把对方完全污名化,即使在佛道二教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他们也都承认对方有一定道理,至少“提供了一种好的生活方式”(Chan,1953:180)。宋代以来,很多人相信三教都来自一个源头:道。有了“一道分殊”的认识,很多人都希望从自己的信仰出发整合三教,也即三教合一(Berling,1980;Jordan & Overmyer,1986:8-12)。简言之,无论是儒道佛还是民间宗教,都不是排他性的宗教。
非排他性宗教在中国的兴盛反驳了“历史越悠久,信仰越趋近一神教”的命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社会事实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宗教市场理论奠基于排他性宗教的概念框架和命题。接下来,我们将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来进行分析。
三、微观研究:委身和改教
在微观层次上,宗教委身(religious commitment)和改教(conversion)一直是西方宗教社会学包括宗教市场理论研究的重点。这两个概念都与排他性宗教密切相关。我们先来看看委身。在客观层面,委身指的是宗教参与程度,比如参与仪式、捐献财物和遵循圣规等;在主观层面,委身“涉及对一个宗教组织所支持的解释的相信和了解,并且有适当的情感”(斯达克、芬克,2004:127)。
我们已经知道,通过集体聚会做见证,堂会有利于降低宗教的风险,但同其他集体行动一样,堂会也很容易遇到“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也就是说有人享受成果却不付出代价,比如台湾的“米饭基督徒”(rice Christians),他们以基督徒的身份领取教会救济,但却很少参与基督教的活动(宋光宇,1995)。一般说来,当某个社会运动充斥着搭便车者时,那么参与者的热情会降低,该运动距离失败也不远了。
解决宗教搭便车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成员的委身程度。当信徒都愿意积极付出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来参与宗教活动时,这个宗教团体就是有活力的。那么哪些机制有助于提高成员的委身程度呢?首先是堂会的规模。“堂会的大小跟成员平均委身程度反向相关”(斯达克、芬克,2004:192)。群体的规模越大,潜在的搭便车者越多。数据显示,信众的宗教参与会随着堂会规模的增大而下降(斯达克、芬克,2004:194)。其次是排他性的程度。宗教市场理论认为,“信众的委身程度与(宗教的)排他性程度之间存在着互惠(reciprocal)关系。”(斯达克、芬克,2004:142)。排他性程度越高,与外群体的分别越大,信徒的委身程度可能就越高(Kanter,1972)。另外,制度的严格(strictness)也会造就虔诚的信徒。一些新兴宗教要求成员穿着奇装异服在闹市招募成员,另一些保守的教派则不允许成员有任何世俗的娱乐,比如跳舞、看电影等。这些严苛的规定将搭便车者拒之门外,因此严格的宗教团体往往比温和的宗教能够更好地提供宗教服务,也能成长更快(Iannaccone,1994)。
以上种种对宗教委身的论述实际上都是基于对排他性宗教的研究。如果我们把这些论述用来解释华人社会中的宗教与行为,那么无异于缘木求鱼。事实上,儒道佛对委身甚是冷漠,以至于英文的“commitment”在中文里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汇,“委身”一词乃是译者杨凤岗无奈之余的选择(斯达克、芬克,2004:25)。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在家里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家庭之外,人们会遇到各种神灵及庙宇。这些庙宇混合了各种宗教,身份难辨,也无需分辨,“在某些乡村庙宇中,即使庙祝也搞不清他们到底属于哪个宗教”(Yang,1961:25)。如果有需要,人们会去许愿,等愿望满足后再去还愿;如果不灵验,那么很简单,换个神再拜。总之,在多神教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不注重委身,要求信众忠诚地信仰某一特定宗教是一种奢侈。
我们不能否认传统中国社会也有一些重视宗教聚会的堂会型宗教,即教派(sect),它们的延续也依赖虔信徒(committed believers)的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了中国教派在多神信仰的社会环境中培养虔信徒的策略。这一教派对其他宗教传统持开放的态度,吸取其有利因素,并加以改造。同时,他们秉持“先以欲勾牵,而后令入佛智”的信念,以渐进的方式让信众弃凡入圣。这与非此即彼的基督宗教有所不同(卢云峰,2008)。
宗教委身在西方社会非常重要,但是在非排他性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华人社会,宗教委身变得可有可无,让人觉得陌生甚至怪异。在华人社会,信众强调“心诚则灵”。“诚”似乎是一个与“委身”相似的概念,它既涉及到主观的宗教情感层面,也可以一些客观的指标,比如供物、捐献等来衡量。但就笔者阅读所及,目前对“诚”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宗教社会学微观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改教(conversion)在运用到中国社会时也同样需要进行反思。改教指的是“跨宗教传统的转换”(斯达克、芬克,2004:143),比如从佛教转信基督教,或者相反。宗教社会学对改教的研究汗牛充栋,在此不一一陈述(详见Snow & Machalek,1984)。在欧美,改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督宗教重视成员资格(menbership),改教意味着成员资格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网络发生彻底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除非发生重大的生活变故或事件,比如移民或结婚,否则人们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宗教身份(Hefner,1993)。
西方社会里改教是关系到个人身份的大事,因此人们会慎重对待,但在中国,改教无足轻重。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传统宗教不重视成员资格。杨庆堃曾写到“中国宗教的首要特征是成员资格的普遍缺失”(Yang,1961:327)。当人们到庙里烧香拜佛时,谁会考虑他们是否具有成员资格呢?来者都是客。即使某些教派对成员资格有一些要求,比如举行某种仪式等,信众也大多不以为意。人们随时准备改变,或者说增加自己的宗教身份。韩书瑞观察到,即使在最重视宗教资格的教派中,教徒也经常“从一个教派转到另一个教派,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总是寻找‘最好’的宗教”(Naquin,1976:37)。在东亚,一个人同时拥有多个宗教身份是常态。日本宗教信徒数是其人口总数的两倍,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日本人信仰两种宗教(Miller,1995)。壮则奉儒教积极入世,暮则信老庄归隐山林,在中国传统士人眼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谁一辈子只信一宗反倒觉得异常。
在西方,改教无异于天人交战。而对中国信众来说,这只不过是例行节目。说到底,宗教形态的差异(排他性宗教vs.非排他性宗教)导致了认知和行为的差异。如此大的差异提醒我们必须把“改教”这一概念放到具体的文化脉络中来把握。在这方面,人类学家走在了社会学家前面。焦大卫根据他在台湾的田野经验,指出中国人的改教具有累加性(additivity)、制约性(conditionality)和众神可交替性(pantheon interchangeability)。累加性指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包容所有宗教,多多益善。因此中国人表面上的改教非常容易。但是他们大多是在不放弃原有信仰的前提下接纳新的宗教,很少有人因改教而改变原有世界观的情形。人们之所以接受某个教派(包括基督教)的教义是因为这些训导与他们既有的世界观相通,新的信仰受制于已有的智慧,这就是所谓的制约性。另外,国人喜欢把各种宗教进行同质化的类比,比如把基督教的上帝理解为教派里的无生老母,把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等同为道教的老子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众神可交替性”(Jordan,1993)。这样的改教,既无损于改信者原有的认知体系,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网络。
焦大卫的研究似乎可以成为“中国式改教”研究的起点,不过改教绝非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宗教行动。在中国,香客多过信徒,进香也远比改教更为普遍和重要。香火是信众对神明进行参拜时所必用的物品,也是一个神祇灵力的象征。一座庙香火越鼎盛,表明该庙神祇越灵验,信众越多,资源越丰富。进香是指信众到外地的庙宇参拜,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组团前往,或者由当地庙方发起。早在唐代,大规模的进香活动便已出现(Naquin & Yu,1992:11)。清末民初,每年到华北妙峰山朝拜碧霞元君的香客摩肩接踵(吴效群,2006)。在台湾,每年大约有五百万人,也即将近台湾地区总人口的20%,到供奉妈祖的北港朝天宫进香(Sangren,2000)。2006年,前往普陀山朝圣和旅游的人数超过三百万。所有这些都说明进香在当代中国仍然盛行。
在朝圣过程中,香客们可以公开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神迹。桑格瑞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参加进香基本上就是一个分享灵验故事的聚会,香客们相互交换自己的神奇体验,开启友好的交谈。通过这些交谈,香客们找到对自己宗教体验有共鸣的听众,并从中学习别人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换句话说,进香为朝圣者提供了一个公共场合来确认他们信仰的正确性,以及他们生活的宗教意义”(Sangren,2000:91)。这些香客以前素不相识,神的灵验让他们共同参与到进香活动中。这样的见证当然能增强彼此对神灵的信心。
进香路上的苦行表演同样能强化香客的信仰和增进进香活动的宗教氛围。在描述妙峰山的朝圣者时,韩书瑞写道,“打扮成悔罪者的香客身穿囚衣,脖子上套着枷铐,自囚在路边募捐还愿,用来修复当地一座庙;还有的身背马鞍,像马一样匍匐上山,一言不发,以感谢神灵治愈了其亲人的疾病……他们以极端的行为显示出理想信徒所具有的态度:真诚、奉献、坚忍、全心全意和感恩戴德”(Naquin,1992:362)。肉体上的痛苦成为菩萨灵验最有力的证据。
从宗教市场理论的视角来看,进香是一项有利于减少宗教产品风险的制度安排,见证和苦行者都出于纯粹的宗教动机,不带有丝毫功利目的,这自然最好地证明了神灵的灵验。当宗教集会被中国历代官府严厉管制时,进香成为最重要的公共宗教活动形式,扮演了与西方堂会相类似的角色。桑格瑞评论道:“中国的佛教在维持仪式和教义上的统一性时,不是依靠正式的组织和官僚机构的约束,而是通过非正式的制度,比如游方和尚和虔诚信徒的进香”(Sangren,1987:123)。遗憾的是,尽管人类学家早就认识到进香的重要性,社会学家却对此少有研究。
在此做一简单的总结。在微观层次上,委身和改教在基督宗教传统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在中国社会中似有似无。在传统中国,香客多过信徒。我们应关注中国社会中的委身和改教,但同时也不要忽略“诚”的概念和进香。
四、中观层次:教派—教会理论
在中观层次上,宗教市场理论对宗教组织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其基础是“教派—教会理论”(sect-church theory)。“教派—教会”理论聚焦于宗教团体与外部社会的关系(Johnson,1963),教派是与主流社会对立的宗教团体,教会则与外部社会关系融洽。该理论认为,教派在其成立之初往往剑走偏锋,教义激进,因此与外部社会存在很大的张力(tension)。因为张力有助于减少“搭便车者”从而能更好地提供宗教服务,所以那些与世俗社会关系紧张的教派往往成长得最快(Iannaccone,1994)。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组织规模的扩大,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世代更替(succession of generations),教派会逐渐修正其教义,变得温和(Niebuhr,1929)。但是教会化的过程往往也是组织衰落的过程。为了维持其活力,有些教会也会主动提高与外部社会的张力,变得像教派(Finke & Stark,2001)。
中国不缺少与外部社会关系紧张的教派。汉末的太平道可以被视为中国教派传统的源头(马西沙、韩秉方,1992)。到了元代,白莲教渐成气候并参与了元末起义,“白莲教”也因此成为中国异端宗教运动的代名词(Naquin,1985;ter Haar,1992)。更多的教派在明代涌现出来,大多信仰无生老母,认为末劫将至,只有入教才能避劫。这些教派通过制作宝卷来宣扬教义,强调个人的救赎,也各自拥有祖师传承(Overmyer,1999)。
明政府把教派视为“邪教”并严厉镇压,清政府继续了这一政策。然而,“即使清代实行了严酷的镇压,教派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而是稳定地增长”(Seiwert,2003:445)。西谚云,夜猫的惨叫不是预示着一只死猫的出现,而是一群小猫的诞生,同样,对某个教派的镇压不会让教派灭绝,而是直接导致众多更小教派的出现。在教首被斩以后,一个教派往往分化成若干小教派,这就直接导致教派在数量上的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官府压制的确对中国的教派运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教派运动很难完成向教会的转变。在欧洲和日本,由于长期分裂,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因此被某个世俗权力压制的教派有可能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承认和庇护,“路德能够得到黑森的菲力普的支持,而亲鸾的净土真宗能在大阪建立自己的据点,并受到后来建立幕府统治的德川家康的敬奉和礼遇”(欧大年,1986:75)。
中国政治上长期的大一统格局让教派无处遁身,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教派一旦被禁,它们或者转为秘密,或者分裂成若干小团体。转为地下意味着这些教派始终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教会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频繁的分裂则让中国的教派运动难以建立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扩大规模。需要指出的是,稳定和制度化的结构是“教派—教会转化”的关键之一。同时,官府的镇压让知识分子很少参与教派运动,因此教派的领导者大多是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缺乏教育,对各宗教的教义一知半解,很难把握系统的神学理论,更不用说进行教义创新,这无异于从智识上将教派运动斩首(欧大年,1986:75-78)。当教义的转化和提升受到阻碍时,教派向教会的转化也无从谈起。因此,在传统中国,教派向教会转化的情况即使有也非常罕见。我们必须对“教派—教会”理论进行修正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教派发展(Lu & Lang,2006)。
除了缺少从教派向教会的变迁,另一个社会事实也让“教派—教会”理论在中国社会的运用大打折扣,那就是教派在中国社会的宗教份额中只占很少一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这与美国社会教派和宗派占主流的情况有所不同。很多学者在描绘中国宗教图景的时候或者把教派忽略不计,或者把它视为民间宗教的一部分(Overmyer,1987)。从统计的角度看,教派在华人社会的确影响甚微。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显示,在1984年,仅有1.7%的被调查者信仰无生老母(Lu et al.,2008)。因为无生老母是很多教派信仰的主神,所以这基本反映了台湾地区当时教派信仰者的规模。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宗教组织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教派。如下所述,香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分灵—分香体系是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组织。
由于官府的管制,组织严密的宗教组织在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多见。进香组织及其网络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大多数神灵,无论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都通过分灵或分香的方式扩展其影响。如果某庙所供奉的神祇被认为很灵验,就会有人到这庙里来分香,在外地另建新庙时,新庙即为原庙的分香庙。原庙为祖庙,分香庙为子庙。子庙也可以通过分香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子庙。通常分出去的庙,都会固定每隔一段时间让神像回到祖庙“谒祖”,它们从祖庙的香炉中勺取香灰带回,然后将其掺到自己的香炉中,这意味着从祖庙那里补充了新的灵力。通过这些活动和仪式,祖庙与子庙建立起经常的联系。众子庙之间存在着竞争,它们竞相赠送礼物给祖庙,这些礼物通常“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并制成匾额悬挂在庙里的墙壁上”(Dean,1998:54)。
“分香”制度使很多神祇及其庙宇以细胞裂变的方式扩展,其直接后果就是出现一些区域性的民间宗教组织,比如祭祀圈和信仰圈。前者指的是义务性的宗教祭祀团体,后者则是志愿性的、以某一神祇和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的区域性宗教组织(林美容,2003)。神明会、分香子庙及进香活动是构成这些民间宗教组织的主要要素。需要注意的是,与组织结构严密的教派不同,这些地方上的区域性祭祀团体结构松散,属于临时性的组织,不具备科层结构。这些组织在祭祀的时候集合起来,置办供物、搭建戏棚戏台、延请戏班子娱神、祭祀神灵等等(Sangren,1987:55-56)。这些组织的另一项任务是抬着神像去祖庙进香,增加所拜神灵的灵力。在完成祭祀活动后,这些团体大多解散或者负责处理一些如灌溉之类的世俗事务(Dean,1998)。
除了这些区域性的民间宗教组织,传统中国还存在一些影响巨大全国性的进香网络。很多名山成为宗教圣地和进香中心,它们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紧密。比如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是观音信仰的圣地,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进香中心,九华山则是参拜地藏菩萨的圣地。道教方面,除了五岳,华北妙峰山是碧霞元君的圣地,华南湄洲则是有名的妈祖进香中心。这些圣地大多地处偏远,为了方便香客,一些庙宇制作大量的导游图,标明进香路线,沿途的风景名胜、食宿情况和风土人情(Brook,1988)。
“教派—教会”理论是宗教社会学探讨宗教组织的影响最大的理论,但是,在传统中国的宗教图景中,高度科层化的教派和教会从未成为宗教组织的主流。如果我们还继续沿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宗教组织,那么我们将对很多重要的现象视而不见。幸运的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宗教组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传统的分灵—分香体系的存在可以给宗教社会学带来何种理论启示?这些结构松散的组织在现代社会中会有何种演变?
五、宏观层次:宗教市场与管制
在宏观的层面上,宗教市场理论探讨了管制对宗教活力的影响。管制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扶持(subsidy)和压制(repression)(Finke,1997)。宗教市场论者认为管制使宗教衰落,竞争让宗教充满活力(Finke & Stark,1988),比如在西欧,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扶持官方教会,试图维护其垄断地位。因为教牧人员的工资来自国家,同信众无关,所以他们非常懒惰。同缺乏活力的国营企业一样,官办的西欧教会也走向衰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宗教市场,由于美国比较好地贯彻了去管制化政策,自由的市场竞争使宗教团体非常有活力。因为教牧人员的收入来自信徒而非政府,所以这些神职人员非常用心地去经营自己的教区,提供有效的宗教服务。尽管有些宗教团体在竞争中失败,但美国的宗教在总体上非常兴盛。不过管制与宗教活力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两者关系不大,甚至是负相关(Chaves & Gorski,2001)。
管制与宗教活力之关系的争论已很深入,但讨论的范围也变得狭窄,所讨论的对象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洲的宗教市场(Froese,2004)。传统中国世俗政权进行宗教管理的复杂性则可以拓宽对宗教管制的理解。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杨庆堃详细地描述了封建时代官府对宗教进行管制的情形(Yang,1961)。首先,王权力图表明自身对超自然力量的优越性和掌控。神灵系统与世俗政府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因此政府官员对神格较低的鬼神拥有并且可以行使上级的权利。其次,为了避免政治反叛利用对天象的解释来动员群众,世俗政府垄断了祭天仪式以及对天象的解释,并制定了相关的严刑峻法。第三,政府对寺观庵院和僧道进行行政管理,包括核准寺观庵院的建立以及度牒的颁发和管理。最后,世俗权力排斥和压迫异端,防备那些可能发展为强大的组织性势力的任何宗教团体。总之,作为统治集团的儒家官员总是企图系统地控制宗教事务来强化既有的权力结构。
东西方管制的差异部分导致了宗教形态的差异。在欧洲,天主教曾长期占统治地位,世俗权力管制宗教主要是镇压异端、强化天主教在宗教上的垄断地位;但传统中国对宗教的管制多出于政治动机而非宗教动机,其目的是维持多教平衡而不是一教独大。其结果是西方社会一神教占主导,东方则是多元宗教共存。一神教好比专卖店,而多神教则类似超级市场。由于基督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垄断地位,人们对其他神灵或宗教的崇拜被视为异端,因此宗教市场理论强调的诸神竞争基本不存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多元宗教和数量众多的神灵则为研究诸神的诞生和竞争提供了广泛的素材,这也是未来宗教社会学在理论上进行突破的着力点之一(Lang,2004)。
东西方管制的差异也是造成不同宗教心态的原因之一。对天主教垄断地位的维护助长了排他主义的流行,各宗教团体都认为只有自己完全垄断了真理,所有其他宗教都是错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权强调和而不同,禁止宗教组织发展出具有排他性的理论和信仰。为了达成宗教和谐,世俗政权默认甚至支持三教合一的主张,认为所有宗教皆有其善的一面,在表面差异的背后,各宗教实质上基本相同,都是道的体现。这样一来,企图统合各教的综摄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Lang & Lu,2004)。简言之,排他主义和综摄主义并不完全是宗教自身发展的结果,它们也受到外在力量比如宗教管制的影响。
最后,传统中国社会对宗教的管制也部分影响到宗教的组织形式。因为儒家政权担心宗教团体可能会成为反叛的工具,所以始终对宗教组织的规模和构成加以防范。从10世纪始至民国时代,政府以核发度牒的形式控制僧道的规模。《大清律》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籫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主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沈之奇,2000)。这些措施阻碍了佛教和道教发展成类似罗马天主教的、高度科层化和制度化的宗教组织。与此同时,由于民间宗教不需要神职人员,不需要大笔投资建设庙宇道观,也不要求信众定期聚会,因此在政治上相对安全。因为政治风险小,所以地方庙宇和以分灵体系为主体的民间宗教在传统中国的宗教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不过,随着宗教管制的解除,台湾各宗教迅速教团化。佛教开始模仿基督教建立组织严密的教团;民间宗教的庙宇也逐渐成为法人社团,编写经书、组织信众聚会读经;一些民间宗教的从业者,比如乩童,开始设帐授徒,成为制度化的新兴宗教的创立者。总之,台湾地区的宗教解禁直接导致了宗教组织形态的变迁,聚会型宗教日渐兴盛(Lu et al.,2008)。
六、讨论与结论
宗教社会学在草创之初曾有恢宏的气度。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著作本质上是跨文化比较研究,视野远及印度和中国。涂尔干分析的重点之一是原始宗教,比如澳洲的土著宗教。但二战之后,宗教社会学的路越走越窄,格局也越来越小,与主流社会学界绝缘并被孤立(isolated and insulated)。到了上世纪80年代,特纳感慨到,宗教社会学实际上沦为“基督宗教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Christianity)(Turner,1983:5)。20年过去了,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美国最主要的两个宗教社会学刊物《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和《科学研究宗教学刊》(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在1996-2002发表的有关亚洲宗教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少,宗教社会学研究仍然过分偏重西方社会中的宗教(Lang,2004)。
作为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新范式,宗教市场理论逻辑严密,论证细致,而且能给经验研究提供很好的思路,但是如斯达克自己所言,理论和理论家不是用来膜拜的,而是被超越的对象。斯达克本人从不掩饰他对经典社会理论家的轻蔑和构建“真正”理论的雄心(Stark,1997)。在他看来,经典理论家的缺陷不在于他们的论述错了,而在于他们永远正确。斯达克深受波普尔影响,认为真正的理论应该是可以而且必须能被证伪的,理论必须有明确的解释边界和限制条件,一旦越界便不再成立。
宗教市场理论同样也有自己的解释边界。斯达克坦承其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排他性宗教。如果我们把这套理论不假思索地运用到华人社会的非他性宗教,那么势必会出现桔淮北而枳的情形。非排他性宗教有自身的逻辑和重点。具体说来,在微观层次上,宗教委身和改教一直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但在非排他性宗教占主流的华人社会,这两个概念可有可无。在中观层次上,教派—教会理论可以延伸到中国,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教派在华人宗教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小,远不及儒道佛和民间宗教。中国社会中典型的宗教组织是祭祀圈以及庙会、香会等草根组织,而不是教派。在宏观层次上,东西方在宗教管制的动机、形态和后果上存在很大差异。宗教市场理论基本忽略了这些丰富性,只是关注政府如何促成宗教垄断这一种管制方式。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以上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宗教市场理论,不如说是针对二战以来的宗教社会学。我无意强调中国宗教的“文化特异性”(方文,2008),但我的确认为研究华人社会的非排他性宗教有助于摆脱宗教社会学中存在的基督宗教中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