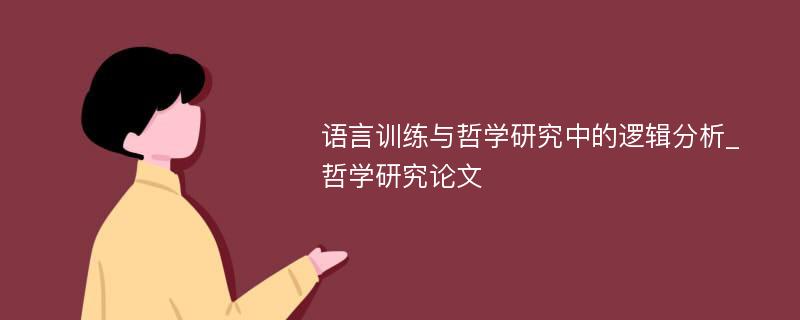
哲学研究中的语言和逻辑分析训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方法的重要性
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凡事应讲究一个方法。方法对头,做事可能得心应手,方法不对,则可能事倍而功半。做学问应不应该讲究方法?搞哲学研究应不应当在方法上专门下一番功夫?依我的经验,答案是肯定的。
应当预先声明,高度重视方法并不意味着盲目崇拜方法,以为方法万能。不甚确切地说,方法类似使事情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良好的训练方法并不能使每一个运动员都成为世界冠军,正确的学习和思维习惯并不能使哲学研究者成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大思想家。方法可以使人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在许多成功者身上,都可以看出良好的方法和训练的痕迹。对优秀的思想者和学问家作精心分析,往往可以发现他们无非有一样或几样看家本领,解决某一类问题对他们而言是拿手好戏,方法论的训练使他们的思想和个性打上了鲜明的特征。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是工具,对于做学问的人而言,就是思维方法、思维习惯,以及某种特殊的知识技能,它要靠自觉地学习和刻苦的训练才能得到。
对哲学研究而言,有许多工具性的方法和知识是必备的,或者说是多多益善,比如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历史知识,等等,但与哲学这门学科的内在特性最相关的,我认为是语言和逻辑分析的能力。
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因为人们早就知道,思考和写作离不开正确使用语言,使得论证和表达符合逻辑。我们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可以看到,斯大林建议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应“包括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来检查措词的确切性。”我现在想强调,哲学研究对于语言和逻辑分析素养的要求,应超过一般学术或文化工作对它们的要求。
哲学不是经验科学,对经验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的能力和手段,对于哲学家而言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哲学以研究人的思维为己任,哲学的研究不是结论和经验事实之间比照的问题,多半是一个表达的问题。语言和逻辑分析的重要性,自哲学诞生起就一直备受关注,到了20世纪更成了中心话题。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实质上就是语言和逻辑分析法,他在交谈中对于对方关于“正义”、“美德”的观点不断发出诘问,以期归纳出正确的定义。罗素曾讲过,许许多多哲学问题,在分析和澄清之后可以发现,它们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逻辑问题。此话可能说得有些片面和偏激,但聪明人不会急于去指出和批评其片面偏激处,而是体察其合理和有启发性的一面。
二、两个例子
也许有人会说:你是以研究罗素哲学思想起家,以研究西方分析哲学为专长,所以才鼓吹语言与逻辑分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果关系应该颠倒过来说才对。恰恰是意识到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长期争论而毫无结果,究其原因无非是问题本属词句之争,双方在事实、立场、规范方面并无对立和分歧,才促使我重视语言和逻辑的分析。
有两个哲学争论的例子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对它们的思考发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时我正在考虑自己的专业方向。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从政治层面上说,康生等人组织对主张“合二而一”的哲学家杨献珍及其支持者批判和围剿,将他们的观点打成“修正主义理论”,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其间是非曲直,一清二楚,不容置疑。但在学理层面,不少哲学工作者仍想弄清楚,究竟是“一分为二”对,还是“合二而一”对。许多人认为这种争论不但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意义重大的,他们挖空心思、竭尽全力为自己的主张搜罗证据。但我在仔细分析各方的论点论据之后发现,双方的对立只涉及表达和词句,他们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并无实质分歧。
主张“一分为二”的人气势汹汹地质问:对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是斗争还是妥协,该“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而对立面则不甘示弱,他们的反诘也相当凌厉:台湾应回到祖国怀抱,宝岛与大陆的关系,应“合二而一”,还是“一分为二”?主张“合二而一”的人以化学为例说,氧和氢化合生成水,是“合二而一”的典型事例,而对方则反击说,这个化合过程是有条件的,即使考察常态之下的水,从微观层次上看,氢氧粒子之间的对立、排斥倾向始终存在。
我断然认为,以上争论是无谓之争。争论双方对于是否应当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台湾是否应当回归,立场完全一致,对于氢氧的化合分解过程,他们承认化学提供的一切知识。争论只出现于对同一事实、过程某个倾向、侧面的强调。论战者都是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原理的坚定信奉者,分歧仅在于这个原理应当表述为“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我认定,与自然科学的争论相反,这样的争论注定没有结果。事实果然如此,事实也只能如此。
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有一篇文章在重申对于马列主义信念的同时,也顺带重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世上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并由此推论说,马列主义最终也是要灭亡的。有位作者认为这么说十分大逆不道,著文批判,这当然是可以的,但他作了下面这样的论证:假使马克思主义有一天真会灭亡,那么马克思关于“事物有发生、发展、灭亡过程”的观点自然也会灭亡,这样一来,说任何事物都必然消灭的结论也就不成立了。作者自以为作了一个巧妙的论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任何懂得语义学悖论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论证是无效的,当辩证法断言“一切事物皆会消亡”时,断言本身比所断定的事物高了一个层次,如果一定要把这个断言理解成可以自返,那么就会出现悖论。
我写了两篇文章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详尽分析,但编辑们对我的论证方式完全不理解。虽然人们思想十分解放,但那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于一种全新的理路,对于脱离旧框架的新话语方式,他们仍然是隔膜的。照他们的思路,从唯物辩证法的公理出发作推导,一定能在对立的观点中判定出对错,结论不能是无意义,或出现了逻辑悖论。
三、获得方法需要训练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你所强调的无非是,研究哲学应该重视语言和逻辑问题,不要在这方面犯错误,这当然不错,但未免有老生常谈之嫌,因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谁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和逻辑知识呢?重申应在这方面引起注意,有多少新意呢?
我想说的是,凭朴素的理解和直观,固然可以发现一般的语言或逻辑上的毛病,但要洞察某些复杂的哲学论争问题的关键不是别的,而仅仅在语言和逻辑方面,要有把握地指出这一点,有说服力地证明这一点,一般的常识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专门的、长期的训练,需要在语言哲学、逻辑哲学方面狠下功夫,虽然最终目的并不是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20世纪的语言和逻辑分析,有相当丰富的内涵,相当精巧的技术,相当精彩的例证。比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人誉为“哲学的典范”,摩尔对语言意义中细微差别的敏感,维特根斯坦和赖尔对于“哲学中的语言病”的诊断,奥斯汀和塞尔对语言执行不同行为功能的精彩描述和归类,就不是可以通过浮泛的了解能掌握其方法中精髓的。已故的美籍华裔知名哲学家傅伟勋在其回顾总结自己学术历程的《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一文中说,他虽然只对人的存在这一根本哲学问题感兴趣,但因为深知“哲学问题探索法”的重要,“明明知道自己不会变成逻辑专家或解析哲学专家,却强迫自己逐渐转向现代哲学解析的研究”。在备受中国学界重视的当代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罗蒂、阿佩尔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分析哲学的熟悉程度,虽然他们的贡献并不在分析哲学方面,而且还多少表现出反对分析哲学的倾向。
如果要谈我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我承认,虽然自己写了不少东西,但其中有意思的并不多,其中尚值得一看的,即自以为有点独到见解的,都与在语言逻辑分析方面下过的功夫有关。让我以有关康德哲学思想两个论点为例来说明一下。
在《“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书中,我讨论了康德关于“存在不是谓词”这一命题,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关系到本体论和上帝存在的证明。当代哲学家斯特劳森和皮尔斯对康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我则力图捍卫康德的立场,由于批评者设置的诘难十分精致复杂,而且是在语言和逻辑层面上展开,因此,我不得不同样在此层面上作细致的厘清工作。具体论证无法在这里重述,我只想说,没有较为充分的语言和逻辑分析的训练,是无法进入这个问题的。
在《新儒家与康德——评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和超越》一文(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中,我提出,牟宗三在自由意志、智的直觉、物自身三个重要问题上批评康德,证明中国儒家思想高明于西方哲学,论证理由不充足,批判和超越的失败是并未理解康德所面对的难点,牟氏实际上是回避和绕开了问题,却自以为解决了问题。我的看法是,每当康德在某个终极性问题面前停下来,因为无法证明而将其视为设准时,牟宗三都自称可以证明,而其反复使用的证据都是仁爱心等经验层面上可见的东西,他断言这是所能证明的东西的直接呈现,但实际上二者并无逻辑联系。我自己十分明白,是语言和逻辑分析的训练使我能够发现牟氏论证中的问题,并以清晰有力的语言证明其阙失之处。
我决不认为仅仅依靠语言和逻辑分析就可以在哲学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但我确实常常感到,能熟练地运用这种分析,犹如手中有一件锐利武器,帮助我见别人之未见,表述自己的见解更自信、更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