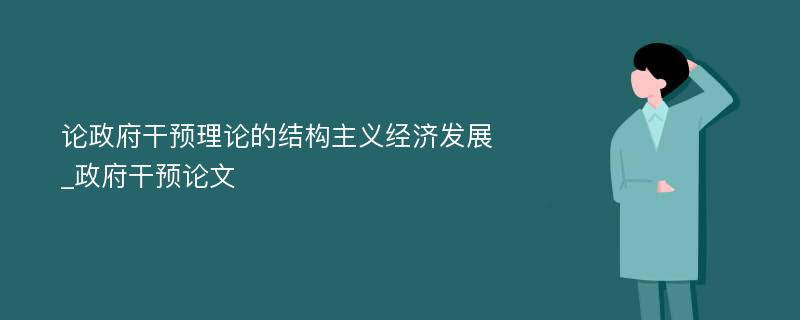
关于政府干预理论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思路论文,理论论文,政府干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40~60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一直是西方发展经济学舞台上的主角。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确立新古典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对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其主要锋芒指向后者的政府干预理论。他们的主要论点是:结构主义理论中隐含了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无限能力的假设;政府干预为寻租打开了广泛的空间,与政府干预相伴随的是广泛的贪污、行贿、受贿等活动,由此造成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糕;外向型经济可使政府不容易助长寻租或直接非生产性寻利(directly-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以下简称DUP)行为;为了纠正政府干预造成的扭曲,必须“矫正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等等。面对新古典主义者的攻击,结构主义者在70年代大都保持沉默,但自80年代初开始,他们系统地给予了回击。结构主义者正是在反驳新古典主义者上述论点的基础上,从4个方面系统地推进了自己的政府干预理论。
一、批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效率观点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一向认为,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市场失效是政府实行干预的前提,而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反对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其依据是他们关于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调节足以带来效率的推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结构主义者在推进其政府干预理论时,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新古典理论中的市场效率命题。
W.A.刘易斯指出,价格并不等于实际社会成本,这一点无论在穷国或富国都大致一样。新古典理论的价格形成学说之所以受到攻击的原因就在于,即使价格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它们也可能是不均等的。他提到了价格未能促成均衡的例证,如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贸易条件难以被接受,因为穷国的热带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的价格所反映的是可供选择的价值而不是“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的价格;又如在“增长极”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该“增长极”会因为资源更多地向增长中心配置而使其他地方的增长潜力遭到破坏,造成“增长极”周边地区资源在总量上与“增长极”相同但产出却更少的后果。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家在他们进行思考时所不能忽略的非经济因素就是政府行为。尽管政府支出在穷国的国民收入中占较小的份额,但穷国中的政府更紧密地同现代部门搅和在一起”;“要想理解任何经济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就必须对政府会作出何种反应进行评估”;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运作得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率。于是,政府就总是被请求出面以矫正市场缺陷和市场不均衡”。(注:Lewis,W.A.,1984,"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4,No.1,p.4.)
J.M.劳回应了T.W.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对结构主义者的抨击。他指出,舒尔茨有关传统农业“虽然穷但却仍然有效率”的命题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更为基本的假设,这就是:明晰的和隐含的市场的存在能确保所有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因此不存在任何剩余劳动。舒尔茨实际上认为价格信号的配置作用非常有效,以至于它甚至决定了政府在促进增长的公共投资计划中的优先顺序;如果价格太低,政府将不会在扩充基础设施和从事提高产出的研究方面作出足够的努力。对此劳作出了反驳: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投资不足的局面并非价格太低所致,而是某些强有力的政治因素在农业及其相关政策上得以体现的结果。他提到,印度大米产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较低,大米研究试验区的产出水平也偏低,这些现象反映了这类地区的政治—结构条件以及这类因素在这个国家中的政治权重的大小,而不是低价格的影响。他还对舒尔茨关于更高的价格激励能唤起人们作出反应的说法给予了回击。他指出,舒尔茨实际上抹煞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与发达国家的农业企业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巨大差异,有关农业生产中价格激励作用的历史的和经验的分析,均未能支持舒尔茨等“价格机制主义者”(price mechanists)的论点。舒尔茨等人开出的用高价格来促使农业摆脱停滞的药方,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怀疑。他列举了两点理由:其一,发展中国家“以佃农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也许会‘逆向地’对贸易条件的改善作出反应”;其二,“该药方没有考虑到公共投资往往在农业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这类投资“可能会通过强化农业中的二元结构的方式使增长减缓”。(注:Lao J.M.,1986," Agriculture in Recent Development Theory"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une,Vol.22,No.1,p.60.)
P.斯特里顿从两个方面反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效率观点:第一,批评了新古典主义者倡导的“矫正价格”的说法。他赞成把“矫正价格”这一概念区分为“使价格得到矫正”(setting prices right)以及“让价格逐渐得到矫正而政府无所作为”(letting prices come right from state inaction)这样两种含义,以消除在这一概念理解上的歧义。他反击了“矫正价格”本身至少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的说法。在他看来,即便价格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公共部门的互补性的行动与之配合,其结果也只会是低效率的或反生产性的(counterproductive),价格只有在政府采取互补性行动的条件下才能对供求产生影响。他写道,对于东亚经济的成功来说,“‘矫正价格’不是主要的秘方,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充足的秘方”。(注:Streeton,P.,1993," Markets and States:Against Minimalism" ,in World Development,Vol.21,No.8,p.1286.)第二,对市场具有效率的一般性结论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自由市场是既可以行善又可以从恶的中性制度。他赞同J.罗宾逊关于“无形的手”也能以窒息的方式发生作用的说法,认为应当考虑在什么条件下市场是有效的,什么条件得以满足后市场能有效地运作,使之能够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H.夏皮罗和L.泰勒写道,尽管价格也许能为市场变动提供足够的信号,但是价格机制却不能为产业政策提供指导,也不能依赖价格机制来诱使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源实现转移。政府干预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可以通过保护、补贴、廉价信贷等政府干预方式,为投资者提供资助,并通过直接投资来突破关键性的瓶颈。他们指出,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取消扭曲将提高帕累托意义上的市场效率,进而导致更好的宏观经济绩效,关于这一说法人们很难找到坚实的依据。他们认为,成功的工业化同扭曲并行不悖,但沿着这一方向所作的努力不应当被夸大。尽管在长期内大幅度地偏离市场信号的成本是高昂的,但在短期内这种偏离却可以激励企业家精神并促进生产率增长。他们引述了由位于赫尔辛基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对18个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与调节计划所做的研究(L.泰勒是该研究报告的评阅人),结果显示,部分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其价格改革和贸易状况的改善与包括总需求操作、出口补贴、公共投资以及易货贸易等在内的政府干预相一致,而其他仅仅实行了价格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却是悲惨的结果。这些国家主张“国家最低限度干预论”(state minimalism)的观点,“忽略了当今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与其他一些穷国)所面临的不利的生态条件、出口数量和价格暴跌以及政治动乱这些客观困难,同时它还忽略了工业化并不是在完全的自由市场体制下走向繁荣这一历史事实”。(注:Shapiro,H.& Taylor,L.,1990,The State and Industrial Strategy,in World Development,Vol.18,No.6,p.872.)
P.巴丹也指出,在经济调节过程中,仅凭“矫正价格”是不够的;在实际情况下,调节的结果取决于一国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此外,新古典主义者开出的“矫正价格”和促使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靠拢的处方,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需要的,但对于成功的工业化来说,该处方不是一项必要条件,而且肯定不是一项充分条件。他还认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实际上沿袭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他不赞同D.诺思等人在解释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夸大相对价格作用的说法。这种说法是:相对价格诱发了产权的演进,使之有利于更为昂贵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从而激活了历史上制度变迁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改变劳动对土地的相对价格的人口变动则产生了一种激励,促使人们重新界定土地产权和重新安排劳动关系。巴丹指出,人口、市场条件和相对价格变动不足以解释各国之间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差异;“相对价格变动也许最多只能改变不同阶级的集体行动的成本和收益(为政治上的创业者创造新的机会),但却不能预先确定阶级力量的均衡,也不能预先确定社会冲突的后果”。(注:Bardhan,P.(ed.),1989,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rarian Institu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8.)
二、对新古典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批评
如果说新古典主义者抨击结构主义者的主要理由,在于政府干预造成了“政府失效”的话,那么,结构主义者则把回击新古典主义者的主攻方向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上。H.夏皮罗和L.泰勒指出,由于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至少设定了市场能够发挥功能的假定,并预设了政府只需起最低限度的“守夜人”作用,加上传统新古典主义者素来就有在经济分析中把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分隔开来的传统,所以国家作为一个明显的行动者在有关经济发展的分析中被忽略了,他们并没有构想出一个国家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新古典主义者试图通过把政府政策描述为个人在政治领域中的最优化行为的结果,将政府政策内生化到一般均衡体系之中。这一尝试的结果是初步搭起了包括“公共选择”、“寻租”、“DUP活动”等分析思路在内的新古典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夏皮罗和泰勒看来,在这一框架中,国家不完善假设取代了市场不完善假设,新古典主义者所要做的,只是力图把国家作用的问题限定在市场和国家这两个有着根本缺陷的恶魔之间作出选择的范围之内。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新古典经济学特有的将经济与政治视为两个不同领域的职业倾向。经济与政治相分离,使得新古典经济学陷于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任何政治上的安排不可能在国家的行为不受到寻租和DUP活动影响的情况下作出;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国家在脱离经济的背景下采取行动。夏皮罗和泰勒对此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批评:第一,造成市场扭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寻租和DUP活动之外,还包括跨国公司的存在、某些国际市场上强大的寡头垄断的存在、接近技术的渠道不畅通,以及同自由贸易假定相矛盾等其他因素,即使自由贸易体制有更大的开放性,也不能确保出口促进战略一定比进口替代战略更少地受DUP活动的影响;第二,从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国往往采用先进口替代然后转为出口促进的战略,相反,小国则更容易实行对外贸易,因为小国若实行先进口替代然后转为出口促进的战略,其成效并不十分理想。
P.巴丹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国家学说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只是被动地对不同利益集团和游说者的寻租行为及DUP活动作出反应。新古典主义者强调的仅仅在于同这类政治过程相关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而这种浪费被度量为对竞争性均衡的偏离,即某种既不存在任何信息和交易也无需在任何政治成本环境中所假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把国家仅仅看作是一个各个集团相互竞争的竞技场,而不是把国家本身视为在同其他各种集团进行冲突与协作的错综复杂的博弈中的一个有策略的行动者”(注:Bardhan,P.,1988,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Economies,in H.Chenery & T.N.Srinivasan(ed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I,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B.V.,pp.64~65.)。他相信,“在缺乏一种完善的国家理论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政策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注:Bardhan,P.,1984,Land,Labor and Rural Poverty:Essay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viii.)。
P.斯特里顿从三个方面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第一,新古典主义者把寻租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政治现象,并毫无例外地归结为由公共部门的行动所引起的,减少寻租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政府。斯特里顿认为,新古典主义者的上述看法是错误的,至少这些看法缺乏足够的经验例证。事实上,私人部门中的寻租活动同样司空见惯。私人在合同配置中采用分包形式,这一过程中形成租金的方式,同进口配额如出一辙。他提到,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人们“反对公众的共谋”,“用诡计来提价”,以及地主和其他人“在从未播种的土地上收获”,实际上指的就是私人操纵的租金产生的过程。此外,一概将寻租归因为某些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是有片面性的,在一定条件下,压力集团有可能对经济发展起有利的作用。第二,新古典理论有关国家行为的假设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斯特里顿发现,新古典主义者在两个方向上走了极端:在A.C.皮古、A.勒纳、J.廷伯根、J.米德等人的著述中,政府是不会做错事的;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包括新制度学派在内)却坚持认为,政府绝不会做正确的事。在斯特里顿看来,新古典主义者分别从两个极端上作出了关于政府行为的假设,公共部门因而混淆了私人动机和公共部门动机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虽然与私人部门一样,追求私利的行为也会发生,但若认为追求私利是公共部门行动的唯一动机那就很荒唐了。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区别降低到统一的自利层次上,并且将理性行为等同于自利行为,这无助于理解决策过程;再者,自利行为也能以冲动、前后自相矛盾、反复无常、非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三,对主张甩掉政府而听任市场的“国家最低限度干预论”提出了质疑。斯特里顿问道,从极低效率的国家活动转变为高效率的国家活动是否通过一个“最低限度国家”就能实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了使市场正常运转,一个强大的、在某些场合中甚至是扩张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他写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不到‘看不见的手’”(注:Streeton,P.,1993,Markets and States:Against Minimalism,in World Development,Vol.21,No.8,p.1293.);“倘若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迹象的话,它肯定被一只强有力的看得见的胳膊所引导”(注:Streeton,P.,1996,Governance,in M.G.Quibria & J.Malcolm Dowling(eds.),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n Asian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4.)。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些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依赖于在现实中很少存在的诸多条件。亚当·斯密往往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奉为赞成自由放任和“最低限度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威,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斯特里顿看来,斯密捍卫的是特定的自由,而不是一般的自由;他反对的是特定的政府干预(尤其是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府干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干预。斯密认为国家应当承担三个方面的使命,即保护市民使之免遭暴力和侵略,保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使之免于不公正和压迫,以及建立并维护某些公共工程与公共机构。斯特里顿承认,包括新制度学派在内的新古典主义者有关寻租、DUP活动以及公共选择的分析有助于对糟糕的政策作出解释,但他们为了能说明掠夺性的政府的恶行,在对自由市场备加赞颂的同时,再一次通过推理把国家排除在外,进而再一次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作出了划分。
三、关于东亚经济起飞过程中政府干预作用的讨论
H.夏皮罗和L.泰勒指出,新古典主义者将东亚地区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最低限度干预论”的实践者。他们把20世纪60~70年代这一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与仍然在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以便从经验上证明他们“来自于贸易的动态收益”和“由市场自由化所驱动的出口扩张变为有选择的工业化战略”的说法具有合理性。夏皮罗和泰勒对此予以反驳。他们将东亚地区政府成功干预的经验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实行一般指导,而对于厂商对市场作出反应的决策,政府不实行直接的分极化管理;通过咨询过程在生产者和国家之间形成集中信息和把信息有选择地在厂商中传播的反馈机制;国家依据极为优惠的利率为新企业提供风险资本;在那些由国家指定的并且有可能形成规模经济的“冲刺行业”中实行保护并控制执照的发放,以形成进入壁垒;在厂商能够达到绩效标准的前提下采用包括由国家向厂商提供低利率贷款等在内的激励措施;对包括健康与教育在内的广义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把国家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协调延伸到资本形成的过程中等等。他们赞赏韩国政府在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反对新古典理论关于公共工程势必“挤出”私人投资的说法,认为恰恰是公共工程借助于互补作用而“挤进”私人投资,而不是通过推动利率上升来“挤出”私人投资。正是由于各项激励措施的引导以及与公共投资的相互协调,韩国才完成了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韩国民众的识字率以及工程师和受过技术训练的人口比率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韩国的成功就在于政府将正规教育和在职训练调节到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水平。
P.巴丹认为,东亚地区的政府积极干预主义(activism)远远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中性的经济政策的框架。他将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催化作用一般地归纳为推动至关重要的学习过程,抵消外部性造成的影响,政府作为代用品替代已消失的资本市场这三个方面。他发现,东亚地区的政府在实施干预时使用了几种独特的政策工具,包括以微妙而又果断的方式干预资本市场;对信贷配置实行管制(有时甚至以不含糊地撤出贷款的方式相威胁)以推动和融通产业投资;为风险承保并为贷款作担保;建立公共开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鼓励金融市场中新生要素的发展;推动现有厂商提高其技术并向那些在发展目标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重要部门转移。他赞同青木昌彦等人的观点,认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当私人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制度尚处于欠发达状态而且协调(coordination)尚未达到自我强化程度时,东亚地区的政府“创造了以绩效或结果为条件的寻租机会(如通过动员储蓄使创新实现商业化,实行出口‘竞赛’等),对私人代理人所面临的战略性激励措施施加影响,从而促进制度的发展”(注:Bardhan,P.,2001,Distributive Conflicts,Collective Action,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in G.M.Meier & J.E.Stiglitz(eds.),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74~275.)。他还发现,东亚地区政府对整个教育体系的投资,远比个人投资更适合于提高民众的平均绩效水平,这表明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成效,远胜于新古典模型中经常讨论的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此外,巴丹还指出,以往有关政府干预的文献主要探讨了政府干预的程度问题,而从未关注政府干预的质量问题。在他看来,需要理解为什么干预的质量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巨大,即便各国采用相似的政策工具,或在有些情况下干预的程度相似,结果却大相径庭。
P.斯特里顿专门讨论了东亚政府在促成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他认为,迅速的出口自由化只能局限于在原料和在低附加值的行业中获取现成的比较优势。为了获取高附加值行业(这类行业往往是进口替代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现代技术中的比较优势,必须借助于强大的、看得见的政府的资助。
四、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改进政府管理能力的讨论
近十多年来,P.巴丹对政府干预理论的推进主要集中于讨论如何提升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管理能力,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分权化管理。巴丹指出,发展中国家中的政府不是因为太软弱,以至于无法扮演权利和制度捍卫者的角色,就是因为它在自身需求方面掠夺性太强,以至于对权利与制度构成威胁。他承认,“由于缺乏获取地方性信息的渠道,在当地缺乏信誉以及因浪费性寻租过程而易于受到攻击等原因,国家有其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机构的种种局限”;“但国家不应当后退到如古典自由主义所分析的最低限度的作用上;相反,国家(只要它作为一种催化剂发挥作用的话)应当在动员可能使人们参与当地的发展过程中起积极作用”(注:Bardhan,P.,1997,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Development Centre,OECD,p.60.)。他反对把讨论局限于私人市场与集权化官僚体制这两个极端的传统做法,认为需要一种更为精细的国家理论,而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则提供了一条出路,以走出围绕国家与市场这两个极端而展开争论的死胡同。他认为分权化的主要优点,在于使决策权落到掌握信息的地方政府手中,使之拥有在质量上类似于市场机制并优于国家的激励优势;优点还在于地方政府同市场机制一样拥有信息优势,因而使地方政府有时在协调和政策实施方面优于市场;此外,与分权化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对当地事务的责任心,这有利于改进公共服务,并且在管理公共资源方面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避免“公共的悲剧”的发生。他不赞同那种设想在跨政府之间通过围绕地方管辖权展开竞争来吸引处于流动状态的居民,以确保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品的蒂博特模型,认为这个以对公共品的偏好显示为主要假设的新古典模型在穷国是无效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许多公共品具有地方特性,该模型很可能将使用这类公共品的非居民排除在外,进而使偏好显示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引入现实的政治过程、寡头垄断间的竞争以及管辖区之间的外部性等因素,蒂博特模型中的市场效率特征将不复存在。巴丹也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实行分权化体制的两个主要劣势:一是在分权化条件下由腐败引发的成本远远高于集权条件下腐败的成本;二是分权化若不与足够的再分配转移支付相伴随,将使地区间不平等状况加剧,因为资源禀赋充裕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将拉大同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第二,政府的协调能力。在巴丹看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宏观管理中面临“协调失效”(coordination failure)的难题,即一方面社会深层次的冲突往往表现为宏观层面上的低效率及国家干预的不协调;另一方面,比宏观层次更为尖锐的难题是许多穷国在地方社区层次上存在着“制度失效”(institutional failure)。他认为东亚地区的政府通过对私人部门的协调提供促进和互补手段的方式,在解决“协调失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在南亚国家(如印度),整个社会呈现出极度的分割状态,建立起同协调有关的制度显然比东亚地区困难得多。他认为,新古典主义者普遍低估了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层面上进行总协调的困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行政能力低下和政治凝聚力不够),并且低估了在对资本的微观管理中出现的激励和组织难题。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言,资本的微观管理问题也许是太复杂了。第三,反腐败问题。巴丹深知,讨论提升政府管理能力的问题离不开反腐败。他不完全赞同新古典主义者关于腐败是由于实行管制的国家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制度过于繁琐而产生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说服力还不够,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政府干预程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腐败差异。他认为,腐败涉及国家理论中更深层次的问题,而减少腐败的一个途径就是削弱政府官员在对居民们发放许可证、提供补贴或转移支付方面的权力;另一个途径是采取行政方面的改革措施,例如削减政府部门的营利功能,在政府部门内部建立起完善的、鼓励匿名举报腐败行为的程序,允许周期性地查究政府官员来路不明的资产等。他同时强调,不少国家周期性地开展反腐败运动,这类运动的效力因场合不同而不同,重要的是使各种诚信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制度化,内容包括建立独立的公共审计机构,设立由市民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以提供信息和监督,建立对官吏具有某种监控作用的地方巡视官机构,形成强有力的新闻曝光制度等。
P.斯特里顿则主张设计一种决策机构,使之能够兼有分权和中央调控在信息与激励方面的优点。在他看来,国家与市场既相互需要,又彼此削弱。国家借助于过度管制、发放执照和官僚主义的繁琐程序来破坏市场;市场注定要通过贿赂、游说和相互捧场而导致政府腐败。因此,需要一个市民社会(以私人自愿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为主要形式)在国家与市场二者之间形成更为建设性的关系。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对于形成良好的政府管理特别重要,这是因为“信任与相互关系这类投资于市民生活的准则与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被视为有效率的政府和经济进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注:Streeton,P.,1996,Governance,in M.G.Quibria & J.Malcolm Dowling(eds.),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n Asian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y Press,p.28.)。市民社会的各种制度如教会、专业化组织、工联、市民团体、利益集团、媒体等往往是非民主化的,但它们往往能够对国家和市场之间相互削弱与相互倒台的关系起着干预和限制的作用。国家过于软弱或者过于强大,都不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同理,如果私人组织的力量太强大,也会阻碍市民社会的成长,进而导致社会的解体。
五、简要的评价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行干预,这个问题一直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内部持结构主义思路与持新古典主义思路两派学者给予关注和展开论战的焦点。这两个学派之间的长期论战,不仅把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实行干预的理论探讨不断引向深入,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有关国家干预的一般理论的发展。在本文收笔之时,笔者仅就结构主义者对新古典主义理论所作的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思路的政府干预理论本身取得的进展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结构主义者在回击新古典主义者的抨击时,紧紧抓住了新古典理论的薄弱之处。首先,反驳新古典理论认为的价格机制足以实现效率的命题。结构主义者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效”势必导致非均衡这一推论出发,强调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所造成的种种深层次结构因素对发展过程的影响,单靠价格机制的运作难以带来市场效率。在他们看来,“高价格激励”与“矫正价格”不过是把“价格机制带来效率”这一传统命题换了一种说法。价格调节的配置效率之所以存在着局限,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价格配置机制不足以促成包括生产要素、制度及国民经济结构等这类长期的和深层次的结构因素产生变化。正如巴丹所言,在结构主义者所描述的背景中,“通常在新古典文献中强调的配置效率问题往往在重要性上被认为只居于次要地位”。(注:Bardhan,P.,1990,Symposium on the State and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4,No.3,Summer,pp.5~6.)他们还提到,新古典主义者总是强调市场效率,但如果市场运行得太有效率,也会带来问题。斯特里顿写道:“如果仅仅是一个纠正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一任务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但如果由市场传播的信号是建立在土地、其他资产和收入分配极为不均的基础上,那么正是因为市场成功地对这类信号作出了反应才造成了麻烦。”他提到了A.森对印度粮食供给充足时反倒发生饥荒现象所做的分析,由于穷人中某些特定阶层的购买力下降,“在这类条件下,尽管市场在传播信号、形成激励和配置资源方面非常成功,但人们却在忍饥挨饿”(注:Streeton,P.,1993,Markets and States:Against Minimalism,in World Development,Vol.21,No.8,p.1295.)。其次,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政府干预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国家理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的“新古典主义复兴”,使得对于理解市场和国家各自重要性的一些主要差别被混淆,其根源就在于,包括新制度主义者(有时亦被称做“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具有“将个别简单地推及总体”之嫌,即把政治领域的国家行为几乎等同于经济领域的个人最大化行为,因而混淆了个人动机与公共部门动机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种理论尤其难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结构主义者特别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寻租理论文献为例,说明这类文献更能解释政府干预造成的“政府失效”,却不擅长于说明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干预实现了“政府成功”的原因。最后,他还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局限性。结构主义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传统,致使这个学派对国家重要性的承认仅限于如何运用国家权力来履行合同与保护产权,以及如何建立起国家信誉,以便不对这些产权的私人拥有者提出没收要求的狭小视野中。巴丹举例说,在谈到环境资源恶化时,新制度主义者总是推出明晰产权一类的政策建议,但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大多数依赖于公共地等资源,一旦这类资源的产权被明晰化,则如同英国“圈地运动”中发生的情形那样,穷人的状况将更趋恶化。这意味着公共资源的产权私有化只能是对穷人的剥夺,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太多的难题超出了产权层面。可见,当结构主义者涉及产权等与制度相关的问题时,他们的理论视角往往比包括新制度学派在内的新古典主义者广阔得多。
第二,结构主义国家干预理论的新进展。首先,他们对政府干预与规模收益递增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推论。结构主义者针对新古典主义者关于政府干预必然造成“扭曲”进而降低效率的说法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经济发展伴随着的“扭曲”在短期内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这一推论除了考虑到不发达国家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之外,实际上还隐含着有关政府干预同收益递增相互关系的推论。论证收益递增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发展经济学近年来成果颇丰的领域。本文中提到的夏皮罗和泰勒对扭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所做的讨论,同H.B.钱纳里对非均衡和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所作的分析非常近似。H.B.钱纳里认为,在要素市场分割和调节滞后等非均衡现象中潜伏着通过减少瓶颈以及把资源再次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以加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潜力大于发达国家。其次,结构主义者提出了政府干预的质量问题。以往的发展经济学文献要么强调政府干预带来破坏性,要么围绕政府干预在程度上的差异作文章。新一代结构主义者则突出干预的质量问题。巴丹在总结东亚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干预质量的最重要的方面除了外部性之外,还在于选择性。有选择地实行政府干预,可“节省稀缺的管理技能,使政策操作的社会成本能更容易得到准确测算,并且能对成本作出调节,使之对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变动作出反应”(注:Bardhan,P.,1990,Symposium on the State and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4,No.3,Summer,p.6.)。最后,围绕提升发展中国家政府管理能力的问题展开讨论。结构主义思路在这一领域的新发展,除了推进了分权化和反腐败的探讨之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讨论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各级政府间的“协调失效”上。他们把亚洲的政府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处理“协调失效”方面取得成功的“硬国家”(hard state),如韩国;另一类是不那么成功的“软国家”(soft state),如南亚国家。巴丹将南亚地区的政府在分权化管理的协调方面面临的困难归结为收入分配冲突、各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对称、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性等因素。在他看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开放过程中”应当注重提高“其解决冲突和实行妥协的能力”(注:Bardhan,P.,1990,Symposium on the State and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4,No.3,Summer,p.6.),并且注意利用一些地方性的合作制度,使之在“协调失效”方面发挥作用。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仍然在推进“协调失效”的研究方面付诸努力。A.K.杜特和J.罗斯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提到,“近年来跨学科的研究表明,市场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起到协调作用,而市场和国家的本质与国家或市场所能发挥的作用相比更为重要。”(注:Dutt,A.K.& Ros,J.(eds.),2003,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s:Essays in Honor of Lance Taylor,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p.7.)
标签:政府干预论文; 新古典主义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结构主义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