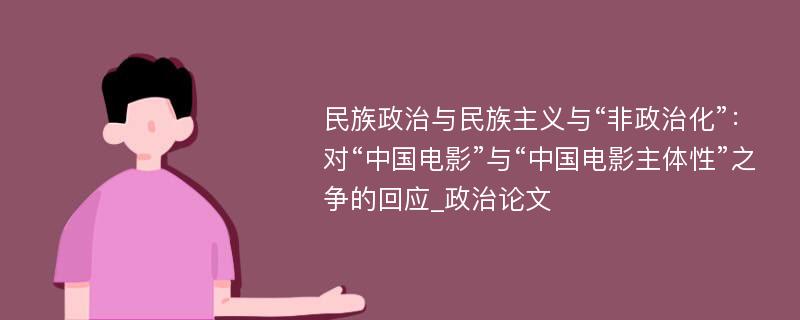
民族性、“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国家主义:对“华语电影”与“中国电影主体性”之争的一个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义论文,政治论文,华语论文,主体性论文,民族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电影》于2014年第四期刊发了戴维斯加州大学鲁晓鹏教授一篇关于“华语电影”与“重写电影史”问题的访谈,由此篇访谈所引发的对于该议题及相关问题的争论,在大陆学界一直持续至今,且有愈辩愈烈之势①。2014年12月18日,争论的部分参与者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②;时隔半年之后的2015年6月20日,辩论现场“移师”复旦③,时值“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国际学会”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众多海外学者也因此契机被“卷入”了这场争论。笔者也因该机会,有幸目睹和见证了这场声势浩大、气氛热烈的辩论。辩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0点大家还意犹未尽,问题面向之复杂、交锋程度之激烈,可见一斑。辩论中虽时有机锋,但笔者感觉由于各种原因,辩者在有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似乎未能有真正的“交手”。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对我们理解这场争论和对“华语电影”这个理论范式的展开是不无帮助的。 华语电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与民族性 由于鲁晓鹏、李道新、石川、孙绍谊等此前发文参与争鸣的学者悉数到场,加之美国学者柏佑铭(Yomi Braester)、王汝杰、李力、萧继薇、肖慧等教授,中国台湾学者唐维敏教授与北师大唐宏峰教授的参与④,更由于华东师大的吕新雨教授携长文《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的加入⑤,使得复旦辩论能在更加丰富的维度上展开,也使得有某些问题逐渐清晰,而另一些问题则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电影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是此前争论的一个焦点,而“中国性”正是此焦点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华语电影是否因其边界的扩展而颠覆了“中国性”呢?讨论首先是由吕新雨文章中所提出的少数民族电影的问题而引入的,而吕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为切入点进入对华语电影的批判,也承接了李道新进入该议题的出发点,即华语电影范式对少数民族电影的拒绝或遗漏。虽然不同社群对“华语”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阐述,但华语作为汉民族的共通母语承载着该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性——这个将语言与民族性相联系的认识却是一个较一致的认知起点⑥。因此,以“华语”为承担的华语电影,因其无法容纳中国其他民族电影,被视为对“统一”的中国和“中国性”提出了挑战。尽管鲁晓鹏在《华语电影概念探微》一文中“修正”了华语电影的概念,将少数民族语言电影纳入华语电影⑦,但这种“值得欢迎”的“修正”由于是“鉴于现实的倒逼和需要,并没有成为‘华语电影’研究的历史观,也没有在其学术理路上获得有效的回响”而继续被质疑⑧。 由于华语电影对“中国性”的“质疑”和“挑战”,它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的产物,体现着西方的意识形态;由是,中国电影的“主体性”问题便呈现出来了。从李道新和吕新雨的表述来看,这种“主体性”可归纳为对“统一”的中国认同,特别是政治认同的维护。然而有趣的是,李和吕对这个“主体性”阐述出两种迥异其趣的认识,并规划出两条性质相左的道路。虽然两者在对华语电影共同批判的“统一战线”中态度上保持着旗帜鲜明的高度一致。 李道新对华语电影的批判首先源自于对“民族—国家”(“国族”)意义上的中国电影的确认。他认为少数民族的母语电影溢出了华语电影的边界,如以“华语”的框架来讨论中国电影,势必会“使国家、地区和社群的身份认同产生迷惑”⑨;由是,已有的“中国电影”的概念不可被“华语电影”所取代,言外之意是,“中国电影”跨越了上述不同母语间的藩篱,是一个有着与中国疆界和国家一致性(中国各民族),甚至超出疆界和国家(海外华语社群)的指认。这其中暗含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中国电影在被视为同质语言的地区试图超越疆界,而另一方面在境内异质语言区域面临被超越的时候恪守疆域的界线。在此,显然国家政治对于民族表述具有某种统摄的力量。 这一点在李道新对于鲁晓鹏提出的所谓的“中国性的崩溃”之说的批判中表现得尤为明确,虽然鲁曾多次著文澄清“崩溃”实乃“裂隙”之误译⑩。李认为陈犀禾等国内学者对华语电影的阐述较鲁晓鹏的论述更具有效性,因为鲁在华语电影中读出的是中国性的“崩溃”,而陈等看到的是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之势(11)。 由此可见,李道新所言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电影,不仅是回到“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更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在中国语境中“统一”和“同一”的合理合法性。那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回到了对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解释权的争夺之上:“华语电影”指出了“语言与民族之间的不对等性与非对称性”(12),因此威胁到中国民族国家的统一,表明了一种“去中国化”的倾向;而“中国电影”是维护中国民族国家这个统一的主体的。但正如鲁晓鹏和叶月瑜在其合编的论文集《华语电影——历史、诗学、政治》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这种语言与民族之间的不对等性与非对称性“表明当今世界华人在身体政治与文化连同方面既有联系和统一,也有断裂和碎片。”(13)也如鲁晓鹏在其后表明,华语电影并非要“去中国化”,“华语电影可以从民族,从国家和疆界开始,做成一个向心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一个离心的东西。你可以解构,可以建构,可以反思,可以批评,可以质疑,可以重建。”(14) 然而,李道新却坚持:中国电影学术的主要特点是建构性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研究就不再主动选择意识形态范式及其批判性、解构性立场,而是倾向于跟现实和产业互动”(15)。好似一旦解构,便威胁到“中国电影”其合理性。 这里除了体现对“解构”的一种普遍的误读之外,还涉及一个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首先“解构”并非是“解散”“破坏”的代名词,而是通过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过程,来实现对某一概念和范畴的更高层次的认识,是一种辩证的哲学思想——“解”与“构”本身构成了一种辩证的张力。在“中国电影”的问题上,用“解构”的视角审视中国电影中“民族”—“国家”的不对等性与非对称性,并非是要否认“中国电影”的合理性,更不言“去中国化”,而是不将“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普遍的自在的实体,来反思其内在的建构。其次,如果说中国电影研究者不再选择的“意识形态范式”特指极左时期以政治为纲的意识形态,那么这种变化体现的是一种对学术精神的正常回归;而如果其“主动”地不再选择“批判性”立场,将“建构”变为某种与权力的“合谋”,那么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便显得十分可疑,而这样的“中国电影学术”,笔者认为,还是少一些为好(16)。 主体性的中国电影将“国族”电影与“跨国(区)”的华语电影对立,视基于国族认同的中国电影史为“中国主体性内在规定性”、一个“目标诉求”;而与之相对,跨国(区)的华语电影研究则是一个“具体的研究策略问题”、“一条路径而已”(17)。这样的“本”与“末”的设置又是基于对具有所谓“普泛性”的“国族主体性”和作为“特例”的“跨国(区)主体性”的认识。在全球电影百年发展史与当今全球社会情境下,这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对这种局限的跨越也是跨国(区)的华语电影产生的历史情境。 跨国(区)的华语电影研究并非要将国族电影研究弃置于历史的回收站,而是在发现国族电影研究局限性的地方,以新的视角展开新的可能性。李道新援引英国学者裴开瑞(Chris Berry)对民族性的论述来说明华语电影研究“在从‘民族电影’向‘跨国电影’进行学术转型的过程中,不必要地抛弃了‘民族性’概念”(18)。其实,这里颇有断章取义之嫌。综观裴文全篇,作者并非要为国族电影正名或还魂(因为民族性并未消亡,“不但在我们这个跨国时代里依然生生不息,在跨国电影研究中,它同样是一个有长久学术生命的研究对象”),也非要以民族性来逆转面向跨国电影的学术转型(如作者所言,“‘对民族电影的研究必须要转变成对跨国电影的研究。’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作者要追问的是,“跨国时代中的民族性是否就等同于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秩序中的民族性?”(19)并反思跨国时代民族性的多面性。裴特别以当代中国大片与新加坡电影为例,阐述它们如何在跨国电影制作规则下,借力当代跨国电影的全球机制来获得自己的主体性。 显然,裴开瑞所言的“民族性的普遍存在”与李道新所说的“普遍主义的民族性”是不同的。裴观察到跨国电影中民族性的“普遍存在”并非确认其“普遍性”,而是恰恰相反,他看到民族性的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是在认识民族性“可变的而不是绝对”的前提之下完成的(20)。也就是说,在裴看来,中国的民族性和跨国性一样,并不具有所谓的“普泛性”。裴对中国民族性和中国电影关系的追问,在他和胡敏娜(Mary Farquhar)的著作《银幕上的中国:电影与国家》(2006)中得以更详尽地展开。在该书的导论中,作者明确地指出:“旧的民族电影模式试图将民族视为一个已为人知、无需质疑的问题,而我们的理论框架将‘民族为何’的问题,即民族是如何被建构、维护和挑战的问题置于我们分析的焦点。”(21) 其实,如裴开瑞与胡敏娜这样在跨国(区)和华语电影的研究范式被广泛接受的背景下讨论国族电影和民族性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如张英进出版于2004年的专著《中国民族电影》便是极有分量的一例。在绪论中,张指出中国电影中的“中国”并非一个“先验的、同质的、一成不变的本质性的概念”,其指涉模糊,需被“去神秘化”。华语电影与中国电影具有不同的指涉范围,往往宽于中国境内电影的范围,但有时也窄于这个范围。张选择使用“中国民族电影”的概念,因为相对于中国电影中“国家”的含义来说,文化与历史意义上的“民族”能更为有效的书写中国电影史。他总结道:“我们与其为中国电影中的中国性这个不确定的和多面性的问题所不断困扰,不如深入研究中国电影中‘国族’这个概念是如何在历史上被构建、传播和质疑的。”(22)这种质疑显然并非是要否定国族的有效性,而是置其于批判性的反思之中,带着问题意识来讨论国族。 上述这样的讨论是将中国电影与跨国(区)华语电影置于一种有弹性的、有活力的互动关系之中。如张英进所言,国族应被视为“一个企及小至‘地方’大至‘全球’的空间连续体(spatial continuum)”,并应置于“由‘地方’、‘区域’到‘全球’所构成的地域谱系”中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23)。又如裴开瑞与胡敏娜明确指出:“将国族与跨国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跨国不应被理解为“一个更高的秩序,而是一个将差别连接起来的更大的领域,这样地区、国家、地方的特质就能以不同的方式融合或竞争来相互影响。我们在此所要强调的不是化解中国电影中不同地区电影间的差别,将其融为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而是将这些电影所共同体现的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开放的、多元的、竞争的和充满活力的建构。”(24) 其实,这样的中国电影研究与李道新所说的“差异竞合,多元一体”(25)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其“国族电影研究也是一种跨国电影研究”(26)之说;只是在此,国族认同的所谓“内在规定性”已然被打开,中国电影的所谓“完整的、一以贯之的历史脉络”需要被反思而不是拒绝争论(27)。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电影不是要去“容纳”也无法“容纳”跨国主体性;反过来,华语电影并无意于“规范”国族电影,更无意于将国族变为其“一部分”或“附属品”(28)。 诚如孙绍谊与石川所言,我们应该“从反省意义上来混杂使用‘华语电影’、‘中国电影’或更多相关概念。所谓反省,是说我们在使用某一概念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另一概念的存在和有效性,避免非此即彼、以此取代和否定彼的倾向。”我们也应该“摆脱传统的‘大一统’思维惯性,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具有建设性的态度,来包容和接纳各种关于华语文化多元化和差异化发展的论述。”(29) 对中国国族电影的反思源自对中国性的“裂隙”的展开,这不是一个“去中国化”的过程,而是要看到现有范式的局限,对现有范式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反思与扩展,在其局限性的领域发掘另一种更合理、更有效的视角来阐释并与前者展开对话,而非定规某一范式的根本合理性和普遍性。这个过程正是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展开的,而非如李道新和吕新雨所批判的不顾中国历史语境。 “去政治性”的政治——华语电影“左”“右”受敌 吕新雨以对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解读来介入对华语电影的批评,有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也呈现出一些思考的盲点。特别是参照李道新对华语电影的批评,吕的观点会产生更多新的问题或问题意识。只可惜在复旦争论中,两者急于共同与华语电影的拥护者辩论,而未能展开他们之间的对话。或许笔者下面的一些浅薄之见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是“母语电影”的问题。少数民族电影是李道新和吕新雨进入华语电影批评的一个共同切入点,然而对于少数民族“母语”电影两者却有着几乎相反的理解。李以母语承担族裔文化与身份为前提,认为作为母语电影的华语电影与中国电影里的(少数民族/原住民)母语电影都“承担着呈现、保护、弘扬与推广母语及其文化的职责和使命。”(30)而吕则将作为“类型”电影的母语电影置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电影生产与消费的情境之中,批判其所产生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奇观化”以及“自我他者化”的倾向(31)。 虽然他们对“母语电影”这一褒一贬的观点可以理解为观察视角的差异使之然,然而由此差异所提示出的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则更引人深思。如果说吕新雨对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和华语电影的批判,最终落实于她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严厉批评的话,那么李道新对为少数民族母语电影所质疑的华语电影的批判,则最终传达出他对当今全球电影工业生产机制的所持的开放性的态度。 李道新谈论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给华语电影所带来的挑战,是由对“华语规划”的讨论所引发的。李将华语电影视为“语言规划中华语规划的自然结果和必然产物”,是“电影的华语规划的一部分”,因此华语规划中少数民族语言被遗漏的尴尬,是华语电影“出现自我纠结、相互缠绕,或外延膨胀、所指模糊等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32)。然而,这一说法在李对华语电影的批判中是值得回味的,因为我们会看到,李之前的铺叙其真正的指向实际在于全球电影工业市场。 对李来说,华语电影的真正弱点在于面对“好莱坞以及其他国家的那些同样‘只讲一种通用语的独白的世界’的主流电影”时的无力,而这种无力来自于华语规划和华语电影过于“窄化”的内涵(33)。那么,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电影才足以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的电影相抗衡,而“正是在‘统一’中国电影史这个问题上,作为语言、产业与文化一体化可能性的‘华语电影’,跟作为国家、民族与地域一体化必然性的‘中国电影’,在立场与使命上恰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34)因循李的逻辑继续梳理下去,我们会发现,李所期待的这个能与西方主流电影相抗衡的主体性的中国电影,更大程度上是“电影工业”而非“电影文化”意义上的电影。如他比较华语电影与国族电影所言: 华语电影这个概念确实具有产业意义,但无法在工业意义上使用。世界电影工业基本上都是以好莱坞为中心,美国主体性和美国中心主义应该说是毫无疑义的。但在电影产业层面上,“华语电影”呈现出某种值得期待的前景。但好莱坞体系之外的国族电影,既是产业也是工业,是无法被“华语电影”的“非工业性”所取代的(35)。 李在此对产业和工业的区分,显然意在强调“工业”的中国电影,而非“非工业”的华语电影是在电影工业层面上与“美国主体性”相对的“中国主体性”的承载体,也是对抗美国中心主义的力量。这里且不言以“产业”和“工业”来区分华语电影和国族电影是否合理。事实是,华语电影在制作、发行、放映等各环节上或许比国族电影呈现出更大的活力与潜力;但是将对华语电影的批判落实于市场领域中对抗好莱坞的无力,进而言之,文化对于工业的无力,这样的批评本身是否显得有些苍白呢? 李谈到,“迄今为止,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美学、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来进行讨论,不再是中国电影学术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状态决定的。关注作为一种制度、一种产业乃至工业的状况,强调电影从创意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和流程,这种综合研究在此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36)其实,这样的“综合研究”并非“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张英进早在2007年提出的“比较电影研究”的范式便指出综合多种面向——面向身外(跨国、全球化)、面向自身(文化传统、美学传统)、面向身后(历史、记忆)以及面向身旁(跨媒介实践、跨学科)和不同领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它考察资本跨地域、跨国家的流动,以及某民族国家或地区在某时段所采纳或遗弃的抵抗的或同谋的策略;在交流和表述领域,它分析媒体和技术的具体特性和相关联性;在发行、放映和接受领域,它探索人们是如何推销和消费电影的)的中国电影研究途径,并得以实践(37)。只是张的综合并未抛弃“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美学、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的重要面向。 如果说李谈到当今中国电影研究的主流不再以电影文化向度为主(对于这点笔者也感到深深的怀疑),是“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状态”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政界、业界、学界和创作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是中国电影学术的特殊性”(38),那么,吊诡的是,这种在海内外中国研究中已不新鲜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在中国电影研究中的实践,所导致的正是中国电影对好莱坞工业逻辑的臣服,而非对中国主体性的主张。正如白睿文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电影逐渐成为“有好莱坞特色的中国电影”(39);叶月瑜与戴乐为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中影集团在全球电影市场上的好莱坞式的运作,提出了“再国族化”(re-nationalization)问题(40);而裴开瑞同样也提醒我们中国电影全球运作的商业成功所引发的“民族主义的胜利感”(nationalist triumph)与“超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41)。这样一些当今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不正是学术界对其批判立场的放弃与对工业和市场的情有独钟所导致的结果吗? 李对电影工业的和产业的主张是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远离,他谈道:“中国没有经历西方理论的演变历程,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对于我们是另外一种思想体验和批评实践。”(42)这显然无法代表中国电影学术界的状况,但却表明了李所说的“主体性”中国电影研究的真切内涵——“建构性”的(即放弃批判性的,特别是马克思思想资源中对市场的批判)和工业性的(即对工业和市场的关注、对文化和美学的无力感)。李又谈道: 我对“中国主体性”的强调,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美国中心主义”,更不是否定让我心生向往的“跨国主体性”,是因为无论“美国中心主义”,还是“跨国主体性”,都要正视并直面“中国主体性”的存在及其必要性。否则,交流便会成为无对象的交流,对话便会变成独语(43)。 这样的“中国主体性”倒更像美国好莱坞文化的“倒逼”,却又吊诡地将自身置于好莱坞的全球资本主义工业逻辑。如果说吕新雨所一直主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的话,那么李道新所提出的这样的“主体性”中国电影则是否更应是其所该批判的目标昵?而她对呼唤从“经典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意义上”批判“华语语系”电影的鲁晓鹏的批判,就显得有些让人困惑了。 笔者希望提醒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国家主义”的问题。吕新雨在评论鲁晓鹏提出华语电影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电影时写道:“在这个统览性的修正中,‘文化中国’的‘华语电影’其实已经是以中国的国家认同为前提了。”(44)或许,主体性的中国电影研究中,以国家认同为前提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此问题有二:其一,在认同国家之前,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样的国家认同;其二,如何避免走向一种国家主义?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李道新和吕新雨在批判华语电影的过程中均以强调对“中国”这个主体的认同来批评华语电影研究者对该认同的缺乏,即所谓“去中国化”问题(而这个批评是笔者和众多华语电影研究者所不能认同的);但他们所认同的“中国”显然并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中国”。吕明确表明她所指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红色中国”(45),而从李的论述来看,他所指的中国却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在工业市场中与美国中心主义展开“对话”的中国。有趣的是,后面这个中国正是前面红色中国所批判的“资本与国家在市场意义上的联合”、创造奇观化“母语电影”的中国(46)。 这两个不同意义上的中国是由于两者所考虑问题的语境的不同而产生的。李道新和吕新雨所认同的中国虽然都是民族和国家统一和具有对等性的中国,可是李从语言和文化身份角度切入,确认了华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异质性,并由美国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主义的现实语境肯定“国家、民族与地域一体化必然性”;而吕则是通过新中国社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特定历史实践来确认国家民族的一体性的,她写道:“今天真正能包括族裔、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不是别的,正是作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47)这里,国家和民族一体性当然可以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社群”的角度来解读,但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中,同时也暗含着一个从“中国各民族”(ethnicity)走向“中华民族”(nationality/ethnicity)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建构和转化过程,吕在其长文中所讨论的正是这一过程在电影领域中的实践。 那么对中国主体性的确认过程中,如何才能避免走向一种国家主义呢?在复旦辩论中,吕新雨多次提到,在全球影坛各种势力角力的过程中,我们最后一张“底牌”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48)。这样的回答,或许是出于对其所认为的华语电影的“去中国化”进行直接反击的急切愿望,但从笔者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回答显然过于简单,也有滑向国家主义之嫌。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与当代全球语境中的中国显然是缺乏一定的历史连续性的。 吕新雨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电影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并援引《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大卫·哈维的话——“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narcissistic consumerism)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来确证国家权力的重要性(49)。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哈维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其主要特征是资本与国家的联合,其对立面或思想资源应该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国家权力。 同样,在批判自由主义化的时候,吕也在强调所谓自由主义其实只是国家主义的另一面目而已:“有批评指出,被当做‘去政治化’样板的美国和印度实行的其实是国家的‘自由主义化’,这两个国家的少数族裔地位一直低下并不断恶化,不是成功而是覆辙。如果没有忘记这两个国家正是文化多元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重镇,就可明白国家的‘自由主义化’并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另一种政治化,是作为普遍主义的国家主义体现而已。”(50)的确,自由主义有其意识形态上的政治遮蔽,国家主义或是其中一种。那么,批判自由主义这种“普遍主义的国家主义”(如果可以这样称谓的话),是否要以另一种国家主义代替呢?同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或许应该是更可取的。 由此提示出笔者希望讨论的第三点:去政治化的政治。对华语电影“去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泛政治化”的指责(51),主要源于华语电影倡导者当初为了实现有效对话而暂时搁置其各自具体政治话语所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可以说是一种有智慧、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与此,李道新与吕新雨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李谈道:“作为一种学术建构的文化产业愿景,‘华语电影’原本具有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诉求。但在鲁晓鹏等海外学者的一些表述中,总会不时流露出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色彩。这也是让我感到比较疑惑的地方。”(52)李对华语电影“去政治化”整体诉求中“反常”的“政治化”不能理解,或许可以理解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远离、对电影工业的专注的学术立场的一种自然表现。相反,吕对华语电影“去政治化”的批评,承接着她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对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批判,视其为一种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遮蔽性的政治。她写道:“‘华语语系’的‘政治化’趋势与‘华语电影’的‘去政治化’看似对立,实质却分享了共同的历史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今天中国大陆‘去政治化’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呼应。”(53) 虽然李道新和吕新雨在此问题上观点相左,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所谓“去政治化”中的“政治”所指的均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华语电影究竟是“去政治化”还是“政治化”了呢?或者说,华语电影究竟是不时流露出“左”的意识形态让投身当今全球电影工业的中国电影学界不快呢,还是呼应了今天大陆“右”的自由主义思潮而使得意图回归社会主义批判性的“新左”们不满呢? 当今大陆电影学界这种对待华语电影的自我矛盾的态度,其实源自于对华语电影的一种深深的误解,或者一知半解。回到华语电影自身的理论设计、展开与实践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其超越两岸三地政治藩篱的愿景与实践,并非对政治批评的放弃。例如在华语电影最早的学术论文集之一《当代华语电影论述》中,编者李天铎在绪论中明确阐释了华语电影所面临的政治——欧美电影体系的东方主义目光、西方学术话语的解读、本土电影人被收编和自我东方化的倾向等等,并提出“找寻一个自主的电影论述”的动机(54)。大陆学者戴锦华、杨远婴、王一川、倪震等也参与了此次华语电影范式在学术界的正式“亮相”。同时期的另一部华语电影著作——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同样对华语电影中的媒体、消费、公共领域和其他问题(见廖炳惠的导论)的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警觉,并收录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章(55)。其后,从叶月瑜、卓伯棠、吴昊编的论文集《三地传奇:华语电影二十年》到鲁晓鹏、叶月瑜合编的第一部华语电影的英文论文集《华语电影:历史、诗学、政治》(56),在这些重要华语电影论著中,政治——具体而言,对华语电影所处的全球资本主义商品化、消费化、市场化所持有的批判性从未有过缺席。而对此无视或视而不见,必然导致对华语电影的误读。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大陆电影学界的确有空谈华语电影的现象,诸多对华语电影的讨论或批评,却少有对上述(和其他)重要著作的介入,更枉谈细读或有建设性的互动。这或许和现今大陆学界获取一些资料困难有关。但如有机会潜心研读,或许对华语电影少一些误解和偏见。 最后笔者希望回到“什么样的政治”这个问题。吕新雨将“华语电影”与“华语语系电影”均归入后殖民主义理论(57),并借用德里克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来批评华语电影:“在把自身投射到过去屏幕上的过程中,后殖民主义推出自己,不但代替了基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区别的,或基于第三世界思想的认识论,而且也代替了这些认识论所激发的革命政治运动”(58)。这里,用德里克来批判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间的“复杂和暧昧的关联”确是贴切,但是需注意的是,德里克的批判落脚于“革命政治运动”的力量,而非国家权力。 德里克对国家主义曾有过明确的批评:“对施密特的追捧是在一种‘远离对社会的关注而投向对国家的关注’的转向中彰显自身的;这种转向导致对民族国家主权的迷恋胜过对社会问题和跨越政治边界的社会关系的关注,而在后者之中,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存在着推动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59)因此,依笔者愚见,吕新雨所说的对抗当今全球电影市场化的“社会主义红色中国”,应落实于“社会主义”,而非“国家”。唯有这样的政治方能克服其所见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普遍的民族主义、去政治化、奇观化等各种市场化中的弊端,而不至于落入国家主义的陷阱。超越国界与政见不同并不是去政治化,而再政治化也不是要回到国家主义中去。 必须承认,任何政治都有其遮蔽性,任何理论话语都有其盲点和不及之处。若以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介入华语电影的讨论,发现其盲点,提示其新的维度,扩展其未及的面向,善莫大焉;但若“仅”以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介入,似乎不免有管中窥豹、一叶障目之嫌;而若由此而断然否定整个华语电影的有效性,则是否武断了些呢? 华语电影研究发轫于两岸三地乃至全球政治对抗松动的年代,被广泛接受于全球资本、技术、人才大流动的时代,但这并不说明华语电影研究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言人。就如电影研究所关照的对象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伴随着整个20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风云变幻、并在21世纪进入一个全球资本化、市场化的新高度,但这并不表明电影就仅是资本的产物。相反,我们从电影中看到林林总总的景象、映像、镜像乃至我们的想象,与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发生形式各异的关联,形成程度不一的张力。 如果说华语电影研究被形塑于其产生发展的时代的话,那么它将以对这个时代更有穿透力的关照来彰显其理论与思想价值。当然,该价值的实现有仗于学者的态度、立场和学术品格。 注释: ①李焕征、鲁晓鹏.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美国加州大学鲁晓鹏教授访谈录[J].当代电影,2014(4):62-67;李道新.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J].当代电影,2014(8):53-58;石川、孙绍谊.关于回应“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访谈的对话[J].当代电影,2014(8):58-64;鲁晓鹏.跨国华语电影研究的接受语境问题:回应与商榷[J].当代电影,2014(10):27-29;陈旭光、鲁晓鹏、王一川、李道新等.跨国华语电影研究:术语、现状、问题与未来——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对话实录[J].当代电影,2015(2):68-78;李道新.“华语电影”讨论背后——中国电影史研究思考、方法及现状[J].当代电影,2015(2):79-83. ②(14)陈旭光、鲁晓鹏、王一川、李道新等.跨国华语电影研究:术语、现状、问题与未来——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对话实录[J].当代电影,2015(2). ③鲁晓鹏、李道新、石川、孙绍谊、吕新雨等.华语电影工作坊[J].当代电影(即出)。 ④唐维敏是“华语电影”最早学术论文集之一——李天铎编《当代华语电影论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公司,1996)——中丘静美与李欧梵的两篇重要论文的中译者。 ⑤(31)(44)(45)(46)(47)(49)(50)(53)吕新雨.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⑥⑨(30)(33)(34)(51)李道新.电影的华语规划与母语电影的尴尬[J].文艺争鸣,2011(15). ⑦鲁晓鹏.华语电影概念探微[J].电影新作,2014(5):4-9. ⑧吕新雨.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诚然,“华语”的概念是否并如何容纳少数民族语言,这一命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其实,“华语”本身的复杂性在“华语电影”概念产生之初便已显现:华语电影的另一倡导者叶月瑜曾对华语和方言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方言”的提法预先设定了“正统”的华语(国语),不恰当的矮化了非“标准音”的语言。由此可见,“华语电影”作为一个开放的范式仍然在不断的展开过程之中。见唐宏峰、冯雪峰.华语电影:语言、身份与工业——叶月瑜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1(5):72-80. ⑩鲁晓鹏.华语电影概念探微[J].电影新作,2014(5);鲁晓鹏.跨国华语电影研究的接受语境问题:回应与商榷[J].当代电影,2014(10). (11)李道新.电影的华语规划与母语电影的尴尬[J].如陈犀禾、刘宇清写道:“华语电影现象的出现顺应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在政治上走向统一和体制上保持多元化的历史进程,华语电影研究可以通过电影这一重要的文化媒体来透视两岸三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的性质、状态、关系及其归属,加强两岸三地之间的文化理解与沟通,把握政治统一和体制多元的真实含意和美好愿景。”见陈犀禾、刘宇清.跨区(国)语境中的华语电影现象及其研究[J].文艺研究,2007(1):85-93. (12)(13)鲁晓鹏、叶月瑜.绘制华语地图[J],唐宏峰译.艺术评论,2009(7):19-25. (15)(17)(26)(27)(28)(35)(36)(38)(42)(43)(52)李道新.“华语电影”讨论背后——中国电影史研究思考、方法及现状[J].当代电影,2015.(2). (16)相对于李道新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可参看鲁晓鹏对该问题的论述:鲁晓鹏、李焕征.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与大学人文教育——鲁晓鹏教授访谈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2期(2015年4月):5-17. (18)(25)李道新.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J].当代电影,2014(8). (19)(20)裴开瑞.跨国华语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抗与主体性[J].尤杰译.电影世界,2006(1):4-18. (21)Berry,Chris,and Mary Farquhar.China on Screen:Cinema and 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3.裴开瑞将其《跨国华语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抗与主体性》一文的英文原稿修改扩充后,收入《银幕上的中国》一书(第8章)。 (22)Zhang,Yingjin.Chinese National Cinema.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4.4-5. (23)Zhang,Yingjin.Cinema,Space,and Polylocality in a Globalizi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2010.19. (24)Berry,Chris,and Mary Farquhar.China on Screen:Cinema and Nation.195,5. (29)石川、孙绍谊.关于回应“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访谈的对话[J].当代电影,2014(8). (32)李道新.电影的华语规划与母语电影的尴尬[J].文艺争鸣,2011(15).这里,华语电影是否是华语规划的“自然结果和必然产物”颇值得商榷,因为至少华语规划,特别在其早期是一个政府指导性很强的“规划”,而华语电影这个名词的诞生,如叶月瑜所言,“是一个应运时事的概念”,是在两岸三地政治解冻、交流加强、全球跨国流动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日益增多、合拍片渐成气候等一系列现实情境下,由学术界在民间自然推动而出现的。叶月瑜的观点见唐宏峰、冯雪峰.华语电影:语言、身份与工业——叶月瑜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1(15). (37)Zhang,Yingjin."Comparative Film Studies,Transnational Film Studies:Interdisciplinarity,Crossmediality,and Transcultural Visuality in Chinese Cinema."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1,no.1(2007):29-30. (39)Berry,Michael."Chinese Cinema with Hollywood Characteristics,or How the Karate Kid Became a Chinese Fil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Cinemas,edited by Carlos Rojas and Eileen Cheng-yin Chow.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70-79. (40)Yeh,Emilie Yueh-yu,and Darrell William Davis."Re-Nationalizing China's Film Industry:Case Study on the China Film Group and Film Marketiz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2,no.1(2008):37-51. (41)Berry,Chris."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inema Book,edited by Song Hwee Lim and Julian Ward.New York and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and British Film Institute,2011.9-16. (48)鲁晓鹏、李道新、石川、孙绍谊、吕新雨等.华语电影工作坊[J].当代电影(即出)。 (54)李天铎主编.当代华语电影论述[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公司,1996:7~14. (55)郑树森主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C].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发行大陆版。 (56)叶月瑜、卓伯棠、吴昊主编.三地传奇:华语电影二十年[C].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1999;Lu,Sheldon H.and Emilie Yueh-yu Yeh,eds.Chinese-Language Film:Historiography,Poetics,Politic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57)这个观点亟待商榷:如果说“华语语系”借鉴了有殖民历史渊源的“英语语系”“法语语系”,因此被归入后殖民之列,那么华语电影也被入列则十分令人不解。 (58)[美]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M].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8-69.引自吕新雨.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5.5. (59)Dirlik,Arif."Back to the Future: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Past,Circa 1980." In China and New Left Visions: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ventions,edited by Ban Wang and Jie Lu.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2.36.标签:政治论文; 华语电影论文; 国家主义论文; 主体性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去中国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电影工业论文; 中国语言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华语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