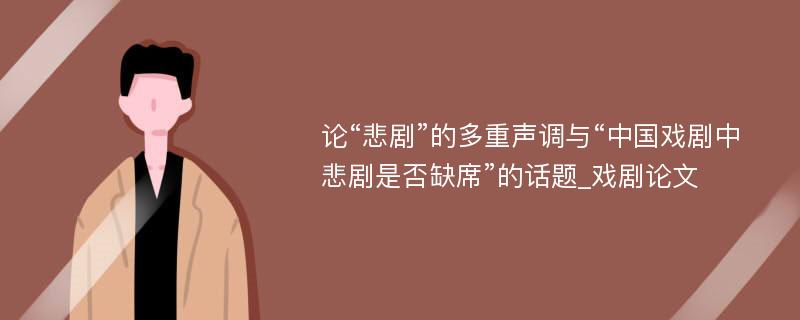
论“悲剧性”的多重色调——兼论“悲剧在中国戏剧中是否缺席”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性论文,色调论文,悲剧论文,话题论文,中国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黑格尔以来,“悲剧在中国乃至东方戏剧中是否缺席”,成了一个不断困扰着中外文论学者的问题。这里的“悲剧”指悲剧戏剧(戏曲)。黑格尔说:中国人缺乏“个人自由独立”的“意识”,这不利于悲剧艺术的“完备发展”,而只有悲剧的“萌芽”①。黑格尔的上述论断不断受到中国学者的否定。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1912)中提出,元杂剧中“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②。他对中国悲剧的成熟有着坚定的自信。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更以充分的证据明示世人:“悲剧”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未缺席。然而,赞同“悲剧在中国乃至东方戏剧中缺席”的西方声音并未因此而消失。1993年在美国出版的当今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就有题为“悲剧在东方戏剧中的缺席”这样一篇短文,将悲剧在东方的缺席归因于两方面:一是佛教的涅槃说消解了中国、印度、日本三国人民的抗争意识;二是“专制政体”消灭了“个体自由独立”的意识③。该词条的作者显然是以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单一结局”的悲剧作为西方悲剧的全部了,无视西方有不少“大团圆”结局的悲剧,如埃斯库罗斯的《被释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欧里庇德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高乃依的《熙德》等。2003年,著名文论家特雷·伊格尔顿出版了专著《甜蜜的暴力》,尽管他对黑格尔的“自由和个体自决原则是悲剧繁荣所必须的”观点表示质疑,但同时他又坚持“只有西方文化才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悲剧艺术——引者)。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正确地说,只有西方文化才有这种形式。悲剧艺术总的来说是一件西方的事情,尽管它在某些东方文化中也有共鸣。在中国,从表现尊贵个体之毁灭的意义来说,不存在完全等于悲剧的东西。”④伊格尔顿的观点至少有两点不能成立,一是“尊贵个体之毁灭”并不能概括西方的全部“悲剧”;二是中国并不乏表现尊贵个体之毁灭的悲剧,如明传奇《精忠旗》(岳飞)、清传奇《长生殿》(杨玉环)、京剧《鞠躬尽瘁诸葛孔明》、豫剧《诸葛亮归天》、京剧《走麦城》(关羽)、话剧《屈原》等。“悲剧”是否为西方专有也有待商榷。这种“例证法”固然针锋相对,却也使“控辩”双方陷入了太极式的周旋,难有实质性的进步。于是,近年来,中国学者转变了“辩护”思路。张燕瑾主张用“风格学”而非“类型学”来研究中国戏剧,他说:对中国古代的戏曲,虽然也有学者持戏剧一般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三大类的观点,“进行过一些分类工作,但古代的戏曲悲则‘哀而不伤’,喜则‘乐而不淫’,悲喜互藏,折衷合度,类型化的美学特征并不明显。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风格学的特征倒比类型的特征鲜明得多”⑤。该说虽正确指出了中国古代戏曲的特点之一,但并未说明中国古代戏曲之“悲”、“喜”凭何而分。邱紫华的《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等著作研究了中国悲剧的民族特色,暗含着对中西悲剧共通性的默认,但它们并未深究这个共通性到底是什么,似乎有绕过同题之嫌。 总之,中西学界至今仍未从学理上彻底地讲清楚“悲剧在中国乃至东方戏剧中是否缺席”这个问题,让人剪不断,理还乱,按下葫芦浮起瓢。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悲剧戏剧”是否专与某一文化共生,而是在于,促使人们做出“悲剧”判断的“悲剧性”是单一形态的还是多样态的。只有明确这个问题,“悲剧在中国乃至东方戏剧中是否缺席”的探讨才会彻底走出困境。为此,我们应从中西悲剧创作出发,探寻“悲剧”之“悲剧性”,分析“悲剧性”的存在形态,挖掘“悲剧性”显现的理论选择后的文化立场与纯洁性诱惑,以较完满地解答这个问题。 一、“悲剧”之“悲剧性” “悲剧”是个多义词,主要有“悲剧戏剧”、“悲剧艺术”、“悲剧审美风格”、“悲剧精神”、“悲剧意识”、日常用语中的“悲剧”等所指。就“悲剧戏剧”而言,西方“悲剧”概念所指也是变化多样。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悲剧大师那里,“悲剧”虽明确指称悲剧戏剧诗,但也是含混的,它既可以是一个尊贵者遭遇厄运的事件,如《俄狄浦斯王》;也可以是一个以安慰结束的与伟大人物有关的恐怖故事,如《被释的普罗米修斯》;或者是以和解结束的紧张故事,如《特洛亚妇女》;还可以是一种具有狂欢色彩的故事,如《带火的普罗米修斯》。亚里士多德视“悲剧”为一个“严肃”的“行动”。塞内加的悲剧让人感觉到生活的苦难和危险,以及暴力的恐惧。中世纪的“悲剧”概念不再与舞台表演有关,而是一个结局不幸的故事,是一种叙述类型。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公元6-7世纪)说:“国家和国王的悲惨故事构成了悲剧。”⑥基督教悲剧叙述人的灵魂如何经历苦难而得到上帝的救赎。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是一种表达警醒和惩戒教育作用的例子。锡德尼(Sidney)在《为诗辩护》中说:“高级和优秀的悲剧,揭开那最大的创伤,显示那为肌肉所掩盖的脓疮;它使得帝王不敢当暴君,使得暴君不敢暴露他们的暴虐心情;它凭激动惊惧和怜悯阐明世事的无常和金光闪闪的屋顶是建筑在何等脆弱的基础上;它使我们知道,那用残酷的威力舞动着宝杖的野蛮帝王惧着怕他的人,恐惧回到造成恐惧者的头上。”⑦16世纪查普曼(Chapman)说:“题材的教化性,对美德和对滑向反面的趋势表现出的优美而节制的热情,是悲剧令人信服的灵魂、核心和界限。”⑧17世纪法国作家拉辛及17世纪后期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赖默、德莱顿,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德国的莱辛等认为悲剧是再现“诗的正义”的文学样式,但艾迪生(Addison)却反对“诗的正义”。19世纪的“悲剧”具有了一种生命悲剧的哲学意味,例如,易卜生的《布兰德》写出了人之精神的孤独,斯特林堡的《通向大马士革之路》写出了人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在形式上它们与古代“悲剧”相异甚大。20世纪西方的悲剧创作,更加多样,现实主义的悲剧既有宏大的历史悲剧、英雄悲剧,也有普通人的日常悲剧;现代派悲剧聚焦于人生的孤独、冷漠、空虚、无聊、无意义、荒诞、绝望,“生命的悲剧意识”被加以悲观主义的极端表现;后现代主义悲剧突显了人及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反戏剧性、反传统性。此外,“悲剧”的风格由古希腊的“严肃”,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美而节制”,17和18世纪的“崇高”,走向19和20世纪的“崇高”“伟大”与对“崇高”“伟大”的“戏拟”“反讽”并存。西方“悲剧”戏剧的语体也有变化,传统的是韵语诗体,18世纪部分采用了无韵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转向了散文体。 可见,仅从主旨、焦点、人物、形式、风格及语体等方面来粗略扫描西方“悲剧戏剧”史,就发现西方悲剧从古到今不断变化。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悲剧”没有相通之处,因为既然某些作品或事件而非其他被学界及民众总用或通常用“悲剧”这一术语来指称,那么它们总有某些相通之处。西方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例如,克利福德·利奇(Clifford leech)认为:“在本质上,它们相互一致。”⑨理查德·B·西华尔(Richard B.Sewall)认为“它们都在同一个深渊上展开”⑩,也即“悲剧”是人应对困境或时代危机的一种方式。尼古拉斯·布卢克(Nicholas Brooke)在《莎士比亚的早期悲剧》(1968)中指出:“在相当宽泛的‘悲剧’术语中,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的范围,一种明确而特殊的范围。”(11) 那么,这个“悲剧”的相通处或“明确而特殊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它呢?古希腊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据公元6世纪拜占廷时的文献《舒达》(Souda)记载,公元前600年左右,科林索斯诗人阿里昂(Ariōn)在写作时用了tragikos tropos,这可能指某种后来为悲剧所吸收的音乐形式或处理音调的方式。显然,此时的古希腊人已经把握了人的情感与乐曲音调乃至悲剧合唱歌之间的关系。据信索隆(阿里昂的同时代人)说过,阿里昂是写作悲剧或具有悲剧性质的作品(drama tēs tragōidias)的第一人(12)。“悲剧性质的”这一形容词态,表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人已经意识到“悲剧”中有一种相通的东西,即“悲剧性质的”(tēs tragōidias)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悲剧的”、“悲剧性的”(tragic)。另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西库昂地区有一种追祭逝者的合唱歌Tragikoi khoroi,内容以描述阿德拉斯托斯(Adrastos)或者后来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遭受的苦难为主(13)。从上面所引证的材料来看,古希腊人当时所理解的“悲剧的”或“悲剧性的”主要是指一种苦难性情感。另外,从效果来判定某一对象是否为“悲剧”是人类较普遍的情思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是悲剧的“特有效果”。拉辛在《〈贝蕾妮斯〉前言》中说:“在悲剧中……其总的效果表现为一种构成了整个悲剧快感的崇高的悲痛,这就足够了。”(14)狄德罗也认为,剧中有“恐惧、怜悯或其他强烈的感情的激发”的属于悲剧(15)。将“悲剧的”或“悲剧性的”这一形容词态内涵固定下来的是丹麦学者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他创造了一个名词性术语“悲剧性”。克尔凯郭尔在《古代戏剧中的悲剧性在现代戏剧中的反映》[见《非此即彼》(1843)上卷]中提出:古今悲剧的联系纽带是“悲剧性”,它是悲剧的本质,是一出真正悲剧的决定因素和必备条件(16)。在这里,克尔凯郭尔对“悲剧性”做了“本质”式理解。笔者认为,“悲剧性”是使一部作品或事件成为“悲剧”的东西,但“悲剧性”与本质主义所理解的“本质”不同,它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由许多特征组成而非由固定的形式或内容组成,某一作品或事件不会因为缺少某一点而被逐出悲剧体验的地带。 “悲剧性”的情感特质为人们日常的悲剧性体验所印证,也为许多学者所肯定。克尔凯郭尔认为,“悲剧性”在古代是极具情绪反应的“忧伤”,在现代是极具反思性的“痛苦”(17)。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雷德利(Andrew Cecil Bradley)也暗示“悲剧性”是“一种痛苦”(18)。乔治·斯坦纳将“悲剧性”体认为一种“感觉”(19),雷蒙德·威廉斯视“悲剧性”为一种“经验”(experience)(20)或一种“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21)。苏联学者格·尼·波斯彼洛夫认为,“悲剧性”“是文学作品激情的种类”,是一种情致(22)。现在的《简明牛津词典》(1982)解释“悲剧性的”为“十分悲伤的”“痛苦的”“苦恼的”“悲惨的”(23)。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中也指出,“悲剧性”是一种“情感结构”(24)。 可见,“悲剧性”是一种情感,人的最基本、最持久、最浓厚的情绪情感之一,而人的情感中蕴含着认知因素,“悲剧性”体验也含有信仰、价值、观念、爱好、理想等所制约的认知因素,且不可弥补的缺憾感是其核心。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悲剧”或“悲剧性”这些术语,但古代中国文人的笔下却充斥着大量吟哦哀、伤、怨、忧、愁、冤、怒、愤、苦、惨、悲的戏曲作品。因而,在“悲剧性”视野里,中西文化及艺术具有相通性,“悲剧性”贯穿了古今中外一切对人的生存和存在状况给予深切忧虑和真诚关注的悲剧性作品,“悲剧性”成了文化的连续性、人类基本情感及其表征的相对稳定性和相通性的一个例证。 二、“悲剧性”的多重色调 由上面而来的问题是,作为人的情感一认知的“悲剧性”,它是单质的、纯粹的还是多质的或者多重色调的?我们将从情感色谱学角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悲剧性”的存在样态及其表达地带。 狄德罗说:“一切精神事物都有中间和两极之分。一切戏剧活动都是精神事物,因此似乎也应该有个中间类型和两个极端类型。”(25)据此,他在悲剧和喜剧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间地带的“严肃剧”,完善了戏剧类型三分法。他没有将任何戏剧类型绝对单质化,而是敏锐地意识到同一类型的戏剧有不同色调。他说:“喜剧的一切不同色调都可以包括在喜剧本身和严肃剧之间;悲剧的一切不同色调也可以包括在严肃剧和悲剧之间。”(26)但狄德罗并未具体说明“悲剧”有哪些“不同色调”,更未进一步去探讨形成“悲剧”不同色调之根本的“悲剧性”又具体呈现为哪些不同的情感色调?它们之间有何逻辑联系? 最新的神经科学实验研究认为,人类的大脑面对不同事物时,大脑的兴奋区域会发生改变,同一区域的神经元活动也有强弱程度等的变化(27)。因而,从色谱学角度分析人的情感是可行的。 悲剧性与其他情感体验一样,在深度、广度、强度和持续时间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在情感意蕴上具有不同的指向,由此导致了悲剧性具有不同的情感色调。 仅从体验的深度看,最直露的悲剧性是日常悲伤、悲惨、悲哀之情,较深层次的是对他人的同情、移情,更深层次的是对宇宙生命的同情感,大悲大同情。 从情感深度、强度及意味等综合的角度看,悲剧性大概有下面五种色调:伤感(哀而不怒)一悲愤(怒而不争)—悲壮(争而不胜)—崇高感(虽败犹胜,乐缘未来)—英雄感(苦争终胜,苦尽终于喜悦)。这五者呈一种倒“U”字关系,从两端向中间递升,其缺憾感程度不断增强;越接近“伤感”悲剧性越具有现实和日常色彩,越接近“英雄感”悲剧性越具有理想和传奇色彩。伤感悲剧性这端近于悲观主义,前接表现日常生活的严肃色调艺术;英雄感悲剧性这端近于乐观主义,后接传奇色调的作品;悲壮感悲剧性兼具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悲剧性的这五种色调本身并不具有美学和艺术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只要是对其所关注对象的悲剧性给予了充分的挖掘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表现,它就是成功的。 “悲剧性”的多重色调在文本中有普遍表现。“伤感”色调的悲剧性是普泛的基本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苦难剧、哀感剧、哀情剧、悲惨剧和悲怆剧中,表现的是人生或生活总有不如意。这种悲剧性更多的是突出那些缺憾感在人内心中的情绪性反应:淡淡的哀愁和忧伤。这种色调的悲剧性在中国古典悲剧性文学中比较常见。例如,恋爱者聚不得的悲剧性、离别的悲剧性、乡愁的悲剧性、闰怨的悲剧性、怨弃的悲剧性、伤春的悲剧性、悲秋的悲剧性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等的悲剧性大都属于此类。这种色调的悲剧性,在日常生活悲剧中也很常见。一位老者在居民楼旁遛弯时,突然一阵大风刮过,他被旁边楼房阳台上掉下的花盆砸伤了,这一意外事故带给人们的就是一种苦难或者哀情性的悲剧性体验。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偶然的意外的非人为事故具有某种更可怕的恐惧感。 “悲愤感”色调的悲剧性表现为一种怒而不争的悲剧性,主人公内心强烈的情感还没有外化为现实的行动,主要体现在悲愤、怨愤、冤屈、愤怒型悲剧中,表现的是生活总难以忍受。这种色调的悲剧性在中国古典“冤”剧中体现充分。例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本剧打动人心的主要力量在于窦娥的善良、孝顺、无私的美好品德和她的苦难遭遇及千古奇冤。剧中对窦娥的反抗精神虽也给予了十分突出的表现,但是,作为当时社会中普通妇女的窦娥只有对天地不公的“怨”,她还没有走向与社会的直接真正对抗。 “悲壮感”色调的悲剧性是哀感与振奋交织、哀痛大于振奋的悲剧性,多体现在高悲剧中,它主要通过结局的一悲到底来实现,主人公虽具有彻底的抗争精神,但争而不胜,以被毁灭或双方陈尸舞台而收场,引发人们强烈的悲伤以及发奋抗争之情,表现的是生活必须改善但总难改善。中西方都不乏此种色调悲剧性主导的悲剧,如中国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孔雀东南飞》《谭嗣同》,西方的《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等。哈姆莱特由思想转向行动,高悲剧的效果出现了,体现出一种刚烈悲壮之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生命的绝唱,在凛然豪迈中显现出了悲壮之美。 “崇高感”色调的悲剧性,是主导“乐观悲剧”的悲剧性。先烈人物虽败犹荣,因为他理解并接受了自己牺牲的价值和意义,于是以自己的牺牲为集体事业的胜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他在自己的牺牲中看到了事业胜利的曙光,坦然笑对牺牲,乐缘未来。牺牲者转为殉道者再转为拯救者,主人公成了时间和历史的化身,表达的是生活必须改善但需要时间。这一色调的悲剧性主导的悲剧作品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中较常见。振奋、鼓舞的乐观主义激情超过了主人公的牺牲带给人们的悲伤,表现了事业必胜的乐观信念,主人公成了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的楷模。因而,这类悲剧性作品具有一种崇高感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 “英雄感”色调的悲剧性,是主导情节剧的悲剧性。正面主人公经过苦苦抗争获得了胜利,皆大欢喜,振奋和传奇取代了曾经的悲伤。海尔曼在《悲剧和情节剧:关于体裁形式的沉思》(1960)一文中认为,情节剧中的“人”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裂的性格,也就是单纯的善或恶、力量或软弱,而悲剧人物的性格是分裂的,他被视为力量和软弱,处于不同的力量或动机或价值观间,他的本性是双重或多重的,各部分间往往有着戏剧性的作用,“情节剧表达的是单一的情感,悲剧表达的是复杂的情感”,“在情节剧中,人的欲望被毁灭了,或者它成功了;在悲剧中,它在受难中被得来的真理给调和(升华)了”(28)。海尔曼对悲剧与情节剧的分析是精辟的,但他把“悲剧”等同于“高悲剧”了,忽视了其他色调悲剧性主导的悲剧,也把“情节剧”的主人公简单化了,还错误地抹杀了“情节剧”的悲剧性。笔者认为,在情节剧剧终,英雄胜利了,恶人失败了;而在高悲剧和乐观悲剧中,人或在失败中经验胜利,或在胜利中经验失败。例如,《李尔王》就表达了复杂的情感。出走荒原后的李尔激起了我们多重感情,既同情他的遭遇,同时又有些责备他,因为暴风雨的遭遇及他和小女儿的死都是由于他的过错招致的;其巧言令色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野心而走上忤逆之路,她们被短暂的“胜利”白光一闪而亮后便坠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其疯狂追逐欲望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最终惩罚的恐惧,还要为自己的欲望在父亲曾经的专横和偏好谄媚里培育出的罪恶付出生命。这样一来,情节剧在善恶二元对立中传达自己的意志,表达的是生活能够改变,但需要超越常人的神性,因而极易实现意识形态和政治教化功能,极易被实用主义的政治所利用,经常倾向于对当下问题的思考,例如中国的《赵氏孤儿》,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的大片;而高悲剧关注的是人的双重乃至多重性的复杂存在,所面临的是永久的基本存在问题,更具有宗教和哲学意味,表达的是生活总是个猜不透的谜。 总之,笔者讲悲剧性的多重色调意在强调,首先,“悲剧性”不是纯粹单质的情感,“悲剧性”不是绝对同质的情感,悲剧性的情感色调是多种的,悲剧性的表现不只有一种形态。这就要求我们,不要以“高悲剧”的特点来绳墨一切悲剧性现象。唯此,悲剧性研究的跨文化沟通意义才会实现。同时,在悲剧性日常生活化的今天,我们才会顺利穿行于生活中的悲剧性与文学艺术中的悲剧性之间,达致对生活和文学的本质及其关系的更深刻、更全面理解。其次,悲剧性的多重色调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一种模糊性相对区分,遵循的是情感的模糊逻辑而非二元对立的形式逻辑。上述悲剧性的五种色调不可能穷尽悲剧性的所有色调,它们只是对悲剧性多重色调的一种理论抽绎,并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情感色谱,表达的是人生或生活总有缺憾。一部“悲剧”是上述诸色调悲剧性的单一或杂多的各种形式的综合显现,这使得“悲剧”作品既具有“家族相似性”,又呈现出不同样态。因而,我们不能把“悲剧”简单化,不能把悲剧精神偏解为抗争精神,其实,悲剧精神是一种担当精神,一个人物能否成为悲剧人物,与其是否自由自决并不必然相关,主动挑战引发悲剧,被动应战也可产生悲剧。 三、“悲剧性”显现中的立场选择 “悲剧性”既然是多色调的,呈现出情感的色谱性,那为什么不少西方悲剧理论家以悲壮感主导的高悲剧为“悲剧”的正宗而判定“悲剧”在中国乃至东方戏剧中缺席呢?要辨清这个问题,还需正确理解下面几点。 第一,判定“悲剧在中国乃至东方戏剧中的缺席”,从“悲剧性”的情感色谱学视角来看,这是陷入了“中—西”及“唯名论—实在论”双重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没有抓住“悲剧”之“悲剧性”的多色调、色谱性这一根本特点。中国古典悲剧的主题多围绕着“忠”“孝”“节”“义”,散发着哀、伤、怨、忧、愁、冤、怒、愤、苦、惨、悲等气息,虽“风格”多样,却都腾挪婉转于“悲剧性”的广阔地带中,灵动着“悲剧”的气韵。于是,从“悲剧性”的情感色谱来看。“悲剧在中国乃至东方戏剧中是否缺席”就成了一个伪问题。 第二,在西方文化中,不同的悲剧理论家也有不同旨趣的选择。例如,柏拉图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双重结局”,结局直接显示正义,赞成的是英雄感色调的悲剧性主导的悲剧。但在西方古典悲剧中更多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间接昭示正义的“单一结局”的悲剧,也即悲壮感色调的悲剧性主导的悲剧。他们理论选择的分歧,表面上看是直接表达与反向表达的艺术策略的不同;深层则是在正义境界问题上的分歧:柏拉图倾向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倾向现实主义。19世纪初的黑格尔之所以能提出中国只有“悲剧”的“萌芽”而没有“完备发展”的观点,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对中国历史把握得不准确。他以为,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人是“普遍的意志”,其他人都只有“敬谨服从,相应地放弃了他的自省和独立”(29),“只有一种顺从听命的意识”(30)。然而,中国历史上各种形式和层次的“起义”一再表明古代中国人并非都一直“顺从听命”。二是他的历史哲学观不正确。他认为,“世界历史”从中国、蒙古开始,中经印度、波斯、埃及,再到希腊、罗马,最后完成于日耳曼世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个人”的独立自由自决意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不断“成熟”的过程,也即从东方只有“‘一个’是自由的”,中经希腊罗马世界的“‘有些’是自由的”,到日耳曼世界的“‘全体’是自由的”过程(31)。显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基于其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否认了世界历史的多元发展史实,把历史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精神”发展,用“理念”逻辑取代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从“理念”论出发,黑格尔高度赞同“那种正面的有实体性因素的同情”,认为那是“高尚伟大的人的同情和怜悯”,是“真正的哀怜”,“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而坚决否弃那种“对于旁人的灾祸和苦痛的同情”,认为那“是一种有限的消极的平凡感情。这种怜悯是小乡镇妇女们特别容易感觉到的”(32)。显然,黑格尔推崇悲壮色调的悲剧性,而否认悲伤性哀怜具有“悲剧性”意蕴。黑格尔以自己的旨趣为标准而否定了大众对于生命、人生的基本缺憾的悲伤感这一悲剧性体验,导致他对“悲剧性”的理解失去了生命的最普遍基础。因而,西方的悲剧理论既不是铁板一块,“悲剧在中国乃至东方戏剧中缺席”这一误判也是出于某些理论家的旨趣成见。 第三,悲剧理论家要积极抗拒“理论纯洁性”诱惑,将文学理论的创新点深深植根于人类的文学—社会现实之中。亚里士多德因力挺“单一结局”的悲剧而强化了悲壮感色调的悲剧性主导的高悲剧的正宗地位,忽视了其他色调的悲剧性,致使其理论适用范围明显缩小。黑格尔理论上追求令人“振奋”的悲剧,但他所高度评价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则是“悲伤、怜悯”多于“振奋”,这个矛盾表明黑格尔由于受到理论“纯洁性”的诱惑,使他不自觉地滑入了理论偏见的泥淖。伊格尔顿一方面认为“悲剧艺术总的来说是一件西方的事情,尽管它在某些东方文化中也有共鸣”。另一方面他又承认:“现实生活悲剧,这对于所有人类文化来说都司空见惯。”(33)这里的矛盾表明伊格尔顿在摆脱理论纯洁性诱惑上的不彻底。可见,历史上的任何悲剧理论都是理论家针对具体悲剧现象而抽绎出的具体论断,它们既具有真理性,又具有时代的、语境的和理论家个体的局限性。对于已有的悲剧理论我们既要充分尊重,又需审慎反思。此外,我们既要克服墨守陈规的理论自卑意识,维护好自己的理论创新权利,不断提高自己理论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又要克服偏好高蹈的理论自恋心理,纠正完全脱离具体的悲剧性现象而恣意理论推演、热衷理论自我繁殖的错误做法(34)。真理向前再多走一步也许就是谬误。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悲剧理论是否有效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是否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文艺作品中的各种悲剧性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是否对各种悲剧性现象具有充分的阐释力,而不仅仅是理论本身的自洽。因而,人们只有聚焦于文学一社会中的悲剧性现象,才又可能探寻到悲剧理论创新的可靠路径。 第四,历史上文论话语格局的不平衡性和世界文化秩序的非公正性,放大和固化了人们基于既有文化立场而作的“悲剧”标准选择的成见。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对东方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促使东方国家一些先进分子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危机感的产生,于是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被动或主动学习,成为从19世纪后半叶到今天一个多世纪里甘当“西方”的小学生的整个东方国家的“课业”,此态势下的“西学东渐”既满足了中国等东方国家急切的“图强救亡”的民族动机,又强化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平衡格局和不公正的世界文化秩序。进而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照着西方说”一度成为我国理论界的时髦,西方学界也在文化自负中漠视了我国理论界的自我探索。西方悲剧理论在中国的选择性译介和接受即是上述的明证(35)。结果,西方悲剧理论在中国的影响至今不衰,而中国学者的悲剧思想被西方学者了解的却比较少。1977年苏联《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论文集发表了波兹涅耶娃的论文《悲剧性及其在中国的理论理解的最初尝试》,比较分析了刘勰与孔子对“哀”和“伤”的不同理解(36)。这是外国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的悲剧理论的较早论文。中国学者的悲剧理论被外国著名学者赞同的就更少,目前仅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1933,英文版,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关于“基督教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反悲剧精神的”论断被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肯定性引用(37)。因而,中国学者欲使西方学者改变偏见,就须加强文献沟通、建立公正的世界文化新秩序。 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一种文化中的学者与其纠缠于何谓“悲剧”的正宗,还不如自觉走出“唯名论-实在论”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摆脱理论纯洁性诱惑,超越自身文化的褊狭,以“全人类”乃至“生命”的身份和立场,从情感色谱学的角度,去体味人类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中的瑰丽多姿的“悲剧性”,去消解各种悲剧理论成见。在此意义上,每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从时间到空间都一直息息相关,惺惺相惜。此外,对于开放式的集合范畴的比较研究要慎之又慎。人的情感一认知毕竟不是几个类型所能规定的,情感色谱学的考察也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悲剧性作品的新思路。 收稿日期:2014-05-09 注释: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7-298页。 ②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③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ume 23,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93,pp.167-168. ④Terry Eagleton,Sweet Violence,Malden:Blackwell,2003,p.71. ⑤张燕瑾主编:《中国古代戏曲专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⑥转引自[英]克利福德·利奇:《悲剧》,尹鸿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⑦[英]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37页。 ⑧转引自[英]克利福德·利奇:《悲剧》,尹鸿译,第5页。 ⑨[英]克利福德·和奇:《悲剧》,尹鸿译,第45-46页。 ⑩Richard B.Sewall,The Vision of Traged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p.8. (11)转引自[英]克利福德·利奇:《悲剧》,尹鸿译,第32页。 (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附录”第248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附录”第248-249页。 (14)转引自[英]克利福德·利奇:《悲剧》,尹鸿译,第5页。 (15)[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张冠尧、挂裕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16)参见王齐:《克尔凯郭尔关于悲剧的“理论”——兼论悲剧精神的现代意义》,《外国美学》第十七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8-169页。 (17)参见王齐:《克尔凯郭尔关于悲剧的“理论”——兼论悲剧精神的现代意义》,《外国美学》第十七辑,第148-169页。 (18)[英]A·C·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3-34页。 (19)George Steiner,The Death of Tragedy,London:Faber,1961,p.5. (20)Raymond Williams,Modem Traged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3. (21)Raymond Williams,Modem Traged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21. (22)[苏]格·尼·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44页。 (23)J.B.Sykes,eds,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82,p.1136. (24)Terry Eagleton,Sweet Violence,Malden:Blackwell,2003,p.9. (25)[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第82-83页。 (26)[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第84页。 (27)参见本报记者:《读心术怎样看见你的秘密》,《渤海早报》2011年,第29版。 (28)Robert Bechtold Heilman,"Tragedy and Melodrama:Speculations on Generic Form," In:Robert W.Corrigan,eds.,Tragedy:Vision and Form,New York:Harper & Row,1981,p.214. (2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30)[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37页。 (3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06页。 (32)[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第288页。 (33)Terry Eagleton,Sweet Viloence,Malden:Blackwell,2003,p.71. (34)万晓高:《反面人物悲剧性探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35)万晓高:《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五四文学的意义》,《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6)[苏]л·д·波兹涅耶娃:《悲剧性及其在中国的理论理解的最初尝试》,《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79页。参见李逸津:《俄罗斯翻译阐释〈文心雕龙〉的成绩与不足》,“汉学研究网”,2005-10-29。 (37)Terry Eagleton,Sweet Violence,Malden:Blackwell,2003,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