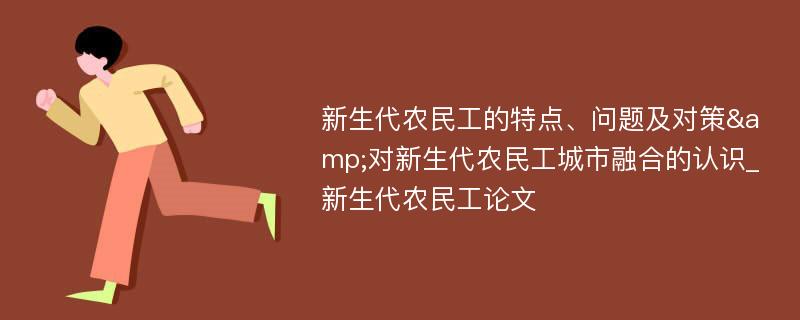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对策论文,特征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已开始着换代的变化,这一变动引起了笔者注意,并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王春光,2001),在这个人群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一开始,本人主要是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情况,理由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在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没有想到这样的提法,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以至于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这也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自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之后,笔者继续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社会心理、日常生活行动和制度等3个层面,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概括为“半城市化”现象或问题。在对比中外城市化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代人左右的“半城市化”状况,大部分国家成功地从制度层面化解了“半城市化”问题,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却没有有效地化解这个问题,使其演变成另一个结构性问题——“城市贫民窟”现象。目前我国城市正在经历快速的改造和扩张过程,没有为这样的问题转换提供空间。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半城市化”将沿着城市化比较成功的国家所经历的路径演变,而不是按巴西等国家的方式进展。这就取决于我国对城乡体制的改革力度和配套程度。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政策尤其是对待农民工的政策一直处在调整之中,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政策环境是有了大大的改善,但是这种调整是“碎步前行”式的,尤其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期望和要求,难以解决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的融合困境问题。2009年我们在广东、浙江等几个使用农民工最多的省份的调查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调查表明①,66.1%的农民工在30岁以下(含30岁),45%的农民工在25岁以下,也就是说,66%的农民工是在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其中大部分是在1984年以后出生。由此可见,在当今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已经占主导地位了。他们没有经历过第一代农民工所处的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他们来说,外出打工是自然的现象,大多数没有经历过不允许进城打工的制度限制。他们之所以选择进城务工,是为了“多赚钱改善生活”(60.9%)、“成家立业”(29.7%),还有人就是为了感受城市现代气息,寻找自由和发展机会等。他们中未婚的(48%)多于已婚的(45%)。我们虽然不能由此断定他们一定会在城市安家落户,但是,他们是有这样的可能和需求。在我们的个案访谈中,不少年轻的农民工对长期落户城市,抱着强烈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确实有这样的明显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他们将面临到许多障碍和困难。
尽管有这样的矛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时间越来越长,出现“长期化”、“常住化”现象,在沿海一些城市,一部分农民工“移民”倾向越来越明显,按沿海某市公安部门的人员介绍,有的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移民”。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下的人口属于临时性暂住人口,半年以上居住的人口属于“常住人口”。现在,像深圳、上海等城市开始将“暂住证”改为“居住证”,虽然只是一字之差,而且并没有等同于市民权利,但是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事实移民”现象。沿海某城市的外来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平均时间为44.23个月,即3年半时间以上,而众数是36个月,即3年时间,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该城市居住3年以上。3年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与过去的临时性务工不同的是,他们开始趋向稳定就业,力图在一个城市待更长的时间。一些农民工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城市时间长了,不仅有了一定的适应,而且也熟悉了当地的就业情况和信息,有了一些关系网络,因此,不愿轻易改变城市打工。我们对国外移民的调查研究也显示,凡是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移民想改变居住地的愿望就越低,因为改变居住地的负担和风险就越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内的农民工群体。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甚至不愿年年回家过年,一方面担心交通不方便,特别是买不到票;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回到乡村过年,还不如在城市过年热闹,回到老家,找不到可以交流和玩耍的朋友或对象。常住化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携家带口的农民工人数在增加。据浙江省教育厅的调查显示,从2004-2007年,流动人口子女就学人数增长很快,2005年比上年同比上升了12.07%,2006年同比上升了7.69%,2007年同比上升了21%;而杭州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增长更快,2004年同比上升27.7%,2005年同比上升19.9%,2006年同比上升20.6%,即从2003年的6.5万外来务工子女上升到2006年12万人,接近翻了一番。外来务工子女增加,意味着携家带口的现象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是以家庭的形式进入城市。我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31%左右的农民工跟他们的家人在他们打工的城镇生活在一起,而回答已婚的农民工只占45%,由此可见,在已婚的农民工中,只有14%的人没有将家人带出来,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与家人一起进入城镇生活,预计这一现象还会增加。与家人一起外出打工,会给他们带来稳定的生活支持,会使他们在流入地的居住长期化,变成“常住人口”甚至事实上的“移民”。
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重视他们在城市碰到的融合公平性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想不想成为市民、有没有能力成为市民是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给不给他们公平机会。有不少研究者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农民工根本没有能力成为市民,因此就不必急着改革城市户籍制度。实际上前一个是他们自由选择的问题;后一个是政府承担的责任问题。如果不解决机会公平问题,那么,农民工就很难成为市民。从目前来看,他们面临的机会公平问题仍然很多,涉及平等的就业机会、居住机会、受教育机会、社会保障机会、社会参与机会、医疗卫生、基本生存安全等福利权利问题。超过半数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或者稳定地享受“同工同酬”待遇,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超过70%有这样的感受。农民工中只有56.19%的人享有8小时工作权利,有43.31%的人每天工作达9~14小时,还有少数人每天工作多达15小时以上,处于超强度劳动状态;至于节假日休息情况,我们的调查显示,2009年第三季每周休息2天的农民工只占27.52%,不到三分之一;36.24%的人每周只休息1天时间;还有27.78%的民工每周很少休息过或者根本没有休息过。有46.35%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有50.88%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23.5%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是自己掏钱买培训,只有2.65%的民工完全免费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训,还有16.68%的人自己掏一部分钱,而政府或单位也掏一部分钱,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的农民工达到51.24%,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53.04%,参加城镇失业保险的达到23.97%。对那些有子女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是住房问题;二是子女教育问题。虽然中央多次强调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但是目前能享受这样待遇的人还很少,都要交纳一定的费用。至于住房问题,没有一个城市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在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许多所谓政策都还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化作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这里的原因是:首先,有关农民工社会政策都是以不改变农民工的流动为前提而设计出来的,或者说是确认他们的目前流动状况为基础的,而没有计划将他们真正纳入到城市化进程,因此,这样的政策为地方政府(特别是流入地政府)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其次,这些政策是在现有的行政制度框架下出台和实施的,并不是以改革这个制度框架为目的,因此,这些政策一旦与制度框架相矛盾、冲突,就会被这个框架化为乌有。最后,任何社会政策的实施还要依靠惠及对象的讨价还价能力,不论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三方谈判机制中,还是在与政府的谈判上,农民工都是非常弱势的,是不被重视的对象。因此,尽管国家出台了这样、那样的社会政策,但是,农民工很难维护这些政策给予他们的权益。
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最大亮点是做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籍限制的政策宣示,显然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把农民工视为暂住者的做法,给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启了一扇城市化的窗户,虽然这扇窗户还不够大,因为大城市还没有被纳入到这扇窗户的覆盖范围,而大多数农民工却是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城市的城市化大门也能向农民工敞开,就可以更好地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化”的渴求。
注释:
①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院社会保障所社科基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