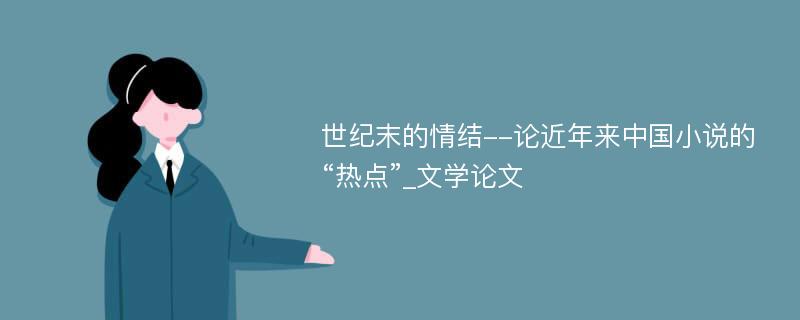
世纪末情结——近年中国小说“热点”漫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情结论文,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近些年来的中国小说界潮起潮落,“热点”复杂多变。从王朔小说到“新写实小说”的兴起和衰落,再到陕西作家群贾平凹、路遥、陈忠实各领风骚的作品,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叫“世纪末情结”的东西。
【关键词】 小说“热点” 世纪末情结
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令世界为之颤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中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使文坛万马齐喑,成为一片荒漠。
“文革”结束使中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也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七八十年代,我们的文坛曾百花齐放,佳作如林,一派繁荣景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结出过累累硕果,令人目不暇接。可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的文坛不再单纯澄明,出现了多变而复杂的局面。
报刊杂志铺天盖地而来,港、台文学“名星”你方唱罢我登场,琼瑶、金庸、玄小佛、三毛、席慕蓉……各自使出杀手锏,赚取我们各阶层读者廉价的眼泪,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呢?我们自己的小说呢?——订数下降,出版社让作者自己掏钱“包销”,社会上找不到知音,作家只得违心地向“纪实”、“言情”靠扰……
这是怎么啦?
就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一个相当年轻的作家迅速走红了。
他,就是王朔。
王朔在京城里长大,高中毕业后到北海舰队当过一段卫生兵,复员后又当过药品推销员,1983年辞去公职,开始干起创作个体户来。很难说清什么时候,他发现并介入了一个独特的生存群体——于社会大转折时期,被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挤出正常的生活轨道,在城市底层挣扎,不被理解又渴望被理解,不愿接受传统道德束缚又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因而玩世不恭、甚至走火入魔的青年群。他们中有个体户、劳改释放犯、待业青年、因单位不景气而无所事事、游荡街头的工人,还有因钱赚得太多不知怎么花或钱太少了内心不平衡的角色,以及有大量的闲暇、无法宣泄的精力而无所适从者。在我们这个大变革的社会里,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期,金钱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使他们困惑,不知所从。在这个人人都活得“很累”的时代里,他们成了“边缘人”、“多余的人”,别人无暇也无兴趣去顾及他们。于是,他们中的有些人颓废了,堕落了——但他们是不甘堕落的,社会应当宽容地、公允地对待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自我奋斗而崛起,在社会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可是大部分人至今仍无所适从。
他们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爱欲憎”,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至少我们社会中的某一部分,容易把人“看死”呢?
在这种情况下,王朔成了这一特殊生存群体的代言人。
请看他的小说的名称:《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也没有》、《过把瘾就死》、《顽主》、《玩儿的就是心跳》……他在小说中极力调侃一场,拿一切政治、道德、信仰、理想、欲望、感情开玩笑,甚至拿自己开玩笑,似乎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可尊重的东西。他说:“我通过流氓的眼睛看世界!”“我压根儿就是一个俗人,从不敢装高雅,当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什么的。”他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先写男人的感情被女人玩弄,又写女人的感情被男人玩弄,高雅的大学生却与出入大宾馆“以色诈财”的流氓为伍。当人们还不能理清自己的心态,也未能准确地在社会中找出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当人们捧着可怜的几张钞票在飞涨的物价前叹息不已,却又看到一个个“大款”挎着“小蜜”出入于高级饭店,挥金如土的时候;当有人“炒股”炒疯了的时候;当一个人受尽了欺骗,不能爱其所爱,心比天高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王朔喷云吐雾似的半生不熟的语言成了民间的流行语。王朔的作品怎能不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呢?
于是,在《我是你爸爸》中,老知青马林生(他事业无成,离了婚,物质和精神上都几乎一无所有)只能与儿子探讨诸如“再婚”一类的人生“大事”,因为他心境空虚,缺乏知音,不被人理解啊!于是,《渴望》写出了刘慧芳。他那么善良,做了那么多好事,但却不被人理解,好人倒楣到家了。谁说“好人一生平安”?于是,《编辑部的故事》把知识分子的小毛病一个个放大给人看,嘲弄自己给大伙开心……
这一阶段,可以说王朔不仅在“特定的青年生存群体”圈子里游弋,而且已经走进了千千万万个读者的心,走进了众多的家庭。王朔“热”起来了。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接受他,你可以不承认他,你也可以拒绝他、批评他,甚至居高临下地贬低他,但你不能否定他的存在和影响。
可是,物极必反。终于有一天,《爱你没商量》使观众和读者感到真正宝贵的感情受到了鄙视,觉得自己好像被欺骗、被玩弄了。“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的《海马歌舞厅》更使人们大倒胃口!
王朔衰落了。
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一二年”。
与王朔同时或稍后,“新写实小说”又风靡了还在读小说的中国人,令人刮目相看。它以特有的色调和韵味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固有范畴,体现出一种新的价值选择和审美意向。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喧闹是以“实验文学”的中止为代价的。自“伤痕”、“反思”、“改革”、“寻根”之后,在新时期文学中,“人”的意义和价格不断被放大,“暴风雪”中的知青英雄,上任伊始的改革精英,忍辱负重的“李顺大”以及启示探索的“章永璘”,成了社会人文的神话。作家们在美好的理想破灭后,就将“形而上”的探究转变为对“形而下”的生存状态的观照描写了,新时期文学所特有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和启蒙意识被消解在“烦恼人生”之中。“新写实小说”将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悲凉、失落和重构的努力基本上都涵括进来了。含而不露的语言,不事编造地展示生活之流的自然平实的叙述方法和结构形式,平静、冷漠、冷峻、不介入的视角,使其充分表现出对读者的尊重,也使读者将其轻易接受并认同了。
“新写实小说”无疑是对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冲击,它有所借鉴,有所创新,有人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
它将如何发展呢?
三
就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一些作家弃笔从商的时候,陕西作家却突然爆出了大冷门。从1993年以来,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健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相继在北京国家级大出版社出版,且发行至几万、十几万册。如果再算上前几年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的贾平凹的《浮躁》,以及获得一片赞扬声的李天芳、邹志安、杨争光等作家的作品,陕西的作家确实给文坛带来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有人称之为“陕军东征”,的确又形象又发人深思。
陕西是中国“黄河文明”的发源地,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二朝的古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向来十分浓重,文学创作也有较好的传统。
早在建国初期,陕西作家杜鹏程就写出了《保卫延安》,成为讴歌中国革命战争史的划时代巨著。柳青的《创业史》是中国农民觉醒并自力更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写照。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陕西涌现了路遥、贾平凹等一批实力雄厚的作家,他们散居乡下,从容不迫地笔耕着,日积月累地塑造着陕西人的性格和他们的文化心理。长期的艰苦积累,终于迎来了近年的大丰收。
路遥的六卷巨著《平凡的世界》是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力作。它以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原西县双水村为落笔点,并辐射到远近的城乡交叉地带,展现了自1975年以后约十年间,中国西部农村广阔的生活画面,表现了广大农民这些最平凡的人,在从动荡走向转折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道路,试图探寻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与未来。孙少安决心以自己的挣扎奋斗改变农村的落实现状及自身命运。他当生产队长,办砖场,可是失败了。然而他没有沮丧,在总结教训后贷款再干,决心闯出一条新路。而他的弟弟孙少平则一心想到外面闯世界,到工地当壮工,到煤矿挖煤,以陕北农村青年特有的坚韧和毅力,迎接生活的考验。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平凡的世界里一颗颗粗糙而美好的心灵。他们身份卑微,无权无势,默默地劳动着、创造着、爱着、生活着,为自己,也为别人。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存在,才使我们感到了人生的意义,看到了世界的美好与希望。路遥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炽热的激情,语言朴素、明净,带有远山风情和内在的韧力。
被戏称为“商州人精”的贾平凹很早就以他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等而蜚声文坛。1993年,他的新作《废都》引起轰动,因其内容和性描写而众说纷纭,甚至被列为“禁书”。贾平凹说:“《废都》是安妥我灵魂的一本书”“我感觉‘废都’二字里有太多的沧桑,这是难以言传的沧桑感。我不仅想到西京是中国的一个废都,而且想到中国在地球中的状态,地球在宇宙中的状态。废都绝非特定地域中的人的心态如何?它包含一种感觉。现在已到世纪末了,废都中的人心态如何?情结怎样?这是我要捕捉的。”他还说:“废都里的人自然有过去的辉煌和辉煌带来的文化重负,自然有如今‘废’字下的失落、尴尬、不服气又无奈的可怜。这样的废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来。”
在《废都》中,作者写了西京四大名人,即作家庄之蝶、书法家龚靖华、画家汪希眠和艺术家阮知非等文化人尴尬的生活。他们不是玩弄女人,就是贩毒、吸毒、赌博、卖假画、走穴……小说着重写了庄之蝶与景雪荫、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女人的性关系,写他从性爱中寻求解脱。可是,小说并不止此,它暗藏着更深的玄机。那样爱唱幽默歌谣的收破烂老头,那位常生活在人鬼难分的幻觉和种种神秘感应中的牛月清母亲,那头古怪的老牛及其古怪的“哲学”,那回荡在古城墙上的悲凉而不吉利的埙声,都体现出作家对现实和未来的某种预感和恐惧。一场本不复杂可又变得十分复杂的官司令庄之蝶囿于其中,并牵扯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各色人等竞相表演。庄之蝶似乎活得最自在,其实活得最累、最尴尬。他一直想有所作为,他一直想适应一切,却都事与愿违。所以,他到性爱中寻求解脱,寻求自然,寻求美,可是美却在他手中一个个毁灭。作者通过这个人,写出了中国古都今日的浮世绘。人生就是这样,你无法逃避,也无法选择。至此我们应该找到了贾平凹所谓“百鬼狰狞,上帝无言”的注脚。
继《废都》之后,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语)为题记发表,再次在文坛上掀起一阵巨浪。
《白鹿原》在陈忠实笔下,是陕西关中自清末到四十年代半个多世纪的一个大舞台,是富有艺术性的历史生活的“原汤原汁”。《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既不是《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生宝,也不是《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更不是赵树理笔下的“糊涂涂”,而是一个全新的农民文学形象。《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模式,它突破了某种政治的、革命的或与此相关的其他认知局限,在民族文化的层次上,展示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观,展现了一幅更接近原生态的农民生活画卷,使人读后怦然心动。陈忠实花了近五年时间,沉人生活底层,查县志、听乡音、写笔记,耐着寂寞,耐着清贫,耐着误解,终于写出了这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这本身不也能给我们某种启示吗?
从以上评述的文学现象里,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一种叫“世纪末情结”的东西。
标签:文学论文; 贾平凹论文; 废都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白鹿原论文; 读书论文; 王朔论文; 陈忠实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