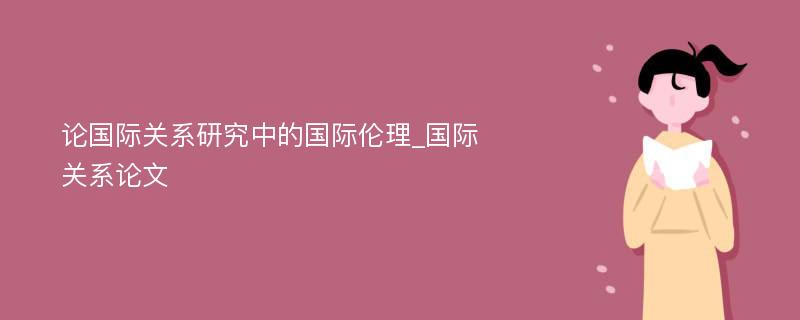
论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伦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伦理论文,学中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28-36
伦理现象在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倡议,以及一些国家提出的“规范性权力”、“价值观外交”等。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也往往是受规范性因素驱动的:相信知识能够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这是学者们投身研究的基本信念;而在早期现实主义者看来,揭示乌托邦主义是导致灾难的原因之一,这是一项合乎道德的知识工程。①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的伦理现象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现状来说是一个挑战:伦理研究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而且从现实主义观点看,国际政治的实质是用权力争取国家利益,伦理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就是“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住利己主义的冰水”。这种看法难免会产生一个困惑,即如果“伦理不起作用”或“伦理只是欺骗”是国际共识,诉诸伦理为何是反复出现的国际现象?如果不是国际共识,那么这两条论断是否会导致政治实践远离学术研究的初衷?国际关系学有必要“认真对待伦理”。事实上,忽视伦理的学科现状也正逐步得到缓解,一些西方学者对伦理现象投入了不少关注。②
本文回溯了国际伦理研究的起伏及原因,并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初步评述。本文认为,全面的国际伦理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国际伦理标准;国际伦理的限度与可能性;国际伦理现象。当前的研究忽略了第三个层面,为此研究者应该注重运用理性选择和规范动力两种视角,并有意识地进行跨学科研究。
一、国际关系伦理研究的起伏
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是国际伦理研究在主流理论中并未占据突出位置。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范式来说,一度作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国际伦理已被边缘化,出现了议题“收缩”的局面。③早期的自由主义对国际伦理的重视已记入学科编年史。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古典现实主义者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伦理政治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少学者就此对国际伦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卡尔把国际政治学科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他的时代,现实主义的学科史功能是摆脱乌托邦阶段,步入科学阶段;在现实主义之后,“成熟阶段”的政治思考必然包括权力和伦理两个方面。他断然否认了应将道德从政治中排除出去的看法,认为“政治行动必须以道德与权力之间的协调为基础”。④摩根索写道:“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遍道德原则不可能以其抽象的普遍公式应用于各国的具体行动,但又认为普遍道德原则必然渗透到具体的时间地点的情况中。”⑤可以说,摩根索看待国际伦理的方式与其看待“由权力界定的利益”的方式是相似的——道德与利益普遍存在于政治行动中,但不能依据抽象原则对二者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内容做预先规定。尼布尔从基督教现实主义伦理学出发,认为应当把现实主义与道德结合起来,道德力量可以带来政治威望,而政治威望本身就是不可缺少的权力来源。⑥
尽管卡尔等人承认国际伦理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但后世的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更多的继承了他们强调权力—利益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对国际伦理的思索,甚至回避国际伦理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是依据权力政治的现状、国际伦理变革的非现实性、国家利益等对国家行为做一点伦理判断。⑦国际关系学与国际伦理研究渐行渐远。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古典现实主义者对国际伦理的研究方式导致了其作品容易被误读:将伦理—道德与权力—利益并置,为平衡乌托邦主义的影响而较强调后者,以及忽视了对国际伦理变革可能性的深入讨论,这种处理方式使他们的伦理思考被权力、国家利益等概念遮蔽了。原因之二在于:受行为主义革命重视经验—实证研究的影响,国际关系学中出现了实证解释偏见(Bias Towards Positive Explanation)。⑧如果说古典现实主义者的人文立场使他们重视伦理思考的话,那么经过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后,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者明显回避了国际伦理这个议题。这在美国学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即多坚持价值无涉的立场,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描述现象、解释问题,而不是以一种更为思辨的方式考量微妙的伦理问题。原因之三是:主流的国际关系学坚守自身的学科身份与学术定位,通过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的对立将自己与政治学区别开来,因而出现了生存偏见(Bias Towards Survival),认为国际关系学处理的是国家的生存问题,而不是追求良善的政治生活。⑨这种偏见使国内政治研究中规范的政治理论难以渗透到国际关系学中。此外,冷战的时代背景也影响了研究课题的选择:冷战使国家安全和体系稳定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国际伦理研究则被认为离题甚远,⑩尽管冷战双方都认为自己参与的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伦理研究逐渐得到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这既有学科发展内在逻辑方面的原因,也是国际格局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在实践方面,就“需求”而言,冷战的终结使全球问题占据了国际政治议程的重要位置。例如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面对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文明冲突”,如何实现跨文化对话?对环境保护、劳工标准、跨国移民、国际维和等问题,从权力—利益的角度是否能做出合理的安排?在对新的治理方式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国际伦理是无法回避的。就“供给”而言,冷战时代阻碍国际伦理研究的生存逻辑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政治精英开始诉诸伦理话语而不只是安全话语以吸引听众,相对来说具有较强伦理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全球治理中,这为国际伦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
就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逻辑而言,建构主义的兴起是国际伦理研究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行为和国际后果受到国际规范等观念因素的影响,其开启的研究工程以及与政治理论学者、批判学派、自由主义的对话,促进了伦理研究回归到国际关系学中(11)。
首先,建构主义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包含着很强的伦理内涵。规范是指对国际行为体恰当行为的共有预期,它不同于其他行为标准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其涉及“应然”,即对什么是合理行为的判断。(12)文化是指规定行为体的身份、行为和彼此关系的标准,包括规范和价值等评价性标准。(13)这些概念所强调的“恰当行为”、“评价标准”等,也是国际伦理研究的议题中应有之意。由此,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行为不只依据“后果逻辑”,也依据“适当性逻辑”。怀疑国际伦理适用性的原因之一就是体现为生存偏见的后果逻辑,因此建构主义在核心概念上为“将伦理带回国际关系学”开创了空间。
其次,建构主义看待国家利益的方式突破了利益—伦理的两分法。国际伦理怀疑论者往往根据国家利益的首要性而否定国际伦理变革的可能性,这就假定决策者明确地认识到了国家利益,国家从工具理性出发而选择特定的道德立场。在建构主义的研究中,国家的存在理由也包括价值理性。国家利益往往不是自明的、内生的或固定不变的,其偏好往往经过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教导、塑造和社会化而形成,其中不少组织具有伦理取向的特点。(14)无论是利益诱导型的还是伦理教化型的说服,一旦这些伦理取向的组织说服了国家改变对自我利益的认知,就会使伦理在国家的偏好形成和偏好排序过程中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使国家利益与伦理要求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最后,国际规范的可变性意味着普遍的国际伦理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现实主义多从利己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现状出发,批评功利主义—世界主义的国际伦理为不现实。对规范变迁的研究有利于打破现状偏见,使国际关系学与政治伦理研究相互接近。(15)无政府状态和主权原则是质疑国际伦理的两个前提假设,然而在建构主义者的研究中,当前国际体系的这两个构成原则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是具有历史偶然性和可塑性的,例如主权承认的标准在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16)实践和观念的变化会产生新的构成原则,这意味着不能因为当下的“不实现”而预先排除出现一种新的国际规范的可能性。规范的可变性要求学者们对国际伦理进行更系统的研究。
二、研究现状:政治理论与建构主义
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本文把当前的国际伦理研究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研究者来自政治理论界以及国际关系学中的批判学派,强调的是规范研究,主要涉及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另一类学者多来自建构主义,强调从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结合中讨论国际伦理的限度和可能性。
1.政治理论: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是政治理论内部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简单地说,前者认为个人的权利和福利优先于群体,而后者认为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才能实现。(17)当这场争论从国内社会事务蔓延到世界事务时就表现为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焦点在于道德判断是不是能够超越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边界,国际关系学中的多数理论都可以归入世界主义或社群主义。(18)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通之处都是以个人而不是国家作为道德判断与伦理关怀的基本单位,普遍的理性(Reason)意味着超越国家界限的普遍伦理,主张通过超越国家的全球公共领域进行治理。比较能体现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关联的当属罗尔斯。此外,西蒙·卡尼(Simon Caney)、托马斯·波奇(Thomas Pogge)等也坚持世界主义的立场,相信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普遍适用的,同时主张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19)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分析了主权国家出现的历史进程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伦理,指出主权国家体系缩小了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具有高度的排斥性,认为全球化将会带来新的政治共同体,出现新的世界主义伦理。(20)质疑国际伦理在世界事务中适用性的学者多是未经明言地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当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华尔泽(Walzer)。社群主义认为,伦理道德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多样性意味着跨越国家界限的普遍道德尚不存在也很难出现,因而全球治理仍需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
作为国际伦理谱系的两个极端,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都容易招致一些批评。(21)就世界主义来说,很难否认的一点是人们在感情上倾向于为本民族、本文化中的同伴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而对民族—文化纽带的认知较为薄弱的其他人则显得淡漠;必须应对不同的个人在利益、观念方面的潜在冲突,这一任务并不比解决国家间冲突来得轻松;与当前的国际实践相距甚远,使世界主义的伦理诉求很难避免乌托邦主义的嫌疑;世界主义伦理是否只是反映了个别文化(如西方文化)的立场,在实践中是否会为文化霸权大开方便之门,这些诘问是切中要害的。就社群主义来说,其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尊重固然切合实际,但应该以何种共同观念作为跨文化对话的平台才能既不失包容性又促进共识,如何避免滑向道德相对主义,这些课题是社群主义必须认真应对的。
尽管可以把国际伦理观大致地划分为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但这样的粗略划分在一些细微之处还是具有误导性的,例如有社群主义者承认某些全球道德义务可以超越国家边界,而一些世界主义者也同意共同体内的地方性文化与全球正义可以兼容。(22)因此在国际关系伦理研究中,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分歧不是不可弥合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沟通社群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议题,主要内容是尊重差异、促进对话、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伦理。(23)对国际关系伦理来说,这一议题不失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2.建构主义: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
伦理与现实的关系在一开始就吸引了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伦理研究大多依靠严密的推理得出符合逻辑的推论,属于规范研究,而现状研究主要依靠符合社会科学标准的观察与解释,属于经验研究。然而,规范与经验往往相互交织。如果说国际关系学过去一直忽视规范研究的话,那么政治理论则经常性地对经验研究重视不够,往往只是从抽象前提出发对伦理原则进行逻辑演绎,而不关注推论出的原则在现实政治中具有多大的可行性。(24)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古典现实主义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从对国际现象的经验观察中得出了国际伦理要求与国家实际行为存在偏离的结论。默文·弗罗斯特(Mervyn Prost)则以较具科学哲学色彩的方式指出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研究者在对经验现象的分析过程中也必然涉及规范理论。弗罗斯特认为:“国际关系实践中行为体的价值体系并不只是简单地存在于那里;如果存在,这种价值体系也有待于国际关系学者从行动表面解读出来……对国际关系的任何形式的解释都必须从对一个行为(或一组行为)的理解(Understanding)开始,为了理解一个行为,研究者不得不卷入实质性的规范理论”。(25)依据这一看法,描述和解释都渗透着研究者所持有的特定伦理观,正是这种伦理观驱动了研究者投身于学术研究并影响了其对实质性议题的看法,例如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利己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观。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交织的特点是否意味着伦理命题在经验上是非现实的、经验命题在伦理上是非中立的,因而二者在可靠性上都值得怀疑?对非现实性问题,一些学者从建构主义在经验研究上所具有的优点这一角度进行了回答。建构主义的最大特点不在于其对国际关系本体论问题和实质性议题的看法,而在于其整体主义、“自上而下”的认识论(不同于持有个体主义、“自下而上”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是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侧面,因此二者往往在很多问题产生了相似的至少是互补的描述与解释。(26)建构主义的认识论立场比较“温和”,多处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间。因而建构主义的经验研究往往意识到其经验命题的可靠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具有背景依赖性而不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其结论是对其他研究项目的补充而非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主义的经验研究指出了国际伦理进步的限度和可能性,既不像乌托邦主义那样过于乐观,也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拒绝讨论国际伦理变革的可能性。(27)对非中立性问题,凯瑟琳·辛金克指出“最好的伦理判断需要最好的经验研究”,需要用可靠的反事实推理避免道德推论的偏差性,应该进行经验比较(Empirical Comparison),即将国际行为导致的后果与历史或现状进行对比,而不是理想比较(Comparison to The Ideal),即与研究者本人所设想的某种十全十美的理想状态进行对比。(28)后一种比较之所以不可靠,在于忽视了很多伦理要求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例如在一些情况下人道干预诉求与主权原则之间就不可得兼。如果研究者有选择性地将两个或其中一个问题与理想情况(如就调整主权原则达成国际共识并合乎国际法地进行人道干预)进行对比,就回避了政治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道德两难,使经验研究中渗透着过多的研究者自身的伦理偏向。
三、研究层次与研究方法
正如规范政治理论与建构主义所表明的,当前的国际伦理研究大致归结为两个层次。一是政治理论研究强调的规范层面的国际伦理判断,即真实世界中的政治秩序(或无序)、政策、结果等是不是合意的?如果答案为否,那么何种新秩序才能促进人的良善生活?依据何种标准做出判断?另外,很多学者都承认国际研究是由研究者个人的伦理信念所推动的,因此这一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学术研究是否以及怎样承担伦理责任?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伦理学、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等多个学科,国际关系学也无法回避。
二是建构主义强调的国际伦理的限度与可能性,具有规范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特点,这一取向更符合卡尔所谓“成熟阶段”的学科要求。这一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现实政治的约束下如何在国际伦理的道路上有所前进?现实政治留给国际伦理的限度有多大?如何判断这种限度?如何在政治现实与伦理要求间做出权衡?如何在多种冲突性或竞争性的伦理要求间进行取舍?这些研究针对具体议题、将问题置于现实情景中,力求得出道德上合意、现实中可行的政策结论。这要求研究者对伦理主张可能导致的各种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有充分了解,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深入考察。
然而,这两个层面无法涵盖国际伦理研究应该处理的所有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建构主义的国际伦理研究,都预先假定了伦理在国际事务中是重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国际伦理怀疑论者之间的分歧是深刻的,后者或认为伦理在国际事务中并不重要,或认为伦理概念并不具有分析上的重要意义,或否认国际伦理变革的可能性。因此,国际伦理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澄清一些根深蒂固的疑惑:伦理因素在国际事务中起作用吗?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国家为什么频繁地诉诸伦理话语?如果答案为是,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起到什么作用?伦理是否仅仅是依附于权力—利益的伴随变量?如果伦理仅仅是掩饰或欺骗并且假设这一点为国际共识,伦理话语就无法实现策略功能,那么国家为什么还会采用诉诸伦理的策略?这一层面的问题涉及国际伦理现象,更多的属于经验研究,是国际伦理研究工程中应该首先澄清的问题,也是目前研究中略显缺失的一环。
对国际伦理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一些学者所倡导的国际政治理论(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与国际伦理研究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需要国际关系学、政治理论、国际法三个学科间的对话,进行实证、规范和法律研究。(29)此外,至少对伦理现象而言,理性选择和规范动力这两种视角是不应忽视的。
理性选择将伦理话语与国家的主观效用相联系,看似支持了伦理怀疑论者的看法,但其贡献在于具体勾勒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伦理话语视为国家利益的策略工具。通过把伦理话语理解为一种信号(Signal),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和法律言辞是国家在追寻自我利益过程中出现的均衡现象;伦理规范作为社会惯例的一种,起到了聚点(Focal Point)的作用,在协调博弈中有效率地实现多重均衡的过滤。(30)同样,用信号传递模型也可以重新表述伦理怀疑论者的立场,他们认为伦理信号发送方的类型与信号本身完全无关,信号都被接受方当成“空谈”(Cheap Talk)或“噪声”(Voice)而不予理会。这一假定的依据是废话均衡(Babbling Equilibrium),该均衡在真实世界中的适用性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很少把信号看作是与对手的类型不相关的,决策者经常要求他国就相关问题表态、对表态的内容进行细致解读,这表明国家之间不只“观其行”,也“听其言”,“一方传诉诸伦理话语,另一方不理会”的策略组合并不在现实中的均衡路径上。第二,依据废话均衡的逻辑,所有言辞都可以成为均衡中的废话,(31)因此人们会预期道德话语与霸权话语出现的频率应相当。显然这一预期不符合国际政治事实:决策者对自己的言论非常谨慎,经常向其他国家释放善意,更多使用道德话语而不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话语。因此,简单地说伦理不起作用的结论存在着漏洞。
国际伦理怀疑论提出的真正挑战不在于伦理是否起作用,而是伦理话语在什么条件下与国家的真实类型相关,用信号博弈的话来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混同均衡、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分离均衡。诉诸具体情景中的博弈结构是对该问题的一个解决思路,例如伦理话语在协调博弈中有效率地实现了多重均衡的过滤,也是可信的;在完全冲突博弈中属于不可信的“废话”;而在其他情况下的作用更为复杂。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或可澄清伦理话语在特定情景中的作用。另外,伦理话语对特定听众的作用也值得研究。当国家诉诸伦理话语时可能针对多种听众——卷入争端的他国政府或涉身事外的第三国、国际组织、NGO或他国公众、本国公众或本国各利益集团等等。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澄清特定听众效应也有助于加深对国际伦理现象的理解。
有学者认为仅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国际伦理现象是不完全的,主张还应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32)伦理因素容易激起人们的道德激情或道德义愤,因此这一主张不无道理。心理学研究可以纳入理性选择的研究框架中。“非理性的理性”这一说法暗示了诸如感情这样的心理现象是一种节省信息处理成本的简化机制,可以用理性选择加以解释。(33)
规范动力是国际伦理现象研究应该借鉴的另一个视角。国际规范在历史上发生过不少重大变迁。为什么曾长期被认为在道德上不成问题的国际行为(如奴隶贸易、武力讨债等)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在一系列可能的行为标准中,为什么当前成为国际规范的是一种特定的利己主义—社群主义伦理观?对规范变迁的经验研究关乎现存的国际伦理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固定不变?这关乎新的国际伦理将如何起源、传播、制度化、稳定,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以进化论为思考方式,从基因—文化共同演化(Gene-cultural Co-evolution)的角度对国际规范进行动力学分析,这是颇有前景的研究路径。有学者从自然选择的角度进行了尝试,用进化视角重新解释了现实主义伦理观的起源,将利己主义和支配欲望建立在生物学基础(“自私的基因”)上,将社群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建立在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和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之上。(34)对于相信国际伦理进步的人来说,尽管这些“将达尔文主义带入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似乎印证了古典现实主义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但进化论同时意味着现状具有历史依赖性、并非固定不变,也意味着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带入国际关系学”、通过文化演化实现伦理变革。若干研究者从文化演化的角度讨论了规范变迁,并对国际伦理革新表达了较为乐观的看法。(35)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进化论的思考方式一直隐含在伦理学传统之中。(36)从根本上说,进化论不只是生物学理论,其更多的是一种系统动力学理论,尤其适合处理系统中的行为体—结构问题,这一特征使进化论及其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两种机制对现代社会科学中多学科发挥重要影响。进化论取向的国际关系研究也不乏其例。(37)规范变迁是其中与国际伦理联系比较密切的一种,研究者可以从规范动力的视角分析伦理规范的变异、选择和传递。
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Coleman)指出,社会理论研究需要跨越多个学科领域,找到贯通这些学科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他认为理性选择正是这样一个基础。(38)作为一种动力学机制的进化论也可以成为学科对话的基础。如果说学科分工如经济分工一样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话,那么跨学科交流就相当于通过市场交易以实现比较优势,而理性选择与进化论则是学术市场交易中的通货。对国际伦理这样的复杂现象来说,通过合适的基础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是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
四、结论
早期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伦理投入了巨大的关注,但此后伦理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边缘化,学者们避免涉及伦理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对古典现实主义的作品存在一些误读,忽略了其关注伦理—道德的一面而片面继承了其强调权力—利益的一面;受无政府状态的生存逻辑的强烈影响,认为学科处理的是国家生存问题而不是追求良善生活问题;接受实证主义尤其是科学行为主义的看法,其主张的实证—经验研究方法在处理规范问题时遇到困难;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时代背景给国际伦理研究投下了阴影。无论是从全球问题的问题解决角度,从卡尔所谓“成熟科学”的学科建设角度,还是从实践学术伦理信念的道德使命角度来说,国际关系学都应该深入研究国际伦理问题。
政治学中的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中的建构主义一起构成了冷战后国际伦理研究的主力。尤其是建构主义对规范、观念、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对国家利益自明性的质疑,引起了其他学派对伦理研究的重视。目前的研究现状是,政治理论强调对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规范研究,而建构主义则重视从规范与经验相结合的角度讨论国际伦理的限度与可能性。本文认为,国际伦理研究急需澄清若干困惑,急需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回答伦理是否起作用,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起到何种作用等问题,因此本文主张国际伦理研究应该划分为三个层次:国际伦理判断、国际伦理的限度与可能性和国际伦理现象。对最后一个层次来说,理性选择和规范动力是值得重视的。国际伦理无疑涉及大量难以处理的复杂现象,但复杂性应该成为进一步的动力而不是回避问题的借口。复杂性意味着应对国际伦理进行跨学科研究。
收稿日期:2010年5月。
注释:
①Mervyn Frost,Towards a Norma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December 1988,p.380; 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4,p.163.
②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包括余潇枫著:《国际关系伦理学》,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年版;熊文驰、马骏主编:《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一些期刊论文。
③Christian Reus-Smit,"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Ethical Reasoning," in Richard M.Price,ed.,Moral Limit and Possibility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54-60.
④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pp.5-10,97-98.
⑤[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4页。
⑥程又中、付强:“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道德观”,载《伦理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89-93页。
⑦David Chandler and Volker Heins,eds.,Rethinking Ethical Foreign Policy:Pitfalls,Possibilities and Paradoxes,London:Routledge,2007,pp.5-6; Andrew Hurrell,"Norms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pp.139-140.
⑧Mervyn Frost,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nstitution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19.
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No.1,April 1960,p.48.
⑩Mervyn Frost,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5-6.
(11)其他学派也参与了国际伦理研究的复兴,例如基欧汉近年来的国际伦理研究,可参见Allen Buchanan and Robert O.Keohane,"The Preventive Use of Force:A Cosmopolitan Institutional Proposal,"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8,No.1,Winter 2004,pp.1-22; J.L.Holzgrefe and Robert O.Keohane,ed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Ethical,Legal,and Political Dilemm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2)Ann Florini,"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No.3,September 1996,pp.364-365.
(13)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5-6.
(14)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美]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著,韩召颖等译:《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跨国倡议网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Martha Finnemore and Ke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Autumn 1998,pp.915-916.
(16)Thomas J.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eds.,State Sovereignty and Social Constru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1.
(17)顾肃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2-530页。
(18)[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548页。
(19)Simon Caney,Justice beyond Borders:A Global Political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63-265; Thomas Pogge,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Cosmopolitan Responsibilities and Reform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美]约翰·罗尔斯著,张晓辉等译:《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2页。
(20)Andrew Linklater,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Ethical Foundation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Press,1998.
(21)李开盛:“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两种思想传统及其争鸣”,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2期,第54-59页。
(22)Tan Kok-Chor,Justice without Borders:Cosmopolitanism,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Eduard Jordaan,"Dialogic Cosmopolitanism and Glob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1,No.4,December 2009,p.732.
(23)Richard Shapcott,Justice,Community and Dialog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4)Christian Reus-Smit,"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Ethical Reasoning," pp.60-65.
(25)Mervyn Frost,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34-35.
(26)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Reationalism v.Constructivism: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53.
(27)Richard M.Price,ed.,Moral Limit and Possibility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7-18.
(28)Kathryn Sikkink,"The Role of Consequences,Comparison and Counter-factuals in Constructive Ethical Thought," in Richard M.Price,ed.,Moral Limit and Possibility in World Politics,pp.104-111.
(29)Duncan Snidal and Alexander Wendt,"Why there is International Theory now," International Theory,Vol.1,No.1,March 2009,pp.1-7.
(30)Jack A.Goldsmith and Eric A.Posner,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67-184;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12-13; 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pp.68-70;;[美]肯·宾默尔著,李晋译:《自然正义》,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
(31)Joseph Farrell and Matthew Rabin,"Cheap Talk,"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Vol.10,No.3,Summer 1996,p.108.
(32)Richard Ned Lebow,Coercion,Cooperation,and Ethics,New York:Routledge,2007,pp.295-324.
(33)Herbert A.Simon,"Human Nature in Politics: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9,No.2,June 1985,pp.301-302; Jack Hirshleifer,"The Affection and the Passion:Their Economic Logic," Rationality and Society,Vol.5,No.2,April 1993,pp.185-202.
(34)R.Paul Shaw and Yuwa Wong,"Ethnic Mobilization and the Seeds of Warfare: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1,No.1,March 1987,pp.5-31; Bradley A.Thayer,"Bringing in Darwin:Evolutionary Theory,Realism,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2,Autumn 2000,pp.124-151.
(35)Stewart Patrick,"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Choice,Learning,Power,and Identity," in William R.Thompson,ed.,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1,pp.133-174; Michael Barnett,"Evolution Without Progress? Humanitarianism in a World of Hur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3,No.4,October 2009,pp.621-663.
(36)舒远招:《西方进化伦理学:进化论运用于伦理学的尝试》,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7)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21,No.1,April 1988,pp.66-94; Hendrik Spruyt,"International Sele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e Anarchy as Order,"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4,Autumn 1994,pp.527-557;[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8)[美]詹姆斯,S·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