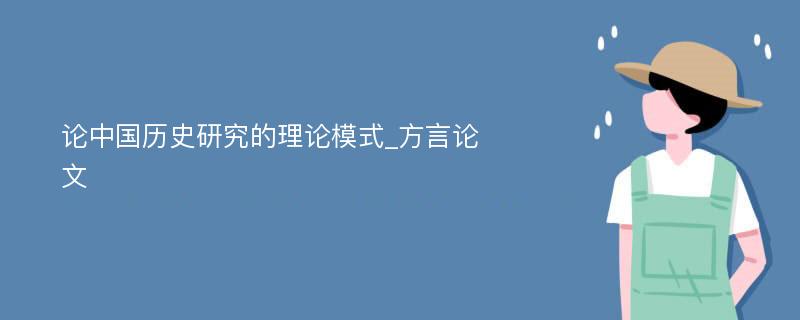
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史研究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汉语史的研究,现当代主要有四种理论模式。虽然其中只有一种是涵盖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和语音结构的,其余的主要是针对汉语语音史,然而建立在某种语史观之上的理论模式,即使仅从某一语言要素切入,也必然以种种方式涉及到其他语言要素,从而牵动整个语言史。从这一意义上而论,汉语语音史的理论模式也就是汉语语言史的研究模式。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建立的直线型模式,或称之为“高本汉传统”。深受欧洲十九世纪“单线进化论”思潮熏陶的高本汉,他认为汉语发展从上古到中古,到现代方言是一直线的,由周秦古音演变为《切韵》音系,又由《切韵》音系分化为现代汉语各方言。他的中国古音重建就是以中古音构拟为枢纽,由之上推周秦、下接现代方言,由此出现了汉语演变史的那种“蛇吞青蛙的隆腹现象”。其症结是把《切韵》音系曲解为单一音系,一方面认为《切韵》是中古的长安(或洛阳)话,另一方面又认为现有所有汉语方言都是《切韵》的子语,因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两难局面。再由《切韵》音系上溯至《诗经》音系,则形成了从上古到中古由简而繁的分化过程;下推方言,则形成了从中古到现代由繁而简的归并过程。这种汉语音系演变简—繁—简的橄榄状态完全不符合语言发展的实际状态,因为它抽去了横向的空间差异,企图以一维的纵向时间差异贯穿方(语)言分歧的复杂现象,从而曲解了汉语言发展史。高本汉的直线型模式,是用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谱系树理论硬性框范东亚语言,用语言分化论处理中古汉语与近代汉语各方言关系的结果。直线型语史观的基础是“一元扩散论”的文化史观。这一此模式隐含的“汉文化中心论”满足了人们的潜在民族情结,并且因简单化而便于研究时操作,而得到了中国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同,尽管有所调整,但基本模式未变。
高本汉模式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受到批评,新的模式随之产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教授、 美籍华人学者张琨 KunChang,从时空二维研究汉语语音史,强调南北方言差异, 建立了差异型理论模式。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切韵〉的综合性质》、《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汉语音韵史中的方言差异》与《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其高足张贤豹先生以为:“张琨教授夫妇(1972年)合著的《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是20世纪初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问世以来最值得重视的汉语音韵史著作。1972年是汉语音韵学的分水岭,1972年以前是高本汉时代,1972年以后是张琨时代。”张琨重申《切韵》是一部具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的是公元601 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由此可以投影出原始汉语系统。他批判道,把原始汉语设想为一个语言,后来才分裂为方言群——如先分裂成原始吴语、原始闽语等等,然后再分裂为各个方言——这是荒谬的假设。方言差异无疑是自古而然的现象,早期的汉语方言必定比今天更复杂。由于语言接触机会增多,方言才越来越加感受到标准语统一的影响力。因此,所谓汉语的原始系统,不是一个历史上的语言,而是一个假想的对立系统,这是为了用最简单、最合语言实际的办法来解释已知的历史文献上的记录。不仅现在的方言差异是南北方言平行发展的结果,而且文学语言基础也有南北之异。周秦、汉代的文学语言基础是北方方言,而齐梁时代是南方方言,唐宋以降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与高本汉的时间一维语史观相比,张琨的南北差异、方言分歧的时空二维观较切合汉语实际。但一些问题尚须深入探讨。何为古代北方方言,何为古代南方方言?南方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北方方言又如何变化?齐梁的南方方言(文学语言基础)是江南吴语,还是南迁中原汉语的南方化?唐宋元与明清的文学语言基础——北方方言是否有地区之异?中原正音、江淮官话、燕代方言与唐宋以降的文学语言基础各有什么关系?先秦的文学语言基础是北方方言,是否意味着《诗经》音系与《楚辞》音系同为一种?如果以为把原始汉语设想为一个语言是荒谬的假设,又如何认定早期的一些语言是汉语方言?原始汉语又从何而来?原始闽语、吴越语、楚湘语等与原始华夏汉语是同一语言还是不同语言?中国古代的“方言”概念与西欧的“方言”概念有何异同?凡此种种,只有结合考古文化系统及相关史料,只有把华夏汉语的形成与延伸置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持久冲突交融的历史背景上审视,才有希望解决。差异型模式虽然较直线型模式有所进步,但仍然未摆脱狭隘的文明一元分化论,对中华大地上区域文明的复杂性把握不足,因此,在文化史观上与高本汉尚无根本性区别。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计划”研究中的一些学者,批评了高本汉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现代方言为研究古代汉语的基础, 而不必参考古文献记录的证据, 而被称为“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e。他们的操作程序是,首先为每一种单独的方言群分别构拟出它们的原始语,如原始官话、原始粤语、原始吴语和原始闽语等,由此再构拟一个全面的原始汉语。构拟出来的原始汉语,不象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语言,而是带有内部变异的若干种历时系统。这种方式估且称之为方言逆推模式。这一派主要学者及研究成果有:华盛顿大学教授罗杰瑞Jerry L.Norman的《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和《原始闽语的韵母》(1981),耶鲁大学教授司徒修Hugh M.Stimson的《汉语原始北方话的研究:北京话的阴平调》(1969),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贝乐得William L.Ballard的《原始汉语:塞擦音初探》(1968)和《原始湘语及其他》(1970),华盛顿大学教授美籍华人余霭芹Anne Y.Hashimoto的《原始粤语的辅音和复辅音》(1970),乔治敦大学教授美籍华人杨福绵的《原始汉语的前缀* s—》(1975), 还有欧柯诺Kevin A.O'connor的《原始客家话》(1976)。“普林斯顿学派”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即“有兴趣以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进行构拟的汉学家”。关于普林斯顿假说,牵涉到如下问题:(一)、现代方言区内部的差异度。各大方言区内次方言或土语群之间可用于比较的差异度各不相同。豫燕语(不包括晋语、江淮语的北方话)内部较为一致,可比性不高,闽语有“十里不同音”之说,内部差异性较大,可比性较高。语言内部的差异度决定可比性,而可比性与构拟结果的复原度有着一定的制约关系。(二)、现代方言的存古度。换而言之,依据现代方言为基础构拟出来的早期语言,约当于什么年代的汉语言面貌。如抛开文献记录,一味依赖活语言构拟,其年代则无从确定。若以传统的中古音系为参照物,各方言的存古度是不同的。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所论南方几大方言形成的历史层次,吴、湘语是第一层次,粤语是第二层次,闽语是第三层次,客赣语是第四层次,这是依据分化论从发生学角度所做的假定。有证据表明,南方方言原来是非汉语言,由于汉文化与汉语的扩展才使土著语演变为汉语方言,因此这些方言中有可能残存土著语的底层成分。撇开这些非汉底层成分,由于影响的年代不同及方言演变的差异,闽语、粤语、吴语、湘语、客家话、徽语、赣语、江淮语、晋语、豫燕语各自的存古度大致呈递减状态。若以现代闽语为基础构拟出来的早期闽语可能约当于中古以前的汉语言,若以现代江淮语为基础构拟出来的早期语言可能约当于宋元明之间的不语言,但若以现代狭义北方话为基础构拟出来的早期“豫燕语”则只能约当于元明以后的汉语言。可见,依据现代各方言构拟出来的早期方言并不处于同一语史平面上,也就为继而逆推原始汉语带来极大困难。(三)、南方、北方语言的同源性。根据考古文化,中华大地上在新石器时代没有单一的原始母文化,这就表明没有相应的单一的原始母语,人种体质类型的差异及演变、历史文献的记载也支持着这一观点。与西欧的同一语言仅在某个别音素上有所差别的(如古希腊方言)不同,中国周秦汉时代的“方言”即邦言,是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音素的差别,而是词汇的不同、语法结构的不同,因而中国最早的方言学著作杨雄的《方言》表现为词语的网罗,而“转语”则是不同邦言之间借词引起的结果。现代汉语的几大方言的形成是秦汉以后华夏文明与语言对周边不同的文明与语言逐步扩散且同化程度各别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华夏汉语也受到周边语言的浸染而发生了巨烈的嬗变。普林斯顿学派试图以不平行的早期方言为基础,逆推出原始汉语,其结果还是个谜。虽然他们使用的材料及操作方法与高本汉大不相同,但立论的语史观还是相当一致。因而,高本汉曾经有过利用方言直接构拟早期汉语的设想,也就不足为奇了。显而易见,利用现代方言为基础构拟早期汉语的逆向推溯模式,是对一味依赖文献、仅将方言作为构拟音值参考的高本汉传统的反动与挑战,但是全然抛开历史文献,将汉语的演变发展与没有文献的语言的演变发展等同视之,不仅不能恰当地重建历史汉语,而且构拟会不着边际。
高本汉模式与普林斯顿模式,都是以“西洋镜”观察汉语史,难免游移于中国文化史背景之外。张琨模式已注意到结合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的转移来考察汉文学语言基础的变异,但对汉民族主体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生成与延伸背景尚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日本汉学家桥本万太郎(1932—1987)从文明类型入手,将东亚大陆语言确定为与印欧“牧畜民型语言”不同的“农耕民型语言”。在《语言地理类型学》(1977)里建立了与西方语言谱系说不同的“推移”理论模式。他认为,既然东亚大陆语言的现状在地理上表现出的类型推移是语言历史演变各层次的投影,从而便可以把“横”的区域考察与“纵”的历史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去追寻语言发展的踪迹。桥本审察汉语发展的视域已不限于汉语、汉语方言,而扩展至周边语言,构画出东亚大陆语言推移结构连续体。他立足于东亚大陆的民族移动和社会变迁,一直是从北向南展开的脉络,而中原地带经历过北方游牧民族不知多少次的反复入侵,过去的十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都处在北方阿尔泰诸民族的控制下,提出了北方汉语阿尔泰化与汉语同化南方语言的论断。推移模式不仅针对语音结构,而且涵盖句法结构与基本词汇,因此是一个完整的语言史研究模型。桥本实际上运用了文化圈理论,语言结构连续体区域推移状态与这一文化圈内文明传播方式互为表里。但是,桥本的观点受到大陆语言学界一些人的冷淡与抵制,据说主要是感情上接受不了“汉语是南北少数民族语言挤压形成”和汉语方言原是不同语言的结论。桥本理论草创,未能进一步细密,大陆一些学者又未加以深究,其中“汉语南北挤压形成论”即是一种误解,与桥本所论“北方汉语阿尔泰化并同化南方语言”不相切合。至于南方方言原与汉语是不同语言,这在先秦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始皇能书同文,但不能语同音。杨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方言为邦国之言,即不同语言,因此朝鲜语也收列其中。究其原因,国内语言学界受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太深,以为谱系树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未及对东西方语言的文化模式差异加以探索,实际上是固守“高本”而拒认“桥本”。此外,大陆语言学界由于种种纠缠不清的原因,存在着十分严重的轻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满足于引进国外理论而缺少跨学科的理论研究。语言学家追求语言研究的“纯正”,对文化史的研究不甚关心,对史前文化背影了解很少,更不用说运用文化圈、文化区域的理论,虽然不满意桥本模式,可又未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式。有趣的是,桥本在写《语言地理类型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中国大陆。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使人们感到莫名的悲哀。桥本的理论并非没有缺陷,推移论的基础“黄河文明中心一元扩展单动说”,与八十年代考古文化研究的成果大相径庭。但书成于七十年代,尚可理解。然正是这一“黄河文明中心说”,又与中国语言学界一些学者奉行的高本汉传统赖以成立的文化史观有相通之处。
二
推移方式应当是已经具有某个强有力的文明中心以后出现的态势。在这个中心形成过程中,层叠性混成才是这一中心区域语言发展的态势。
原始华夏语通行于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这一区域,北与阿尔泰戎狄,西与藏缅氐羌,东南与南岛夷越毗邻。华夏语与这些周边区域的语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而言之,河洛地区成了阿尔泰、藏缅、南岛三种文化与语言的交汇之处。历史语言学家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分别探讨华夏汉语与这三种毗邻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或语言接触中的渗透关系。
依据汉语与藏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和藏语同源,主张此说的西方学者有西门华德等,中国学者有王静如、俞敏等,其代表作如俞敏的《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本世纪初期,一些外国学者如康拉德、吴克德等,通过词汇对比证明在澳斯特利语(孟高棉语和南岛语)和汉藏语(汉泰语和藏缅语)之间有发生学关系,试图提出一个汉藏泰澳超级语系重新解释东亚及南太平洋诸岛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问题,并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些。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北部和中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凌纯声认为印尼人来源于中国中部的洞庭、鄱阳两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今天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法国学者L.沙加尔在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汉语南岛语同源论》。邢公畹同意沙加尔的观点,发表了《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依据汉语和阿尔泰语同质关联的部分,有人认为汉语与阿尔泰语有发生学关系。竟成的《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和《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对此做了初步探讨。竟成认为,汉语与阿尔泰语之间的关系可能反映了语系分化之前这一地域中的语言状况,因此有必要提出非谱系性或前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概念。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黄帝是北方游牧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根据黄帝擒杀蚩尤请风伯雨师,反映蚩尤族原在东南方,习惯于阴雨气候;黄帝请旱神女魃,反映黄帝族属于“迁徙无常处”的北方游牧部落,能适应干旱的环境。又据《国语》“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十二姓中有一些是戎狄,由此亦透露那些以黄帝为想象祖先的北方氏族部落,原来就是戎人和狄人,后来才融为华夏族。夏后氏,姒姓,也是戎人,夏禹亦称为“戎禹”。《诗经·商颂·长发》:“禹敷下土方”。土方,估计在今河套一带,夏后氏当是从这里沿黄河南下而进入中原。当夏后氏南下之后,有些戎人还居留在原地,如秦汉之“匈奴”,故《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由此推定,黄帝为北方阿尔泰人胡狄族之始祖。
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中华大地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即青莲岗文化系统、仰韶文化系统与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这三种文化创造者的体质特征分别为:蒙古人种南亚类型;蒙古人种东亚、南亚类型并存,青铜时代东亚类型;蒙古人种北亚、东亚类型并存,晚期趋于混合。这三种文化创造者的语言盖分别为:太古夷越语(原始南岛语)、太古氐羌语(原始藏缅语)和太古胡狄语(原始阿尔泰语)。与人种体质特征类型的混合相平行,语言的混成融合也不可避免。
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相互证发的是古史传说中的三大氏族系统:兴于江淮而发展至黄河下游的伏羲氏太皓,为夷越(苗蛮)之始祖;兴于渭水而发展至黄河中流的神农氏炎帝,为氐羌之始祖;兴于北方草原而后南下,直至江汉的轩辕氏黄帝,为胡狄之始祖。原始部落战争促成了华夏族的形成。共工与蚩尤战,为羌夷之战,西北与东南文化交流。共工败,炎帝“乃说于黄帝”,炎黄结成联盟,是氐羌与胡狄文化交流。黄帝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是北方游牧民族打败东南农耕民族。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是北方游牧民族战胜西北农耕民族。黄帝乘势进居江汉,“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黄帝的胜利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因此,被后世奉为“人文之初、华夏之祖”。游牧民族强悍,征战常胜,然农耕文明先进,因此,胜利了的统治者不得不被战败者的先进文化所同化。经颛顼(夷越系)、帝喾(夷越系)、尧(胡狄系)、舜(夷越系)、禹(胡狄系)的统治,华夏族在中原地区逐步形成。同时,原始夷越语、氐羌语、胡狄语也逐步混合而成原始华夏语。而没有卷进融合漩涡的周边初民,或留居旧土,或四处迁徙。西北的远至青藏高原,朔方的远至大漠以北,东南的越过长江,直至南太平洋诸岛。
夏人(胡狄系)未传文献,因此语言特征不明,但中原居民称“夏”始于此。商人(夷越系)语言中,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顺行结构NA为南方语言之特色。周人(姬姓,承黄帝之姓;其祖母姜原,姜人与羌人同种;周人盖氐羌与胡狄之混血)来自西北,在其统治的几百年间,使华夏语“氐羌化”,形成了“氐羌”色彩浓烈的以王畿一带方言为基础的“雅言”。“雅”与“夏”古语相通,周人自称“有夏”,所谓雅言即“夏言”。没有融合同化的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则被姬周视为“异族”,于是有夏、夷之别。在氏族或民族融合中得以形成并发展的华夏语,不可能是纯粹的而不是混成的,只是古代华夏语言的异质性与聚合性被传至后世的表意文字掩盖了。
由此可见,不管是汉、藏同源说,汉—南同源说,还是汉—阿同源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依据各自选择的材料——语言材料、人种学与文化史方面的材料——分别论证了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同源发生关系。原始华夏民族的形成是史前民族或种族融合的结果,与之同步发展形成的华夏语不可能不具有与其被吸收融合语言的对应之处。与其说汉语仅仅与某一语言有同源发生关系,不如说在发展的长河中,后来被称为“华夏汉语”的这种语言与毗邻三大语言的祖语都先后出现过渗透、换用与混成关系,换而言之,原始华夏语就是一种多元性的层叠性的混合语。
混合语既是语言混合的结果,又是文化融合的现象。居住在云南的蒙古族一支,自称卡卓,所操现代卡卓语即为白语与彝语混合而成的混合语。广西融水县永乐乡壮族居民,操一种“五色话”,即由汉、壮、仫佬、毛难、侗五种语言混合而成的一种语言。青海同仁县一部分土族居民所操的“五屯话”,也是一种长期受到藏语影响,以汉语为基础发展而成的混合语。所谓“五屯”,有人称作“五通”,即兼通汉、藏、蒙、土、撒拉五种语言。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或语言谱系树模式占统治的时代,不恰当地强调语言的分化,而将语言的混合忽略了。
在华夏语的混成发生过程中,语言的渗透、换用、融合相当错综复杂,引起了音节结构的变化,以至语言类型的转变。根据研究可以推测,不同语言混成华夏汉语的结果则是由原初的单词语音结构双音节——由于前一音节元音的弱化脱落——演变为带有复辅音的单音节,随着辅音音缀的相继失落,最终形成了单辅音的单音节结构,语言类型由粘着型转变为孤立型。现存中国最古文献,多为周秦时代所撰。因为周人是氐羌与胡狄之混血,所以周代文献《尚书》、《诗经》中的语言,既与藏语有同源之处,双音节词中又具有与阿尔泰语元音和谐相似的特征。因为周人因袭了夷越系的殷商文化,而东夷、百越、南蛮又未能一下子同化,所以在古代汉语中仍然可以发现大量的与南岛语言对应的词项。
秦汉以来,以三次大动乱(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为高峰,北方游牧民族象潮汐有时,呈周期性向中原农耕文化区域泛滥,一次次逐鹿中原,大有步黄帝遗踵之雄风,屡屡建立王朝,统治中原乃至南北。从始皇结束姬周封建联邦制统一中国,到清帝皇冠落地的2132年间,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原和全国长达840年之久, 这还不包括具有鲜卑血统的隋唐王朝统治中国的326年。在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时, 中原士族居民大量南迁,近徙江淮,远至闽广。汉语在人民迁徙与民族融合中“北杂夷虏,南浸吴越”,于是出现了北留汉语的阿尔泰化与南迁汉语的南方化,与之相应的是阿尔泰语的汉化与南方语言的汉化,形成了桥本万太郎所描述的那种东亚大陆语言结构连续体的状态。
毫无疑问,推移模式反映了周秦以后汉语与周边语言相互影响、互动发展的基本态势。但是,只有在强大的文明中心形成以后,才有以汉语为主导的推移性延伸。在强大的文明中心形成过程中,周秦以前的中原汉语以混成趋势为主。如果不进行寻根推源式的探讨,中原汉语则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成了周秦以后周边南北少数民族语言的混合物。依据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与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系统、人种体质类型,与古史传说中的氏族系统及原始氏族战争等史料相互印证,我由此提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进而,对桥本万太郎“推移”模式加以修正,力图建立“混成发生、推移演变”的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
三
总之,关于东亚大陆语言发展的历史态势,可以设定远古有着多种不同的,但可总括为三大远古语系的语言;在民族接触交流中,不管是战争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在三大考古文化交汇的河洛地区,形成了一种与强大文明相伴随的混合型语言;这种混合型的华夏汉语,伴随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及中原文明的辐射,像一个巨大的漩涡,逐步地同化着所接触到的周边南北语言,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改变着自己。依据这一观点,可以认为,周秦以前中原地区的语言发展主流是因交替换用而出现的混成,与华夏民族的融合形成、华夏文明的崛起勃发相一致;秦汉以后汉语的发展因北方民族进踞中原、中原士族南迁而出现的推移,表现为中原北留汉语的阿尔泰化和南迁汉语的南方化及阿尔泰语的汉化和南方语言的汉化,与汉民族和汉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延伸相一致。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文明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冲突并趋于融合的历史;与之相应,华夏汉语语言史就是一部多种民族语言混成推移交融的历史。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体现着一定的语史观。语史观所涉及的并不限于语音史,它涵盖以语音史为基础的词汇史、语法史。语史观也并不仅仅是语言历时演变史观,其深层是文化史观。文化史观的转变,会引起语史观及研究模式的嬗变。研究方法——理论模式——语史观——文化史观,四者层层深入,由表及里。因此,“混成发生、推移演变”模式的价值并不仅在汉语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标签:方言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南方与北方论文; 中国语言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语言史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切韵论文; 高本汉论文; 中原论文; 阿尔泰语论文; 汉藏语系论文; 官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