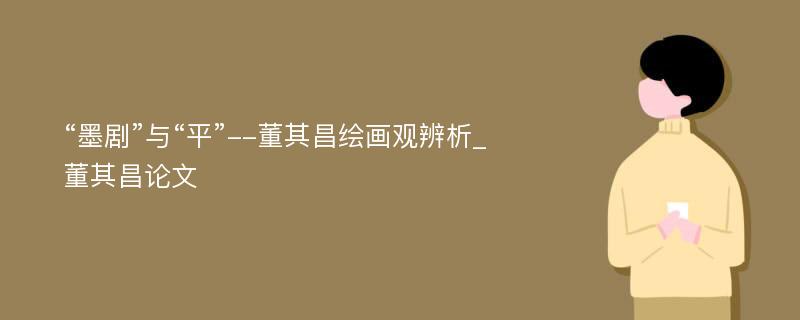
“墨戏”与“平淡”——董其昌绘画观一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淡论文,墨戏论文,观一辨论文,董其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气韵必在生知,转工转远”
董其昌评画,大旨而言,是精工与超逸并举的。他说:“赵令穰,伯驹,承旨,三家合并,虽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虽纵而有法。两家法门,如鸟双翼。吾将老焉。”①赵令穰们走的是“精工之极”(“妍”)的画路,而董源们却以“平淡天真”(“纵”)为画旨。这两路画家本是董氏“南北二宗论”中的对峙者,但是,一者“妍而不甜”,另一“纵而有法”,则构成了绘画达成至高境界而不可或缺的“两家法门”。
然而,董其昌的偏好依然是明显的。在文人画(南宗画派)开山祖王维之下,他独尊董源。他认为宋元明文人画大家皆是董源的“正传”、“衣钵”。在宋代画家中,他以米芾、米友仁父子为最高,认为米氏父子深得董源之意,说“不师北苑,乌能梦见南宫(米芾)耶”。同时他认为“元季四大家,独倪云林品格尤超”,称其“一变古法,以天真幽淡为宗”,而倪云林的根基在董源,“若不从北苑筑基,不容易到尔”②。米芾在《画史》中评价董源说:“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③董其昌对董源的推崇,正以米芾所谓“董源平淡天真多”立意。
董其昌对董源、倪瓒们的推崇,有其现实的针对。在晚明画坛,以商养画,不仅匠气隆重,而且模仿之风泛滥,似无规范而又俗套流行。董其昌所要反对的,是拘于技艺的“画史习气”和以名家自恃的“纵横习气”。在他看来,这样的画风就是绘画品质由“古淡”而堕入“甜俗”的根源。他说:“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④“画史习气”源自北宗李思训父子以尖硬的线条勾勒、着色绘山水,追求的是“刻画之工”。南宗王维开始用破墨晕染(渲淡)的手法绘山水,“一变钩斫之法”,而董源则师王维而出,“脱尽廉纤刻画之习”,“以墨染云气,有吐吞变灭之势”⑤。倪瓒在元代画家之中境界最高,就是因为没有画史习气,是米芾之后“古淡天然”的第一人。
关于精工和平淡的关系,苏东坡曾有一段论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⑥其后,朱熹也说:“今人言道理,说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处极难。被那旧习缠绕,如何便摆脱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个新巧易作,要平淡便难。然须还他新巧,然后造于平淡。”⑦东坡和朱熹都以平淡为文艺的终极境界、最高追求,但是,他们又都认为平淡是建立于精工之极(绚烂、新巧之极)的基础上的,是对后者的超越,即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对于东坡、朱熹之论,董其昌是赞同的。他说:“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⑧而且,他对于自己过分强调平淡超逸而可能荒废技艺、以不“工”为“淡”的思想,有专门的警惕。他说:
画家以神品为宗极,又有以逸品加于神品之上者。曰:失于自然,而后神也。此诚笃论。恐护短者篡入其中。士大夫当穷工极研,师友造化,能为摩诘,而后为王洽之泼墨,能为营邱,而后为二米之云山。乃是关画师之口,而供赏音之耳目。⑨
董其昌认为,要达到倪瓒绘画的“逸品”境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穷工极研,即在技艺上达到“精工之极”的程度;师友造化,即在精神上要以自然为师,与自然同化。
但是,董其昌并不认为“穷工极研”(或“精工之极”)就能达到“淡”的超逸境界。他说:“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有(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⑩“潘子辈学余画,视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与语也。画有六法,若其气韵,必在生知,转工转远。”(11)“淡之玄味,必由天骨”,“若其气韵,必在生知”,其意都是指平淡超逸的气韵,是从画家人格性情中来的,非但不是来自艰苦顽强的技能训练(“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反而会因为专务于技艺精进而远离(“转工转远”)。实际上,承认“工而后淡”的董其昌还是认为,技艺的不足并不构成韵致的缺陷。他在将赵令穰与倪云林作比时就说,虽然倪“工致不敌”,但以“荒率苍古”胜。“荒率苍古”当然是淡的极高境界,归于“逸品”之韵,是单凭艺术功力所不能达到的。董其昌评沈周学倪瓒时说:“盖迂翁妙处,实不可学。启南力胜于韵,故相去犹隔一尘也,逊之为迂翁萧疏简贵。”(12)
二、“米家墨戏,足正千古画史谬习”
董其昌对米氏父子的“墨戏”绘画,推崇有加。所谓“米家墨戏”,是指米氏父子独创的描绘山水的手法和风格。宋人有如下介绍:“米南宫多游江湖间。每卜居,必择山水明秀处。其初本不能作画,后以目所见,日渐模仿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13)“米友仁,元章之子也。……天机超逸,不事绳墨,其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其风气肖乃翁也。每日(自)题其画曰:‘墨戏’。”(14)作为一种绘画手法和风格,“墨戏”有两个特点:其一,从绘画技法而言,重晕染而略刻画,用董氏话说,是“有墨无笔”;其二,从创作状态而言,可谓是率性自然,不拘楷法。
董其昌认为,“有笔无墨”的特点是“见落笔蹊径而少自然”;“有墨无笔”的特点是“去斧凿而多变态”。“有笔无墨”是“明”的画风,而“有墨无笔”也就是“暗”的画风。“画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棱钩角是也,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15)董其昌有“画家之妙,全在烟云变灭中”之说,看米友仁的代表作《云山墨戏图卷》(又名《潇湘白云图》)、《潇湘奇观图》(又名《海岳庵图卷》)等所展现的“云横雾塞”的“墨戏”确实非常吻合董氏的山水画理念。董其昌说:
米元晖作潇湘白云图,自题云:夜雨初霁,晓云欲出,其状若此。此卷余从项晦伯购之,携以自随。至洞庭湖舟次,斜阳篷底,一望空阔,长天云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戏也。自此每将暮辄卷帘看画卷,觉所将卷为剩物矣。(16)
“每将暮辄卷帘看画卷,觉所将卷为剩物”,是高度肯定了米友仁绘画与自然山水的吻合和印证。所谓“觉所将卷为剩物”,并非否定米氏画卷的价值,而是指出米画与山水可以互为替代。无疑,董氏此题着眼于画境再现山水的真实性。但是,在董其昌的收藏中,还有他至为推崇的董源的《潇湘图》,而此图所展现的潇湘景致,与米氏所绘完全不同。董其昌题此图说: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于长安。卷有文寿承题,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图也。既展之即定为潇湘图。盖宣和画谱所载而以选诗为境。所谓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耳。忆余丙申,持节长沙,行潇湘道中,蒹葭渔网,汀洲丛木,茅庵樵径,晴峦远堤,一一如此图。令人不动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画为假山水,而以山水为真画者。何颠倒见也。(17)
正如董其昌所言,董源笔下的潇湘景致,不仅山水树石历历在目,而且渔人淑女宛然可悦,是一派“山川奇秀”之景;它与以“米家墨戏”手法呈现的“长天云物,怪怪奇奇”的潇湘风貌是大不一样的。董源与米友仁的区别,以景物观照和模写而言,前者着眼于稳定、具象的山水,后者着眼于流动、变幻的云烟。
同一景致,董源为何以山水为重,而米友仁却属意流云呢?董其昌对此问题有特别的思考。他题米友仁《海岳庵图卷》说:
元晖未尝以洞庭北固之江山为胜,而以其云物为盛。所谓天闲万马,皆吾师也。但不知云物何以独于两地可以入画。或以江上诸名山所凭空阔,四天无遮,得穷其朝朝暮暮之变态耳。此非静者,何繇深解。故论书者曰:“一须人品高。”岂非品高则闲静,无他好萦故耶。(18)
米友仁的“墨戏”,不写山川奇秀,而写长空流云的变化,展现的是“天闲万马”式的悠然闲静。宋代姜夔论书法说:“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19)董其昌认为,米友仁作画,属意云烟,是出自其“品高则闲静,无他好萦故”。米友仁自题《海岳庵图卷》说:
先公居镇江四十年,作庵于城东高岗上,以海岳命名……卷乃庵上所见山,大抵山之奇观,变态万层,多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知此。余生平熟潇湘奇观,每于登临佳处,辄复写其真趣于卷,以悦吾目,并非他人使为之。此岂悦他人之物者乎?此纸渗墨,本不可运笔,仲谋勤请,不容辞,故为戏作。(20)
“写其真趣于卷,以悦吾目,并非他人使为之”,这就是“品高则闲静,无他好萦故”。这实则就是米氏父子以绘画作“墨戏”的精神所在。米芾自题《云山卷》说:
世人知余喜画,竞欲得之。鲜有晓余所以为画者,非具顶门上慧眼者,不足以视,不可以古今画家者流画求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著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寥廓同其流荡。焚生事,折腰为米,大非得已。(21)
可见父子精神一致。
米芾称“余所以为画者,非具顶门上慧眼者,不足以视”,而米友仁亦称“余墨戏气韵不凡,他日未易量也”(22)。依董其昌之说,小米有“王维画皆如刻画,不足学”之论,可见米氏父子高标自许。董其昌对米友仁也有所批评:“元晖睥睨千古,不让右丞,可容易凑泊,开后人护短径路耶。”(23)但是,对于米氏父子“惟以云山为墨戏”的绘画精神,董其昌仍然给予高度肯定。他说:
米元晖自谓墨戏,足正千古画史谬习。虽右丞亦在诋诃,致有巨眼。余以意为之,聊与高彦敬上下,非能尽米家父子之变也。(24)
高克恭是与赵孟頫同时的元代重要画家。董其昌说:“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独高彦敬兼有众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刀余地,运斤成风,古今一人而已。”(25)此话足见董其昌对高氏评价之高,但是,他又认为自己学二米,“以意为之”,可以与高克恭一比高低,却不能“尽米家父子之变”。因此,董对米氏父子的推崇是无以复加的。
董其昌极力推崇米氏父子,正如他在南北二宗论中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一样,根本着眼点不在于绘画技法,而在于绘画精神。“米元晖自谓墨戏,足正千古画史谬习”,这句话道出了他的用意所在。所谓“千古画史谬习”,就是汲汲于功名、拘束于规范的画家习气。“墨戏”的本质是“得诸笔墨蹊径之外”。董其昌说: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尝敢以耗气应也。尤精者,或以醉,或以梦,或以病,游戏神通,无所不可,何必神怡气王,造物乃完哉?世传张旭,号草圣,饮酒数斗,以头濡墨,纵书壁上,凄见苦雨,观者叹愕;王子安为文,每磨墨数升,蒙被而卧,熟睡而起,词不加点,若有鬼神。此皆得诸笔墨蹊径之外者。(26)
董其昌明确将米芾评介为“在蹊径之外者”。他说:“宋人中米襄阳(米芾)在蹊径之外,余皆从陶铸而来。”(27)所谓“从陶铸而来”,就是在规范模式的学习训练中得到画艺的培养,是“画史谬习”的根源所在。对“画史谬习”的批评,由庄子开始。庄子早在战国时代所批评的那些在宋元君面前“受揖而立,舐笔和墨”的画史就是“画史谬习”的代表者,而那个被他称赞为“真画者”、“解衣般礴臝”的画史,就是“墨戏”的开山祖宗了: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28)
“在蹊径之外者”,如米芾父子,是创作手法和精神状态都达到了无拘无束、自然超逸的境界,这就是庄子所谓“解衣般礴臝”的“真画者”。
三、“质任自然,是之谓淡”
董其昌认为,艺术能否成为传世之作,根本在于能否到达“淡”的境界(“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关于什么是“淡”,他有如下论述:
撰造之家,有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者,极其才情之变,可以无所不能。而《大雅》平淡,关乎神明。非名心薄而世味浅者,终莫能近焉,谈何容易?《出师二表》,表里《伊训》。《归去来辞》,羽翼《国风》。此皆无门无径。质任自然,是之谓淡。乃武侯之明志,靖节之养真者何物?岂澄练之力乎?六代之衰,失其解矣。大都人巧虽饶,天真多覆。宫虽叶,累黍或乖。思涸,故取续凫之长;肤清,故假靓妆之媚。或气尽语竭,如临大敌,而神不安。或贪多务得,如列市肆,而韵不远。(29)
从上段论述,可以概括出“淡”的三个要素:其一,“淡”是一种神妙而超越的境界,“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其二,“淡”须以淡薄名利、超越世俗之心才能体认,“非名心薄而世味浅者,终莫能近焉,谈何容易”。其三,“淡”的本质是自然而行,没有模范可依;虚假造作,贪多务得,均不能达到“淡”。“质任自然,是之谓淡。”不能达到“淡”,则“神不安”、“韵不远”。
“淡”是自先秦以来,由道家哲学发端的一个哲学理念。老子说:“道之出口,淡乎其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30)他是将“淡”作为宇宙万物之根本“道”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也决定了相应的人生观念:“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无味”就是“淡”。王弼注说:“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之极也。”(31)循老子的哲学,庄子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32)这种“以淡为本”的宇宙观延伸为人生哲学,就形成为一种隐逸于万物,而游心于无穷的人生情怀。庄子用一则寓言表达这个观念: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33)
“天根”询问如何治天下,而“无名以答”,此则寓言的隐喻,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实质就是“质任自然”。但是,庄子还是给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就是“治天下”的根本是将自我生命投放于大千世界,消除刑名篱樊,合于大道(“与造物者为人”),以自然无为之心处事应物(“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
“以淡为本”的宇宙观,同时也形成相应的生命观和养生观。庄子说:
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34)
庄子认为,养生保命的要义是在知行两方面都不做生命所不能做之事。要保养身体,必须用相应的物品,但是物品富裕,并不就能保全身体。生命的存在是以身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有身体,并不等于有生命。人对于自身的生命存亡,是没有最终决定权的,人所做的养生行为,是“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形(身体)不等于生(生命),但生不能免于形(“其为不免矣”),而养形又并不足以保生。如此,人究竟应当如何处置为好?庄子说:
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35)
“弃世”就是弃事,即不以世事劳累其身,“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就是忘生,即不操心于生死存亡,“遗生则精不亏”。庄子认为,人生在世,就不免于有身体存在,而且以之为累;要求生命的保全和精神的自在,应当采取的途径,不是抛弃身体(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弃事忘生。如果我们能做到弃事忘生,就可以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获得保全统一,并且实现与外在世界的融合(“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弃事忘生,是将“淡”的人生哲学应用于自我身体的表现。“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应用于外,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应用于内,就是弃事遗生,其本质是隐逸的生命精神。
在中国绘画史上,对“平淡天真”的画风的追求,是本于庄子所开辟的“隐逸”的生命精神的。就绘画而言,“隐逸”并非是形体隐于山林,而是生命“隐于画史”。米芾《画史》序言说:
杜甫诗谓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甫老汲汲于功名,岂不知固有时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秕埃坷,奚足道哉?虽孺子知其不逮少保……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无足为者。尝作诗云:“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36)
米芾将王者之功与书画之事对比,认为王者之功虽然威赫一时,转眼却成妇孺眼中的笑柄,而书画却可持久传颂,为人争购、珍藏。在米芾看来,现实功名追逐,不过是一场游戏,只是其中人不知道辜负了人生,而书画之妙,才是人生寄乐处。“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描绘的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书画自娱的悠闲逍遥的状态,是米芾“平生所嗜,此外不足为”之事。
米芾重书画、轻功名之论,可与曹丕《典论·论文》之说相比较。曹丕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37)
与米芾一样,曹丕也以功名为轻,文学为重。但是,曹丕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与米芾不同的。米芾认为书画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越帝王功业,具有更广泛、持久的效用。在曹丕看来,古哲先贤创文制经,是为抗御生命的流逝而成就永垂不朽的大业、盛事;在米芾看来,书画不过是“平生所嗜,此外不足为”的寄兴自娱之事。对于米芾,“忘怀万虑,与碧寥廓同其流荡”,是书画的真趣所在。
董其昌的生平,是很可以看作庄子的养生哲学的实践。清代学者姜绍书的《无声诗史》对他有一个概要的介绍: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华亭人。万历戊子、己丑,联掇经魁,遂读中秘书,日与陶周望望龄,袁伯修中道,游戏禅悦。视一切功名文字,黄鹄之笑壤虫而已。时贵侧目,出补外藩,视学楚中,旋反初服。高卧十八年,而名日益重……及魏阉盗权,士大夫跼蹐救过不暇,人皆叹公之先几远引焉。崇祯间晋礼部尚书。年近大耄,犹手不释卷。灯下读蝇头书,写蝇头字。盖化工在手,烟云供养,故神明不衰乃耳……画仿北苑、巨然、千里、松雪、大痴、山樵、云林。精研六法,结岳融川,笔与神合,气韵生动,得于自然。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也。(38)
董其昌出身贫寒,科举入仕,功名显赫,但并不汲汲于权位,相反,屡次向皇上请辞返乡。他在朝中任官时,经历了明代历史上最黑暗残酷的宦官魏忠贤专权时代,但他虽然倾向东林党,却并未招致魏党的清洗;及至魏忠贤被惩处的时候,他又早已离开朝廷,隐息乡里。在文艺上,他与公安三袁交往甚深,“游戏禅悦”,但他既未顺从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主张,又没有真正遁入禅家的清寂(39)。他的一生事业,功名显盛,却难言功业;书画传世,但他只以寄乐翰墨自许。“视一切功名文字,黄鹄之笑壤虫而已”,这句话如果不能作为他平生的完整写照,至少也是他一生进退成毁的感慨体悟。董其昌出入仕途,可理解为庄子所谓“不免于形”的作为,而他时时知退,在位高权重时请辞,则是“弃事忘生”之为。正是有这入世中的“弃事忘生”,使他的人生显赫而依然“平淡天真”,“形全精复”。“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庄子此言,董其昌实践于生活,而成就于书画,这就是他所说的“画中云烟供养”。他说:“黄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颜。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无疾而逝。盖画中云烟供养也。”(40)他自己也如是(41)。
庄子提出“以淡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也提出了“不形之形”的形式观。庄子认为,“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人的形体也是来自于无形而复归于无形的。他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袠,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42)
老子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说。依老子之言,我们可以将庄子之言理解为:“不形”是万物之本,即“道”;“形”是对道的表现。“道”是无形的,但必然表现于“形”,是“不形之形”;“形”表现无形的道,故是“形之不形”。“形”与“不形”,在两个意义上是不可分的:其一,“形”的根本是“不形”,“不形”存在于“形”中;其一,“形”作为具体有限的存在,来自于“不形”,又必归于“不形”,“形”与“不形”是相生相灭、相始相终的。因此,“不形之形”即“形之不形”,本无分别,本无可言。庄子所提供的是“形”与“不形”相统一、相转化的观念,进而启示人们从与生俱来的“形名”约束中解脱出来(“解其天弢,堕其天袠”),从而默然合于天地自然的生化运行。他说:“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43)
“刻雕众形而不为巧”,这就是“淡”在形式上的体现。这种“淡”,是源于对生命的形而上体验,并且化成了一种生命精神和人生性情。董其昌追随米氏父子,反对绘画的“刻画”之功,主张“画欲暗不欲明”,是从庄子的哲学精神而出的。他说:“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44)所谓“天骨”,就是“以淡为本”的人生情怀。
*本文引用古籍,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刘文俊总纂《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照相版),北京爱如数字化技术中心出品。
注释:
①⑤⑧⑨(12)(15)(16)(17)(18)(24)(25)(27)(40)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四,明崇祯三年董庭刻本,第328页,第345页,第342页,第343页,第342页,第342页,第338页,第336页,第338页,第331页,第339页,第332页,第328页。
②(11)(2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34页,第23页,第29页。
③(36)米芾:《画史》,明《津逮秘书》本,第3页,第1页。
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录考》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页。
⑥赵令畤:《侯鲭录》卷八,清《知不足斋丛书》本,第52页。
⑦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
⑩(29)(44)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一,明崇祯三年董庭刻本,第284页,第78—79页,第284页。
(13)赵希鹄:《洞天清录》,清《海山仙馆丛书》本,第18页。
(14)邓椿:《画继》卷三,明《津逮秘书》本,第9—10页。
(19)姜夔:《续书谱》,明《百川学海》刻本,第6页。
(20)(21)(22)汪砢玉:《珊瑚网》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7页,第465页,第477页。
(26)董其昌:《容台集》文集卷二,明崇祯三年董庭刻本,第82页。
(28)(32)(34)(35)(42)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9页,第457页,第630页,第632页,第746—747页。
(30)(31)《老子》,《古逸丛书》影唐写本,第18页,第33页。
(33)(43)郭庆藩:《庄子集释》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2—294页,第281页。
(37)萧统编《文选》卷五二,胡刻本,第1155页。
(38)姜绍书:《无声诗史》卷四,清康熙观妙斋刻本,第31页。
(39)关于董其昌“貌禅实庄”,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255页)。
(41)此处对董其昌的评价,仅是从生命精神的层面解读这位经历明代数朝帝王而全身而退的礼部尚书董其昌。无疑,现实层面的董其昌,远比此处的评价复杂、矛盾。可参见高居翰《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5—157页)。
标签:董其昌论文; 米芾论文; 书法论文; 艺术论文; 董源论文; 四库全书论文; 美术论文; 米友仁论文; 容台集论文; 书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