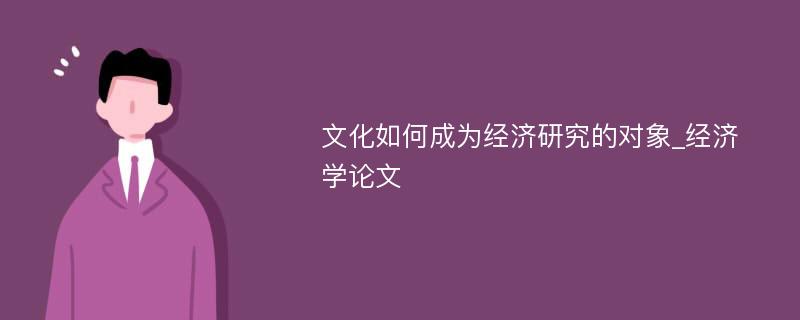
文化如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象论文,文化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02-0005-08
自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手段乃至整体研究视野不断扩展递进,各种新学术流派轮番登上理论舞台,为经济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一幅幅精彩多姿、激动人心的理论画卷。近几十年来,关于文化与经济增长关联的研究逐渐增多[1],一门系统的文化经济学似乎正在酝酿形成之中。对此有理由作一审慎追问:一门独立的文化经济学是可能的吗?经济学人需要为经济学众多“独立学派联合体”的又一个新成员——文化经济学——的到来和加入做好准备吗?
一、经济学研究视野的递进
经济学家最初是从比较容易观测感知的客观物质变量来探讨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奥秘。从斯密一直到马歇尔,主要把劳动力、土地(包括矿藏、水源等自然资源)、资本(包括厂房、机器等实物资本)等具有客观物质属性的生产要素视为财富生产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进一步发现,一些不易被观测感知的非物质变量也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如技术、知识、信息、法律、制度等经济变量,它们本身并不是一种客观物质要素,而是人类主观精神思维的成果,但是它们通过嵌入、影响和改变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客观物质生产要素而对经济过程产生重要作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技术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不仅如此,经济学家此后还进一步发现,那些无法通过感官直接观测感知的纯粹主观精神变量也对经济活动从而对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精神因素由此也渐次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阈。譬如,经济学家把关于经济前景的乐观或者悲观预期的心理因素——信心——作为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重要影响变量,由此编制出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作为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参数①。经济学家还研究发现,天性乐观、充满希望的民族和人群比天生悲观的民族和人群有更好的经济增长前景[2]。诚信和信任也成为经济学家研究认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精神变量。福山等经济学家发现,具有诚信精神和相互信任心态的人群和地区,比欺诈和投机盛行因而难以达成人际互信的人群与区域,具有明显较快的经济增长速率[3]。因为地区人群的诚信和互信精神可以显著降低交易与管理成本,扩大交易与相互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耐心也是经济学家观测到的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影响的心理因素,能够忍受挫折与劳苦、锲而不舍地追求经济发展的民族和区域人群,总会比其他民族和区域人群更加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
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初,韦伯就系统地论述了基督教信仰和价值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韦伯发现,基督教“天职”观和克勤克俭的价值取向、行为范式对资本主义早期职业人格的塑造形成具有明显作用[4]。韦伯的思想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领域获得了强烈反响,使他很快成为蜚声世界的重要思想家。然而,韦伯的理论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积极回应与认同。深受经验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无法在自身的经验实证理论框架内接纳文化精神这种主观理论元素。所以韦伯以后很久,文化与经济的关联主要成为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研究领域,而迟迟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
哈耶克是游走在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交叉边缘地带的经济学家,他一直关注宗教信仰、家庭与社会情感、文化习俗等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与关联[5]。他和他所归属的整个奥地利学派偏重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的理论风格和思维进路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证体系始终处于龃龉冲突状态。与哈耶克同属于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把企业家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创新力量,认为企业家特有的精神禀赋是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者的基本精神因素。熊彼特在《经济发展原理》一书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对企业家的精神特质作了深入细致剖析[6]。显然,韦伯关于文化价值与精神禀赋作用于经济过程的思想长期以来主要只是在奥地利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一丝回响,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
主流经济学家虽然不屑于在自身的语境与理论逻辑中讨论文化,因为把文化这个无法通过经验把握的研究对象纳入经济分析不符合经济学深陷于其中的经验实证主义理论传统。但是,经济学家又无法回避一个国家、区域的文化价值精神会影响该国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愈益深入人心的“韦伯命题”。所以,一些受主流经济学理论教条禁锢较轻的经济学家,如诺斯,开始把被主流经济学从正门排斥出去的东西经过改装打扮后又从后门迎了进来。诺斯沿袭了制度学派的基本理论立场,把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背景条件。诺斯认为,不仅由明确的法律典章规定的“显性”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而且由看不见的文化习俗、价值传统、伦理精神、行为习惯等文化因素决定的“隐性”制度同样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7]。被韦伯指认为“文化”的东西,在诺斯那里被作为与“显性制度”不同的“隐性制度”进入了经济学。循由诺斯开辟的这条理论通道,经济学家得以开始了与文化这种主观精神变量对话的理论行程。在诺斯之前,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的理论研究对象要么是具有典型的客观物质属性的对象,如:劳动力、土地、厂房、机器、货币等,要么是以某种客观物质为载体的对象,如:知识、技术、信息、制度等。而经过诺斯的这个理论转换,一种纯粹的主观精神变量被纳入以经验实证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经济学与文化精神对接的第二条理论通道则是由舒尔茨开辟的。舒尔茨发现,人的作用与价值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日益彰显。他把人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禀赋视为一种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认为这种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与传统物质、金融资本相媲美甚至超越[8]。在对人力资本概念的深入阐述中,舒尔茨把人力资本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由教育和研发(R&D)造就形成的知识、技术型人力资本,另一类是源于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宗教传统的文化人格和精神型人力资本。通过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范式,文化精神这种主观精神变量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进入了经济学。但是,后来经济学家在承接和阐释舒尔茨人力资本概念的理论意蕴时,多只是关注能够通过教育科研投入金额、大学毕业生人数、技术发明专利数量等客观指标加以测度的第一类型人力资本,而把尚无有效方法进行客观经验测度的第二类型人力资本有意抛舍掉。尽管如此,文化精神这个由韦伯最先发现的影响和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变量,经过诺斯和舒尔茨分别提供的两条曲折理论通道,终于在经济学家视阈里绽出了。文化精神无论是通过诺斯的隐性制度还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进入经济学,都表明经济行为人群体的主观文化精神禀赋是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不可忽略的重要决定因素。经济学家不仅需要考虑自然资源、环境气候、资本禀赋等客观物质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仅需要考虑法律、制度、技术、信息等软环境条件和经济行为人群的教育水平、技术能力、健康状态、食物营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需要研究经济行为主体的文化人格和精神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不同国家、民族、区域的文化习俗、价值传统、精神风尚存在的差异性,会显著影响其经济发展的路径与绩效,这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直观事实。
令人欣慰的是,自诺斯和舒尔茨以后,开始有更多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文化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迈克尔·波特在分析探究不同国家、区域经济竞争力差异形成的原因时写道:“我们发现,某些信念、态度、价值观确实有助于经济繁荣和发展”;“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9]43劳伦斯·哈里森在跟踪研究非洲、拉美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时也同样发现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他由此得出结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9]6塞缪尔·亨廷顿也在研究中发现,韩国和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60年代初时还大致相等,但是30年后,韩国发展成为世界排名第14位的工业化国家,而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韩国的1/14。他总结道:“发展快慢如此悬著,能作何解释呢?无疑,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是一种重要原因”。[9]2显然,文化已经叩动了经济学家的理论良知,成为经济学家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变量。不考虑文化精神因素,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虽然照搬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大量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技术与资本,然而却长期不能摆脱贫困与落后的“陷阱”;也不能解释中国国内不同区域在相同制度环境和资源要素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发展差异。
二、文化难以融入经济学的原因
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尽管难以排除文化精神因素的影响,但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内文化精神变量又始终被隐匿遮蔽,其主要原因有:经济学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深受十八世纪欧洲机械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学诞生的十八世纪是欧洲机械唯物主义思潮十分盛行的一个时期。受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影响,当时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土地、气候、矿藏、机器等客观物质要素和自然环境对经济过程的决定作用,几乎完全忽视人的主观精神因素与经济活动过程的内在关联。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拉美特利关于“人是机器”的思维逻辑与理论隐喻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经济学家普遍把具有丰富精神个性的经济行为人贬降为与物质形态的机器无异的“动力机”,人的精神性在当时经济学家的理论视阈里几乎完全消失了。经济学将人作“拟物化”处理是对经济运行过程作机械物理运动理解的需要。作为十七、十八世纪最高科学成就和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最有力科学佐证的当时的牛顿物理学,把宇宙空间所有运动都理解为机械力学运动,并且为这种机械力学运动提供了一种精确而完美的分析计算工具。但是,这种几乎完美无缺的机械力学理论却无法用来分析和把握非物理属性的人的主观精神活动,更无法用它来分析人的主观精神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与作用。因此,只有将人“去精神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才是可能的。但是这样造成的理论失真,却是从此人的主观文化精神因素对经济过程的密切关联、作用与影响,被排除到了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视阈之外。斯密写《国富论》时,把经济行为人丰富的精神特质舍弃后,仅仅保留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趋利性[10]。斯密作了这样的理论抽象之后并没有真正忘记人的主观精神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而引起内心理论直觉的严重不安。斯密在随后花费巨幅笔墨撰写的《道德情操论》中,又深入细致地剖析了人的多方面主观精神禀赋,如同情、慈善、利他等情感及其对人的行为理性的影响[11]。与斯密不同,马克思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了另一种抽象。马克思把在自由自在活动中全面实现人的本质能力作为人的真实需求,而把斯密视阈中的“理性经济人”视为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异化”扭曲的人[12]。以此为理论基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人的丰富精神本质的摧残和毁弃,是使人从人的本质背离沦落异化的社会现实力量。马歇尔是斯密以后西方经济学的综合继承者。他遭遇到与斯密相同的理论窘境:一方面要坚持人的动物式的趋利性,另一方面又要守护人的精神崇高和伦理价值追求。所以,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多处表现出对人性理解的犹豫和迟疑,以及在对人的物质自利性和同情利他心分析判断时来回理论跳越和心灵颤抖的心路历程[13]。
在马歇尔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学又深受经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经验数据计量检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工具手段,也成为经济学家选择研究变量的基本准则。那些不具备客观经验表象的“形而上”对象,或者难以通过有效技术手段获得经验测度数据的主观心理对象,受到经济学家冷遇和排斥。在这一段时期,经济行为人丰富的精神特质在主流经济学家分析视阈里基本上是缺失的。物质趋利性成为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人唯一的人格理性定势。主流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主体文化精神特质的舍弃,究竟是一种必要且合理的抽象?还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阉割呢?将经济行为人的文化精神性格“去魅化”能够被容许的理性边界又究竟有多远呢?这是经济学家当今亟须从理论上厘清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忽视文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基本文化背景和历史源流同属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国家的基本文化价值取向都是崇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因此,西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不同国家自然资源、产业资本、工业技术和基本制度方面存在的差异,而无法用不同国家之间基本社会文化精神的差异来解释。历史文化背景的同质性使得文化因素退隐为其他各种显性变量之后的隐性变量。但是,当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视野跟随着西方国家商品、技术、资本外拓的脚步延伸到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区域,并试图解释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其它国家和区域(如中国、日本、南美和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考虑这些国家和区域的传统文化背景条件,仅仅用自然资源、产业资本、工业技术和基本制度等等适合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理论范式,就无法对这些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作出合理解释与准确预测。譬如,以个人功利为基本价值取向和以完全理性为基本理论假定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解释中国人曾经在世俗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忠孝为先”的忠义孝节行为呢?又如何能够理解中国民间社会所崇尚的“义字当头”、“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好汉行为呢?所以,如果基本文化背景和行为价值取向出现显著区别,文化就成为经济解释的强关联变量。也正是在对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看到了文化对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文化精神如何作用于经济过程
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理解存在差异。社会学意义上理解的文化可以泛指人类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所有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包括三种不同文化形态:第一种是有形的器物类文化,如建筑、生产工具、绘画、雕塑等实物形态文化;第二种是无形的主观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道德理念、审美判断等依存于人类内心的主观精神;第三种是介于有形器物和无形精神之间的第三态类型的文化,即虽然生发于人类主观心智,但是又外化于客观物质对象之上的人类思维成果,如知识、技术、信息、法律等。在本文的理论意域内,文化既不是指第一种器物类型文化,也不是指第三种已经物化于客观对象之上的知识类型文化,而是指第二种类型与人类心智主体密不可分的主观精神文化。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主流文化是由这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人群共同分享和信奉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信念、价值准则、效用偏好、行为范式和思维习惯;并且经耳濡目染、口口相传、世代承袭流传下来。
作为主观精神的文化变量是如何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呢?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选择和经济运行过程是由人完成的。人不是机器,而是具有主观精神并且受主观精神控制和主宰的有灵性的行为主体。文化精神通过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与运行。文化精神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又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价值目标导向作用。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的选择和确立要受主观文化价值精神的引导,行为人的终极价值追求——这种终极价值追求可能是在特定宗教信仰、社会伦理风尚、家族文化传统长期耳濡目染和渐习渐行的过程中形成的——对其在特定经济活动情境下的目标选择具有强支配决定作用。经济行为人的文化价值精神会以一种内在的自觉定向和导引,帮助他制定和寻获行为的目标与方向,告诉他应当“做什么”。如: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崇尚“以农为本”;士大夫文化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绿林江湖文化崇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深受这些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人们的行为价值指向,或者是男耕女织、安土乐命;或者是悬梁刺股、皓首穷经、科举入仕;或者是揭竿而起、啸聚山林。以上种种文化行为导向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利益行为导向是格格不入的。二是行为战略导向作用。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行为战略也受行为人的主观精神制约。人们的经济行为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是创新的还是守成的?是风险偏好的还是风险厌恶规避的?是趋利的还是重义的?是守诺重信的还是机会主义的?是审慎稳妥的还是激进跨越的?总是与行为人的文化精神和性格禀赋密切关联。受小农耕读文化影响的地区,人们的一般行为选择总是偏向封闭保守和风险厌恶型的;而受商业文化影响的地区的人们的行为战略选择则总是更加开放和更具有冒险性。中西部地区的农耕文化传统是:“守土重迁”;“以土为本”;“父母在,不远游”;“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日难”。受这种传统的文化影响的人会很少离家远行,他们的行动空间平均半径相对比较狭窄。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活传统却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外出经商是当地人自古以来就热衷和流行的生活传统。受这种商业交易文化传统影响,人们的行动空间半径要广远得多。如浙江宁波、温州商人的活动空间半径往往超出省界国界,遍及新疆、西藏和欧美等遥远的他乡异国。不同文化的风险特性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譬如:海洋文化比内陆文化具有更强的风险偏好和风险适应度,因为海洋环境和海洋上的航海捕捞活动具有比内陆生产和日常活动大得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习惯于海上生产和生活的人显然比习惯于内陆生产和生活的人有对风险更好的适应性。因此,沿海地区的人往往比内陆地区的人有更强的创新倾向和风险担当;沿海地区的区域文化也往往比内陆文化有更强的风险色彩。秉承海洋文化传统的人群更加适合风险性强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而受内陆文化影响的人群更适合常规性的无风险生产经营活动。同是内陆文化的山区文化和平原文化也存在明显差异。山区文化相对比较褊狭保守、封闭曲晦,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他种文化;而平原文化相对比较坦荡直率和开放,与外部文化的融合度较强。平原文化影响下的人会更多选择与他人的交流交往和合作行为;而山区文化影响下的人的心态使他们比较难选择与不同文化类型的人之间的交流交往和合作。
其次,是文化的“激励”作用。文化精神还是经济行为人的一种精神动源。或者给他提供忍受劳苦、克服困难的坚韧与毅力,或者给他提供不怕风险、勇于探索、敢于“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的勇气。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人提供一种持续不断的信念流,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精神支撑。如同工业生产体系需要电、油、煤等物质能源提供动力一样,文化精神则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需的精神动源。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仅仅把物质生存需求作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获得激励的源泉,那么一旦人们的物质生存需求获得满足,就会失去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确实,人们能够观察到一些现象,说明人们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之后从事工作的内在动力下降或者消失。所谓“小富即安”就是形容这一类现象。但是仍然有许多富人虽然拥有的财富完全可以满足自身、家人甚至子孙后代的物质生活需求,但是从事工作的内在动力仍然丝毫不减,和当年穷困匮乏时同样努力地工作。这种持续的从事工作的内在动力是生存需求动机所不能解释的,需要用文化精神动机来加以解释。这正如经济增长的“索罗剩余”不能用物质资本解释而需要用人力资本解释一样。由文化精神境界决定的企业家的内在精神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甚至比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更加重要的精神资本与心理资源。企业家在已经拥有了超过生存所需的物质财富之后的创业和创新行为,只能用企业家的文化精神、品格、禀赋、境界来加以解释。
再次,是文化的“规约”作用。文化还是经济行为人的内在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依靠行为人的文化精神自觉来自动维系,因此不同于依靠外部强制的法律规范。如果说文化的行为导向作用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则文化的行为规约作用是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如何做”,为经济行为人在行为选择过程中提供一种规约与限制,或者使外在行为规范变成行为人的内在行为自觉。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的失范行为,如机会主义的违约和失信行为、假冒伪劣欺骗行为,等。这些失范行为只有一部分可以借助明确的法律规范来加以惩罚和制约。因为法律不可能覆盖成千上万人极其复杂的所有行为过程和行为环节。而且即使有明确的法律可以依循,法律过程的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也过于昂贵以至于诉诸法律不具有经济性。因此,经济行为人的大量行为需要依靠法律之外的文化观念、行为道德来加以规范与约束。譬如,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许多行为依据的只是彼此的口头约定,而不是白纸黑字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商业协议和合同。这些大量的口头行为约定的履行就需要依靠当事人内在的诚信精神来保证,特别是陌生人之间口头约定的商业交易行为就完全基于双方遵守承诺的内在精神自觉,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强制手段可以要求对方将一种口头承诺行为付诸实行。熟人之间的口头协议和约定或许可以凭借一方失信之后来自对方的报复行为来保证实施。而生人之间除了一言之诺之外,并没有一种其他嵌入机制来维系口头承诺的效力,而仅仅凭借承诺人履行承诺的内在精神自觉。这种精神自觉来自失信后的负疚感、沉重感和道德自责。而是否会产生失信毁诺后的道德自责,取决于他内在精神禀赋的类型和特质。所以,一种好的区域文化精神是一个区域经济活动的润滑剂和粘合剂,能够使得该区域经济活动更加顺畅,更少摩擦与冲突。即使出现摩擦冲突,一种好的区域文化精神也能够使它更快得到解决。因此,一种好的区域文化,会使这个地区的投资、交易、合作等各种经济活动更加活跃和频繁,从而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相反,如果一个区域受一种坏文化的影响,譬如受那种投机欺诈猖獗的“黑”、“恶”商业文化影响,那么,很多正常的投资、交易、合作等经济活动就无法展开,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就无疑将陷入停顿。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一些地区由于没有形成诚信的商业文化精神,人们奉行能骗则骗、能蒙则蒙的行为策略,导致诈骗和失信行为盛行,使得外地客商望而生畏、避而远之。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国外情况同样如此。拉美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大量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要素,但是经济仍然难以改变落后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诚信、廉洁、公正的社会文化精神没有得到推广弘扬。文化精神对经济过程的以上三种作用,可以简约归纳为“导向”、“激励”、“规约”作用。
文化精神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不仅在个体行为层面反映出来,更会在群体行为层面显著表现出来。由于受不同类型文化精神风尚的支配,不同行为人群体会呈现出明显的行为特征差异。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因为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以及由于海洋和内陆地理环境不同造成的文化性格差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与商业特色。所以,从国家、民族、区域大样本人群的层面上,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①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率先编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随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始建立和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1997年12月,我国国家统计局也开始研究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简称CCI,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
标签:经济学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资源禀赋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