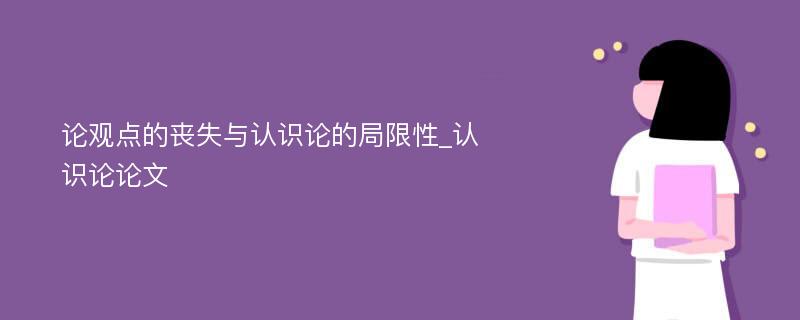
意见的失落与认识论的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意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体的认识可分为“人类”的认识与“个别主体”的认识,近代哲学以来,哲学对主体问题的关注的突出特点是只关照认识的“类主体”,而对个体主体置之不理,造成这一结果与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意见的失落有很大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在于阐述意见这一范畴失落的原因及其所造成的认识论的局限。
意见的理论溯源
意见,作为认识论的范畴是指见蔽相杂、真假未明、未经严密的逻辑检验或实践证明的阶段性认识。意见范畴在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古代特别是汉朝以前的哲学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将意见提升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解释成为同真理相对立的“意见”,很可能是从色诺尼开始的[①a]。他将自己对神的思想叫作“真理”,把别人的不同看法叫作“意见”或类似真理的“猜测”。这种思想在巴门尼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巴门尼德将自己的哲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真理的,另一部分是关于意见的。他将主体的认识分成两部分,即“意见性的理性”即指靠自己的观察而作出的判断以及提出的看法,另一部分即是真理性的认识,他将其称为“认识的理性”,他认为,意见性认识有微弱的思想能力,它只提供或然性的、非确定的知识,而认识的理性则是可靠的。
柏拉图的哲学也给予意见以一席之地,柏拉图把理念世界称为绝对的存在;把感官所接触着的现实世界(可见世界)称为存在与非存在的结合,或者说只有一半是存在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绝对的非存在。在认识论上,柏拉图认为,知识相应于绝对的存在(即“理念”),无知相应于绝对的非存在(即“物质”),因为绝对存在的东西总是可以认识的,绝对不存在的东西当然无认识可言,而相应于绝对的存在和绝对的非存在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就是介于知识与无知之间的东西,他称之为“意见”。知识是绝对真实的;比起知识来,“意见”是十分暧昧含混的,是可真可伪的。这就明显地存在着二个世界以及相应的两种认识:生成变化的可见世界(感觉世界),它是意见的对象,为感觉所认识;永恒不变真实存在的可知世界(理念世界),它是知识的对象,不能为感觉而只能为思维所认识。
柏拉图又认为,可见世界还可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指我们周围的生物、自然物、人造物等实际的东西,另一部分则是这些东西的“肖像”,是对前者的“摹仿”。相应地,“意见”也分为两部分:相应于实际东西的“信念”,相应于“肖像”的则是“想象”(或猜测)。同样地,可知世界也可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并不直接隶属于善本身的理念,另一个部分则是直接隶属于善的理念以及善本身。相应地知识也分为两种:知性的(或理智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
在古希腊的其他的哲学中(如赫拉克利特),也有谈到意见这一认识范畴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明确地将“真理”和意见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在认识论领域内将二者区分开,对立起来。将“意见”放在黑暗的居所,将真理放在光明的世界,认为意见的本性是不可靠的、欺人的,而真理则是对“存在”本身的认识,是可靠的,它是用推论和证明的方法得到的普遍知识,它与用感觉得到的意见形成鲜明的对照。“知识和意见是两种能力……是不同的能力”[①b];第二,意见是认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阶段。要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必须经过这一阶段,如巴门尼德说:“你应该学习各种事情,从圆满真理的牢固核心,直到毫不包含真情的凡夫俗子的意见。意见尽管不真,你还要加以体验,因为必须通过彻底全面钻研,才能对假相作出判断。”[②b]第三,意见虽然不可靠,是欺人的,但它终究还是人们的见解、观点、看法,并且是多数人的看法或见解,这种见解不同于真理也不同于谬误,它是一种见弊相杂的认识,“意见是介于知识与无知之间的东西”[③b]。因此,意见并非毫无价值,不值得考察和研究。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特别是在汉代以前的哲学中,虽然没有明显地提出意见这一范畴,但在对“知”的几个层次进行考察中,称意见性的认识为“言”“论”。“言”“论”也即是意见,如韩非认为:“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敬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这里的“言”即指意见,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正懂得圣人之术的君主,不适就于世俗的意见,而是按照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依据实际效果来审查意见是否正确。换句话说,意见、言论只是一种有待检验的认识,不能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他又说:明王“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韩非子·备内》)这是说,英明的君主,要判断一种意见、言论(“陈言”)是否正确,那就要用“参伍之验”的方法去考察。具体来说,就是明王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就不能专从一方面看,而必须把许多方面的情况(众端)搜集起来,进行分类排队(伍),加以比较研究(参),看这种意见、言论是不是在各方面都能得到证实(验)。如能得到证实,那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在这里,“陈言”、“众端”即可作“意见”解,意见(言论、陈言、众端)是认识过程中必经的一种阶段性认识成果。
可见,意见一词在早期的哲学中,是作为与真理相对立的范畴来考察的,但在后来的哲学中,却用“谬误”一词来代替“意见”,使之成为与真理对立的范畴,使认识论产生许多局限,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其社会、认识论和思想根源的。
意见失落的根源
虽然在早期的哲学中,意见是与真理对立的范畴,但这一范畴后来却失落了,之所以失落,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权威”的确立和封建专制制度是造成意见失落的社会根源。不管是在西方的希腊,还是在东方的中国,早期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在古希腊,哲学流派纷呈,并没有所谓的“权威”,因而与此相适应的是,比较重视作为个体认识的意见,虽然在巴门尼德及柏拉图的哲学中,初见端倪地把凡人的认识看作是“意见”,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将认识主体的这种意见性的认识当成谬误。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世俗社会专制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反映到认识领域,在认识中也必须确立一个权威的主体(“皇帝”)来定夺一切。因而只有“帝王”的认识是真理,其他人的认识皆是谬误,因而到了中世纪,“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④b]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基督教。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就由奴隶主的宗教转变为封建主的宗教,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工具。基督教在西欧封建社会中的这种统治地位,使中世纪哲学成为为封建制度和基督教服务的所谓经院哲学,其任务就是论证基督教教义。这种哲学严重脱离实际,贬低甚至否定现实的认识,否定个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抬高信仰,提倡盲从;个别主体要想得到真理性的认识,必须有上帝的启示、教会的教诲和经院哲学家的开导,凭自身的感觉,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的认识,换句话说,真理只存在于上帝与教会那里,不论是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的奥古斯丁主义,还是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托马斯主义,在这方面的思想是一致的,无助的个体的认识只能是一种谬误。这样,由于中世纪权威和专制制度的确立,个别主体对事物、神的认识只是一种虚假的认识,是错误的,这就把巴门尼德的个别主体的认识作为一种意见,抛出了认识论的界限之外,而代之以“错误”或“谬误”。
中世纪之后,虽然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中世纪给哲学所留下来的危害,并试图对之进行改造,但是改造的结果,是以“理性”代替“上帝”,重新确立一个新的“权威”。虽然这一权威使由上帝占领的领域重新还给人,在认识上,就是由对天国、对上帝的认识回归到对人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但认识论领域的“权威”却依然是存在的。虽然,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的哲学发展,形成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的对立和斗争,英国哲学家们把实验和观察的方法绝对化,推崇感觉经验,贬低理性思考的作用,坚持经验论的立场。在欧洲大陆,法国的笛卡尔、荷兰的斯宾诺莎和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人则推崇数学上所运用的演绎法,同样也把这一方法绝对化,片面夸大理性思维的作用,否认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坚持唯理论立场。但不管它们在方法论与逻辑学上存在哪些区别,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没有给作为认识范畴的意见一席之地。这除了理性的权威仍没有消失外,另外就要归之于当时的思维方法(以下我们将详细加以分析)与当时科学的发展。这种置意见于不顾的哲学直到尼采等哲学家之后才有所改变。
在中国,自秦朝始,历代帝王无不将他们的“言论”称为真理,而将别人的意见称为“谬误”。汉代,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于是孔子就由儒家创始人上升为“素王”再上升到“神”,而圣人及其言论也就成为判断人们的言行是非的标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众言淆乱,则折诸圣”。
认识,实际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必然要把意见作为认识的范畴,但是,权威、专制正好与这种重视个体认识的认识论思想背道而驰,这是意见为什么会失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其次,意见的失落有其认识论上的根源。这一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从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所寻求的是“存在本身”,“存在本身”不是多,而是“一”,是绝对自在的,具有终极始因性的存在,这种终极存在的表现为“万物由它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重归于它”的存在物,是以一驭万、万物分有并受其制约的“始基”。随着哲学思维的发展,这种本体被认为是物理世界之后支配物理世界的“逻各斯”,它或者是柏拉图的“至善理念”,或者是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哲学成为一套取消差异、追示同一的整体性观念,这种观念,被西方哲学经历的“认识论转折”所承继,在这场转折中,认识论与本体论形成了共同思路,即试图对人的认识预设出“第一原理”从而消除个别的差异。因而在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这种“脐带”式的联系中,古希腊的“意见”学说,作为重视个体认识成果的一部分,作为个体认识的见解,不仅没有得到继承,反而被遗忘了。其次,认识主体的模糊不清,也是造成意见失落的另一哲学原因。在传统的认识论中,认识过程中的类主体和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不清的,特别是个体主体,其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经常被取消。纵观以往的认识论史,在主体结构上主要是从类意义上使用的,如在讨论人与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其所使用的主体概念是类主体,或者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主体。忽视个体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只关注群体对外(自然)的力量,个体的力量则在“一致对外”的呼声中被忽视了。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基本上都是在类主体的意义上使用这一主体概念的,当培根说知识起源于经验时,他的主体概念就是在类的意义上使用的。后来的哲学家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承续了培根的思想。在康德那里,与“自在之物”相对立的主体显然是类主体或一般主体,到了黑格尔,则企图以绝对观念(类)的外化来解释其运行中的有限性(个体)问题,结果却使类主体与个体主体难以分别。可以说,本世纪前,还没有一个哲学家专门从单独主体的角度讨论认识论。
第三,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造成意见失落的思想根源。近代的自然科学使近代哲学形成整体上具有抽象、片面的形而上学局限,习惯于“是—是,否—否”的绝对化思维方式(当然,这并不排斥个别哲学家的局部思想中有辩证法因素)。这是因为这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暂时从普遍联系中抽取出来,当作孤立不变的东西加以观察。将事物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在认识过程中的表现则是:将阶段性的认识成果要么看成是真的,要么看成是假的,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真假不分的认识成果,与此相关,将意见剔除在认识论之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于意见的失落而造成的认识论缺陷
由于意见的失落使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存在一些易见的缺陷。
第一,由于意见的失落,使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有了生存的土壤。由于意见在认识过程中的“缺位”,造成了认识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其突出的表现是将认识成果简单地划分为“真理”与“谬误”,这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在认识过程中遗留的痕迹。实际上,近年来我们对一些认识论问题的讨论,都是与意见的失落有关的,如真理多元论与相对真理论。
在认识过程的阐述上,我们习惯上将认识过程描述为真理与谬误不断斗争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严格说来并不是认识的过程,而是真理传播的过程。诚然,真理的传播与对真理的认识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因为,许多真理性的认识正是在认识过程中得以传播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对真理的认识与真理的传播就没有界限。因为真理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如果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即将某种认识作为真理进行传播,那么必然使为某一些阶级及某些集团利益的宣传、说教视为真理,必然造成真理的多元论,或真理的相对论。其结果是否定真理的存在,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教训。
第二,在认识上,只见一般不见个别,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生存提供了空间。由于将意见剔除在认识论之外,传统的认识论,不管是经验主义还是唯理性主义,都未能解决认识的一般与个别的问题,唯理性主义自笛卡尔到莱布尼茨,寻找的是认识的“一般”,当然不可能顾及个人的经验,不可能顾及意见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最终走向不可知论。英国的经验论者坚持狭隘的经验论立场,过分崇尚感觉经验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又试图将感觉作为“一般”的知识,不给“意见”以合法的地位,而将其抬高为“真理”,最终陷入怀疑论,恩格斯在评价经验论时曾指出他们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感性的认识的范围内,因此,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摸到“共相”和“一般”。而当他们发现这都是不可能做到时,便干脆否认一般和“共相”的客观实在性,而将其归之于人的虚构,最终是否认作为“一般”的真理的存在。可以看出,传统的哲学对“一般”的真理的追求,是以一种极端的绝对的形式出现的,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两极相通,其共同之处在于试图将“个别”的意见看成一般的真理。
第三,忽视认识个别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造成认识过程的非人性化。
意见失落与哲学只重视类主体关联,反过来,由于意见的失落又使认识过程中的主体被忽视,造成认识过程中的非人性化。
首先,由于意见的失落,使一些对认识具有根本性影响的主体因素被划在认识论之外。诸如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知识、阅历、社会关系等,都没有被关注和提及,偶尔说到这些问题又因为不曾和现实的个体相联系,结论则不免失之空泛、武断和勉强。其次,由想象和推理来取代实证,用类来消除个体。特别是,由于意见性认识所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特点,不能简单地用真理与谬误加以说明,意见的失落使许多哲学家不得不用类的共性取代个体的差异性,用普遍性抹去特殊性。结果,无限丰富的人类认识图景变成了只受原则宰割的逻辑推演模式,使人性的许多特点在逻辑推演中成为“边缘人”。
第四,忽视认识的社会性,忽视认识的主体—主体关系,或主体间关系。
与前一个缺陷相联系,由于对个别认识主体的重视不够,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就使认识的主体间关系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于人及其世界的把握应当从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入手,而在人的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主要展开与生成着两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主体—客体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主体—主体的关系或主体间关系。在主体间关系中,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形成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因此认识关系的基础不仅仅是人同自然之间的天然的相互关系,主体对客体观念的把握总是在社会机制(社会关系系统、交往形式系统、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作用的范围内展开并实现的,它不仅必然地包含着“主体—客体”关系,而且内在的关联着“主体—主体”关系,这两重关系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又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此,他是将“社会关系”作为实践与认识的基础,实践一开始便是社会的,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们的共同、协调的活动。之后,他又说“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①c]。可见认识过程离不开认识的主体间性。
由于意见的失落所造成的主体间性的缺陷,已为许多哲学家所关注,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呼声,到胡塞尔对认识的主体间性的研究,无不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关怀。前者的目的是把人从神学道德的无情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人性的本真状态,重新恢复个别主体在认知关系中的基本地位,从而重视凡人的认识成果,重视个别主体的意见性认识。胡塞尔则进一步让主体性进入主体间性以致他在其哲学生涯的后半期(1910—1938年)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并写下数以千页计的手稿(现已被编纂为三大卷的《论主体间性现象学》出版),在其晚年写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和《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对这个问题也都有论述,这些论述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从认识史来看,只有给予意见在认识论中以合法地位,才能使主体间性的研究更加丰富,因为在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交往活动,恰恰是通过争论来发生关系,而争论的基础即是认识主体的阶段性的认识成果,即意见性的主体认识。
第五,自由的学术气氛缺乏认识论的依据。
一种具体认识(意见)在刚刚道明、尚未受到实践检验时,人们是无法知道其真谬的,假如这时错把它当作谬误马上否定了,就会使真理夭折,相反,则会将意见当成真理。再者,真理都是由一定认识主体发现并在社会中传播开来的,真理一开始又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倘若社会中缺乏民主,没有学术自由,人们不能自由研究问题和发表见解。尤其是那些地位低下的小人物,那些持有新的意见、观点的少数人,不能自由地发表言论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观点,就难以发挥群众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显然,真理的发展依赖于学术自由,人们能够自由地发表各种观点、意见,自由地进行学术探讨,人们之间也能够自由地平等地相互商讨、相互争辩、相互批评,这样才能使具体的真理之正确性充分显露出来,使谬误暴露出来,并使具体的真理性认识可以在百家争鸣中修正个别错误而发展完善。但是由于我们在认识论中没有给意见以充分的重视,其合法地位被取消,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不是将个别主体视作与自己相同的平等、自由、自主的主体,而是将其视作客体,甚至将其视为外在物。这就使人丧失价值、尊严。使主体处于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之中,处于一种未分化和非创造的状态之中,从而使自由的学术气氛失去其认识论的根据。
注释:
①a 参见拙作:《意见及认识过程中的群己关系》,《学术月刊》1994年第12期。
①b②b③b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87、31、88页。
④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①c 《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5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