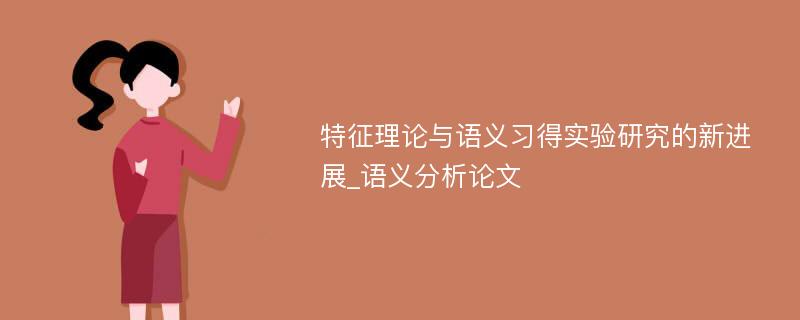
语义获得的特征理论及其实验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新进展论文,实验研究论文,特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2)01—0119—05
对任何一种语言来说,语音和语法只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只有语言的含义才是我们真正想要传递的信息,言语活动的核心特征是富于含义。在心理语言学上,关于词的含义及其获得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特征理论和原形理论。
一、特征理论及其实验依据
1.特征理论的基本观点
特征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克拉克(Clark,1973)。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1)词的含义由一些特征组成,或者说由一些意义片组成。 每个词都包含着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多方面的属性,把标示某个词的各种必要的属性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这个词的含义。例如,“狗”这个词包括了“四条腿、会吠、全身长毛、有尾巴、是动物”几种必要的属性,缺少一个特征就不能标示这个词,同时,这些特征已经足够标示这个词,不必再加什么。每个词都是一个“词义特征群”或“词义属性束”,把这些特征或属性结合起来就揭示了这个词的含义。
(2)儿童在获得词义的过程中,首先掌握这些特征, 然后才掌握词的完整的含义。儿童通过不断的学习,将越来越多的语义特征整合到他们的词汇含义中去,直至达到成人语言的标准。儿童先掌握最一般的特征,然后依次掌握较为具体的特征。在语言获得过程中,儿童不能像成人那样赋予词语以固定不变的含义,而往往在决定词语——词义的相互关系时犯一些错误。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儿童没有完全掌握词语所包含的特征,在理解一个具体的词语的时候,要么增加,要么丢失了一些特征。
2.特征理论的实验依据
最先开始语义研究的心理学家是Donaldson和Wales,他们在爱丁堡大学从事关于语言获得和认知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研究时,发表了一篇关于学前儿童对“多”和“少”的理解的论文。在实践中儿童能轻松而正确地理解“多”,却不能理解“少”。其实验是这样的:首先给被试呈现一张图片,图片上画的是两棵已经结果的苹果树,然后问儿童:“哪棵树的苹果少一些?”结果儿童毫不犹豫地指向那棵结有更多苹果的树,他们的行为似乎表明“少”的意思就是“多”。这一发现通过不同材料的实验得到了印证(Palermo,1973,1974)。
克拉克(1973)的一个实验研究了儿童对“before”和“after ”这两个词的掌握情况。克拉克认为“before”的特征为(+时间,-同时性,+预先),而“after”的特征则为(+时间,-同时性, -预先)。这样,按照特征理论解释,儿童首先认识到这两个词都与时间有关;其次它们与事件的序列顺序有关;最后,“before”指在此以前的事件而“after”指在此以后的事件(只有掌握了这个特征, 儿童才能有差别地对待这两个词,而不是认为它们有相同的意思)。这个实验具体是这样的:先给儿童呈现一些使用before或after这两个词的句子。 然后,要求儿童利用一些玩具按先后顺序来表示句子所陈述的动作。按照特征理论,可以预测两个词都不认识的儿童将根据动作在句子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将之表现出来;一旦他们掌握了这两个词,最初的反应便是将“before”和“after”都当成“before”来表现句子中的动作, 直到最后才出现正确的反应。大体说来,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假设,尽管有少数儿童似乎把这两个词当成同义词,认为它们的意思都是“before”。
在Klatzky,Clark和Mecken(1973)的一项实验中,要求儿童用由无意义单词所组成的新词汇去描述在高度、长度、厚度等方面都不同的物体。这些词的维度包括大小、高低、厚薄、长短等。结果表明儿童学习具有肯定含义的无意义单词要比学习具有否定含义的无意义单词要快,也就是说,儿童对反义形容词(如长、短)的掌握具有内在的不对称性。
与此同时,克拉克着重研究了儿童语言获得过程中的泛化现象。她对通过观察记录而进行的有关儿童语言获得的大量的研究资料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资料尽管涉及许多不同的语种,但在所有不同语种的儿童身上都找到了语言泛化现象,而且一般出现在一岁到两岁半这个年龄阶段。这种现象要持续一年左右,但对某一具体词的泛化现象不会超过八个月。只有在儿童的词汇量迅速增长,喜欢问诸如“那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的时候,泛化现象才会结束。泛化所依据的特征一般源于运动、形状、大小、声音、味道和结构等知觉刺激输入。克拉克给每一种类型都列出了大量的事例。如一个儿童会用“mooi”去表示“moon”、圆的蛋糕、窗户上和书本上圆的记号和其他圆的东西;而另一个儿童则会用“cola”去表示与味道有关的事物,如巧克力、糖、葡萄、果馅饼、无花果等。
克拉克认为泛化是一种普遍深入的现象,上面讨论的反义形容词的学习也是一种泛化现象。另外,她还将另外两种现象解释为泛化。一是乔姆斯基的一些相关研究;二是有关对动词“tell”和“ask ”的理解的研究。克拉克认为儿童会将“tell”的含义泛化至“ask”, 直到掌握“ask”的特征之后,“ask”才与“tell”区别开来。而对皮亚杰关于儿童掌握“brother”和“sister”的含义有几个发展阶段的研究, 克拉克认为儿童首先是将它们作为“boy”和“girl”的同义词, 然后再加上同胞这一特征,最后才知道它们表示的是同一个家庭中两个孩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克拉克从这些互不相同的泛化事实中得出:儿童的词汇中词的含义往往是不完整的,因为他们总会丢失其中一个甚至更多的特征。正是由于特征的缺失导致了词使用时意义联系的不精确性,即泛化现象。只有当词语的特征成为儿童词汇结构的一部分时,才能明确区分词语的含义并正确地使用这些词语。
特征理论认为词义是由不同的特征组成的,而且儿童是逐步掌握这些特征直到理解词语的完整含义。这样,有关特征的起源、特征的基础等问题便随之而来。克拉克认为词语最初的特征与知觉的发展有关。她假设有一套普遍通用的原初意义,这些知觉特征只是它的一个子集。她进一步假设词义最初的组成部分是片段化的个人所知觉到的特征。只有在一系列的特征都掌握之后它们才有可能被整合成一个单一完整的意思(这意味着语义特征及其形成对个体来说是先于语言的发展。这与皮亚杰认为思维先于语言的发展的观点是一致的)。按照这一观点,儿童对词语的含义的掌握开始于对客体的知觉,同时克拉克认为知觉到的特征也是掌握反义词的基础。Wales和Campbell(1970 )认为的反义形容词在维度上的等级关系,对克拉克来说就是知觉特征。形容词“大”“小”很早就被掌握,是因为它们的含义所包含的知觉特征使得它们的应用不受限制。而表示其他维度的形容词如“长”和“短”,“宽”和“窄”的应用则受到它们在其维度上附加的知觉特征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将一个“高”的物体描述为“大”,但却不能将一个“大”的物体描述为“高”。因此,克拉克认为越一般的词越容易掌握,因为它们所包含的特征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越具体或越具有区分性的特征就越难掌握,这些特征可以组合出许多更具体的含义。
克拉克假设儿童掌握词语特征的先后与特征的概括水平有关,也就是说与知觉显著性有关。她认为三维的知觉特征的掌握要先于二维的知觉特征,因为前者较后者显著且知觉起来更自然些。这样,“big ”和“in”因指称三维的事物和空间关系,对它们的掌握要先于“small ”和“long”(只指两个维度的事物和空间关系)。由于儿童主要是掌握那些有点、线、面为参照的、与深度、位置、方向、空间有关的以及表时间的词语,因此,凡是与知觉理解性和恒常性有关的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儿童对词语的掌握。比如说,自然界中每一维度的含义都是由一些以某一点为参照的肯定和否定的特征所组成,其肯定一面便作为这一维度的名称(如:长—长度,高—高度)并且最先被掌握,因为儿童预先就被安排在知觉维度肯定的一面。克拉克由此假设儿童对关系的、空间的、时间的维度的知觉具有一种不对称性。那些无标记词如“big, long,wide”的掌握要先于与之相应的有标记如“small,short,narrow”;同样,“front”先于“back”,因为前者在知觉显著性方面占优势; 而“up”在视觉上显著于“down”,“before”与“front ”有某些类似,因而对它的掌握要先于“after”。总而言之, 就像是早期的意义区分一样,对反义词的含义的知觉也存在着某种偏向。
二、特征理论的缺陷
1.与特征理论相矛盾的事实与实验
尽管早期的一些研究事实似乎都能证实特征理论的假设,但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去探索其他解释儿童语义获得的途径。相关研究积累起来的诸多事实,似乎与特征理论的一些理论前提和预测发生矛盾。
Huttenlocher(1974)的研究结果对特征理论提出了质疑。克拉克所谓的泛化事实只是语言使用上的错误,即儿童利用一个词去指称不同的事物;Huttenlocher发现泛化(即一词多用的现象),只能说明儿童词汇的贫乏而并不意味着儿童对词义加以泛化。在对三个儿童的纵向研究中,她发现了儿童在语言使用上的泛化(与克拉克在对儿童早期日记记录进行分析时的发现一样)。但是,她并没有发现语言理解方面的泛化现象。比如说,当儿童的词汇中没有“猫”时,会用“狗”去指称“猫”。但是,当要求儿童在诸多动物中指出“狗”时,他不会指“猫”。也就是说,当儿童想要传递一个信息或识别某个事物时,他们只能利用自己已有的词汇,而这些有限的词汇往往不能很好地完成表达任务。这样,我们就只能说儿童因词汇的分管导致语言使用的泛化,但在语言理解上却是分化的。
质疑特征理论的第二个领域是对儿童掌握反义词的研究。
Amidon和Carey(1972)认为克拉克关于五、六岁儿童理解“before”和“after”的研究结果只是说明了语法的作用,与“before ”和“after”这两个词的意义特征无关。 Johson(1975)重复了这一实验,发现儿童对“before”和“ after ”的理解与句子的句法结构有关。 Harner(1976)则发现儿童对“before”和“after”理解没有差别, 只是以紧接着的过去和将来为参照要比以较遥远的过去和将来为参照准确得多。这些研究都没有为特征理论“对反义词中无标记的、具有肯定含义的一个的理解要先于有标记的、具有否定含义的一个”这一观点提供证据。
另外,还有两个实验研究对特征理论提出了质疑。其一检验了儿童掌握维度形容词的情况(Brewer和Stons,1975), 其二研究了儿童对与空间有关的词的理解(Kuczaj和Maaratsos,1975)。 这两项研究都表明儿童对具体的词的掌握要先于与之相关的维度(如“long”先于“length”),这一结果正好与特征理论的预测相反(先掌握一般的特征,然后才掌握更具体的特征)。
Brewer和Stons 的实验很简单:先给被试呈现四个代表两对反义词的事物。比如放置在竖立金属网上不同高度的两个球和两块厚度不同的塑料泡沫。然后要求被试指出那个高的(低的、厚的、或薄的)。对儿童在实验中所犯错误的分析表明,最常见的错误是儿童指着薄的那个而要求却是指出低的那个,或指着高的那个而要求则是指出厚的那个。也就是说,儿童不是不能区分同一范围的有标记词与无标记词,而是不能区分不同的有标记词或无标记词。在该实验中,儿童对反义词中无标记词的操作优于有标记词。巴特利特(1976)的研究也发现对大小、尺寸等维度具体词的掌握要早于维度本身;而且,没有事实证明无标记词的掌握要早于有标记词。
Kuczaj和Maratsos考察了儿童对“front,back,beside ”的掌握。实验要求两岁半到四岁的儿童将物体放在自身、有前后关系的物体(如电话机、卡车)、没有前后关系的物体(如眼镜、木棍)的“前面,旁边或后面”。 结果表明每个儿童都是同时掌握“front , back , beside”这三个词,只是不同年龄所依赖的语境不同,它们依次是自身、有前后关系的物体,新颖的物体,最后才是无前后关系的物体;儿童对“side”的掌握则要迟于“front,back”。 但没有儿童像特征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先掌握“front”,再掌握“back ”或者把两者的意思混淆。儿童首先意识到“front”,“back ”指的是一个物体一条轴线的两端,当获得这一知识的参照从自身扩展到它物时,儿童就基本掌握了这两个词。儿童是否同时掌握两个反义词取决于这两个词具体的意思与它们相关维度的意思哪一个更复杂。如果相关维度本身比两个词具体的意思更容易理解,儿童便会在没有理解这两个词的具体意思的时候首先掌握这一维度概念,如“front”和“back”。 如果相关维度要比词的意思复杂,如“more”和“less”,那么无标记词的掌握就要先于有标记词。
最后,Wilcox和Palermo(1975 )的一项对儿童理解与空间有关的单词“in,on,under”的研究, 也对特征理论对语义获得的解释提出了疑问。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她要求1到5岁的儿童用一些玩具表示这些词的含义,如将玩具动物放到盒子、隧道、卡车、桥、桌子的上面、下面等。 先给被试一些句子如“Put the X(on,under,in)the Y”,然后要求被试用玩具将句子的含义表示出来。结果表明,儿童作业的正确率从“under”到“on”到“in”依次上升; 而儿童实际掌握这三个词的顺序也是“in”,“on”,“under”。
面对上述实验或事实,克拉克(1973,1974)便将其对词义获得的解释扩展到包括非言语策略。她认为,在语言获得过程中,语义的获得与儿童在语言交流中理解语言的策略相互作用。通过有关的实验研究,克拉克认为儿童开始并不知道“in,on或under”的意思;慢慢地, 他们才知道这些词都与地点有关(即具有“地点”这一特征);然后,他们可以将“in”和“on”区分开来;最后,他们才能够将on和under 区分开来。在儿童仅知道“地点”这一特征的阶段(1岁到3岁),他们对语言的理解以客体的知觉特征和它们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为参照。当给出的句子含有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单词时,儿童将遵循这样的法则:
(1)如果一个物体是被要求放到一个容器的某个位置, 他们就将它放到这个容器的里面。
(2)如果一个物体是被要求放到一个水平面的某个位置, 他们就将它放到这个平面的上面。
如果条件允许,儿童将首先使用第一条法则,否则他们便使用第二条法则。这样一来,儿童总是能解决包含有“in”的问题;对于包含有“on”的问题,在没有要求放到某个容器某个位置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完成;可一旦碰到含有“under”的句子,便会出现错误。
但是,Wilcox和Palermo(1975)却对此提出了异议:首先, 儿童并不一定像掌握反义形容词一样,去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掌握“in , on和under”的意思。因为这三个单词之间的关系与“big”和“tall”之间的关系不一样,而且这三个单词之间并没有类似“big ”和“small”之间的这种反义关系。其次, 克拉克实验情境并没有给儿童提供选择具体的非言语策略的余地。如果给儿童一个小小的玩具狗,那他们就倾向于将它放到隧道或者盒子的里面而不是上面、放到一辆卡车和婴儿床的上面而不是下面、或者放到桥和桌子的上面而不是下面,因为这样放置更符合习惯。
Wilcox和Palermo在实验中曾要求1到3岁的儿童合常规、 反常规地放置些物品(比如给儿童一只船要求把它放在一座桥的上面,或给一条路要求把它放在一辆卡车的里面)。对合常规的问题,克拉克发现的发展的趋势清楚地被重复;可儿童解决反常规问题的能力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年长一点的孩子更多倾向于将船放在桥的下面而不管问题要求的是放在下面还是上面。这一结果与Strohner和Nelson(1974)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Strohner和Nelson通过实验发现3 岁儿童倾向于用常规策略理解句子。当面临反常规的问题时,儿童并不会采用克拉克所提出那两条规则而是把物体放置在他们认为最为合适的位置。儿童的年龄越大,就越清楚船是行驶在桥的下面,道路应该放在卡车的下面,也就越会忽略所给问题的具体要求。这里并没有证明儿童理解“on”比理解“in”要难,尽管总的来说对“under ”的理解要比对前两者理解都要差。
总而言之,对儿童语义获得的不断研究使得特征理论认为儿童通过逐步掌握组合成词的特征而逐步获得词的含义的说法逊色不少。这主要表现在:缺乏支持词语理解的泛化现象的证据;缺乏反义形容词(more和less除外)同义性的证据;缺乏支持“对反义形容词具体特征的掌握先于一般特征”的观点的证据;以及其对实验情境对儿童操作成绩影响的忽略。
2.特征理论的逻辑和推理问题
相对于上述实验事实,给特征理论以更大打击的是那些逻辑和推理上的异议。Rosch(1973),Nelson(1974)和Palermo(1976)等都在这方面对特征理论提出了质疑。特征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它认为要理解一个概念的含义,必须从中提取出它的一些特征。然而,要提取一个概念的特征,前提必须是已经理解了整个概念,这样你才知道能从中提取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就如Nelson(1974)所说:“……特征提取理论是以预先就知道某个概念的含义来解释特征的抽取的;也就是说,对一个具体的概念来说,你如果知道了怎样将它的一般元素提取为一般特征,那么你也就知道了这个概念的含义本身。”Nelson进一步指出第二个问题:特征理论并没有提出将一些特征组合成一个整体,进而形成一个概念的具体方法和原则。简言之,一系列的特征并不意味着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据一个已知概念,我们可以列出这个概念的所有特征;但是只有当这些特征得到合理地组合以后,才能形成我们所能理解的完整的概念。
Rosch(1973)指出, 一些概念并不是通过逐个掌握其特征而获得的;相反,由于人类的生物学特性,它们属于先天固有的类别。按照他的说法,不少词汇是由人的生物属性所决定的,是通用的、跨文化的,对它们的掌握是以整体为单位,而不是将之分解,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掌握。他进一步指出词语内部是高度结构化的,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词语的内部结构可以被认为是核心意义、原形、或最佳事例。比如说,苹果可以被当作是最接近“水果”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的最佳事例;但西红柿或胡桃尽管也属于“水果”这一范畴,却不能被认为是最佳事例。一个概念的外延可被看作是一个相似度族系(Rosch和Mervis, 1975),一般而言,处于这一族系外围的成员彼此之间相似度较小,但随着所处位置向中心的逐步推进,彼此之间就越来越相似。比如说“红色”这一概念,它必然包括了最典型的一种红色;同时,其他非典型的红色我们称之为粉红、橘红和紫红等,它们除了具有“红”这一核心含义外,彼此之间的相似度就比较小,比如紫红和橘红两种红色的相似度很小。
如果Rosch的假设是正确的, 那么使用同一种基本颜色名词而说不同种语言的人,对于哪一特定的颜色最符合哪一个颜色名词,却有一致的意见。假设两种不同的语言都有“红”这个词。当要求讲这些语言的人从一系列颜色中找出一个关于红色的最好的例子时,他们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尽管他们所认为红色的范围可能是不同的,但他们所谓关于一个典型的、纯正的红色的概念却是相同的。他们所用的红色词汇虽然不同,他们的知觉却是相同的。事实上,Rosch(1973 )的研究资料表明在新几内亚岛上处于石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达尼人,虽然仅有两个基本的颜色名称,却能像具有全部11个基本颜色名望的语言的人那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感知颜色的变化。这样看来,人类先天就有一套作为各类颜色类别的典型的颜色。Rosch(1973)的研究表明:(1)如果呈现某一颜色类别的核心颜色,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知道它所属的颜色类别。(2)对某一颜色类别而言,最容易被辨别的是其核心颜色。(3)某一颜色类别似乎是按照其核心颜色加以定义的。Mervis、Catlin 和Rosch(1975)研究表明,尽管在定义颜色的范围方面,年幼儿童比年长儿童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但每一个颜色种类的典型在他们心目中都是稳定不变的。
Palermo(1976)曾试图将Macnamara(1972)、Rosch(1973 )和Nelson(1974)的意见综合起来,以支持他的语义获得理论,这个理论是Rosch所强调的原形理论的一种扩展。首先, 他认为特征理论在重视对词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的同时忽略了语言的功能;其次,考虑语言的交流功能时不得不考虑语境,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这是特征理论面临的一个难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提倡特征理论的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语言的比喻用法排除在外。
很明显,比喻使得词语的意义变的非常丰富。语言中如果排除了像“The mouth of the river”、“the configuration of ideas”、 “the eyes of a needle”、“crooked people”等这样的用法,就好像剥去了它交际功能的外壳。此外,就算是用特征理论来加以解释,词语的比喻用法与非比喻用法的界限并不清晰。就mouth这个词来说, 它可以有多种用法:常规用法,反常规用法甚至没有实际意义的用法。面对具体的语句如“the mouth of the man, ”“the mouth of the amoeba,”“the mouth of the river,”“the mouth of the cave,”“the mouth of the mountain,”“the mouth of the church,”“the mouth of the mind”等,我们就很难说它是“mouth”的哪一种用法。当然,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在适当的语境下理解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把语言的比喻用法当成是常规用法、非常规用法或者无意义用法,不仅忽略了语言的功能,而且忽略了语言交流的知觉基础。
任何一种有关语义的理论,尤其是与心理学关联的语义理论,必须考虑到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环境和比喻这一修辞手法。特征理论将这三者都忽略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极少注意与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特征理论考虑这些问题有些困难:第一,对词进行特征的分析相当于机械论和还原论。每一个词都被分解成一些具有一定等级结构或者不具任何等级结构的抽象的特征,这些特征被认为是词义的组成部分。Nelson(1974)就指出,特征理论通常不去考虑这些特征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去考虑这些单个的特征如何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说一个词的含义由X,Y和Z三个特征所组成的, 这并没有说明在具体的语言交际中,是怎样权衡这些特征并将它们组合成想要表达的意思。
其次,特征理论实际上是用具体的界线将词语加以分离。这也许能够促进语音的识别。但相对于语义来说,语音识别只是一个划分界线的问题。语音可以被直接知觉为一个个不同的整体,可是由它们所组成的具有一定含义的词语却没有这种特征。可以说“pill”和“bill”有一个音素不同,也可以说“girl”和“woman”有一个语义特征不同。 可是像“table”和“liberty”这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它们是不可以用一些具体不变的特征加以定义的。
一旦考虑词语的比喻用法,特征理论的局限性就显得尤为突出,它对语义获得的解释也就显得很不充分。因为比喻会不断增加词语的引伸含义,即不断增加词语所包含特征的数目。
三、原形理论能解决问题吗
上述问题的深究促使原形理论的产生。这种理论将有助于解释个体以某种适当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而这种意思同时也能够被听话人所认同和理解。Palermo 假定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由一些概念原形、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形和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时空表征所组成的。这样一来,词语的意义便建立在对词义的认知基础或者说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语言便成了表征意义认知的一种途径。在所有的发展水平上,语言可能表达出词语的某些认知基础,但并不必然要表征其全部的认知基础;也就是说,并不是词语所指的所有意思都能在语言中表达出来。这一点可以在儿童身上看到,因为儿童在未掌握语言之前就具有某些概念,尽管他们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一现象不仅局限于儿童,一些表示内部状况的词语的意思在我们的语言模式中也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这样,有关语言发展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双重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种理论在认知基础上解释概念的形成;同时,我们还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儿童是怎样用语言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必须指出,原形理论是针对特征理论的一些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并不否认特征是从概念中抽取出来的。“四条腿的、会叫的、全身有毛的、长尾巴的、属于动物”等特征都是一种叫做“狗”的动物所具有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还不知道有关“狗”这种动物的时候,是不可能从中抽取其特征的;而在我们没有真正知道所有这些特征之前,也同样没法掌握“狗”这一动物。也就是说,分析不能没有综合作为基础,而综合本身就在更高水平上包括了分析。只有通过理论建构和实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儿童语言获得的过程,才能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人类语言的复杂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