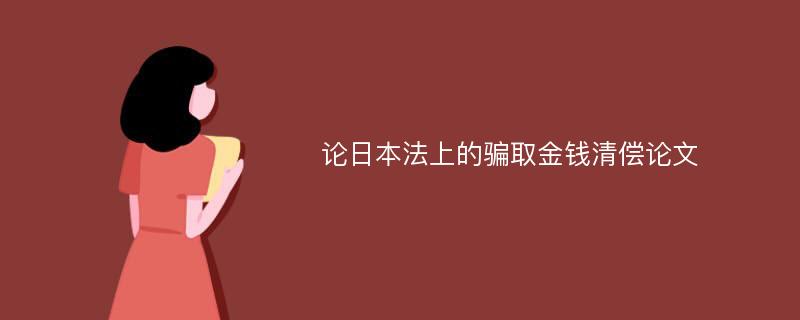
论日本法上的骗取金钱清偿
章 程*
内容摘要: 在骗取金钱清偿的案型上,日本曾经历三阶段裁判与学说的历史,从战前大审院将金钱作为一般有体物认可善意取得制度,到战后最高裁判所认可金钱“占有即所有”,以不当得利制度处理,到目前学说和判例对“占有即所有”基础上的不当得利进行再反思,其中有辗转继受所产生的问题,也有回应现实的案型的努力,值得我国司法实务与理论进一步比较与吸收。
关键词: 骗取金钱清偿 不当得利 追及效力 优先效力 法律上原因
一、问题的所在
(一)骗取金钱清偿的概念
以骗取的金钱清偿他人债务,被骗取人是否可以向受领人要求返还这一问题,返还的法律构成又如何,由于涉及对金钱这种一般等价物性质认识的不同,在欧陆的民法原创国即不无争议,从日本开始继受法典与学说开始,层层的继受与转译,导致东亚民法学对此问题的认知更添迷雾。〔1〕 对此问题的反思,参见朱晓喆:《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反思民法上货币“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司法运用》,《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6页—135页。
广义而言,“骗取金钱清偿”所包含的案型亦不止于“骗取”这一方式,实务中还常见金钱并非骗取而来,而是以自他人处合法受领而来(如保管)的金钱用以清偿既有债务的类型。
严格意义上的“金钱”,仅指交易所在的特定主权国家发行的具有强制流通力的法定货币,但现实案型中很多情形并非以金钱来清偿债务,而是以银行转账的存款货币方式为之。关于存款的性质,其本身即涉及金钱所有问题的理论争议,〔2〕 如有支持此时仍存在所有权说的,参见孟勤国:《〈物权法〉的现代意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页;张里安、李前伦:《论银行账户资金的权利属性——横向公司诉冶金公司、汉口支行案之理论评析》,《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83页以下。支持其为债权的,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页。 但笔者不拟涉及,至少在笔者拟讨论案情的问题脉络下,仅就其流通性与特定性而言,讨论存款货币与狭义法定货币之间差别的意义不大。〔3〕 金钱货币和存款货币在理论上当然存在不同,对金钱一般谈所有权,而存款货币的本质是对银行的债权,而债权的取得虽仍有信赖保护原理的适用,但一般不可能成为善意取得的对象。然而如下文所述,日本法从1930年代开始,就认为对金钱不适用善意取得,而以不当得利处理之,因此至少在采不当得利说之后,骗取金钱货币清偿与骗取存款货币清偿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
(二)我国法的规范与实务案型
1.我国的法规范现状
我国民事诸法中对骗取金钱清偿的法律构成与法律效果并未有直接的规定,按照2007年施行的《物权法》第106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其并没有将金钱自一般动产中区分出来,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民事法本身也并无关于混同等的任何规定,因此,对骗取金钱清偿案中,被骗取人应以何种法律构成向受领人请求返还,我国法上是留有解释空间的。
无锡案裁定书中提到,“强盛公司作为赃款的接受单位,与新大中公司并无债权债务关系,又不能提供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依据”,从中可以推知,强盛公司若要取得涉案财物,必须通过法律行为取得,且必须构成善意取得。而在嘉兴案中,法院直接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5条的规定认为,金钱属于此处的动产,并非占有即所有,对赃款的处分,应按善意取得的逻辑判定是否移转所有权。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医学技术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同时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巨大发展促进各行各业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医学影像学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1]。由于近年来许多新兴的影像设备投入到医疗市场中,传统的放射技术已经被新兴的影像技术所取代,使得医学影像技术逐渐提高,为诊断医师提供了更加清晰明了的可用于诊断的图像。医学影像技术方面的改进,可以对疾病进行更加清晰的显示,提高疾病诊断的正确率,以期为患者带来更佳的疾病诊断治疗服务。
司法解释中谈到的“财物”,所指并非仅是金钱,而是包括金钱在内的广义的个别财产。〔5〕 关于我国法上财产的广狭义理解,参见张谷:《试析“财产”一词在中国私法上的几种用法》,《中德私法研究》2013年第1期,第133—145页。 因此,对“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这一表述,应可有两解,一种想法是此条谕示了包括金钱在内的物都可能成为善意取得的对象,一种想法则是此处仅指善意取得成立则不予追缴,但善意取得的对象是否包括金钱——因为该司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而非物权法——并不属于该条的解释范围。至少仅从该司法解释前文的表述“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来看,后一理解应该更贴合司法解释的本意,毕竟还有构成在民法上构成骗取金钱,但刑法上尚不构成诈骗罪的情况,此时刑法上的追缴还无从谈起。换言之,还不能从该司法解释中就当然推出骗取金钱清偿的问题,必然要用善意取得制度来解决。
2.司法实务的案型与立场
那么我国的司法实务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究竟如何,实务中又有何案型呢?下面就从“徐州强盛城市煤气有限公司与黎耀金、蒋志强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6〕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执异36号执行裁定书。 (以下称无锡案)与“洛南县浩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克春返还原物纠纷”〔7〕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终2160号民事判决书。 (以下称嘉兴案)入手,对此中所涉及的案型与法律构成略作概观。
(1)司法实务的案型
A.占有移转原因不明型
在无锡案中,被执行人蒋某强将以转贷为由,与无锡新大中薄板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黎某金合意,由黎某金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新大中公司资金2816万元挪用给蒋,蒋将该款用于投资强盛公司的筹建与经营活动。新中大公司取得对黎蒋二人的胜诉刑事判决后,欲追赃款,此时强盛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最终裁定追缴被执行人黎二人挪用至第三人强盛公司的赃款。
图1为基于少模光纤耦合的前置光放大空间光通信系统示意图(直接探测),接收光学系统可以等效为焦距为f、直径为D的薄透镜.理想情况下,被调制的空间光经过无像差的理想接收光学天线汇聚到后焦面形成艾里斑,光能量耦合入放置在后焦面位置的少模光纤纤芯中,经光纤送入少模前置光放大器,最后通过多模光纤进入雪崩光电二极管(Avalanche Photodiode,APD)探测器.各模式传输信息相同,模间串扰可忽略.
在此案中,黎某金对金钱的占有是合法的,并非来自骗取行为。黎某金与蒋某强的转贷合同本身是虚伪表示,其真实的意思是挪用,并不存在法律行为作为其原因,而赃款自蒋处再到强盛公司,金钱的占有移转因法律行为还是仅是事实行为,金钱的占有移转是出资或为清偿既有债务,或单纯让强盛公司受利益,强盛公司是否知道这是赃款,这些事实在裁定书中均不明确。
B.以骗取金钱清偿型
与无锡案不同,在嘉兴案中嘉兴中院审理查明,原审第三人胥生海自矿业公司出骗取资金1443万元,并将其中180万元转入徐某春账户内并表示系“归还徐某春借款”,而徐某春在收到款项180万元的同日又将其中的100万元转至罗某琼银行卡上,对此徐某春表示系“归还其向徐某兵的借款”。矿业公司以徐某春、徐某兵不构成善意取得为由,上诉二审法院请求徐某春、徐某兵返还赃款。嘉兴中院审理查明,并无证据证明在徐某春、徐某兵、罗某琼受让涉案款项时知晓这些款项就系胥某海犯罪所得,因此认定,在矿业公司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徐某春、徐某兵、罗某琼受让涉案款项不构成善意的情况下,其要求三人返还涉案款项缺乏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此案中,胥某海将自矿业公司处诈骗所得赃款用于清偿与徐某春的债务,是典型的骗取金钱清偿既有债务。金钱之所以发生占有的移转,原因在胥某海对借贷债务的清偿行为。
(2)追及效力的法律构成
值得注意的,反倒是在2011年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联合在一个与刑事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诈骗取得财物为他人所得的情形何时应予追缴的条款。解释中规定“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
(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将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与刑法上的追缴制度连接了起来。
因此,可以说司法实务对追及效力的法律构成是一致的,即否认金钱占有的移转当然导致所有的移转,而是以善意取得制度为架构,认可在不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形,所有权人直接可以向受领人以物权请求权请求返还。〔8〕 如前注〔3〕所提及,理论上此处的判决非无问题,嘉兴案的情形是骗取存款货币清偿,而非骗取狭义的金钱货币清偿,原则上没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3)优先效力的法律构成
在认可追及效力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是否可以基于金钱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在请求返还时主张物权性的优先效力?〔9〕 优先效力与追及效力是否为独立的两种物权效力,本身当然也不无疑问。学说上对物权效力的强调和区分始于日本,相当程度上是有法典继受不足的背景,后来这种学说又由民国学者继受,传于今日的中国大陆地区民法学界。但在中文世界中,对物权的优先效力与追及效力是否为一,两岸的学说观点也未尽一致,即使是在日本学界,在很多情形下优先效力与追及效力也经常混用,笔者为区分讨论层次,区别使用优先效力与追及效力,也将别除、异议等权利均归于优先效力。 是仅能主张物权请求权,还是也能主张执行中的异议,破产中的别除等权利?嘉兴案中对此并未表明态度,但无锡案裁定书中提及“强盛公司作为赃款的接受单位,与新大中公司并无债权债务关系,又不能提供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依据,故在强盛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对涉案赃款不应作为合法的破产财产处理,而应予归还新大中公司,强盛公司不履行归还赃款的义务”,由此推知,新大中公司可从强盛公司的破产财产中别除出赃款的价值,也即对赃款的价值存在物权性的优先效力。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计量资料表示,组间对比行χ2检验和t检验,独立影响因素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裁定书中,这种优先效力的原因仅来自善意取得的不成立,也即金钱所有权仍存在于新大中公司处,必然衍生出基于物权请求权的优先效力,并未要求该金钱或其代位物有何特定性,亦未要求不与强盛公司的其它金钱或财产产生混同。
(4)司法实务的未竟课题
由此可见,司法实务均认为金钱的所有权并非当然随占有的移转而移转,而是与一般有体物相同,必须基于有权处分或善意取得方能取得金钱的所有权。
2.1.2 质谱条件 离子源:Turbo VTM离子源;电离模式:电喷雾离子化(ESI-);气帘气体积流量:30 L/min;喷雾电压:-4 500 V;雾化气体积流量:50 L/min;加热辅助气体积流量:50 L/min;扫描方式:质谱多反应监测(MRM);离子化温度:550℃。优化的条件参数见表2,提取离子流图见图1。
与上述无锡案与嘉兴案的案情比较,两者显然与双重骗取型无关,其中嘉兴案是典型的自己债务清偿型,无锡案因为事实不明,有可能同样归于自己债务清偿型,亦有可能可归于第三人无偿受益型(如在无既存债务需履行的情形)。为使比较的材料聚焦,下文将限缩讨论对象,除必要判例的介绍外,以下不讨论双重骗取的案型,直接就自己债务清偿型与第三人无偿受益型的判例与学说进行讨论。
但在金钱未被善意取得的情形下,要返还原物通常不可能,若返还同等价值的金钱,这本质上其实已与普通动产或不动产原物不存时的不当得利返还无异,均是返还同等价值的金钱,为何上述实务中此处的被骗取人——如无锡案中的新大中公司——仍能在金钱价值范围内享有物权性的优先效力,包括破产中的别除、执行中的异议等,但是一般有体物原物不存时则是纯粹的债权请求权,没有任何优先效力。换言之,如果认可金钱的返还请求权在其价值范围内享有物权性的优先效力,此处如何从体系协调不当得利法与物权法两者关系,就成为问题。
(三)比较的视点和材料
与我国司法实务相比,早在大审院时代,日本法上骗取金钱清偿的案型就远远多于上述两种,好美清光教授就曾经整理了如下大审院时代的主要几种案型(为讨论方便需要,笔者将骗取行为人命为B,被骗取人命为A,受领金钱人命为C):自己债务清偿型如B以自A处合法受领之金钱清偿对C的债务、或B以自A处骗取之金钱清偿对C的债务(或由A直接交付给C);双重骗取型如B从AC处均骗取金钱,又将从A处骗取之金钱清偿C的债务;第三人受益型如因骗取人或合法受领人B的行为使C无偿获得利益(为C清偿对D的债务等)。〔11〕 参见[日]好美清光:《騙取金銭による弁済について :不当利得類型論の視点から》,《一橋論叢》1986年总第95卷第1期,第13—16页;另参见[日]平田健治:《“騙取金銭による弁済と不当利得”覚え書き》,《阪大法学》2009年总第58卷第6期,第1282页。
不过,金钱本身是极为特殊的种类物,即使让所有权人可以请求返还,返还义务人所需要返还的也并非原物,而仅需要返还同等价值的金钱即可。在一般动产或不动产未被善意取得的情形,所有权人原则上既有基于物权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又基于不当得利的占有返还请求权,只有在原物返还请求权消灭的情形下,返还的客体才会变为作为不当得利的金钱价值。此时,若原物不存在,原物返还请求权才变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则原所有权人也就变成取得人的一般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10〕 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页及以下。 换言之,此时须看原物是否存在,来判定请求权的性质是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还是原所有权人的不当得利债权请求权。
二、日本法判例与学说的演进
(一)制定法的沉默
《日本民法》第192条善意取得的规定中,并未规定金钱是否为善意取得的对象,换言之,以第192条的解释论而言,并不能从其中当然解释出“金钱占有即所有”,故无善意取得制度之适用这一命题。〔12〕 参见[日]川島武宜、川井健編集:《新版注釈民法》第7卷,第149页以下(好美清光执笔),日本有斐阁2007年版。
在《日本民法》第703条关于不当得利的一般规范中,规定“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的财产或劳务受有利益,因此造成他人损失者,于利益存在限度内负有返还义务”。仅仅言明受有利益和造成损失之间需存在因果关系,但并未明确因果关系如何判定。如骗取金钱清偿,被骗取人和受领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仅从法条文意而观,并无明确的解释结论。〔13〕 参见[日]谷口知平、甲斐道太郎編集:《新版注釈民法》第18卷,第335页以下(加藤雅信执笔),日本有斐阁2015年版。
“互联网+”模式下的数字校园是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生物感知技术以及信息处理的联动和运用,使智慧校园在相关平台与技术的支撑下拥有可实践性的信息模式,使高校的信息沟通和网络沟通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保证高校的数据交换与信息交流的基本环境融合也在校园的基础环境之中。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善意取得还是不当得利的规定,骗取金钱清偿的案型下,被骗取人如何、向谁请求返还,法律构成如何,返还的效果又如何这些问题都赋予判例和学说去解决。
(二)大审院时期的判例与学说
1.以合法受领的金钱清偿债务案型
现有变电站均通过调度数据专网接入调控中心D5000系统服务器。通过调度专用数据网(光端机)分出一个站间带宽不小于2 Mb/s(每秒下载速度不少于300 KB/s)的局域网通道接口给网络五防系统使用,使网络五防服务器与控端五防主站、所辖各变电站五防子站组成局域网络,网络结构图如图4所示。
在B以自A处合法受领的金钱清偿C的债务的案型中,大审院在早期认为,不当得利上的因果关系被解释为“依照交易观念可得确认”〔14〕 大判明治44年5月24日,《大审院民事判决录》第17辑,第330页。 即可,因此认可AC之间的得利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但在末弘严太郎借鉴德国学说强调因果关系直接性后,〔15〕 [日]末弘厳太郎:《債権各論》,第932页,日本有斐阁1918年版。 大审院后期也开始强调“因果关系的直接性”,认为如果B从A处受领的金钱与自身的金钱发生混同,则金钱便成为B自己所有,再以之向C清偿则欠缺因果关系的直接性;但如果将从A处受领的金钱直接交付于C,则此时存在直接因果关系。〔16〕 大判昭和2年7月4日,《法律新闻》第2734号第15页。由此显然可知,此处因果关系的直接性与建立于给付不当得利的给付概念之上的因果关系,并不相同。
在法律原因的判断上,大审院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只要C因B有效的债务清偿而受有利益,就有法律上原因故不成立不当得利;〔17〕 大判大正元年10月2日,《大审院民事判决录》第18辑,第772页。 另一种见解认为C只有满足善意取得要件,才可认为存在法律上原因而不成立不当得利。〔18〕 大判昭和15年12月16日,《大审院民事判例集》第19卷,第2237页。
由于在实际处理时,杂波及噪声的统计特性未知,某一距离门的杂噪协方差矩阵往往由其极大似然估计(MLE)形式代替,即
2.以骗取的金钱清偿债务的案型
在B以自A处骗取的金钱清偿对C的债务的案型,大审院的判决均在末弘因果关系直接性理论提出之后,因此在此案型中一向要求因果关系要有直接性,如发生与B的金钱混同的情形,即不认可直接因果关系的成立。〔19〕 大判昭和10年2月7日,《大审院民事判例集》第14卷,第196页。
最高裁判所在上述两则判决之后,就确定了现在的立场,即以金钱占有即所有为基础,以不当得利而非善意取得来为被骗取人的返还请求权立基。然而,不当得利说也存在显著的问题。
3.第三人无偿受益案型
在B以自A处骗取所得金钱直接使他人C受有利益(如为C对D的债务)之时,同样在末弘理论之后的判例都强调A、C间需要有直接因果关系,如发生与B的金钱混同的情形,即不认可直接因果关系的成立。
当前国内在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①建筑工程投资方和施工单位普遍缺乏对给排水工程重要性的认识,施工中管道安装的质量要求更易被忽略;②政府相关部门对给排水工程的重视不够,还未形成健全完善的监督体制,难以对施工单位进行有效监管;③专业技术指导人才和跨学科综合型人才缺乏,施工前无法做到对工程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给排水管道安装与光缆、电路等相关工程也无法进行统一设计;④施工单位不太重视员工的技术水平和实操能力,由于一线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导致施工效率和质量都难以保证。
此时,若金钱在B处未发生混同,那么D对金钱的取得,一般会认为构成善意取得,而因为此处不存在既有债务的清偿,因此A、C之间的是否有(支出型)不当得利的问题,均看两者的得利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1〕 大判大正9年5月12日,《大审院民事判决录》第26号,第652页;大判大正9年11月24日,《大审院民事判决录》第26号第1862页。
1.不当得利说的问题
可以看出,在以上三种案型的大审院判决中,大审院有一个基本立场,即金钱仍被作为一般有体物而非作为单纯的价值载体来对待,而非“占有即所有”。
因此,A丧失所有权不能追及的第一种情形,是发生与B的金钱混同,此时B骗取A金钱的行为和B用自己的金钱向C清偿的行为是两个行为,也即A的损失基于B的骗取,而C的得利源自于B的清偿,A、C之间的损失和得利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丧失所有权的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虽未混同,但C善意取得A的所有权,此时A则反射性地丧失所有权,因此无法依据所有权的效力进行追及。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审院时代的判例,裁判并未将金钱所有权从一般有体物所有权中抽离出来特别对待,但以金钱所有权的返还为中心处理的,基本是A对C的追及效力问题,上述判例中并未涉及返还过程中的优先效力问题。
(三)最高裁判所时期的判例转向
1.学说的转变
进入最高裁判所时期,日本关于骗取金钱清偿的裁判立场一改以往大审院的态度,究其原因,还在于学说的引导。
(1)金钱占有即所有观念的提出
上文提及,大审院时期裁判观念的核心之一,是直接因果关系,而直接因果关系的深层基础,在于金钱所有权原则不随占有移转。但在1937年末川博发表《货币及其所有权》一文却推翻了这一基础,该论文将金钱抽离出物的领域,将其作为抽象价值的表现物,认为“金钱所有权原则上随占有一同移转”。〔22〕 [日]末川博:《民法論集》,評論社1959年版,第25页以下,初出《経済学雑誌》1937年第1卷第2号。 依“占有即所有”这一观点推论,金钱一旦脱离占有原则上即丧失所有权。换言之,在金钱上不承认物权请求权,仅承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该理论一提出后,很快便成为通说。
(2)因果关系的转变
同时,因为在不当得利制度的解释上,日本学界早期一直是统一说/衡平说占据通说地位,〔23〕 参见[日]衣斐辰司:《不当利得における因果関係》,载星野英一編集《民法講座》,日本有斐阁1985年版,第60页及以下。 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我妻荣承继衡平说的观点,认为对不当得利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必限于直接因果关系,只需“社会通念上的因果关系”即可,〔24〕 [日]我妻荣:《債権各論》,第 997 页。 此时应当根据骗取金钱受领人的主观样态、其与被骗取人的关系等来判定,不当得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
(3)特别类型的抽离
另外,对于第三人无偿受益这种特殊案型,学说多认为在原权利人丧失权利而第三者无偿受益的情形,应进行实质的利益衡量,保护原权利人,此点在比较法上或在善意取得或在不当得利法中本有规定,但在日本并不存在,日本若完全按照直接因果关系法律逻辑推理,会造成实质上的利益不平衡。〔25〕 同上书,第 1012 页。
2.判例的转向
(1)金钱占有即所有的确立
受到上述通说即末川理论的影响,在1954年的最高裁判所判决中,法院认为即使消费保管合同被无效,已经移转给金融机构占有的金钱也仍应是保管所有。而在1964年的骗取金钱案的最高裁判所判决书中明言“……支配金钱现实占有之人无论其因何理由取得,都应视为金钱的所有人……”〔26〕 最判昭和29年11月5日,《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8卷第11号第1675页。 以此为由,该案中的金钱的被骗取人的第三人异议之诉败诉。
因此,一旦占有即所有的规则确立,原金钱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即告消灭,不但物权本有的追及效力和优先效力会丧失,因此只能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而且以金钱所有权人原则不变为基础的直接因果关系理论也必将面临重新调整。
(2)因果关系的转变
一旦金钱所有权随占有移转而移转,则所有的骗取金钱清偿都会归于上述的混同情形,也即按照大审院的“直接因果关系”判断,骗取金钱的受领人的金钱来自骗取人所有的金钱,而受骗取人金钱所有权的丧失仅与骗取人有关,无论受领人主观状态如何。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让被骗取人丧失所有权,不可能在完全不考虑受领人的主观状态的状况。因此,最高裁判所在1974年一则关于双重骗取的判决中,认为从被骗取人到受领人之间的金钱移转“只要社会通念上认为是以A的金钱满足了C的利益”〔27〕 最判昭和49年9月26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28卷第6号第1243页。 的情形即可,在论述因果关系时,判决书甚至几乎全文照抄了我妻荣在其《债权各论》教科书中的表述,认为“自被骗取人处得到的金钱若与骗取人自身的金钱混同,或者因兑换、存款,甚至是基于其他目的将其中一部分消费后再以其他方式补偿等情形,只要上述行为被认为是因为受领人的目的而为,(被骗取人到受领人的金钱移转)即存在因果关系”,〔28〕 前引〔24〕,我妻荣书。 从而抛弃了从大审院以来要求“直接因果关系”的判断,采纳了我妻荣“社会通念上的因果关系”的理论。
(3)对金钱同一性的认识变化
在上述最高裁判所1974年判决中,从另一个角度看因果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大审院之前还是将金钱作为一般的有体物来看待,判断因果关系时注重其物理上的同一性,但是在最高裁判所的判断完全不同,无论金钱产生何种形态上的变化,在判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时,只判断金钱在价值上是否有同一性或曰连续性。
(4)法律上原因的判断与追及效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何为此处的法律上原因,最高裁判所也有变化。在1967年一则关于单纯的骗取金钱清偿自己债务的判决中,最高裁判所认为受领人只要是“自骗取人对自己债务的清偿是时善意受领,就可以认为有法律上原因”。〔29〕 参见前引〔26〕,判决书。 也就是说,这里被骗取人的主观要件需要时善意。但在上述1974年最高裁判所双重骗取的判决中,即“被骗取人自骗取人处受领上述金钱若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则其在与被骗取人关系上不存在法律上的原因,构成不当得利”。〔30〕 参见前引〔27〕,判决书。
这两则判决相同之处,在于利用“法律上原因”这一要件,在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下,也赋予了作为债权人的被骗取人相当于物权人的追及效力。而两判决之间最大的差别,一在于主观要件从1967年判决中的“善意”限制为1974年判决中的“善意无重大过失”。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在1967年判决中,善意的积极举证责任在受领人一方,而在1974年判决中,金钱受领人的善意无重大过失则是被推定的。〔31〕 前引〔11〕,好美清光书,第 21 页。
从两则判决间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967年判决中,强调受领人去积极证明自己的善意,其后仍然可见把金钱作为一般物来考虑的善意取得法理的影响——虽然在返还的法律构成上已用不当得利,但在1974年判决中,最高裁判所翻转举证责任的做法显然更立足于金钱流通性的考量,〔32〕 好美清光认为这里显然参考了有价证券善意取得的要件,参见前引〔12〕书(好美清光执笔)。 但其法理基础究竟是以不当得利之名行善意取得之实,还是单纯从不当得利中法律上原因的角度去做的考量,在理论定位上则并不十分清晰。〔33〕 [日]我妻荣:《事務管理·不当利得·不法行為(新法学全集)》,日本有斐阁,第51页及以下。
(四)学说的回应与判例的发展
4.小结
在法律原因的判断上,大审院认为C的善意取得构成法律上原因,若金钱(因为B的骗取行为)由A直接交付给C,也构成法律上的原因,排除不当得利的适用。〔20〕 大判大正13年7月23日,《法律新闻》第2297号,第15页。
首先,不当得利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若依照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一般原理,被骗取人对受领人的清偿,本存在法律上的原因。最高裁判所让骗取人与受领人之间直接成立不当得利,而对受领人的主观要件又完全了善意取得的逻辑——要求受领人“善意无重大过失”,且对此主观要件进行推定——因此以不当得利之名,行善意取得之实的批判,不绝如缕。
路人匆忙地来去。不时有汽车从阿里身边呼啸擦过。马路前前后后都没母亲的身影。阿里到底忍不住了,又说:“罗爹爹,我姆妈呢?”
其次,如果按照大审院善意取得的判决逻辑,在不成立善意取得时,被骗取人仍然有所有权,仍有在金钱价值范围内主张优先受偿的可能。但是在最高裁判所不当得利的判决逻辑下,被骗取人就是单纯的债权人,无论返还义务人是骗取人还是受领人,在返还义务人陷于无资力的情况,依照债务人平等的原则,被骗取人只能和其他债权人一样按份受偿。相比起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其他有体物的被骗取人,金钱的被骗取人所受保护显然过于薄弱。〔34〕 [日]田高宽贵:《金銭の特殊性》,载大村敦志編集《民法の争点》,日本有斐阁2007年版,第164—165页。
换言之,对于被骗取人就金钱价值的追及效力,最高裁.、判例的发展
从客观方面来看,在能够维持金钱价值特定性及流通性无问题的情形下,判例也限制性地认可所有与占有的不一致。如最高裁判所在1992年的一则判决中,〔35〕 最判平成4年4月10日《判例時報》第1421号第77页。 共同继承人之一B将被继承人A原所有的现金以“A的遗产管理人B”的名义存入银行,其他共同继承人则请求B支付遗产分割前与法定继承份额相对应的金钱数额,最高裁判所否定了共同继承人的请求。
对于“金钱占有即所有”这一教条,今日的判例也并非全无改变。
3.学说上的再检讨
(1)个别财产归属与责任财产保全进路
针对目前的不当得利说的固有问题,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从方向性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进路。一种认为仍应主要从金钱价值的抽象归属着眼,在能够维持金钱价值甚至其代位物特定性的基础上,仍应认可其在实现过程中的追及效力,四宫和夫即以“物权性的价值返还请求权”命名之。〔36〕 [日]四宫和夫:《物権的価値返還請求権について》,载《四宫和夫民法论集》,第97页及以下,日本有斐阁1990年版,初出《私法学の新たな展開(我妻荣先生追悼論文集)》,日本有斐阁1975年版。 注意此处的特定性,只要能从交易过程中能确认价值上的同一性或连续性即可,并不需要与一般有体物一样的特定。〔37〕 近期的学说也多认为,有必要给予金钱被骗取者优先地位,但论证的路径则与金钱的物权性保护不同。道垣内说以信托法理的为基干,认为对金钱的优先效力应可从将金钱所有人作为委托人的基础上推导出来(道垣内弘人《信託法理と私法体系》,有斐阁1996年版,第202页及以下)。松冈的系列论文也指出,非基于金钱所有权理论的价值返还请求,在外国法也在所多有,如德国法上的“价值追踪”和美国法上的Trcaing法理等,松冈在参照上述外国法理论的基础上,对认可优先效的要件进行了具体探讨([日]松冈久和《アメリカ法における追及の法理と特定性》,林良平先生献呈《現代における物権法と債権法の交錯》,日本有斐阁1998年版,第357页以下,该论文中所引松冈其他论文亦请参照)。
殷桃是重庆人。她跟金星诠释重庆女孩和成都女孩的分歧,都说“好烦”,成都女孩是嗲嗲的撒娇的,重庆女孩,她是真烦,“语气十分干脆。”
3.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实践基础。大多研究者认为,对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和拓展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培育路径研究;对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研究有利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培育且有助于共享发展理念的有效践行。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实践基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与此相对,另一种进路认为,在骗取人有资力情形,其实并不需要主张追即效力,此时之所以需要主张追及效力,基本可以认为是骗取人财产不足的无资力情形。而如果限于骗取人无资力的情形,此时应该通过债权人撤销权来处理。若依债权人撤销权的方式,只有在满足骗取人无资力及受领人有诈害债权意思等要件的情形下,才通过债权的保全才实现追及效力。依此逻辑,可以保持金钱最大限度地流通性,对骗取人人的其他债权人而言,在没有诈害意思的情况下即不需返还,如此不致对其产生过大的交易风险。〔38〕 [日]加藤雅信:《財産法の体系と不当利得法の構造》,日本有斐阁1986年版,第654页及以下,初出《法学協会雑誌》1981年。
AP病程中,外泌体在胰腺组织间液pH值的变化中也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部分外泌体依靠本身的V-ATPase(一种细胞膜上的质子泵)主动提高囊泡内H+的浓度,导致组织液酸化,进而对周围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16]。
“让银行真实、全面地掌握民企信息,是为它们提供融资服务的前提。”某大型商业银行分行副行长吴先屏介绍,企业信息散落在工商、税务等多个单位和部门,信息不共享,导致银行获得的客户信息不完全,往往出现企业多头贷款、过度融资等问题。
综上可知,这两种学说,一种是从金钱作为特定财产的归属出发,另一种是从责任财产(总体)中回收债权的可能性出发,因此在骗取金钱的案型中,前者是个别财产的归属侵害,后者仅仅是责任财产减少的期待侵害。〔39〕 前引〔11〕,[日]平田健治文,第 1285 页。
(2)异议与别除等优先效力
强制执行法的异议与破产法上的别除,一般也被认为物权法上优先效力的延伸。但如果按照上述判例与学说逻辑,除非在能够维持金钱价值特定性及流通性均无问题的情形下,换言之,在有相应的公示的基础上,确实产生金钱的所有与占有不一致的情形,可提异议或别除。如果是在金钱的归属没有相应公示的情形,若直接认可其异议和执行的权利,将对交易安全产生极大影响。至少在目前可见日本的案例中,没有见到金钱归属无相应公示的情形下提异议、别除或判决支持的情况。
代结语:我国实务案型的再检讨
日本与我国一样,并没有对金钱是否可以作为善意取得的对象作出规定。因此,对骗取金钱清偿这一问题,主要靠判例和学说的共同作用。如上所述,从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上看,日本的判例和学说立场经历了非常鲜明的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在把金钱作为一般有体物的基础上,以不当得利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为基础,优先适善意取得制度来处理,不当得利制度仅作为补充。第二阶段是以学说引入“金钱占有即所有”的概念为契机,判例改以金钱的价值特定性为基础,完全用不当得利制度处理,但同时改因果关系的认定为社会通念上的因果关系,用以补足一定情形下被骗取人对受领人的追及效力。第三阶段则是学说反思时期,最主要围绕追及效力的问题,一方面对不当得利构造的理论基础进行批判和再反思适用,另一方面判例也开始反思何种情形下金钱所有和占有分离的问题,认可在特定公示范围内无占有的金钱所有。
对比日本,重新回看我国的两则实务案型,可以看出,我国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地就以善意取得制度来处理骗取金钱问题,特别在无锡案中,在忽视金钱货币和存款货币差别的基础上,还同时认可了基于所有权的追及效力和别除这一特别的优先效力,而对受领人特定财产的公示如何、其他债权人的保护均未论及。若依此法理而为,日后将产生极大的交易风险。
此外,特别是在无锡案中,究竟受领人取得金钱或其代位物的占有,究竟是何种原因,是否还可能存在类似日本法上受领人无偿利益取得的问题,这些事实都未交代清楚,在裁定书中也未作为前提来探讨。因此,很难期待能从中抽象出明确的法理和裁判规范。
涉及骗取金钱的问题,日本法上因为不同时期对不同学说的继受,发展出了一条特别的理路,无论大审院的直接因果关系、金钱的占有即所有或社会通念上的因果关系,如是教条的继受,今天回看都未必有非常清晰一致的逻辑。但是从日本所经历的三阶段的讨论来看,金钱的占有何时被认定是所有,如何在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引入绝对权的保护,边界为何,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这些问题今日都已能看得比较清楚。相比之下,我国实务要去面对的问题,恐怕是我们是否要固守善意取得这一种法律构成,还是现在就该去勇敢迈出第一步,在金钱的物债效力之间去思考不同案型中不同法律构成的可能。
Abstract: When dealing with cases of paying off debt with money from a third party by deception,Japan civil law has three-stage history of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ory.In the empire of Japan,the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of Japan treated money as general tangible property and recognized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money.While after the World War II,the Supreme Court of Japan held that“once possessed,the possessor owns the money,”and then followed the law of unjust enrichment.Based on this possession theory,Japanese civil law has put more effort o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judicial practice,including cases aroused in derivative acquisition,and their study has made great sense to the whole world.Thus,the further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these problems between Japanese law and Chinese law would benefit us enormously in this field both academically and practically.
Key words: paying off debt with money from a third party by deception,unjust enrichment,running with the asset,rights of privilege,legal causes
中国分类号: D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039-(2019)02-0104-112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