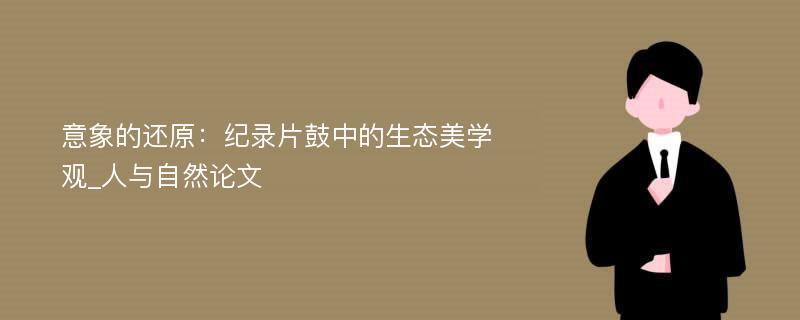
影像的复魅:纪录片《德拉姆》中的生态美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录片论文,美学论文,德拉论文,影像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09)04-0050-0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09.04.010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纪录电影《德拉姆》自问世以来,评者如潮,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无论是竭力推崇还是吹毛求疵,众多评论文字令人遗憾地几乎都局限在传统艺术批评的窠臼中,以至于勉为其难、语焉不详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使一部虽然称不上是杰作,但本应引发影视制作观念转变的作品,淹没在批评的嘈杂中。个中原因就是批评视野的局限,忽视了影片的生态美学内涵。
一、冷峻影像中的自然美复魅
国内对《德拉姆》最为权威和最有影响的评价是2005年首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奖最佳导演奖的评委评语:“透过冷峻的镜头视角,传递博大的人文关怀,一段茶马古道上寻访中思索的旅程,让国人初识纪录片深邃的艺术意境。被认为是中国导演本年度最具国际水准的一部作品。”①
评语写得很到位,精致又情感化,表扬的核心在于“博大的人文关怀”和“深邃的艺术意境”,前提是“冷峻的镜头”,而这恰恰以最寻常的“从主客体二分到主客体融合”的认识论美学原则,背离了导演的“生态整体观”创作初衷。
导演之所以要“冷峻”纪录,是因为他虔诚的创作心态:“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就像高原的山脉一样,不卑不亢,充满了神奇般的色彩,与自然和谐地并存——我们这些外边来的人,只能仰视他们、欣赏他们、赞美他们——这里能够给你一种力量,一份祥和及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赞美而改变自己。”②
从生态美学观看,“仰视”体现了导演镜头下的茶马古道的自然美和作为自然美一部分的原生态民族,“从祛魅到复魅”的价值。所谓“祛魅”,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使我们对自然失去了神秘感;而所谓“复魅”,就是要恢复对自然必要的敬畏、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在田壮壮的心目中,自然美不是与社会美、形式美和艺术美对称性存在的美,而是通过影像独立出来的魅力。正如曾繁仁所概括的,是为了在烦躁的当代生活中“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恢复大自然的神圣性,恢复大自然的潜在审美性”[1]262。纪录片的最高目的,是要将散落在边地的自然——茶马古道的景、人、事,以影像崇拜的方式展现出来。
田壮壮天生具有诗人般敏感细腻的感受能力,他用一颗赤子之心去谛听鸟儿的歌唱,欣赏天空的色彩,嗅闻花朵的芳香,品味雨水的味道。影片大量使用空镜头,客观呈现大自然的神奇、神圣和潜在审美性。
大自然的神奇性是指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无论人类的科技如何发达,都不能穷尽它的奥秘。《德拉姆》中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体现在无处不在的雾气上。它虚无缥缈、变化无常,是平安女神——德拉姆的化身。女神庇佑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天地之间充塞着神灵的恩泽。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摄人心魄:女神缓缓揭开笼罩村庄的面纱,好似一幅空灵飘逸的山水画逐渐展开,美丽的脸庞赫然呈现,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导演在幕后花絮中解释这个镜头的获得纯靠运气,是大自然造化的神奇和美丽。观众久久凝视着这个镜头,感受到宇宙万物的神秘与生命空间的拓展。
大自然的神圣性是指自然是人的生命本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好比婴儿与母亲之间血肉相连、难以割舍的依存关系。《德拉姆》纪录了茶马古道怒江流域段马帮的生活以及居住在大江两侧居民的生活,已不仅仅是现实本身的呈现,而是田壮壮将感悟和思考进行艺术化表述和茶马古道影像意义化的过程。银幕上的怒江绕山前行,时而穿过乱石,惊涛拍岸;时而流入森林,微波荡漾。索道下的怒江好像狂吼的猛兽,让人不寒而栗,张扬了两岸人民粗犷、刚毅和不屈的民族个性。截然相反的是,月光下的怒江则像一条闪闪发光的腰链,温婉缠绵,塑造了两岸人民温柔多情、乐善好施的美好形象。纪录中的怒江影像在还原中变异成了一个颇具神圣感的抒情形象:哺育了两岸人民,他们彼此之间拥有休戚与共、血浓于水的情感。怒江隔断了这里与外部的联系,造成了物质资源的贫瘠,但也映衬得生活更具有历史沧桑感。天宽地阔将怒江两岸居民生活的苦难简化成生命的达观,所有的愚昧、悲痛都被散布在天地间的微风吹得干干净净。104岁的老太太经历岁月的摧残和生活的压迫,依然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被妻子抛弃的村长毅然顶住流言的压力,默默为村民奉献自己的精力;与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赶马人拼命赚钱,为将来幸福的生活努力打拼。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尊重就像大江奔流永不停歇。
大自然具有潜在审美性是指大自然的美并不是因为人类的存在才显现,它本身就具有形式美以及力量美。康德认为艺术只有近似于自然才美的观点,体现了自然和艺术的审美共同性,而黑格尔则断言,艺术美高于自然美,他将自然美开除出美学殿堂。田壮壮明显倾向于康德的观念,镜头语言中的自然风景成为凌驾一切、毋庸置疑的美感对象。自然中的美具有客观性、不可磨灭性,它们不是因为人类的欣赏才存在美感。在这种观念统帅下,田壮壮的摄影机与拍摄的对象总是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用谦虚卑微的姿态去仰望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从怒乡丙中洛到藏地察瓦龙,总路程共90里,一路上,风景如诗如画。太阳从对面的山坡绽放出笑脸,为林霏披上一件金色的外衣,层林随着微风舞动好似巨浪翻滚。江水湍急,一只雄鹰展翅飞过,雄健的身体镀上一层金边,在青山绿水中自由翱翔。藏地的路自身具备生命特质,它不是因为马帮的穿梭才展露它的美丽,脾气暴躁的时候,一股微风便会招惹得狂沙漫舞,展现扑朔迷离的彪悍美;脾气柔和的时候,阳光普照下小路条条分明,展现清晰透彻的温顺美。但同时自然美与人类头脑机制中所固有的审美具有一脉相通的特质,正如藏路体现的彪悍温顺犹如男人女人的性格。用方东美的话概括就是,“自然”是“天地相交、万物生长的温床”;是“宇宙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是“含蕴着理性的神奇与热情交织而成的创造力”;是“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的混融圆通”[2]。
二、沉闷影像下的绿色诗意原则
有论者再三批评影片的沉闷,沉闷的原因主要表现为诗意的景象和逻辑无序之间的矛盾:《德拉姆》采用诗意式制作,这种模式的纪录片通常比故事片呈现出更多完全不同的镜头和场景,很少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以叙事结构组织在一起,而大多是围绕一种操控着的逻辑化主题……《德拉姆》的致命伤就在于缺乏这种意义逻辑,因此尽管它的每个画面都堪称一流,但没有一个有力度的视角串起这些散在的碎片[3]。而我们认为,那“操控着的逻辑化主题”恰恰是影片点睛之处,论者在批评单纯的形式美意义上的诗意时,却未能发现或者说是忽略了、或者是无法明晰那沉闷的影像里蕴含的“操控着的逻辑化主题”:生态性的绿色诗意。实际上,影片是有意不强化逻辑组织,而把绿色原则撒播在分散的影像中。
绿色原则是生态美学的核心观点,是在生态危机愈加深重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深刻地包括了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美学关系。绿色原则在宏观上表现为:从人类中心过渡到生态整体,从工具理性过渡到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过渡到有机整体,是更宽泛的人道主义。
如影片中失去了心爱的马的赶马人正多说:“牲口很可怜,要驮很多东西,它不像人能说话,说我太累了,你给我驮的东西太重了。我生气的时候用鞭子打它们,其实我是心疼的,它被石头砸死了了我特别伤心。”这难道不是绿色诗意吗,不是“多元共生”、“生态平等”和“生态同情”观念的直接体现吗?在生态学中,生物的多样性是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繁荣发展的最基本特性之一,只有多样性,生命才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美丽。“多元共生”意味着和谐共在,也是人类审美意识赖以生成的前提,因为丰富的世界蕴涵了无限的内在生态价值和生态美,意味着人与万物的平等,人类才在诗意栖居的家园中安心。文艺作品的绿色之思,重点之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普遍共生,而不仅仅是人的胜利和伟大。
绿色原则在微观上表现为四个原则,首先是“尊重自然”;然后是“生态自我”,将狭义的局限于人类的本我扩大到整体系统的大我;其三是“生态平等”,所有生物有普遍共生性,都享有在自己的生命链中所应有的平等发展权利;最后是“生态同情”,对万物怀有仁爱和博爱精神[1]259。
生态美学绿色原则在文艺中体现的新艺术精神就是“自然写作”。在影片中,导演实际上就是用摄影机进行自然写作,让观众尽可能地接近自然,以人与自然友好和谐为最高的题材选择,对自然采取歌颂的态度,通过作品的描述引发读者对环境的哲思。比如在人物访谈的选择上,可以看出导演对“生态自我”的理解:104岁的怒族老人卓玛用才,漫长的一生仿佛无法支持所谓的诗意表达,但却是小我融合在大我中的表现。
进一步看,正因为过于强调影片的人文诉求,违背了生态绿色原则,才导致了理解《德拉姆》的偏差。
当影片获得翠贝卡电影节纪录片大奖后,《纽约时报》的资深影评人斯科特评论说:“影片以田园牧歌般的韵律,令人惊叹的风景将人带入那看上去尚未被都市文明污染的原住民生活中……具有远远超越其地理和风土特色、可以引起全球共鸣的深刻内涵。”③许多评论文章就是从此处着手赞美所谓“深刻内涵”的。《德拉姆》DVD封底宣传语中就综合了诸多评论观点,认为“深刻内涵”是指“绚丽深邃而伟大的行程”中的人文性。如江宁认为,《德拉姆》就是这样一部拂去了历史烟尘、接近生活本相且蕴含了深刻意义的扛鼎之作:留住历史,留住记忆……是一次艰辛又浪漫的人文之旅,从主题的开掘上看,试图通过人与自然环境艰险、严酷而又不屈的抗争,揭示人性中最具魅力、最有原初激情的顽强生命力……在一次又一次近似沉闷的讲述里,我们感受到……对生命的感激和对生活的坚持[4]。
此类评价的核心就是误解斯科特原意的、典型的自以为是的社会学评论。其实,我们谁都不否认影片的人文价值,但人文性或者说“以人为本”,在影片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张扬,不是导演的原意。当代生态批评,就像解构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修正主义批评、解构男权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样,是为了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策略[5]。表面上看是把长期以来的人类重要性放在一边,实际上,生态美学的宏观意义,是从人类中心过渡到生态整体。斯科特强调的“超越其地理和风土特色、可以引起全球共鸣的深刻内涵”,其实是一种明确的生态文明观,指通过影像所呈现的生态美为处于文明危机的人类提供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沉浸在都市文明中的人们远离大地和自然,往日的生机活力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死气沉沉的腐肉。田壮壮反省现代社会不合理的生活结构,携带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朋友——摄影机,聚齐一大帮志同道合的友人,逃离被死亡笼罩的城市,将自己放逐到散发着原始气息的边陲境地,身负梦想,走过一段炼狱般的艰难旅程,将简单直白却又亘古不变的“神谕”用影像的方式传达给芸芸众生:自然才是拯救社会、疗救心灵的一剂良药。
在当前,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理念,“生态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和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论、路径及其实践结果……是对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质的提升和飞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就本质与含义而论,生态文明是当代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力资本经济相互融通构成的整体性文明”[6]。以这样的高度看田壮壮的创作,《德拉姆》的绿色原则弥足珍贵。
三、符号影像后的生态存在美
生态美学是一种当代存在论美学。生态存在论美学有几个基本范畴:生态论的存在观、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诗意栖居、家园意识、场所意识等[1]293。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应从认识论过渡到存在论,已成为后现代理论家们的共识。在认识论中,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在存在论中,“此在”和世界有一种在世关系,人与自然是统一的。
《德拉姆》的沉闷或者说散乱,其实在追求生态论的存在观中的“此在”,而这“此在”存在于“天地神人四方世界”结构中,展开后获得审美的生存必由之路,“四方游戏”是“此在”在世界中的生存状态,而最终的效果是“诗意地栖居”。
在我们看来,《德拉姆》影像符号的生态存在美,集中在它对“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和“家园意识”的恰当表现上。
早在史前时代,仓颉造字就体现了“人生天地间”的意境。“大”字象征一个伸开双臂、叉开双腿、站立着的人;“立”字就是在这个人的脚下加一道横线,那横线就是大地;如果在这个人的头顶上方加一横线那就是“天”[7]。这反映了原初人民敬重土地、顺从天意的思想,人是居住在天地之间的生物,天地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场所和物质基础。老子把这种原始混沌的生态思想提炼成哲学语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海德格尔借鉴了老子“域中有四大”的框架,将“道”置换成“神”,阐述“神”是一种规律,是万物遵循的法则,它隐匿于其他三者之中。
由于海拔和环境的关系,《德拉姆》中的居民是最空灵的旅行者,是更接近天空的生存。同时他们也是最厚重的耕作者,脚深陷于大地之中,吸收天地灵气。虽然人烟稀少、道路闭塞,但让人惊愕的是这里融合了多种教义,西洋宗教、土著宗教、佛教在这里和平相处,宗教信仰使各少数民族居民其乐融融。影片中的“神”就像是一种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和宗教熏陶下的坚定信仰。
影片中“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主要体现在“茶”这个物质上。《德拉姆》又名《茶马古道》,把茶、马、古道归为一体。茶接受阳光的爱抚、雨水的滋润和大地的养分,直接与人的生存有关。西藏人民长年吞食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难以消化,茶成了生活的必需品。为了消除藏族人民的生活危机,也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云南边界的马帮就长期往返于危险的古道运送茶、粮食等货物,茶马古道不仅仅是贸易之道,是两地人民的生命通道,同时也寄宿着神灵。“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与自然万物都能通过神发生交感。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社会,这种生命一体化观念,不仅体现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上”[8]。影片中,家家火塘边都摆着一壶酥油茶,女主人用酥油茶桶打酥油茶,技术娴熟,动作潇洒,富有生命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呈现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特质。一束圣光从天顶照射下来,火焰如盛开的花朵刺激眼球,罐子里的酥油茶热闹地跳跃,女主人弓着身子,用勺子不停地搅拌,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平静,生活被一种诗意所包围。这种温暖瞬间传递给观众,喝酥油茶也像一首壮美的诗,粗糙朴质的大碗中盛着浓稠的茶,一饮而尽的快感和喝完后的神清气爽,让人感慨造物的神奇,人与神在烧茶、喝茶等日常活动中进行肉体磨合和精神碰撞。
再看家园意识表现出的生态理想美。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新时代的本质是由神话、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④。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也说:“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中国人,找到了这一造型范式来体现自己的世界观。这种沉入自身,沉入‘伟大的无’(它同时又是衍生万物的本原)当然是对每个人在单独面对大自然时的那种激越状态的诗化解释。在一个人单独面对大自然时他会感受到一种自我融入大自然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独特感觉,在这种感觉下,宇宙与个体之间的矛盾消除了。而通常,宇宙与个体总是对立的,正如人与风景也是对立的一样。”[9]
田壮壮借鉴中国山水画“无”的表现方式,用自然、质朴的镜头语言,借助神奇浪漫而又危机四伏的自然风光,描绘了居民贫瘠而又富足的生活,营造了一个民风淳朴、天真的理想国度。影片一开头便是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的公路,没有飞速疾驰的汽车,没有震耳欲聋的喇叭,几匹马零零散散地站在路旁,安静地等待主人到来。稻田里插着绿色秧苗,洋溢着青翠的气息,人们悠闲散漫地来回走动。田壮壮说:“云南的风光是美的,到处是不用结构和组织的画面和构图。但是,到了那边之后,你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你都会觉得简单、朴实、平凡。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无法创作出来的生活美。”[10]贪婪、虚伪和世故等恶劣的品质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善良、真诚和好客。山间破烂的喇嘛庙里居住着最虔诚的信徒,少年们坚信皈依宗教可以逃避罪孽;白色房子映衬在青山绿水之间,那是迥异于喇嘛教的外来宗教——基督教。80岁的老人带着族人,倾听着上帝的召唤。热切的眼神,安详的动作,已然领悟上帝的教诲。
这就暗含了海德格尔所谓的人与自然相处是诗意的高境界。马帮运用最原始的工具进行运输,他们踏着不急不慢的步子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卷起山路层层的泥沙,被郁郁丛林吸收回去。马队像上天派来的使者,打破荒山野岭的沉寂;马蹄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仿佛与流水光年打了个照面。燃起篝火去点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配合着篝火温暖的光辉,天上的点点繁星熠熠发光、交相辉映。最原始的地方保持最原始的面貌和家园。“‘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的感觉,因而才使那个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与。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11]而这个由大地赐予的人间仙境可能由于现代化的侵入慢慢被腐蚀,最美丽的女教师可能会嫁给城市里来的江湖老大,拥有六种语言的家族可能会做起旅游生意,公路的修建,电器的涌入,可能会让这里淳朴的一切逐渐消失。虽然有这种隐患,但是导演仍衷心地赞美眼前的村庄:它紧贴自然,满眼笼罩葱绿,心灵清澈见底。
收稿日期:2009-03-02
注释:
①《第一届中国导演协会年度奖获奖名单》“最佳导演奖”评语,见《电影艺术》2005年第2期第30页.
②材料来自《德拉姆》DVD封底宣传语.
③材料来自《德拉姆》DVD封底宣传语.
④参见: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