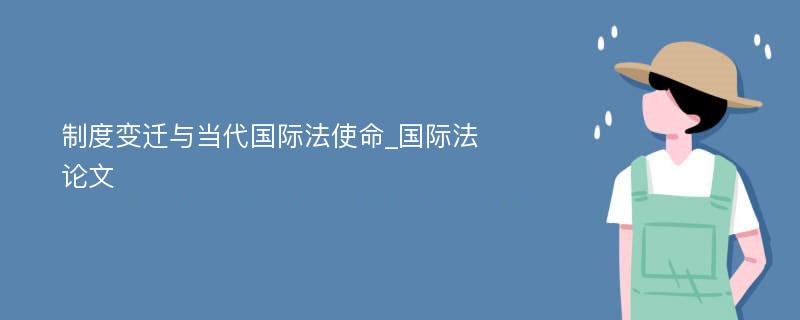
体系转型与当代国际法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使命论文,当代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律规范与产生它的体系背景联系密切。一方面,国际法是体系背景的时代折射,体系变迁影响国际法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法作为对体系变迁的反映和规范,又具有一定的指引、能动作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代,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引起的全球碰撞使法律规范的治理、建构作用越发突出。探究体系转型时期国际法的历史使命和建构功能,有助于拓宽国际法的发展视野和促进国际社会的协调、有序发展。
一、体系变迁与国际法的社会基础
体系变迁影响国际法的发展。从法哲学的角度首先对体系变迁及其社会基础进行宏观考察,能够得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正确看待国际法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以此为基础,主动构建和定位国际法的发展路径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这些认识主要有:
其一,法律演进与体系变迁紧密相联。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自类人猿演化成人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已表现为由原始氏族到单一民族再到多民族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基于“地理临近,语言、历史、文化相似,利益趋同,责任与共”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而“有社会就有法”,与此种社会变迁相适应,法律的发展表现为,由原始习惯为主到伦理法律相兼再到成文法律为主。国家的形成,使以强制为后盾的法律逐渐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调整成员利益的统治工具。而晚近法律的全球化态势,使国内法的发展走向了国际化的轨道,“国家之间的法”随着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出现了世界性的“强行化”趋势。
体系演进的动态迁延启示我们,作为一定社会的控制工具,法律是某种社会情势的反映,并且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起着指引、评价和规范作用,因而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时,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动,因而法律必须经常作出相应调整,而不能削足适履地以过时规定作为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尺。现实生活中,国际关系学者往往过于重视主体实力,忽略国际法的作用;国际法学者则过于强调法律的静态规范作用,忽视法律后面的实力因素。实际上,实力变迁引发法律调整,但这种调整是使法律更好地适应、规范未来,而不是满足强权的需要。
其二,世界不仅是一个逐渐累积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普遍联系不断扩大的过程。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制形成的是欧洲国家“主权的宪法性原则”;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制也限于“欧洲协调”,但此后亚洲的土耳其和美洲等地区逐渐纳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则使国际体系的重心开始向欧洲两翼转移;而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更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此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协调迅速进入了“国家的传统管辖领域”。世界体系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恰如克劳德所总结的,“欧洲协调”体系和随之而来的大国特别会议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前身;海牙会议则是联合国大会的前奏,会议确立的“一国一票”平等观念和决议由多数票通过,逐渐成为国际组织一项可以接受的规则;而国际功能组织的发展,则为现代国际组织奠定了组织结构——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①体系的组织化使各要素相互影响和彼此互动的进程加快,世界成为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社会规范由此成为需要。
其三,体系进化的文明、法制趋势。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金在其《各国如何行动》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各国的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被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②由战争到和平表明了社会变迁的文明进步趋势,由此,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的建构越来越具有可能。历史的交替演进无一不是通过大规模战争确立的,体系的崩溃或形成反映了体系内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变化。体系的变革淹没了众多战争的苦痛和社会的野蛮。然而战后不仅战争、而且武力使用的禁止,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使国际法治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和需要。现如今,举凡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或者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不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调整直接或间接相关。任何国家都不能为所欲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须以国际背景为参照。如此形势,使得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直接出现相互建构、彼此制约的情形,避免了几百年来国际法单向依附国际政治、片面沦为国际政治工具的非正常情势,从而促使国际体系日渐向正义、文明、法治的方向演进。体系的变迁表明,国际组织、国际法律规范与产生它的体系背景联系紧密,体系变迁通过作用于国际法的社会基础而影响国际法的产生和功效。另一方面,冷战后的体系转型,对国际法的规范、建构要求也愈益突出。这种转型的社会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格局的“多中心”化。雅尔塔体制崩溃后的美国成为超级霸权,但这只是一个“单极时刻”。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所说的“五大力量中心”有消有长,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开始迎头赶上,中、美、俄、欧之间出现战略对话甚至结构互动,而海湾战争后美国霸权的上升趋势经科索沃、伊拉克战争遭受挫折。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因德、法、俄等带头反对而师出无名,不仅如此,此后伊拉克的持续动荡更使美焦头烂额。当前来看,美欧关系虽有修补,但中、俄、美、欧、日、印互动加深,相互依存趋紧,世界多极化发展虽有曲折但难以避免。二是国际社会的市民化发展。与国际格局多极化、民主化相呼应,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际体系的社会基础发生深刻变革。各地区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国际组织大量增生,对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权力现状施以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在诸多领域得以不断突破,民主、和平、人权等进步潮流深入人心;发展的号角吹遍全球,商品、人员、资金、技术在世界各地流动;互联网迅速普及,世界舆论形成强大的道义浪潮;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全球治理呼声增高。
体系背景的转换为国际法的规范、建构作用提供了要求和可能。当前,与体系的躁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于僵化的国际法体制已日显老套,难以完全包容、消解新旧冲突引发的张力。联合国改革由于“涉及各大国、各地区不同国家和集团的利益,关系到在联合国内建立何种新的力量平衡以及联合国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③而难有实质进展。但冷战后特殊的时势为安南秘书长提供了借力用力的契机。通过召开千年发展会议特别是联合国60周年世界首脑会议,处于“十字路口”的联合国“中央地位”被重新肯定,国际法的权威得以申张;“安全、发展、人权”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升级后的人权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并列成为联合国的三驾马车;国际社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被提上重要日程。联合国改革在力量积蓄中稳步推进。总之,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全球化联系的发展、各国共同利益的增加,已成为作为客观秩序的国际格局与作为主观秩序的国际规则④发生变革的基本动因。
二、体系变迁与国际法的社会建构
上述体系基础构成了国际法发展的广阔背景。一方面体系变迁宏观上推动了国际法的价值发展,另一方面微观上国际法对体系内容的形成又具有指引、建构作用。即所谓“法律是政治(社会)的工具,但同时政治又被期望在法律的框架内变化”。⑤
体系变迁之所以影响国际法的发展,是因为法律乃是对一定社会现状的表述和反映。作为社会的一种控制工具,法律与体系联系非常紧密,社会的发展和利益对比的改变,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通过合作或斗争来作出微妙或激烈的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往往要由法律来固定,并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推动或调适。就像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政治必然体现社会的要求,而法律必然反映政治的主张。因此,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国际法律,国际体系为国际法提供社会基础和体制保障,而国际法对国际体系进行法律确认和体现。
一般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意志协调,即相互妥协,但主权国家为什么要相互协调或妥协呢?国际社会既然是主权国家平等的社会,协调或妥协就只能来源于对共同价值和利益的追求。《奥本海国际法》指出,从一种立场来观察,国际法就像国内法一样,是道德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产物,同时也是道德和经济因素有利发展的基础。⑥而道德、经济因素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纽约大学熊玠教授所称的体系价值,即一定的体系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或理想,而“如果规范可以被看成是‘游戏规则’,体系价值则为特定时期国家间关系这一游戏本身下了定义”。例如,《联合国宪章》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确认来源于列宁和美国总统威尔逊之间的政治宣传战,“起初含义很窄,二次大战后,受体系价值的影响,开始成为全世界都为之奋斗的理想”。⑦在“西南非洲”一案中,体系价值甚至使国际法院的前后判决(咨询)出现变更。体系价值或主流道德直接限定了国际法的发展。
另一方面,国际法的发展对体系变迁也具有相应的建构作用。这种建构作用表现在:(1)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承载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2)法律将社会的共同利益注入到社会成员的行为之中;(3)法律根据社会的理论、价值和目的构建社会的未来。⑧纵观战后以来国际法的社会建构作用,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废弃战争到禁止使用武力。国际法是从战争法发迹的,从两次海牙会议对和平的倡导到国联盟约对战争的限制,从非战公约对战争权利的废弃再到《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反映了人们运用法律规范、制止战争的要求。总的来看,《联合国宪章》的第一要务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在科技(特别是核、生、化以及电子制导技术)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战争日益成为人类难以承受之重,而失去了和平的平台,所有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如此价值规范,使禁武成为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无可阻挡,其强行法性质,甚至使非联合国会员国亦不能例外。今天,任何武力的肆意滥用,都不但会成为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而且会被《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措施所拦截,从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成为国际法推动的价值共识。
第二,人权保障成为国际法的“合法关注”事项。如果说维护和平是《联合国宪章》追求的外在秩序要求,促进发展、保障人权就是其寻求的重要内在正义。实际上,就其本质来说,无论社会演进的人本论还是国家起源的契约论,其基点都在于人的权利。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无论经济压榨、奴役这种广义的权利侵犯还是具体的个人权利或集体权利的极度扭曲,都可能点燃战争的引信。因之,保障人权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基础。为此,《宪章》序言开宗明义宣布,“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第1条宗旨规定,“促成国际合作,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以此,宪章成为战后人权国际法的重要母源和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依据,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和尊重。
第三,环境保护进入国际法调整领域。环境是人类生存的重要载体,人类在从手工、机械时代进入到电子、原子能时代的同时,也使生态变得日益脆弱,法律调整进入环境保护越来越成为必要。国际环境争端第一案,特雷尔冶炼厂案确认了跨界环境损害的赔偿原则;禁止核试验案也以法国声明不再进行大气核试验而告终。1972年和1992年的两次世界环境大会成为人类保护全球环境的统一行动,确立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世贸组织确认,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人权是人类生存的重要价值所在,从而以“软法”著称的国际环境法通过借助贸易机制、政府间协定而逐渐具有可执行力。美国即因拒绝批准2001年《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而承担了空前的体系压力,在此,各种环境保护规范成为评价是非的判断标准。
第四,人类共同利益出现新曙光。共同利益是国际法规范新发展起来的概念。共同利益原指海床洋底、南极以及宇宙天体等共同财产。自1967年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帕尔多提出人类共同财产这一概念以来,包含人权、环境保护等共同利益的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人类共同利益是国际社会发展紧密关系的物质基础,没有各国联系的密切,没有对国际争斗的深切反思和“共赢”前景的美好期盼,共同利益(合作国际法)这一法律规范不可能这么快地得到承认和发展。一般认为,国际组织是不拥有领土主权的共同体组织,随着共同财产概念的发展,特别是国际海洋管理局对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管理,这一论断似乎被推向了局部真理的边缘。可以认为,人类共同利益观念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曙光,是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构成性规范,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外空条约》的实施,这一规范价值正被逐渐引向深入。
第五,普遍优惠制度形成国际共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鸿沟是历史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目前的两极分化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的进步。基于这些认识,1975年欧共体与非加太国家签署的《洛美协定》迈出了给予发展中国家普遍优惠的重要一步,并使两者的共进共荣趋势不可遏止。1994年关贸总协定的第4部分继承了原关贸总协定1965年增加的3个条款,鼓励发达国家在贸易条件下“有意识有目的地努力”给予发展中国家帮助,并且在谈判中向发展中成员方做出的减让不期望得到互惠。国际经济法领域的普惠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合作中追求实质平等互利价值的形成。
第六,强行法出现。国际法由于欠缺强制力长期被认为是带有原始性的“软法”。同时,现代以来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发展使国际法的有序化问题日益紧迫。⑨众多法律的交叉发展和议题的相互渗透使严肃的法律规定变得时有矛盾,虽然《联合国宪章》第103条原则确定了宪章的“优先地位”,但并没有因此使与之矛盾的法律归于无效,泛泛的规定难以掩饰对鲜活现实的拘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的“强行法”,终使国际法的位阶制度得以显明。1970年的巴塞罗那电力设施案引申出了国家的“对世义务”。强行法规范是国际法发展的宪法性概念,它所保护的是国际社会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利益,违反强行法的法律规范直接无效,而违犯强行法的行为也会被国际法强制制止。强行法制度的出台,不但有益于国际法的体系整合,而且有利于国际法效力的加强。表面无序的国际社会有了“刚性”不断加强的法律体系,便于国际法对国际社会的统摄和规范。
总之,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的社会建构不但存在,而且有力地影响、规范了主体的社会行为,当然这种建构是以体系发展为支撑的。
三、体系发展中的国际法功能使命
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时代。如果说二战后是大国霸权体系形成的绝佳时机,那么冷战后则是全球法治发展的新契机。国际格局的转换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国际法在新条件下能够有所作为。当前,时代变革已投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国际法的任务应该是主动迎接变革和挑战,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朝有序方向发展。反思体系发展中的国际法功能使命,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体系价值与国际法的建构使命。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是马克思主义辩证论的基本观点。在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强调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新自由主义肯定国际制度的独立变量作用,建构主义则主张国际规范的合法性对大国间认同的建构。三种理论各有所长但互有偏颇,国际秩序的平稳运行实际上是权力、利益、制度、共识等“合力”作用的结果,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螺旋上升”没能脱开辩证论的基本论点。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肯定社会物质结构(权力、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不能否定社会规范结构的相应作用。
“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与物质现实同样重要、同样有影响。”⑩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称从学派的角度看,现实主义主张硬权力,自由主义倾向软权力,“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使那些无形的权力更显重要,国家凝聚力、世界性文化和国际机构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了”。(11)卡赞斯坦将作为软权力之一的规范,进一步分为构成性和调整性两类,认为在一些情形下,规范像准则一样起作用,具有构成性效果;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规范像标准一样起作用,即表明什么是合适的行为,从而产生调节性结果。因此,规范或构成认同或调节行为,或二者兼有。(12)国际法的构成性规范(大国主导)指引着国际法发展的未来,并通过一定范围内国际社会(中小国家)的普遍接受而成为调节性规范,“中小国家很多是在联合国规范的作用下成立、活动和变迁的,它们的许多观念和行为受到了联合国的建构。用费丽莫的话说,就是国家部分通过与他者即其它国家、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来理解利益,后者说服国家相信某个新目标的价值或善意。”(13)总之,建构之后调节,调节之上建构,两者共同规范着国际社会的有序发展。
当然,国际法的建构是以体系背景为支撑的,“国际法提供稳定的国际关系,这种稳定反过来是各国追求其国家利益的必要基础”(14)。安南秘书长在有关联合国改革的《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报告中对当前的国际体系进行了宏观分析,指出《宪章》所载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今天与1945年一样有效并且切合实际。然而,虽然宗旨应当坚定,原则应当永恒,但是实际做法和体制必须与时俱进。联合国必须根据21世纪的需要和环境而全面调整。冷战后,两极对峙的结束以及全球化、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国际体系的价值重心出现位移。安全取代和平成为新的追求,同时发展、人权等价值被提上新的高度,成为了当前时代新的体系价值。
体系价值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而国际法规范通过对体系价值进行建构具体编织着国际社会的未来。在发展方面,国际社会继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后,要求发达国家至迟于2015年实现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作官方发展援助并制定时间表,呼吁尽快完成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充分致力于实现以发展为重点的目标。在安全方面,国际社会进一步达成新的安全共识,认为各种威胁彼此关联,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靠自己实现自我保护,为此,国际社会在加强以安理会为主的集体安全体制的同时,承诺充分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及《化学武器公约》等法律,并且设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等机构。在人权保护方面,国际社会在冷战后主要发展出了“保护的责任”,以作为对灭绝种族行为、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战争罪采取集体行动的基础,确认在国家当局不愿或不能保护本国公民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安理会采取代位性保护行动。国际社会在2002年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升了人权理事会的作用。总之,冷战后安全、发展、人权成为了国际法的重要价值支柱,而国际法的相应完善,使三者互为犄角,相互依赖,共同构建、维护着秩序的稳定发展。
其二,法的功能与国际法的调节作用。与建构作用相比,调节、规范作用是国际法的基本特征。这种调节作用之所以发挥主要在于它的法律属性,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能对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提供制度约束。根据前南国际刑事法庭首任庭长卡塞斯的分析,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国家越来越受国际法制约:日益增多的国际条约、愈来愈严厉的对国家使用武力的限制以及国际法本身强制力的加强。(15)第一个因素使国家处于国际法包围中,违法“无处可逃”;第二个因素不但使国家间使用武力受到严格限制,而且使一国境内的战争或武装冲突有关责任人员有可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16)第三个因素无疑使国际法拥有了“牙齿”,违犯法律需要付出代价。
总起来看,国际法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有三。一是规范与预期。法律是构成性价值的规则表达。国际法通过明确的条约规定,能使国际行为减少模糊,增加明确,形成预期,使国际社会真正“有法可依”。国际法的规范作用本身能指引国际社会行为主体朝规则、秩序的方向演进,因为通过条约形式把各种规范法制化,实际上等于确定了建立秩序的指南。更重要的是,如此行为是通过各当事国的多边谈判平等实现的,不但能克服法律的空缺或模糊,而且能防止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专横强制,从而促进行为主体的合理预期,保证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二是衡量与评价。法的评价作用主要是指法律判断、衡量他人行为的合法与否,相对健全的国际法规范能为行为主体的行为评价提供客观标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的遵循程度往往不能与国内法相比,国家特别是大国出于短期利益考量,可能不时违犯国际法的规定。此种情况,国际法虽然不能完全进行强制阻止,但它至少能为国家行为提供可资辨别的尺度,使违犯行为昭然若揭。例如,对伊拉克的非法入侵,就使美国变得灰头土脸。三是约束与惩罚。国际法是各国意志的最后协调,因而其遵守一般会符合国家的利益,而其违反也就一定会受到某种机制的制裁。《宪章》序言宣告,“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它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也规定,条约必须遵守,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随着共同利益的增长,国际法各种司法、仲裁机构效力增强,次级规则增多,强行法出现,此等情况无疑是国际法强制约束力加强的明显表现。
其三,全球网络与国际法的组织促进。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无论国际法的建构作用还是调节作用,都离不开其发挥作用的组织平台。自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组织——莱茵河管理委员会成立至今,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趋势愈来愈明显。据统计,国际组织数量2004年已达58859个,其中政府间组织为7350个。(17)上至宇宙天体,下至海床洋底,举凡人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甚至人权、国籍、交通、通讯等生活无不与国际组织的协调息息相关,可以说,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框架。今天,没有国际组织就不可能有有序的社会生活,国际组织的出现,使国际社会朝准中央集权的方向演进。
当前,这些准中央权威机构主要有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普遍、最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除安理会拥有某种超国家性质的权力外,《宪章》第103条明确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同时,“由各国政府间协定所成立之各种专门机关,依其组织约章之规定,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有关部门负有广大国际责任者,应依第63条之规定使与联合国发生关系”(第57条)。取代关贸总协定的世贸组织,管辖范围空前扩大,拥有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有“经济联合国”的美誉。其他地区性组织如欧盟、东盟等,推进区域一体化的作用更加明显。
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本身是对国际法发展的组织促进,各种主要国际组织的约章是国际法的基本渊源,而其活动特别是其条约编纂和司法性裁判活动成为国际法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全球化、组织化的推动下,整个世界成为联系更加紧密的共同体。发展中大国例如“金砖四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改变了世界格局。(18)凡此种种,无疑给国际组织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国际组织的未来应是不断加强其公正性和实效性,推动自身朝更加独立的国际法主体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国际法民主趋势发展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与时俱进,通过国际组织加强国际法效力的使命所在。当前世贸组织采用的“反向协商一致”原则、2008年2月欧盟议会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即简化版欧盟宪法条约)规定的“双重多数”(19(原则以及学者提出的将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大国一致)改进为“2-3票(缀连)否决制”(20)(多数一致)等,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注释:
①Inis L.Claude,Jr.,Swords into Plowshares:The Problems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th ed.,New York:Random House,1971.
②See Henkin Louis,How Nations Behave:Law and Foreign Policy,2nd edition,1979,p.1.
③江国青:“联合国的改革与发展”,《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47-54页。
④有学者将国际秩序划分为客观秩序和主观秩序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国际格局,后者主要指国际规则。参见陈向阳:“联合国改革与21世纪国际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9期,第48-52页;潘忠歧:《世纪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⑤Onuma Yasuaki,"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nal Law,Vol.14,No.1,2003.pp,105-139.
⑥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⑦熊玠著,余逊达、张铁军译:《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44页。
⑧Philip Allot,"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aw",in Michael Byers(ed.) ,The Ro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69.
⑨古祖雪:“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5-147页。
⑩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128.
(11)Joseph 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all 1990,p.168.
(12)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5.
(13)贾烈英:“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以联合国为例”,《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第97页。
(14)Antonio Casses,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5.
(15)Antonio Casses,International Law,p.11-12.
(16)曾令良:“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110-119页。
(17)"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05/2006),pp.2966-2969,http://www.uia.org/statistics/ organizations/types-2004.pdf.
(18)参见崔立如:《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秩序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1-4页。
(19)“双重多数”原则即一项决议通过须获55%的欧盟成员国支持并且支持国人口达到欧盟总人口的65%,http://news.sina.com.cn/w/2007-06-26/052912090526s.shtml.
(20)梁西:“国际困境: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从日德印巴争当常任理事国说起”,《法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