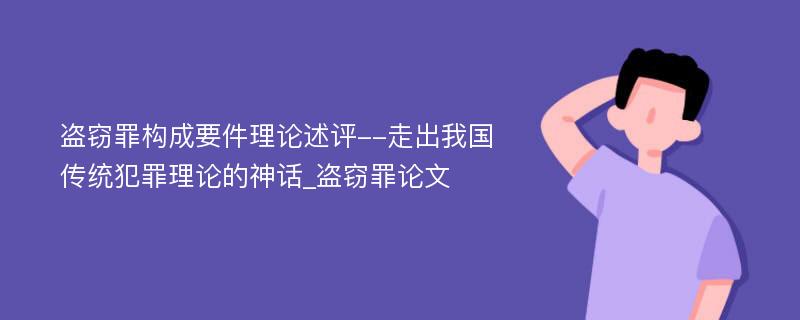
盗窃罪构成要件理论之检讨——走出我国传统犯罪论的迷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思论文,盗窃罪论文,传统论文,构成要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社会中,盗窃罪一直是发案率最高的犯罪,研究与盗窃罪相关的学理问题,不可谓不重要。然而,审视我国刑法学界,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应该存在的情况:传统理论满足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满足于传统的对于盗窃行为必须是“秘密窃取”的似是而非的定性,未有继续深入。笔者认为,对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如此重要的法学论题的理论(确切而言是客观构成要件①)探究既不应浅尝辄止,又不应束之高阁不敢问津。近年来,传统理论也开始面临来自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本文从对盗窃罪构成要件理论的缺陷的论述出发,拟对传统理论做出检讨,重新确立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并且进一步揭示传统理论出现偏差的原因,继而揭示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的缺陷所在。
一、盗窃罪构成要件理论之缺陷
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看来,盗窃罪俨然不是什么存在重大争议的罪名。但是,往往是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有时偏偏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更何况,在笔者看来,传统理论中对盗窃罪的定性的缺陷也并非“意想不到”,而是至为明显。
(一)我国传统理论对秘密窃取的判断标准
在我国传统理论中,盗窃罪的权威表述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②盗窃罪的客观构成必须有秘密窃取的行为,这被认为是盗窃罪的本质特征。所谓秘密窃取,在传统理论看来,并非指客观上窃取财物的行为不为人知,而是指“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不使他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是意图秘密窃取,即使客观上已经被他人发觉或者注视,也不影响盗窃性质的认定”③。另外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所谓秘密窃取是指犯罪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为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所知的方法将财物暗中取走”④,或者是“所谓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自认为不使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财物”⑤。以上表述由于过于简化,在解释具体案例时会引起歧义,因而有些学者将秘密窃取的含义细化,进一步阐述为:“首先,所谓的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而是仅仅针对窃取当时财物控制人而言,如果窃取行为人窃取财物时被财物控制人以外的第三人发觉,只要还没有被财物控制人发觉,则不影响秘密窃取财物行为的秘密性。其次,所谓的秘密只不过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行为人自以为财物控制人不知道或没发觉其窃取财物的行为,至于客观上财物控制人是否发觉行为人的窃取行为,对秘密窃取的成立并无影响。”⑥此外,还有学者归纳了传统理论对秘密窃取界定的“三性”,即:“1、特定性。秘密意味着使人不知,是在暗中背着他人进行的。作为盗窃罪的秘密,其内涵是特定的,即指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不在场,或虽然在场,但未注意、察觉或防备的情况下实施的盗窃行为。因此,盗窃罪的秘密是相对于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来说的一种隐藏性的行为;2、主观性。盗窃罪之秘密是指行为人自以为采取了一种背着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扒窃时以为别人没有发现,实际已在他人注视之下,仍然属于秘密窃取;3、相对性。秘密与公然的区别是相对的。秘密窃取之秘密,仅仅意味着行为人意图在财物所有人未察觉的情况下将财物据为己有,并不排除盗窃罪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⑦
上述说法基本上大同小异,归结起来无非是想表达以下几点:第一,盗窃罪必须具有秘密窃取行为作为客观构成要件的要素;第二,所谓秘密窃取,并非是指行为真的具有隐秘性,在客观上不为任何人所知,而是指行为人自以为采取了不为人发现特别是不为被害人所察觉的方法取得了财物,突出了秘密窃取的主观性。以上所表达的观点在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鲜有学者质疑。不过,近几年来,学界也开始出现了反对的声音。笔者同样也对现有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界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上,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二)对传统的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理论的批判
显然,从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采取了不为人知的方法窃取财物,而非客观表现方式上确实隐秘的话,逻辑上则必然意味着:哪怕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只要行为人以为自己窃取的行为不被旁人察觉,行为即构成盗窃。或者相反,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窃取行为是公开的,即使客观上没有被任何人发觉,就不能以盗窃论处,而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抢夺。这些传统观点仔细推敲起来,很难让人接受,现将批判意见归结如下:
1.传统观点有混淆主客观要件之嫌疑
传统观点定义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自认为采取了隐秘的方式窃财,“自认为”三个字使得秘密窃取行为成了行为人内心的一种设想和感知,以至于可以脱离客观实际情况而独立存在。那么所谓秘密窃取,就应当属于主观构成要件要素,而非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结果,秘密窃取成了类似于倾向犯中的内心倾向的事物,但这与传统观点认为秘密窃取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表述自相矛盾。⑧
2.所谓的“自认为”之表述违反了刑法学的基本原理
按照传统理论的逻辑,如果说秘密窃取的界定可以脱离客观实际,那么就应该承认客观上表现为公开的窃取行为一样构成盗窃罪。例如,在行为人的窃取行为已被被害人发现之时,假若行为人仍然以为自己是在秘密窃取的状态下,那么此行为就应以盗窃论处。但是,按照刑法学的理论,故意犯罪人必须对其客观行为有所认识,其中对故意内容的认识因素必须包括“对行为本身的认识,即对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内容及其性质的认识”⑨。“具体犯罪的故意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依赖于客观构成要件。大体可以认为,故意是对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的认识、容认。”⑩亦即,客观构成要件具有主观规制机能,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上述例子中,即使行为公开,也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公开的。换言之,即便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公然窃取,也必须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秘密的。这又是传统观点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之一。也就是说,虽然传统观点间接地承认了盗窃行为可以是公开的,而且公然窃取在司法实践中也大量存在着,但是又在理论上固执地认为盗窃罪必须是秘密窃取。那么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就只能提出秘密窃取只需要行为人“自认为采取了不为人知的方法”即可。殊不知,这一提法本身就违反了刑法学的基本原理,因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以秘密窃取为必要,对于上述情形,由于客观事实和主观认识发生了偏差,就应当适用刑法中认识错误(事实错误中抽象的认识错误)的原理加以解决。可惜的是,传统理论也没有将认识错误的原理应用到盗窃罪的认定中来。而且,有关于认识错误的理论纷争及学说观点十分复杂,也未必能很好的指导司法实践。(11)如果要澄清“秘密窃取”与“自认为”这种主客观之争中的迷思,倒不如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成形的客观归责理论,作较深入的了解,因为客观归责理论的初衷,是以客观归责为主轴,重新架构犯罪行为的阶层体系,亦即重新建立统一的归责理论,并且是以行为的客观面作为归责的基础和重心。
3.传统观点也不符合司法实践
如果坚持秘密窃取同时也是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那么,在对司法实践中一些公然窃取财物行为的定性将出现困难。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并不能得出盗窃罪的客观手段限于秘密窃取的结论。即‘秘密窃取’并非为立法精神中固有之意。外国学说与实务认为‘和平的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是盗窃罪的要点,明确的将具有公然性但缺乏夺取性的取财行为定性为盗窃罪”。而且“从司法实践看,存在既不符合抢夺罪的犯罪构成也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的具有公然性但缺乏夺取性的取财行为。若将盗窃罪的客观手段仅限于‘秘密窃取’,对于此类行为将导致‘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从而放纵犯罪”。例如,“甲(21岁)意图盗窃而进入民宅,入室后,发现仅有一老太太在家,虽见老太太已发现自己,还是当着老太太的面不慌不忙的将放在桌上的手机(价值3000元)拿起后出门。本例中,行为人并非秘密取财,也非公然夺取,而是公然拿取。即没有‘对物使用暴力’,不具有夺取性,不符合抢夺罪的犯罪构成,也没有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即不符合通说中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然而,从社会危害性看,这种公然拿取的行为比秘密窃取的性质更为恶劣,有更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显然将这种社会危害性更重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不符合立法精神。因而无论从法律还是情理上分析,盗窃罪的客观手段不应限于秘密窃取,对这种不符合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公然拿取的行为理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12)
当然,第三种观点是以抢夺罪须具备对物暴力为理论根基的。因为只有如此界定,才会导致盗窃和抢夺中出现了无法定性的“中间地带”。也有的学者认为:“从‘抢夺’的字面意义来理解,是‘用强力把别人的东西夺过来’。在刑事法意义上理解,通说认为,‘抢夺的方法,是公然夺取,即采用可以使被害人立即发觉的方式,公开夺取其持有的或管理下的财物。”结合上文关于盗窃罪的界定,作者认为两罪区分在一般情况下不成问题。但是,在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例如,行为人当着财物所有人或管理人的面,以和平的手段拿走财物,显然,此种情形既不属于通说的盗窃,因为即使相对于财物所有人或管理人也不是‘秘密,进行的,而是‘公然地’,也不属于通说的抢夺,因为未使用强力的方法,而是采用非暴力即和平的手段”,则现有理论出现了尴尬局面。(13)
以上的批判意见,有些是从传统观点自身的固有逻辑上的缺陷展开的,有些是从司法实践的需要展开分析。如果传统观点不能回答以上质疑,就有必要解构传统的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提出新的理论。笔者认为,没有必要限定盗窃行为必须是具有秘密性,更不能认为此处秘密性仅以存在于行为人内心为足够。除了上述反对理由之外,笔者还认为,为了正确处理认定共犯过程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同样应当否认盗窃罪的秘密窃取为其构成要件要素。试举一例,甲与乙共谋盗窃,商定由甲实施盗窃行为,乙负责在外望风。结果甲进入被害人住宅后实施了抢劫行为,而乙在外望风对此一无所知。依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甲乙两人构成共同犯罪,对甲自然以抢劫罪论处,对乙则以盗窃罪论处,两者在两罪的重合范围内即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14)理由是望风行为本身并不构成任何犯罪,乙只有和甲的行为形成共同犯罪,才能对其进行刑事评价。甲自然构成抢劫罪无疑,但乙没有抢劫的故意,不能以抢劫罪论处。然而又不能否认乙的望风行为是甲抢劫行为的帮助行为,对其又不能以无罪论处。乙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盗窃的帮助行为,应当以盗窃罪帮助犯论处;甲是盗窃罪的正犯,但同时更是抢劫罪的正犯,应当认定为抢劫。显然,如果要贯彻部分犯罪共同说,就必须承认盗窃罪可以是表现为公然获取财物的行为,因为抢劫罪当然是表现为公然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只有承认盗窃罪可以是表现为公然获取财物的行为,盗窃罪和抢劫罪方能在公然获取财物这一点上出现重合,两者才能以盗窃罪的共同犯罪来论处。否则,盗窃罪和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就没有重合的范围。那么,两罪就无法形成共同犯罪,必然出现对乙无法定罪或定罪不准确的情况。
二、传统盗窃罪理论缺陷的犯罪论原因
(一)我国传统犯罪论弊端的综合检讨
关于我国传统犯罪论的弊端及其完善抑或革新,从来都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本文中,笔者旨在重点探讨由盗窃罪构成要件解释引出的对我国传统犯罪论的迷思,并且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内容不涉及争论颇大的改革问题。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德日为代表)为参照,如果说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是一种递进式的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互相制约的话,那么我国传统理论中“犯罪构成”之四大要件形成的是一个闭合的耦合性体系,互为存在前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各要件间具有封闭式、自我完结式逻辑结构。(15)各要件本身不能独立存在,即只有在成立犯罪的情况下才能探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或犯罪主观方面的具体内容,呈现出一种依附关系。这四个方面的要件是谁也不会独立在先、谁也不会独立在后,任何一个方面的要件,如若离开其他三个方面的要件或其中之一,都难以推理;要件的齐合充分体现出要件的同时性和横向联系性。此种体系从逻辑构建而言,相对于大陆法系的层层递进,可谓平面型体系。(16)“平面的犯罪构成的特点是,犯罪构成由具有等价性的要件组成,各个要件处于平面关系,行为要么符合全部构成要件,因而成立犯罪;要么一个要件也不符合,根本不成立犯罪。因此,要件的排列顺序似乎也并不重要,从客观到主观者有之,从主观到客观者有之,主客观要素混杂者有之。”(17)这样的体系的危险性就是可能导致先定罪,后考察各个要件的具体符合性,入罪功能强大而出罪功能薄弱(当然,本文并非针对这一点)。关于四大要件本身之相互关系和是否独立(是否可独立考察),传统理论也认为:“各个犯罪构成要件只有处于结合为一整体的关系中,才能在各自的范围内揭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具体内容……任何一个犯罪构成要件,都不能孤立于其他要件之外而独立地反映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把各个犯罪构成要件分别孤立起来,那么每个要件都会丧失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意义和作用。”(18)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封闭的耦合性体系和递进式的体系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构建问题或逻辑的形式上之差异,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区别:由于四大要件相互间缺乏层次性、递进性,因而各个要件没有一种制约关系。千万不能小看这种制约关系,如果把犯罪论体系视为一个系统的话,则系统论本身的观点就是承认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制约。在大陆法系阶层论犯罪论体系中,包括客观要件规制主观要件在内的一系列制约关系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定罪准确而出罪途径又畅通的犯罪成立理论。而反观我国的传统犯罪论体系,理论构建的先天缺陷使得本应具有的各系统内部要素的制约关系流于形式,不能在实质意义上发挥作用。四大要件虽然统一于“犯罪构成”这一旗帜下,却有“各自为政”之嫌。行为构成犯罪,必然是符合四大要件的行为。然而若真如传统理论认为的四大要件单独不能孤立于其他要件反映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必须统一作为整体在行为构罪的前提下才能讨论其社会危害性的话,那么只能在成立犯罪的情形下认定各要件的实质含义。如此的话,由于各要件相互之间缺乏制约性,于是要件的排列顺序似乎就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在各类教科书上或者论文中学者所罗列的各种关于四大要件的排列顺序,充其量只能认为是一种定罪的思维顺序,而非四大要件本身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所以,这样的犯罪论体系实际上不能限制司法人员的擅断,不利于保护公民免遭刑狱之祸,不能限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相反,它极可能导致认定犯罪从主观到客观、混淆主客观要件的情形,因为既然是在构罪的前提下讨论个各要件,就没必要纠缠于各要件之间复杂的递进制约关系了。但是,犯罪成立并非如同“搭积木”一样简单,(19)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就像定罪结论的简单罗列,虽标榜主客观统一,但似乎也没能真正做到,相反,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偏重于主观构成要件,在解释分则罪名时经常出现主观归罪的结论。以上观点绝非笔者一家之言,在此试举几例。李立众博士指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属于平面型理论,这注定了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顺序性不强,没有层次性……四个要件之间不可能存在严格的递进式的环环相扣关系。”(20)周光权教授认为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对重大关系存在混淆,其中之一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并不清晰,(21)事实上这正是缺乏制约性的体现,比如在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时就暴露出了传统犯罪论体系容易导致主观归罪的局面。张明楷教授认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常见话语是:‘故意、过失支配行为人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危害行为是在故意、过失心理支配下实施的’。这种观念导致由故意、过失的内容决定行为性质,因而导致由主观到客观地认定犯罪(一概将不能犯认定为未遂犯便是如此)。如果认为这是一种缺陷,它与传统的平面体系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传统的平面体系,并没有将主观要件置于客观要件之前。但是,也难以完全否认这种缺陷与平面的体系存在某种关系。因为平面的体系使构成要件具有等价关系,没有防止人们先判断主观要件符合性。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是先考虑主观要件后考虑客观要件,甚至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大旗下,行主观归罪之实。”(22)谢望原教授认为:“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六大问题:1、‘四大要件’等量齐观、简单相加的构成论,既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也不符合系统论的观点……6、没有说明犯罪构成与犯罪诸要件的关系,也没有科学地阐明各要件的关系和层次结构。”(23)刑法理论对我国传统犯罪论的反思与批判从未间断过,这些批判意见,都指向了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的软肋。在我国传统的如同定罪结论的分解罗列的平面耦合式犯罪论体系中,很难认为各个要件之间具有强烈的制约关系,客观要件具有规制主观要件的机能,因为他们形成不了一个严密的系统。即使同样强调主观必须对客观事实有所认识,也难免只是就事论事,不能加以体系化一以贯之。甚至,有国外学者也批评道:“仅仅这样平面的区分犯罪要素,并不能正确地把握犯罪的实体。……有忽视客观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各自内在的差异之嫌,而且,这样仅仅平板地对待犯罪的要素,既难以判定犯罪的成立与否,又难以具体地论及所成立的犯罪的轻重。”(24)在我国逐步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高举保障人权旗帜的今天,这样的批评言论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二)传统犯罪论影响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反思
回到盗窃罪的问题,上面已经指出,我国传统理论中对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解释,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主客观要件及其关系。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的缺陷,刑法总论指导分论,总论特别是犯罪论体系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分论罪名解释的恰当性。正是由于这种平面耦合式的犯罪论体系中,四大要件没有严格的制约关系,犯罪成立缺乏体系性,导致在先定罪后考察各个要件的逻辑推理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客观要件对主观要件的规制。传统理论坚持主客观统一,但究竟何为主客观统一以及如何坚持,则令人不解。而在坚持主客观统一的语境下,结果往往是偏重主观方面,甚至出现主观归罪的情况也不罕见,典型表现就是在区分不能犯与未遂犯时传统理论采取了可抽象危险说,(25)不能犯几乎没有存在的余地。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姑且不论为何传统理论会认为盗窃罪的客观行为必须是秘密窃取(可能是机械地照搬盗窃一词之语义或是以生活事实取代刑法条文本身的真正含义),当然,在客观要件上从一般常态来说盗窃是包含有秘密窃取的行为的,主观上行为人也必须是认为自己在秘密窃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行为上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问题是传统理论又不能否认盗窃行为客观上确实是可以表现为公开取财的行为的,为了避免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缩小,无奈之下只能把秘密窃取加上“自认为”三个字来限制,而非真正地从盗窃抢夺两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表现上去寻找区别。恰恰是“自认为”三个字,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可以认为,在平面耦合式的犯罪论体系的指导下,传统理论在解释刑法分则罪名时,坚持主客观统一的结果是再一次倒向了或说是偏向了主观而忽视了客观。于是,这样考虑的后果就使得盗窃罪与抢夺罪在客观构成要件上没有任何区别,只能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认定行为的性质,从而出现了“以心论罪”的主观主义的结论,进而引起了一系列混乱,这样的结论是十分荒谬的。我们应知道任何盗窃行为必定要破坏对财物的占有关系的侵犯,是需要从一种占有关系的破坏到另一个占有关系的建立,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不侵犯占有关系的行为绝不可能构成盗窃罪。侵占脱离占有物只能是侵占遗忘物或者埋藏物。作为盗窃罪的对象,必须是秘密窃取他人实际占有的财物。如果我们承认盗窃罪可以表现为公然的方式来实际占有财物,不是拘泥于秘密窃取,那么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三)传统犯罪论下盗窃罪主客观要件混淆之真相
传统理论认为盗窃罪的“秘密窃取”最大的疏忽之处就是没有厘清犯罪论体系中主观与客观构成要件的关系,“自认为”三个字混淆了主客观要件,使两者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谬误。如上所说,刑法总论指导分论,总论的犯罪成立的理论制约着分论中对具体罪名构成要件的解释。分论罪名解释出现问题的根源,归根结底应当从总论中去找。纵观中外,无论是何种犯罪论体系,行为构成犯罪都要求具备主观的要件与客观的要件。此两者的关系,是总论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一般认为,两者关系是客观要件的内容规制主观要件的认识范围,即客观构成要件具有主观规制机能(针对故意犯罪和部分过失犯罪而言)。对此,国外理论认为:“(构成要件)还具有规制故意内容的机能。犯罪原则上必须出于故意,但是,由于故意的内容是对符合构成要件所必要的事实范围的认识和实现的意思,因此,在结局上,决定成立故意所必要的事实范围的还是构成要件。”(26)“故意的认识对象是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即构成要件的记述的要素和规范的要素的全体。”(27)我国传统理论同样认为,故意的认识对象是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即行为人必须对自己行为本身、行为结果、两者之因果联系等有所认识。(28)实质上这也体现了客观要件对主观要件的规制。所谓客观构成要件规制主观故意,是指有什么样的客观行为,理应具备什么样的主观内容。例如,杀人者应当认识到自己所杀害的对象是人,抢劫枪支弹药者应当认识到自己抢劫的是枪支弹药,这在我国和国外刑法理论中是一样的。当然,国外刑法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这可能与国外刑法典中没有给故意过失下定义,以至于学理上出现诸多故意过失学说,而所有的故意学说都要求行为人对客观构成要素有所认识有关。虽然国内外学界都重视这一认识,但是我国传统理论却不能将此贯彻到底,亦即,不管是初习刑法的人,或是已浸淫刑法学相当时日的研究者,往往因为这种种主客观理论纠葛,感到十分受折磨而认为: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在解释盗窃罪(包括许多其他罪名)的客观构成要件中,不过是一连串的“主观与客观的迷思”。
三、结语
学术不应当一味地标新立异,蔑视传统,但墨守成规、反对发展革新同样不可取。对于任何权威的观点,任何人都有权利加以质疑,即使他的理由可能尚显稚嫩、不够充分。前者不应对新的学说观点嗤之以鼻,更不能为维护一己之利而扼杀新生力量。真理越辩越明,反对出现反对的声音是虚弱和无能的代表。本文批判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两个经典命题,绝非标榜创新哗众取宠,仅仅是抒发在学习过程中对同一问题的看法的不同见解而已。还望同行悉心斧正。
注释:
①本文中的犯罪论体系采用张明楷教授的“二要件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98页以下。
②高铭喧、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7页。
③高铭喧、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8页。
④万应君:《盗窃罪基本问题研究》,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210.32.205.72/WFRS-MIRROR/cddbn/cddbn.Articles/Y699231.PDF,2009年4月25日。
⑤薛全忠:《盗窃罪研究》,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210.32.205.72/WFRS-MRROR/cddbn/cddbn.Articles/Y761379.PDF.2009年4月25日。
⑥孙玉璞:《盗窃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210.32.205.72/WFRS-MIRROR/cddbn/cddbn.Articles/Y1187579.PDF,2009年4月25日。
⑦陈兴良:《盗窃罪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5-26页。
⑧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法学家》2006年第2期。
⑨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⑩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11)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法学家》2006年第2期。
(12)包蓉:《对盗窃罪客观方面的几点思考》,《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3)刘树德:《试析抢夺、抢劫及盗窃之界分》,《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1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以下。
(15)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以下。
(16)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关键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17)张明楷:《犯罪构成理论的课题》,《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3期。
(18)李立众:《犯罪成立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0-31页。
(19)(21)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6页。
(20)李立众:《犯罪成立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0-31页。
(22)张明楷:《犯罪构成理论的课题》,《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3期。
(23)谢望原:《关于犯罪模式论的反思与构想》,《文史哲》1993年第5期。
(24)[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2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以下。
(26)[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27)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28)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