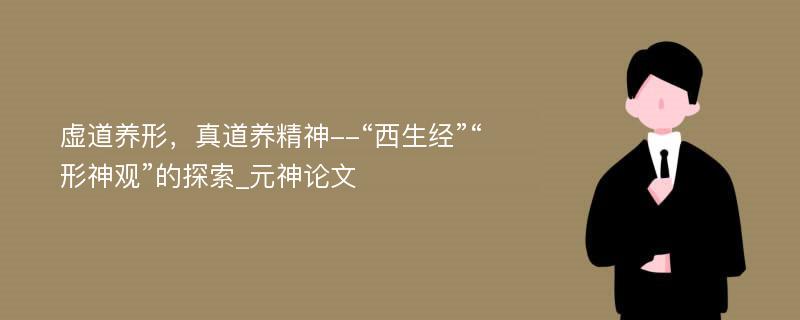
伪道养形,真道养神——《西升经》的形神观探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神论文,真道论文,伪道养形论文,西升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一般认为《西升经》产生于西晋,其主要依据就是葛洪《神仙传·老子传》提到《西升经》。另外,晋释道安《二教论》引《老子西升经》,又引《西升玄经》①,这都表明《西升经》在葛洪之前已问世。关于《西升经》的作者,李养正先生在其《道教概说》中大胆假设:楼观道派的开创者,三国时魏末扶风人梁谌“托言尹轨降授,造作经书,极可能是《西升经》的初作者”②。此说尚须小心的求证,在没有获得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只能算是一种假说。《西升经》形成的方式,我推测起来,大约以某种通灵的方法由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得到老子对于尹喜的“神启”,记载下来,后被集合成经,与《太平经》的成书颇相类似。因此《西升经》中自相矛盾处不少,显得观点不完全相同。关于《西升经》的作者,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推测,但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之前,不能说这一问题的解决已经铁案如山。关于《西升经》成书的时代、文化背景,按李养正先生《道教概说》的意见:“楼观道在传播道教方面的显著特点是阐扬老子之道及宣扬老子西升及化胡之说,同时也较深地卷入了佛道之争;另一特点是,其教义由宣扬炼形之术,转而向义理化发展,强调‘神生形’与‘形神合同,固能长久’。有代表性之楼观道经书,我以为是《西升经》和《化胡经》。”“继《西升经》之后行世的是《老子化胡经》。两经程度不同的皆用老子西升化胡之说作为贬低和排斥佛教的论据。”③如果此观点成立,那么《西升经》既是当时佛道论争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为当时的佛道论争服务的武器。由《西升经》开篇即言“老子西升,开道竺乾”④来考察,其西行教化的意图昭然若揭,我们似乎用不着怀疑《西升经》“老子西升化胡”的文化背景。但其是否为楼观道的代表性道经,还难以下断论。《西升经》是魏晋道教生命哲学中一股清新的小溪,代表了某种新的势头。此种新势头就是:尽力吮吸佛教生命哲学的营养,对道教传统的神仙不死的生命哲学给予改造,甚至于作了某些否定。
《西升经》已经吸收了一些佛教的观念,比如:“子若行吾道,当知上慧源,智亦不独生,皆须对因缘。”⑤此所谓“因缘”,即是佛教重要名相,与道教“自然”完全不同。若按道教,智慧乃自然而然发生,而在佛教,智慧是因缘聚会,依各种条件而起。“因缘”与“自然”为佛道论争的中心议题,后来道教也借“因缘”解释“自然”,如唐代《道教义枢》将“因缘”作为“自然”的底蕴,意在调和佛道二教,从理论上说明二者的不冲突⑥。而《西升经》这里讲智慧“皆须对因缘”,显系借用佛教理念来说明智慧的成因。又如:“子当无相启,勿以有相关。”⑦此所谓“无相”,也是佛教重要名相。佛教认定宇宙的真相是所谓“无相”,据《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宇宙间一切相皆为虚假相,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相?“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⑧这意思是说,宇宙实相即“无相”。《西升经》这里引佛教“无相”来说明,如果抱持“有相”去认识世界的真相,就会关闭大道的“众妙之门”,只有以“无相”去观察世界的真相,才能开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再如:“万物无有常,成者不久完。”“有常可使无,无常可使有。”⑨这里所说的“万物无常”,即佛教“三法印”之一的“诸行无常”,指世间生灭变化的万物都不是永恒的,不可常住。《杂阿含经》卷十:“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诸行无常。”⑩《大智度论》卷二十二:“佛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如观色念念无常,即知为空。”(11)观照无常即了知世界本空,这是佛教讲无常的旨意所在。《西升经》援引“无常”,旨在说明万物有生成就有毁坏,生成之物不可能永久完好,此乃自然之道。尽管《西升经》对佛家名相的运用尚属个别,且用以阐明自己的思想,但已经开启了引佛教辞语入道经的苗头,为晋代以降一部分道经的佛典化作了铺垫。
比较而言,《西升经》更加娴熟运用的还是《道德经》的思想,可以说其基本的格调与《道德经》大同小异(12)。除了“伪道养形,真道养神”、“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等命题属于《西升经》自己的东西,其他多与《道德经》雷同。譬如《意微章第三十一》:“老子曰,患生不意,祸生丝微。善生于恶,利生于害,大生于小,难生于易,高生于下,远生于近,外生于内,贵生于贱,动生于安,盛生于衰,阴生于阳。是故有无之相生,虚实之相成。是以有归有,无归无也。”(13)试比较《道德经》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再比较《道德经》所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14)又如《为道章第十八》:“橐籥之器,在其用者。虚实有无,方圆大小,长短广狭,听人所为,不与人争。善人在于天下,譬如橐籥乎?非与万物交争,其德常归焉。以其虚空,无欲故也。”(15)这“无欲”、“不争”的思想,显然取材于《道德经》所谓:“少私寡欲”;“常无欲”;“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而“橐籥”之喻,则取于《道德经》“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16)再如《深妙章第十四》云:“占往知来,不如朴质。”(17)“朴质”一说,尤为《道德经》所反复强调:“见素抱朴”;“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我无欲而民自朴”(18)。可见,《西升经》承接了《道德经》的重要范畴——“朴”。《西升经》对《道德经》的继承和发挥充满整篇经文,而对道教“形神俱妙”的形神观则散发出一股叛逆精神。
《西升经》中,道教肉体不死成仙的传统观念,已经被佛教式的否定形体所取代。《深妙章》宣称:“道有真伪”。刘仁会解:“乖宗者伪,会理者真。”(19)所谓乖宗的“宗”,所谓会理的“理”,在《西升经》看来就是“神”,符合这个道理的即是“真”,否则即“伪”。《邪正章第七》说:“道别于是,言有伪真。伪道养形,真道养神”。(20)照此说来,传统道教讲形体不朽、养护身体便成了“伪道”,道教的肉体可以不死说,就这样被否定了。对于真道养神和伪道养形,李荣揭示说:“动皆合理为之正,举必乖真谓之邪。邪是虚假故言伪,正是究竟故言真。真能入妙,所以养神;伪乃是粗,所以养形。养形者谓以滋味充身,养神者谓以清净修心。”刘仁会的解释:“有为有欲者养形,无为无欲者养神。养形者为灰为土,养神者能亡能存矣。”韦处玄认为:“形不可留,因欲养而留之,故曰伪也。无为养神,则寂然感通,故曰真也。”(21)真道是“正”,是“妙”,是“无为无欲”,所以“养神”,也就是“清净修心”;伪道是“邪”,是“粗”,是“有为有欲”,所以“养形”,亦即以“滋味充身”。形体的粗劣不足挂齿,精神的玄妙值得珍惜,爱憎之心,轻重之意,油然而生。
要厘清“伪道养形,真道养神”这一《西升经》最具创造性的命题,以便从更宽阔的视角考察其思想内涵,发掘其思想深度,这里很有必要提纲挈领地阐明道教的形神观,有必要首先对道教所谓“形”与“神”作一番透彻地分析研究,庶几可以把握《西升经》所谓“养形”、“养神”的涵义。
道教所谓“形神”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分别透视,先说“形”:
(1)形是由“气”这种质料构成的,人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气:“人皆禀天地之元气而生身。”人的身体由元气而来。“人在气中,气在人中。人不离气,气不离人。人藉气而生,因失气而死。死生之理,尽在气也。”(22)“气,身也”(23)。“夫人生成,分一气而为身”(24)。“道运而有气,气变而有形。”(25)“形之托者,气也。若气衰则形耗”(26)。形与气的关系是:“形者,气之舍;气者,形之主。借形养气,气壮而形固矣;运气炼形,形全而气自真矣。”(27)形为气之居舍,气为形之主宰。借助于形养护气,“气壮”之后,则使形体得到加固。“人受元气,以得成形。”(28)“所生之本,始于精气。精气结而为形,即知形为受气之本,气为有形之根。气不得形,则无因而立;形不得气,则无因而成。”(29)形气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人之一身,禀天道秀气而有生,托阴阳陶铸而成形。故一身之中,以精气为本。”(30)“世人初禀气受形之时,身中已有阴阳二气,二气在身,身外自然分出形影。”(31)人禀阴阳二气陶铸而成形,阴阳二气在身,所以人身外自然分出形影。阴阳一体,形影不离。
(2)形是空幻,形是假有:“修炼之士,视身如沤泡,终有生灭。”(32)“有身致大患,忘我复何忧。形骸最亲切,毕竟成土丘。……疑团自粉碎,休休复休休。莫为空幻具,还作真个囚。”(33)“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执着幻形。”(34)“如幻如泡是此身”。“此身皆属幻妄假合有为之法,皆是虚设耳。”(35)然而,不幸的是,“愚者直谓此身可以不朽,爱恋世缘,作为千年万年之计,不知浮世光阴,捻指易过,不可常恃为欢。而有形有质之躯,既从幻生,终归幻灭。”(36)“种种形相,俱为幻假,眷此幻身,与我为累。”(37)人的身体是假幻、是泡沫,是生命的累赘,切勿执着。
(3)神仙的身体与人不同,神仙无形,与道同体:“神仙无形之形者”。因此,“生道若合一,即神仙长存。夫言生道合一,即是身入无形,与道合同一体也。”(38)天真是纯阳之气构成,故无形:“天真无形,鬼物无影者,以其身是纯阳纯阴气故也。皆是无形之形也。夫纯阴纯阳,无形之形也,是以无影可分出也。夫天真是纯阳元气化凝元神而成,金华上仙即是无形之形。”“道成之后,分身解脱,便是无形妙法。”“天界神仙,无形之形。”(39)如果与神仙一样“养其无象,守其无体,故长久;执着之者,丧其本真,故早已。有形终有坏,无形故长在。……幻体有形终有坏,法身无相故长存。”(40)神仙的“法身无相”,与佛教所谓“无相即菩提”,有何分别?
(4)真人有形无体、无身、无影:“无则与道合同,有形而无体。故真人能存能亡,承虚而行,日中无影,皆是无身。身与无合,故无有体影也。”(41)真人与一般人有异,有身体而无影子,所以能存能亡。
(5)形体坏死后,可以经他入“济度”而“返形为阳”:“末学之士,未遂成道,则仙曹未有名籍,遇数则终,形识当坏,不免同入太阴,返视阳仙,诚隔霄壤。若同学之流,为之济度,方得返形为阳。”(42)也可借助“神缨”返形:“神缨者,紫微灵童也,主灭度之尸。若得神缨歌无量之章,则返形于三炼之房,受自然之气,乐无穷之遐龄也。”(43)人可经修炼将“有形”转化为长在的“无形”:“十月功足,形化为气,气化为神,神与道合而无形。”(44)人还可以把幻形变成真体,真体转化为幻形,变化莫测,获得自在:“内其神而神固,外其身而身存。然后易彼幻形成其真体,出此真体转彼幻形。是知大地山河无非我体,虫鱼鸾雀悉成我身,可以翱翔六合,放旷八表。”(45)经修炼至此,人形变化为仙形。
由上述可知,道教所谓“形”与西方哲学、宗教所说的肉体并不完全相等,比较后者而言,其内涵更为丰富,不仅指人之肉体,而且指神仙之形体。人的形体可经过刻苦修炼,成为神通广大、变化多端的“无形真体”,甚至人的尸体也可以通过种种法术“返形”而得无限之“遐龄”。于是在道教中,人体与神仙形体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二者是可以发生转化的。
再说“神”(46)。与人身体有关的“神”,其内涵非常复杂,归纳起来有:
(1)神是“性”,或者说“元性”,反之,性就是“神”。“神是性兮气是命”。(47)“神则性也,气则命也。”(48)“神乃人之性也。”“神乃性也。”(49)“神者,元性也。”“神者,性之别名也。”(50)“神中以性为极,性乃神之命也。”(51)“神者,性之真也。”(52)“元神为性,精气之主也。以其两在而不测,灵通而无方,故命之曰神。”“神即性也,性定则神自安,神安则精自住。”(53)“神者,形之真。神即性也,气即命也。”(54)“神即性,气即命。……炼气归神乃仙佛之真谛。”(55)“性者神也,命者气也。”(56)“神禀于道,静而合乎性;人禀于神,动而合乎情。故率性则神凝,为情则神扰。”(57)
(2)神是人心,人心就是神:“心,神也”(58)。心即是神,神即是心,故心外无神:“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始无愧神,可对神,仍可对心,抑非心之外遂无神也。”(59)因而欺心便是欺神,欺神便是欺心:“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60)心神无形无时:“心意者,神也。神无形,往来无时。”(61)心为神舍,神居住于心:“心者,神舍,常清一。一有染着,心乱神耗,则沦入鬼趣矣。”(62)“心者,神之舍也。”(63)神与心、形之间的关系是:“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宝也。故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将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养神,则自安于内;清虚栖心,则不诱于外。神恬心清,则形无累矣。”(64)神与心以及气之间的关系则比较复杂:“气主心,心邪则气邪,心正则气正。令人所举手动足、喜怒哀乐,莫不由心。心之动息,莫不是气。气感意,意从心。心和则气全,气全则身全。气灭则神灭,神灭则为委土矣。”(65)气主宰心,“心”的和谐反过来又保证“气”的齐全,气灭则形神皆灭。可见道教在传统上主流的观点是主张神灭论的(66)。
(3)神即是气,气即是神:“神之为气,气之为神。”(67)“神者,一身之元气也。”(68)“神者,性命之根,太虚之灵气也。”(69)“太阳天气故称神。”(70)“气者,神也”。(71)气与神结合而不分离,就是神仙:“气神相结,谓之神仙。《阴符经注》云:‘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子母相见,得做神仙。’”(72)神一旦离去,气也就烟消云散,生命于是不复存在:“神去气散,其可得生?”(73)神与气之间的关系:“气之与神,常相随而行;神之与气,常相宗为强。神去则气亡,气绝则身丧。”(74)“气中有神,神抱于气,因气抱于一神,炼神合道”。“魂魄精者,以应人之精气神。神乃精之主,精乃神之本,名则分三,不离一气。”(75)“夫身为神,气为窟宅。神气若存,身康力健;神气若散,身乃谢焉。若欲存身,先安神气。即气为神母,神为气子,神气若具,长生不死。”(76)
(4)神是精、阳精。“神者,精也。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灵神也。精去则骨枯,骨枯则死矣。是以为道务宝其精。”(77)修道务必宝其精,宝精亦即保神。因为“神者,阳之精,天之分。庄子曰:不离乎精,谓之神。”“气本生乎精,精藏乎肾,则知气者,精为之根也。”(78)神为阳精,神离不开精,而精又为气之根,可见神、气皆与精有关,在道教又分别称“精神”、“精气”。有的道书尤其重视精:“一者,精也。精乃元气之母,人之本也。在身为气,在骨为髓,在意为神,皆精之化也。”(79)精“化”在形体中表现为气,化在心意中表现为神。《修真十书》卷二十四《杂著捷径·保精神》认为:“精者,神之本;气者,神之主”(80)。也说明神与精、气都相关。精气神三合为一,实乃密不可分,分离则死。
(5)神就是魂。所谓“神者魂也,魄者阴也”(81)。“三魂安则众神安,三魂不安则众神不安。故《黄庭经》云:三魂,阳神也。”(82)“人之生也,魂魄主之。……魂即神也”(83)。神即是魂,魂即是神,神魂不能分离。故魂去不归,成了游魂,身神灭亡,人身无主,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如三度魂归不合魄即去,身神毙矣。魄者,阴也,常欲得魂不归。魂若不归,魄即与鬼通连。魂欲人生,魄欲人死。魂悲,魄笑曰:归无我舍,五鬼侵室。三魂绝而不归,即魄与五鬼为徒,令人游梦怪恶,谓之游魂,身无主矣。”(84)也有道经认为神的功能是制魂魄:“神所以制魂定魄”。(85)“神不出身,抱魂制魄,遂成无上神仙也。”(86)
(6)神为阳;然又有阳神、阴神之分。“神者,阳也。神之神者,阳中之阳,即玄之又玄之谓也。”(87)“形,阴也,犹地也;神,阳也,犹天也。”(88)形与神相对而言,形为阴,神为阳,但神本身又可分为阳神与阴神:“阳神之出,鬼神不可得而见,不可得而知。鬼神可知可见者,则与阴神同类,非阳神也。三年千日之功存养既成,气足神全,出入自由,身外之身即法身,聚则成形,散则成气,不可以形迹拟议。阴神即无形迹,不能分身化形。阳神可以一身至百十身,各各可以饮食,可以应酬,合之又复一,所谓圣而不可知之为神。隐显莫测,变化无穷,千里万里,须臾即到,过去未来之事,一一皆先知,方可谓之阳神。”(89)阳神不是鬼神一类,鬼神与阴神同类;阳神可分身化形,也可合而为一,变化莫测,可预先知道过去未来之事。
(7)神为无形至灵。“或问曰:神主于静,使心有所欲,何也?愚应之曰:神者,无形之至灵者也。”(90)“灵明知觉之谓神。”(91)“彼此不觉之谓神。”“神之为言灵也。”“一点元灵是至神。”(92)
(8)神有“元神”与“欲神”的分别:“夫神者,有元神焉,有欲神焉。”此所谓“元神者,乃先天以来一点灵光也。欲神者,气质之性也。元神者,先天之性也。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自为气质之性所蔽之后,如云掩月,气质之性虽定,先天之性则无有。”(93)区分神的层次,以便于明明白白地指引修道者从后天返回先天,揭开气质之性对人的遮蔽,回归先天之性。《道法心传》解释神为“先天元神”:“夫神者,乃先天之元神,为太极之祖也。虚无自然,包含万象,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变化无方,去来无碍,清净则存,浊躁则亡。”(94)先天元神与元神为先天之性,意思相同。
(9)神遍存于万物,人身体的各个器官皆有神,神皆有名字:“至道不烦诀存真,泥丸百节皆有神。发神苍华字太元,脑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垄字灵坚,耳神空闲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伦,齿神崿锋字罗千。”“心神丹元字守灵,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翳郁导烟主浊清,肾神玄冥字育婴,脾神常在字魂停,胆神龙曜字威明。六腑五臓神体精,皆在心内运天经。”(95)神不仅具有名字,甚至于还有形状服色:“人之目,左为司徒公,右为司空公。两目神六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一云:目神名虚监生,字道童,形长三寸六分,衣五色。眉间神三人,南极老人、元光、天灵君也。口旁神二人,厨宰、守神也。口中神一人,太一君也,字丹朱。舌神名始梁峙,字道歧,形长七寸,正赤色。鼻神名冲龙玉,字道微,形长二寸五分,青白黄色。鼻中神一人,名太乙,字通卢。两耳神四人,阴阳精也,名娇女。”(96)
(10)神性无生死:“和气神识者,随形而有生死,其神性实无生死。……气有聚散之异,神无生灭之别。”(97)这与“神之为气,气之为神”的说法有矛盾。
归纳上述所说,道教所谓“神”与西方哲学、宗教所说“灵魂”的单一性,具有很大的差别,充分体现了道教那种多神论的特征。神是形的保护者、主宰者,神即是人的心性,人修心炼性,其实就是存神炼神的功夫,故道教心性学是结合神来言说的。从“神是性、气是命”来看,神与气代表人的性命,道教所谓性命双修,实质上就是讲形神合炼,从而守住形神不相分离。神与人体生命活力的“气”密不可分,神即是气,气即是神,而形的构成也正是气,于是形神之间经由“气”完全融会贯通为一体,于是人的形体离开神、气就会即刻死亡。神是阳,阳神可分身,可先知,变化无穷,而道教又十分讲究炼成“纯阳之体”,则体内尽是阳神,因而不死。阳神即魂,称为阳魂阴魄,神“制魂定魄”,成就“无上神仙”。在道教那里,人身体的每一部位都有神在发挥作用,每个器官都有各自的保护神,这是把道教的万物有神论观念移植到人体内,以说明守住这些神灵的重要性。在此,形与神不是一对一的单一关系,不是西方那种肉体对灵魂的一重关系,而是把形体与神灵分解为多对多的多重关系,形神关系因此变得错综复杂。当然,如果我们从总体上去把握,道教论说的形神关系最终还是统一不可分而非多重可分割的关系。
“伪道养形,真道养神”这一《西升经》最具创造性的命题,对于传统道教来说,其要害就在于把“形”与“神”割裂开来,肯定“神”的价值而否定“形”在修炼神仙不死过程中的作用。
《西升经》对于肉体的否定是十分明显的,它劝人“不贪身形”,因为“形为灰土”,人拘泥于身形完好,便是“大患”所在。《邪正章第七》指出:“身为恼本,痛癢寒温。意为形思,愁毒忧烦。吾拘于身,知为大患。观古视今,谁存形完。”宋徽宗注解:“外则一身,未免阴阳之寇;内则志意,莫逃人道之患。则以有身为大患故也。盖有则有尽,无则无穷。神独存而常全,形有生而有灭。”(98)李荣的解释:“有身有患,非为困声色,苦于香味,痛癢寒温,皆为恼本也。”“身为寒热所恼,心为忧愁所毒。唯心与身,内外俱患,其致云何?必须外忘于身,内灰于心,身心尚忘,何患之有?此劝舍有为也。”“远观往古,近视当今,为变化之所流逐,阴阳之所代谢,谁得完存者?”(99)既然从古到今的经验已经证明人的肉体终将成为土灰,不可能永久保持“形完”,那么对于肉体的贬斥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无怪《生道章第六》嘲笑愚人“但知养身,不知戮形”(100)。《生置章第十七》坦诚地告诉人们:“念我未生时,无有身也,直以积气聚血,成我身耳。”“人未生时,岂有身乎?无身当何忧乎,当何欲哉!”(101)“无身”即没有了忧患烦恼,没有了痛苦恐惧,这是何等的干脆痛快。《圣辞章第十一》劝导说:“子不贪身形,不与有为怨。”(102)《戒示章第三十九》说:“绝身灭有,绵绵长存”。(103)正是由于《西升经》对身形抱这样一种“绝身灭有”的态度,所以它高唱:“空虚灭无,何用仙飞!”(104)这简直是把道教肉体飞升成仙的生命理想完全否决了,至此,我们差不多快要认不出《西升经》的道教面目了。
当然,它在一些地方也还保留了传统道教重视肉体的说法。《道虚章第二十》强调:“无为养身,形骸全也。天地充实,长保年也。”(105)《哀人章第二十一》老子教诲说:“人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爱神,爱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身,守身长久,长存也。”(106)《常安章第二十三》借助于“孝”敬母亲来比喻爱身,说是“天下尚孝,可谓养母。常能爱母,身乃长久。”(107)《观诸章第十二》说:“事兴则形动,动则外通谋。谋思危之首,危者将不久。不久将欲衰,衰者将不寿。以身观声名,物事难可聚。”这话的意思,据徐道邈解释:“物事滋兴,则动用身形,身形噪动,则心智外通,谋虑得失。”“不能静神内念,而役智外谋,谋虑既繁,神劳志失,此乃伤性之由缘,危殆之端首。危者不久,将致衰损也。形弊于外,神劳于内,内外俱伤,将恐不久。衰煞则神忘气散,亦将不能享寿存生也。”又解“物事者,财贷之事也。身为道器,名为身贼,故名成则身败,身安则道隆。以斯而观,名声财贷难可聚积也。”(108)就是说,为了防止修炼者身体衰老“不寿”,绝不可因为贪图名声财贷而危害身体安康。这些都是其保留道教传统的地方。
《西升经》在轻视身形的同时,却重视精神的作用,渴求获得精神的永恒,由此走向了对于精神主宰作用的高度肯定。《生置章第十七》强调说:“生我者神,……故外其身,存其神”(109)。人是由精神而得以生存的,只有精神才能与“道”相通,存亡自在,即所谓:“真神通道,能亡能存”(110)。《邪正章第七》所谓:“神能飞形,并能移山”,就是置精神于形体之上并无限夸大精神的功用。对此韦处玄解释得好:“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所不能哉?故能飞形而移山也。”(111)如此高扬精神的作用,当然就会要求修炼者“外其身,存其神”。因为存神才可以获得永恒,解脱生死。有生就有死,生即意味着死,要解脱生死,一劳永逸的办法是最好不生,不生自然不会有死,所以《圣人之辞章第十一》说:“以是生死有,不如无为安”(112)。与其有生死,还不如无生死为好,这与佛教所谓“无生无灭”,可谓无独有偶。而“无生”自然也就无所谓对身体关怀备至,更用不着去追求“养形”了。如何才能达成“无身”?《道虚章第二十》的答案:“若常能清静无为,无自复也。反于未生,而无身也。”(113)经常保持清静无为,回归于未生时的状态,自然而然不再有令人烦恼、使人陷于“大患”的身体。
多半是新,少半是旧,这就是《西升经》讲形神关系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不同于道教传统的新的生命哲学。这里所谓新,除了继承道家的一些思想,还有来自于佛教的影响;而所谓旧,则保存了道教传统。《道德经》曾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14)《西升经》抓住老子这一说法,吸收佛教生命哲学的某些内容,加以阐扬,从而形成其否定肉体不死的新型生命观。除此而外,《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说:“形非我有也,我所以得生者,从虚无自然中来,因缘寄胎,受化而生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我真父母不在此也。父母爱重,尊高无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附因缘,秉受育养之恩,故以礼报而称为父母焉。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寄之为屋宅,因之为营室,以舍我也。附之以为形,示之以有无。故得道者,无复有形也。及我无身,我有何患?所以有患者为我有身耳,有身则百患生,无身则入自然,立行合道,则身神一也。身神并一则为真身,归于始生父母而成道也,无复患也,终不死也。”(115)显然受到佛教因缘说影响,以肉身为假幻,以无形的“身神”为真身,破除肉体成仙说。可以说,以《西升经》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新的生命观,犹如道教生命哲学潮流中分流的一股清新的小溪,带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从注重“练形”走向“炼神”。这股注重“炼神”的清新小溪流淌到南北朝隋唐乃至于宋元以降,便逐步发展成为道教生命哲学中的一大流派。
早期道教在世人心目中,是以“练形”著称的。如刘宋时颜延之《庭诰》比较道佛二教说:“为道者,盖流出于仙法,故以练形为上;崇佛者,本在于神教,故以治心为先。练形之家,必就深旷,反飞灵,糇丹石,粒芝精,所以还年却老,延华驻彩,欲使体合纁霞,轨遍天海,此其所长。”(116)由此可见,一直到南北朝初期,道教明显区别于佛教的特征,在社会上一般人眼中就是“练形为上”。《西山群仙会真记》卷二《养形》论养形之道:“万象群生,不能无形。惟人也,集灵以生,资道以成,不知养形之端,精魄耗散,而阴壳空存。未死之前,已如槁木,余喘既绝,尽为粪壤。养形之道,可不深思!”(117)不知养形之道,也就不能最终得神仙之“道”。《三洞群仙录序》对此表述得更为明白:“炼形致仙,虽贤者不能笃信。故神仙显迹,昭示世人,使炼气存真,保命养神,以祈度世,脱嚣尘,超凡秽,而游乎八极之外。……仙者,养形以存生也。”(118)《谷神篇序》也称:“修道者即是修身也,炼丹者即是炼形也。”(119)《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八《仙化成人品第十九》说:“炼形成真者,神仙事也。……神全数足,白日登晨,是谓炼形不死之道。”(120)《大丹直指》卷上:“若用炼形,而曰地仙,形神俱妙。”(121)炼形而为形神俱妙的地仙。《真一金丹诀》:“真一金丹炼形之道,付吕青牛受之,因从终南修炼功成,神形俱妙。”(122)《吕祖全书》卷三十《修真传道集·论炼形》:“必欲长生不死,以炼形住世而劫劫长存;必欲超凡入圣,以炼形化气而身外有身。”(123)都讲形神俱妙,即形神统一不分,由此走向长生不死。但道教传统炼形而使肉体不朽以至神仙长生的宣说,遭到儒家和佛教的尖锐批评。《牟子理惑论》牟子自称:“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并讥讽嘲笑道:“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124)。《三国志·虞翻传》记载:“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125)曹植《辩道论》认为神仙之书完全“虚妄”,仙人之说是“虚妄之词”、“眩惑之说”(126)。《抱朴子内篇》记载了儒者否认神仙不死的观点,如《论仙》载:“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127)。韩愈《谁氏子》:“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128)唐人李邕上疏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129)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借“无仙子”之口云:“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130)种种批评可谓铺天盖地而来。
针对儒家和佛教的批评,道教逐步将其关注的重点指向“炼神”。《太上混元真录》告诉世人:“伪道养形,真道养神。神真通道,能亡能存。神能飞形,并复移山,形为灰土,其可识焉。……观古视今,谁存形完?”(131)《丹经极论》也强调说:“真道养神。……生我者道,活我者神,将神守之,以道养神是也。”(132)照这些说法,传统道教讲“养形”便成了“伪道”,“真道”在于“养神”,由此也否定了道教传统的肉体不死说。唐代道教学者王玄览《玄珠录》卷下说:“谷神不死。谷神上下二养:存存者坐忘养,存者随形养。形养将形仙,坐忘养舍形入真”(133)。这是把修道分为上下两个等级:“形养”是炼形,只能够获得较低品位的所谓“形仙”,所以属于修道方法的下乘;“坐忘”则是炼神,最终“舍形”入于高品位的真常之道,故属于修道方法的上乘。《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二十说:“今之炼度,不炼其形,乃炼其神。身中之神,一经冶炼,自然身有光明,金楼玉室,无不生神。既生神则尸亡魄落,阳神整具,自然无灾害、无魔怪,可以登超凌之域也。若不炼其神,则魂衰魄盛,尸尘汨乱,易生疾病,去死无日,永为下鬼。”(134)炼神而生神,生神则可“登超凌之域”,也就是超越生死。炼神就是要把神留住于身:“人能留神于身,不视不听,不言不食,内知而抱玄,岁月坚久,其神久留,久留方凝成神仙。”(135)神对于人之生命的重要性就在于:“夫神在则为人,神去则为尸。岂不痛哉!”(136)“大君曰:如此之流,皆入仙格。服饵灵草,容壮难老。药则为里,术则为表。百神易集,形可长保。”(137)神一旦离开形,人必死无疑,而神不离散,则形可长保。炼神为修道者的必备功课,不言而喻。
大体说来,汉魏南北朝道教注重炼形,隋唐以后关注点在炼神。不论炼形还是炼神,道教在根本上其实还是要修炼形神的永恒统一,这样才能成仙不死(138)。《修丹妙用至理论》指明:“夫修生者,本以为身。身济则神存,神存则成真。”(139)神的存在离不开身体,而身体无神则不能成真。《大道论·保生章》告诫:“神不离形,形不离神。神形相守,长生仙行成矣,保生之道遂矣。”(140)神形相守也就是形神的永恒统一。《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通义》卷二要求修道者形神双修:“能修经教,涤炼形神,则生身受度,劫劫不失人身而真性长存矣!(141)《太上长文大洞灵宝幽玄上品妙经·人神感应章》宣称:“欲要人命长,须令养形宅,固精血,炼神气,安魂魄,必可长生。”(142)这也是要求形神双炼。《太上洞玄济众经》从所谓“始生父母”的角度讲形神并一:“形非我有,所以得生者,从虚无自然中来。因缘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贵重,尊高无上,今所生父母,我寄备因缘,禀受养育之恩,故以礼报而称为父母焉。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寄之为屋宅,因之为营构,以舍我也。附之以为形,示之以有无,故得道者,无复有形也,及无身神也。一身神并一,则为真身,归于始生父母而成道也。”(143)所谓回归“始生父母”而成道,实指“身神并一”的“真身”返回到“虚无自然”中去,因为人就是从那里来的,能以“真身”回去,即是得道。
道教有许多经书反复讲形神俱妙:“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与道合真。”(144)“慎内,内不出外,外包内也,抱神也。闭外,外不入内,内包外也,守形也。长生,形神俱妙也,合外内之道也。”“炼成纯阳,生意竞足,形神俱妙,天地阴阳在我矣,有何不壮而长久乎。”“守一,形神不离也,犹抱一守中也。处和,形神俱妙也,犹和光致和也。”(145)“形神俱妙,超凡入圣。”(146)形神俱妙意味着超凡入圣,解脱死亡。所谓:“无量大神,皆由我身是也。修真之士,金液炼形,而后形神俱妙,周回十方,皆可度世、度厄,回骸起死矣。”(147)形神俱妙意味着永劫不坏:“人得道之深者,骨肉都融,形神共妙,可分之为亿万,不为足可合之为一。不为有余,永劫不坏,形可延也,冥冥莫测,形可隐也。”(148)既然形神俱妙是要维持形神的长久不离,使形可延,“永劫不坏”,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云笈七籤》卷五六《元气论》的解答是:“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要常养神,勿失生道。长使道与生相保,神与生相守,则形神俱久矣。”(149)不失道,不去生,总之就是不失生道,使生与道和神恒相厮守,就能“形神俱久”。
所谓“形神俱妙”,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形神统一,永不分离,与不死之道合为一体,从而超越生死。后来全真道与内丹学兴起,也没有放弃传统的“形神俱妙”说,尽管他们持神不灭论,主张精神飞升,但其中内涵已发生变化:“玄珠既显,采归炉内,有无混融,二气感通,如影之随形,如谷之应声,自然心凝形释,骨肉都融,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玄珠成象,太乙含真,金液炼形,骨散寒琼,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皆自然也。”“上士行之不怠,直超圣域,顿悟圆通,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逍遥极乐,永劫不坏,即大觉金仙之位也。”(150)“故论性而不沦于空,命在其中矣;守母而复归于朴,性在其中矣。是谓了命关于性地,是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151)“若是学天仙之人,须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可也。”(152)“炼到形神俱妙处,遂知父母未生初。”(153)这样的“形神俱妙”,是一种“心凝形释,骨肉都融”、“金液炼形,骨散寒琼”、“与太虚同体”的“形神俱妙”,是形灭而神不灭的“形神俱妙”,这与道教传统的主流观点——形灭神灭、形神合一不灭——已经全然不同,但毕竟从形式上尚没有把形神割裂开来。而《西升经》“伪道养形,真道养神”重估道教传统的要害之处,恰恰就在于割裂形神,连形式上的“形神俱妙”都不讲,对“养形”与“养神”分别作出高低不同的价值判断,将“养形”判决为“伪道”,把“养神”赞颂为“真道”,抽去了传统道教肉身成仙信仰的奠基石。从破坏道教一贯主张的形神统一观入手,《西升经》提出了自己对于生命问题的新思维,那就是精神不死。
值得注意的是,《西升经》也有对形神相生相成不可分的阐述。《云笈七籤》卷六十引《西升经》称:“身者,神之舍、神之主也。主人安静,神即居之;主人躁动,神即去之。神去气散,其可得生?是以人耳目手足皆不能自运,必假神以御之。学道养生之人,常拘其神以为身主,主既不去,宅岂崩坏也。”(154)身体作为“神”的房子,只要房子的主人“神”没有离去,这房子就不会“崩坏”。《我命章第二十六》声明说:“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李荣注解点明:“不视故不为色所盲,不听故不为声所聋,不知故不为智所困,绝声色而清净,去分别而无为。神不离人,故云不出于身。身将神合,命与道同,故云长久。”(155)经过刻苦修炼,做到不视、不听、不知,清静无为,即可神不离开人身,身神合一,命与道一样长久。徐道邈注解《生置章第十七》“我身乃神之车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主人安静,神即居之;躁动,神即去之”时揭示:“夫马之运车,如神之载形也。神处人身,若人居室舍。舍全则人安,身康则神乐。故智士保身以养神,运形而升仙也。”“身形静,神即止其宫府也;躁动有为,神即去其居馆。”李荣对此的解释是:“身能载神,神能乘人,故曰车也。身能容神,神以身为屋,故云舍也。自外来寄于身,故云主人也。”又指出“车牢始能载物,舍静方可安人。为主既也喧哗,作客何能久住?必须坚守于身,而神自乘之;净洗于心,神自正之;内外安静,神自居之。若身有染秽,心腹躁动,神即离人,故云去之。”(156)《神生章第二十二》“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这话的意思,诸家皆以形神的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作注解。冲玄子解释说:“神为生形之用,无用则形不生;形为养神之利,无利则神不成也。”“形假神以得生,神含形以得成。形神不合,无由生成也。”形与神的关系是“利用相须,更相生成。”刘仁会注解称:“形非神不生,神非形不成也。”“随其神化以生形类,故曰形不能自生;随其形类以成神功,故曰神不能自成。”说明为什么形不能自生,神不能自成的道理。“形神虽异,相藉生成,生成之道,不合不得,故曰形神合同。”形神二者为何更相生?这是因为“神由形用,形为神生,形用既彰,神功所致,则神生形也;形由神生,神由形用,神功既著,著乃由形,则形生神也。故曰更相生。”为何更相成?这是因为“形不自兴,必资神化,神动形作,功用乃成,成由神生,则神成形也;神不独化,动必资形,形作神随,神功乃见,见由神用,则形成神也。故曰更相成。”(157)从这些注解看,《西升经》所言说的仍是道教传统的形神观。诸家皆认为《西升经·神生章》阐述了形神虽异,但形非神不生,神非形不成,形神不结合在一起,则无由生成的道理。既然如此,这显然与《西升经》提出的“伪道养形,真道养神”把形神分割开来的命题自相矛盾,因为按照《西升经》“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的结论,则修炼中不可能将形神分割为“养形”与“养神”来操作,分开则无生命的生成,也就无所谓形神的“更相生,更相成”了。《西升经》形神观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或许与其成书出自不同的通灵者、前后得到的“神启”不一有关。此外,《西升经》没有对“神”的永恒不灭作出明确论证。我们知道,柏拉图在其《裴洞篇》论说灵魂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灵魂得到解放,就花了大量篇幅、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证明“灵魂是不灭的”,“一个人死时他的灵魂并不跟他一同消灭”。(158)这就为其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单独存在提供了自圆其说的依据,不论此依据是否正确。而《西升经》“伪道养形,真道养神”的命题恰恰找不到说明“神”可以脱离“形”而独立存在的依据,没有充分论证为何“养神”才是“真道”,于是便容易留给人空喊口号的印象,而这也正是自古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悲哀!
形神俱妙、形神可固,这是道教“神仙长生不死”信仰最重要的哲理依据之一。道教深深知道,如果抽去这条依据,那就无异于是釜底抽薪,使其神仙不死说不攻自破。因此,道教中许多学者都十分强调形神的统一,宣传形神永固从而超越生死的思想,并时时申述这一论断。人何以能够成为人?《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起经》的答案:“黄神来入骨肉形中,成为人也。”(159)那么,人的身体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太乙元真保命长生经》的答案是:“积阳为神,积阴为形,阴阳两半,合成其身。”(160)形神两半相合,于是有人的身体形成。道教所谓死亡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云笈七籤》卷六十《胎息经》答复:“气入身来为之生,神去离形为之死。”(161)《三洞群仙录序》说:“自壮而老,自老而衰,自衰而死,骨肉复土,形神离矣。”(162)《真龙虎九仙经》罗真人注云:“众神不安,人则患生,神散曰死。”(163)《墉城集仙录》卷一《圣母元君》指明:“神在则为人,神去则为尸。”“人之生也,皆由于神,神镇则生,神断则死。”(164)《西升经集注》卷四所载刘仁会的观点:“神住曰生,神去曰死。”(165)由此可见,死亡就是神与形互相分离的结果。在道教那里,形与神是人的生命最基本的两大构成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的死亡,是神与形分散开来的结果,反过来讲,人若要不死,就必须永久保持形神的统一。如《大道论·保生章》所说:“神不离形,形不离神。神形相守,长生仙行成矣。”(166)形与神统一于道。如《太上老君内观经》说:“道贵长存,保神固根,精气不散,纯白不分,形神合道,飞升昆仑。先天以生,后天以存,出入无间,不由其门。”(167)形神若能与长存之“道”合为一体,形与神的统一才有保障。在高举“道”的旗帜下,永久地保持形与神的统一,这是道教论证人能不死成仙的一个主要依据,它与神仙不死的信仰能否在道教的神学理论中得以成立有关,与人能否超越生死有关。换句话说,在道教的主流意识看来,人能够超越生死的基础就是“形神俱妙”,人超越生死就奠定在形神永恒统一的这个基础上。《西升经》所谓“伪道养形,真道养神”这一最具独创性的命题,尽管有空喊口号的嫌疑,但却在口号声中把“形”与“神”割裂开来,这就等于对道教主流论证人经修炼能不死成仙的主要依据之一“形神俱妙”进行釜底抽薪,否决了传统道教所主张的“炼形”,从而走向“炼神”。《西升经》的形神观尚未全盘抛弃道教的传统言说,其中还有一些论述上的自相矛盾,譬如既割裂形神,又肯定形神相辅相成,既否定形体,又在某些地方保留了身体在修炼中的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它打开了道教生命哲学发展趋势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