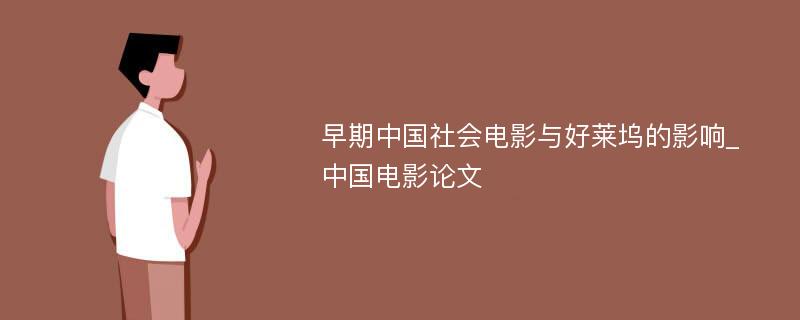
中国早期社会片与好莱坞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莱坞论文,中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5)07—0193—07 社会片是运用影像手段真实地反映现代社会人生,注重“对社会上不良的制度下攻击,予人以研究问题之暗示”[1](P.26)的电影作品。 国产社会片摄制较早的是1916年张石川的《黑籍冤魂》,而真正形成创作热潮则是在1924至1927年间。其中受好莱坞影响比较明显的创作者,主要有“长城”、“民新”等公司,以及“明星”公司的洪深等。1922年,洪深为中国影片制造公司拟文征求电影剧本,就强调“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能表示国风,媾通国际感情”,故须摈弃“诲淫”、“诲盗”、“演人类劣性”、“不近人情”、“专演神怪”等题材内容,而要真实表现当前的社会人生。[2]“长城”公司梅雪俦、李泽源等留美回国青年,认为“中国有无数大问题是待解决的,非采用问题剧制成影片,不足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①,他们不满于当时中国电影的远离现实,立志拍出反映社会、唤醒民众的作品来,于是确立以拍摄“移风易俗,针砭社会”的“问题剧”为主的制片方针,并聘请侯曜担任编导。侯曜“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与“长城”公司一拍即合,他的影片揭示婚姻、恋爱、家庭、女权、非战等社会问题,从不同角度对现实提出尖锐批判。1926年由香港迁往上海的“民新”公司,尽管后来拍片良莠不齐,然开始阶段,张扬“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②,以欧阳予倩为主体创作的电影,体现出与“长城”公司大致相同的倾向。 中国早期社会片创作,可以说是好莱坞社会片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剧共同影响的产物。中国早期社会片的主要创作者侯曜、欧阳予倩、洪深等,他们同时都是话剧作家,如侯曜所说:“我是一个崇拜易卜生的人,所以我所编的剧本也都包含社会问题”③,都受到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欧洲近代社会问题剧的深刻影响。当然从电影摄制来说,美国社会片在题材主题、形式结构、镜头影像等方面给予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明显。 美国社会片在中国译介放映是1916年前后,但那时不能与滑稽片、侦探片相比;比较多地译介放映美国社会片是从1922年前后开始。据查《申报》,1922年,有《乱世孤雏》《小伯爵》《纽约之可儿》等;1923年,有《牢狱三结义》《无名英雄》《成衣艳史》《孤儿幸遇记》《人间地狱》《人类难舟》《陋巷》《妇女参政会》《纽约一夕谈》等;1924年,有《洗衣女》《儿女英雄》《孤儿苦遇》《爹爹》《富人之法律》《殖边英雄》《鸦片地狱》《渔家女》《法律何在》等;1925年,有《雪下孤雏》《马戏日》《热血巾》《鞭影泪声》《茶花女》《以色列之月》《我王万岁》等;1926年,有《铁血男儿》《义勇儿女》《孤儿后福记》《贼》《情血》《边外奇缘》等;1927年,有《党人魂》《战地之花》《纽约第五街》等。1920年代末,因为国片摄制倒向古装片和武侠神怪片,美国社会片的译介放映日益衰减。 上述影片译介放映对中国电影人和观众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格里菲斯导演的《乱世孤雏》,讲述姐姐为了给失明的妹妹治疗眼睛而进城求医,受到社会黑暗的种种压迫与侮辱的故事。该片在中国激起深切同情,认为“在此平等主义高唱入云之际,自宜借影片之力,使社会一般人民引起平等之观念”,“对于我目前困苦颠连、醉生梦死之中国人民,尤有重大之教训也”[3]。其他好莱坞社会片也是这样,如《鸦片地狱》描写美国鸦片祸害之实情,此片有“警世之意,作晨钟之撞,发人迷梦”,“吾国亦正在禁烟时也,吾甚愿是片之能普映全国,使数十万沉湎黑籍者,得有所鉴,而猛醒自戒也”[4];借俄国红白两党之斗争描写被压迫者反抗的《党人魂》,“形容帝族之奢华骄傲,及平民之怨声沸焉,无微不至,实可为帝国主义者之当头棒喝……可为我东方病夫之健身剂”[5];《杀人之罪》描写上层社会奢侈淫靡的生活,“可以给我们一些深刻的教诲”,“现在我们岂不像罗马最荒淫时代吗,富者们只肯把他们的金钱,费掷于酒乐,对于苦创万状的贫者,怎肯有些微的体恤”[6]等等。正如描写贫苦洗衣女被虐待遭遇的《洗衣女》,国人认为其“适合世界潮流,鼓吹优待劳工问题”,国片“颇可模仿”之,[7]舆论界强调中国需要这样反映现实的社会片。 正是在上述美国电影的冲击影响下,中国影坛1924至1927年间,也出现了一个社会片创作热潮。“长城”公司推出《弃妇》(侯曜编导,1924年)、《爱神的玩偶》(濮舜卿编剧/侯曜、梅雪俦导演,1925年)、《春闺梦里人》(侯曜编剧/梅雪俦、李泽源导演,1925年)、《乡姑娘》(杨小仲编导,1926年)、《一串珍珠》(侯曜编导,1926年)、《伪君子》(侯曜编导,1926年)、《儿子英雄》(陈趾青编剧/杨小仲导演,1928年);“民新”公司有《玉洁冰清》(欧阳予倩编导,1926年)、《和平之神》(侯曜编导,1926年)、《天涯歌女》(欧阳予倩编导,1927年)、《复活的玫瑰》(侯曜编剧/黎民伟、侯曜导演,1927年)、《海角诗人》(侯曜编导,1927年);“明星”公司有《冯大少爷》(洪深编导,1925年)、《卫女士的职业》(洪深编剧/张石川、洪深导演,1927年);“大中华百合”公司有《采茶女》(徐琥编导,1924年)、《小厂主》(王元龙编剧/陆洁导演,1925年)、《透明的上海》(陆洁编导,1926年)、《殖边外史》(王元龙编导,1927年)。此外,还有“上海”公司的《弃儿》(但杜宇,1924年)、“友联”公司的《倡门之子》(陈铿然,1926年),“天一”公司的《新茶花》(裘芑香、汪福庆,1927年)、“耐梅”公司的《奇女子》(杨耐梅、史东山,1928年)等。 一、揭示社会问题以批判现实黑暗 好莱坞社会片对中国早期社会片的冲击和影响,就现实描写和社会批判来说,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描写现实黑暗以抉发社会之罪恶。 《牢狱三结义》写贫家子与社会势力抗争而受不白之冤入狱,《洗衣女》反映劳工遭受上层社会的欺辱,以及《陋巷》揭示芸芸众生的贫困潦倒等,这些美国电影所描写的底层社会艰难生存的情形,在《可怜的闺女》《倡门之子》《伪君子》等中国社会片中都有明显的影子。《可怜的闺女》讲述汪小莲伙同杨七姑诱骗沈慧英,描写拆白党之种种罪恶,观之使人既惊心动魄,叹拆白党之阴险狠毒,又悲伤感慨,怜闺女之被诱失足。《倡门之子》搬演一个妓女的小男孩被冒充为富家之子带人豪门之后发生的故事,描写社会现状和家庭罪恶,抨击了世态炎凉、人情冷薄和学校之黑暗。《伪君子》更是从底层的感受出发,痛斥现实社会简直就是伪君子社会,像监狱、疯人院、坟墓一般龌龊肮脏。 还有批判都市繁华掩盖下的丑陋和罪恶,在《纽约一夕谈》《纽约夜生活》《纽约第五街》等好莱坞社会片与《透明的上海》《上海一舞女》《冯大少爷》等国产社会片之间,都可以看到其影响关系。如《透明的上海》,此片将暗无天日之上海写得透明透亮,与上述揭示纽约奢侈淫秽的生活与罪恶的影片相似,它描写了社会上层的奢靡生活与下层社会的贫穷痛苦,凸显了这种对比所体现出来的掩盖在都市繁华下金钱权势的为非作歹,以及底层人民遭受的欺辱与压迫。洪深的《冯大少爷》也是揭发都市繁华掩盖下的丑恶,写富商冯家耀在灯红酒绿中走向堕落,又被荡妇老五与金六保谋骗财产,几乎家破人亡,不啻是对富豪之家的当头棒喝。《上海一舞女》同样是描写表面风光美艳的舞女在都市社会中的辛酸生活。 第二,在男女婚姻恋爱描写中去揭示社会问题。 社会片也描写婚姻恋爱。《茶花女》《渔家女》《妇女参政会》等好莱坞电影都是在男女婚恋描写中去揭示社会问题,批判现实黑暗。受其影响,《复活的玫瑰》《爱神的玩偶》《天涯歌女》《新茶花》《弃妇》等中国社会片亦是这样。此类影片大都是反映妇女在婚姻恋爱中的悲苦遭遇,表现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被欺辱被损害的人生。这类题材在中国早期社会片中拍摄最多,因为在1920年代中国历史的剧烈转型中,这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电影家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予以表现。 《复活的玫瑰》《爱神的玩偶》《摘星之女》《玉洁冰清》等片,着重描写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幸遭遇。《复活的玫瑰》抨击“指腹为婚”的封建陋习,以及这种封建陋习对自由恋爱的摧残,写尽旧礼教之罪恶。《爱神的玩偶》描写青年女子明国英与罗人俊的恋爱遭到家庭及社会的压制,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强不爱以为爱,有爱而不得,不欲人爱而人偏要爱”[8]的社会问题。欧阳予倩的《玉洁冰清》其表现视角稍有不同,富翁钱维德放高利贷盘剥穷人,其女孟琪倾心帐房先生黄发渊之子伯坚,而伯坚却因鄙视其父为追求金钱权势而做的联姻决定,遂拒绝钱维德的婚约,后伯坚与素仙相爱,但由于家世悬殊不被父母允许而被迫分开,痛苦万分,最后两人在孟琪帮助下破镜重圆。影片透过婚恋描写揭示出普遍的社会问题,表达了“憎恨唯利是图的市侩,而对劳动人民表示着同情”[9](P.360)的思想。 《弃妇》《卫女士的职业》《天涯歌女》《新茶花》《采茶女》《奇女子》等片,则将妇女走上社会而受欺辱的心酸展现出来。《弃妇》有好莱坞社会片《妇女参政会》的痕迹,写一妇女在夫家无故被休,走上社会横遭嫉妒,后从事女子参政又遭诬陷,远逃空谷还遭到偷窃,最终在尼姑庵中贫病死去。“该剧描写妇女受家庭社会种种之苦痛,大声疾呼,以欲唤醒女同胞,急谋解放为目的”④。《天涯歌女》通过歌女凌霄与陆余沉的爱情悲剧,表现社会对弱者的欺压。片中歌女极尽凄凉呜咽之惨,使养父母之心之罪暴露人间,利诱威迫之劣绅恶迹揭示无遗,是“替一些被压迫者说一句公道话”[9](P.365)。《新茶花》《采茶女》《乡姑娘》都有《茶花女》的明显影响,以男女恋爱遭遇批判社会黑暗势力为所欲为的丑恶。《卫女士的职业》《奇女子》等片,也是搬演男女青年之爱情遭受社会之压抑。 第三,从儿童视角表现社会人生之艰难。 美国儿童片在中国早期影坛译介很多,尤其是贾克哥根主演的电影,如《孤儿后福记》《义勇儿女》《贼史》《雪下孤雏》《马戏日》《纽约之可儿》《爹爹》《我王万岁》等,都是一方面写少儿生活之艰辛与世道之险恶,另一方面以喜剧手法写少儿之聪慧狡黠,帮人释难而得到关爱。这些影片也激起中国电影家拍摄儿童片的兴趣。特别是“上海”公司,因为有被称为“东方贾克哥根”的但二春,而拍摄了《弃儿》《弟弟》《小公子》。其他电影公司也拍摄了《儿子英雄》《孤雏悲声》《小朋友》等片。如同贾克哥根的儿童片都是社会片,中国早期的这些儿童片,也都是从儿童视角表现社会人生之艰难。《弃儿》写邢珍与金子昌私奔时生下一子,金子昌弃婴于路旁被路人收养,弃儿从小过着辛酸的生活。后盗贼吴惠将他带入贼窟教其行窃,弃儿虽受逼迫,却不愿同流合污,甚至在吴惠谋害慧珠时机智地将其救走。慧珠感念其恩,助其寻得亲生父母,弃儿一家终得团圆。影片模仿贾克哥根的《贼史》,写流浪儿的不幸遭遇和聪明调皮,很受观众欢迎。《儿子英雄》写一少妇的丈夫生性懦弱常受人欺辱,儿子年幼却性格刚强。少妇与一无赖私通,欲设计陷害丈夫后携家财逃跑,儿子英勇追捕,最终让那无赖自食苦果。影片“以轻趣冷隽之描写,叙述一含有无限悲哀,地方色彩极浓厚,曲折动人之故事”,描写穷人“受环境之种种压迫”,“使人不禁起无限之同情心”。[10] 还有其他题材的社会片创作,如在《春闺梦里人》与《儿女英雄》、《殖边外史》与《边外英雄》、《大义灭亲》与《妇人之仇敌》、《电影女明星》与《女明星艳史》之间,也都有明显的影响因缘。《儿女英雄》是美国描写战争题材以表现社会问题的著名影片,“当欧战时,抱夫死子亡之痛苦,不知凡几,诚古今来之大劫,独此片能描写当时之情状”[11]。侯曜受其影响摄制《春闺梦里人》,也是突出描写军阀混战中尸横遍野、家破人亡的悲惨情形,表现了战争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深重灾难。《边外英雄》描写美国西部垦殖生活之困苦及一段情史,曲折而有趣。国片《殖边外史》“与外国片《边外英雄》,有同等之价值”,“以提倡移民垦殖为经,小儿女之真爱为纬”,“表演移民垦殖,辛苦备尝,广漠荒土,终成良田,不啻我国民族史一部分之写真”。[12]《大义灭亲》是借鉴好莱坞片《妇人之仇敌》,两片“皆激励爱国心之作品也,不过一则远引而至,一则单刀直入,此其布局之异点耳”[13]。《电影女明星》也与好莱坞片《女明星艳史》相似,皆是以摄影场为背景,描写女明星耀眼光环背后的辛酸遭遇,揭示电影界生活之真相和社会之良莠混杂。 二、电影的文学深度和现代意识 好莱坞社会片创作不仅强调直面现实去描写社会问题,它还强调社会人生描写要有文学深度和现代意识,给予中国电影家深刻印象。因此,“长城”公司强调电影摄制要严格选择剧本,“不得良好的剧本,宁可停工三五个月,断不肯敷衍塞责为名利而摄制诲淫诲盗的影片,贻害社会,玷污国家”④。同样地,电影家强调电影创作要具有文学性,电影剧本应具备四种要素:“感情、想像、思想、形式”⑤。他们认为这样去拍摄电影,影片的思想感情、形式结构、性格刻画和艺术想像才能较好地表现人生和批评人生。 电影家着重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借鉴和探索的: 首先,强调结构布局要有文学的意味和深刻的寓意。借鉴美国社会片“能够运用艺术的手腕,刻画人间的罪恶”,其“事实的描写,在平淡中有醰醰之味”,中国早期社会片亦追求如此“深重的艺术性”[14]。时评洪深“于中国旧文学上也下了不少的功夫。那么文学对于电影上当然有不少的帮助”,其《卫女士的职业》《冯大少爷》等影片摄制处处透着“文学的意味”[15];《透明的上海》“既有充分之艺术,且处处予人以深刻之感想,把金钱及势力,描写得精警之至”[16]等,这些影片都以结构布局具有文学的意味和深刻的寓意而多受赞誉。突出表现在这样两点:其一是剧情合乎情理,结构严谨缜密,描写简练含蓄。即如好莱坞社会片,其“剧中人之所行所为,勿论其一举手,一张口,一皱眉,一蹙额,莫不予人以真实之感”,“其构造故事与描写此故事由‘起因’‘逐步发展’以至‘结局’时是否曾令每个阶段之变化,皆含有充分之‘必然性’”[17]。中国早期社会片较好的创作,如《卫女士的职业》对于社会问题“痛下针砭。描写步骤,鞭辟入里”,《透明的上海》的“结构紧凑,绝无涣散及不相连续之弊”,“前后呼应,无漏洞疵点”,《采茶女》的“布局之新颖,正如朱君(瘦菊)向作小说处处奇峰突起,深入浅出”等等⑥,都颇获好评。其二是注重在情节对比描写中体现深刻寓意。因为社会片重在揭示社会问题、批判现实黑暗,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像对比是最有力的描写手法。如《乱世孤雏》描写贵族妇人之冠价值数万金,而侯爵之车压死贫儿却只赔偿几块钱了事;再如《最后命令》描写俄国革命前后的社会阶层对比——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与底层百姓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情景。国产片亦是如此。如《玉洁冰清》,以钱维德锱铢必较、剥削贫民之可恶,与黄伯坚心地光明、气节高尚之可佩对比,衬出“玉洁冰清”来;又以一方面富者盘剥重利之苛,一方面良民身受其害之苦,使观众得知贫富不均实有天渊之别。《透明的上海》写将军之子王少珊自恃权钱之势威逼利诱芙芬、韵玉姑嫂俩,《弃妇》写丈夫王其伟的喜新厌旧、粗暴阴狠和妻子芷芳的自强自立、命运多舛,也都是在情节对比中尖锐批判现实黑暗。 其次,强调电影要透过情节去体现“生命”和“意义”。美国社会片在这方面都有深入的挖掘。《茶花女》中一对相爱的男女因家庭门第之别生出误会,而酿成生死悲剧。有论者认为此片不能只看情节,而应“辨别剧中的生命”,“看出剧中的意义”,国片“有奥妙点的很少”而应借鉴之。[18]《党人魂》中“无论其为贵族,为平民,各能保持其固有之威严,虽死不作摇尾乞怜之态”的精神,《铁血男儿》表现“美国人奋斗致富之精神之毅力”,都“足令人肃然起敬”⑦等等,也是中国电影家和观众对好莱坞社会片如此特点的注重。因此,“长城”公司拍片首先要求有意义:“全剧有全剧命意,每景有每景的旨趣”,要注重“剧之生命、精神”①;电影家也强调社会片拍摄,“影片能将编剧者的感情传达于观众,而编剧者的感情确是能将人生幸福有相互连和的就是有艺术价值”⑧。《复活的玫瑰》描写余晓星与秀云相恋至深,然两人身上都有包办婚姻的枷锁,尽管他们伤心不已却毫无办法。婚后晓星饱尝包办婚姻的苦果而远走香港,秀云受到婆家欺辱亦只身来到香港谋生。在经过种种艰难曲折之后,两人明了彼此心意而最终紧紧偎抱。影片立意“替普天下的青年男女,道其心中所不敢言,不忍言的话”——“我们青年男女的恋爱权,都被社会的黑暗势力劫掠完了”,体现出“向旧礼教恶势力争回他们的恋爱权”的反抗精神⑨。《天涯歌女》写歌女凌霄为其养父母操纵作为摇钱树,被恃财倚势之劣绅任意欺凌,后得姊妹之助逃出虎穴,然社会压迫之下只能沦落天涯。时评“凌霄掷弃张嗣武之珠宝,足见不以利禄熏心,此是何等廉洁的精神”[19];而编导的用意,正是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人奴性太深”,而努力于让“中国人奴性渐除”⑩,正是肯定了歌女对于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 第三是《茶花女》等好莱坞社会片打破大团圆模式,“情节好在没有结束,使人有余味可寻”[18],让中国电影家感受到社会片的独特魅力,并且懂得社会片要有“社会的兴味”,其现实批判要能引起观众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天涯歌女》描写名女伶李凌霄不肯嫁给劣绅张嗣武,而横遭迫害流浪他乡。饥寒交迫,她抱着琵琶,夜晚沿街卖唱,她唱道:“一任他量珠来聘,我岂肯奴颜婢膝!一任他势逼威凌,我岂肯便把头低!他们有的是钱和势,难道说我没有气和力?便没有气和力,也有血和泪”。不屈服于黑暗势力,最终在数九寒天,她唱着、唱着倒在街头的风雪交加之中。她以死表达了对那个黑暗社会的强烈抗议。编导也是以其人生遭遇,“想替一些被压迫者说一句公平话”,并引导观众对于她悲惨命运的同情和思考。《弃妇》的女主人公在经历种种社会压抑之后心灰意冷,最终也是在尼姑庵中郁郁而终,让人感慨,启人深思。《冯大少爷》搬演一个纨绔子弟走向堕落的人生,结局是冯大少爷发觉自己被老五与金六保欺骗,妻子与儿子则沉湎于游乐场不归家,不禁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这种结局看似有点像传统文艺浪子回头的“大团圆”,而实际上,全片情节发展已细致铺陈冯大少爷放荡形骸所造成的家庭悲剧,这里乃是当头棒喝的严厉警示,故其“寓意亦深远,颇耐人寻味”[20]。 中国电影在最初是连故事片拍摄都没有剧本的,至多是导演肚子里有个故事提纲,有些影片摄制甚至连简单的故事提纲也没有。早期中国电影创作曾长期没有编剧,故事片拍摄,比较流行的是使用“幕表”。杨小仲回忆192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拍摄《孝妇羹》《荒山得金》《莲花落》等情形时说,影片内容“由陈春生选定,把情节用幕表式排列出来,写了简单的戏白,就由任彭年执行导演。在摄影场里,由陈对他口述剧情对白,任就凭此分镜头拍摄,演员事先完全不明白今日临场所要演的戏,只是听从导演的意旨指挥而已。”[21]可见不重视剧本在早期中国电影界的情形之严重。1924年前后,虽然“剧本是一剧之本”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认识到没有好的剧本就不可能产生好的影片,但是长期以来积重难返,大多数电影摄制其文学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形下,不难看出,深受好莱坞影响的中国早期社会片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不重视剧本创作,更不重视电影的思想内涵、审美结构和文学价值的弊端,提高了中国电影的文学深度和现代意识。 郑君里曾批评中国早期社会片“很少表示过正面打击封建势力的决心,通常只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去描写、同情一些人生的悲剧。”[22](P.1397)郑君里1936年说的这段话明显带有左翼色彩。由于处在资本积累、无序竞争的阶段,中国早期社会片优秀或较为优秀的作品还不多;然而相较于当时的滑稽片、侦探片、言情片、伦理片等电影类型,它渗透着更多的时代色彩和“五四”文学精神。当然,也有少数影片如《道义之交》《海角诗人》等盲目模仿好莱坞,将城市与农村对立以否定物质文明弊端,却走向“东方的精神文化,可以战胜西方之物质文明”(11)的描写,那是思想糊涂而缺乏文学深度和现代意识的体现。 三、“实不啻现代社会之写真” 一般影片需要真实,描写社会问题以批判现实黑暗的社会片尤其需要真实。当时的影评就是以“社会之写真”去要求社会片的。如评价美国社会片《第七重天》深刻,就因为它是“现代社会的写真”[23]。同样地,国产片《玉洁冰清》受到赞誉,是因为它“实不啻现代社会之写真”[24];《殖边外史》获得较好评价,也是因为它“不啻我国民族史一部分之写真”[12]。因为只有真实地描写社会人生,才能体现善的思想和影片的美感;也只有对社会人生的真实表现,才有教育观众的艺术力量。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大成功的社会片,也是批评其现实描写不够真实。《大义灭亲》表现爱国主题是积极的,但有评论指出:电影“贵在求真”,片中梅丽兰为郑民威请赦的情节,是借用格里菲斯《乱世孤雏》中丹东为即将受极刑的贵族谢瓦利尔和恋人路易斯请赦的情节。但《乱世孤雏》中是力争多时,一纸赦书始行获得,又经许多波折才使得如愿,而《大义灭亲》中女主角拿到总统特赦,手续太简单,而使剧情显得不真实。所以尽管此片“宗旨非常纯正而光明,不过人家将大意一看,就会说不是实事戏,因为距离社会的背景,稍嫌远些,不能使人感化”[25]。又如《弃儿》,片中女主角邢珍与金子昌仅见面两次就与之私奔,弃儿年幼却身手不凡。有评论指出,“余意乡妇虽慕虚荣,决不致如此不知耻;弃儿年方六岁,虽知慧珠出门,追踪无及,何知慧珠所奔方向,而能救女于烈火之中”,也因为不真实而有损“立意”。[26] “实不啻现代社会之写真”,社会片的如此审美特性,就要求导演“细心研究彻底领会”剧本,要求导演在演员表演、影像呈现等方面能“将剧之生命、精神,发挥殆尽”①。 社会片注重“现代社会之写真”,必然会使其镜头影像的呈现趋于客观写实。在电影艺术上更多受到刘别谦、卓别林熏染的洪深,其《冯大少爷》《卫女士的职业》等片的镜头画面却没有一点西洋色彩,就在于其影像能够真切地表现中国社会人生。在艺术和技术上深受好莱坞影响的“长城”公司,其影片摄影之精美向来为国内外观众所称道,然而,他们更强调电影创作要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影像技艺要能够真实地呈现社会人生。所以中国电影家也开始注重社会片拍摄的现场感和真实性,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场景或场面。例如,《复活的玫瑰》最后秀云蹈海一幕,为追求真实而采取了实景拍摄,演员“自高峭山巅,跃入澎湃大海,水没及顶,辗转浮沉,表情与动作,一步紧张一步”[27]。《天涯歌女》的最后一幕也是选用实景,“沦落天涯的歌女,在一个沉黑的雪夜,彷徨奔走,无家可归,终至受不住寒气的袭击而跌倒于深雪之中,伊的孤苦凄楚的光景,简直可以和《赖婚》中间丽琳甘许狂奔雪地那场的表演,同样的使人得着深刻不忘的印象”[28]。为了追求真实,当时很多社会片的一些重要场景或场面都是实景拍摄的。 社会片的真实与一般影片相比较,其“社会之写真”还在于它更注重细节的描写。如美国社会片《第七重天》,此片“极平常,极普通,但也极深刻”,就因为其“社会的写真”“能感动观众。尤其在许多细微的所在”[23]。国产社会片在这一方面也非常重视。《弃儿》中但二春扮演的弃儿,为突显下层社会的困顿与辛酸而有被恶徒诱骗窃物的细节,引起人们争论。“有论者谓其有失儿童教育之意”,然周瘦鹃以《弃儿》与美国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社会片《贼史》进行比较,指出:“迭更司作《贼史》何尝无诱令儿童窃物耶”,“盖写何等人物令恰称身份”,“故观影戏当具世界的眼光!”[29]洪深的《冯大少爷》描绘社会人生真切动人,也是因为其影片对于“社会生活之片断描写”的情节叙事和心理刻画的细致入微,给予人们深刻的感受。《透明的上海》中为表现王少珊太太独守闺房的苦楚,有她在闺中正拿着一本《伉俪福》翻阅,一面看人家伉俪情深、旖旎风流,一面感受自己遇人不良的细节,给观众强烈的印象。但片中场景、服装某些细节“侧重欧化”、显得不真实也受到批评,强调“要注重些我们东方的文化”[30]。 社会片要成为“现代社会之写真”,还要求演员能真实地表演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情感。《洗衣女》《乱世孤雏》等美国社会片表演的“描写世情,入木三分”,及其重视“心理的表演”,[31]让中国电影家懂得其中真谛。受其影响,“长城”公司拍摄电影重剧本,也重演员表情、动作的表演艺术,要求“确能将剧中人个性表演出来”①。洪深的电影“描写如许人物,能够个性完全独立,各不相混”,欧阳予倩要求演员“能够拿自己的性格,完全弃去,而容受剧中人的性格;就是忘了自己,完全拿自己化成剧中人”(12),都是从“现代社会之写真”出发对表演的要求。所以,王汉伦在《弃妇》中扮演吴芷芳,“表情和动作,很有几分功夫”,传达性格情感逼真,而能使“观者同主角的动作归于一途”[32];杨耐梅饰演《奇女子》中的妓女“异常认真。她能体验奇女子所处的境遇,所以在表情上异常真切”[33];《天涯歌女》中李旦旦表演歌女离家那一场戏,“当姊妹分手的时候,李旦旦抱持着她剧中的爱姊,一粒粒的泪珠,从眼眶中滚到粉颊上,使全场的人们都感到说不出的悲哀”,她“熟练自然的表情和动作可以使这部影片生色不少”[34]。其他如胡蝶在《新茶花》中饰演茶花女,但二春在《弃儿》中饰演弃儿等,一举一动,形容逼肖,都能将角色的性格情感曲曲传出。 此外,《边外英雄》等美国社会片外景摄影之真、之美,国人认为“可作中国影戏之范本”[35]。由此,社会片的摄制改变了中国早期电影大都是摄影棚里演戏的套路,而走向真实的社会人生和大千世界,其外景拍摄也在注重真实的基础上讲究美感。《弃儿》中“背景之优者,有火景、荒林、花园等幕,均有美术观念”,“联观之为影戏,分观之不异无量数绝妙画图”(13),体现出电影家对于社会片外景影像之真、之美的追求。《大义灭亲》也是如此,其外景是在庐山摄取,如三叠泉飞瀑、铁船山云海、大寺林天桥、御碑亭夕照、黄岩寺石塔等,皆真实且富有美感。 所以尽管还存在某些不足,中国早期社会片的“实不啻现代社会之写真”,又在电影的导演、表演和影像呈现等方面,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 ①雪俦、泽源:《导演的经过》,长城公司特刊《春闺梦里人》号,1925年。 ②予倩:《民新影片公司宣言》,民新公司特刊《玉洁冰清》号,1926年。 ③侯曜:《悲欢离合的生活》,民新公司特刊第2期《和平之神》号,1926年。 ④《弃妇》影片消息,1924年12月13日《申报》。 ⑤侯曜:《电影在文学上的位置》,民新公司特刊《玉洁冰清》号,1926年。 ⑥分别见叶如来《捧〈女书记〉兼捧洪深》(1927年10月25日《申报》),微笑生《记〈透明的上海〉》(1926年4月25日《申报》),鹃《参观〈采茶女〉影片而后》(1924年9月1日《申报》)。 ⑦分别见鹃《〈党人魂〉与〈湖边春梦〉》(1927年10月13日《申报》),曾竹铭《〈铁血男儿〉即将开映》(1926年11月2日《申报》)。 ⑧侯曜:《什么是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大中华百合公司特刊《透明的上海》号,1926年。 ⑨侯曜:《收回恋爱权宣言》,民新公司特刊《复活的玫瑰》号,1927年。 ⑩欧阳予倩:《我编〈天涯歌女〉的感想》,民新公司特刊《天涯歌女》号,1927年。 (11)孙师毅:《从〈回家以后〉到〈三年以后〉》,民新公司特刊《三年以后》号,1926年。 (12)参见宋痴萍《谈谈洪深先生的编剧手段》(《电影月报》1928年第3期)、予倩《导演漫谈》(民新公司特刊《三年以后》号,1926年)。 (13)参见郑怀桥《〈弃儿〉影片之余评》(1924年2月26日《申报》),瘦鹃《书〈弃儿〉影片》(1924年1月26日《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