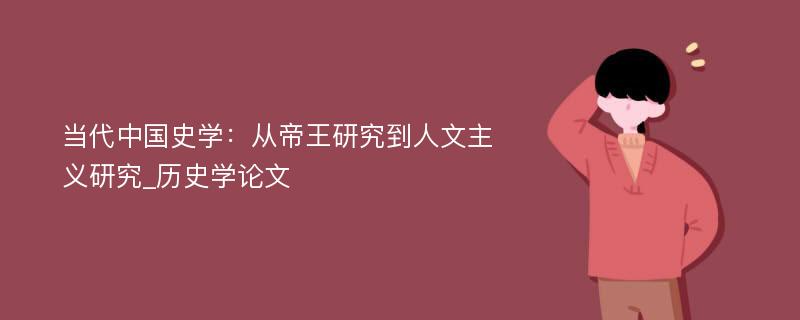
当代中国史学:从帝王之学走向普遍性的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遍性论文,史学论文,帝王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之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史学,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这30年来中国史学最根本的变化,可以说,就是从帝王之学一步步走向普遍性的人学。
主要讨论四个问题。第一,30年来中国历史学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过去很多人喜欢讲史学危机,其实所涉及的就是怎么看这3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第二,历史学作为普遍性人学的主要表现;第三,在中国史学的这一转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思想冲突;第四,史学成为普遍性的人学未来的一点展望。
一
30年来,中国历史学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史学革命谈了好多次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时候讲史学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戚本禹的一篇文章也谈史学革命。但是,中国历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帝王之学这一点没有改变。历史学是人学,研究的是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历史学关注的主要还是帝王将相和统治者。一般的人,芸芸众生通常都处于历史学考察对象之外。梁启超在20世纪初讲,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帝王将相的谱系之学。实际上,过去的中国传统史学,从《春秋》所谓“笔则笔,削则削”,到《史记》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直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统治者执政提供思想资源,是名副其实的佐政之学,资治之学,是帮助统治者吸取历史上的统治经验,来维系自身统治的这样一种学问。二十四史这类正史,就是这样一种统治者的统治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传统思想中,正史是最具有实践性或操作性的学说。20世纪,从梁启超讲史学革命,到毛泽东提出“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把历史的主角从帝王将相换成奴隶,换成农民战争的领袖,要用奴隶创造历史来取代英雄创造历史,都是要改变传统的帝王之学。但实际上常常只是用形式变换了的另一种帝王之学来取代传统的帝王之学。因为当时史学核心的任务是为夺取政权以及巩固政权服务,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进行所谓对过去历史的颠覆和对中国古代历史以及近代历史的重建。近30年来中国史学最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开始把历史学从传统的帝王之学、从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的学问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或者说最具有现代性的普遍性的人学。正是因为这样一场转变,中国史学发生了一场真正革命性的变化。
30年来,历史学走向普遍性的人学,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对传统的历史学所关注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开始逐步地让他们一个个从天上、从神坛上走下来,来到地上,来到人间,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的活生生的真实的人。把历史人物从神化、或者妖魔化,转变到人化,让他们真正地还原为普通的人、活生生的人,以此所取代以往的帝王之学。30年来,中国史学所发生的这一变化,最初是从毛泽东从神坛走下来开始的。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间,那么长时间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从神坛上走下来,对整个历史研究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大量的历史人物,原来或者被妖魔化的,或者被神化的,由此都开始在历史研究中还原其本来面目。像对陈独秀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另一个总司令胡适,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整个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个群体,对被视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大量的历史人物,对曾被历史研究所遗忘的一些人,都得到较为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梁漱溟到陈寅恪,从辜鸿铭、杜亚泉到熊十力、马一浮等等,一时都成为研究的热点。相反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长时间被我们神化了的,现在也开始恢复他们的本来面貌。比如太平天国、洪秀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最高代表,特别是在天京(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真实的状况,也不再曲意廻护。这些年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恢复应有的历史记忆。
30年来,我们在抹去大家所关注的众多重要人物身上被神化的色彩和被妖魔化的色彩方面,作了大量的非常有成效的工作,这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使得已经被我们从历史记忆中间抹去的很多人的真面目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
二
历史学走向普遍性的人学,最主要的表现是历史学把自己关注的重点,从原先为帝王、为统治者服务,到后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服务,转向认识人本身,了解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究竟怎么样生产,怎么样生活。了解我们人类保有、传承、变革和创造了哪些东西,是根据那些条件,经由什么样的路线。明辨人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人怎样才能超越现有的状况,走向未来。一句话,我们把历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地转向认识人类自身,认识整个人类社会。这使得历史学者关注的对象、研究的领域比先前无比扩大了。
首先,人们把人的自然性或自然的人,又重新放在史学的研究对象之内。诸如人口史,多年来,由于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结果,把人口史研究基本上丢掉了。这些年来人口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版。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过去纯粹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在新出版的《李济文集》中,收入李济的博士论文,他最先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人。现在有条件进行更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搜集更多更完整的数据,来深化这样的研究工作。最近通过广泛开展的基因调查和基因研究,研究中国人种来源,研究南岛的人种来源,都很有成效。人的健康与疾病,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生态史,环境史,包括自然灾害史、气候史、流行病史,现在都很热。汶川大地震,使人们关注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的中国地震历史地图(三卷本)。人的自然性,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统统被放在历史研究视野之外。斯大林当年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间讲过,自然环境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很小。毛泽东当年也是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历史研究把这一部分,即人的自然性研究,放弃了。现在重新回过头来,发现这些问题极其重要,不能忽略。
当然,关注最多的还是人的社会性。人之所以作为人,最主要的特征当然是因为人具有社会性,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但是我们过去谈人的社会存在只讲阶级关系,阶级的存在,现在才关注到人的社会性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内容。人处在各种社会联系、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中。马克思当年就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本质上就体现在各种社会联系、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中。上海图书馆有中国最大的家谱收藏,这些年来对血缘网络,包括家族史、家庭史、婚姻史等等的研究超过了过去任何时候。地缘网络,地缘关系,表现于地方史、地区史、包括同乡史、会馆史等等的兴盛,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史、乡村史、区域史,很多也都体现了地缘网络。历史上的权势网络的演变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社区的研究、社团的研究、各种社会群体的研究、阶级和阶层的研究、国家的研究、政党的研究、民族的研究,等等,一直到黑社会、帮会等的研究,都使得人们对人的社会性多层次的、多元的内涵,有了比过去更完整、更丰富的认识,不再把那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第三,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的思维性。人是能够思维的动物,人们知识的积累和传输,知识结构和学科构成的演进,人们各式各样的观念怎么形成怎么演变,人们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变化,人们的宗教、信仰,日常的思维、日常的风俗习惯等等怎么改变,这些都成为近些年来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比如,人们用了几十年的“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封建”这个概念,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又如,“革命”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怎么演变的,最近已经出了好几本著作。这些都属于观念史的研究。
实际上,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古代一些观念和知识体系怎么形成、怎么演变,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国家人民,他们的核心观念是怎么形成、怎么演变的,近代的西方、近代的东洋,包括日本这些国家,一些观念怎么形成、怎么演变的,中国近代以来,这些知识、这些观念怎么形成、怎么演变的,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因为多少年来,人们都把这些东西都看成是不需要去讨论、不需要去研究的既定前提。现在发现,原来这些观念的形成,都有一个特定的条件。如果我们把它一旦看成是不需要再去讨论、不需要再去检讨,不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前,而它原来的基础、它的出发点本身就有问题,从这里引申出来一系列的知识、观念,就会走向严重偏向的一条路径上去。所以,回过头来,有必要重新研究知识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宗教的历史、信仰的历史,把知识的传输,知识的积累,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改变,作为重新认识我们人自身,重新认识我们人自身的思维性、思维特征、思维方式的演进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认识人自身方面,人们还越来越关注到人的物质生活或物质生产、物质消费。人之所以成为人,既有生产的历史,也有生活的历史。不同的社会成员,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多少年来,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人们的生活,研究过人们的消费。因为过去只讲生产关系,只讲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主要又讲剥削、压迫,把人们生活的这一大块内容,基本上遗忘了,抹去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太多,要研究各种不同层次,各个不同方面。现在大家关注的全球的粮食问题,1949年以来,人们的粮食供应,粮食生产,粮食消费的状况,现在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粮食的生产、粮食的运输转出、粮食的供应、粮食的消费、粮食的各个品种等等,虽然它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很小部分,但是它揭示了一个整个社会发展的状况。
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的精神生产和消费状况,也为人们所关注。历史研究更多地转向人的知、情、意,转向人性的最根本方面。这次汶川大地震,牵动了全国所有人的心。最重要的什么?我觉得是人们最根本的、人性中间善良的那部分——人的知性、人的情感、人的意志,平常潜藏的那部分,一下子都迸发出来。大众的、普通人的知性和理性发展的状况,人们的感情和审美的演变状况,人们的意志和心理的发展状况,过去我们历史学关心得太少。人们精神生活,特别是大众的日常的精神生活,成为人们现在研究一个新的亮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调查,包括文献的调查,大量口述资料、人们日常生活中间遗留下来的各种实物资料的汇集,为历史研究打开一大片新天地。
过去只讲阶级性的时候,很少讲到人性,但是其实一直不能回避人的性善、性恶的问题,人身上的人性和所保留着的兽性或动物性的关系问题。过去在历史研究中间,很少真正关注最普通的民众精神生活状态,实际上,历史是无比丰富的。特别是现在历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对大量的保留在民间的种种文献的、实物的、口述的资料重新进行研究,使得我们对人自身的认识发生很大的改变。历史不再由几个英雄人物、帝王将相、领袖人物所主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历史上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历史是所有的人共同去创造的,人的生命的价值、人的存在意义也正在这里。离开了最基层的、最普通的民众,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解。自从年鉴学派以来,人们开始关注到社会最基层的方面。尽管我们讲了多少年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我们关注的重点还是几个领袖人物、伟大人物。近30年的历史研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长时间内被我们所忽视的、最普通的大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性、他们的思维性,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进入到历史视野,这使得整个历史学具有比先前远为广大的研究空间,也使得研究方法更为多样。这是30年来中国历史学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的变化最主要的方面。
三
历史学的这一转型,并没有最终完成,现在还在继续之中。这一转型更不是一帆风顺。30年来,历史学界,思想上的冲突、学术上的冲突,一直没有终止过。它主要环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第一,在史学研究中间,继续保持一家独尊的局面,还是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30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包含自然科学等等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展开,推动了百家争鸣大格局的形成。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很多自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没有认真系统研读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长时期是根据斯大林和《联共[布]党史教程》的解释。很多人用《联共[布]党史教程》和斯大林对马克思解释来代替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和思想。长时间我们只认苏联一家,后来变成只有毛泽东本人的解释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他都不是。但是世界上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流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到,要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者从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从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可以得到有益的东西,因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间也有它自己可能接近真理的地方,也可能有某些真理的颗粒。胡绳这个话在一些人眼中间直是大逆不道。但这其实是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道理。要不然,马克思主义怎么产生呢?马克思本人能够直接从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间吸取营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就不能了呢?至今还是有一些人,总想继续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继续维系或者重建独尊一家的局面,实际上就是独尊他们自己,想继续用一颗脑袋代替13亿颗脑袋,由一批不动脑子,更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科学的人来垄断对历史的解释。哪一个历史学家敢说,我的见解就是历史的定论?新资料不断出现,新方法不断运用,人们总是在不断地研究,不断地进行争论,而历史本身的发展,则会在自己演进的过程中间把先前潜藏着的许多方面逐步地显示出来。一个历史学家,无论水平多高,也不可能垄断对历史的解释。这个背后的问题,其实还是历史研究应当将尊重历史真实放在第一位,或是将尊重某一种观点,或是某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和垄断放在第一位。
第二,所谓本土化和西方化的问题。30年来中国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走的正是中国自己的路。我们曾经想照搬苏联模式,走不通。在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对于加拿大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甚至罗马尼亚模式,我们都去考察过,后来发现都不行,中国还得走自己的路。在历史研究中间同样。很多人担心我们是不是全盘西化了?西方化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30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外部世界有了频繁的接触,开始了平等的对话,也对普世价值有了更大程度上的认同。国外史学研究新的方法、新的流派,他们的新的历史观点,使得我们眼界大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思考,都使得我们对先前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能够重新加以思考。正是因为这样,30年来我们史学界思想特别活跃,研究成果特别多样,这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我们的历史学真正走出了自我封闭的状态。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把传统的帝王之学真正转变为普遍性的人学。很多人把本土化和西方化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之间,在频繁的接触碰撞争论中间,才能开拓我们的视野,把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出来,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时代的中国新文化。历史学要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人学,需要一个全面的转型,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只有在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在同世界各种文明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以及我们自身深刻的反思与再创造中间才能实现。
第三,在史学研究与转型中间,我们政治权力的全能化对史学研究、史学转型还有很大影响,这又引发一系列冲突。这里面最突出的是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都引进量化的考核体系,用这套东西来制约、检查我们整个的历史研究。这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也推动了我们的研究,因为量化意味着必须要出成果。但是,被扰乱了的是学风。其次,历史研究和政绩、形象联系到一起,搞了很多工程。学术工程化有好处,可以集中很大一部分钱,来做很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但是工程化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比规模,赶进度,劳民伤财,华而不实。再次,就是经费配置,我们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有利于那些有一定地位的史学人才获得很丰厚的研究经费,不利于那些在史学研究中间可能会作出突出成绩,愿意沉潜下来做研究、而不愿意申请项目、不愿意受这样那样的管制、不愿意填写大量的表格的研究者。但是,确确实实,史学研究最需要的正是有一大批这样长期默默进行耕耘的学者。
四
中国史学成为普遍性人学未来的展望。
尽管如前所述,30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存在很多困难,争论也是不断,还有很多的障碍,但总的趋向,可以说,历史学研究中,史学成为普遍性的人学,这一趋向已很难逆转。江泽民在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已经明确地把马克思当年一再坚持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我们核心的价值、核心的目标重新提了出来。这是多少年来,从苏联共产党到中国共产党都不敢提的,叫“每个人”,而且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届中共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一再强调“以人为本”。这次汶川大地震,真正彰显了什么是“以人为本”。温家宝总理提出来,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每一个人的生命。把中国普通人的生命,一下放到这么高的地位,确实彰显了生命的价值,人性的价值。“以人为本”,真正是把普通的老百姓当成历史的主体,当成社会的主体。当然,我们要真正达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这样一个危难时刻,人的价值,得到这样大的彰显,就使得我们让历史学成为普遍性的人学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们直接与世界相联系的广大网络中,中国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封闭自己。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让芸芸众生,他们的主体性能得到方便呈现。网络时代,最普通的人也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一个脑袋左右所有人脑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不再是一两个人可以主宰的了。人民、最普通的老百姓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一个时代,在中国已经开始了。尽管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历史学作为普遍性的人学,它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