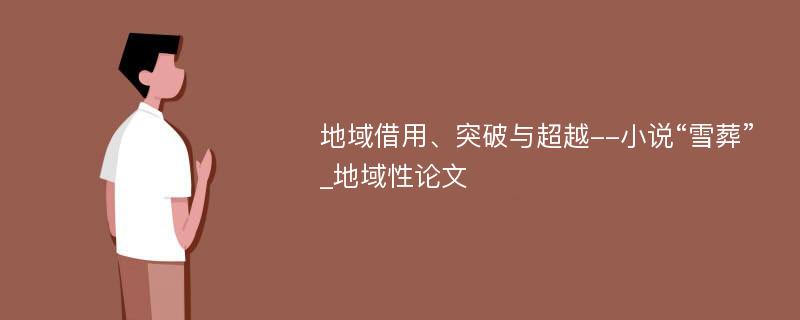
地域性的借重、突破与超越——论长篇小说《雪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性论文,长篇小说论文,雪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地域性”是文学创作的双刃剑
这里所说的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性,与一般所说的文学的地方特色不同,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特定地域的社会现实、生存状态、文化传统、风情民俗、自然风物、独特题材、语言特点等属于创作资源的内容;二是指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创作意识、表达方式等带有特定地域性的文化品格和特点。前者关系创作客体,后者关系创作主体。这两方面的有机契合,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优势,借助于这些优势可以取得某些特殊的成果,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和风格、反映特定地域文化精神的作品。但是,这不应该是文学创作追求的最终目标,真正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地域文学,应该既有地方内容、地域文化精神又有普遍意义和人类精神,中外文学史上的成功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中国,借助于地域性创作的作家很多,但是只有鲁迅、沈从文等部分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很多作品却无声无息。文学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地域性因素只是文学创作达到一定水平的可能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有地域性比没有地域性更有优势;但是,这种可能优势能否变成现实优势,还要依赖于其他许多因素。进入创作过程,如果作家的视野、眼光仍旧局限于地域性,把所谓真实地反映地域特色作为艺术目标,而不具备以更高的精神境界和博大的情怀反观和审视对象的创作意识,不具备驾驭和处理地域性资源的艺术能力,那么,地域性就有可能成为局限性,它可以掩盖创作的不足,却不能提高艺术水平。为此,我更愿意把地域性看作文学创作的特殊源泉和作家带有地域特点的精神资源;在理论上,需要把作为创作前提和资源优势的“地域性”与作为创作结果的作品所具有的“地方特色”区别开来。这种区分不是概念游戏,它的必要性和依据是,许多地域文学,当然包括西部文学创作中,曾经出现了不少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地域风格却达不到较高艺术水平的作品,其优势仅在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地方风情的特殊性。而文学创作高水平的要求和目的,并不应仅仅停留在有地方特色上。就作家来说,大凡都想使自己的创作在现在超越空间局限而具有人类性,在将来还想经住时间考验而具有永恒性,这些理想是单凭“地域性”不能达到的。在这里,以似乎偏激的表述也许会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地域性是特色的标识而不是水平的标志,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可以因地域性而增色,低水平的文学也可能借重地域性而流行,在文学创作中,地域性是双刃剑。如果过分依赖于地域性,或者说把地域性作为文学追求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它作为创作资源优势和思维方式的优势,这种地域优势可能变为地域局限。
联系到西部文学,我想这个问题更值得思考。应该承认,地域性确实成就了许多文学爱好者,使他们成为作家;借助于地域性,地方文学在当代文坛也可以有一席之地。现在和将来,文学创作中还会、也有必要借助于地域性。所以,不能简单化地对待地域性。但是,同时应该认识到,处于地理、社会和文化边缘的地方文学,要想提高水平,进入中心,不能仅仅靠地域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的价值不是依赖地域性而是超越了地域性才被公认。“西部文学”的概念就带有西部地域性涵义,它曾经为西部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且西部文学在实践中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本文不讨论西部文学理论本身,而只想指出,处于西部地区的作家,其人生历程、生活积累和体验、文化观念意识,乃至表达方式,一般都会自然地带有西部地域性,他们最容易陷入地域性,而最难超越地域性。为什么有的业余作家,第一部作品一举成名,而后来的创作就难以超越,其中原因之一恐怕是地域性资源开始贫乏或者陷入地域局限而不能超越。他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性。从广义上说,每个作家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他的创作都有地域性印迹。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地域性。然而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对现实的观察、对生活经验的积累等毕竟是有限的,文学创作更多地要靠作家对生活的重新认识、理解、品味、创造性想象等。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作为精神生产,有限的资源可以创造出无限的产品,在这个层面,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艺术能力是决定因素。满足于地域性资源和地域性意识,久而久之,会抑制作家的创造性意识和艺术技巧的提高。理论在这个时候,主要应该引导作家怎样突破地域性局限而不是鼓励作家执着于地域性。突破地域性局限,是提高西部地域文学水平的一个现实问题。在文学创作客体方面,要借助于地域性资源,在文学风格上要体现地域性特色,在创作主体方面,则要突破地域性局限。这不但不与地方特色和地域优势相对立,而且还是地域文学走向全国的必要前提。所以,我总的看法是,西部文学只有借助地域性而又突破地域性,才能真正做到有西部“风骨”,有自己个性,真正独立于民族文学之林。
近年来,西部(甘肃)小说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不少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的成功经验之一,正是借重地域性又超越了地域性。长篇小说《雪葬》(范文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可以作为例证和个案。
二、“雪葬”的寓意性和主题的深刻性对地域性的突破
“雪葬”书名的命名有特殊的寓意,这与作品的立意相关。
与入土为安的土葬相比,与面向苍穹的天葬相比,与投入自然怀抱的海葬相比,与让灵魂在烈火中永生的火葬相比,闻所未闻的“雪葬”使我们纳闷,“雪葬”是一种什么丧葬礼俗?对此,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正面解释,只交代了葬礼是在大雪天进行的。不过可以肯空,雪葬不是作品所描写的赵家营和柳沟河的丧葬礼俗,或者说,这本就是一个无从考证也无需叫真的葬仪。但我仍相信,作品的这一命名是有特殊寓意的,而寓意产生于联想。“雪葬”使我们想到雪里埋死人的隐喻,想到气氛的肃杀严酷,想到“清白”,想到所谓苍天有眼的天道观念或者死者的不白之冤……
小说起笔,“天阴云沉,苍穹欲垂”环境的描写和“赵家营村口的大槐下,准备观看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气氛的渲染,成功地挑动着读者的好奇心:一个农村的葬礼,何以会引起如此不同寻常的反响?死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小说并没有急于答疑解惑,而是对于死者死因的各种传言的介绍分析,特别是右派爷的一番略带神秘的感叹,使读者进一步意识到这场葬礼的不同寻常。小说继而转向对赵家营历史文化的追溯,特别是通过家族史对赵家营社会历史进行追溯,这种追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艺术概括。这更加加重了读者的疑问,作者要让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出场?他的“雪葬”与这一切又有何种关联?这些悬念,这些设问,不仅是为了故事倒叙的方便,而是一个意欲突出思考和质疑性主题的艺术构思和结构设置。这决定了小说必然要通过个人命运的关注而揭示现实矛盾和生活底蕴、探索社会问题,也决定了作品叙事过程将始终与总体上的质疑、探索和不动声色地追根溯源相照应。小说借助于地域性却并不以对特定地域风俗的反映为目的,不靠特殊地域的特殊题材取胜。这无疑显示了作者创作视野突破了地域性的局限。
随着小说情节的一步步展开,在遥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舞台上,主人公开始出场并有所作为了,而作者的艺术解释、理性思考同时也开始了,答案也逐步给出:
一个在落后农村长大、在畸形时期备受精神创伤和挫折的“二百五”,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会有怎样的欲求、希望和情感?答案是,他会自暴自弃,但并未泯灭朴素的理想,甚至还潜藏报复的心理,而他的生活环境和时代提供的条件使他有机会把这种心理情绪变为试图改变自己处境的现实追求,心理隐痛成为他日后出人头地的驱动力。
一个源于解决基本的人生需要而倒插门的男人在新的环境中会有什么作为?答案是,他有遗憾和不甘,也有新的欲望和面临多种可能,一有机会,他会加倍寻求补偿,包括心理和生理的满足。这是他进取的依据之一,也是为悲剧埋下的伏笔之一。
一个离开了自己家族及其文化传统的后生,在道德约束稍微松弛而新的诱惑不断刺激的境遇中会有怎样的表现?答案是,他仍保留基本的文化心理,会顾及自己的家族舆论,也有光宗耀祖的意识。但他也比较容易获得精神解放,接受新事物,试图开辟人生的新景观。当时代为他提供条件、偶然的机遇把他推向变革的舞台时,他会凭自己感觉和良心为人处事。这是他身上常常呈现新旧混杂的矛盾状态的文化原因。
一个由时代大潮推上改革舞台的农民在与官员和商人打交道中会有怎样的遭遇和命运结局?答案是,由于外在因素造就的“当代英雄”,也会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一个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也会被所谓的改革所击倒。
小说所形象地解释的上述问题,显示着作者对特定地域题材的处理向度不是在追求地方性,而是利用地域性题材资源思考普遍社会和人性问题。他告诉人们,赵天佑,正是似乎由于“苍天”的保佑,出乎人们预料地成为当地的一个出场“人物”,成为赵家营家族中一个当代的英雄。然而,“右派爷”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和活着的“大槐树”,不时出现并不断告诫着不谙世事、不知深浅的这位赵家的“英雄”:不要得意忘形,显赫中有卑微,成功中有危机,人们以复杂的心情拭目以待。最终,人们看到赵天佑的悲剧,他自杀了。悲剧的发生突然且方式极端,但似乎并不出人们所料。当然,他可以不自杀,可以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以一个失败了的当今农民的身份活着,让他从哪里爬上去再跌回哪里去。这也不失为一种悲剧,也有意义。他的结局还会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比如,他可以逃跑,还可以赖账,把一切看得无所谓,当一个曾经风光过的“二百五”,这种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再比如,这有一种理想化的处理方式,让他依靠法律,追回骗款,克服困难,挺过来之后从头开始,这也未尝不可。这就是说,他的悲剧结局的表现方式不止一种。但是,作者认定,不管结局的方式怎样,实质只有一个,他的悲剧命运已经无可避免。于是作者毫不犹豫地给予他自杀的结局。这种选择避免了艺术的俗套,也避免了对悲剧力量的削弱。这也是赵天佑自己选择的方式,他必然会选择这种方式。这符合作品表现的生活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他的自杀的方式是简单的,但他的自杀包含很多的意味,包括一些无法证明、无法言说的意味。比如,心理的承受力,宗族文化的压力,现实的阴暗面,经济上的责任,个人的脸面等等。这种激发人们更多的联想而不拘泥于单一的解释,同样是一种突破地域性限制的体现。
赵天佑的悲剧有其特殊性,更有普遍意义。他的悲剧是个人的特定的悲剧,也是西部农民的悲剧。在别处,也许他不会死,但在西部的云水市,在偏僻的柳沟河,作为赵家营的子孙,他必然会死。他的死又有普遍性,而且异常深刻和发人深省。赵天佑的悲剧不应该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暂时不能够实现之间的冲突引起的悲剧,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本来能够实现而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现实悲剧,是喜剧时代的人生悲剧,这种悲剧包含着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各种因素。当追溯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时,我们看到了大时代的复杂性,喜剧时代的矛盾性。通过经营药材致富又由于各种矛盾最终失败这件事告诉人们,改革的大潮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淹没一个人,时势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毁掉好人。赵天佑是“自杀”,也是“被害”。历史呼唤改革,人民希望改革,出路惟有改革,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和悲剧的深刻性也在于,假改革之名而毁掉改革是最可怕的,是改革的大敌。改革也会被利用,被歪曲,多少好事假改革之名变成坏事,多少坏人假改革之名为所欲为。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政治文明已越来越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改革的要害已不再是理论上空洞的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代表谁的利益,为了什么去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任何改革都有可能变成权利的再争夺和利益的再分配,喜剧时代上演悲剧就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对改革问题的思考。赵天佑命运的大起大落,是时代条件、社会环境、经济活动中的矛盾、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一个中国农民的结果。从作者表现出的敏锐性和深刻性来说,他思考的不是某些特殊地区的特殊问题,而是普遍问题。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雪葬”的命意和作品的内涵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价值。其一,小说通过发生在中国西部一个仍不发达的村庄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特别是赵天佑作为一个被改革潮流推上社会舞台却最终失败的农民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中国农村改革中的深层矛盾,揭示了改革中的普遍问题,由对缺乏约束的权利导致悲剧的思考,突现了政治改革的极端必要性、紧迫性。从这个层面说,《雪葬》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反映改革的力作。其二,小说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和性格的刻画,又充分注意到他的家族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俗、道德意识、价值观念等等文化因素,赵天佑的生活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冲突和精神矛盾,常常在肤浅的现代意识与浓厚的传统观念,多彩的城市文化与沉闷的乡土文化,强烈的欲望刺激与内在约束之间游弋。从这个层面说,这又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小说。其三,小说对于赵天佑性格的描写,并没有落入一般小说描写农民改革家的理念模式,没有简单化、观念化和公式化,而是切入人性的层面,给予展露人性和内心世界的机会和空间,表现主人公的欲望和由欲望所驱使的行动。比如,作品写赵天佑作为一个男人与几个女人的纠葛就颇有章法。从小时候在农村工棚的麦草铺上接受充满刺激的“性教育”开始,到结婚成家后与梅梅的偷情,再到在广东的舞会上小姐给予他的“启发”,最后他胆敢放肆地“耍”副市长的小姨子,这过程是他的欲望一步步被刺激、而道德意识一次次被漠视,感性体验一次次被强化、而理性约束一次次被击溃的过程。他的情欲与他的权利和物质基础的发展成正比。他的悲剧结局与欲望的无节制有直接的关系。作品的这种描写,不是道德说教,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从这个层面看,这部小说又带有对人性探索的性质,是一部揭示商品经济时代人性与天理、利益与道德冲突的小说。这些构思和艺术表现,都是借助于地域性而突破地域性局限的表现。
当然,小说在以上这几个层面其实都还有深化的空间。比如,我们看到了赵天佑的悲剧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却未能看到他在面临悲剧结果时的挣扎和抗争(当然是赵天佑式的挣扎和抗争),他在这过程中展示的精神世界。他的死是必然的,但他并不想死,以他所已经有的人生经历和并不轻易认输的性格来看,他应该有挣扎和抗争的举动,特别是与自己的精神中的矛盾的抗争。所以,我感到对他的死的艺术处理似乎有过于仓促和轻易之感。按照作品业已反映的生活逻辑和主题开掘的可能,赵天佑的悲剧的深刻性不但表现为一个本来不该自杀的人自杀了,更表现在一个不该自杀的人不想自杀经过挣扎而又不得不自杀。从前者读者会感到悲愤、震惊和不平,从后者读者将还会领悟到更多的人性内容,因为前者以悲剧事件感动人,而后者以悲剧意识、悲剧精神启迪人、陶冶人、净化人的灵魂。这又说明,作者还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精神滋养。
三、《雪葬》在艺术上对地域性的借重与突破
《雪葬》从话语表达、形象塑造和意蕴开掘三个层面,都有出色的表现。都借助地域性又突破地域性。
在话语表达层面,地域气息的营造,语言的灵动、幽默诙谐,表现手法的圆熟,结构与人物命运的有机关联,作者对题材的驾驭能力与艺术控制能力等等,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比如,赵天佑曾经生活过的赵家营和现在生活的柳沟河,既是不同的生活空间,也是与人物性格、命运相关的不同环境。赵家营是赵天佑童年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也是特定地域传统文化的象征。从作品中反复让赵天佑在最得意时聆听以“右派爷”为代表的赵家营文化的警示和对其进行价值评判来看,这两个地方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在赵家营是轮不到赵天佑出场的,而在柳沟河他则成了有实权有影响力的人物,有了展露他的性格的基础,可见这种空间的设置包含着深意。作者的这一用意却以赵天佑的倒插门很自然地解决了,在结构上天衣无缝,在内涵上没有变成对地域风情或者生活真实的简单反映。这正显示了作者在话语表达层面的成熟,对地域性的超越。另外,从作品的语言风格可以感受到,作家是真正沉潜在他的表现对象中的,特定地域农民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交际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幽默、智慧、机敏是其环境中所特有的,同时,作者又不仅是为了展示地方方言,而在揭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是文化,是心灵的“舞蹈”,是生命意识和人性的展现。另外,小说在事件叙述中的艺术概括能力和驾驭能力很突出,如“十二寡妇扫涝坝”的祈雨过程,写得十分生动传神,精彩纷呈。右派爷的来历和遭遇悲喜交加,令人深思又忍俊不禁。这一形象及其所蕴涵的艺术价值不仅属于柳沟河、云水市、西部,也属于全中国。
在形象层面,不但性格的鲜明性和人物的个性化相当出色,而且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示也很充分,对人物的本能、欲望、情绪、情感等等把握也很准确。人物形象塑造中,写赵天佑打破了好人坏人的模式,写了一个有少年痛苦经历、有欲望、有机遇的人的生命过程。作为新一代农民,作为致富带头人,他都是典型的。作为新一代农民,他有新的生活希望,也有苦恼,有作为农民的心理情感。作为农民改革家,他有其优点和缺点;作为农村干部,他有其特点和局限。这一形象似乎告诉人们,中国农民企业家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书本或者学校教出来的,他们走上历史舞台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被动性和随意性,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索的问题。除主人公赵天佑之外,右派爷、李义龙、吕作秀、茹丽华等都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其中右派爷这个形象具有特殊的个性,又有普遍的价值。“右派爷”的来历及其在后来的“奇遇”,极为荒诞又不失现实依据,使人在“含泪的微笑”中回味着世事的辛酸。同时,他更是一种象征和代表,是会说话的“大槐树”,在他的身上浓缩和凝固着时间和历史。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细微深刻,有创造性,也显示出对地域性的辩证理解。如李义龙作为被肯定的形象,吕作秀作为被鞭挞的对象,都有他们性格的基本规定性,但一点也不概念化,他们的行为和心理活动都有依据,与个人的地位、处境、利益、品行、人格、良心、欲望等密切相关。比如李义龙,是一位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领导,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作为也不出一个好人的基本准则和道德底线,但也并非不为自己利益考虑,并非没有微妙的情感波动,这种人性的深刻把握和洞察不是狭隘的意识所能做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没有静态的分析和心灵独白,但人物的情感倾向、心理活动等便跃然纸上。他们大都是凭直觉、凭感性、凭人生经验来处理事情,他们心理情感的表现形式是农民式的,是赵家营和柳河沟式的,这也是借重地域性又超越地域性的体现。
在意蕴层面,对西部农村生活中的“变”与“常”进行的思考,体现出作者自己的历史哲学观。也许,作者的历史观中包含着某些矛盾,对人物的行为的价值判断有着犹豫(比如对于赵天佑的行为的评价),但是,重要的是作者已经具备了历史意识,并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哲学的含义,这正是这部小说超越一般反映和追踪改革进程的创作模式、避免借题发挥自己肤浅见解而具有深刻意义的重要原因。小说由此也就超越了题材的限制和描写对象的地域性限制,着眼于历史、文化与人性的层面,因而通达某些带有普遍性、人类共同性的境界。比如,作品对文化传统与人物性格关系的揭示中,就具有较深的哲理意蕴:赵天佑的童年痛苦经历,并没有使他日后走向异端,他仍然不失赵家营后生的本分,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这种经历的印迹却成为日后他不断想要成为一个“人物”的潜意识,一种心理动力。他并不贪财,有钱时十分大方,这大方中既有农民的厚道,也有某种心理的满足,因为潜意识中,他更想成为普通人眼中的特殊人物,老想着衣锦还乡,为赵家营家族再添辉煌。所以他不十分爱钱,而更爱虚名,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心,不是一般的炫耀,而与谋求他的人格尊严相联系,与潜藏很深的心理欲求相联系。这里有着赵家营文化深深的痕迹,也有童年生活对他性格扭曲的影子。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所做所为的一些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动机。这一切,都依赖于作者对地域性的突破和超越,并把它转化为艺术成果。
《雪葬》等甘肃作品在改变着文坛对西部(甘肃)文学的印象。西部作家以其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体验,发现了现实中深刻的矛盾,发现了生活中人性的裂变;西部(甘肃)作家在自己的大地上辛勤耕耘而获得丰收,他们必然令人刮目相看。
西部文学不仅提供了读者不熟悉的生活场面、不了解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内容,而且提供了关于文学创作的普遍的启示。西部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精神,使我们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理论产生新的质疑,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重新思考。西部文学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谁之罪的质问,是古老的命题却有新的内容,这是西部人文精神的表现。
那些被表面的急剧变化所掩盖的生活底蕴,在西部作家的作品中被正视和突现;那些因各种诱惑而失落的文学精神在西部作家中还保留着;那些被证明是文学真理的创作方法在西部小说中被坚守着。借重西部地域性而又突破和超越地域性,西部文学创作所提供的经验将成为构筑整个中国文学精神大厦不可替代的要素,西部文学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特殊的艺术和思想资源。
标签:地域性论文; 雪葬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人性论文; 读书论文; 自杀论文; 赵天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