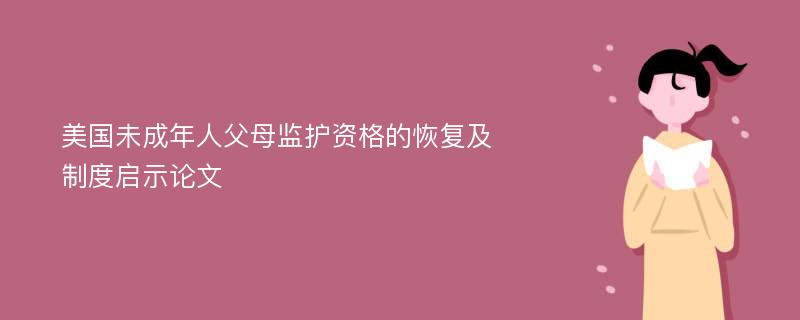
美国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的恢复及制度启示
冯 恺*赵律玮
内容摘要 :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资格被剥夺后,在适格的条件下可得以恢复。美国法强调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要求各州对监护资格受剥夺之父母进行“合理努力”,并针对相关流程及服务内容设置具体规则,旨在矫正问题父母和实现家庭团圆。我国《民法总则》第38条虽已确认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制度,但其立法根据和实施机制不够充分,关于“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标准过于抽象,也未考虑国家公权力的进一步介入。鉴于《民法总则》第38条的未决问题,美国法的成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关键词 :父母监护资格;合理努力;家庭恢复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允许国家公权力介入儿童保护已渐成各国的立法趋势,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制度便是其中表现之一。未成年人临时监护的实现涉及两个基本环节:一是在符合法定情形时,经由一定程序使受侵害未成年子女和家庭相“分离”,此意味着临时监护的发生;二是此种“分离”并非终极性的选择,仍可通过一定合理努力,使未成年人“回归”家庭或作其他形式的安置,这是临时监护的结束。两个机制的协同运作,使得未成年人在原家庭出现不稳定因素时及时离开危险,又在家庭环境恢复正常时回归家庭,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谋求儿童和家庭的共同发展。我国学界和法律实践多关注家庭“分离”即父母监护资格被剥夺问题,对家庭“回归”也即父母监护资格恢复问题的研究不足,《民法总则》第38条关于父母监护资格恢复的规定仍存在若干适用问题。与之比较,美国历经长期的立法发展和司法完善,在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恢复问题上积累了大量的成熟经验。根据其官方统计,近一半未成年人在父母监护资格被剥夺后最终又回归家庭,表明监护资格恢复制度在良化家庭秩序中发挥了正效应。[注] The AFCARS (Adoption and Foster Care Analysis and Reporting System) Report No. 23: Preliminary FY 2015 Estimates as of June 2016.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pp.1-3. 比较法上的良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 、美国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恢复的制度源起
(一)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制度的确立
随着现代法治的推进,儿童权利保护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关注,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制度随之得以确立和发展。1974年《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联邦和各州有权在儿童遇到危急情形时将其带离家庭进行临时监护。此后,为了回应法律实践中暴露的种种问题,美国国会不断更新立法以弥补原有制度的缺陷。根据1997年《收养与安全家庭法案》(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的规定,如果儿童在过去的22个月内有15个月处于临时监护下,各州应立刻提起对原父母监护人的撤销监护权诉讼。[注] Katherine A. Hort, Note, “Is Twenty-two Months Beyond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ASFA's Guidelines for the Termination of Parental Rights, Fordham URIB. L.J. Vol.28, 2000, p.1881. 同时,在父母监护人资格被撤销后,儿童离开家庭后的60天内,各州必须为了帮助儿童回归家庭进行各种“合理努力” 。[注] 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 of 1997, 131:Id. § 1356.21(b)(1), (d). 1980年《收养救助与儿童福利法案》(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进一步规定:接受联邦基金的各州应为儿童脱离临时监护进行“合理努力”,为原监护人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以使儿童回归原家庭。[注] 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AACWA) of 1980, Pub. L. No. 96-272, § 471 (a) (15), 94 Stat. 500, 503. 这些规定在未成年人临时监护一般制度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以“合理努力”为核心的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制度。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为儿童提供了重要的个人发展环境。如果不能为儿童找到更为健康的成长环境,切断儿童与原本家庭的联系就是非必要之举。从临时监护的实践来看,为儿童寻找收养家庭等安置方式往往耗费大量的政府和社会成本,而对问题父母进行教育和矫治的成本则相对较低。基于此,尽可能帮助未成年子女脱离临时监护和回归家庭成为美国法中的一种主流趋势,各州普遍将回归家庭作为优先选择的永久性安置方式。譬如,根据北卡罗莱纳州2011年数据统计,在儿童脱离临时监护后获得的安置方式中,家庭团圆居于首位,占比高达46.5%,其次才是收养(26.5%)和其他方式。[注] North Carolina Di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Family and Children's Resource Program, “Reunification in North Carolina: How Are We Doing”, Children's Services Practice Notes, Vol.18, 2013, p.1. 联邦儿童福利局的调研结果表明,帮助父母参与国家、州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以恢复家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州政府通过提供更为精准和针对个案的评估、计划和服务,能够为每一个可能重新团圆的家庭提供更多切实的机会。[注]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Family reunification: What the evidence show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2011, p.4. 因此,修复原父母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实现家庭的恢复和团圆,成为美国各州为儿童制定个案计划的重点,也成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和实践中最受关注的部分。
(二)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恢复的理论前提
1.父母对儿童享有基本的、不可侵犯的监护权和抚养权。美国最高法院在塞特斯基诉克莱默案的判决中写道:“亲生父母养育、看护、管理儿童的基本自由权利,不会因为他们并非模范父母或者暂时将监护权转移给了州政府而彻底丧失”。[注] Santosky v. Kramer, 455 U.S. 1982, pp.745-753. 从儿童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父母应当担任起养育子女的责任;正常情况下,也只有父母有权养育和管理子女的一切事务,其他人包括国家在内都不可能直接拥有此项天然的权利。即便父母的监护权在特定情形下受到暂时性限制,权利的自然基础也并未丧失。出于对这项基本权利的尊重,在未成年人脱离临时监护问题上,美国法优先考虑让儿童回归父母的监护。
2.大部分父母并非恶意。德·弗朗西斯指出,现代社会的儿童虐待问题极少出自暴虐的故意,大多数儿童受虐待或者忽视,主要源自“有问题”的父母,此类父母自身存在某种个性缺陷,容易外化为对被监护人的失格行为。[注] 杨敏:《儿童保护:美国经验及其启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某种意义上,唯有对这些问题父母进行矫正,消除其行为失格的内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受害儿童的不利处境。实证数据也表明,问题父母一定程度上能够被矫正和继续养育自己的子女。
3.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被亲生父母所养育和尽可能不与父母相分离,普遍被认为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并成为法院考虑未成年人利益时的第一要素。[注] Raymond C. O’Brien, “Reasonable Efforts and Parent-Child Reunification”, Michigan State Law Review, 2013, p.1034. 为父母提供一定的补救机会,通过矫正父母的问题来实现家庭团圆,令儿童得以继续生活在原生家庭中,无疑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正如戈登所指出的那样,使儿童尽快回归变得安全的家庭之中,最大程度地减少因亲子关系受扰乱给他们带来的心理损害,的确有助于对他们的保护。[注] Robert M. Gordon, “Drifting Through Byzantium: The Promise and Failure of the 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 of 1997”, MINN. L. REV. Vol.83, 1999, pp.653-654.
二、美国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恢复的制度运行
(一)监护资格恢复的启动——决定应否进行“合理努力”
鉴于存在的种种批评,美国立法及理论上力图克服家庭恢复制度的不足。根据《促进收养与儿童福利法案》的规定,儿童福利机构以家庭团圆为目标进行“合理努力”六个月后,如果发现此种努力无法产生良好的效果,家庭并未显现好转的端倪,则必须制定另一项“并行计划”,确保儿童在最终无法回归家庭的情况下有另一种良好的安置。[注]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Reasonable Efforts to Preserve or Reunify Families and Achieve Permanency for Childre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2016, p.4. 对部分问题父母而言,即便他们已经完成了相应的培训课程甚至通过了测试,让儿童回到他们身边仍然是危险的。诚如学者克里斯蒂纳所言:“合理努力的积极效果似乎只能发生在这些父母身上:心眼不‘坏’但有外部因素问题的父母,以及心眼虽‘坏’但真诚渴望改变且有变好潜力的父母。”[注] Cristine H. Kim, “Putting Reason Back Into the Reasonable Efforts Requirement i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ases”, U. ILL. L. REV. 1999, p.314. 在父母问题难以消除的情况下,进行合理努力只会无谓地耗费金钱、时间和精力,进而发生戈登所言的恶果:临时监护不断被延长,儿童不得不辗转于不同的临时监护家庭或者机构之间,与原本家庭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疏远,并无法得到永久性安排。[注]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Long Foster Care Stays Reduce Children’s Permanency Chances”, Child Law Practice, Vol. 32, No. 10, 2013, p.159. 如果趁早放弃家庭恢复的努力,将工作重心尽快转向其他的永久性安排上(如收养),则可避免儿童长久滞留于临时监护之中,减少儿童与父母被迫重新接触的痛苦。[注] Robert M. Gordon, “Drifting Through Byzantium: The Promise and Failure of the 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 of 1997”, MINN. L. REV. Vol.83, 1999, pp.653-654. 此种情况下,及时放弃家庭恢复的努力反而是对涉事家庭的另一种“合理努力”,因此成为法院和福利机构在综合考虑目标家庭的各项情况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注] In re Heather C., 751 A.2d. p.456.
燃气企业因为受到自身特性的影响,在开展财务信息化建设工作时,根据需要可以将不同地点、区域具有共性较强的、重复率高的、易于标准化和流程化的财务业务或职能从分、子公司中剥离出来,之后将其融合到信息平台中,实现信息传递和共享。只有这样,才能将规模效应以及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减少财务运行成本,提升财务运营效率以及服务质量,从而降低财务运行风险,给燃气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
各州儿童福利机构作为家庭恢复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将针对个案区分不同情形决定应否进行“合理努力”。一旦作出进行“合理努力”的决定,儿童福利机构应针对受害未成年子女拟定个案计划,进行“合理努力”帮助他们回归家庭。联邦政府有权对各州实施相关法律的财政预算进行审核,确认各州实际执行的情况并据此发放财政补贴。各州为了获得联邦财政的支持,通常也会提出各种切实有效的具体方案,努力帮助父母监护人恢复监护能力和促进家庭团圆。
(二)监护资格恢复的基本环节
1.个案评估与计划(assessment and case planning)。根据美国联邦法的规定,各州必须为处于临时监护下的未成年人制定个案计划(case planning),[注] 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of 1980 (P.L. 96-272), 42 U.S.C. 671(16). 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定未成年人在临时监护期间将居于何种环境,由谁具体行使临时监护权以及其教育和健康保健得到何种安置;二是为儿童脱离临时监护制定“永久性计划”,此种计划安排可以是回归家庭、由其他亲属抚养或他人领养等形式。具体采用何种安排形式,由各州根据法律规定和个案情况作出决定。其中,未成年人回归原家庭是各州普遍考虑且占据比例最高的方式,往往只有存在法定情形时才会放弃回归家庭的努力。[注]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Reasonable Efforts to Preserve or Reunify Families and Achieve Permanency for Childre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2016, p.1.
3.幸福。“幸福”的判定较之其他因素更为困难。尽管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和标准不尽一致,美国还是将此点作为一项司法评价标准,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儿童的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作为儿童应当享受怎样的生活和得到怎样的幸福尚不具备充分的意识,因此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在“幸福”的认定问题上,法院往往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考察其父母是否真正发自内心地给予他们无私的爱,因为只有“稳定和真挚的爱,才能真正使儿童从受虐的伤痛中逐渐恢复”[注] Iowa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Returning Children Home Safely and Permanently”, Iowa: The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Division, Iowa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2008, p.3. ,亲子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儿童在父母的陪伴下获得“幸福”。
2.签订家庭契约(family engagement)。当个人评估与计划得以完成并经法院通过后,负责案件的社会工作者与原监护人订立契约,以确保相关计划得到落实。订立家庭契约的基本目的在于:原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仍能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发生完全破裂。契约的内容一般包括:社工同原监护人保持定期的联系;定期安排儿童同父母见面;临时寄养家庭对原家庭的恢复提供各项便利;专业顾问对家庭恢复进行一定的指导等。[注]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Reasonable Efforts to Preserve or Reunify Families and Achieve Permanency for Childre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2016, p.4.
怪味胡豆中不具有其他怪味食品的酸味,说明用“集酸、甜、麻、辣、咸、鲜、香七味于一体”的复合味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怪味食品的风味特征。因此,有必要参考豆味、烟熏味和青草味的研究方法[28-30],通过对不同品种的怪味食品进行全面的定量描述分析,建立出怪味的感官描述词,对于理解怪味和开发怪味食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实践效果来看,家庭契约的订立对促成家庭恢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家庭契约明确了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具有确定性效力。在现实中,有些父母出于对国家福利机构的不信任而不愿意配合矫正工作,契约的订立成为他们的“定心丸”。另一方面,契约的订立使父母监护人意识到自己的参与具有切实可见的价值,因此更愿意配合矫正工作。
在韩国,教师讲课大多以韩语授课,但是在课前会给学生们提前发送课上讲解的课件,课件是英文的。让学生在提前预习课堂讲解内容的同时,也提高了英语能力。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伴随着我国“城中村”改造,兴起了大批的居住建筑。一方面建筑材料的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另一方面,人们居住环境在不断地改善,为了营造一个适合生活、生产及开展各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会不断的消耗能源。建筑的能耗非常严重,约占社会总能耗的1/3,我国是人口大国,居住建筑规模巨大,其耗能的总量占总建筑能耗的57%左右。如果不注重居住建筑节能,房屋建得越多,能源耗费就越大,将会给社会和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能源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居住建筑节能十分迫切。
美国实现父母监护资格恢复的过程,每一步均显示了慎重性:从最初对儿童家庭背景和家庭关系的调查和评估,到儿童回归家庭后的后续性服务,都从个案的具体问题和需求出发进行细致设计。同时,相关工作的专业性,也需要儿童福利机构配备一定比例的专业人员。譬如,密歇根州要求为每一目标家庭配备两名专业工作人员,分别负责专门问题的矫正治疗和家庭关系处理的技巧教育;其中一名为硕士毕业,另一名为学士毕业,对其专业领域也有特定要求。[注] 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Reasonable Efforts to Preserve or Reunify Families and Achieve Permanency for Childre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2016, p.12.
(三)判断能否恢复监护资格的基本原则
“合理努力”的法定期限届满后,各州法院将对个案计划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复审。父母的监护资格能否得以恢复,其未成年子女能否回归家庭,须由法院作出最终裁定。考虑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法院通常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作出判断,即安全(safety)、永久(permanency)和幸福(well-being)[注] Cheng, T. 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unifica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long-term Foster Car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Vol.32, 2010, pp.1311-1316. 。
1.安全。存在家庭虐待和忽视等不利情形时,儿童的生活环境变得不安全,从而对儿童的正常发展产生障碍。在此意义上,儿童回归家庭的首要影响因素即安全。决定应否恢复父母的监护资格时,法院考虑的问题往往包括:导致家庭不安全的因素是否已消除;儿童能否彻底远离来自家庭内部的威胁;儿童福利机构和社区在解决安全问题上做了哪些努力及其实际效果如何等。而且,有关安全性的考察不仅仅针对原监护人进行,还针对整个家庭乃至家庭所在的社区而为之,以确认原家庭的总体环境对受害儿童已变得安全。
2.永久。恢复正常家庭所需的安全和稳定不能是一时的,而应具有一定的持久性。法院对是否“永久”作出认定时,往往需要观察子女和父母在临时监护期间的具体互动,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无保持长久稳定的可能性,以及父母有无能力理性应对子女可能出现的生理或心理问题等。为了得出一个合理的判断,法院需要对父母的经济情况及其养育子女的能力进行多项认定和评估。这一工作复杂而困难,现实中一部分监护权被剥夺的父母,多因为难以证明能永久、稳定地照顾子女而丧失家庭恢复的机会。
化学植筋技术,因为其所使用的设备简单,并且操作过程简易,效率高,投入少,在建筑行业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本文所述的水利工程中植筋技术的应用取得的使用效果非常良好,在今后的工程当中将会被广泛推广。
个案计划应基于一定的调查评估结果而确定。从临时监护的制度实践来看,令儿童处于危险境地的成因复杂多样,如果不能找出引发家庭虐待、忽略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儿童即便能够回归家庭,原有问题仍会出现,令其陷入重复性临时监护的恶性局面。因此,对每一个问题家长或家庭的调查和评估至关重要,此种调查评估也将直接决定着个案计划的内容,即今后应如何为该家庭进行“合理努力”,为矫正问题父母和实现家庭恢复作出何种具体的安排。
三、美国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恢复的制度问题
进行“合理努力”后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方可实现家庭恢复的立法理想,然而,美国各州的个案实践并不能一一达到预期的效果。受到特定因素的制约,一部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资格难以通过官方的合理努力得以恢复。
(一)父母自身原因影响“合理努力”的实践效果
1.存在贫困、成瘾、身心疾病等情形。对于家庭恢复而言,贫困是最容易诱发恶性循环的因素之一,许多儿童即因家庭处于贫困境况、父母无法提供良好的居住和教育等基本照护条件而被带出家庭。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美国的贫困儿童数量达到1550万,大约每5名儿童中就有1名儿童处于贫困之中,而贫困家庭更容易在养育子女方面发生失误,父母稍有不慎就可能再次受到指控。[注] Kathleen A. Bailie, “The Other ‘Neglected’ Parties in Child Protective Proceedings: Parents in Poverty and the Role of the Lawyers Who Represent Them”, Fordham L. Rev. Vol.66, 1998, p.2294. 从此点检视,原父母监护人即便参加了各种矫正项目,如果贫困的境况没有得以根本改变,最后仍可能终极性地丧失对子女的监护资格。
同时,对药物或者酒精等物质成瘾、患有重大身体疾病(如残疾)和心理疾病(如重度抑郁)的父母而言,期待在短期内彻底地实现康复的目标并不现实。根据《收养与安全家庭法案》的要求,法院须在法定期间后作出是否撤销父母监护资格的决定,此类父母因身心疾病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继续照料孩子,往往会面临监护资格被撤销的诉讼。[注] 42 U.S.C.A.§ 675(4)(E).
2.父母主观上拒绝配合。实践中,一些父母主观上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虐待、忽视行为有何不妥,无法理解自己为何需要被矫正,因此对官方的合理努力和矫正工作予以排斥。如果父母自身拒绝配合,外界进行再多的努力也于事无补。各州法院在认定合理努力的期望目标是否达成,以决定父母是否适合继续拥有监护权时,一个重要的审查因素便是父母的配合程度。[注] 42 U.S.C.A.§675(5)(E)(iii). 即便父母拥有体面的工作或更好的居住条件,如果他们主观上不愿意配合和参与以矫正为目的的服务项目,法院也有权以此为由终极性地剥夺其监护资格。[注] Department of Family Serves. v. Currier, 2013 WY 16, 295 P.3d 837, 839 (Wyo. 2013). 譬如,在In re Katelynn Y.案中,儿童福利机构终止对母亲一方停止合理努力,但继续对父亲一方提供服务,因为母亲“从不参与服务项目”,而父亲“不仅在监禁期间内参加了服务项目,还在出狱之后主动寻求各种服务的帮助”。[注] In re Katelynn Y., 147 Cal. Rptr. 3d 423, 426 (Ct. App. 2012).
(二)经费不足及责任缺失影响“合理努力”的立法目标
1.经费不足且比例失衡。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至少46个州的主要社会服务开支发生大幅缩减,儿童保护经费问题突出,如何运用有限的经费成为摆在各个福利机构面前的难题。[注] Bruce A. Boyer & Amy E. Halbrook, “Advocating for Children in Care in a Climate of Economic Reces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nd Child Maltreatment”, Nw. J. L. & Soc. Pol’y. Vol.6, 2011, p.307. 未能达成家庭恢复目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源于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为了将有限资源发挥最大实效,各州往往选择性地将资源用于那些更有意愿、更可能被矫正和造福儿童的父母。与之相应,法院在审议应否对问题父母进行合理努力时,也常常不得不考虑经费情况,因为“在这个资源紧缺的时代,各州可以将有限的经费用于最有可能恢复团圆的家庭”[注] In re Gabriel K., 136 Cal. Rptr. 3d 813, 819 (Ct. App. 2012). 。因此,越是欠缺财政支持的州,法院在决定应否进行合理努力时越是慎重和“吝啬”,也越可能作出否定进行合理努力的裁决。
然而,立法上应否确立监护资格恢复制度的问题,在学理上仍未盖棺定论。究其根源,多因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资格被撤销后,如再行变更监护关系以恢复其监护人资格,对原监护人的震慑和威慑作用将发生一定克减。早期即有学者主张确立特别制度以缓解其副作用,此以佟丽华提出的中止制度为代表,主张原监护人待资格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向法院申请恢复其监护资格,两年内未提出或其申请被驳回的,原监护人丧失监护人资格。[注] 佟丽华:《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思考和建议》,载《法学杂志》2005第3期。 在《民法总则》出台之前,各种专家意见稿围绕父母监护资格恢复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只有法学会版中设置了监护资格恢复制度条款(“法学会稿”第32条),且一度成为整个监护制度中最受批评的一条。部分学者主张应谨慎恢复父母监护权。[注] 王慧:《<民法总则>撤销父母监护权条款的罅漏与完善》,载《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持强烈反对意见的学者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其认为: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依法被撤销,新监护人也随之被指定后,被打乱的监护秩序已经恢复,不宜仅仅因“确有悔改”即恢复其监护人资格,否则会再次打乱刚刚恢复的监护秩序;而且,所谓“确有悔改”极难通过证据认定,终止新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必然挑起矛盾冲突。[注] 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第5期。 然而,《民法总则》最终选择了支持性方案,在第38条中确立了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制度:“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在桥上筑起亭台楼阁,是为了给行人一个暂避风雨和歇脚观景的地方。徽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润,多雨水,尤其春夏两季,天气变化更是无常,前脚出门还晴着,后脚出门就下起雨来。
2.方案不合理时难以归责。应否进行“合理努力”和提供矫正服务,进行的“合理努力”有无成效以及父母监护资格应否最终被剥夺等重要问题,一般由各地儿童福利机构负责作出决定和形成具体方案,并经由当地法院审查和裁决。如果工作方案不合理,就会影响到家庭恢复目标的实现。然而,儿童福利机构和法院无须对方案不合理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其基本根据在于:此种服务虽然是联邦法规定必须执行的,但它在本质上属于“福利”和“获益”,而非父母的“权利”。如在Suter v. Artist M.案中,Suter的父母控告儿童福利机构未遵循《收养救助与儿童福利法案》关于合理努力的要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请求不予支持,并认为:各州及其下属福利机构对父母进行合理努力和矫正,本身并非一种“在联邦法上能够强制执行的权利”,父母不得因各州机构未能做出足够合理的努力而提起诉讼。[注] Suter v. Artist M., 503 U.S.pp.347-348 (1992). 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在审查In re Katelynn Y.案时也指出:“帮助家庭恢复的服务是一种福利性的行为而非公民的宪法权利,儿童福利机构有权决定何时终止提供这种服务。”[注] In re Katelynn Y., 147 Cal. Rptr. 3d 423, 426 (Ct. App. 2012). 这一局限性长期以来为美国民众所诟病。[注] Courtney Serrato, “How Reasonable are Reasonable Efforts for the Children of Incarcerated Parents”, Golden G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46, 2016, p.177.
(三)围绕“合理努力”的批评及可能应对
鉴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进行“合理努力”的效果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发生一定的克减,因此招致对这一制度的诸多批评。除了前述父母难以矫正、资金不足、儿童福利机构和法院处理不当以及为家庭提供的服务不够充分等实践问题之外,很多评论者将抨击的对象指向了“合理努力”本身的合理性。譬如,德芝向众议院委员会成员指出:“合理”一词常常被读作“合理努力”,从而拟制出一种境况——儿童被置于危险之中,以家庭保护和团圆的名义受到再次虐待……简言之,我们常常进行“无用的努力”,这本质上是不合理的。[注] Kathleen S. Bean, “Aggravated Circumstances, Reasonable Efforts, and ASFA”, Boston College Third World Law Journal, Vol.29, 2009, p.114. 宾斯菲尔德也对国会指称:各州正在“恶劣”的情况下进行“合理努力”,儿童或者被再次置于危险的家庭环境之中,或者因家庭恢复工作持续不断而长久居于被寄养的境地。[注] Go Binsfeld, “Barriers to Adoption: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 on Hum”, Resources of the H. Comm. on Ways & Means, 104th Cong. 1996. P.37. 尤其是,当存在客观上无法实现家庭恢复的因素时,如果各州过分强调让受虐待和受忽视的儿童回归家庭,就可能以家庭保护的名义危害儿童,[注] H.R. REP. No. 105-177, p.8. 从而发生学者所批评的后果,即各州以牺牲儿童的安全或心理健康为代价追求“合理努力”目标的实现,[注] Michael J. Bufkin, “The ‘Reasonable Efforts’ Requirement: Does It Place Children at In-creased Risk of Abuse or Neglect”, U. LouIsvt LLEJ. FAM. L. Vol.35, 1997, p.374. 使儿童继续长久地滞留于寄养状态或者被遣返回不安全的家中。[注] Deborah L. Sanders, “Toward Creating a Policy of Permanence for America’s Disposable Children: The Evolution of Federal Funding Statutes for Foster Care from 1961 to Present”, INT'L J.L. POL’v & FAm. Vol.17, 2003, p.222.
3.提供具体服务(service delivery)。对父母监护人进行何种努力和提供何种具体服务,不仅取决于各州对“合理努力”的理解,还要根据个案计划以及订立契约的内容予以确定。例如,根据纽约州的相关规定,儿童进入临时监护后,原监护人有权获知与恢复家庭关系相关的一切信息,包括与负责本案的社工取得联系、参加家庭会议、参与州政府针对监护人组织的各项社会服务等。[注]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You Don’t Have to Stop Being a Parent While You are in a Residential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Facility”, New York: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2016, p.2. 根据多数州的实践经验,儿童福利机构为矫正原监护人所提供的具体服务主要包括:(1)定期安排父母和子女见面;(2)认知-行为矫正训练;(3)定期的心理诊断与治疗,如戒毒或者摆脱其他物质滥用的康复疗程;(4)组织安排家庭恢复活动,指导父母如何合理行使监护权和培训教育儿童的技巧等。[注] Corcoran, J. “Family Interventions With Child Physical Abuse and Neglect: A Critical Review”,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Vol.22, 2000, pp.563-591. 同时,为了防范儿童重复进入临时监护,一些州在儿童回归家庭之后将进一步提供后续性服务。例如,提高父母(特别是存在物质滥用问题的父母)处理子女问题的能力,帮助目标家庭与社区、其他社会组织构建纽带和互通有无。
在美国法中,进行“合理努力”是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制度的核心,决定应否进行“合理努力”也被视为启动这一制度的起点。联邦法授权各州自行决定应否对原监护人进行“合理努力”,并对“合理努力”的具体内容作出解释和认定。譬如,俄勒冈州法院在K.D.案中声称:当地人权服务机构在个案计划中规定的服务,“不能仅仅是形式上的帮助,而应为具体而真诚的服务”,这些努力“应当在合理时间内消除致使儿童被带出家庭的根源”,并“能够使家庭团圆成为可能”。[注] State ex rel. Juvenile Dep’t of Jackson Cnty v. K.D., 209 P.3d 810 (Or. App. 2009). 为了更好地适用,国会试图澄清进行“合理努力”的要件,采取的措施包括规定了“合理努力”的除外情形。根据《收养与安全家庭法案》的规定,放弃“合理努力”的法定情形主要包括:父母存在杀害、严重虐待子女等犯罪行为,父母对受害子女的兄弟姐妹的监护资格已经被剥夺,以及具有兜底性的“其他严重情形”。[注] ASFA of 1997, Pub. L. No. 105-189, § 101(a), 111 Stat. 2115 (codified as amended at 42 U.S.C. § 671(a) (15) (D) (2006)). 对满足何种条件时方构成所指的“其他严重情形”,该联邦法并无进一步描述,完全交由各州诠释。为了克服规定的模糊性,一些州针对“严重情形”给出更详尽的定义,如佐治亚州允许在“父母将孩子置于包括但不限于遗弃、酷刑、长期虐待和性虐待等严重情形下”,放弃进行“合理努力”和实现家庭恢复的目标。[注] GA. CODE ANN. § 15-11-58(a) (4) (A) (2008). 存在法定事由的情况下,各州一般选择放弃帮助原监护人恢复家庭的努力,作出永久性安排时也不再将原监护人纳入考虑。[注] Kathleen S. Bean, “Aggravated Circumstances,Reasonable Efforts, and ASFA”, Boston College Third World Law Journal, Vol.29, 2009, p.225.
此外,法院针对个案行使自由裁量权,一定程度上亦有利于纠正法律适用中的偏差。譬如,根据联邦法的一般原则,存在“多个子女中已有父母监护权被撤销”的法定情形时,一般不再考虑启动家庭恢复程序,但法院仍会根据个案的特殊性作出弹性裁决。In re. K.L.J. & T.L.J.案中,当事人母亲共有7个子女,其中对4个孩子的监护权已被剥夺,1个孩子出生不久即告死亡,州机构依法将另外2个子女带出家庭。此种情形下,爱荷华州上诉法院仍颁发了进行合理努力的法令,要求州儿童福利机构为父母监护人提供矫正服务,因为,“如果这个母亲今后生了更多的孩子,这些服务或许对她有所裨益”。[注] In re Div. of Family Serves v. Smith, 896 A.2d. pp.188-190 (Del. Fam. Ct. 2005). 进行合理努力的考察过程,不仅让法院能够在判决剥夺监护资格时存在“清晰、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可能造福于当事人今后生下的其他孩子,一定程度上避免她将来再次与自己的子女分离。[注] In re. K.L.J. & T.L.J. No. 2-753/12-1102, p.1 (Iowa Ct. App. filed Sept. 6, 2012). 特拉华家事法庭在In re Division of Family Services v. Smith案中也指出:虽然该案中作为监护人的母亲已两次被撤销监护权,但是由于“父母可能已经在养育的技巧和能力上有所进步”,儿童保护机构仅凭两次被撤销记录即拒绝进行合理努力的做法欠妥。[注] In re the Matter of DIVISION OF FAMILY SERVICES v. Connie SMITH, 896 A.2d. pp.187-188.
四、我国《民法总则》第38条中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恢复的未决问题及美国法上的启示
(一)立法根据与实现机制不充分
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剥夺问题早在1986年《民法通则》中就得以确立,但长达30年之久未能启动而沦为“僵尸条款”,这严重影响了受侵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的颁布打破了这一僵局,它重申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剥夺问题,并通过第40条确立了父母监护资格的恢复制度,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确有悔改表现并且适宜担任监护人的,可以判决恢复其监护人资格,原指定监护人的监护人资格终止”。这一制度为父母监护资格受剥夺的未成年人提供了重返家庭的二次机会,对维持亲子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系统内选人用人巡察的情况看,干部队伍专业不专,业务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业务骨干看不懂行业内基本数据,依赖中介公司提供服务。为此,全系统要强化干部专业能力、专业精神,锻造干部实践能力、实干作风。要以“百名业务能手”培育为载体,全面加强系统业务能手培养,实现全系统干部“综合素质优良、工作作风扎实,岗位技能熟练、工作优质高效,业务规程娴熟、实战能力强劲”的目标,不断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与此同时,各州政府相关经费的分配比例也被批评不尽合理。当儿童进入临时监护后,各州可通过正当程序从联邦政府获得财政补贴,这一补贴并无上限[注] Will L. Crossley, “Defining Reasonable Efforts: Demystifying the State’s Burden Under Federal Chil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B.U. PUB. INT. L.J. Vol.12, 2003, p.274. 。然而,根据2000—2012年的统计数据,联邦政府用于非临时监护的儿童福利支出基本维持在17亿美元左右,处于不减不增的状态;用于临时监护的经费支出比例高达73%,但用于提供矫正服务等合理努力的经费比例仅占10%。[注] Am. Humane Ass’n. “Analysis of the President’s FY 2012 Budget 3”, Available at http:// www.americanhumane.org/assets/pdfs/children/fy-2012-budget-analysis-children.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1月6日。 显然,经费比例的失衡阻碍了各州推进合理努力和实现家庭恢复的正常步伐。
显然,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制度在《民法总则》中的确立,就其理论根据而言很难说已获得充足论证,甚至官方的相关立法解释也对此语焉不详。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的确立是权衡各方利弊的结果,[注] 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上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84页。 客观上也延续了《意见》的实践精神。较之《意见》相关规定,《民法总则》第38条添加了“监护人申请”和“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除外”两个限定条件,但仍存在若干问题。譬如,它脱胎于《意见》,却不加区分地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两种不同主体一并规定,无视《意见》专为未成年人而设,并非适合直接嫁接到成年人监护,以及未成年人监护和成年人监护遵循不同运作逻辑之事实[注] 李霞:《监护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 。更为突出的是,第38条仅赋予法院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未进一步在规范层面建构起具体的监护资格恢复制度。司法实践表明,实现监护资格恢复的主要问题是程序和评价机制的不健全。[注] 吴燕、季冬梅:《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研讨会综述》,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 年第5期。 父母监护资格被剥夺的受害子女进入临时监护状态后,应如何认定父母申请恢复监护资格的条件?按照何种具体流程实现家庭恢复的目标?如何定位儿童福利机构和法院各自的法律角色?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父母监护资格的恢复在终极意义上未必能为未成年子女带来更大利益。
3) 港内航道日平均流量229艘次,除港作拖船外1/2以上为占用主航道航行的渔船和中小型货船。由筲其岛两侧进出洋山港内航道的多为渔船和小型船舶,与主航道内正常航行的船舶存在交叉相遇,日均流量在60艘次以上,但该处并没有规划航道。
(二)认定条件有待细化
根据《民法总则》第38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父母申请恢复监护资格须以“确有悔改表现”为前提,但立法上并未进一步解释应根据何种标准作出具体认定。社科院项目组撰写的评注认为,可从主观和客观方面确认父母是否构成“确有悔改表现”:一是父母在主观上具有恢复监护人资格的意愿;二是父母客观上恢复了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并沿用《意见》第39条第2款规定的考察方式,即征求现任监护人意见,委托社会机构或组织在对父母监护意愿、悔改表现、监护能力、身心状况、工作生活情况等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评估报告,结合父母自己提供的证据做出综合判断。[注] 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 上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页。 同时,对法院的授权为“核准主义”方法,即使父母客观上具备了相关要件,法院仍保留对最终裁判是否恢复其监护资格的自由裁量权。[注] 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上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86页。 然而,将监护资格恢复制度的具体化交由《意见》承担的做法,其恰当性仍有待质疑,[注] 李霞、陈迪:《<民法总则>(草案)第34、35条评析》,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需要在法律上作出更为妥当的解释。
《民法总则》第38条关于监护资格恢复的除外性适用情形的规定也不尽周延。《意见》第40条第2款一一列举了父母不得恢复监护资格的除外情形:(1)性侵害、出卖未成年人;(2)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六个月以上、多次遗弃未成年人,并且造成重伤以上严重后果;(3)因监护侵害行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然而,《民法总则》第38条并未延续《意见》的界定模式,而使用了“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总括性表述。由此,司法上适用第38条时仍不得不参照《意见》的具体规定。与之比较,美国法所采“列举+兜底条款”的规定模式更为周延,即一方面具体列举包括“父母存在杀害、严重虐待子女等犯罪情形,以及父母对受害子女的兄弟姐妹的监护权已经被剥夺”在内的放弃“合理努力”的法定事由,另一方面又设定兜底性条款,使其范围延伸到“其他的严重情形”。从所列举事由来看,父母实施犯罪的对象也不仅仅包括诉讼所涉子女,同时包括其他被监护子女在内,较之《民法总则》第38条所指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对象范围更为宽泛。
看到这样几幅画,老樟树下的喧闹突然死一般的寂静了。周老相公、周大毛,周阿龙等没有一个人说话,李老师一下子乐了,说,怎么了,怎么了,想不到吧想不到吧,咱岭北出人才啊,出了个画画小天才啦!
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在认定父母构成“确有悔改表现”之后,应否基于特定的价值原则最终决定恢复父母的监护资格呢?此点也未在《民法总则》第38条的考虑范围之内。尽管《意见》要求考察父母客观上是否恢复了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但此种考察及其实现的方式并非基于明确的法律原则。如前所述,美国法院在最终决定是否恢复父母的监护资格时,通常会遵循三个判断标准:安全、永久和幸福。事实上,处于我国司法实务一线的检察官和法官也普遍认为,撤销父母监护权后的儿童后置安排问题,是他们决定是否适用这一干预措施的重要制约因素。[注] 王慧:《<民法总则>撤销父母监护权条款的罅漏与完善》,载《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因此,无论是撤销父母的监护资格,还是恢复父母的监护资格,目标均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家庭利益,即使其能够“安全、永久和幸福”地生活于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我国法应对相关原则予以申明,为法院决定应否恢复父母的监护资格确立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
(三)未允许国家公权力的更多介入
从历史发展来看,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制度本质上表现了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即未成年人监护不再被简单地归入家庭的私事,而被认为是父母、社会和国家的共同责任,国家凭借各种社会公权手段、社会公共机制介入未成年人监护中,实践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注] 曹诗权:《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演进规律与现实走向》,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在美国法中,法院作出应否恢复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的决定,仅仅是整套制度运行的终点,与之相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国家应为受害儿童的家庭恢复进行一定的“合理努力”,以矫正问题父母和促进家庭团圆。在此理念支配下,美国法围绕监护资格恢复的启动(决定是否进行合理努力及其例外)、程序、判断标准等具体问题一一作出了制度回应。从实践效果来看,通过进行“合理努力”这一“阀门”,对无能力进行自力救济的问题父母予以社会矫正,能够更有力地促成家庭的良性恢复。反观我国《民法总则》第38条的立法意图,一定程度上仅仅要求立法者被动等待丧失监护资格的父母“自行悔改”,并未考虑通过介入更多的国家公权力以促成“悔改”的结果。在这一理念支配下,现有第38条自然也未对促成问题父母“悔改”提供制度性和程序性支持。
在美国,过半比例的受害未成年子女最终得以返回原家庭,这一良性后果归结于通过国家公权力矫正问题父母的努力。为了保障《民法总则》第38条的有效实现,我国应允许国家公权力的更多介入,并确立具体运行机制促进家庭恢复目标的实现。其核心问题包括设立父母矫正机制,即通过外力手段促使问题父母作出“改良”,而非仅仅依赖于父母的自我“悔改”。基于此,法律须进一步确立实施父母矫正的具体流程,让各方了解该父母作为监护人的责任意识是否得到改善,其监护能力是否得到矫正和恢复,以判断最终有无必要恢复其监护权。我国可借鉴美国法经验,在允许公权力进一步介入的前提下开展父母矫正工作:(1)针对申请恢复监护资格的个案进行调查评估,制定适合个案的父母矫正方案;(2)订立合同,就与社工定期联系、安排与子女定期见面、专业顾问指导等事宜作出安排;(3)明确矫正的内容,如矫正训练计划、心理诊断与治疗、安排家庭恢复活动等。父母矫正程序完成后,相关评估结果将成为法院审查决定父母是否“确有悔改”的重要依据。
当然,为了实现父母矫正的目标,我国法中应进一步明确儿童福利机构在父母监护资格恢复中的法律职能。在美国,儿童福利机构和法院均对父母监护资格的恢复发挥重要作用:儿童福利机构制订和推行以“合理努力”为核心的家庭恢复计划,法院则对相关重大问题进行审查和最终决定是否恢复父母的监护资格。从制度的启动到运行,儿童福利机构的作用不可或缺:一方面,它有权区分不同的情形,决定应否启动监护恢复程序和进行“合理努力”;另一方面,它有权根据为受害儿童拟订的个案计划,对问题父母进行矫正和提供具体服务。与之比较,我国《民法总则》第38条仅仅突出了法院在父母监护资格恢复过程中的作用,法院无须儿童福利机构的协助即可自行决定应否恢复,而作为重要执行主体的儿童福利机构的法律角色却明显缺位。在缺乏儿童福利机构持续性专业支持的情况下,法院不得不针对个案逐一审查,法律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累积量具有与随机变量线性组合相关的特性,所以可利用在电力系统的线性模型中。功率注入和线路流量的潮流方程用非线性方程表示:
五、结语
对未成年子女父母监护资格的剥夺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对受侵害子女的后续安置。从美国法比较经验来看,父母监护资格的有条件恢复和促使儿童回归家庭,是诸多安置方式中占据比例最高、最为有效的一种;家庭恢复制度的实施,使得未成年人临时监护的基本理念得到贯彻——暂时将儿童带出危险的环境,又在时机合适时令儿童回归家庭。我国《民法总则》第38条虽在基本法层面上确认了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的恢复问题,但内容仍然过于粗疏,应结合比较法上的经验做几方面改进:一是进一步明确立法根据与实现机制,增强现行规定的可信性与可行性;二是进一步细化“父母确有悔改”的认定条件,对除外性条款作出更为周延的解释,并确立判断应否恢复父母监护资格的基本价值原则;三是允许国家公权力进一步介入,发挥儿童福利机构在父母监护资格恢复中的基础性作用,确立具体的父母矫正机制,通过外力促成“确有悔改”的良性后果,最大程度上实现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和家庭团圆的目标。
Restoration of Parental Guardianship of Min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stitutional Inspiration
Feng Kai Zhao Lv -wei
Abstract : After the parental guardianship of minors is deprived, it can be restored under proper conditions. The US law emphasizes the involvement of State power and requires the states to make “reasonable efforts” to parents whose guardianship is deprived. Specific rules are set for the procedures and the service provis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rrection of problematic parents and realization of family unification. Article 38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of China confirms the restoration of parental guardianship; however, its legislative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re insufficient.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requirement of “true repentance performance” is still abstract. The further involvement of State power hasn’t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Around the outstanding issues of Article 38, the mature experience of US law is worthy to be learned.
Keywords : Parental Guardianship; Reasonable Efforts; Family Unification
中图分类号 :D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76(2019)01-0035-10
DOI :10.19563/j.cnki.sdfx.2019.01.005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国法制出版社法学部编辑,法学硕士。
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反校园欺凌立法的困境及进路研究” (项目编号:17YJA820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赵 毅 )
标签:父母监护资格论文; 合理努力论文; 家庭恢复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论文; 中国法制出版社法学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