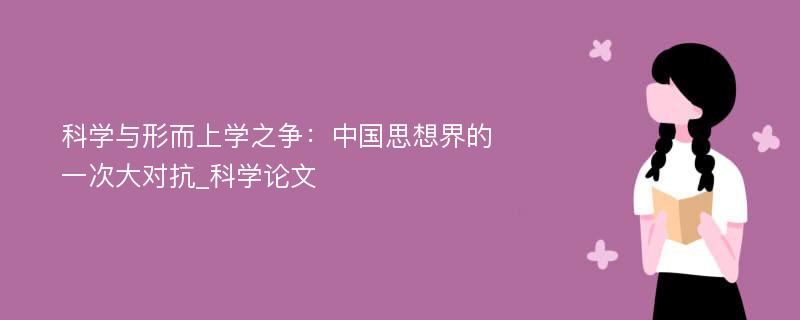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国思想界的一场大交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界论文,玄学论文,论战论文,中国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的纷争和论战一幕接一幕,可谓好戏连台,精彩纷呈。分属各种派别的知识分子彼此唇枪舌剑,口诛笔伐,弦箭文章起,心潮逐浪高。发生于80年前的科学主义与玄学主义之争,就是诸多纷争和论战中可圈可点的一场思想大交锋。
丁文江挑战“玄学鬼”:对头原来是老友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国知识界迅速向西学敞开怀抱,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纷纷涌入国门。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内各种思想潮流及学派并存,呈争奇斗艳之势;高等学府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也变得更为活跃。但正是思想学术界群雄并起、多极并存的状况,反而使大多数面临人生道路选择的莘莘学子们,陷入了彷徨无定、难以抉择的苦闷之中。
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师生邀请当时颇有名望的哲学家张君劢到校,作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演讲。张君劢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造成创痛、带来精神幻灭的教训,宣扬自由意志,提出重建“精神文明”的问题,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文明而不能指导人生观。
张君劢的讲稿经由《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丁文江立即起而反驳。丁文江,字在君,是对中国地质学有很大贡献的科学家。他认为科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是知识分子的终极关切,他甚至期望:“用科学方法求出是非真伪,将来也许可以把人生观统一。”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在丁文江看来实在美好,但是却因遇到了张君劢这在哲学家的捣乱而不能推行起来。于是,他在自己和胡适共同创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喊出“打倒玄学鬼”的口号,由此拉开“科玄论战”的序幕。
科玄论战波及了当时中国大半个知识界,参战者有胡适、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瞿世英等学界名流数十人,其中既有成名已久的思想巨擘、学术大家,也有属于后起之辈的晚生新秀。这场论战轰轰烈烈地闹了大半年,才偃旗息鼓,鸣金收兵。随后,泰东书局选辑了论战中“玄学派”的几十篇文章,印成一书,定名为《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序;上海亚东图书馆则选辑了论战中“科学派”的几十篇,也印成一书,起名为《科学与人生观》,由陈独秀、胡适作序。两书内容基本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中只有陈独秀谈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话题,但却并不深刻。
科玄论战爆发时,探讨人生观问题的并非张君劢一人,但丁文江为什么偏偏向他发出挑战呢?个中原因,或许只能用“交往过甚、相知过深”来解释。
张君劢是上海宝山人,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弱冠之年即考中秀才,国学功底较为深厚。他曾于1906至1910年留学日本,攻读政治和哲学,并与梁启超结识,以梁为师,参加政闻社,跻身立宪派。
丁文江为江苏泰兴人,早年也曾留学日本并与梁启超结识,后又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专习地质。1911年回国后,获清廷格致科进士。
就历史渊源来说,张君劢和丁文江都与梁启超有深厚关系。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知大势已去,不得不改弦更张,抛却君主立宪的老调而诩赞共和,并摇身一变而为研究系的领袖。张、丁二人惟梁启超马首是瞻,追随左右。他们与蔡锷、蒋百里、汤觉桓、罗文干、张东荪、林长民等,共同成为研究系的中坚人物。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北洋政府特派梁启超等人担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顾问,张君劢、丁文江均名列其中,随梁同行。
不过,他们二人的人生旨趣和事业追求却差异较大。张君劢虽一生标榜讲学,以哲学家、宪法权威自居,但他像梁启超一样,其实内心非常热衷于政治活动。民国初年,他就追随梁启超出入北洋权贵之门,奔走名流要人之间,时而上条陈,时而主笔政,颇露头角。梁启超任财政部长时,曾想委任他做中国银行总裁,但他似乎有自知之明,感到中国银行情形复杂,非他这个书呆子所能胜任,便辞谢不干,转而推荐弟弟张嘉璈代他承接这个肥缺。1913至1915年时,他曾因政治失意而留学德国,研习唯心论哲学。其间恰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推测德国必败,回国后便大肆宣扬他的“对德宣战论”,说中国如参加协约国,将来胜利了就可以提高国际地位,恢复已失主权。这一论调,与当时许多盲目相信德国军事力量雄厚的人所持的观点大不相同,但却正中想借“参战”为名来扩充自己实力的段祺瑞下怀。后来中国对德宣战,并成为战胜国的一员,但却没有像张君劢说的那样,改变任人宰割的弱国地位。不过,对张君劢个人来说,经过此事后,倒使他一举成名。
丁文江虽也长期跟随梁启超,并曾一度在政府中任职,但他基本上只是一个“技术官僚”,所做的多是与地质研究、教学或实地调查有关的工作。他从英国学成回来后,先在上海南洋中学担任理化教员;民国成立后,入北京政府工商部为技正,兼任地质科科长。当时政府为培养地质人才创设了地质研究所,丁文江不仅承担了筹备工作,而且负责该所的教学事务,领导人员多次开展地质调查活动。在山东枣庄煤矿的计划钻探中,丁文江贡献尤多。1922年,他参与发起中国地质学会,并与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但是,丁文江不像张君劢那样对政治具有狂热的兴趣,后来他甚至对自己所从事过的政治性活动,也从不对地质同仁谈起。
从张君劢和丁文江的许多不同之处可以发现,二人之所以在“人生观”问题上产生对立,丁文江之所以选择张君劢作为挑战对象,并非偶然。
玄学与科学:公说公理,婆说婆理
科玄论战的主要对手虽然是张君劢和丁文江,但实际上他俩不过是打先锋,真正的主角则是胡适和梁启超。在科学主义与玄学主义之争的背后,隐含的则是西学与国学之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这从双方所抛出的一系列观点中,即可得到证明。
玄学派是以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立论根据的。罗素曾指出,西方“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解释”。这与张君劢关于西方文化以物质文明为主,中国文化以精神文明为主的观点一致。他们主要着眼于民族性维度,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即说:“此二三十年来之欧洲思潮,名曰反机械主义可也,名曰反主智主义可也,名曰反定命主义可也,名曰反非宗教论亦可也。”他并认为“此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曰自由意志之说阐发,曰人类引为可以参加宇宙实在”。
应当说,由于西方科学在19世纪以后取得了惊人成就,各种科学成果在人们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便降临人间,根本不管人类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是否与之适应就横行天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逐渐动摇了人们对科学所持的乐观看法。当时,西方社会对科技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忧虑,逐渐意识到没有文化的控制,科学的发展就会成为人类自杀的工具,甚至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正是出于对科学负面作用和消极后果的忧患意识,出于对人的生命的同情和关切,出于对知识分子意志自由的尊重和信仰,张君劢等“玄学派”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提出对科学的挑战。
作为科学派的理论资源和文化支点的,是西方的实证主义精神。这是西方近代化的产物,体现着鲜明的近代文化精神。它利用进化论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即使在西方科学及其实证主义已经显示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深刻危机时,科学派也极力想用时代性为其张目。
丁文江认为,不存在比科学更高的哲学方法,科学方法是人们能够掌握的最高方法;科学方法不仅是社会科学所要遵循的方法,而且是一切学术、乃至一切思维应遵循的惟一方法。他说,哲学是实证科学的总和,更应以实证科学为榜样。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中,丁文江挖苦道:“玄学于是从根本哲学退避到本体论,他还不知悔过,依然向自然科学摆他的架子,说自觉你不能研究,感官触觉以外的本体你不能研究,你是形而下,我是形而上;你是死的,我是活的。科学不屑与他争口舌:知道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鬼不投降。”
胡适后来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列举了中国遍地是“坛道院,仙方鬼照相”等迷信陋习后,也指出:“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于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于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于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
在丁文江那里,站在方法论的角度上看,科学是真理的化身,具有无上尊严。在胡适那里,则站在进化论的角度上看,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资格来批评科学;科学精神对中国来说,代表的是一种先进文化;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苦于科学的发展不足而不是发展过度。
科学与玄学在人生观方面的论战,实际上涉及的是能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说明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社会科学是否能采用科学方法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双方的回答都有错误。
张君劢以玄学唯心主义人生观来反对科学的人生观,认为人生观就是“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限制的,它自身也没有什么规则,“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所以,不管科学如何发达,都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他实际上是从纯主观的意义上来谈人生观,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不过是神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因而,这不过只是给“人生”开了一张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头支票”。
丁文江反驳说:“人生观同科学的界限分不开。”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内容是人的心理现象,人生观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刚好在科学的研究范围内,所以科学能够解释人生观。丁文江、胡适等甚至认为,科学不仅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且世间一切现象都受科学方法的支配,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绳。这就陷入了“科学万能,科学方法万能”论的泥淖,带有明显的“科学崇拜”倾向。科学被信仰化了,不仅提供了对宇宙和人生的普遍有效解释,而且成了评判、裁定一切学说和理念的准则。
陈独秀当时坚持的也是这种观点。在论战中,任永叔认为科学的人生观是不可能的;范寿康认为科学不能真正解决人生观问题。在《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一文中,范寿康说:“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对此,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批驳道:“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 各 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
硝烟散后,局里局外的评说
究竟是什么问题激发和推动了如此多的文化名流参与科玄论战?陈独秀的回答是:“一个是‘科学的人生观是否错误’?一个是“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后者的讨论多于前者。”
科玄论战的发生,说明中国思想界走过了短暂的启蒙阶段后,已经不再满足于原先对“科学”和“人”的理解了,开始对这两大问题进行再思考。这场论战同时意味着,现代中国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联系,正在透过表层而深入到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内部。
科玄论战的硝烟似散未散,当年躲在幕后的双方主将胡适和梁启超,就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了这场论战。
胡适说:张君劢的清华园演讲,“丁在君先生的发难,六个月的时间,二十五万字的煌煌大文,大吹大擂地把这个问题捧了出来,叫乌烟瘴气的中国知道这个大问题的重要”。
梁启超则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中说:“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可喜的现象。”
当年的其他学者在回顾这场论战时,也都高度肯定了它的意义。
在1935年出版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作者郭湛波说: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大体有四次:第一次是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反孔,第二次是东西文化论战。这两次论战均为“大战的准备”,而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才是“大战突发”,“真是战云弥漫,短兵相接;血战数次,以决胜负”。而且这次论战,由于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向胡适发出挑战,“又种下下次思想论战的种子”,即后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贺麟在其名著《当代中国哲学》中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们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才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
蔡元培在1923年时即说,严格地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成立”。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只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准备,“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才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开端。
艾思奇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的末尾所开列的一份图表,更是具有特殊价值。他在表中说,自辛亥革命以后至1922年,中国哲学分为两个阶段:一为“在封建基础上的新思想之输入”时期,这一段截至1915年;二为“‘五四’文化运动资产阶级底哲学科学方法”时期。艾思奇还指出:“欧洲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在中国仅短缩而为五六年的‘五四’文化运动。”而第三阶段则正是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起,至1927年后唯物辩证法“掩蔽了全思想界”止。
艾思齐的论述,向人们澄清了“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这一问题。这是正确认识20世纪中国哲学史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的传播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正是在稍后于五四时期才发生较为深广影响的,即便在五四时期即已被一部分人熟悉了的唯物史观,也同样如此。
正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提供了契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瞿秋白为论战而写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此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在谈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段历史时,也绝对不能忽略瞿秋白的这篇文章。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与玄学派纷纷使用了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新式武器”。张君劢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工具,认为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所以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丁文江则以马赫主义为旗帜,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因为“科学的材料是人类心理的内容”。但这些学术上的“新式武器”,并不能导致任何一方必然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只是表明双方的论战是唯心主义阵营里的一场混战:否认科学能够解释人生观,就是否认人生观的客观依据,是唯心论;而认为科学研究的内容是人的心理现象,实际上是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也是唯心论。
在瞿秋白看来,论战双方在理论上都非常肤浅,抓不到问题的实质。据此,他在陈独秀等人批判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剖析,指出二者“‘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规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
在他所写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等一系列文章中,瞿秋白抓住两者争论的本质性问题展开了正面论述。他既肯定社会规律的客观存在,又肯定人的意志可以自由;自由来自必然,必然又支配自由;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人类社会就在这种辩证的矛盾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这个思想,既反对了张君劢的“意志自由论”,又反对了丁文江、胡适的所谓“科学规律”,最终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意志自由与社会规律的关系,从而结束了中国现代史上这场著名的科玄大论战。
标签:科学论文; 梁启超论文; 张君劢论文; 人生观论文; 玄学论文; 丁文江论文; 陈独秀论文; 胡适论文; 自由意志论文; 丁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