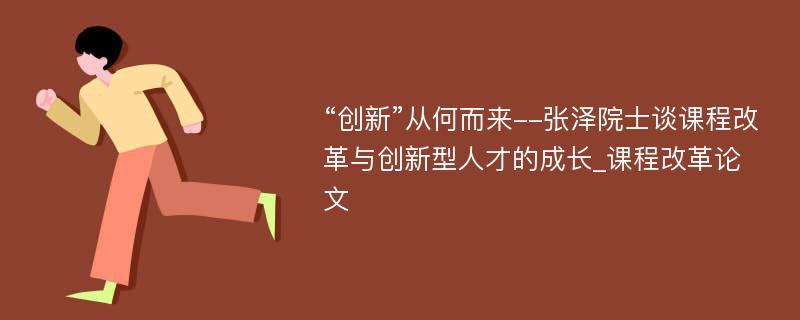
“创新”从何处来——张泽院士谈课程改革与创新人才的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院士论文,课程改革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泽,天津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科院北京电镜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亚洲晶体学会主席。现任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材料学会副理事长。
尽管现实问题不少,但我对我们国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原因何在?就在于我看到教育正在改革,具体地讲,就在于我看到了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记者:张院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都提出了许多有关教育的议案、提案,您作为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对此有何感想?
张泽: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即将闭幕时,我得到一个数据,本次会议收到的政协提案共有5571件,其中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提案551件,“三农”方面的提案603件,就业方面的提案632件,教育方面的提案657件。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时,教育类提案仍然最多,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给我很深的感触。可见教育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奠基性作用已经比较深入人心。
近年来,我们国家提出要在2020年初步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而当前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更加凸显了自主创新的重要价值。如果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经济发展过多依赖低附加值的加工出口,那么就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要提高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就需要创新型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需要教育去培养。
记者:您觉得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做得如何?其原因何在?
张泽:要培养创新人才,就需要重视科学。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有科学技术领域才有创新,也不是说人人都要成为科学家,我认为,想要创新,就必须具备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想要做出创新性的工作,都离不开这三者。
应该说,中国从国家层面上真正重视科学,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就我看到的资料和接触到的信息来看,我们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比如,不少大学毕业生比较缺乏自主思考能力,这就是一个影响创新的大问题。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3~1727)早在18世纪就提醒过我们:不要不假思索地去追逐权威,不要不假思索地去追随传统或社会习惯,要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为什么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仍然缺乏自主思考能力?我想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的“填鸭”式教育有关,在这种教育里,我们过分强调教师的“教”,而忽视了学生的“学”,学生的主动性被扼杀,成了装知识的容器。同时,这也与我们长期的“听话”教育有关,孩子小时听父母的,上学听老师的,工作听领导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具备自主思考的能力?
又如,部分大学毕业生缺乏动手实践能力,而创新绝对不能停留在“头脑风暴”的层面。学生不会实践,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没有给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忽视知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过分注重学科知识,忽视跨学科综合素质的培养,而实践往往又都是需要具备综合素质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广受批评的应试教育,因为纸笔考试很难测评动手实践的能力,所以许多学校干脆就把实践能力的培养忽略掉,最终造成学生素质上的重大缺陷。
在今年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不少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委员都提到,大学生就业难,除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大学生就业观念、职业预期有待改变之外,用人单位提供大量一线岗位和部分大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关键原因。可见这种素质缺陷,不仅在宏观上影响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实现,还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一个大学生的生计与出路。
尽管现实问题不少,但我对我们国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原因何在?就在于我看到教育正在改革,具体地讲,就在于我看到了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中国的教育改革,更充分地体现在基础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课程领域;课程改革是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储备人才,是在教育领域实实在在地践行科学发展观。
记者:我想,您刚才的话对所有课程改革工作者都是非常“暖人心”的激励。那么,您能具体谈谈您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看法吗?
张泽:我想从我的两个基本看法谈起——第一,中国的教育改革,更充分地体现在基础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课程领域;第二,课程改革是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储备人才,是在教育领域实实在在地践行科学发展观。
为什么说中国的教育改革,更充分地体现在基础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课程领域?就在于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真正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正在与全球的课程发展接轨。最近我接触到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方面的一些专家,得知我们的基础教育领域目前正在加入、借鉴OECD(经济合作组织)组织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IEA(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主持的TIMSS(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测试研究)项目,以及由美国国会授权并赞助的NAEP(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项目。这就是真正的教育改革国际化,用参与国际一流项目,吸取国际领先经验的方式来进行教育改革,反过来看,这种水平的改革在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域中还比较少见。
为什么说课程改革是在教育领域实实在在地践行科学发展观?按我的粗浅理解,所谓科学发展,就是要按规律办事,教育也有自己的规律。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教育的两个关键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就“培养什么人”而言,它的规律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终生发展来培养人才;就“怎样培养人”而言,它的规律就是要让孩子积极、主动、富有创造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学习。
回到刚才提到的PISA项目上来,它试图用纸笔测验衡量初中学生的阅读能力、数学能力和科学能力,希望了解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各国初中学生,是否具备了未来生活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并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参与、借鉴PISA,实际上就是要明确基础教育的培养标准,弄清楚我们的社会需要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具备怎样的素质。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培养标准和选拔标准是有很大区别的,培养标准面向全体,选拔标准面向部分;培养标准针对学生的整体素养,选拔标准针对学生能否进一步深造。长期以来我们用选拔标准取代培养标准,教育工作围着考试转,出现了许多问题。现在,至少基础教育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有了培养标准,再加上工具和方法,这样中学生毕业后就有基本的适应社会的能力了。这件事情是历史性的,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就我对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了解,我觉得里面提出的很多观念都是合乎规律、非常正确的。比如教师要从单纯的教学生转变为组织、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学生要从死记硬背转变为主动学习、自主探索。诸如这样的先进理念如果能贯彻到教学的“神经末梢”,那我们的基础教育大有希望,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也有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不过,目前深化课程改革的阻力很大,您觉得根本原因在哪里?对于深化课程改革,您有怎样的建议?
张泽:改革,特别是意义重大的改革,如果没有阻力那才是怪事。我想,课程改革遭遇阻力,从具体的原因来看,有既得利益群体,尤其是那些靠应试教育发财,“吃孩子”的人的反对;也有一些出发点很好,但是对课程改革不熟悉、不了解的人的批评。
对于前一种阻力,我的建议是要系统地改革,仅仅依靠课程改革“单兵突进”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都行动起来才能化解这样的阻力。或者可以这么说:教育的每个领域都进行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样水平和力度的改革,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只有系统化地深入改革,才能化解系统性的阻力。
对于后一种阻力,我的建议是这些批评者最好能亲自到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去走一走、看一看,有条件的话参与一下课程改革,多做些全面的调查研究,而不要仅凭一些二手、三手信息或他人的说法就做评论。我曾经参与了小学《科学》教材的编写工作,那对我真是一个从身体到精神的巨大挑战。一个课件、一句话、一个字都要反复斟酌,考虑许多不同环境和条件下的教育效果,极其严谨复杂,而其中许多内容都是我在研究所和大学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我想,如果有这么一个参与的过程,相信很多批评者的看法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就课程改革本身来说,一定要加强社会宣传,循序渐进,寻求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要寻求社会文化的认同与支撑。如果没有这些支撑,没有长期奋斗的准备,那么课程改革是很难真正成功的,也很难摆脱此前许多改革举措“其兴也速,其亡也遽”的命运。
如果没有重视科学、重视教育、重视创新的社会文化,我们很难建成创新型国家,着眼于培养创新人才的课程改革恐怕也很难真正扎下根来。
记者:您刚才提到社会文化的问题,您能具体谈谈怎样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实施吗?
张泽: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不能真正重视科学、重视教育、重视创新,那么这个国家是很难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由于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遵循科学的方法,因此,如果没有重视科学、重视教育、重视创新的社会文化,课程改革恐怕也很难真正扎下根来。刚才我提到课程改革遭遇阻力的原因,我觉得,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社会文化上。
第一,我们的社会文化是不是真的重视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连科学都不重视,那么谈何发展?谈何创新?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宝贵,但是也有重大的缺陷,就是不重视科学技术。中国古人很聪明,但是他们的智慧很少投向科学技术,而是主要关注人伦和道德,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关系方面,我们的先人登峰造极,但是在关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却做得相当不够。
中国的科技发达得很早,周代就出现了《考工记》这样的工程技术书,但是它只有成为《周礼》的一部分才能保留下来。先秦《墨经》中记录时空、机械、杠杆等内容,但是由于“独尊儒术”,很少受人关注。西汉《淮南子》和《春秋繁露》里也有不少科学现象的记录,比如静电、共振、声、光、磁,但是都没有成为这些著作的主流,更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此后也有沈括、郭守敬、李时珍这样的科学家出现,但是都没有引发社会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和尊崇,社会文化的主流仍然是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入仕不成则隐退,“穷则独善其身”。
西方则不一样,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 BC)就特别重视研究自然,用启发的办法教学,训练思维的逻辑性,最后甚至为此献出生命。柏拉图(Plato,427~347 BC)的学园门口刻着一句话——“不懂数学者莫入”,他也主要教授数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广泛研究世界万物,认为应该先了解自然才能了解人类,为传统科学的分科打下了基础。经过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最终摧垮了神权,西方社会对科学的崇敬已经无以复加。1727年3月牛顿去世,英国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行,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为他抬棺,王公贵族、政府官员、文人学士都聚集在教堂中向牛顿告别。目睹这一情景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写道:“他在世时就备受国人尊崇,下葬时也宛如一位带给人民幸福的君主。”正是社会文化对科学、科学家的高度推崇,才造就了“日不落帝国”数百年的领先地位。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博士曾经提出的“李约瑟难题”,简言之就是: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或者说,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起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而不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领先的中国?我不揣浅陋地给出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不可能促成近代科学的诞生。应该说,传统文化忽视科学的流弊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在今年“两会”上我看到一份官方的调查,长大了想当科学家的小学生,其所占比例仅仅高于想当农民和工人的孩子。据称,我国电视节目中,与国民科学素养有关的节目仅有不到6%,而日本的这一数据是15%,美国则是20%。可见,在引导社会尊重科学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第二,我们的社会文化是不是真的重视教育。1805年,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击败普鲁士,普鲁士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占领了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在柏林的城市公园上连续做了三个月有关教育救国的讲演,法军在周边持枪环立,但费希特不为所动,将教育救国的建议提给教育大臣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同时,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70~1840)对从法国占领区逃出来的教授们说:“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因为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于是他将皇宫捐出来办柏林(洪堡)大学,任命费希特为第一任校长;又捐资办基础教育,规定所有普鲁士人必须接受教育。由于国民基础教育水平提高,1870年,普鲁士击溃法国,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当时的军事总指挥,普军元帅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感叹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
德国人对科学文化的疯狂崇拜,教育、教师受到的崇高待遇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其结果是:1864年到1869年,世界生理学的100项重大发现,89项属于德国;1855年到1870年,德国拥有136项电、光、热方面的重大发明,英法两国合计才有91项;1869年,德国拥有33项医学发明,英法合计还不到30项。就是由于全社会对教育、科学、创新的高度重视,德国才在短时间内后来居上,在科技和经济上超过了老牌强国英法。这段历史很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西方社会对科学的尊崇,对教育的重视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发现血液循环的赛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和支持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被残忍地烧死;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晚年被软禁,极其孤独;普鲁士则经历了几乎亡国的痛苦才得出了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结论。但是,这不等于人类必须经历这样的洗礼,当前,我们完全有条件吸取前人的经验,更好地实现社会文化的成功转型,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
创新不一定需要超群的天才,不一定需要很好的条件,也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支持与严格的监督,而是需要合乎创新要求的综合素质。每人都有创新的可能,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是否能让他实现这种可能。
记者:基础教育要为培养创新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就需要明确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应该说,从知识和技能层面,基础教育无法独立承担培养创新人才的任务,那么我们该着力于哪些方面呢?作为著名的科学家,您对创新人才应有的素质有怎样的看法?
张泽:我的看法和一些人的观点恰好相反,我觉得创新人才的成长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往往是人格、自信、敏感性、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意志力、质疑能力、实践能力等等,而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甚至也不仅靠天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必须从中小学开始培养,其中的一些素质,甚至在中小学阶段就已基本定型了。
我觉得,从一些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经历中,我们能够得出上述的判断。目前数字产品非常流行,比起前几年来,不仅应用的面更广,产品质量更好,价格也更低。这一切都要感谢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法国科学家艾尔伯·费尔特(Albert Fert,1938~ )和德国科学家皮特·格林伯格(Peter Grünberg,1939~ )。他们在巨磁电阻效应方面的杰出贡献是获奖的理由,而且他们也打破了此前十多年来物理学奖得主中必有美国科学家的局面。
仔细分析这两位科学家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成功主要并不是得益于超凡的天才。费尔特1970年在巴黎第十一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88年发表了使其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当时已经50岁,在此之前他的最高职务仅仅是巴黎第十一大学固体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小组组长。格林伯格1963年毕业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1969年在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非出自一流名校,1992年才当上教授。他1988年写出的使其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在投稿过程中还被“枪毙”过。这两位科学家,从经历来看并非天才超凡卓绝的人,但是他们甘于寂寞,长期从事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了成功。在这当中,他们的意志力、坚忍不拔的毅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宽松的研究环境也功不可没。
发现X射线的伦琴(Wilhelm Conrad Roentgen,1845~1923)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他从小性格倔强,不愿改变自己的主张,在中国人看来,这不算是一个好的个性。但是伦琴品德高尚,对荣誉金钱非常淡漠。在发现X射线后,有人看到这项发明的商业价值,想用高价购买X射线的专利权,牟取暴利,巴伐利亚的王子甚至以贵族爵位来笼络伦琴,都被他一概予以拒绝,他说:“阳光有专利吗?空气有专利吗?”就连诺贝尔奖的5万瑞典克朗奖金,他也转赠给了沃兹堡大学。伦琴还说:“我的发现属于全人类,但愿这一发现能被全世界科学家所利用,这样,就会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因此,伦琴没有申请X射线的专利权。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得知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他为接收X光发明了一种极好的荧光屏,和X光射线管配合使用,为了表示对伦琴的尊重,爱迪生也拒绝申请荧光屏的专利。在伦琴和爱迪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格对于创新的巨大作用。
费利佩·伦纳德(Philipp Eduard Anton Lenard,1862~1947)接续伦琴的工作,因在阴极射线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被授予190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获奖的成果——X光衍射的灵感,来自于他在读博士后时,与一位朋友的一次饮茶聊天。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敏感性和想象力的价值。此后,在伦纳德与几位同学准备进行这方面实验时,他的老师,著名科学家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1857~1894)以及伦琴都不赞成,认为意义不大,但是伦纳德还是坚持了下来。在这里,自信和意志力的作用非常重要。
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一对英国父子,W·H·布拉格(William Henry Bragg,1862~1942)和W·L·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1890~1971),他们的贡献主要是利用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这里体现的是实践能力,或者说应用能力,X射线的发现与他们无关,但是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让这种射线真正获得了用武之地。同样的,恩斯特·鲁斯卡(Ernst Ruska,1906~1988)利用电子的波动性发明电子显微镜,宾宁(G.Binnig,1947~ )和罗勒(H,Roher Gerber,1933~ )利用量子力学原理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从而一起获得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也是实践能力作用于创新的例子。
创新还需要有其他一些素质。1906年,约瑟夫·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发现了电子,而且几乎是用一个灯泡就测出了电子的电荷和质量。但是,法国贵族路易·德·布罗伊(Prince Louis~victor de Broglie,1892~1987)质疑电子是一种粒子的观点,发现了电子的波动性,并因此获得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约瑟夫·汤姆逊的儿子乔治·汤姆逊(George Paget Thomson,1892~1975)也怀疑父亲的结论,他发现了晶体对电子的衍射现象,证实了电子是一种波,因此获得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看起来,比较强的质疑能力和吸纳综合前人成果能力,也是创新型人才必备的素质。
从这些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非智能、天分的因素在创新中起到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创新不一定需要超群的天才,不一定需要很好的条件,也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支持与严格的监督,而是需要合乎创新要求的综合素质。我认为,每人都有创新的可能,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是否能让他实现这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