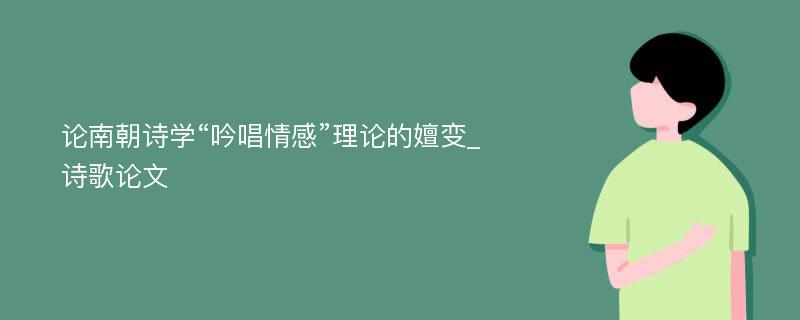
论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022X(2000)03—0035—06
“吟咏情性”是南朝诗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南朝诗论家们曾经一再强调这一观念,而这一命题也确为南朝的唯美诗学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然而,这个命题不是南朝诗学的发明,而是从汉代诗学中移用过来的。众所周知,汉代诗学与南朝诗学在价值取向上正好处于对立的两极,前者注重政教、功利,后者偏重娱乐、审美。为什么彼此对立的两派诗学都使用着同一个命题?南朝诗学又是如何改造这个命题的?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
要考察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加工、改造,首先必须弄清汉代诗学对这一命题是如何理解的。
我们这里所谓的汉代诗学是指以《毛诗序》为代表,强调诗歌政教功能的儒家诗歌理论。“吟咏情性”这一命题便首先是由《毛诗序》提出来的。《毛诗序》在阐述了诗歌的发生与本质后,提到了变风、变雅,指出: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这段论述,从《毛诗序》全文看,原不处于中心地位,但正是这里提出的“吟咏情性”一语,却成为日后南朝诗学的核心观念。那么,在汉代诗学里,这个命题包含着哪些意义呢?
让我们先来看汉人是如何理解情与性的。诚然,我们在《毛诗序》中找不到对情与性的直接释义,但我们从班固的《汉书·礼乐志》中却读到这样一段话:
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喜怒哀乐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
这就是说,班固是把情具体解释为人喜怒哀乐的情感活动,而把性解释为人的“血气心知”,也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禀性。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是班固发明的,而是直接导源于《礼记·乐记》。在《乐记》中,除了有上引班固的第二段论述外,还有如下的一段话: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六者(按:指哀、乐、喜、怒、敬、爱)非性也,感于物而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这就进一步厘清了情与性的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情与性的关系,即性是静的,原初的;情是动的,后起的,是在性的基础上受到外物的刺激而发生的。但我们从汉人对“吟咏情性”这一命题的实际使用来看,他们在情性中又是比较偏重于情这一方面的。如此看来,“吟咏情性”说所包含的第一层含义便是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质。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我们还是没有接触到汉代诗学的核心观念。于是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汉人所要吟咏的是什么样的情?是不是只要是丰富的感情都在诗歌吟咏的范围之内?答案很明确,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适合于吟咏,汉人所要吟咏的情事实上是经过选择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情可以吟咏?什么样的情不适合吟咏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代诗学就在“吟咏情性”这一命题中引进了“礼”的概念。他们要用礼来充任检查官,建立一种筛选机制,接纳合乎礼义,有助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感情,而排除那种“流僻邪散”,不合礼义之情。一句话,就是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以达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以上引文均见《毛诗序》),感化人心,移风易俗的目的。经过这样的诠释,“吟咏情性”这一命题就被染上了一层浓厚的伦理色彩了。这是该命题所包含的第二层含义。
到此为止,我们大体上把汉人“吟咏情性”说的基本含义讲清楚了。但问题是当我们最终回到对情性二字的理解时,不免会有一个疑问,尽管汉人对情性的理解偏重于情,但“性”难道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设吗?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情与性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先秦两汉时期对人性本质的探讨是当时思想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围绕着性的问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性恶论(以荀子为代表)、性无善恶论(以告子为代表)、性善情恶论(以董仲舒为代表)等等。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大体上都是以善恶论性,而赋予性以浓厚的伦理意义。那么,汉代诗学在性的问题上又是持什么看法呢?我们从汉代诗学的有关论述来看,似乎有着性恶论的痕迹。例如汉代诗学把性理解为“血气心知”,即人的自然本能,这就与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班固所谓“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就隐含着人性本恶,必须加以节制但无法灭绝的意思。至于《乐记》所谓“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从物也。人从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此大乱之道也”,就更是比较明显的性恶思想了。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从思想渊源来说,汉代诗学与荀子有着比较明显的血缘关系,荀子的《乐论》直接影响了《乐记》、《毛诗序》及班固的美学观,而荀子则是性恶论的代表。因此,假如不把话说得绝对,认为汉代诗学受到性恶论的影响大致还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提到,性是情的基础,是更为根本的东西。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汉人对情的理解与处理,就比较容易把握与接受了。正因为人性本恶,人们才有可能产生种种放僻邪侈的感情,才有用礼义来加以制约的必要。这样看来,性是汉代诗学立论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汉代诗学对情的看法是直接建立在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上的。
诗歌是抒情的,所抒之情必须是合乎礼义的;人性是有弱点的,因而情感中有一部分是邪恶的,必须以礼节之。这大体上就是汉代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诠解。
二
对汉人“吟咏情性”说的涵义有了基本的了解后,再来看南朝诗学对这一命题的改造就比较清楚一些了。
一个能在不同时期被不同派别共同接受的命题大体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命题本身具有可以共享的思想资源;二是该命题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包含着可供进一步开掘的资源和向特定方向引伸的理论空间。“吟咏情性”说正属于这种情况。
“吟咏情性”说所揭示的诗歌抒情的特点正是汉代诗学与南朝诗学的结合点。但南朝诗学毕竟不是汉代诗学,它在价值取向上与汉代诗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因而它在接受“吟咏情性”这一命题时,当然不会原封不动地照搬汉人的解释,而必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新的解读。那么南朝诗学又是如何改造这个命题的呢?它是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造的呢?我们不妨仍从情、性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先看情的问题。南朝诗学对情的基本涵义的理解与汉代诗学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情的内容与范围。在南朝诗学中,礼对情的制约作用正逐渐被淡化,原先被汉代诗学所排斥的那一部分情感内容已堂而皇之地被大量接纳进诗歌中来。与汉代诗歌相比,南朝诗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诗中的感情日趋世俗化,比较侧重于表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感情。这些感情往往无关于政教,有的甚至并不合乎礼义,但南朝人对此并不介意,一概纳入诗中。因为在南朝诗学看来,诗歌只是自我愉悦和求得心理平衡的手段,而不是什么教化的工具。他们之所以重情完全是着眼于情的审美效果,而根本不在乎是否合乎礼义,是否有助于政教。这一点,我们从钟嵘《诗品序》论诗歌情感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其辞曰: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上述诗歌情感大抵是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感慨和苦闷,其无关于政教,非着眼于风化是非常明显的。从诗歌创作的情况看,南朝前期(刘宋)诗歌中的悖礼之情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以休鲍为代表的“委巷中歌谣”(《南史·颜延之传》),以“淫哇不典正”的侧艳情调直接冲击着正统的礼义观念。只是这一类诗还多集中在拟乐府中,在非乐府的文人诗中尚不多见,更没有占据诗坛的主导地位。这表明了尽管其时诗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礼的制约作用毕竟还没有完全取消,诗歌对悖礼之情也还没有完全洞开大门。随着诗中礼义机制的逐渐淡化,到齐梁时期宫体诗登场,礼的防线就被全面突破了,那些从传统眼光看来明显属于放荡悖礼的情感就公然登堂入室,不仅在拟乐府诗中得到表现,而且还大量出现在非乐府的文人诗中。例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用一种类似静物写生的手法,分别从女子的面容、发鬟、肌肤、内衣等角度,对女子的睡态作了精细的描摹。结末一句又明显带着一种玩赏、调笑的情调。这一类诗在当时是充斥诗坛,风行一时的,以至人们“递相放习”,“朝野纷纷”(《隋书·经籍志》),“宫体所传,且变朝野”(《南史·梁本纪》),成为诗坛的主潮。对于这类诗,若从传统儒家的眼光来看,显然表现的是一种放荡悖礼之情,是典型的郑卫之音,是应该坚决予以摒弃的。但南朝诗学对此毫不忌讳,反而大加称赏,赞之为“性情卓绝,新致英奇”(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全梁文》卷十一)。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从理论上公开否弃礼义,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全梁文》卷十一)的理论。这就彻底撤除了礼的防线,不存在什么情可以写什么情不可以写的问题了,从而最终走到了汉代诗学的对立面。由此可见,南朝诗学虽然接受了诗歌抒情的主张,却抛弃了汉人以礼节情的观点。情的基本涵义没有变,但情的范围和内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命题改造的一个方面。
在性的问题上,南朝诗学所作的改造则是对其内涵的偷换。南朝人当然也同意汉人关于性是先天禀受的说法,却完全拒斥汉人对性的伦理学解释。他们在对“吟咏情性”的阐释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强调诗歌创作所需要的特殊才能。我们注意到,南朝诗学家在表述“吟咏情性”的思想时,常常用“情灵”、“性灵”来替代“情性”,如所谓“情灵摇荡”、“感荡性灵”、“综述性灵”等等。这个“灵”字,原本指的是通神之巫,引申为一种带有神异、非理性色彩的精神状态,即所谓灵感、灵气者。在南朝人看来,诗歌创作不仅仅只是一种感情的抒发,而且还是作者天赋才能的表现。例如沈约在讲到诗歌的起源时就说过“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禀气怀灵,理无或异”。他肯定谢灵运的诗“兴会标举”(《宋书·谢灵运传论》),又指出这种灵气在诗歌创作中的神妙作用:“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答陆厥书》)萧子显说得更明确:“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那么这种情性在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他接着说到:“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这也就是说,诗歌创作不应该冥思苦索,惨淡经营,而应“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南齐书·文学传论》)。刘勰在谈到作家的创作条件时说:“才为盟主,学为辅佐。”(《文心雕龙·事类》)在先天的才与后天的学之间,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归根结底,文学创作是作家天赋才能的体现。这些论述无不揭示了诗歌创作的非理性特点。在南朝诗人看来,诗歌创作应是作者天性、才情的自然流露,是一种神秘奇妙的力量推动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同时也是针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堆叠故实的倾向,南朝诗学主张诗歌创作应该“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他们看来,一味地堆垛学问,适足以窒碍性情的发露,所以钟嵘提出“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诗品序》),所推崇的正是那种自然英旨、直寻流畅的性情之作。不仅如此,南朝的一些诗论家还进一步通过与学术研究的比较来显现诗歌创作的特殊性,以此来强调诗歌创作所需要的特殊才能。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描绘了文(主要指诗赋)的特点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绮填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创作这种作品所需要的特殊才情,当然不是人力追求的结果,也不是仅仅靠着深厚的学力就能培养出来的。萧绎高度评价文,而对于不需要“情灵摇荡”的儒、学、笔不免有所轻视,显然也有重才情的意味。颜之推虽是北朝的诗学家,但他早年生活在南朝,他的诗学思想兼融南北,而对诗歌性质的看法则完全接受了南朝诗学的影响。他也强调诗歌具有“吟咏情性”的特点,认为“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不仅如此,颜氏还由此出发进一步指出了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的不同特点:“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以上引文均见《颜氏家训·文章》)话说得很明白,学术研究可以靠着勤学苦思获得成就,但诗歌创作则不行,它是一种天赋才能的表现,是学不来,教不会的,因此,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从事诗歌创作,只有具备了诗人气质的人才有可能写得好诗。很清楚,南朝人对“性”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性”的概念中已经注入了才的因素,着重指的是诗歌创作所需要的天赋才能,这与汉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南朝诗学之所以能对性的内涵作出新解释,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它可资凭借的哲学背景。如所周知,汉魏之际,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加剧,以探究人才本质与成因为内容的学说——才性论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时期关于人物品鉴的著作就有七部之多(从有关类书的辑录看,实际上不止此数),只是其中的绝大部分著作后世均告亡佚,现存的只有魏刘劭的《人物志》。才性论的基本思想即在探究才与性的关系,以为人的才能决定于人的天性,而天性又是由人所禀受的阴阳五行之气所决定的。人禀受的气不同,人的性格也就不同,所谓“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燥,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引任子语),人的才能就是在先天气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才性论在魏晋之际曾盛行一时,成为后来玄学的先导,而当玄学风行之际,才性问题又成为玄学论争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据史料记载,当时有所谓才性四本的说法:“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魏志》)也就是在才性问题上的四种不同说法。才性论虽然也讲性,但它所讲的性更多的是同人的才能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性言其质,才名其用”(袁准《才性论》,见《艺术类聚》卷二十一),才性之间是质与用的关系。这与汉人以善恶论性,而与情构成相对的关系,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不同。同样都认为性是一种先天的禀受、气质,但其内涵不一样,这就有了偷换概念的可能。换言之,经过了魏晋才性论的洗礼,有了这样的哲学背景,再来审视“吟咏情性”这一命题,南朝诗学也就有了与汉代诗学不同的新的理解,也就有了引进新含义取代旧含义的思想资源。
正是经过南朝诗学对情与性两个慨念的重新解读,“吟咏情性”这个命题也就表达了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这就是,诗歌既要抒发个人生活中产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诗人独特的才情。于是,一个原本为政教诗学服务的传统命题就被改造成具有唯美色彩的新命题了。
三
在追踪了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命题的改造过程后,我们接着要来探寻的问题是,既然汉代诗学与南朝诗学在价值取向上是彼此对立的,那么为什么南朝诗学还要袭用一个旧的命题呢?我以为,南朝诗学特殊的思想状态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南朝诗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中呢?简单地说,它正处于两股对立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南朝诗学是一种唯美的诗学,有着向唯美方向发展的趋势与动力。我们只要把这一问题放到整个中古诗歌发展的大框架里,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是围绕着对诗歌特性的探讨和实验展开的。从汉末到西晋,诗歌大体上是沿着“缘情绮靡”的路子发展的,而当其弊病越来越明显时,诗风就酝酿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西晋末到晋宋之交,诗歌便进入了玄言诗时代,诗由缘情走向了体道,绮靡华丽转变为质朴平淡。这条路子尽管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的特征又给诗歌带来了新的危机,促使诗人寻求新的出路。于是从刘宋开始,诗歌便由理性重新回到了感性,诗人们力图通过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革新,来增强诗歌的感性美。从内容方面说,南朝诗歌大体上是以体物为妙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向缘情回归的倾向,特别是到了齐梁时期,这种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语言方面看,鉴于玄言诗的枯涩简淡,南朝诗人在词采、声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力求在语言上有新的特色,这就促使南朝诗歌沿着声色大开的路子前进,朝着唯美的方向发展。趋新求变,追求感官的美,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诗歌思想的主导倾向。
然而,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尽管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作了全新的解释,但他们毕竟沿用的是一个传统的命题,这个现象本身就显示了南朝诗学与汉代诗学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南朝诗学是与汉代诗学截然对立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诗学观念,这从大体上说当然是不错的。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南朝诗学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到了汉代诗学的对立面,开始背弃或者超越了传统儒家的诗学观,但我们还得承认南朝诗学是从儒家诗学中发展出来的,它的许多为人诟病的观点往往是从儒家诗论中片面引伸出来的。南朝诗学强调情采,从根本上说也是可以为传统的儒家诗学所容纳的。南朝诗学重视词采,讲究形式,也能在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说法中找到根据。即使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样“出格”的主张,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也还是可以看作是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命题的片面引申。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南朝诗学看作是儒家诗论片面发展的结果。再从南朝诗学的一些主要代表如沈约、萧子显、萧统、萧纲、萧绎、钟嵘、刘勰等人的思想来看,虽然儒、道、佛兼综,与正统的思想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无疑仍然属于儒家,这其实也是当时思想界的普遍状况。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决定了南朝诗学家们一般不可能另树旗帜与传统理论决裂,而最多只能在传统思想中寻找到既能代表传统,又适于作新解释的命题来体现自己的思想。换句话说,南朝诗学对传统诗学的革新往往是在旧的旗号的掩护下偷运着自己的货色,是在传统外衣的包装下推出自己的新主张。或者说,南朝诗学仍然企图从传统的儒家诗论中为自己诗学主张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而这一点又正好说明,南朝诗学与汉代诗学尽管对立,却仍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既背离儒家传统,又与儒家传统有着联系,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互相作用,形成了必要的张力,这就是为什么南朝诗学要对“吟咏情性”这一命题加以接受和改造的主要原因。
收稿日期:1999—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