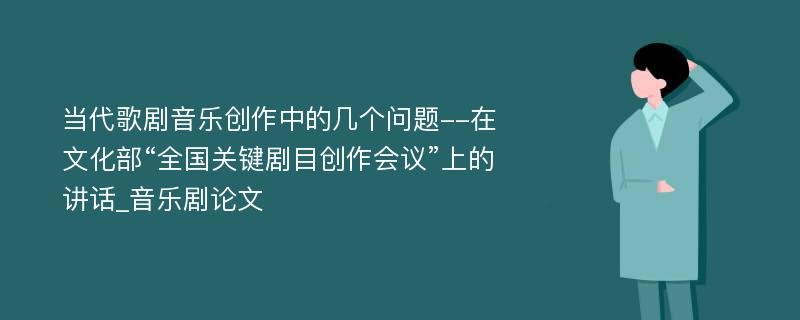
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几个问题——在文化部“全国重点剧目创作会议”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部论文,剧目论文,音乐剧论文,歌剧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司领导要我来谈谈歌剧和音乐剧的创作问题。我想先简要回顾一下新时期的创作实践,然后就其中若干问题谈几点个人见解。所说仅供参考,并敬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雅俗分流与“歌剧盲区”
新时期歌剧创作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歌剧观念和风格出现了雅俗分流的趋势:一股是雅化潮流,其基本特征是向欧洲严肃大歌剧靠拢,创作中国严肃歌剧;一股是俗化潮流,其基本特征是向欧美音乐剧靠拢,创作中国本土音乐剧。
二十年来,我们在严肃歌剧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称辉煌。就作品而言,在国内正式公演并在当代观众的歌剧生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剧目,80年代中期以前,以《伤逝》为前导,成为中国歌剧雅化趋势的发轫;到《原野》的出现,为雅化趋势确立了一个很高的专业格调。8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出现《深宫欲海》《仰天长啸》《张骞》《从前有座山》《归去来》《阿里郎》《安重根》(汉城版)《徐福》《马可·波罗》《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楚霸王》等一大批优秀剧目,使雅化趋势真正汇聚为一股艺术潮流;直到近几年来《孙武》《苍原》《阿美姑娘》《巫山神女》《舍楞将军》《屈原》等剧的闪亮登场,为我国歌剧创作注入了源头活水,使雅化潮流更见阔大。就作曲家而言,像石夫等七十岁左右的老一辈作曲家依然活跃在歌剧创作领域,而金湘、刘振球、徐占海、王世光、张玉龙、萧白等一批五十多岁、六十岁左右的中年作曲家正在如日中天,堪称中国当代歌剧创作的中流砥柱;至于像崔新、徐坚强这样一些四十岁上下的新生代作曲家在歌剧领域的崛起,以及一批三十岁上下的青年艺术家正在抓紧积累经验,磨砺刀枪,时时准备介入严肃歌剧创作,则是我国严肃歌剧创作后继有人的标志。
与雅化潮流相比之下,作为俗化潮流主要标志的音乐剧创作却在吵吵嚷嚷中显出无奈与寂寥。虽然从数量看,据不完全统计,自1981年至今在全国各地公演的原创音乐剧早已超过百部,获得各种奖项的剧目也不少,但真正在社会上有影响、观众中有市场、经济上有票房的“三有剧目”,至多只有80年代的《搭错车》和《芳草心》等三两部勉强可以作数。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势头渐旺,市场趋热,人气也高,推出的新剧目接二连三,制作规模越来越大,但人们期待已久的“三有剧目”却屡唤不出。因此,近20年来,投身于中国原创音乐剧创作与制作的单位和个人虽说数量很多,分布面广及全国各地,但相对稳定、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音乐剧创作群体至今未能形成,造诣超群、众望所归的音乐剧艺术家一个也未出现。
中国歌剧创作的雅俗分流,当然是同改革开放这个总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因此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为精英文化的严肃歌剧,其创作和制作水准从来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综合实力的象征,而它的服务对象是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干部和白领阶层;作为通俗文化的音乐剧,也正由于它的娱乐艺术本性和市场特征而将它的服务对象定位于广大的都市青年、大中学生和蓝领阶层。
于是我们发现,作为我国歌剧雅俗分流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在严肃歌剧和音乐剧之间露出了一个广阔的空白地带——这就是广大农民和农村市场。近20年来的歌剧实践证明,农民与农村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排除在歌剧艺术的视野之外,成了严肃大歌剧不爱、通俗音乐剧不疼的“盲区”。这种状况,无论从农民在我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农村文化市场在全国文化市场所占的地位说,还是就农民群众与歌剧艺术之间相互需要的紧迫性说,“歌剧盲区”不能不是近20年来中国歌剧发展的一个重大缺憾。针对这种状况,近来山东作曲家刘源提出了“乡村歌剧”的概念,并在作品《拉郎配》中将它作为艺术理想来追求。尽管对这个概念的理论阐发还很粗浅,《拉郎配》在艺术上也不成熟,但它毕竟提出了当代歌剧如何面向农民、如何占领农村文化娱乐市场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为中国歌剧和音乐剧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生存发展空间。为此,我曾在一些文章中极力宣传“乡村歌剧”,并再次呼吁歌剧界给予足够重视。
二、关于歌剧的音乐性与戏剧性问题
长期以来,音乐性与戏剧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歌剧界。中国歌剧史70余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强调戏剧性忽视音乐性的,到了新时期之后才有根本改观。现在来看当代严肃歌剧的音乐性及音乐的戏剧性,其专业化程度虽不能说无懈可击,但作曲家处理手法之丰富与技巧之纯熟,却是此前任何一部同类歌剧所难以比拟的。
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剧本的作用、歌剧的戏剧品格,以及情节、冲突、动作、性格、形象这些基本的戏剧元素被弱化了,似乎歌剧剧本不再是歌剧的“一剧之本”,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何有利于歌剧音乐的充分发挥与表现;刻画人物及其性格,以及在冲突中塑造歌剧形象的任务依然未能引起歌剧家们的足够重视,因此不少剧本情节简陋、结构松散、故事平淡,人物性格及其发展缺乏内在根据,戏剧冲突人为痕迹很重;即使是正式上演的剧本,甚至是获奖剧本,也很少能够在这些方面经得起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双重推敲。
第二,音乐性被强调到了不恰当的高度,甚至高踞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当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将严肃歌剧简单理解为“一唱到底”了,但大多数作曲家依然不善于处理歌剧音乐的戏剧性课题,不善于用音乐手段来展开戏剧冲突,推进情节发展,因此一到抒情性场面便两眼放光下笔有神拼命渲染,但到了冲突性场面就心里发毛办法不多草草收兵,致使抒情性场面臃肿、冲突性场面简陋、戏剧节奏拖沓,歌剧形象犹如“注水猪肉”,一旦脱去水分便干瘪得难看,因此在戏剧品格和剧场特性方面显得特别乏味。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理论上认同瓦格纳“歌剧是用音乐展开的戏剧”这一权威定义的人们,在创作实践中往往将自己的作品变成了“为音乐而展开的戏剧”或“用戏剧展开的音乐”,即把欧洲古典歌剧时期早被抛弃了的那种“化妆音乐会”模式重新拣了回来,因此是一次“歌剧返祖”,我将之称为“欧洲古典歌剧综合症”。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向西洋歌剧学习时过多地把目光和兴趣停留在古典主义及早期浪漫派歌剧,比较重视莫扎特、罗西尼、俄罗斯及东欧民族乐派歌剧、早期威尔第等人作品的典范性和他们的艺术经验,却较少研究以中期瓦格纳、晚期威尔第和普契尼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歌剧,德彪西的印象派歌剧,以及以勋伯格、贝尔格、斯特拉文斯基、萧斯塔科维奇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歌剧,从而使我们的歌剧观念显得比较滞后,风格趋于古典;另一方面,即以对古典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歌剧的研究而论,我们也未能从其杰作(例如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威尔第的《弄臣》、比才的《卡门》等)中有效地吸收代表着那个时代并预示着下个时代的艺术精华和革新因素,有时甚至把某些消极、落后的观念(例如一贯轻视剧本和戏剧因素的作用、不适当地强调音乐的绝对地位、抒情咏叹调泛滥、声乐炫技表演盛行,以及古典编号体结构对戏剧情节和戏剧节奏连续发展的阻断与破坏,等等)当作基本经验来推崇和遵奉,其结果当然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为了有效地防止“欧洲古典歌剧综合症”,我建议作曲家们不妨严肃认真、仔细深入地解剖几个麻雀,下苦功夫研究一番威尔第的《阿依达》和《奥赛罗》、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和《罗恩格林》以及普契尼的《托斯卡》,我以为这五部杰作向我们提供了处理歌剧音乐性和戏剧性的绝好范例,而其观念、风格、结构、语言、技法既不似古典派那样过分传统和滞后,也不如现代主义那样过分激进和超前,在两极之间取其中,因此非常适应当代中国歌剧家的戏剧观念、艺术积累和中国观众的鉴赏能力;以此作为当代歌剧的风格立足点,应当是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子。
三、关于“大投资、大场面、大制作”
近年来,我国歌剧和音乐剧界崇尚“大投资、大场面、大制作”的风气很盛,“三大”成了歌剧音乐剧创作演出的必要前提,似乎没了这“三大”真有点儿寸步难行的味道。90年代以来,我本人看过不下三四十部歌剧和音乐剧,发现一个普遍现象:论艺术水平并不见涨,但制作成本却呈直线窜升趋势。音乐剧投资多则500万,少则100来万,而严肃大歌剧的制作成本则基本上都在100多万——300万之间。在80年代,许多院团花十来万、二三十万人民币就能制作一部歌剧或音乐剧,在今天绝对成了天方夜谭。
当然,不应当一般地反对“三大”。只要艺术生产规模确实需要,在财力上又有条件,艺术家们为什么要拒绝来自政府、企业或其他方面的慷慨?比如为了迎接建国50周年及澳门回归大庆,有选择地在有条件的单位或地区确定若干重点剧目,投入巨资,组织精兵强将,推出气度雄伟、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细的鸿篇巨制,确实应该。
不过,依赖“三大”,迷信“三大”,将它视为歌剧音乐剧创作演出的灵丹妙药、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认为搞歌剧音乐剧、搞精品非“三大”不可,投资动辄超过百万,剧组少说二三百人;盲目攀比之风盛行,不但在大都市、经济发达地区和省份搞,而且在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要搞,不但国家级剧院、省区级剧院搞,而且地市级剧团也要搞,有条件的搞,没有条件的硬着头皮也要搞,你也“三大”,我也“三大”,大家拼经费、拼设备、拼人海战术、拼舞台上花里胡梢,好像伟大作品只要用人、财、物拼命往上堆就一定能堆出来似的。加之许多剧目由于立项错误、把关不严、选题失准、决策有误或用人不当等原因,投入越多就失败得越惨。实际上,1990年以来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歌剧音乐剧总有几十部之多,国家总投资几千万上亿,但真正站得住的被在座各位公认的精品能有几部?虽然艺术创造(尤其是严肃歌剧)不能这样简单地算经济账,但眼看人民血汗哗哗地流,投入、产出如此不成比例,作为艺术家,我们于心何忍?
歌剧界这种言必称“三大”的风气,在理论上是对西方歌剧音乐剧制作方针的误解和误读(在欧美,中小制作并取得成功的作品不乏其例),在实践中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增加纳税人负担,劳民伤财,助长豪华、奢侈、浮躁、偷懒乃至腐败之风,回避艰苦的艺术创造,误国误民误艺术,殊不可取。
要扭转“三大”风气,首先要提倡从中国国情和各地具体情况出发,从剧目创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把中小投资、中小制作作为我们创作演出的基本方针和常见规模;确实需要“三大”的,更要反复论证、科学决策,严格把好选题关、立项关、用人关,大胆探索,谨慎操作,苦练内功,务使大投资有大效益,大场面有大手笔,大制作有大影响。
四、关于音乐剧的两个误解和两点建议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原创音乐剧渐成气候了。但在社会上乃至专业界,对音乐剧这种外来的舞台戏剧品种在认识上依然存在着大量误解。这些误解不破除,我国原创音乐剧要想实现突破性进展将是困难的。
我以为,人们对音乐剧的最大误读莫过于舞蹈方面。许多人不把音乐剧中的舞蹈看作是一种戏剧性因素,而只将它当作色彩性、展示性因素来使用。因此,许多音乐剧中的舞段和舞蹈场面完全游离于戏剧情节之外,与人物性格、戏剧动作毫无关联,一些编导甚至不惜将情节和冲突完全停顿下来作纯舞蹈的长篇表演和尽情展示;还有一些编导不懂得如何在音乐剧中用舞蹈手段来写戏、写人,不会营造某种机遇以便将舞蹈有机融入到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情感与行为中,融入到戏剧的情节与冲突中,使之成为塑造人物、推进情节发展的一个动力源;他们最习惯和最拿手的,就是将歌舞晚会那一套千篇一律的“舞伴歌”、“歌伴舞”模式照搬到音乐剧中来,以为这就是典型的音乐剧舞蹈了——这当然是一种莫大的误解。
还有一种误解,即把音乐剧局限在某一种规范之内,尤其是把能够接触到的某一部或某几部欧美音乐剧杰作视为圭臬,视为音乐剧的普遍规律,甚至视为不可移易的法则,用人家的尺子到处衡量中国原创音乐剧的长短,如果不合这把尺子就斥责我们创作的“不是音乐剧”——这种对欧美音乐剧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误解,在一个时期内曾经风行于音乐剧界、文化界和新闻界,当然也影响着创作人员的心态,使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变得小心翼翼地起来,生怕越雷池一步,生怕犯了天条而被人指责不是音乐剧,因此自己明明想搞音乐剧,搞出来的也是音乐剧,但宁可给它另取一个名字,也不轻易地叫做音乐剧。其实,欧美音乐剧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含着许许多多的风格,综合程度与面貌极其丰富多彩。其中既有歌、舞、剧三者并重的样式,如《西区的故事》;也有舞蹈成分极重的,如《群舞演员》;“话剧加唱”在中国歌剧中曾经受到激烈的批评,但在欧美音乐剧中则是家常便饭,如著名的《音乐之声》和《窈窕淑女》;当然也有对白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对白、音乐成分很重、形式上有些接近大歌剧的,如30年代的《波吉与贝丝》和80年代的《歌剧院幽灵》。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搞出来的作品与任何一部欧美音乐剧也对不上号,但只要观众欢迎、市场接纳,这就是成功的中国音乐剧,这就是中国艺术家对世界音乐剧的独特贡献!我们应当有这种信心和雄心。
最后我对中国音乐剧提出两点建议。
其一是提醒大家在发展中国原创音乐剧时,不要忘了中国传统戏曲。虽然从文化性质说音乐剧与戏曲有重大区别,但就艺术构成和组合状态看,两者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王国维为传统戏曲所下的定义“以歌舞演故事”甚至可以直接视为对音乐剧艺术特征的准确概括。实际上传统戏曲是个宝库,有许多极为宝贵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此,我们搞中国音乐剧,要用两只眼睛看,两只耳朵听,一双手都要伸出去,绝不要像半身不遂似的,只盯着欧美、日本,对自己身边的东西,反而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其二是,中国原创音乐剧在向欧美音乐剧学习时,应该怎样为自己定位?换句话说,欧美音乐剧已有百年历史,我们应当盯着其中的哪一个时代、哪一种风格才比较切合中国市场和观众的实际呢?我的建议是:从制作规模说,提倡二三十万至百万元以下的中小规模、中小制作。从时代风格说,美国百老汇50年代——70年代的歌舞剧风格更适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此前的略显滞后,此后的又嫌超前。从戏剧风格说,还是以喜剧、讽刺喜剧、抒情喜剧、悲喜剧为主,强调幽默感、娱乐性和剧场趣味,较易为观众接受;一开始就搞正剧、悲剧,戏剧内容、呈现方式和节奏很容易陷入沉闷、滞重,音乐剧活泼、幽默和强烈的娱乐性、趣味性优势反而被抑制住了。
1999年对于中国歌剧和音乐剧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不光是说今年适逢建国50周年、澳门回归及世纪交替这“三喜临门”,我们歌剧和音乐剧正好驾此浩然长风,迎接创作繁荣、佳作迭出新高潮的到来,而且也是说,我国歌剧和音乐剧经过开放20年来的实践和积累,有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锻炼了队伍,增长了才干,现在是到了出大师、出杰作的时候了!我真诚地预祝,这大师,这杰作,能够有一部分从在座的同行之中涌现出来!
标签:音乐剧论文; 戏剧论文; 歌剧论文; 音乐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音乐论文; 古典音乐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