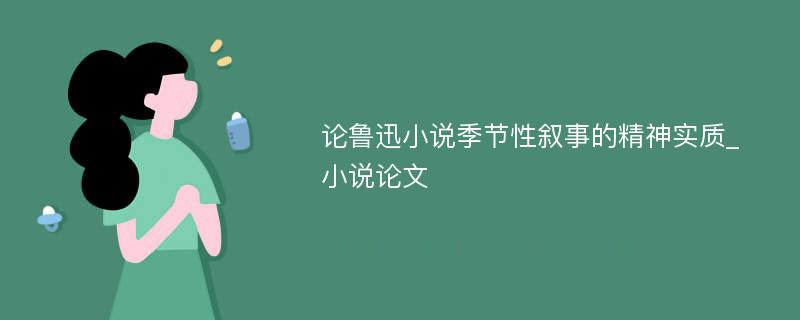
论鲁迅小说的季节叙事的精神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本质论文,季节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4)06-0081-05
季节是鲁迅的小说中最重要的时空叙事机制,鲁迅为自己的小说设置了春夏秋冬四种 不同的季节场景。在小说中,这些季节场景并不仅仅是故事发生时间的一种参照,而主 要是表达了叙述者在不同的季节中的生存感受。本文主要以当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鲁迅 小说的季节场景与作家的生存体验之间的关联性为出发点,力图探索鲁迅小说的季节叙 事的精神本质。
一
作为小说的叙事控制机制之一,鲁迅小说的时空叙事主要表现在季节的设置上。尽管鲁迅的小说在篇幅上相对是短小的,然而,在时空叙事的建构上,鲁迅的小说却表现出少有的复杂性。从时空叙事的类型上来看,鲁迅的小说主要运用了三种季节叙事场景。
冬季叙事是鲁迅的小说中运用得最多的时空叙事机制。虽然鲁迅出生在江南水乡,但 是,他的小说中的冬季叙事具有典型的北方特色。从鲁迅的小说中,我们首先感受到的 是冬季叙事带来的阴冷和寒意。叙述者不仅是为小说营造一种冬季场景,而且也对冬季 场景进行了主体性的扩张,这种时空叙事方式产生的情感效应最集中地体现在农村题材 的小说中。《故乡》讲述的是叙事人回到阔别了20多年的故乡的故事。对于长期远离家 乡的游子来说,故乡总能勾起他们的许多美好记忆,故乡在他们心中总是温馨的。然而 ,《故乡》的叙事人面对的却是毫无暖意的“故乡”:“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 ,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 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1](P476)在这种情形下,叙事人的心情当然 就“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而当看到家中房屋的“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时” ,就更“没有什么好心绪”了。故乡也许有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但“我”是为了“专 别他而来的”,再加上看到闰土像一个“木偶人”的凄凉景况时,阴冷的感觉就更加明 显了。叙述者显然是从叙事主体的情感角度为基点,有意强化了小说开头的冬季叙事的 冷清格调。《祝福》也采用了冬季叙事的时空机制,但是叙述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刻意 强调冬天的严酷。在小说开头对年关气象的描写中,人们似乎感到了一种新年到来时的 “暖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声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2](P5)虽然天空中布满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但是“幽微的火药香”也使人们想到了即将到来的岁末团聚的欢欣。然而,随着叙事人对祥林嫂故事的讲述,小说的冬季叙事的暖色逐渐被冷色所代替。当祥林嫂向“我”询问了一个人死后有无灵魂后,“阴沉的雪天”使叙事人产生了“不祥的豫感”;而当“我”听到祥林嫂的死讯后,飞舞的 “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到沉寂。”冬季场景 的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叙事人情绪的波动完全是依照祥林嫂的命运的变动来安排的。
如果说鲁迅小说的冬季叙事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冬天所固有的凄冷气息的话,那么,他 的小说的夏季叙事所表现出来的冷暖色调要复杂得多。尽管现实生活中的夏天是酷热难 当的,但是,《明天》中的夏季叙事却凉得有点怕人。单四嫂子为儿子的病而彻夜未眠 ,焦躁不安,天还没有亮就抱着儿子去就诊。回家的路上她已经累得有点麻木了,尽管 “太阳早出了”,但是单四嫂子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热气,她的衣服甚至“渐渐的冰着肌 肤”;儿子死了之后,她又“张着眼”从太阳落山一直坐到“东方渐渐发白,窗缝里透 进银白色的曙光……银白色的曙光渐渐显出绯红,太阳光接着照到屋脊。”[1](P454) 单四嫂子哭了一整天,当“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时,她居然“有点平稳了”。 虽然叙述者的夏季叙事选择的是暖色调的“太阳”,但是,小说中的太阳是“零度”的 ,没有夏日的灼人气焰。与《明天》对夏季叙事的冷处理不同,《示众》中的夏季叙事 完全是热浪滚滚的。从小说开头的叙述中,读者立刻感受到了盛夏的可怕:“火焰焰的 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 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动物们对酷 暑是无能为力的,然而看客们却对“盛夏的威力”满不在乎。为了能够看到被示众者, 秃头宁愿自己的脑袋“被太阳晒得光油油的”;瘦子则伸长了脖子,看得“竟至于连嘴 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胖大汉被围在人群中间,挤得连自己的“两乳之间的洼 下的一片汗”也顾不上擦;抱着小孩的老妈子也不管自己的“梳着喜鹊尾巴似的‘苏州 俏’”撞了车夫的鼻梁仍然使劲往里钻。对于这些看客们来说,炎热的天气阻挡不了他 们围观的欲望,他们想要知道这个“蓝布大衫上罩着白背心的男人”究竟“犯了什么事 ”[2](P69)。正是凭借强化了的夏季叙事场景,小说才充分展示了看客们的无聊心理。
春季叙事和秋季叙事的组合形成了鲁迅小说的第三种季节叙事场景。冬季与夏季处于 冷与暖的两极,它们在鲁迅的小说中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季节叙事场景,而春季与秋季因 其在冷与暖之间的过渡性常常被叙述者设置在同一篇小说中,从而使其具有了独立的时 空叙事形态。《药》中的第一段故事发生在“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 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此时也正是夏瑜被害的时 间,叙述者把“秋天的后半夜”的阴凉与人物的心理感觉相联系,因而当华老栓拿着钱 到街头去换人血馒头时身上“觉得有些发冷”。《药》中的第二段故事发生在清明时节 ,尽管已经到了春天,但是天气“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这样冷清 的天气与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她们都在为死去的儿子悲伤,尽 管两人的儿子的死亡原因是截然不同的。祭奠完毕后,她们似乎听到“一丝发抖的声音 ,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1](P448)叙述者以“冷” 和“静”为中心,使秋天和春天构成了一个季节叙事整体。在《伤逝》中,叙述者把故 事的发生放在了暮春。这是一段“最为幸福”的时光,子君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和世 俗观念的偏见,勇敢地和涓生同居了。然而,悲剧早已暗伏并且开始生长,叙述者将它 的全面爆发放在了秋季。起先是涓生丢了局里的差事,继之是他为杂志译稿毫无结果; 当生活完全没有着落时,子君饲养的油鸡成了餐桌上的美味。在熬过了“极难忍受的冬 天”后,子君无可奈何地回到了老家,最后在“父亲的烈日一般地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 霜的冷眼”中死去了。春季是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起点,也是他们的爱情终点,而秋季则 是这个过程的推动者。在“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2](P121)的双重氛围中,叙述者完 成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故事的春季叙事与秋季叙事。
二
鲁迅对以季节为主体的时空叙事机制的选择与运用不仅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时 空场域,而且也表达了叙述者明确的情感指向,透过小说的季节叙事层面,我们看到了 渗透在小说中的叙述者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内涵。由于季节叙事的多样性,鲁迅小说的情 感内涵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它们的产生不仅是与小说的季节叙事直接相关的,而且也是 叙述者的生存体验的情绪化表现。
在鲁迅小说的冬季场景中,叙述者的冬季叙事无疑是阴冷的。然而,在阴冷的冬季叙 事的笼罩下,却显示出叙述者热切的情感趋向,阴冷与热切的两极对立和冲突形成了鲁 迅小说的第一种情感模式:“冬—热”。《在酒楼上》的叙事人“我”回到故乡时正是 “深冬雪后,风景凄情”。为了排遣寂寞,“我”来到了过去经常光顾的小酒楼,却不 期遇到了“旧同窗”和“旧同事”吕纬甫。没有想到的是先前“敏捷精悍”的吕纬甫此 时已经行动迟缓,又黑又浓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光采”,须发“乱蓬蓬”的,精 神相当的颓唐。窗外“渍痕斑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而“铅色的天,白皑皑的 绝无精采”,这一切与吕纬甫神情上的萎靡共同营造了一种凄凉的氛围。然而,“我” 因偶遇朋友的热情并没有被吕纬甫的沮丧所压抑,在酒菜的“热气”中,“我”高兴地 谈论过去的生活以消除他精神上的沮丧。吕纬甫也渐渐地“眼圈微红”了,眼睛闪出“ 射人的光来”,甚至“满脸已经通红”,似乎“我”对他的热烈的“期望”已经兑现了 ,“我”对吕纬甫的热心显然是不希望他如此“沦落”下去。《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 “吃洋教”的“新党”,祖母死后只是在灵前“弯了一弯腰”,入棺时没有像村里人想 象的那样嚎啕大哭,因此被看作是一个“异样”的人。然而,大殓结束后人们准备散去 时,魏连殳却“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就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 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2](P88)魏连殳的“独立特行”与周围的 人形成了行为和意识上的对立,他只能生活在冰冷的社会氛围中。“我”在一个冬天第 三次见到他时,他的生活状况依然如旧,甚至连“‘天真’的孩子也仇视起来”了。“ 我”只好劝他结婚,要他改变生活方式,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真心地希 望他“活下去”。显然,小说的叙述者将自己的同情通过叙事人“我”投射到魏连殳身 上了,因为鲁迅一直觉得“自己并无如此‘冷静’”[3](P54)。
与冬季场景的阴冷相比,鲁迅小说的夏季场景常常是炎热的。尽管由于叙述者的主观 扩张,鲁迅小说的夏季叙事的情感基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夏季叙述流露出来的 情感态度却共同指向了冷漠,“夏—冷”成为鲁迅小说的第二种情感模式。《风波》的 故事发生时正当夏天的傍晚,“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红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 ,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老人们坐在土场上不停地“摇着大芭蕉扇”,驱赶着难熬的 热气。这一切都意味着小说的夏季叙事是火热的,然而,叙述者的情绪并不因夏日气温 的上升而高涨,反而变得相当的冷淡。叙述者表现出来的与夏季叙事完全相反的情感趋 向主要体现在对小说人物的态度上。赵七爷在阶级层面上属于统治者,在伦理层面上属 于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他总要用虚假的道德维护自己的权威,所以当八一嫂说错了话时 他就感到气愤;七斤虽然在阶级层面上属于被统治者,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何尝不向赵 七爷看齐,在心里也“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希望村里人和妻子能够给他“相当的 尊敬”。叙述者对赵七爷一类的人物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对七斤一类的人物虽然没有 什么恶意,但是似乎也没有必要将热烈的情感天平倾斜过去,因而只能表现出淡漠的情 绪来。《示众》的夏季叙事本来就具有象征性,小说中的夏季场景固然是燥热的,而叙 述者在夏季叙事过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它,从而为看客们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时空背景 。无论是胖孩子、小学生,还是秃头的老头子、红鼻子胖子,或者是梳“苏州俏”的老 妈子、夹洋伞的长子等等,他们都“呼着热气”,全然不顾身上流下来的汗,要使劲挤 进围观人群的中心。叙述者愈是强调夏季叙事的酷热和看客们对酷热的无所谓,便愈是 显示出叙述主体情绪上的冷静,乃至冷漠。看客们的麻木和无聊意味着他们“只能是被 启蒙的对象”[4],“化大众”实在是必要的。夏季叙事的酷热与叙述主体的冷漠的强 烈对峙,使鲁迅的小说呈现出强大的情感张力,从中也可以发现鲁迅的精神世界的复杂 性。
如果说鲁迅小说的冬季叙事与夏季叙事主要是以冬季的阴冷与夏季的炎热象征性地表 达了叙述者的冷热对立的情感趋向的话,那么鲁迅小说的春季叙事和秋季叙事则是以冷 与热之间的过渡性特征显示了叙述者的“爱憎不相离”[5](P173)的情感内涵,“春秋 —爱憎”成为鲁迅小说的第三种情感模式。在《药》中,叙述者的爱和憎的感情是投射 在不同的人物形象上的。华老栓夫妇不得不于“秋天的后半夜”起床,用省吃俭用存下 来的钱去换人血馒头;夏四奶奶更是不知道儿子的死因,只有在清明时节提着“破旧的 朱漆圆篮”去为儿子祭奠,叙述者对他们的精神愚昧是痛心的,但是又极为同情他们的 命运,因而对他们是充满了“含泪的温情”的,是“爱”他们的。而对于那些争看杀人 场面的看客,和在茶馆里聊天的茶客,叙述者则是持严肃的批判态度的,是“憎”他们 的。到了《阿Q正传》,叙述者的爱和憎的感情便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阿Q成了“爱憎 不相离”的情感模式的集中体现者。阿Q的故事主要是在春季叙事和秋季叙事中完成的 。在春天,阿Q不仅被王胡打败了,接受了“生平第一件的屈辱”,而且也挨了假洋鬼 子的揍,遭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因为向吴妈求婚,阿Q不仅损失了所有冬天的衣物,而且也失去了在未庄居住的资格。在秋天,阿Q为了谋生只好跑到城里去,等到回来时却成了未庄的“名人”——未庄人眼中的“偷儿”;在要求参加“革命”遭到拒绝后,阿Q最后成了赵家遭抢的替罪羊而被杀头。一方面,阿Q因为饱受欺压而完全丧失了生存的可能,他是不幸的;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耽于幻想、自我欺骗、易于健忘、向更弱者泄恨等等“由精神胜利法派生出来的病态”,他又是可恶的。叙述者是“憎”阿Q的,也是“爱”阿Q的,“憎”与“爱”在阿Q身上是相互交织的。在从春季叙事向秋季叙事的转化过程中,叙述者对阿Q的感情也经历了“由憎而爱”[6](P207)的转换。
三
鲁迅的小说对季节叙事的刻意强调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表达了叙述者的精神体验。在鲁 迅的小说中,季节叙事和叙述者的情感指向常常是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种表述方 式和思维定式既是外部世界在叙述者心灵上的投影,又是叙述者内心世界的外射,是 “对象自我化与自我对象化”[5](P41)的高度融合。也就是说,鲁迅小说的季节叙事是 充满了主体意识的,是叙述者的精神本质的显现。
鲁迅小说的季节叙事显现出来的叙述者的第一种精神体验是孤独。在整个“五四”时 期,鲁迅一直处于孤独的生存状态之中,鲁迅的孤独一方面来自他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 对个体超越性的追求,他力图凭借自我的生存体验来发现人的精神本质,以便摆脱“庸 众”的包围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来自他与封建礼教、黑暗现实和社会流俗等 等之间的不相容以及与“庸众”之间的无法沟通。《故乡》中的“我”在严寒的冬季回 到家乡的现实目的是为了搬家,但是在精神深处却是为了寻梦。“我”是以平等的方式 期待着与闰土的见面,然而闰土的一声“老爷”不但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希望,而 且也将“我”推向了与闰土无法交流的孤独境地,“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 将我隔成孤身”,只好在肃杀的寒气中离开了故乡。《祝福》里的“我”临近年关回到 故乡只能“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因为“我”早已“没有家”。由于是寄人篱下 ,当然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冲突,“我”与鲁四老爷之间的谈话是“总不投机的”,最 后只有“我”一个人“剩在书房里”。如果说“我”与鲁四老爷之间是“不愿”交流的 话,那么“我”与祥林嫂之间则是“不能”沟通。因为“我”在河边碰到祥林嫂时她已 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所以“我”准备着她向“我”讨钱。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 向“我”询问了“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问题,而“我”只能以“说不 清”作答。“我”对祥林嫂的回答与其说是出于对她的同情,不愿让她陷入精神上的绝 望,还不如说是由于祥林嫂与“我”之间的差异使“我”无法进入她的内心世界。祥林 嫂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愿意与她交流;“我”同样也是孤独的,因为“我”无法与她 沟通。在“阴沉的雪天”里坐在“无聊的书房”里,“我”似乎只有离开鲁镇才能摆脱 孤独的困扰。
鲁迅的孤独的精神体验不仅表现为他与“庸众”的无法沟通,而且也表现在作为思想 启蒙者的自我在寻求个人价值时的无人认同。在鲁迅的小说中,不仅大多数的小说叙事 人“我”是如此,而且像魏连殳、吕纬甫和涓生等大多数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他们都因为坚持一种“高傲的姿态”[7](P436)而被周围的人们孤立了起来。魏连殳由于倡导“破坏家庭”、在祖母入殓后才开始“大哭”、将房屋“无期地借给”侍奉祖母的女工等一系列的“非孝”行为而被村里人排斥,在“淡漠的孤寂和悲哀”里熬着日子。当他的行为一再受到流言的批评和攻击时,他只好当了杜师长的顾问,“躬行”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力图报复社会。吕纬甫曾经是一个敢拔城隍庙神像的胡子、为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而打架的人,然而10年后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了。吕纬甫如同一只“蜂子或蝇子”,当他最初的个人追求得不到周围人们的认可时只好随俗,在人生的旅途上绕了一个“小圈子”。在无人认同的生存环境中,吕纬甫、魏连殳等人像是一匹孤独的狼嗥叫,而“我”同样也是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正是通过这些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生活道路上的“回、归”,叙述者“寄寓了自己孤独寂寞的情怀”[8]。
鲁迅小说的季节叙事显现出来的叙述者的第二种精神体验是绝望。虽然鲁迅的小说因 为季节叙事的不同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情感趋向,但是,完全不同的季节叙事却产生了 大致相同的精神体验。在无人呼应的孤独的生存状态下,叙述者感到了空前的绝望。不 仅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绝望中,而且小说的叙事人也因为他们没有希望的生活而充满了 绝望。在冬季叙事里,《故乡》中的“我”回归故乡的心情本来就是“悲凉”的,对故 乡也就不抱什么希望。当“我”看到闰土从一大堆不必搬走的东西里拣了一副香炉的烛 台时,“我”对闰土彻底绝望了。因为当一个人生活在偶像崇拜中时,还能有什么希望 呢?叙事人没有从闰土身上看到任何希望,而《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丧失了活下去的 信念的,因而只能带着人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疑问在恐惧中死去。尽管“我”对《孤 独者》中的魏连殳和《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是充满了希望的,然而,魏连殳在放弃了 个人的价值追求后孤独地死去了,吕纬甫也并没有在“我”的期盼中走向“新生”,只 有“我”独自在深夜中嗥叫,在寒风和雪片交织的“罗网”中游走。在夏季叙事里,《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虽然是一个“粗笨女人”,但是她也能够感受到儿子的死亡带给她 的只是“静和大的空虚”,对于别人来说“明天”也许是满载着希望的,但是,对于单 四嫂子来说,“明天”则意味着更大的绝望。《风波》中的七斤虽然因为被人剪了辫子 而在“皇帝坐了龙庭”时被赵七爷、自己的妻子和村里人所贱视,但是,当“皇帝不坐 龙庭”时,赵七爷的辫子重新“盘在顶上了”,七斤也得到了村里人的“相当待遇了” ,鲁镇又回到了往日的死寂状态中。在春季叙事和秋季叙事里,《药》中的夏四奶奶在 清明上坟时想让一只乌鸦落在儿子的坟头来证明儿子的死是冤枉的,然而,当她回过头 还没有走上二三十步远时,那只乌鸦却大叫一声飞远了,夏四奶奶仅有的一个愿望也落 空了。《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自以为得到了爱情就拥有了一切,然而,当更为重要的 生存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的爱情也就显得不堪一击了。虽然春天已经来临,但是 子君却不得不回到父亲的家里,在“广大的空虚”和“死的寂静”中走向死亡。“我” 虽然可以在祈求子君的饶恕和宽容的忏悔中寻找“新的生路”,但是,这“新的生路” 却更加“虚空”,让“我”看不到边际。尽管鲁迅后来在对绝望与希望的关系的思考中 否定了绝望,但是绝望作为一种精神体验却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小说中。
收稿日期:2004-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