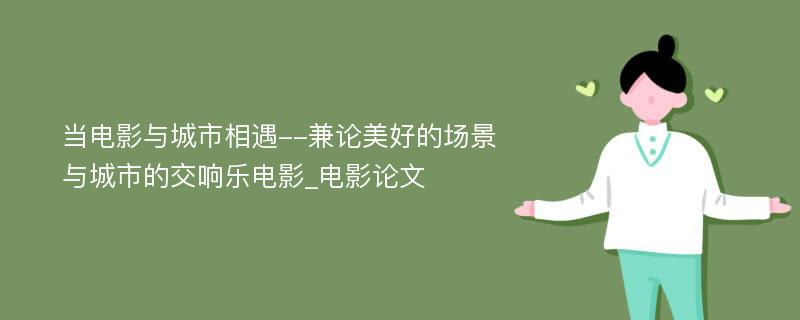
当电影遭遇城市——试论《尼斯景象》与城市交响曲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斯论文,城市论文,电影论文,交响曲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电影开始的地方——城市
巴黎是19世纪末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城市之一。电影诞生于巴黎,而巴黎自然也成为电影捕捉的第一个表现对象,《火车进站》、《工厂的大门》拍摄的正是现代城市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元素:火车和工厂——火车是典型的现代交通工具,而工厂是工业文明的标志。
古老的皮影被誉为电影之父,银幕、影人、声音、投射光等与运动、切换手法已经孕育了电影的基本元素,但那是与农业文明勾连的艺术形式:节奏、主题与传播方式。更重要的,皮影的动力全靠人力,而电的发明不仅改变了物质世界的动力,也促进了艺术形式的转换。
电影与现代城市都是现代科技的产物,电影与城市的相遇建立了一种节奏,呼应着时代的律动。城市——因为工业化而突然成为人类拥挤的居住地,引发陌生的生活经验:钢铁、玻璃建筑,电车,工厂的机器、烟囱以及随之而来的准确的上下班打卡,夜生活、堕落与躁动。美国诗人桑德堡是一位城市歌手,他歌颂城市和现代工业的节奏,如《南太平洋铁路》、《特等快车》和最为著名的《芝加哥》——这首诗回应着火车的节奏与钢铁的力量:
在煤烟下,尘埃抹了他满嘴,露着白牙齿轰笑着,在可怖的命定之重荷下,像一个年轻人似的轰笑着,轰笑着甚至像一个从未战败过的无知的拳击手,矜夸又轰笑着,他的手腕下是脉搏,而他的肋骨下是人民的心脏之跳跃。
轰笑着!①
电影遭遇城市,缘于一种内在元素与节奏交响。于是,一种名为城市交响曲的电影样式诞生了。
二、城市交响曲电影
城市交响曲电影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1890—1976)在1920年完成短片《曼哈塔》(Manhatta),它以前卫的视觉形式展示了四个不同的视觉主题,总长度为七分钟,共有65个镜头。影片分为四个部分,其组合方式接近于音乐上交响曲的结构。《曼哈塔》中的动感大多来自城市中的景观被抽象化后的线条、形状、质量以及脉动所交织的韵律,宛如一种视觉上的交响曲。
《曼哈塔》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其他以视觉韵律为主体的前卫电影的滥觞。1927年德国导演鲁特曼(Walter Ruttman)的《柏林——一个城市的交响曲》(Berlin,Symphony of a City),1929年苏联导演狄加·维尔托夫(Dizga Vertov)的《带摄影机的人》(The Man With Movie Camera),1930年美国导演温柏格(Herman Weinberg)的《城市交响曲》(City Symphony)都是经典的例子。其后城市交响曲电影发展为一个类型,出现于世界各地。
城市交响曲是电影遭遇城市的产物。
电影作为当时最为前卫的一种大众媒介,城市作为科技成果的载体——尤其是火车、汽车与机器,象征了一种崭新的现代工业文明。城市交响曲电影表达的不是普通的城市生活,而是城市的现代节奏。节奏感、形式感、运动感建立起城市交响曲电影的突出特征。
城市交响曲电影是先锋电影与未来主义艺术思潮的合谋,未来主义对力量、速度与钢铁的崇拜赋予城市以激情,先锋派赋予交响曲电影以形式,线条、运动与速度构成城市交响曲表达的主题。
三、法国城市交响曲电影——《尼斯景象》
2006年法国纪录电影展是法国纪录电影的一次检阅,虽然城市纪录电影并不是其中的主流,却是颇有特色的一个部分。《美丽巴黎》、《重温维兰街》、《塞纳河畔》和《尼斯景象》都属于城市电影,《尼斯景象》呈现了城市交响曲的典型形态。
《尼斯景象》诞生于1930年,在《柏林——一个城市的交响曲》和《带摄影机的人》之后。因此,从形式上谈论创新未免失之夸张,但让·维果之所以成为让·维果,正在于他不会简单地重复别人。这位“兰波式的天才”借用了城市交响曲电影的结构方式,却置换了全然不同的新异内涵,把这部作品从普通的城市交响曲电影中提升出来,显示了卓越的创造性与艺术激情。如果把《柏林——一个城市的交响曲》、《带摄影机的人》与《尼斯景象》作一比较,将会发现在城市交响曲的同一模式下展示的不同艺术个性。
《柏林:一个城市的交响曲》以火车进入柏林开始一天的生活,工人打卡上班,机器转动,晚上工人下班,去酒吧饮酒,过夜生活。结构严谨,视觉元素饱满,历时性、完整地呈现了城市生活的一天。这是一部标准的城市交响曲电影:结构、元素、主题与表现方式——万花筒式结构、机器崇拜、运动感、节奏感与形式感——表现为未来主义热情奔流。
《带摄影机的人》采用了城市交响曲的结构,但把它复杂化,变成一个套层结构,犹如一道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它以一架巨大的摄影机开始,以摄影机镜头关闭结束,中间是摄影机活动的历程:火车通过、烟囱、工厂、街道、大坝、海滨浴场、电影车间等。维尔托夫还把摄影师拍摄电影、剪辑师剪辑的过程、电影完成之后的放映这一完整的电影制作过程放进影片,表达对电影本质属性、电影功能与电影语言的思考。城市生活仅仅是影片的表层图像,隐藏在背后的是电影眼睛理论:电影眼睛改变生活,电影眼睛创造生活……这不仅是一部实践与理论完美结合的电影,而且超越了未来主义的机器、力量和速度的崇拜,赋予机器以国家激情与阶级意识。《带摄影机的人》的电影语言、表现元素、主题与表达方式在创作起点与最终实现的效果方面都远远超越了《柏林——一个城市的交响曲》。
让·维果的《尼斯景象》更进一步,它留下的仅仅是万花筒式结构方式,即按照时间线索结构影片:从晨开始,到夜结束,中间是发生在尼斯的活动,而基本构成元素已替换一空:工厂机器、电车、火车以及运动、速度这些城市交响曲电影的核心元素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海滨、街道、休闲的贵族、狂欢的人群、面具与贫民窟景象。让·维果洗劫了未来主义的机器激情,代之以社会观察,但保留了城市交响曲电影的形式:节奏、动感和先锋艺术表达方式。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部电影的特征:“法国先锋派纪录电影的杰作是让·维果的《尼斯景象》。在这部充满激烈的、尖锐的社会讽刺的影片中,既有布努艾尔式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也有维尔托夫理论的影响。维尔托夫的弟弟和门徒鲍里斯·考夫曼是维果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在这部影片里,作者一方面以无情的眼光显示狂欢节的疯狂胡闹,意大利式墓地里的可笑情景,大旅馆里那些富丽堂皇的雕像石柱,衣饰时髦的女人,讨钱的乞丐,高级的小哈巴狗;另一方面,和这些画面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古老尼斯的狭巷里窗口上晾着的衣服,将要倒塌的墙壁,贫民窟里生病的穷孩子们。由于这些形象本身就有直接和深刻的意义,因此这种对比就显得更为感人。”[1] (P42)萨杜尔注意到了《尼斯景象》艺术特征的源流——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与超现实主义,以及影片中呈现的鲜明的左倾意识——贫富对比。
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在《尼斯景象》中得到饱满的展示,这与影片的摄影师鲍里斯·考夫曼是维尔托夫的弟弟有关。鲍里斯大量采用电影眼睛的拍摄方法,即“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影片中的多数镜头是在隐藏状态下拍摄的,人物表情、动作自然生动,如贫民窟中猜拳的场面、沙滩上晒太阳的人、海滨浴客、走下汽车的阔太太、音乐会上昏昏欲睡的面孔,这些镜头为《尼斯景象》作为一部纪录电影的文献价值提供了担保,但无论鲍里斯还是维果都不满足于这种记录,他们的目的是突出创造性与想象力,让摄影机参与创作,而不是简单记录——这同样是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观点。鲍里斯赋予摄影机以生命,摄影机仿佛电影制作者的眼睛,主动参与到寻找与创造的过程,其中旋转镜头的运用别有韵味。摄影机在尼斯街道茫茫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接近一个人,从他的一侧转到另一侧,好像一个人转过头去看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发现不对又悠然走开。鲍里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拍摄,让静止的建筑、雕塑或者风帆动起来,赋予静态意象以动感,如在影片开头进入城市街道的公路几乎在飞奔,运动感是《尼斯景象》视觉形象的突出特征——网球、帆船、海浪、游行的人、舞会这些本来就处于运动中的拍摄对象与静态意象的运动处理让动感充满影片的每一幅画格。
寻求陌生的视角出于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也是鲍里斯的艺术追求,因此,大仰、大俯、怪异的视角与不规则构图成为《尼斯景象》的常规方式:一位老妇人的近景在画面上如同一座山峰般高大,烟囱、房子缓缓移动划过画面,垂直视角下的海滨街道……这些还不够,鲍里斯躲在下水道的井里拍摄街道上的行人(这令人想到《带摄影机的人》中仰拍火车通过的镜头),在几乎垂直的视角仰拍疯狂舞蹈的女子,贫民窟两座高楼中间的一线天,倾斜的建筑,倒吊的雕像……这些陌生化视角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观众在一个习以为常的世界发现了新异的景象。
认识摄影的价值对于理解《尼斯景象》是一条积极的路径,因为这是一部默片。
然而,维果并没有在鲍里斯摄影机的位置上驻足,作为一位导演,他通过对意象的并置、交叉和对比创造了新的含义。在剪辑上,《尼斯景象》以叠画为主,但维果也用慢动和快动镜头强调节奏感与运动感;用抽桢镜头表现城市街道人来人往的熙熙攘攘场景在当代电视上较为普遍,维果在《尼斯景象》中就这么做了,而且都是手动剪辑。慢动是为了让观众对某一意象注目或者思考,街头女子狂舞的慢动场面似乎为了提醒观众思考这些女子狂舞的意义,因为这一镜头在《尼斯景象》中重复了17次,其中慢动为四次,拍摄角度全部为大仰,但其中两个镜头为垂直拍摄,女子肆无忌惮地扬起玉腿,扭动腰肢和屁股,没有羞耻也没有思想——或许是狂欢到放浪形骸之外,或许是放荡不羁。女子狂舞的镜头反复出现,形成交叉剪辑——这也是《尼斯景象》频繁使用的手法,因为城市交响曲电影的万花筒结构缺乏故事线索或人物贯穿,必须通过意象重复、交叉来完成影片结构。如网球与帆船、烟囱与老太的交叉,《尼斯景象》通过交叉剪辑创造节奏。
为了鲜明而饱满地表达观点,维果大胆使用蒙太奇——在一位阔太太昂首阔步走过大街镜头后面,维果剪辑了一只高举脑袋、引颈张望的鹅,这种戏拟式蒙太奇表达了他的反讽。超现实主义场景为《尼斯景象》平添了异样的色彩:一位阔太太坐在海滨凉椅上,身上的服装不断变化——从薄裙、套装、连衣裙直到裸体六种方式——这既可以理解为观众对阔太太的不同心理想象,也可以读解为制作者对人类伪装与袒露的思考,或者其他。同样,擦鞋工人为一位游客擦鞋的镜头突然变为擦一只光脚。这种荒诞场景类似于布努艾尔《一条安达鲁狗》中用刀片割眼睛的镜头。维果拍摄的这两个场景当然是表演性的,并且不是真实再现,而是企图借助这些布努艾尔式的场景表达他对尼斯的认识与想象,也透露出维果的童心、叛逆与不守成法的艺术个性。从观影心理来看,这两个场景突然出现在一部纪录片中造成视觉经验的猝然中断,激发观众的思考,也调节了电影的气氛和趣味。
《尼斯景象》既不是资本家投资的产品,也不是基金会资助的文化项目,维果制作这部影片的动机异乎寻常地单纯:富有的岳父给了一笔钱,他便无忧无虑地把它花掉,而拍电影最契合他表达的愿望。但维果拍摄《尼斯景象》不是简单地记录尼斯生活,而是以现实中捕捉的素材表达作者的情感与观点:他有话要说。事实上,1930年6月14日,在巴黎老鸽笼影院《尼斯景象》放映前维果确实发表了演说:“我想和你们谈一种更为鲜明的社会电影。我对这种电影比较熟悉:这是一种社会纪录片,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纪录的观点(point de vue documenté)。这种社会纪录片与所有的纪录片和每周的新闻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含有作者清楚地在片中采用的观点。这种社会纪录片需要一种立场,因为它要详细说明事实。它即使不表现一个艺术家的观点,至少也要表现一个人的观点,人和艺术家两者都是同样有立场的。摄影机将对准那些应当作文献记录下来并且将通过蒙太奇来加以解释的现象。当然,这里不允许有意识的表演。人物应出其不意地来摄取,否则就无疑抛弃了这种电影的文献价值。如果我们能够显示一个姿势所隐含的意义,能够从一个普通人身上出其不意地揭示出他内在的美或者他滑稽可笑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社会的一次纯物质表现而显示出一个社会的精神,那么,我们就达到了纪录片的目的。而这样的纪录片就含有一种力量,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们以前漠然与之相处的世界的内在面貌。这种社会纪录片将开阔我们的视野。影片《尼斯景象》只是这种电影的一个简单的雏形”[2]。
维果所说的观点纪录片其实并不是一种新鲜的样式,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带摄影机的人》、伊文斯的《英雄之歌》、格里尔逊的《漂网渔船》都是观点鲜明的社会纪录片,但《尼斯景象》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维果把城市交响曲的未来主义机器崇拜改造为社会批判,赋予这种电影形式以社会激情,尽管萨杜尔过于看重豪华景象与贫民窟的对比,从而把社会功能提升为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品质。
拍摄《尼斯景象》时让·维果只有25岁,第一次选择用电影作为表达自己的方式,把反叛、激情与梦想熔铸在一部电影里,创造了一种高度——不是情感的浓郁与观点的锐利,而是赋予情感一种准确的表达形式,一种抗拒时间、免于腐朽的美学元素。
城市交响曲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基本模型,也创造了美学高峰,记录了人类遭遇城市生活的心理图景。当钢筋混凝土与大块玻璃编织着每一天的风景,当钟表兢兢业业地每日提醒我们上班下班的时间,这种曾经激动人心的艺术样式在时间的流动中渐渐沉落。不过,城市交响曲电影并没有消失,它的美学元素依然潜伏在新的艺术中,比如张艺谋为北京奥运拍摄的形象片、电视台日常播出的MTV与电视频道上川流不息的广告片。
注释:
①转引自张同道:《探险的风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