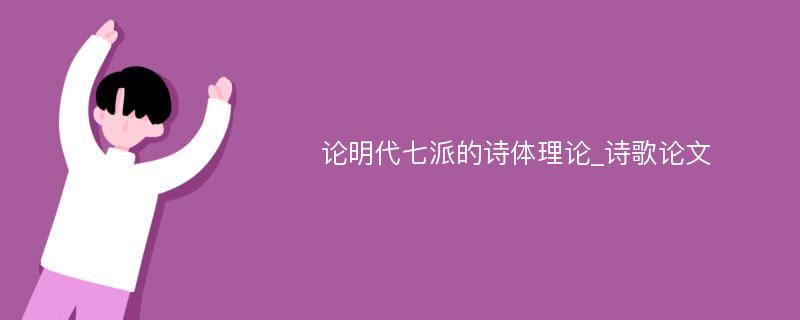
试论明代七子派的诗歌格调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格调论文,试论论文,诗歌论文,七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293(1999)02-0132-06
格调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七子派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使之成为其文学复古运动中最为基本的理论之一。因此,七子派亦被称为“格调派”。探讨七子派的格调理论,对于准确评价七子派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复古运动,都有着重要意义。可是,一些研究者在论述七子派的格调理论时往往只从体格声调上着眼,过分夸大了格调与性情的矛盾,并视格调论为七子派一成不变的教条,全然否定了格调论的存在价值。
七子派对诗歌格调的强调是他们在儒家教化观察指导下从“诗教”向“乐教”的回归,体现了他们对宋明理学家片面强调“诗教”功能、忽视诗歌艺术价值这一作法的不满。当然,强调格调与重视性情之间势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矛盾,但格调理论本身与性情并不冲突。而且,在七子派的格调理论中,“情”的因素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从李梦阳到王世贞、胡应麟以至屠隆和王世懋等人,七子派的格调理论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最为明显的就是:从关注审美客体(诗歌)的体格声调到注重审美主体(诗人)的才情气识。这种变化最终导致某些成员突破了格调论的束缚而迈入了神韵论和性灵论的门坎。限于篇幅,本文着重探讨“前后七子”主要成员的有关论述,对于他们的羽翼人物(即“七子派”的其它成员)的观点,我们将另文详述。
1
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建立是从李梦阳开始的。针对宋代以来诗文界限模糊、诗风萎靡以及理学家好作性气诗、忽视诗歌艺术价值等现象,李梦阳从诗歌“格”与“调”的角度入手,表达了贬斥宋诗、恢复汉魏盛唐格古调逸之诗风的复古主张。在《缶音序》中,他写道: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 1](《空同集》卷52)
在李梦阳看来,唐诗虽乏古调,“却有唐调可歌咏。”而宋诗多作理语,主理不主调。既无宋调,唐调亦亡,古调更不必论。可见,李梦阳尊唐贬宋的思想是建立在体认“格调’这一诗歌特征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1] (《空同集·潜虬山人记》)格古调逸是李梦阳对诗歌“格调”的具体要求,也是他评价诗歌的首要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李梦阳在强调格调的同时并未忘记“情的作用”。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等因素,只有“情以发之”,才能形成真正的好诗。这种以情为本的格调理论源于他对诗歌抒情本质的深刻认识。在他看来,诗歌是“宣志导和”[1](《空同集·与徐氏论文书》)的工具,是“感物造端者也”[1](《空同集·秦君饯送诗序》), 是诗人情感外化的产物,是“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1] (《空同集·鸣春集序》)事实上,以格调论诗,本身就含有对诗歌情感因素的重视,因为,通过“声调”来抒发情感,正是诗歌与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而“声律”与“声调”正是性情或真情发动的结果,所谓“情动于衷而形于言”是也。在《题东庄饯诗后》中,他写道:“情动则言行,比之音而诗生矣。”在《林公诗序》中,他又指出:“夫诗者,人之鉴也。夫人动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睽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1]因此,从理论上讲, 重格调与重性情并不矛盾。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前期重格调,欲全面振兴封建正统文学。因此,他着重的是汉、魏、盛唐,格古调逸的作品,同李东阳一样,李梦阳对格调的追求也必然落实在诗歌的起承转合、音韵、字句、比兴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表现手法上,从而产生了过于重“法”而相对忽视独创性的倾向。如在《驳何氏论文书》中,他不同意何景明所谓“辞断而意属,联物而比类”之法。在《再与何氏书》中,他更明确地表示:“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余所谓法也。”提倡恪守古人之法,而不必自立一门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梦阳的诗文创作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摹拟症。
与前期重视格调、恪守古法相较而言,李梦阳后期则更多地重视性情,力图把“情以发之”落在实处。他对自己前期的创作作了反思:“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并极力宣扬“今真诗乃在民间”[1] (《空同集·诗集自序》)的文学主张。这种主张虽未超出格调论的范围,却已明显地带有一些“性灵论”色彩,对袁宏道的“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2] 《袁宏道集笺校·答李子髯其二》)有一定的开启作用。
前七子中另一领袖人物何景明也非常重视格古调逸、具有雄浑气象的作品。他认为,“自汉魏后而风雅浑厚之气罕有存者。”[3] (《大复集·王右丞诗集序》)又认为:“唐诗工词,宋诗谈理,虽代有作者而汉魏之风蔑如也。国初诗人尚承元习,累朝之所开,渐格而上,至弘治、正德间盛矣”[3](《大复集·汉魏诗集序》)。汉魏、 盛唐之诗歌才是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所孜孜以求的。在《海叟集序》中,他对理学家把诗“比之曲艺小道而不屑为,遂亡其辞”以及明初诗人“率牵于时好而莫之上达,遂亡其意”的作法表示了不满,明确提出近体尊盛唐,古体尊汉魏的主张:
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3](《大复集》卷34)
这种从诗歌流变角度区别体裁以确定推崇目标的作法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他追求古之高格、正格的结果。按照这样的目标,他对杜甫的诗歌也作了一番评论,认为杜诗虽成一家语,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而其调却失流转,诗歌之变体。此种说法体现了何景明对诗歌格调的要求之严。但是,他在《大复集》卷14以“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为标准衡量杜甫那些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显然极不合适,所得结论也自然难以令人信服。这也正反映出其文学思想中教化观念的浓厚。
同李梦阳一样,何景明对诗歌格调的重视也必然落实在词句、音韵、结构、比兴等具体的表现手法和组织结构上。不过,在对待“法”的态度上,他较李梦阳灵活。他认为“法同则语不必同矣”,提倡“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主张“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成一家之言,以传不朽”[3](《大复集·与李空同论诗书》), 更加重视诗人的才情和创造性。
前七子的格调理论在徐祯卿那里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七子中其他6人均为北方人,在文学风格上追求雄深雅健的汉魏、盛唐诗歌风貌。 而徐祯卿曾与唐寅、祝允明、文征明并称“吴中四才子”,其文学风格不免带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据《明史》本传记载,他于弘治十八年登进士第,“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在《谈艺录》中,他曾说:“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入户升堂,固其机也。”又说:“故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厉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后法经而植旨,绳古以崇辞,虽未尽臻其奥,我亦罕见其失也。”不过,在复古的阵营里,徐祯卿在坚持格调论的同时也能坚持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对此,《明史》本传称之为“故习犹在”,李梦阳《迪功集·迪功集序》讥之为“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对于李梦阳的评论,后人多有微议,如七子派成员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就认为:“诗有必不能废者,虽众体未备,而独擅一家之长……我明其徐昌谷、高子业乎!二君诗大不同,而皆巧于用短。徐能以高韵胜,有蝉蜕轩举之风,高能以深情胜,有秋闺愁妇之态。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废兴,二君必无绝响”;王世懋在此敏锐地揭示了徐祯卿、高叔嗣诗歌所具有的清淡空灵、含蓄蕴藉的特点,并预言徐、高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将比李、何更为久远,这其实是对神韵这一美学风格的肯定。清代神韵论的代表人物王士祯对此段话评价甚高,对徐、高之诗更是极力推崇,视为范本。可以说,他是将徐祯卿等人当作神韵论的先导来学习的。事实上,徐祯卿、边贡等七子派成员在提倡格调的同时,已经具有了神韵的倾向,李梦阳与徐祯卿的矛盾就是专讲格调与兼擅神韵的矛盾。
不仅如此,徐祯卿在强调诗歌格调之时,更加重视性情、才情和情感因素,,提出“因情立格”的主张: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助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嘘,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然情实眑渺,必因思以穷其奥,气有粗弱,必因力以夺其偏,词难妥贴,必因才以致其极,才易飘扬,必因质以循其侈,此诗之流也。”[4](《谈艺录》)
徐祯卿在此时的确肯定了“情”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并从源和流两方面对诗歌产生过程中的气、音、声、韵及思、力、才、质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重要性做了说明,进一步发展了李梦阳以情为本的格调理论。
2
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在文坛上再次掀起了复古的高潮。他们继承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的格调理论,同时又较大幅度地做了修正和调整,最终使格调理论走向成熟和终结。
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是李梦阳格调理论的全盘接受者,他没有提出系统的诗歌理论,但从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选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格调理论拘守之严。同李梦阳一样,李攀龙也一味追求雄浑雅健的盛唐格调,诗风最雄壮,摹拟弊病最严重,受到的攻击也最多。许学夷曾对此做过客观的评价。在《诗源辨体·后集纂要》他说:“于鳞七言律,冠冕雄壮,诚足凌跨百代,然不能不起后进之疑者,以其不能尽变也。唐人五七言律,李杜勿论,即王孟诸子,莫不因题制体,遇境生情。于鳞先意定格,一以冠冕雄壮为主,故不惟调多一律,而句意亦每每相同,元美谓‘守其俊语,不轻变化’是也。”可以说,七子派的格调理论在李攀龙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强化。
李攀龙的诗歌选本主要有《古今诗删》和《唐诗选》二书(注:《唐诗选》系从《古今诗删》辑绎而成。),《古今诗删》共34卷,其中唐诗12卷,共740首,所占比重最大,而盛唐诗歌就达445首,占全部唐诗的60%强。《诗删》对于宋元两代诗一概不录,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李攀龙的选诗标准。李攀龙从“伸正绌变”的立场出发,按照格古调逸的标准,对唐人诗作多所挑剥,就连李、杜也不放过。如此鳞选,“合格”的唐诗实在少得可怜,能够入选集中的固然精纯,但大量风格多样的作品却被拒之门外。正如王世贞所言:“令于鳞以意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5] (《弇州四部稿·古今诗删序》),在《艺苑卮言》卷7中, 王世贞又进一步作了说明:“此语虽为于鳞解纷,然亦是大实录”很明显,于鳞此举虽可以“成一家言,以模楷后之操觚者。”但这种偏执一端的作法必然引起世人的不满,就连七子派成员对此也颇有意见。王世贞《艺苑卮言》卷7曾说:“始见于鳞选明诗,余谓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见唐诗, 谓何以衿裾古选。及见古选,谓何以箕裘风雅。乃至陈思《赠白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弃掷。岂所谓英雄欺人,不可尽信耶?”屠隆于《论诗文》也曾说:“李于鳞选唐诗,止取其格峭调响类己者一家货,何其狭也”。屠隆的批评虽措辞激烈,却击中要害。他敏锐地发现了李攀龙一味倡导“高峭”之格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使倡导者和学习者都染上摹拟的病症,后世攻击七子派的主要原因亦在于此。
当然,对于格调理论本身以及这种局限性,七子派内部一直在做着改良与修正,后七子中的修正者则以谢榛为先导。
谢榛在后七子中较早地提倡师法初盛唐十四家诗歌,为后七子提供了论诗纲领。他曾说:“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成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6] (《四溟诗话》卷3,)他视“夺神气”、“求声调”、 “裒精华”为学习盛唐诗歌的三大法宝,足见他对格高的重视。同前七子一样,他对格调的要求也是以格高调畅为标准,“予以奇古为骨,平和为体,兼以初唐、盛唐诸家,合而为一,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则不失正宗矣。”[6] (《四溟诗话》卷4)不过,在谢榛的论诗专著《四溟诗话》中, “格调”一词并不常见,使用较频繁的倒是“气格”、“格”、“格韵”、“调”等与格调密切相关的术语。在谈格律时,谢榛追求神气自得、自然高妙,而反对刻意为“律”。为了克服前七子的格调论所带来的摹拟弊病,谢榛给格调论注入了较多的主体性因素,“气格”一词的创制和频繁使用(在《四溟诗话》中达15次之多)即不无此意。在《诗话》中,就有不少关于诗人“养气”方面的论述。
在学习揣摩汉魏盛唐诗歌格调时,谢榛提出了一个“悟”字,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诗固有定体,人各有悟性。夫有一字之悟,一篇之悟,或由小以扩乎大,因著以入乎微,虽小大不同,至于深化则一也。……若能用小而大之法,当如行深洞中,扪壁尽处,豁然见天,则心有所主,而夺盛唐律髓,建安古调,殊不难矣。”[6] (《四溟诗话》卷4 )对“悟”的强调便与严羽以禅喻诗的作法有了一定的联系,便于解释诸如“灵感”等创作中的特殊现象,也有利于避免诗歌创作中的摹拟病症。与“悟”相联系,他还提出了熟读深参、兼采百家之长的“酿蜜法”,把七子派热衷讲求的“法”由李梦阳等人的“死法”(临帖法)变成了活法。
谢榛所言之“格”,亦即“体格”、“品格”,兼指体裁风格和艺术风格,若仅指“体格”时,谢榛有时也用“体”来表达,如《余诗录》言:“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6](《四溟诗话》卷1),他认为,“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6] (《四溟诗话》卷2)意、理是诗人内心活动的展显,兴、 趣则是诗人内在情感的外在形象化。对兴、趣、意、理的重视是谢榛对诗歌的抒情本质和艺术特征深刻体认的结果。在兴、趣、意、理四者当中,他尤为重兴。他认为,“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6] (《四溟诗话》卷3)“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6] (《四溟诗话》卷1)谢榛所论之“兴”,已不仅含有一般所说的起兴和比喻之意,而且还指主体的审美感受。只有当诗人获得了审美感受并具有创作冲动时,才能写出优美动人的诗歌。七子派格调论本来就对“兴”比较重视,谢榛又列其为诗格之首,可算是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又一发展。
与“兴”相联系,谢榛还多次论述了情景交融这一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如“诗乃模写情景之具,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6](《四溟诗话》卷4)“夫情景相融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6](《四溟诗话》卷4)“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6] (《四溟诗话》卷3)等等。 谢榛的论述为王夫之意境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七子派已经突破了以格调为中心的理论思维模式而转向对“意境”的探讨,切近了诗歌艺术的核心问题。
王世贞是七子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较为圆通灵活,既坚持格调论,又不唯格调论;既讲究诗歌的格古调逸,又注重诗人的才情个性,试图平衡七子派格调论中才情与格调的关系,以纠正七子派一味坚持格调理论的偏颇。在《陈子吉诗选序》中,王世贞对七子派一味追求格古调逸的作法做了反思:
夫诗道辟于弘,正而至隆、万之际,盛且极矣。然其高者以气格声调相高而不根于情实,骤而咏之若中宫商,阅之若备经纬已,徐而求之而无有也。[7](《弇州续稿》卷42)
他认为,格调虽高而不根于情实的诗歌算不上好作品,在《汤迪功诗草序》一文中,他就有“声响而不调则不和,格尊而无情实则不称”之语。可见,他的格调论亦是以情为本的格调论,“情”在他的心目中始终处在先于格调的重要位置。如前所述,七子派的格调理论自李梦阳起一直是重视“情”的,却免不了摹拟之嫌,其原因何在?我们以为,除过七子派一味追求雄浑高古这种单一的格调之外,也与格调理论本身的缺陷有关,即着眼于体格、声调等诗歌艺术的外在特征,而相对忽视创作主体的才情气质。王世贞作为七子派的领袖之一,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及时提出了“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的观点[8](《艺苑卮言》卷1)。也就是说,诗人的才情产生出艺术构思,继而又形成诗歌的基本音调,由音调又可决定作品的体格。这样,诗歌的格、调与诗人的才情思想在王世贞这里达到了有机的结合。在《沈嘉则诗选序》中,王世贞进一步对格调与才气的关系作了说明。王世贞一方面认为有才气方能有格调,对诗人的才气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又强调格调对才气的制约作用。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是王世贞富有辩证观念的体现。承认才气产生格调是对过分重视格调来讲,强调格调的制约作用又是针对过分任情使气的作法而言,他主张格调与才气应当协调一致,因此,他虽然对“遇境而必触,蓄意而必达”的作法有所肯定,但对诗文创作中的率露豪疏之气似有不满,在他看来,只有“抑才以就格,完气以成调”的作品才“几于纯矣”。王世贞认为只要能做到“才剂于格”,“意足于象”,就能达到“诗固自如”的境地,这对于纠正李攀龙诗歌创作中的率露豪疏之气具有积极意义。
王世贞虽然重视才气,不满七子派过分讲求高格朗调而忽视情实的毛病,但他并未放弃对格调的追求。在《陈子吉诗选序》中,他认为“其卑者则犹之夫巴人下里而已。”对格卑者更是不屑一顾。在《与屠长卿书》中,他严格按照格调论的标准对自己的论文创作做了一番检讨,他认为自己的诗文与古之高格不尽符合,并与格卑调弱的六朝、晚唐、宋代诗文有同流合污之嫌,所以应当有所删削。如果说王世贞在对待格调的态度上有所改变,只是不再把格调当作衡量诗文的唯一标准,对格调的要求比较宽泛通达而已。而《宋诗选序》中,他写道:
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而已。此语于格之外者也。[7] (《弇州续稿》卷41)
以前之所以“抑宋”,是因为他认为宋诗格卑调弱,而今天“用宋”,是因为不再把格调当作论诗的唯一标准。所以,在《章经事诗集序》中,他认为:“有所取至于篇,则无问句;有所取至于句,则无问韵。意出于有而入于无,景有浓淡之表,而格在离合之际。”[5] (《弇州四部稿》卷69)“格在离合之际”的思想对拘泥于古之格调的七子派文人来说无疑是一付清醒剂。这一思想落实到诗文学习和创作的具体活动中,就是要做到“师匠宜高,捃拾宜博”[8] (《艺苑卮言》卷1),“不作专家,亦不条调,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 才不累法,有境必穷,有诬必切。”[8](《艺苑卮言》卷7)在此基础上,王世贞提倡“用格”而反对“用于格”,即力主形成自己的诗文风格而不被他人之格所束缚。王世贞又提出了“盖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的千古卓见,从而把七子派的格调论从学习古人格调提升到发抒自我真情实感的新高度,具有了性灵论的气息,也指明了格调理论的发展方向。
从此,七子派中的羽翼人物,以胡应麟、李维桢、屠龙等人为代表的“末五子”成员便沿着王世贞指明的方向对格调理论作着这样、那样的修正和发展工作,以致有些人成了神韵论队伍中的一员,有些人跨进了性灵论的门坎,最终导致七子派格调理论的破产。
收稿日期:1997-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