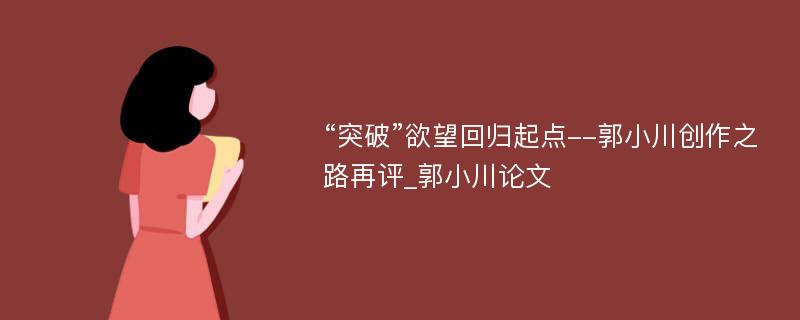
“突围”欲望与重返起点——郭小川创作道路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路论文,欲望论文,起点论文,评价论文,郭小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小川无疑是当代一位重要的抒情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独特的诗人。他的重要性已被各种文学史本文和研究性文章作过充分的论证和描述,而他的独特性却仍有揭示和言说的可能。这一独特性不只是说郭小川以自己的天才创造了他的诗歌时代,比同时代的诗人显示了他更杰出的艺术才能,同时也包含了有过辉煌阅历的天才诗人内心曾产生过的精神痛苦和试图偏离中心、实现突围的欲望和努力。这一点作为郭小川的独特性恰恰是那一时代许多诗人所不具备的。当然,郭小川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努力,时代的迫力和他的承受力使他不得不放弃痛苦和矛盾的冲动,从本质上再度回归原来的立场。
郭小川曾经有着延安一代青年共有或特有的个人履历和精神向往,有着单一向度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共同的故事是:“我过早地同我的祖国一起/担负着巨大的忧患”,“我带着泪痕/投入红色士兵的行列/走上前线”。[①a]这是郭小川基本的思想资源。新中国诞生后诗人就是以这样值得骄傲的情怀鼓励年轻人“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他响遏行云的旋律和亲切的朋友式的热情,使他成为那一时代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郭小川有相当明确的创作目标:“我的出发点是简单明了的。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②a]这一出发点使郭小川充满了追随时代的热情,他甚至很少考虑作品的成熟性,但他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充满创造性的诗人,在三十年的诗歌创作史中,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③a]在这一点上他显示出了与其他诗人的不同,比如同是从延安走过来的诗人,贺敬之的政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合二而一的,因此他的内心没有矛盾和冲突,诗人的创作完全是为了体现他对现实中心话语的理解,竭尽全力地去阐释并维护它。然而在这一点上,郭小川似乎就不“那么坚定”,他一度表示出了自己的犹疑、矛盾、彷徨甚至是“写不下去”的苦恼。尽管他称:“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我自己,将永远不会把这一点遗忘,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动起笔来,那就是由于这种信念催动了我的心血。”[④a]使郭小川的这一表述被事实证明是存有疑问的。就在他作了上述表达之后他接着指出:
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
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
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
就因为这个原故,在我写了一些那样的东西之后,这许许多多的念头常
常苦恼着我,有时真想放弃这个工作,去作自己还能够作的事情。实在的,
我是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了,写不下去了,非得探寻新的出路不可了。[①b]郭小川的这番倾诉并非是姿态。就在他袒露对“新颖而独特的东西”情有独钟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了诸如《致大海》、《山中》、《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等作品。这些作品与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闪耀吧,青春的火光》这样高唱时代主旋律的作品相比,上述作品的情感和倾向多少显示出了诗人的“暧昧性”,他不仅偏离了公共性,诉说了他自己,而且在生活中布满了“诗意”的时代,他提到了他的“心将不免忧伤”等不合时宜的想法。写于同一年的《致大海》也与流行的诗歌区别甚大。大概在何其芳的《回答》之后,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不那么“高昂”的心境。第一次看到诗人的在袒露他的苦恼。诗人遇到了麻烦。他的内心不再是没有浮云飘动的明丽的天空,他也早已不是天真的没有忧虑经验的少年,他遇到了新的矛盾,他与时代不和谐的这一心态使他产生了烦恼。但郭小川这时唯一能做的只是反省检讨自己,他无情地揭示了内心滋生的倦怠、昏睡、无聊的争执、忧心忡忡、孤高自傲或无病呻吟。但就在郭小川自我批判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躁,这不是冷静、理性的自我反省,而更像是一种烦乱情绪的自我宣泄。然而,郭小川遇到的问题显然不止这些。面对以往的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过程中的经历和复杂的个人心态,他亦进行了“新颖而独特”的、不同于诗歌主潮的探讨。《白雪的赞歌》就是这样一首作品。它是自40年代以来,极为少见的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叙事诗,也是游离于《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经典作品表达形式的叙事诗。它显然不那么“大众化”,它的话语形式和情感方式都是知识分子式的,诗中充满了知识分子情调。它叙述的是一位青年女性因身孕而没有随丈夫去前线,留在后方而同一位医生产生了暧昧情感的浪漫故事。这本身在那一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已不多见。而重要的是诗人又真实和有所保留地写出了一个女性的复杂心理。于植面对丈夫“负伤以后失了踪”的不幸和医生爱慕的暗示,她的情感是纷乱的:一方面,她努力工作,让更多的事务占据她闲时的担忧和烦恼,“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狂热,迎接这不熟悉的有趣的生活。修改稿件、刻钢版、印刷,我既不感到忙碌,也不觉得烦琐”;一方面,她又感到医生的“存在就是一种助力”,他四天不再来时,“天天都空让我焦心地把他等待。”而于植对医生“焦心等待的时刻”,恰恰是“关于我亲人的消息,却像清风一般寻不见线索”的时候。郭小川本意是赞美“白雪一样”纯洁的爱情,但他同时书写了特定时期女性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于植须时时暗示自己不能动摇,但事实已远不这样简单,在“凝结”一节中,于植曾不自信地自述:
读者啊,你们一定会怀疑:
难道我真把我的爱人忘记?
是的,我一次也没有为他哭过,
而且从来没有叙说过我的心事。
然而,我的描述必须绝对真实,
你们懂得,自己的亲人又怎能忘记!
我只能告诉你们一条秘语:
坚强的战斗者不能感情用事。但于植的这一承诺显然是存有问题的。当他听到医生离开了她的所在地时:
听见这个没有预料到的消息
我简直遭到了尖锐的一击,
从他原来的寓所缓缓走回来,
热辣辣的眼泪忽然掉下几滴。
当时,我自己也感到几分惊奇,
这个可敬的人不过是普通的同志,
对他自然有着说不尽的感激,
若动起感情来可有些多余。
然而,我的激动的心还不能平息,我的面前不断闪动着他的影子,
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对他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
于植这时实际已确认了自己的犹疑,因此她必须“告诫自己:一刹那的摇摆也不能允许!”“我的信念并没有丧失,我的心谁也不能夺去。”于植最终还是完成了“白雪赞歌”,但她情感历程上的波澜也是不能否认的存在。在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中,郭小川坚持让理性战胜情感,这自然是他的选择,但更是时代的要求。事实上,郭小川对于植情感矛盾的细致揭示,已表明了他对人的情感的由衷兴趣和尊重,不同的是,在需要作出价值判断和选择时,他必须坚持时代崇尚的标准。
医生是个柔弱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寡言少语,忠于职守,他把更多的情感埋藏于心中而很少倾述,他是压抑的,甚至有些自卑和委琐,但他又是自尊并自律的,他深切同情于植的遭遇,并最大可能地去安慰、帮助一个战时的不幸女性,他无声地爱着于植,关心着他丈夫的消息,当他确信于植深爱她丈夫时,自己“带着医疗队来到了前线。从此,我永远斩断我的可耻思想,抹去我最后见面时的无声的语言。”他向自己爱着的人发出了最后的祝福。这位医生在那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中是很少出场的角色,郭小川在他的诗中虽然也将其处理为边缘性的角色,并赋予其“灰色”的调子,但医生的形象总体上仍给人以有修养、敬业、诚实、尊重情感的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郭小川内心对知识分子的真实看法和受到时代影响的深刻印痕,一如他对情感/理性矛盾的倾斜和选择。《白雪的赞歌》不同于《深深的山谷》,前者,郭小川对医生有许多同情的成分,尽管他用中性的话语叙述了他;而后者,作者却毫不犹疑地将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埋葬于深深的山谷,尽管这是完成于同一年代的诗。《白雪的赞歌》是郭小川第一次在诗歌领域向时代的“文学病”发出了冲击的信号。那时的诗人不大敢问津人的内心世界,更不要说敢以赞美的神情去称颂一位在“生活作风”上曾有过动摇的知识女性。但郭小川这样做了,他表示了对人性、人情的由衷兴趣和关怀,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表现那代人特有的自律能力和道德克制。女青年于植和医生没有越“雷池”一步,因此也没有发生“丈夫”归来时当事人陷于困境的不幸,最终这还是一个大团圆的、欢天喜地的传统故事。但这“战地浪漫曲”还是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郭小川的“突围”欲望或“偏离”倾向;他总是要试图探索那“新颖而独特的东西”。
两年之后,郭小川终于写出了他那首尽人皆知的《望星空》,他将内心的矛盾和迷惘更加清晰地告知了世人,这是诗人站在北京街头向星空了望时感受到的。与其说这是对自然空间的描绘或展示,毋宁说这是诗人内心空间的大胆裸露。几年前,诗人的“忧伤”也仅仅限于久居“山中”,而在这里诗人的情绪却来自整个“人间”,诗人的惆怅浓重而无可化解,他无法沿这一思路再抒发下去。他只能“带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郭小川的心情是复杂的,而作为时代的抒情诗人这一复杂的心情就变得格外沉重;时代的和个人的原因都命名郭小川不可能“走的太远”。他内心矛盾重重但他又无法找到解决的途径,他只能面对大海、星空等自然景观述说他的忧虑和迷茫。而这一述说必须有节制,必须找到一个均衡的、不至于发生大的倾斜或震荡,他必须找到一个依托的现实力量。因此,一回到“现实”中,他的“忧伤”、“迷茫”、“惆怅”等心情必须重新欢快起来、高昂起来,因“人间”终会胜过“天堂”,郭小川的内心正是这样被分裂的。
应该说,1956年至1959年间,郭小川有过一段极为可贵的坚持,他曾遭遇过严肃的劝告或批评,《白雪的歌》发表后,臧克家在《人民文学》著文批评,“医生和女主角暧昧情感”,批评了女主人公“一方面念念不忘不知身在何处的丈夫,切盼他早日归来;另一方面,却对眼前的医生发生了‘不限于友谊’的情感”,认为于植的“人格分裂了”[①c]。因此臧克家希望郭小川能多写一些像“向困难进军”一类的战斗性强烈的长诗。郭小川显然没有听从这一奉劝,他坚持甚至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想法直至《望星空》。作为“了望哨”和“侦察兵”的批评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郭小川的这些“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华夫指出,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郭小川同志却写出了这样极端荒谬的诗句,这是政治性的错误,是令人不能容忍的。”[②c]“这首诗里主导的东西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萧三则质问道:“这样消极地抒写个人主义幻灭情绪的作品,怎么能出自一个共产党员之手呢?”“怎么突然写出这样虚无漂渺、颓废绝望的诗呢?是不是因为诗人的灵魂深入个人主义的东西没有被清洗掉,一有所感或抵触就自然地冒出头来,因而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发生了动摇吧?”[③c]面对这样的批评和质问,郭小川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他的思想积累或人格力量还不能保证他内心的坚持,在时代主流话语的迫力下,他迅速地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突围”宣告失败。
其实,郭小川对情有独钟的“新颖而独特的东西”的向往始终是留有余地的,是有限制的。在《月下集》的“权当序言”中他说:“我们的文学应当去发掘我们的伟大的人民的心灵之美,从而把这座心灵的‘火焰山’煽得更旺盛。这里,核心问题是思想。而这所谓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创见。”郭小川后面这一句话相当重要,这是那一时代对文学艺术的理解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程度。然而,他对流行的中心话语不能不有所顾忌,又对“新颖而独特”充满了探索的兴趣。这就是既是“战士”,又是“诗人”的矛盾。这一矛盾无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上。《白雪的赞歌》中的女主人公于植,作者对她的情感处境深深地同情并理解,他曾用相当感伤的诗句叙述了于植的内心活动,写出了作者为一个人,一个青年女性的情感渴望和人的有限性的真实,但于郭小川来说,无论是外部戒律还是他内心的勇气,都不可能使于植这一形象游离时代主旋太远,她只能在想象中煮着自己,而不能放松情感的闸门。在郭小川看来,“政治上和爱情上的坚贞”是一致的,道德化的时代使于植必须回到“丈夫”的身边。而《深深的山谷》中,诗人对女叙事人的爱情境遇充满了同情,对他们延安时代短暂的幸福给予了尽可能的诗性描述,但那个知识分子,毕竟被诗人给埋葬了,诗人不想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并给予理解。女叙事人后来嫁给了那位粗犷无比的“指导员”,而“过得很幸福”。《望星空》的矛盾更为突出,诗人既是忧伤的、惆怅的,但他一走向北京的心脏,他心头的忧伤顿时云消雾散。这是郭小川现象中的独特景观:一方面他唯恐落后于时代,有辱自己的历史和时代使命,因此他必须努力在主旋律的高音区捕捉并突现自己的声音;一方面,他对“作者的创见”又有深刻的觉醒,对“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有特别的警觉。然而郭小川的苦闷、矛盾在他的犹疑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后来的创作虽然名重一时,但他的慎重也越发明显了。
我们发现郭小川虽然没有再直接抒写来似《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闪耀吧,青春的火光》之类的鼓动召示性的作品,但从他六七十年代的创作来看,他显然有意识地向诗歌主潮或中心话语回归。《厦门风姿》和《林区三唱》、“新边塞诗”等,是郭小川6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创作生涯中的又一高峰期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诗歌会让人明显感到郭小川在创作上的谨慎。《厦门风姿》作者四易其稿,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诗人充满了热爱之情,它的荔枝林、相思树、凤凰木、木棉树、高楼广厦、长街小巷、雄风海浪无不为诗人带来神奇的想象,触发启动着诗人的灵感或诗情,但诗人不能久驻厦门的“表面”景观,他唯恐陷的太深,误入歧途,他必须走出他留连的城市景观,“上扶梯、登舰艇”,“驰进大海的怀抱”,“爬土坡、攀石岗”,“深入层峦耸翠的山区”,这时的诗人才会感到踏实,他同流行的以乡村抗拒城市,以硬性对抗柔性的文学时尚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这表现了郭小川在可能的情况下既坚持又适应的策略性考虑。不同的是,当时的郭小川尚处于创作的高峰期。他的抒情才华在很大程度上掩饰了他的这些概念化的理性原则。《厦门风姿》很可能是60年代最出色的抒情作品,因此它也更典型地反映出了郭小川“受挫”后重返起点的心态特征。
《林区三唱》作为劳动人民和劳动的颂歌,在思想内容上已无须再阐释。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郭小川语言风格的变化。郭小川知名的作品如《闪耀吧,青春的光火》、《向困难进军》等是“楼梯式”,《致大海》、《厦门风姿》等都是长句,《望星空》虽然节奏短促,但它的话语形式完全是知识分子式的。而《林区三唱》则采用了民间式的比附,以流畅的,经过改造的民歌风创作的。在这一点上它与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闻捷用瓜子、瓜蔓、瓜瓤等形象喻示枣尔汗的美丽,而郭小川则以山中的老虎美在背、树上的百灵美在嘴排比出林业工人美在内,他在林区捕捉出大量的自然形象来歌颂林业工人,流满了山林特色。在节奏上它不再是《厦门风姿》等作品的跌宕起伏,而是明快短捷,一气呵成,易记易背,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进了一大步。应该说,《林区三唱》或他的“新边塞诗”的探索,在新诗创作中是有一定地位的,但从郭小川的创作生涯和思想历程来分析,“他悲剧性地否定了自己曾有过的开拓”[①d],而重新走向老路,则不能不让人感到由衷的遗憾。
郭小川对现代中国精神传统的忠诚,对“战士”角色的自我定位,使他很难实现对“新颖而独特的东西”的坚持追求,当内心困惑,思想矛盾,艺术追求等问题并发的时候,郭小川首先想到的仍是战士的职责,而艺术在他那里始终未能居于首位。这一点,在郭小川创作于70年代的诗歌作品,如《秋歌二首》以及《登九山》等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后期的郭小川,实际上已丧失了抒情诗写作的激情、感受和能力,只能形象地或直接套用政治术语去阐释流行的时代精神了。
郭小川作为诗人的一生经历了沉重的思想矛盾和情感矛盾,在他艺术最敏感的年代曾有过短暂的“突围”意识,但由于郭小川个人的思想、艺术背景以及时代的原因,他最终未能摆脱这二重重负,他渴望的“新颖而独特的东西”最终仍然不属于他。
注释:
①a②a④a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见《月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a谢冕:《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①b郭小川:《月下集》。
①c以上引文均见臧克家:《郭小川同志的两篇长诗》,载《人民文学》1958年3期。
②c华夫:《评郭小川〈望星空〉》,载《文艺报》1959年23期。
③c萧三:《谈〈望星空〉》,载《人民文学》1960年1期。
①d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