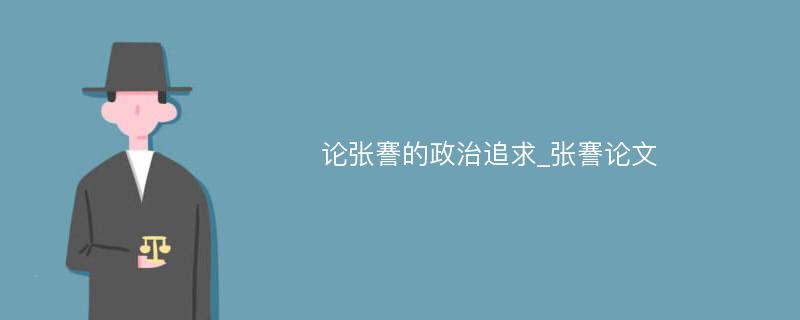
略论张謇的政治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ZhangJian's polititcal pursuits included three aspects:p-romoting political improvements to make his countryprosperous and powerful;carrying out reform gradually;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lity There were three motivations for these pursuits:the inspiration of patriotism,the drive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lations.The cornerstone of Zhang's program was a constitu tional monarchy,which was undoubted-ly an improvement,and therefore accorded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However,Zhang could not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his class status,his knowledge and his personality,so his pol-itical in clination tended to be conservative and moderate.
张謇诚然是公认的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但众所周知,他同时也是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张謇的主要事业是办实业和兴教育,然而他却非常强调处理好政治、教育、实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1〕。 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立宪派十分活跃,对晚清政局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一
张謇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求祖国之富强。在他看来,欲达富强之目的,处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唯有对外力御强敌,对内改良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光绪五年(1879年),年方26岁的张謇在替别人草拟的奏疏中大发宏论,希望清廷切实加强战备,以御外侮:“即如今日诸夷逼处,环伺耽耽,恫喝要求,累岁相望。其宜战而不宜和,无智愚皆知之。而我中国握重兵而负夙望,始终坚持议战者,惟左宗棠一人。其余则或以书生谈兵,而无以征信于天下”,“兵凶战危,亘古无万全之策,而胜败之理,一决于气之盛衰”〔2〕。光绪八年(1882年), 张謇作为吴长庆的主要幕僚随军赴朝鲜,处置“壬午兵变”,应付由于日军入朝造成的紧张局势。他不但参与了这次行动的全过程,而且撰写了《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的基调未能摆脱封建上国思想的框框,但确反映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日本发动侵略的警惕性。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又在朝鲜策划了“甲申政变”,当时已返回故里的张謇对边疆危机仍极为关注,他“愤中国之不振”,为挽回颓势屡有建议。他告诫驻朝将帅“不可再赔兵费于日,更蹈从前覆辙”〔3〕,又代拟“条陈朝鲜事宜”, 指出“中国以朝鲜为门户,朝鲜亦倚中国为长城”,“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因,大权一失,实祸随之”,要求朝廷“时时有必战之心,事事图能战之实”〔4〕。为抵御法军北犯,张謇还亲身投入备战工作, 参与了筹办当地滨海渔团,草拟了《渔团章程》。前线传来谅山大捷的消息,张謇兴奋异常,认为“此宜足禁持和之口”〔5〕。
十年后,张謇预言“以中国为其演试军事之地”的日本终于发动了甲午战争。时值张謇金榜折桂,授职翰林院,遂“极力主战”,成为帝党中的重要决策人物。他指斥李鸿章主和误国,请求“另简重臣,以战求和”〔6〕。后因守制南归,在家乡举办团防, 当获悉屈辱已极的马关和议内容时,张謇愤激不已,大声疾呼:“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7〕!为挽救时局,以图振作, 他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救亡主张,要求加强国防,广开新学,提倡商务,讲求工艺,出洋考察。
当时张謇勾画的自强之策,还没有超出洋务派的思想范畴,于政治改革几乎没有提及。然而对腐朽龌龊的封建官场,张謇是厌恶的,面对“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问”的局面,他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9〕。不愿为官,并非不关心政治, 而是鄙薄腐烂透顶的官场,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如何使濒临绝境的封建政治得到改良呢?在列强瓜分狂潮的刺激下,在维新派“民权”思想的影响下,张謇提出了“去官毒”的主张。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十日(1897年9月6日),张謇致书《时务报》主持者汪康年:“走以为所恶于君权者,官毒之害也。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藉君权不横,而二事实不相关”〔10〕。这不仅是对官僚政治(即“官毒”)的抨击,同时也点明了“官毒”与“君权”的密切联系(即“官毒不藉君权不横”)。虽然此论的前题在于“保君权”,又特别申明官毒、君权“二事实不相关”,但毕竟反映出他对“君权”存在某种程度的不满。
维新运动的兴起激起了张謇重登政治舞台的热情,他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1898年5月6日)到达北京。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即诏定国是,宣布变法。而张謇只提出过一些温和的经济改革主张,对政治变革则持消极态度。他与翁同和的共同看法是虽“法刓必变”,但“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11〕。他们的改革指导思想与康、梁全面变革的计划显然并不合拍。后来,张謇曾这样追述与维新派的关系:“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12〕,这是符合实际的。当变法障碍重重,局势日益险恶时,张謇于六月三日(7月21日, 即翁同和革职归里半个多月后)请假南归,离开了京城湍急的政治漩涡。
张謇不赞成康、梁式的变法,而主张一种更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正如其子张孝若所说,他“看了当时宫廷的纷乱,亲贵的昏聩,内政处处腐败,外交断送权利,越看越痛心,也认为非变法不可”〔13〕。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 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不得不打出“变法”旗号,以取悦列强,欺骗世人。张謇等闻讯颇受鼓舞,两个月后就写出了《变法平议》,洋洋洒洒,两万余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变革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首先对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论述,认为:“法久则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其变法的内容共有42条,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并提出分三个阶段逐步实施。《变法平议》提出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超出“百日维新”的范围,其中虽有“置议院”一项,但这种“议院”仅由京外四、五大臣自辟议员组成,不过是个由官僚招聘组成的咨询机构,与西方资产阶级议院不可同日而语。
在《变法平议》中,特别突出了张謇渐进式的改革思想。它批评戊戌变法“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取一切之法而张之,上疑其专而下不喻其意”〔14〕。“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范围内,循序改进”〔15〕。他的观点是宁可慢一点,只求有成效,与其“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不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16〕
张謇正是在新世纪伊始之际亮出他的变法旗帜的。这位自称“生平万事居人后”的改革者〔17〕,其行进的步伐总要比时代的弄潮儿慢半拍。早在1902年,国内进步舆论已经关注立宪问题,1903年5 月的《大公报》在一篇题为《论中国之立宪要义》的文章中说:“今日中国政府又将出现一新问题,其机已动,其端已见,其潮流已隐隐然涌出者,顾为何哉,盖立宪问题是也”〔18〕。而张謇公开赞成君主立宪则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日本考察之后。在日本的七十天里,他参观了博览会,考察了日本的教育与实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所以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富强起来,“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惰者当之矣”〔19〕。要想富强起来,必须改良政府,改变政体,“不变政体,虽枝枝节节以补救亦无益耳”〔20〕!从此,他积极投身立宪运动。
张謇推动君主立宪的手段不外有三,即:向“官员友人”进劝;为封疆大吏代撰鼓吹立宪的奏稿;译刻《日本宪法》直送内廷。张謇是个真诚的立宪主义者,他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个人的进退都与立宪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张謇的政治追求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即渴望政局的稳定。求稳怕乱的思想象幽灵一样伴随着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戊戌维新期间,新旧两派势成水火,张謇力劝维新派不要“鲁莽”从事,颇不以康、梁举动为然,他曾说:“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不必成,祸之所届, 亦不可测”〔21〕。对于较康、梁更为激进的谭嗣同,张謇竟斥之为“好奇论”,“谬妄已甚”〔22〕。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张謇撰《变法平议》,仍批评“喜言新法者”“逞快喉舌”,“毒流大区而危及宗社”,主张“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视融合新旧的折衷调和路线为“变法之命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狂飚突起,席卷京津,慈禧迫于形势对外“宣战”。帝国主义列强组成联军,入侵中国,攻陷北京。张謇视义和团为“匪”,比之为“黄巾、白波再见”〔23〕,并积极参与了“东南互保”活动。当时“盐枭”首领徐宝山(绰号徐老虎)自称“两江两湖大元帅”,活跃于长江下游,以“勤王”相号召。张謇唯恐东南不稳,致书刘坤一倡“招抚”之策,认为如此则可“内患苟弭,可专意外应矣”〔24〕。并先后与沈瑜庆(正阳关淮盐督销)、施炳燮(刘坤一亲信幕僚)等密议,又与刘坤一会面,促其对“东南互保”的计划拍板定案。为追求东南地区的相对“稳定”,张謇不惜积极奔走,策动东南督抚与列强“合作”来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然而,旧的统治秩序毕竟是难于维护的,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向前推进,仅仅十年后,震惊全国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张謇最不愿意见到“颠覆眩乱”的局面,他认为只有立宪才能避免革命,因为立宪“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之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25〕。当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曾到南京劝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援鄂”,同时希望清廷公布宪法,召开国会,以平民愤。但一旦当他认清“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爇,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时〔26〕,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立即改弦易辙,由立宪转向民主共和,并寄希望于“和平光复”的模式,以避免更大范围内“极烈之暴动”。他还致函江苏咨议局赴京请愿代表,明确表态要顺应历史潮流,“走何力,岂能扼扬子之水,使之逆流”〔27〕。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各省纷纷独立,在张謇看来,当时只有袁世凯才是唯一能够稳定政局的中心人物。于是在南北议和期间,他致力让袁世凯出面总揽大权,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统一”与“秩序”。当袁世凯终于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国内出现暂时和平假象后,张謇也欣欣然以为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遂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企业经营和地方自治。
1913年3月,“宋案”发生,激起国内政局的轩然大波。 南方革命党人酝酿发起了倒袁的“二次革命”,对此,张謇是坚决反对的,他说:“稍能看报识时务者,则皆鉴于前辙,惴惴焉怀生命财产之忧,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28〕因此,力主“持以镇静”,坚持“法律解决”。
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帝制自为。于是,一场新的反袁风暴在全国兴起。面对新的动荡政局,张謇请假南归,欲置身局外,同时又寄希望于黄兴回国“调和南北”,或以“换马”方式,由冯国璋取代袁世凯来恢复“秩序”。但“护国之役”起于云南,南方各省相继响应,张謇又力劝袁世凯“急流勇退”,以早日结束战争。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混战不已,张謇日夜渴求的和平、安定幻梦彻底破灭,这位“饱尝世变”的老人只有心酸地表示“不愿再涉政界”〔29〕,无可奈何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综观张謇一生,其政治追求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祖国的富强与政府之改良;渐进式的改革以及政局的稳定。
二
我们在审视张謇的政治态度和追求时更应着眼于深入探究形成此种追求的内在原因。
首先,应该看到真诚的爱国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乃是张謇政治追求的精神支柱。张謇二十一岁时离开家乡通海地区,从此,走南闯北,投笔从戎,飘洋过海,进一步开拓了眼界,使他对国内政局的演变,列强侵华的动向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甲申中法之役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尤其是甲午战败,割地之多,赔款之巨,屈辱至极,张謇“益愤”。随后各国纷纷攫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他见此情景忧心如焚。正是在这炽烈的爱国热情驱使下,张謇一度成为政坛上极为活跃的人物。
时代列车跨入二十世纪,戊戌后有意逃避政治的张謇终于重登政治舞台,投身立宪运动。他赴日考察,为的是学习东方邻邦的富强之道,回国后趋向实行君主立宪,正是赴日考察的直接结果。他深忧国势衰微,又感自身力薄,遂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1904年2月16 日)的日记中自责道:“海氛方恶,国势方危,区区一隅之地,一人之身所应尽之义务,曾未一一著有效果,而齿又增矣。可愧!可愧!”
另外,经济利益可以说是张謇政治追求的有力杠杆。尽管张謇兴办企业和教育的目的在于富国安邦,可实际的经济利益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态度。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天起,张謇开始了他的办厂活动,创业四年,至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1899年5月23 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从此,张謇正式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中的重要一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大生纱厂趁洋纱进口减少之机产销两旺。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大生”又因日纱在中国市场减销而获利更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大生二厂建成,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大生两厂的纯利累积已达370 余万两,资本总额也增加到近200万两。也就在这一年夏天, 张謇把他另外创办的19家企业合并组成通海实业总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后,他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航运、堆栈等企业。辛亥革命前,一个以纱厂为中心,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大生资本集团已经形成,而且张謇的投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28年之间,张謇共创办了各类企业42个。他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棉铁主义”的口号,梦想建立一个容轻、重工业于一体的民族近代经济体系。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大生两个纱厂的纯利也逐年大幅度增长,其中:大生一厂,1911年为201520 两, 1913年即达到367691两,利润从17.83%增至32.54%;大生二厂同期的纯利,也从112962两增至286821两,利润率从13.05%增至33.13%。丰厚的经济利润使得张謇更加看重市场的平稳,政局的安定。当“二次革命”爆发时,他最担心的是“实业生计大受损害”,甚至不分是非曲直,指责国民党抵抗派为“可恨!”其理由是“沪上罔死之民之众,损失市产之巨……即通(州)实业之受损亦数十万矣”〔30〕。
除了爱国精神,阶级地位,经济利益对张謇的政治追求、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外,社会交往、人际关联和传统教育对他的政治追求也具有触媒的作用。比如好友范当世、周家禄等都敢于面对现实,抨击时弊,他们关心社会,关心时局,强调“行事当为天下全局,不当为一己沽直名”〔31〕,希望张謇能“任天下之重而应世变”〔32〕。对此,张謇都视之为金玉良言,以为“足以药生平之病”〔33〕。这种朋友间的砥砺与切磋对于张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甲午到戊戌,张謇又与以翁同和为代表的帝党人物交往密切,并在他们影响下,参与了积极主战和变法维新,其对李鸿章主和误国的抨击更是震惊朝野,爱国热情跃然纸上。戊戌变法期间,张謇在北京的活动不过两个半月,时值变法高潮,他与翁同和频频接触,“无所不谈”〔34〕。显然,翁同和“西法不可不讲,圣理之学尤不 可忘”〔35〕的温和变革思想在张謇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使他与康、梁主张不能合拍,对维新变法态度消极,终于在维新与守旧势力斗争激烈之际离开京城,置身局外。
张謇所接受的正统儒学教育对他政治观点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无庸置疑的。少年时代,张謇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九岁的张謇从海门训导赵彭渊学习朱熹的《四书大全》和宋明理学著作。两年后,张謇由家乡到了江宁,在这个东南的文化中心结识了李小湖、薛慰农、张裕钊等国内知名学者,号称桐城派大师的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同时,张謇还选读了一些中国史学名著,从16岁时起读《纲鉴易知录》、《通鉴纲目》,稍长,读《资治通鉴》、《三国志》、《史记》、《前汉书》。以后又读了《老子》、《庄子》、《管子》、《晏子》以及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深受明末清初朴学大师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张謇还对《周易》颇有研究,晚年屡屡自称一生得力于《易》。但是他对《易》的理解却着眼于“守正处中”,而不是其中的变化观点。长期接受封建旧式教育,又囿于科举制艺的束缚,使张謇不能不背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诚然,这里既有历史智慧的启迪,先哲思想的感化,也有传统惰性的困扰,封建毒素的纠缠,所缺乏的正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的滋养,因而其政治思想很难突破忠君爱国的格局。
张謇的性格特点使其政治追求更具独特风格——务实、求稳、善变的风格。张謇出身于一个普通农家,祖父因家境穷困而为赘婿,父亲时生活稍有改善,买了20几亩田,但张謇兄弟仍需参加农作并兼作杂工,其父的家训是“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36〕。生活环境的锻造和家庭教育的熏陶,使张謇成年之后仍保留着农民那种讲求实际,不尚空言,不务虚名,憨厚纯朴的性格。
张謇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不轻易接受某种观点和主张,他只相信通过自己亲身观察、体验后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一旦认准了前进的方向,追求的目标,就会不遗余力,孜孜以求,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开始,他追求政治改良,却与民权思想相抵牾,只是在亲自考察了日本后,尤其是在君主立宪的日本于日俄战争中获胜后,他才改弦更张,积极投身立宪运动。他醉心君主立宪,为之奋斗不懈,甚至当革命党人已首义武昌,他仍在动员南方清军“援鄂”。但张謇不是顽冥不化的人物,他讲求实际,不是不变,但不轻变,更着眼于善变,往往是在关键的时刻,在事态发展的转折关头,做出合理的选择。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1898年5月6日),正当维新运动步入高潮时,他赶到北京参与变法;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1904年5月7日),他欣然应邀去南京代张之洞、魏光焘起草请求立宪的奏稿;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年11月13日),他又与其他立宪派头面人物联名电请内蒙古各界人士赞成共和,成为转向共和的一次公开亮相。这三次政治态度的重大转变,当然与时局的变化紧密相关,但却不能视之为政治投机,而应该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合乎历史潮流的政治选择,同时也是张謇的个人性格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反映。
三
对于张謇的政治追求,以往论者见仁见智,评价不一,因而有必要对此种追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做进一步说明。
尽管研究者会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来发表意见,但无论如何似不应漠视张謇政治追求中合理而有价值的一面。
张謇一生追求的主调是君主立宪,甚至可以说他的政治生命是与立宪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37〕。真可谓成也立宪,败也立宪。
我国几千年来一直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素来缺少民主政治的意识,可以说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开始,君主专制代代相传,从未有过民主政治。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加深,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命题,首先是“师夷之长技”,搞了“同光新政”,以后又搞了戊戌维新。19世纪70—90年代,“宪法”一词开始在书刊中出现,直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才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立宪法”“开议院”的建议。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立宪才作为一个实际政治运动出现于中国大地,这种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让更多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这无异是在延绵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的一潭死水中,投进了一块足以激起民主波漪的石头。对于祖祖辈辈只知道“朝廷”“君上”的芸芸众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启蒙。应该说立宪在当时是一种时代要求,尽管与同时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相比,它是驶向同一方向的一列慢车,并在改造还是推翻清政府的问题上各执一端,相互对立,但在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在向西方学习以及向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日本人学习这一点上,也是并行不悖的。毛泽东所描绘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中,同样有着以张謇为代表的真诚的立宪主义者的足迹。
我们当然有必要把真立宪与假立宪区别开来。张謇倡导立宪运动,其根本目的在求民生之安定,祖国之富强,如他所说:“时受外界刺激,悲忧日集,群相晤语,每至流涕。愚者千虑,皆谓非实行立宪,无以救之”〔38〕,立宪是要“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致颠覆眩乱者也”〔39〕。宣统元年十一月(1909年12月),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发动联合请愿。会议结束后,张謇在饯别宴会上撰文与代表共勉说:“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40〕。尽管这种表态显得苍白无力,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爱国的热情,其真诚的愿望与悲壮的气慨溢于言表。
立宪运动是失败了,但张謇的政治追求并非完全没有效果。首先,作为一个颇具声势的政治运动对封建专制主义无疑是种有力的冲击,至少在言论自由这一点上已经有了松动。一位美国评论家在论及宣统元年(1909年)召开的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时曾说:“中国过去从来没有人象现在这样坦率直言过”〔41〕。其次,立宪运动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廷的顽冥不化,证明它是不会向人民让步的,使不少人丢掉了依靠这个腐朽朝廷的改革去实现民主宪政的幻梦,从而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客观上起了舆论动员作用。这种警醒作用影响所及也包括张謇本人在内,他在一份电文中就清楚地表明对这个无可救药的朝廷已经失去了信心:“自先帝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有为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不一无与立宪主旨相与。枢密、疆吏,皆政府而代表朝廷者也。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42〕。既然一切救国救民的和平努力都遭到清廷无情拒绝而没有效果,那么人民还能够容忍吗?这个朝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当然,在张謇的政治追求中也有保守和落后的内容,亦即有它局限的一面。首先是阶级的局限,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他不可能摆脱中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阶级性格,这种性格的表现就是重近利而不计长远;怕动乱而追求安定。民国三年(1914年),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朱执信就直捷了当地指出中国资本家的政治性格是:“不惮牺牲将来以求曲全现在”〔43〕。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曾经这样来描述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追求:“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地去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本身”〔44〕。这一精辟阐述同样适用于用来透视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适用于透视这个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
其次是认识上的局限。虽然张謇在开风气之先上有许多过人之见,但他对腐败透顶而又顽固不化的清政府仍然抱有幻想。当保路风潮席卷全国,清朝统治已经濒临崩溃时,张謇竟与郑孝胥、汤寿潜等立宪派头面人物相继进京,觐见摄政王载沣,并转而赞成“干路国有”政策,甚至还为清廷对付川、粤、鄂铁路风潮出谋画策。他向清廷表示:“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况,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合之”〔45〕。清廷对他表现出来的“热情”和礼遇更使张謇怦然心动,也进一步模糊了他对时局的清醒估计。
第三是个性的局限。张謇为人质朴、务实,老成、持重有余,灵活、敏捷不足。他不拒绝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但反映却不够灵敏、迅速。他声称“生平万事居人后”,虽然不无戏言成分,倒也符合本人的性格特点,这一特点反映在政治上,必然是保守、求稳。
总之,张謇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是人们所公认的,而对他的政治追求,政治实践却评价歧异,褒贬不一,但只要清除“左”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张謇的一生进行全面考察,就必然会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注释:
〔1〕〔19〕《东游日记》,《张季子九录·专录》卷四。
〔2〕《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
〔3〕《为韩乱事致驻防吴提督孝亭函》,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
〔4〕《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
〔5〕〔7〕〔22〕〔23〕〔31〕〔33〕《张謇日记》,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五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6〕《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8〕《啬翁自订年谱》,卷上,第26页。
〔9〕《致沈家培函》,《张季子九录·文录》
〔10〕《汪康年师友手札》,第二册,第1804页。
〔11〕《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
〔12〕《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
〔13〕〔15〕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第156页。
〔14〕〔16〕《变法平议》,《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二。
〔17〕《怡儿生志喜》,《张季子九录·诗集》。
〔18〕《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五期“内务”。
〔20〕内藤太郎:《袁世凯》,中译本,第104页。
〔21〕《啬翁自订年谱》卷下,戊戌六月。
〔24〕《为拳乱致刘督部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
〔25〕〔37〕〔39〕《年谱自序》,《张季子九录·文录》。
〔26〕《张季子九录·诗录》。
〔27〕〔29〕〔30〕《张謇未刊函札》。
〔28〕《调和南北致孙少侯王铁珊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
〔32〕周家禄:《寿恺堂集》,第28卷,第2页。
〔34〕〔35〕《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四月廿五日,四月廿三日。
〔36〕《述训》,《张季子九录·文录》。
〔38〕《郑孝胥张謇等为在上海设预备立宪公会致民政部禀》,转引自《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00—101页。
〔40〕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国风报》第一年,第二期。
〔41〕威廉·埃利斯:《革命的中国》,载1911年10月28日美国《展望》杂志。
〔42〕《九月二十九日请袁内阁代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张謇函稿》,第27册。
〔43〕《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卷第150页。
〔4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一卷第542页。
〔45〕《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本文所引《张季子九录》,张孝若编,中华书局一九三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