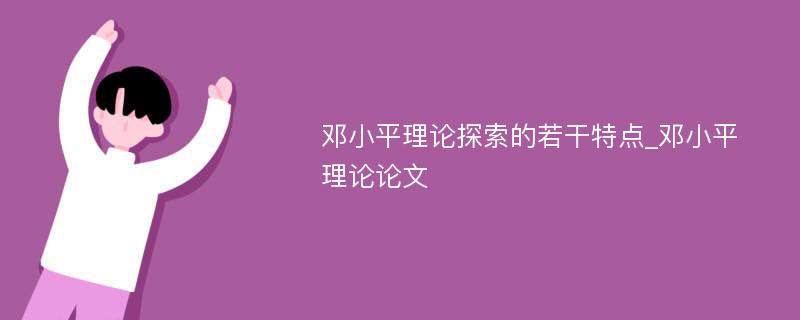
论邓小平理论探索的若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最成功的一位改革家。他不仅是有高度智慧的杰出政治家,而且是思想深刻、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理论为中国开辟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使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僵化甚至瘫痪的状态,变成日益开放、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状态。使中国发生巨变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形成的?本文试图分析他在理论探索方面的一些特点。
一、目光远大、脚踏实地
他提出要“面向世界”,“要赶上时代”;又强调一切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他提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P373),把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古老的、曾经一度封闭的国家,重新纳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又反对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博和契机;又脚踏实地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去回应时代的挑战。
首先,我们以中国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制定来说明这一点。当文化大革命结束、重新打开窗户看世界之时,邓小平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78年8月,他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落后。什么叫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更不一样了。”[2](P76-77)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初邓小平频繁出国访问,大多数时间用来考察经济。1978年10月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79年初访问了美国。这一系列出访,使邓小平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了解了现代化,了解了中国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强有力地推动他用新的思路去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远景规划。在这一系列出访以后,1979年7~8月间,邓小平又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先后视察了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调查研究,一笔一笔地算帐,逐步形成了到本世纪末的目标。他在回到北京以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用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70年代末的水平,平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人口太多,每人一辆汽车,我们不能那么搞,新加坡平均收入每人2700美元,我们达不到。1979年12月,邓小平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之家”。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均达到800~1000美元。1981年提出,10年翻一番,两个10年翻两番的设想。在此基础上,到1982年8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分3步走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设想。
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决策和中国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同样体现了上述特点。他以敏锐的目光,观察到西方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生的新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重视市场作用的东亚正在崛起;而忽视市场机制的苏联东欧国家日子都不好过,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P236)的命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点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P16-17)正是由于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作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重大决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此同时,中国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走向市场经济,就在于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例如: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的,它不仅带来了农业的大发展,而且带来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多种经济成份的大发展,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乡镇企业,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土特产,在中国行之有效,尽管还存在产权不够明晰之处,但它们是必要的过渡。
二、尊重实践、尊重群众
邓小平强调理论的正确与否要由实践来检验。“四人帮”倒台不久,中国就发生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点我们要感谢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危机推动了人们进行思考,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使是毛泽东说的也要由实践来检验。邓小平支持了这个观点,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带来了一场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强调实事求是,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强调用经济改革来带动政治改革,这些都来自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不可能为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国提供行动纲领。他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邓小平的尊重实践是同尊重群众相联系的。有的社会主义者一事当头,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改造人,尤其是改造农民;想到的是反对群众、特别是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性。邓小平也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但他在作出决策、提出理论观点时,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利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他善于总结群众的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是哪位理论家提出的,是哪位政治家设计的?都不是,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农民发明的,是实践中闯出来的。乡镇企业也是农民创造的,是实践中闯出来的,是出乎人们预料的,因此邓小平把这叫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包产到户这个曾经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典型,在邓小平那里变成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明”,变成了中国农村进步、甚至全国进步的一个重要源泉。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时,既重视理性的思考,又注重群众的要求和创造,注重社会经济的自发发展,从而使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同自下而上的推动相结合,使改革取得了自我推动的良好态势。
尊重实践,决不否定理论的重要。否则改革就成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谁能否认中国在改革之初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呢?但是,在邓小平看来,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它必须由实践来修正、丰富和发展。他强调我们在改革中缺乏足够的知识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强调要用自己的实践来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回顾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制定和演变的过程,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农村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功,决定把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才在1984年党的经济体制改革文件中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邓小平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P91)这个决定推动了思想进一步解放,促进了各地的开拓进取,各地的市场活跃起来,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生活也因之明显提高。这些成就又极大地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党的“十三大”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提出:新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三大”以后,我们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根源于两种体制并存,造成磨擦很大、漏洞很多、效益下降、腐败蔓延等问题。这两方面再次强有力地推动改革的深化和理论的创新。到“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写入代表大会的决议。可见,如果离开了实践,仅仅根据我们原有的理论和知识连改革的目标模式都无法正确制定。
尊重群众的创造,并不否认改革需要制度设计。否则就会把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混为一谈。有谁能否认中国历次改革的决议都提出了或详或略的改革蓝图呢!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把邓小平叫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呢!但是它承认事先没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知道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更不可能知道通过一条什么道路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并使人民得到较大的利而受到较小的害。
三、把目标放在首位,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
从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探索改革道路的方法有重大创新,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目标放在首位,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有人揶揄说:“中国的改革是两论起家。一是猫论,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二是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这两论起家恰恰是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改革之初,改革的目标尚不明确,缺乏一个全盘改革的蓝图,可以说改革的理论准备是极不充分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僵化思想和僵化观念更加僵化,根本不可能为改革作理论准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实际生活要求立即进行改革,没有时间先进行理论准备,再进行改革,只能从缓解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某些最紧迫的矛盾人手启动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能够大踏步地前进,闯出一条积极大胆的渐进改革道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论”。
所谓猫论,无非是把目标放在首位的理论。这个目标不是激进改革那种在缺乏足够信息和知识的情况下制定的详尽改革蓝图,而是有足够信息可以判断正确与否的基本要求,这就是“三个有利于”中提出的三大目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否达到这些目标是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在把这些目标放在首位的前提下,进行“大胆地试”,试验要大胆,推广要谨慎。邓小平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1](P113)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错误赶快改。这就是所谓摸论。改革是有风险的,大量的错误不可避免的,某些改革能否成功,它的后果和连锁反应,事先不可能收集到足够的信息,作出完全符合实际的估量,因此它必然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大胆的试、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使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来进行试错。可以通过边试验,边纠正,避免犯大的错误;而激进的快速改革使社会无法通过逆转来避免巨大的风险。先试点,后推广,可以避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争论,通过大胆地试,通过实践来统一认识。不搞争论既意味着允许试,也意味着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试就试,愿意看就看。这样看起来改革的步子放慢了,实际上这是很有效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路子。在改革之初,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况还相当严重,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例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兴办经济特区等都有不同意见,如果试图通过争论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几年、十几年也未必成功,把时间都给争掉了,什么都干不成。相反,通过大胆地试,思想较快地得到了统一,步子反而加快了。通过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闯出了一条积极与渐进相结合、胆子大和步子稳相统一的渐进改革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使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在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发挥积极效应。
过去,许多理论家反对试点和局部改革,他们说:经济体制改革就如交通规则改革,汽车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放几部汽车出去试点,或进行交通规则的局部改革,都必然造成撞车。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如此,试点和局部改革必然造成严重的磨擦而归于失败。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试点是必要的,局部改革是可行的。尽管这样做有种种弊端,它造成经济生活中的严重磨擦,带来腐败的蔓延,而且局部改革拖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越高。但是,由此否定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是极大的错误。
这种方法并不否认改革的整体性要求。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没有整体性的方案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有谁能否认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提出的整体改革方案呢?但是中国的渐进改革并不把整体性改革方案同某些局部先行对立起来。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很大,有的改革不可能在各地同时具备条件或具备同样的有利条件。中国某些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成功实例,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正确。中国的渐进改革也不把整体性要求同改革目标模式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实现对立起来。由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完全实现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天,因此某些旧体制的组织和行为,尽管在改革的终点会被消灭,但往往不可能一下子消亡,而有一个逐步替代的过程。不仅如此,它们在改革过程中往往需要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双轨制就是如此。尽管双轨制的存在确实也带来了经济生活中的种种混乱。但如果试图立即消灭旧体制的一切组织和行为,恐怕会造成更大的混乱,甚至导致经济崩溃。
激进改革的建议者、《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作者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对于激进改革的失败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我的建议是以对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成果的预测为基础的,然而我的判断错了。我没有预见到随后的经济危机,我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期过于乐观”。“宏观稳定不是一次战役,而是一场无止境的战争。稳定性不能通过一步跨越来获得。制度变革只能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革逐步完成。我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很后悔当初在《路》中没有重点提出”,“那时,许多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参与者就受害于对速度的迷恋”。“转轨只能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是革命与演进相结合的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