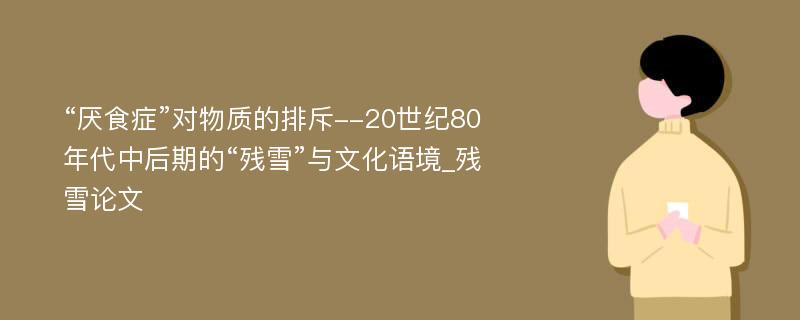
“厌食者”对物的拒绝——残雪与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残雪论文,语境论文,后期论文,年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5年,残雪在发表了《山上的小屋》之后,便持续地创造着一个阴暗,有着南方潮湿和霉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墨色的雨,是墙壁上的霉斑,浑身发粘的汗和酸臭味,是苍蝇、老鼠、蛆、白蚁、蛾子、蜈蚣、臭虫、死麻雀、蝙蝠等等等等。她将现实与梦境混淆在一起,用一种冷峻的眼光,创造了诸多恶、丑的意象,扭曲的梦呓和谵语。残雪像一个孤独的谵语者,不遗余力地将世界的恶与丑揭示出来,触目惊心地放在人们眼前。这样,人们不禁惊异于残雪对于这个肮脏世界的忍耐力,和表现这个世界的持久的热情。虽然研究者也发现:“乖戾心理的描述,将读者带进有关人的精神欲望的内心世界,展示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人性卑陋、丑恶的缺陷。”① 但是,似乎总是缺乏一种有效的解读路径,能够捕捉到残雪的小说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张力。
残雪小说中的“厌食症”主题让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让我们看到,残雪正是在对一个不断兴起的物的世界的抵抗中持续地表现着创造力和批判力。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新的关注点和价值标准。随着人们对于“主义”宏大话语的摒弃,精神性的关注也渐渐淡出。这样,物的世界的不断扩张,就不仅仅是经济建设成绩的显现,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扩张的结果。巴赫金在对《巨人传》的解读中指出:“饮食、交媾、排泄、生育这一系列物质——肉身的活动是人与物质世界交流的手段,潜在地代表着一种依靠大地,依靠下部(肚子、生育器官)生活的理想。”② 巴赫金的理论要在另一种语境下进行理解,但是,他的解读路径让我们看到,文学创作中的饮食、交媾、排泄、生育活动,是对个体与物质世界关系的一种象征。让我们先来分析以下细节:
吃中午饭的时候,他用力嚼着一块软骨,弄出“嘣隆嘣隆”的响声。
“好!好!”慕兰赞赏地说,喉结一动,“咕咚”一声咽下一大口酸汤。
女儿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口里弄出“嘣隆嘣隆”的声音,喉咙不停地“咕咚”作响。
吃完了,他擦着嘴角的酸汤站起来,用指甲剔着牙,像是对老婆,又像是对什么别的人说“窗棂上的蜘蛛逮蚊子,逮了一点多钟了,哪里逮得到!”
“工间操的时候,林老头把屎拉在裤裆里了。”慕兰说,一股酸水随着一个嗝涌上来,她“咕咚”一声又吞了回去。③
这是《苍老的浮云》当中一段关于吃饭的描写。显然,在吃饭的时候看到蜘蛛、蚊子这一类东西时是会影响食欲的,如果听人说起“林老头把屎拉在裤裆里了”之类的话,或听到有人嚼软骨发出“嘣隆嘣隆”的响声,则更会影响食欲。实际上,残雪在她的小说当中,会调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食欲都将是不可能的。“我的胃里面结出了小小的冰块。我坐在围椅的时候,听见它们丁丁当当响个不停。”④ 与此同时,残雪将“吃”本身也描写得古怪和丑陋,比如,嚼软骨时发出“嘣隆嘣隆”的响声,比如,“一股酸水随着一个嗝涌上下”,然后,又“咕咚”一声又吞了回去。所有这一切表明,这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厌食症的患者。
显然,这是一个与《美食家》当中的宴席完全不同的情境。在《美食家》当中,陆文夫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人的食欲,将口唇欲望叙写发挥到了极致。而食欲的描写与当时的文化政治语境有着微妙的关系。食欲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相当重要的方面,食欲的描写相当程度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微观层面上的回应。可以说,80年代大多数小说在大量“饥饿”叙写的同时,对肉身生存的底限是达成共识的,有代表性的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美食家》、《绿化树》、《灵与肉》等等。他们通过各种文学手段改善个体与肉身及其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
残雪是这股潮流当中的异类,她与多数作家做着相反的事情——竭尽全力地批判反思个体与肉身及其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揭露这其中的幻象。在残雪看来,这个物的世界是欲望在梦境当中的化身,残雪用梦境的夸张、扭曲等等所有可能的手段,来揭露物的世界的另一面——欲望。她用她的人物说出来:“势利小人!算计者!我的天呀……”⑤ 在残雪的小说中,物的世界伤害着个体,引起个体的恐慌、焦虑,就像到处爬的老鼠、蛆、白蚁等等,并且,这个物的世界越来越扩张,无法阻挡。于是,其中的人物必须不断地用杀虫剂来消灭他们。杀虫剂代表着用一种暴力的手段来消灭物的世界。
肉身与物质世界的联系还有消化、排泄,这些在残雪的小说中也表现得丑陋和病态,让人知道,这是一个患了重病的肉身。“慕兰传染上了他的失眠证,从此以后也睡不安了,虽然不做梦,却老在床上滚来滚去,伤心地放着臭屁,唠叨:‘自从认识到他的才能范围之后,消化功能就出了毛病。’”⑥ “荡到中午,绳子终于磨断,粪桶砰的一声落在地上,他自己也摔断了一条腿。”⑦
当一个肉身的吃、消化、排泄等等与物质世界的交流手段统统被阻断之后,这个肉身必定是羸弱,而且不可救药地疾病缠身。“在窗外,惨白的月光下,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裸体女人,那身体的轮廓使他蓦地一惊,身上长满了疹子。……那女人正站在窗玻璃外面,干瘪的乳房耷拉下来,浑身载满了火星。”⑧ 对于羸弱、丑陋的肉身,当然会产生厌恶,乃至于不管不顾。“她老不洗头发,她一接近他,头发上那股酸臭味儿就猛冲他的鼻孔。后来有一天,她拿盆子来洗头了。大块的污垢连着头发根从她脑袋上掉下来,落在盆子里,所有的头发全脱光了。”⑨
与此相伴,肉身与物质世界交流的最重的途径——生育,也被毁掉了。“‘有时候’,她对他揶揄地一笑,‘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女人的肚子,只不过是一张皮和一些肮脏的肠子还有鬼知道是什么的一些东西。’”⑩ 小说的主人公也会爱吃一些东西,比如酸黄瓜、梅子,我们会发现,这是怀孕的征兆。在这里,吃酸黄瓜是对怀孕的象征,表达了对怀孕的一丝渴望。但这种若有若无的渴望马上就会转化为厌恶。“然而她到现在还没消失,她在阴暗发霉的小屋里像老鼠一样生活,悄悄地嚼着黄瓜和蚕豆,行踪越来越诡秘。他每星期给她送蚕豆,那惭愧的心情就如同嚼着一只老鼠。‘分开后感觉怎么样?’有一天她吐着蚕豆壳随随便便地问他,好像他是她的一个邻居。‘也许身心两方面都健康得多。’”(11) “老况说他想用老鼠药毒死我,也不过就想一想罢了,他一点胆量也没有,他是一条圆滚滚的蛔虫,我看见他夜里钻进母亲的肠子,十分惬意地巴在那上面了。说不定有一天他母亲会把他屙出来的,一想到他被他母亲从肛门挤出来的样子就好笑。”(12)
在日常经验中,“吃”维持了肉身的生存,但是在残雪的小说当中,某些近乎狂疯的“吃”却是对肉身的伤害,这象征了物的世界对个体的伤害。“她吃起东西来毫无顾忌,满不在乎地嚼得牙巴大响,完全酷似她那疯疯癫癫的父亲。……他看见老婆正在吸吮他的腿子,做出猫吃肉的种种姿态。她的舌头上生着密密麻麻的肉刺,刚才在梦里他就是被这些肉刺扎得痛。他想缩回腿子,无奈她使出从没有过的蛮力按得紧紧的,用力咬着,像要将小腿上的大块肌肉全撕下来吞进肚里去。……每天早上起来,他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还肿起老高。他的身子一天天变细,肌肉一天天消融,淋巴结像一个个鸽子蛋。”(13)
但是,仅仅把残雪小说的意义停留在对物质世界的象征层面是不够的。那个扭曲、夸张的世界让我们联想到了《神曲》当中的某些场景。的确,在一些宗教故事当中,贪吃是一种罪孽,它会受到相当严厉的惩戒,如火烧、荆棘,还有死亡。惩戒同时也意味着对疾病的治愈。无独有偶,在残雪小说当中,这些因素都出现了。“当火苗几乎舔到了天花板的时候,借着晃动的亮光,她看见前夫像蜡一样融化着,越来越矮下去,头部痉挛地一伸一伸,悲惨地打着呃逆,眼珠渐渐收缩为两个细小的白点。‘我的脑血管破裂了……’他可怜地哼了一声,吐出一口黑糊糊的东西。”(14)“墙上的青苔被他不断地抠下,纷纷掉落在地上,他还在跑——朝着臆想中的通道。她听见石磨碾碎了母亲的肢体,惨烈的呼叫也被分裂了,七零八落的,那‘喀嚓’的一声大约是母亲的头盖骨。石磨转动,尸体成了稀薄的一层混合物,从磨盘边缘慢慢地流下。”(15) “他在夜里梦见了荆棘,他赤身裸体扑倒在荆棘上面,浑身抽搐着,慢慢地进入了睡眠。”(16)
通过对残雪小说当中的一组意象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的确包含着对肉身及其周围物的世界的厌恶、憎恨和恐惧,主人公只有在烈火、荆棘和死亡的惩戒当中,才能得到安宁和纯洁感,并获得新生。这隐隐暗示某种宗教的主题,在基督教和佛教当中,这种主题并不鲜见。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残雪对于那个肮脏、病态的世界为何有着如此的忍耐力,和如此持久的憎恨。残雪经常提到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饥饿艺术家以忍耐饥饿对抗着发达资本主义的丰盛的物的世界,并且把忍耐饥饿上升为一种艺术。但是,这种艺术没有人能理解,只是一个与马戏无异的,被大众观看的杂耍。艺术家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最后饿死了。他想让大众理解他的艺术的意义,但是他没有做到,他被理解为一种奇观,一种杂耍。他的艺术也被物化了,奇观、杂耍通过买票就可以看,其中的批判力量被理解为新奇,并且被一次性地消费掉了。残雪的小说在精神上与卡夫卡是相通的。
通过对肉身的惩戒和对物质世界的厌恶来恢复个体的能动性,这条道路在80年代是作为异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少数极端的艺术流派当中。残雪小说的这种意义并未被人们认识到,她更多地是被当作先锋派小说家来看待。尽管80年代小说在肉身生存的底限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80年代小说就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饮食也有它自身的政治伦理学,它意味着一种权力。比如,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感到饥饿?饥饿会产生什么力量?谁会感到饥饿?谁的胃口才是合法的?并可以得到怎样的满足?
90年代初,中国社会逐渐向消费型社会转变,慢慢创造出“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17) 这不仅仅是一个物的世界,而且是一个“新意识形态”扩张的世界。当我们看到残雪小说当中对于肉身及其周围的世界的憎恨的时候,也应同时看到它对于物的世界的批判。残雪把丰盛的物的世界翻了过来,把这之下的老鼠、蛆虫,以及疾病、死亡展示出来,让人意识到,丰盛的物的世界有时也可能是一种假象,它制造出欲望,让个体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这样,它未必就不是一种对个体的伤害,未必就不是对个体能动性的遮蔽。在残雪发表于2003年的《最后的情人》(18) 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梦的世界,那里更加纯净,更加寂静。残雪在揭露物的世界之丑恶之后,显然也在创造一个洁静的世界,这种创造是不廉价的。
注释: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②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③⑤⑥⑨(11)(12)(13)(14)(15) 残雪:《苍老的浮云》,《苍老的浮云(小说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第224页,第232页,第236页,第241页,第259页,第264页,第276页,第279页。
④ 残雪:《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小说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⑦⑩ 残雪:《黄泥街》,《苍老的浮云(小说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8页,第91页,第311页。
⑧(16) 残雪:《下山》,《苍老的浮云(小说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17)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8) 残雪:《最后的情人》,花城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