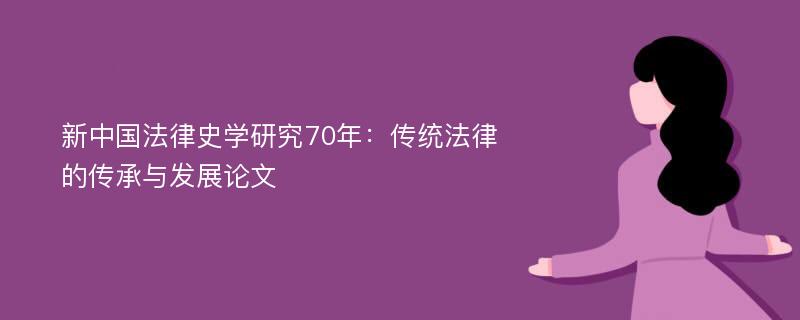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专题§
新中国法律史学研究70年:传统法律的传承与发展
张 生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法律史学是最早复兴的法学学科之一,但限于当时的知识导向,中国传统法律只能通过“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形式得以传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法律史学是最早兴盛发展的法学学科,传承与发展的研究工作主要沿着制度史和思想史两个方向展开,在史料整理、考证解释、通史、断代史和专题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工程之际,如何“阐释建构,贯通古今”,为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提供文化支持,成为传承和发展传统法律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 中国法律史;传统法律;传承;发展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十位著名教授联合发表文化宣言,提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1) 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4期。 中国传统法律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基本体系样式、运作机制、价值理念陈陈相因,却又因应时势屡有变迁。如何客观认识、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清末变法以来一直持续而未完成的文化事业。中国法律史是近代以来我国最早创建的本国法学学科之一,(2) 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设有“中国历代刑律考”“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还有“法律原理学”(后又称法学通论、法理学)“大清律例要义”,其余均为各国部门法、交涉法、财政学、行政机关学。后来程树德、郁嶷、陈顾远、丁元普等在批判借鉴浅井虎夫《支那法制史》的基础上,著有《中国法制史》。杨鸿烈在梁启超批判探究中国古代成文法和法学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形成了制度与思想两分的传统法律体系。 中国法律史学的繁荣发展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不同代际的中国法律史学人怀着深厚的“传统”情节,致力于中华传统法律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尊敬的成就。本文拟从“传统法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对70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做一概要总结。传承是文化甄别延续的维度,发展是文化适应变迁的维度,两者有所区别又浑然一体。传统法律唯有在传承和发展中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滋养现代法治。
一、曲折的复兴:以国家政治史的架构传承中国法(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全面废除了国民政府法律法令的效力,在政策上也改变了全面继受西方法律的知识导向。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 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 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制定新法律、法令, 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更多依据的是革命经验和借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新建的法学学科没有延续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制史,而是仿照苏联法学教育体系,设置了“国家与法权历史”课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编写了《国家与法的历史》(或《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中国国家与法权的历史》)的教科书以及相关的辅助教材。在“国家与法权历史”的结构中,以人类社会和国家发展形态为线索,在每个时期都按“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四个部分来安排。“国家与法权历史”课程以国家政治史为理论框架,机械套用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强调法的政治从属性和工具性,忽视了法律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理论框架强调法的阶级性,形成了一种“阶级本位的政策法”理念, “以政策为最高行为准则, 以法律为次要的行为准则”,(3) 武树臣:《从“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到“国、民本位·混合法”时代——中国法律文化六十年》,曾宪义主编:《法律文化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 存在滋生法律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拥有最为丰富历史典籍。诸子之学中包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自《汉书》以降,志书之中的礼、选举、职官(百官)、刑法、食货多有关国家法律制度,后世的律典、会典,以及会要、通典、通志等断代或通览的政书都记载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制度形态、演变得失。在推行“国家与法权的历史”的理论框架的同时,法律界的前辈们没有停止探索新的知识途径,以传承传统法律,延续近代化法制成果。“1956年4月间,法制委员会就华东政法学院杨兆龙先生提出旧法继承性问题,组织讨论。与会者基本同意旧法可以批判继承。”(4) 张晋藩:《总结过去 开拓未来——中国法制史学研究六十年》,《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第174页。 同年11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5) 1951年11月底,新法学研究会与新政治学研究会合并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简称政法学会),至1953年4月,政法学会正式通过了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 召集了一次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座谈会,讨论了法制史学科的定名、研究对象、史料收集整理、研究方法等问题。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召开的最为重要的一次法律史学科讨论会,会议“发言摘要”篇幅虽然不长,却十分精要,60多年后回味起来,其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令人感叹。从后来发表的“发言摘要”(6) 参见《中国法制史问题座谈会发言摘要》,《法学研究》1957年第1期,第48-55页。 来看,14位发言人(2人提交书面发言材料,2人在同一主题下发言,还包括杂志社的郭纶)中,有5位明确表达“中国法制史”要比“国家与法权历史”能更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地位和特点;有3位在发言中,直接使用“中国法制史”,也同意定名为“中国法制史”。有4位发言人明确表达,不仅是“国家与法权历史”已经开课五六年,重要的是把法律置于国家政治的大历史中加以考察,更为科学。有2位发言人只是谈到具体问题,对学科名称没有发表意见。总体来看,同意将学科定名为“中国法制史”的发言人较多。第一位发言的李祖荫,在题为“向‘法制史’进军的几件准备工作”的发言中,他引用《礼记·月令》考证了“法制”一词的出处,认为“法制二字联用,由来已久”,“现在仍然用‘法制史’,我想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在传承优秀法律遗产方面,他和后边几位发言人都提到“一定要掌握大量资料,同时也要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之后,才能加以采择,万万不可以被资料所束缚”。陈盛清在发言中提出:“整理我国法律文化遗产要打破一些陈旧观念”,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大家要分工合作,“除了集中现有法律工作岗位上的人力以外还可粗搬一些对于旧法学有专长具备解释我国历代法律或法学典籍的条件的人共同参加这一工作。”卢蔚乾、杨玉清和曾炳钧都谈到了法学遗产的范围和研究方法,他们的共识是从经典文献入手、从小的问题入手,“专一人、专一代、专一法”,持以时月,便会取得可观的成果。如果按照这次研讨会的设想得以实施,传统法律的传承与发展的成果必然已经融入社会法治建设之中了。
对于安全级别要求较高的信息系统,也可以考虑在自身应用系统中额外加入身份认证模块,如二次密码、问题验证和令牌等认证方式[3]。
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至1965年分三册出版完成(第一册“古代部分”,第二册“近代部分”,第三册“民主政权”部分)。这部讲义体现了中国法律史学者在国家与法权的框架下,“传承中国古代传统”“批判移植西方法律”“发扬革命根据地法制传统”所做出的努力,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重点整治群众身边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意见》举例:“漠视群众利益和疾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无动于衷、消极应付,对群众合理诉求推诿扯皮、冷硬横推,对群众态度简单粗暴、颐指气使。”这些现象,是严重脱离群众甚至侵害群众利益的恶劣行为,对此中央明确要求,一定要坚决整治。
在城市中心繁华地区,为将对城市环境影响减少到最小,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多采用地下隧道敷设方式[9]。利用Civil 3D部件编辑器定置和装配隧道断面。根据隧道结构,通过定义顶拱半径、侧拱半径、仰拱半径、初次衬砌厚度、二次衬砌厚度等参数控制隧道断面形式。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各参数,建立不同隧道断面形式。根据定置隧道参数生成的隧道三维模型如图2所示。
每一个研究者研究的兴趣和目的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整体,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法律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法律。为了实现传承和发展,法律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连续的层次:“史实”的层面(是什么),“根源”的层面(为什么),“意义”的层面(价值取舍)。当前的法律史研究成果,有很多仅仅注重史料和具体现象的研究,而忽视对传统法律历史根源的挖掘与对价值的探讨。这种研究状况制约了传统法律的发展。有学者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析和反思,徐忠明认为:“首先, 历史考据 ——史料辨析与文献整理,都是中国法律史‘现象’(史实)研究的基本前提;舍此,研究根本无法措手。其次,历史现象背后的‘根源’的挖掘,也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中介层次,谈论中国法律史的意义而不明根源无疑是缘木求鱼,绝不可能。最后,历史‘意义’的追问和诠释,实乃中国法律史之为中国法律史的存在理由,它以史料考据与根源挖掘为基础, 又是发展与提升, 甚至可以这么说,对于意义的诠释才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基本宗旨与最高境界。”(23) 徐忠明:《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第9页。 王志强指出:“20世纪,在海内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和在方法论上逐步转换的过程,在研究取向上表现为从前期的大规模资料整理、译介和考据并利用既有的西方话语系统加以整合的事实描述式研究,逐步发展到通过扩展学科视野对既有框架进行反思和重构的理论阐释式研究的渐进过程。”(24) 王志强:《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取向的回顾与前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体现出描述传承的成果丰硕,阐释发展的研究不足的特点。
二、兴盛与隐忧:传承成果斐然,融贯发展不足(1979年至2019年)
(一)学科的兴盛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以西方法学的立场和框架、以现代部门法的方法,脱离具体历史语境来观察、分析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倾向,产生所谓“以西例中、以今例古的倾向明显,宏大叙事与精细考证的脱节”之弊。(17) 俞荣根、秦 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法思想史研究》,《孔学堂》2018年第3期,第102-103页。 而对中国古代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充斥着时空错位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中心主义的立场。这样的研究范式,阻碍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客观认识和传承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数量化科研考核的体制下,法律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快速增长,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却存在背离历史客观的隐忧。一方面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法律史文献,另一方面法律史文献的利用却并不充分、并不系统,而是机械运用西方的、部门法的逻辑和理论评判中国传统法律。因而有学者指出:“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18) 胡永恒:《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78页。 比较典型的论断,就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和传统法律的评价,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中国在体制上属于“家产官僚制”,即“儒家文化取向的官僚政体”;(19) 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页以下及“译者序”。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具有卡里斯玛人格,拥有天赋的权力,统摄立法、行政、司法权,极权专断;而法律不具有独立性,各级官员的司法裁判类似于古代伊斯兰国家的卡迪司法。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自然科学、民主政治和法治秩序,广泛使用酷刑。(20)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法律领域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多持“极权政体与驭民工具”的评价,如弗朗斯瓦·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梅因的《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等,晚近有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卡尔·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昂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约瑟夫·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S.N.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 这样简单运用西方近代逻辑、理论评判中国传统法律的论断,却有着很广泛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秩序是“非理性”的,却又是“超稳定系统”,具有“不断重建”的恢复能力,(21) 参见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不仅延续了两千多年,甚至在近现代这种“非理性”的规范模式还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以近代西方的逻辑和理论对古代中国传统法律加以评判,必然导致对中国问题解读的片面和非客观。这种做法非但不能传承传统法律,反而抹煞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客观面貌和文化根基。一旦丧失了历史传承,我们的现代法治建设也将失去文化基础。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中国法治的发展一旦丧失传统的根基,以法律西化为主导的法治现代化不过是海市蜃楼,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中国法学的发展一旦丧失话语的主体性,以理论西化为基调的法学繁荣不过是浮光掠影,难以维持长久。”(22) 高鸿钧:《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第167-168页。
法律史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阐释是对传统法律最重要的传承,反映了传统法的本来样态,也是进一步研究阐发的前提。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法律史学科恢复不久,学界前辈们就高度重视法律史料的收集整理:“从基础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再下功夫,尤其要注意对史籍中尚少使用的法律史料,对历史档案中的法律史料和新发现的地下文物中的法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6) 刘海年:《努力发掘新资料,繁荣中国法律史学(代序)》,《法律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继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考古整理之后,岳麓秦简、里耶秦简、睡虎地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出土与整理研究,推进了秦汉法律制度的复原与研究。刘海年、杨一凡先生主编的共3编14册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于199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续编》《中国律学文献》《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相继出版,成为中华法律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沈家本未刻书集纂》《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沈家本全集》为研究沈家本的思想和清末法制变革提供了珍贵史料。《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的编辑出版,为研究近代法律和政治变革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中国台湾学者黄源盛所主持编辑出版的《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大理院刑事判例辑存》《晚清民国刑法史料辑注》《晚清民国民法史料辑注》及《平政院裁决录存》,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法制和司法裁判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以及各地方档案馆、图书馆,通过整理档案、法律古籍,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法律史料资源,也因此涌现出大量利用第一手文献资料的优秀成果,如《碑刻法律史料考》《实验法院: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一次地方试点》《刑鼎—宗族法令与成文法公布——以两周铭文为基础的研究》等。
(二)丰硕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学人经过40余年的艰辛努力与学术积累,在传承传统法律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据赵九燕、杨一凡在《百年中国法律史学论文著作目录》中统计,“19世纪末至2010年100余年,在各种中文报刊、论文集发表的法史论文索引21000余条,公开出版的法史图书索引3100余条”。(13) 赵九燕、杨一凡编:《百年中国法律史学论文著作目录》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凡例”。“法史”即是“中国法律史”。 1949年10月以前发表的论文90篇左右,编印、出版著作约150部,扣除这部分论文和著作,1949年10月至2010年12月发表法律史论文20000多篇,著作近3000部。2011年至2019年8月发表论文13000余篇,出版著作700余部。(14) 参见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法律年鉴》,北京:中国法律年鉴社,2010—2018年。 70年来中国法律史发表文章33000多篇,出版著作3700余部。这些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特别是2011年以来,平均每年发表学术论文1000多篇,出版著作80部左右(含教材在内)。在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中,不同代际的中国法律史学者对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法律史学科成为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的新学科,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光灿、张国华先生主编的12卷本《中国法律思想通史》1998年到1999年陆续出版。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此书以通史的形式,详细梳理历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民事、宗族、诉讼法制等各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法制历史中的经验教训。这两部多卷本集中了当时优秀的法律史学者,吸收了法律史学界研究累积的优秀成果,是中国法律史学学科建设的新的里程碑,标志着这两个分支学科的体系化。(15)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中国法律史学三十年(1978—2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编:《中国法学三十年(1978—200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众多的优秀成果中,学者们聚焦于“传承”这一主题,系统研究了刑法史、民法史、行政法史、经济法史、司法制度史等,试图沟通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并为当代部门法学的研究和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借鉴。此外,法史学者在考证解释通史、断代史和专题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
法律史学的兴盛发展,得益于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传承稳定的学术队伍,形成了有领导力、组织良好的学术团体。1979年9月,我国法律史学者在长春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法律史学学术研讨会,组织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以下简称“法律史学会”)。法律史学会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法学界最早组织成立的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长春会议奠定了法律史学会的学术基础和组织基础。40年前,第一次法律史学会讨论的“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为后来的学者所遵循和发展;会议计划编写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卷本)、《中国法制史》(多卷本),(11) 李光灿、张国华总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11卷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开始出版,张晋藩总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在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已然成为法律史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长春会议上成立的法律史学会,从当年会员不足百人的学术团体,发展到今天已有八百多名个人会员的学术群团,学会内部先后成立了10个专业委员会和分会,(12) 目前有8个专业委员会和分会定期举行学术活动,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独立注册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 成为一个真正全国性的专业学术团体。学会及所属学术单位编辑了多种连续出版的学术集刊如《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中西法律文化》《中华法系》《法律史评论》《法律文化研究》《法律文化论丛》《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法史学刊》等,在各领域对中国法律史研究作出了精深拓展。法律史学会为学术队伍的传承,为法律史学的交流、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组织贡献。
(三)对传承与发展的反思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在时代转折之际,中国法律史学者站立在时代前沿,为中国法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人治”与“法治”的讨论,是当时中国法学界遇到的重大的学术议题之一。法史学的学者在当时激烈的学术争论中担当起主力军的作用,在学术问题上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责任。法律史学者谷春德、吕世伦、刘新先生率先撰文专论人治和法治,张晋藩、曾宪义先生发表了《人治与法治的历史剖析》,张国华先生发表了《略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法治’与‘人治’》, 对历史上关于人治和法治的讨论、西方的人治法治论和法治人治的本来含义,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与总结研究。同时,在此一时期的热点问题如“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法的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讨论中,法史学者都积极参与并产生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如“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复刊后的《法学研究》在第一期登载林榕年先生题为《略谈法律的继承性》的文章,第二期登载栗劲先生题为《必须肯定法的继承性》的文章,引发法律史学界的一系列讨论。学者们最终论证认为,法律的阶级性不能否定法律的继承性。今天看来,这场争论是对建国初期“法的继承性”讨论的深化,它实际上涉及整个法学中最敏感的问题——法的阶级性问题,“这场争论以承认法律有继承性结束,便实现了历史与今天的联接”。(9) 参见徐祥民:《架起联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谈中国法律史学50年的经历》,《山东大学学报》 1999年第3期,第20页。 通过对这些根本的、重要的学术问题的讨论,法史学者以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清本溯源,为中国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使法史学科成为一时“显学”。有学者总结法律史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机遇时说:“在法律几乎‘空白’、法学‘幼稚’而社会又急切呼唤的背景下,相对于当时法理学研究的诸多禁区、部门法学研究的阙如而言,法史学几乎是当时唯一尚有一定基础并可‘研究’的科目。”(10) 马小红:《中国法史及法史学研究反思——兼论学术研究的规律》,《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第232页。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法学院校、科研机构多被解散,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陷于停顿。从1949年到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文化事业尚不发达,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处在复兴状态之中,其传承成果也主要集中在一些粗放型问题和基本史料层面。由于政治运动,“完全阻断了清末以来中国法制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传统”,(7) 张晋藩:《总结过去 开拓未来——中国法制史学研究六十年》,《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第174页。 传承中国传统法律的事业变得愈加曲折。有学者对这段历史时期总结道:“1949年后随着教育界的院系调整,中国法律史学科几乎全面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学科建构的层面而更名为‘国家与法权历史’或‘国家与法的历史’,同时确立了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实现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但是阶级分析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唯一化和教条化运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法律史学科研究的僵化。”(8) 马小红、张岩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时代图景(1949—1966)——马列主义方法论在法律史研究中的表达与实践》,《政法论丛》2018年第2期,第131页。 令人惊喜的是,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考古发掘、整理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史上和法律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1978年,整理小组编辑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在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复原了战国末期到统一之后秦“法治国”的面貌,呈现了中国帝制时代法律的源头。
春天的田野是美丽的:蔚蓝的天空中,慢悠悠地飘过一朵朵洁白无瑕的云,它们没有线条,就像只用白色颜料泼出来一般,随意而自由。山路两旁有成片的野酸枣树、桃树、山楂、野荆,这个时节有些果木正好开花,成群的蜜蜂嗡嗡地在花丛间飞来飞去,一刻不闲地忙碌着。纵横交错的河支细干在小山村中纵情蜿蜒,河水清澈甘冽,调皮的鱼儿在纤柔的水草间来回穿行,时不时吐出一串串晶莹的水泡。这真是一幅美丽的春景图。
三、未来的期待:阐释建构,贯通古今
经历了70年的发展,日益强大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面对“传承与发展传统法律”的问题,需要为现代法治寻根铸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国家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对法律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从系统客观的史料出发,将法律史学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与创新应用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培育,是学界同仁们的时代责任。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该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需要学界同仁既要按照学术规律独立开展研究,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又加强团队合作,在研究阐发、传承转化、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构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滋养现代法治体系的法律史学。
从清末改法修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完成“六法全书”体系,皆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为原则,却未能传承传统法律,而以混合继受外国法为能事,致使数千年的法律传统在近代化进程中发生断裂。民国法学蔡枢衡对混合继受曾有深刻批评,他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法什九是在幼稚的法学知识和短时日的起草中产生出来的。……至于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起草的法律和草案中,不必要的矛盾,不应有的疏漏和可笑的穿凿附会,也常常可以发现。三十年来,法学体系的每一部门中,都已或多或少发现了这类幼稚现象。今后的发现预料还可一天一天多起来。” 他还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法,起初完全是在比较各国立法的氛围中产生出来的。后来的立法理由中虽常常可以发现‘斟酌中国实际情况’的语句,事实上,实在没有斟酌过什么,也没有多少可以斟酌的资料。所以事实上依然没有超出‘依从最新立法例’的境界。这种情形,从现象上看,比较的法例一多,采择自然容易乱。结果不仅每一条文的继承,不能和各该国家的学说、判例、历史或批评之间取得联络,加以考虑。就是连条文和条文之间的关系,原则和例外间的境界,也不容易把握正确。因此,法规成立之后,解释上常可发现主观上出于立法者意料之外,客观上近于笑话的矛盾,不平衡和不一致的现象。若从本质上看,惟新是求的精神实在是无我的表现,也就是次殖民地的反映。”(25) 蔡枢衡:《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55页。 不可否认,对外国法律持续的继受,所吸纳的优秀法律成果已成为现代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现代与传统的文化断裂,造成中国法律失去了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失去了文化的滋养,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不能发挥应有的治理功效,也丧失体系生长发展的能力。
由于医学心理学兼有医学和心理学知识的特殊性,同时又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这就决定了承担该课程的教师同样应兼具医学与心理学双重知识结构。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各医学院校的教师既往知识结构中没有医学心理学知识储备,而我国医学心理学教育规模又不能满足高等院校对医学心理学师资的需求。在学科设置和教育教学思想上受师范院校影响较深,课程教学重理论轻应用,缺乏完善科学的教材体系,教学手段与评价方式比较单一。这导致培养出来的心理学人才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均不能满足社会多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在专业基础、基本专业技能方面,反过来也削弱了学生对医学心理学理论的重视程度。
首先要回到具体的史境中,讲清楚什么是传统法律,要讲清楚传统法律文化的体系样式、构成要素、演变机制、内在价值,对中国传统法律有客观认识和本原的理解。为了讲清楚什么是传统法律,就需要系统收集、考证分析、甄别运用史料。历史的真实与客观性是以史料为前提的,史料的收集、考证、分析没有止境,这就要求我们尽量回归历史本原,去除推测和臆想的成分。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文献的收集、运用产生深远的影响,档案资料、古籍史料、论文专著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文献资源的信息化。在跨度数千年的文献中,可以收集到大量的史料,可以获得最新、最权威的史料考证,信息技术正在促成一种新型的、多元的法律史研究的产生。目前国家正在建设的“基本古籍法律分库”已经收录将近2000种文献资料,其内容还会不断丰富充实。在“讲清楚”的层面,需要回归传统法律生成的历史环境,以其固有概念加以表达,例如在《史记》中有“平准书”,《汉书》以后的正史中有“食货志”,近代有“民生”立法,在不同时代其称谓不同,法律的样态、功能、理念也有很大的差异。从客观传承的角度,不宜将其称为“经济法”“行政法”,而应该以固有的形态、称谓加以复原呈现,并探究其不同称谓下的社会历史含义。
其次,通过传统法律的运作、演变,阐释挖掘其规范技术、规范功能、价值理念的内在传承与发展变化,将传统法律转化成建构现代法律的资源。传统法律的形态是历史的,已经失去现实的生命力了,可是在传承演变过程中,其技术、功能、理念在演变发展中获得生命力,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具有持续性的意义。中国传统法律在数千年的漫长传承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了传承的文化密码,在发展中形成了持久的公平正义精神。传承发展的传统是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的,诚如文化学者所言:“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27) 傅铿:《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译者序》,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我国当代法治资源体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政权的法治传统、中国传统法律和近代以来继受的外国法三个部分构成的,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当代法治体系发展的文化滋养。还以之前提到的“食货制度”为例,在“说清楚”的基础上还要阐释建构:平准、食货、民生,其名称虽异,法律形态、规范范围也不同,但其制度功能和价值理念却是一脉相承的,是现代社会生存保障、工作经营、财产配置、市场干预等保障生存诸制度的整合体系。唐朝杜佑所作《通典》将其列为国家首要制度,现代法治国家,何尝不以民生制度为国家根本?古今国家制度功能与价值理念实则相通。
再次,在转化、发展传统法律的基础上,贯通古今法律体系,用传统法律智慧为当代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历史参照坐标。历史昭示我们,强大的国家都具有传承不绝、不断创新的文化支撑,人是传承者,也是创新者,在连续的传承中创新发展,“现代人正是去理解传统的思想遗产,而不是去迷信。现代人要求对历史遗产古为今用,去芜存菁,他们唾弃那种以为古人死人圣人的言论行为都是金科玉律的愚昧态度。现代人希望做传统文化的主人、发扬光大者和革新派。现代人不肯俯首帖耳地跪倒在传统精神之下,做奴隶、囚犯和盲信者,一句话,现代人比传统人更理解历史遗产的价值,更主动地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和存在形式。”(28)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如果从考证的角度来看,《尚书》诸篇并非尧、舜、禹时期的实录,附会了不少战国时期的制度与理论;《周礼》也并非是周代的礼制,虽以西周为原型,却带有后人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尚书》《周礼》正是古人“贯通古今、托古改制”的作品,这种传承发展的做法实际上推动了法律的发展,形成了一脉相承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对于中国法律问题,既要真正了解传统与历史,又要真正理解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的现实法律问题,以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把握中国传统法律的贯通与融合,为今天的法治建设贡献法律史学者的智识和力量。如学者所言:“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29) 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第70页。 “力求从历史流变中探究出普遍意义,甚至从往昔的经验里厘定出某些现代文明秩序中一般性的原则和规律,以便为当代的法律文明提供必要的参照视境和有益的建设资源”。(30) 胡旭晟:《描述性的法史学与解释性的法史学——我国法史研究新格局评析》,《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第40页。 《尚书》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31) 《尚书·大禹谟》。 《晋书·刑法志》继续发扬了“允执厥中”的治道:“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执厥中,俾后之人永有鉴焉”。(32) 《晋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的监修者恰好是唐律的制定者房玄龄。 在后来的唐律五百条中,体现了“中”的价值理念,可以说“中”是中国传统法中“贯通古今”的核心价值之一。古人之“中”,即我们当代之“公平正义”。
清末以来中国深受列强欺凌,已经丧失了文化自信,丧失了对传统的客观认识,“往时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在分析现代化问题中,很能注意中国保守思想之深厚,与保守势力之强大。追根究底,往往归因于儒家思想之顽固,以为这是妨碍改革阻滞进步的根核。尤可注意者,是这种推论已形成为现代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的解释管钥,构成一种推因的共同公式。人们可以很省力地拿儒家保守作为结论。至于有谁真正弄懂儒家的大致内容与性质,恐怕也颇成疑问”。(33)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 今天,我们要“贯通古今”,最重要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史料、各种阐释理论中,构建一个通览古今的“法律观”:法律是传承发展的结果,法律之良窳端在传统的传承发展。
70 Years of Legal History Research in New China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aw
Zhang Sheng
Abstract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legal history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legal disciplines, but limited by the knowledge direction at that time, Chinese traditional law could only be passed on through the form of “the history of state and legal right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legal historiography is the earliest revived discipline of law, and the research work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s mainly carried out along the two directions of i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sorting out historical materials, 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general history, dynastic history and monographic research. How to “interpret, construct and link up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 provide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untry ruled by law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New Era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aws.
Key words : Chinese legal history, traditional law,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D9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2019)05-0023-08
作者简介: 张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20)
(责任编辑:刘楷悦)
标签:中国法律史论文; 传统法律论文; 传承论文; 发展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