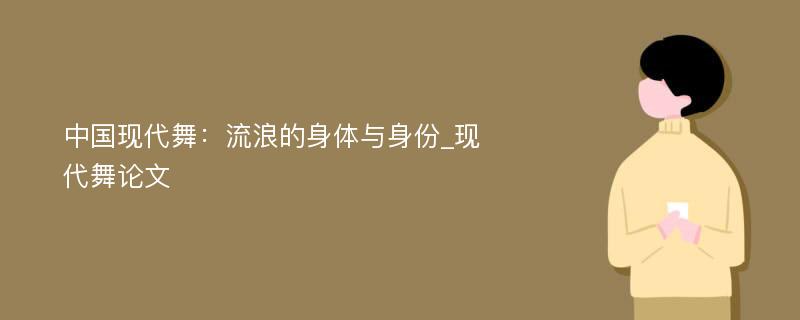
中国现代舞:游移的身体及身份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舞论文,中国论文,身份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7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018(2013)02-0001-05
2010年,中国现代舞突显出蓬勃的发展势头,且这种发展势头并非得益于国内舞蹈行业的重视,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结果。而今的“现代舞”,早已打破了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的“铁幕”和种种意识形态语言,不再只是“西方的”了,现代舞更体现出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而不仅是国籍的差别。全球化时代,世界仿佛被压缩了,无论是“在场”还是“不在场”,地球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混置”于不同的制度、文化、信仰空间,你最能感受到的是当今国际性艺术家的“游移状态”,以及个体的“全球化”;前者是身体的流动游移,后者则是数字化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流动游移与互动。尤其是微媒体、自媒体的发展壮大,令传播方式变革,甚至引发了艺术观念的新变革。
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数字网络,中国内地熟悉现代舞的观众对于海外中国现代舞人的种种艺术探寻也不会完全陌生。对于观众而言,我们可以实现“全球在地化”;而对于国际性的艺术家而言,“四海游移”便是一个惯常的状态了。舞蹈家们游走于全球各地大型国际演出场所,使艺术家们产生了时空表达上的新的舞蹈身体语言,传递着他们对“身份认同”新的身体感知。
艺术的跨界与无界无疑是当代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许多当代艺术家一直关注跨领域合作,艺术家本身也积极尝试使用不同媒介进行创作,而且“跨艺”、“跨界”不仅是艺术同一门类中不同风格的跨越,还存在于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之间,商业艺术与精英艺术之间,甚至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笔者所感兴趣的跨界体现为一种文化,在“跨界艺术”的爆发力、可能性、价值性中,跨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也充满了可能性。艺术家不是为了跨界而跨界,而是他们经过不同层次、类别的深度跨界,为大众启发出了一个超越想象的思想世界,期盼大众以多元角度领会艺术家深刻的内在与跨界艺术的宽广表现。
四海为家的身体状态,“跨艺”或“跨界”的艺术尝试,表导演关系以及观演关系的互动探索……都被投射在作品中,而此类作品也标志出了全球化时代身体经验与感知的差异性。
一、打破“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旧式格局
在西方,现代舞作为精英艺术,虽然小众,但却是舞蹈创作的主流形态;中国现代舞除了也是绝对的小众艺术之外,还处于相对的边缘地位,不过近年变化的趋势日益凸显。
2012年2月29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Modern Dance Comes into Its Own in China”,这篇文章的标题在中国内地有两种翻译:一是“现代舞在中国终获认可”;另一是“现代舞在中国蓬勃发展自己的语言”。由于纽约以及《纽约时报》对于世界现代舞历史及现状具有重要的地位,这篇文章在现代舞业内得到了较多回应。在令人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多的还有一种责任,这是一种积少成多、跬步千里之力。一方面,中国现代舞者近年在国际上获得了较大认同;另一方面,现代舞在中国的现实还是非主流的,所以任重而道远。不过,这篇文章的预测和评估是积极的,它认为中国现代舞在表演机会、资助体系、媒体覆盖率和观众开发等方面,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发展路径。
中国现代舞在国际地位如何?是否应有一个新的定位和自信呢。2005年后,来自中国的现代舞团已经成为了国际艺术节上的常客。尤其是2010年以来,在世界知名的一流剧场、艺术节、舞蹈节上,来自不同渠道的中国现代舞者以舞团或个体的形式集中登场,显露出了一股强劲的现代文化力量,其中包括官方主办的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也有新近成立但已经颇有国际影响力的民营团队——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上海金星舞蹈团、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还有陶身体剧场(北京)、歆舞界(北京)、组合嬲(上海)、二高表演(广州)、谷舞点典舞蹈中心(北京)、凌想舞台(北京)等独立艺术家和未经注册的几十个团队。曹诚渊在自己的博文中,曾赞誉这是中国现代舞的“惊艳天下”。
2011年7月举行的第八届“广东现代舞周”中,22位国际艺术节的艺术总监和节目策划人莅临广州;2012年新一届的“广东现代舞周”,更是为了配合国际艺术策展人寻求节目合作的季节,而推迟到了11月底举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国将有更多独立的现代舞人登上世界舞台。
让世界看见中国现代舞者的“身体表情”,并以我们身体表现能力震动世界舞坛,融入世界艺术大家庭中,是中国舞蹈人的梦想。西方最初开始接受中国的现代艺术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取向,在他们眼里那些现代艺术家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持不同政见者”或叛逆者,是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最好的代言人。而长久以来,中国舞蹈界也有“中国舞”的压力,仿佛进行现代舞的创作,就是西方现代舞了。虽然偶然仍会存在二元对立的政治表情,但如今双方面的态度也正在转变过程中。
其一,国际主流的现代舞展演平台日益显露出对亚洲和中国身体美学的兴趣。
近年来,身体美学日益成为国内外美学研究的理论热点。2002年后,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观传入中国后,中西身体思想之间的学术对话就展开了。舒特斯曼身体美学观的形成也曾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比如荀子名篇《劝学》中对“身”、“体”、“形”、“躯”就有着完整而缜密的阐释;近年甚至有中外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美学不是一种西方式的意识美学,而是一种身体美学。中文中的“身体”,是指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自我的塑造场所,本身就含有身心合一的含义。基于中国古代美学对身体性的自觉,涉足国际的中国现代舞人所展现出的东方人的身体质感,以及东方文化所传递的安静与简单气质,以及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诉求,越来越受到西方舞蹈世界的艺术关注了。
2011年夏季在台北举行的一次舞蹈创作的对话中,英国萨德勒之井舞蹈剧场执行长史帕丁谈到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作品《霾》和陶身体剧场的《2》和《重》,将其与中国少林寺和尚在第62届法国阿维尼翁国际艺术节上表演比利时舞蹈艺术家设计的舞蹈《佛经》以及阿库·汉姆与尼廷·索内——两位分别来自孟加拉和印度的著名英国艺术家创作的《零度复数》并论,来谈论舞蹈创作对个人身份认同的问题。《零度复数》探讨边境、国家、文化、生死临界与真相;《霾》分为三章《灯》、《城》和《岸》,关注生命过程中的未知和无法掌握。《佛经》则是心灵之力和身体之力的互动探索。而《2》和《重》都是陶身体剧场根据东方演员的特别身体质感所创作的。
2011年底,英国萨德勒之井舞蹈剧场执行长史帕丁在公开采访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对国际现代舞生态改变的看法。该剧场还以云门舞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陶身体剧场的世界巡演为焦点,制作了专题片,通过对史帕丁、阿库·汉姆等人的采访,探讨了东方文化在现代舞传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带有东方美学意味的作品,越来越得到西方人的认同,他们甚至表示,东西方其实有比想象更多的共同点。不过,对于挖掘社会学意义的作品,《霾》的接受度就不及其他几个作品。
创办于1982年的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简称BAM)“下一波艺术节”(Next Wave Festival),是全球最重要的艺术节之一。对中国而言,更为有意义的演出便是台湾云门舞集新作《屋漏痕》和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霾》在2011“下一波艺术节”的亮相。笔者尤其关注的是王媛媛的《霾》,这部作品已经在国内国际的舞台上多次亮相,显示出不同于东方美学意义的呈现。
其二,部分中国现代舞团体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并逐渐获得了国际性的艺术话语权。
广义现代舞(包括不同阶段的现代舞)的观念和形态虽源自西方,但其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是一种国际性艺术,代表着一种国际现代文化。现代舞自身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尊重差异,容忍异端。现代舞之“现代性”不再只是“西方的”了,它至少可以代表两重含义:既可以表示西方源发的“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现代性”,即用“国际性”的现代通用语言阐释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也可以代表本土结合传统新生成的“民族的现代性”,即国际知名社会科学家艾森斯塔特所谓的“多元现代性”。
比如在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通常会自主自觉地置于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我们所需要的现代性,既有国际性的现代性,更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舞是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艺术的产物,与西方的现代舞、当代舞处于不同的历史及现实空间。在舞蹈创作上,我们需要汲取时间性的“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独立、反思、人文),却没有必要一味遵循西方的“审美现代性”,模仿和照搬也并不符合现代性精神,要用带有“国际性”特点的民族特有语言表达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下全球化的格局中如何发展进行的思考。显然,东方身体与西方身体所能做的事是很不一样的,好比力量的律动和伸展,动静与内外的铺陈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编导自发、自觉的个人选择,因为现代舞的核心在于每一个个体的独立人格。因此,对于“中国的现代舞有什么特色”的提问最好转换为“中国某位编导创作的现代舞有什么特色”。一方面,他(她)既可以独立选择创作“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舞”,无论是身体语言还是身体美学观念都可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她)的影响。比如王媛媛倾向于在中国文学中寻找灵感,包括脱胎自古典文学的《惊梦-牡丹亭新记》和《金瓶梅》,脱胎自鲁迅作品的《野草》,以及高行健的《山海经传》等。高艳津子的作品也一直尝试触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他(她)也可以独立选择创作立足于人性之本,用东方身体打破或是跨越地域、文化、语言、传统、民族、宗教等格局。比如邢亮认为自己是一个偏技术性的现代舞人,他的《点线面》只是关注人体,而不用情感,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作品中渗透着强烈的思想意识,这些混溶的思想意识源于人类身体认知经验带给他的影响。
再比如近年蜚声国际的陶身体剧场就凭借数字系列的作品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主创兼演员陶冶解释说,“身体”就是一个独特的剧场,希望探讨身体的私人空间与剧场的公共空间交集时,产生的戏剧张力,单纯的一组词句不足以表达出它的复杂性,因此采用了数字的形式作为舞蹈的标题。2012年最新作品是《四》,进一步发展了《Weight x 3》、《2》中对动作技术、身体质感以及舞台关系的思考,延续了极简主义风格。
“身在异乡为异客”是中国现代舞在国际舞台上的旧格局。在旧格局中,中国的现代舞人还不熟悉国际规则,也缺乏一些创作上的自信。西方的艺术节、基金会或媒体则常习惯把中国舞者当成西方编导的“工具”,或是希望表达一些“反体制”的西方政治偏见意图,而没有给予中国舞者身心合一的身体真正的自主选择的尊重。
二、生存空间“国际舞台”与存在空间“文化中国”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舞人的创作就已逐渐分化和发展成两种类型:一是,以大陆为基地的现代舞人,主要依托广东、北京等少数教学专业体系存在,近年来,社会性力量开始凸显;二是,游走在海外的中国现代舞人。
其一,“靠国外的表演才生存得下去”。这是目前官办或民营的现代舞团队共同的、无奈的、真实的话语。国际演出竟然是当前中国现代舞和现代舞人生存的基石。虽然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舞者和小型独立舞团,而且独立的现代舞人已经向二三线城市扩展,还有少数“先锋”的跨界剧团,比如北有纸老虎(北京),南有组合嬲(上海)等,他们集结了国内一些自由艺术家和多种职业的人们一起进行创作,尝试着剧场的综合性、边缘性及更多的可能性。但是谈及职业舞者,陶冶估计“在国内职业做现代舞的不超过100人”,不少人即便曾研修现代舞,却也未必能以现代舞为职业。谈及观众,曹诚渊对记者说“香港有七百多万人口,固定的现代舞观众不超过三千人”,他估计偌大的北京城愿意买票的现代舞观众不会超过这个数目,且北京仍是现代舞生存状态最好的中国城市。由于政府和民间对于现代舞的资助体系尚未建立,也由于观众对现代舞的认知度有限,中国的现代舞依然是边缘艺术,除了内业较有影响力的少数舞团以外,中国的独立艺术尚在缝隙中生长。
由于中国日益开放和文化传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中国的大陆现代舞人也分化成舞台身体语言型,舞蹈剧场跨界型(行为、观念、装置、多媒体等)等,尤其是后者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恰如独立艺术家张献所言:剧场就是行动者的剧场,只要这个人是行动者,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剧场。如今,可以说,中国现代舞人对各种艺术观念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而越来越多元化。
另外,从现代舞生态和社会主办、资助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由于演出方式、渠道、策划方式,资助来源的多样化使今天的中国现代舞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生态。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现代舞观众的人数是逐年增加的。近年,地方政府部门逐渐开始给予现代舞一些政策和资金支持,不仅是官办团体,民营甚至一些未经注册的独立团队也开始获得支持。内地现代舞展演平台也逐渐发展壮大,现代舞人们执着地致力于现代舞的推广和传播。正因为此,现代舞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现代舞的积极推动者——曹诚渊便是“北京舞蹈双周”、“广东现代舞周”的灵魂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过程充满变数,但始于2004年的“广东现代舞周”终于在2012年成功转型,广东省有关政府部门加大了扶持力度,成为了主办方,建立了专项基金。
其二,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忽视旅居海外的中国现代舞人的艺术创作,其中一部分海外中国现代舞人已融入西方主流。无论他们是否加入了外籍,他们依然保留着作为文化背景上的中国身份。海外中国现代舞人由于所处的国际文化背景,因此,每天每时都在接触和思考更加广泛、深入的艺术问题,比如对文化冲突和权力的思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种族、历史的主题与问题,从而使他们的艺术创作具有更大的国际性。
沈伟是来自中国(广东)第一个现代舞实验基地在美国最为成功的舞者。常年在国际上游走的他,早已跻身于世界顶尖编导的行列,算得上是一个“符号”般的人物,被美国媒体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每次新作都会引起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在他的作品里,始终都可以看到他身上不同的文化背景:从湖南到广东,再到美国;也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肢体语言:从中国戏曲到西方放松技术。正因为如此,美国媒体将他与谭盾、盛宗亮、李安等人合称为“第1.5代”移民,赞誉他们“改变了美国文化的体质”。他们所谓的中西结合,只是在使用中国的题材、元素和审美资源,艺术方法完全是西方的、国际性的。跨文化、跨领域、极富创意的肢体语言构成了沈伟独特的审美。沈伟的作品强调完整的创作,要从动作、音乐、布景、服装等全方位观赏,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位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的跨界艺术家。
不过,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现代舞并非主流艺术的当下,沈伟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远不及国际上的赫赫有名,在中国舞蹈界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边是国际的热力追捧,一边却是国内认知度的相对匮乏。虽然在国际上成名十余年,在世界各地剧场空间游刃有余的他也不介意在纽约城市公共空间起舞,但其作品一直与中国内地缘悭一面,在内地偶然亮相,却是在“奥运会开幕式”和某电视台的“跨年晚会”这类本不承载现代舞精神,却人气极高的平台。
全球化时代,沈伟游走于世界各地大型国际演出场所,以及各种室内的、室外的、标准的、异型的表演空间。2012年底,舞团在纽约成立十余年后,他终于首次率团回国正式与中国观众见面,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带来经典作品的中国首演,包括他第一个被全世界认可的作品《天梯》(2000)和最具知名度的《春之祭》(2003)。中国观众终于不再仅限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画卷》篇中的惊鸿一瞥,或是2011年初为家乡父老——湖南台粉丝节尴尬亮相时的水土不服了。沈伟“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局面终于有机会打破了。沈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更多中国人带来启发。毕竟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一切事物都联系在一起,关心表演者并顾及到观赏者才是最触及人心的。
对于不少海外的中国现代舞人而言,自己存在的根基仍然是中国。且近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部分游走海外并获得成功的中国第一、二代现代舞人的回归,他们中有马守则、邢亮、桑吉加、侯莹等。其中,侯莹曾与沈伟舞团有过长达8年的合作。与沈伟的纯国际化和以纽约为大本营的做法不同,侯莹的创作和一系列推广现代舞的工作坊以及ADF中国·河南国际舞蹈大师班等大都与中国内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与侯莹的接触中,她的“剧场理念”和“视野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侯莹看来,当代艺术的未来在中国有很大的前景。这也是我非常佩服侯莹的地方。
2012年,侯莹受第三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之邀,推出了《介2012》。侯莹是一位对自己的身体与思想有着独立判断的艺术家。作为一名现代舞者,她集创作、表演、教育于一身。她不拒绝借鉴,只是她更坚持融会贯通。传统的现代舞体系、沈伟的自然身体运动发展体系以及亚历山大技术等身心学训练体系都给她以充分的滋养,她在吸收的过程中坚持创造,从而让自己的身心更强大。
现代舞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的艺术,无论国内外,现代舞的发展都面临着资金、场地、受众、人才等问题。在中国,现代舞解决了意识形态的框框后,这些方面的问题才刚刚凸显出来。现代舞者需要的,其实仅仅是一片生存的空间和艺术交流的空间。
全球化时代,文化艺术不再是东西方的二元划分,无论现代舞如何千差万别,相同的是人本思想。中国观众需要知道现代舞代表着什么,有理由并有权利选择欣赏什么样的现代舞,但现代舞终究还是小众文化,是需要一定门槛的,“喜闻乐见”并非现代舞的特质。现代舞作品无法竞技,但是现代舞作品却有力量大小的评估。在一定意义上,每一个走进剧场的观众才是作品最终的评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