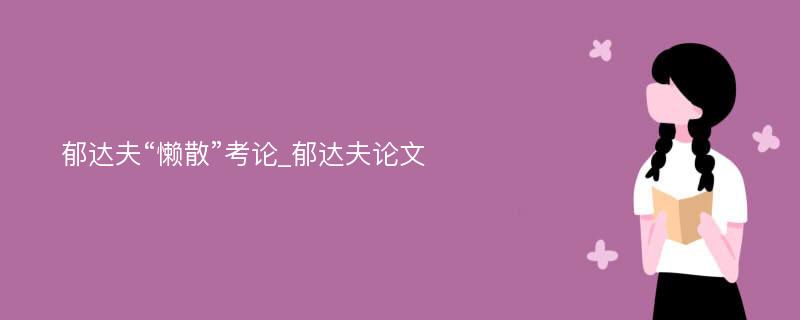
郁达夫“怠工”问题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6)02—0190—05
在创造社同人中,始终如一地保持流浪型知识分子个性气质的,是郁达夫。正是因为这种坚守, 遂使跟随郭沫若南下的郁达夫无法在广州找到安身立命之所。1926年12月27日,郁达夫回到上海,打算专心于文学事业,并负责清理创造社出版部。但是,回沪的郁达夫却在人事关系上陷入了更大的窘境:先是周全平等小伙计们先后离去,与自己一手提携起来的叶灵凤屡次发生冲突,接着因《广州事情》而与成仿吾和郭沫若生了罅隙……本想振作一番,要“努力于新的创造,再来作一次创世纪里的耶和华的工作”[1]65 的郁达夫,蓦然发现自己在创造社内已是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富有诗人气质的郁达夫选择了离开。
1927年8月15日,郁达夫在《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刊登《郁达夫启事》:“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2]。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郁达夫的离去,创造社同人给我们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从个人间微不足道的矛盾纠葛到大的政治取向方面的分歧,无所不有。在诸种说法里,“怠工”这个因素虽然屡屡被提及却从未得到研究者们的足够注意。郑伯奇在《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说:“达夫改组出版部以后,半年间《创造月刊》只编印了一期,但他却参加了新月社的编辑会议,这就更引起大家的怀疑和不满。”[3]38 王独清则认为:“当时创造社在上海的两个中心分子——成仿吾和我——对郁达夫的不满,只是为了他负了社内编辑的重责,却一年来只编了一期月刊,一点工作都没有进行。”[4] 在指斥郁达夫“怠工”方面,郑伯奇与王独清两人的说法在逻辑上存在着惊人的一致,都以为郁达夫的“怠工”激起了创造社其他同人共同的不满,成为郁达夫被“清除”的重要原因。郑、王二人的说法根源何在,可靠性如何,在整个社团的发展方面,向人们启示了些什么?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试图探索创造社这个魅力四射的现代文学社团发展的一些内在制约因素。
刚从广州回到上海,郁达夫就开始了工作。1月8日晚,郁达夫打算着手编辑《创造月刊》第6期。至11日,仅用3天工夫,这期刊物就已编辑成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郁达夫说:“我自己又做了一篇《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等》附在最后,月刊第六期,总算编好。午后二点多钟,才拿到出版部去交出。”[1]57 同时,将已经停刊将近5个月的《洪水》半月刊完全恢复了。1月15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饭后校《洪水》第二十五期稿,已校毕,明日再一校,后日当可出版。……今天一天,应酬忙碌,《洪水》廿六期,仍旧没有编成功,明日总要把它编好。”[1]58 17日的日记写道:“编《洪水》第二十六期;做了一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共有两千多字,编到午后,才编毕。”[1]59 短短半个月时间,郁达夫编好了3期刊物,由此可见其用功之一斑。
在繁忙的刊物编辑工作外,郁达夫还恢复了丛书的正常编辑与出版。《洪水》半月刊第29期、30期都登出“一九二七年春季书目预告”,里面有打算出版的创造社丛书目录:张资平《苔莉》、郭沫若《瓶》、成绍宗《磨房文札》、郁达夫《寒灰集》、张资平《最后的幸福》、穆木天《旅心》和郭沫若《银匣》等。这些书籍1927年3到6月间也全部都出版面世。如果刨去必需的准备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做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工作,到1927年5月12 日《洪水》半月刊第30期出版时为止,创造社出版部5个月已出版6期刊物,每月近两本丛书。一切都像史曋说的那样,出版部“稍加整顿,便恢复原状”[5],迎来了创造社出版部的“中兴”时代,而这些毫无疑问都要归功于郁达夫。郁达夫所做的这些工作与创造社出版部其他任何时期的工作相比,都毫不逊色。
1927年最初5个月的时间,就在创造社事业的发展方面, 郁达夫是创造社同人中最不应被视为“怠工”的一个。我想郁达夫自己对此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是如此的相信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做出的成绩,以致他从来没有对“怠工”的说法给予过驳斥,仿佛他认为那是不值得理会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很难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从广州回到上海,怀抱万丈激情,想要在创造社出版部大干一场的郁达夫,虽然做出了相当的成绩,可是离他的理想相去甚远,在灰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他的目标并没有得到较为圆满的实现。虽然主观上他丝毫没有“怠工”的意思,可事实上他总是力不从心。当年,创造社三鼎足齐聚上海滩,应付创造社三大刊物尚觉困难,以郁达夫一人之力而撑起两份丝毫不亚于《创造》季刊的杂志,其艰辛自然可想而知。随着出版部工作的全面展开,刊物的出版也逐渐显露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创造月刊》第6期标明的出版日期是2月1日,这个日期既与编辑完毕的日期(1月11日)不符,也与印出的日期(2月24日)不符。这一点仅从刊物的编辑与初稿送出日期与刊物上署明的日期两相对照即可明了。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一天,总想把许多回信复出,账目记清,《洪水》二十七期编好,明天好痛痛快快地和映霞畅谈一天。午后将《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送出,我做了一篇《打听诗人的消息》,是怀王以仁的。”[1]87 稿子在27日被送出,印出来最早也应是几天后的事情了。还有,《洪水》半月刊第27期本应在16日出版,刊物印刷日期亦注明是16日,但看郁达夫日记,可知是延期了。在3月12日的日记中,郁达夫说:“回出版部后,又编了一期二十七期的《洪水》,我自家做不出文章来,只译了德国婆塞的诗《春天的离别》。”[1]104 3月12日与2月27日同时记载了编《洪水》半月刊第27期事,实际上第27期编辑时间没有这样长,3月12日乃是误记,所编其实是《洪水》第28期,因为《春天的离别》是登在第28期上的。4月8日的日记记道:“早晨起来,头就昏疼得很,因为《洪水》二十九期的稿子不得不交了,所以做了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三点多钟回家来,又作了一篇批评蒋光慈的小说的文章,共两千多字。今天的一天,总算不白度过去。晚上将《洪水》全部编好了。”[1]126 5月12日的日记记道:“午前将《洪水》第三十期编好”[1]146。按正常情况,第30期应该在4月1日出版。其实,自从第27期之后,《洪水》半月刊的出版就在不断延期。从郁达夫日记可知,已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
其实,创造社出版部里的事务,不只是简单的刊物编辑,还包含校对、印刷与发行等一系列事务;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内部已经发生的矛盾纠葛还等着郁达夫进行处理。与出版部小伙计们的矛盾,其实是最让郁达夫伤心头疼的。从1926年12月27日回到上海到1927年8月15日登报声明离开创造社,郁达夫在出版部前后共计8个月,其中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脱离出版部事务,而在处理出版部事务的时候,又有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刊物或丛书无关的人事关系等团体方面的杂务。除了社团内部的种种烦琐事务,还要应付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使出版部能够平安生存,这又耗去了郁达夫许多精力。自从出版部经历了1926年8月7日被封事件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形势只能以风声鹤唳、如履薄冰来形容。从1927年元月始,国民党当局要查封创造社出版部的消息又时有流传,郁达夫为此很是奔波过一阵,日记中多处记载与此有关,刊物与丛书的编辑发行自然也受到较大的影响。2月24 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说:“《创造》月刊六期,已于昨日印出,然不能发卖,大约这虐杀的恐怖不去掉,我们的产品,总不能卖出去的。”[1]99 至于郁达夫个人,处境亦不妙。《新消息》周刊第3号发表出版部紧要启事:“创造社系纯文艺团体,出版部系营利集股公司,并不带丝毫政治性质,亦并不与任何个人有关,近因各小报记载失实,恐惑众听,特此声明。”[6] 所谓“与任何个人有关”之“任何个人”,既指郁达夫而言,当然也包括在革命军中工作的郭沫若,留在广州的成仿吾等,但是首当其冲的却是在上海的郁达夫。5月上旬,郁达夫离沪去杭。即便如此,还是没有躲过国民党当局注意。5月29日,创造社出版部被搜查,郁达夫在杭州的地址亦被盘诘。为此,郁达夫不得不要创造同人再为他“登报声明已到日本。”[1]155
1927年4月和5月,郑伯奇和王独清先后从广州到上海。5月11日, 郁达夫在写给王映霞的信中说:“我现在有一位朋友来了(王独清),他也是很无聊,但以后他却能帮我弄社里的事务,我可以一心一意的从事于创作了。”[7] 1927年5月16日《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3期出版后, 郁达夫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创造社刊物编印事务。在5月17日的日记中,郁达夫写道:“午后回闸北,觉得人更难堪了, 就把创造社里的事情,全部托付了出去,一个人跑回新华来。”[1]148 正如启事中宣称的那样,事务已全部“托付”王独清。从杭州回来,郁达夫并未将托付出去的事务收回。从5月16日到8月15日,前后共计3个月, 郁达夫没有再编印创造社丛书与刊物。而在郁达夫离开创造社前的三四个月时间里,负出版部具体责任的王独清和郑伯奇,也只编印了《创造月刊》第7期一期刊物。自受托付以来,直到1927 年底,王独清和郑伯奇都呆在上海出版部,中间成仿吾也曾待过一段时间。在长达8 个月的时间里,创造社三大中心人物又做了些什么呢?1期《创造月刊》和6期《洪水》,共7期杂志,而丛书基本没有,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成绩,如果考虑到第7期《创造月刊》和6期《洪水》中的3期都是在郁达夫离开之前编辑出版的话,与郁达夫相比,无疑逊色许多,他们评说郁达夫“怠工”的说法,用于自身却正相宜。
事隔多年后,郑伯奇和王独清却都指责郁达夫“怠工”。责人之疴而不见己之瑕。既不顾及环境因素,又没有与创造社其他阶段的发展相比较,“怠工”之说法难免显得有些臆断,未免失之偏颇。我们所要追问的,恰恰是这种偏颇产生的根源。对当时出版部及郁达夫所处环境的恶劣,其他创造社同人不是不知,但问题是他们恰恰是将这种境况的造成归罪于郁达夫。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中,郁达夫就曾说过:“正由广州带了重大使命去日本的成仿吾氏,却对我说了这几句话:‘这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做了那种文章,致使创造社受了这样的惊慌与损失!那些纸上的空文,有什么用处呢?以后还是不做的好!’”[8] 都是郁达夫文章(即《广州事情》和《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惹的祸,郁达夫自然也就要对此负责。另一方面,虽然与其他同人负责出版部时相比,郁达夫所面临的工作难度及最终出产皆毫不逊色。但是,“怠工”与否,有时并非是统计学上的数字能够说明白的问题。郑、王二人说郁达夫“怠工”,并非没有考虑到创造社发展的历史情况,更不是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无知,而是从他们的那个角度看待郁达夫在创造社出版部里的活动时,必然就会产生出那样的看法。想要弄清“怠工”问题的实质,决不能仅仅着眼于郁达夫的工作实绩情况,而是要探讨“怠工”这个问题提出的原因,从问题的提出者那里寻找症结所在。指责郁达夫“怠工”时,郑、王二人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创造月刊》的编辑,即郁达夫在负责清理出版部期间只出版过一期《创造月刊》。其实,正是对《创造月刊》的态度问题,才是郁达夫背上“怠工”这一罪名的导火索。
据《日记九种》可知,担负回沪清理出版部重任的郁达夫,并没有将恢复《创造月刊》视为当务之急:“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自广州上船,赶回上海,作整理创造社出版部及编辑月刊《洪水》之理事。”这段文字中的“月刊《洪水》”是否为“半月刊《洪水》”的笔误,即漏掉了“半月刊”的“半”字,还是《创造月刊》的省略,即“月刊《洪水》”的真正读法应为“月刊、《洪水》”,分别指《创造月刊》和《洪水》两种刊物。不同的理解意义截然不同。现今普遍被接受的理解中,都认为是“半月刊《洪水》”的笔误,如此一来,事情就变得富有意味。在郁达夫的日记中,清理出版部和编辑《洪水》作为工作目标提出,至于《创造月刊》,似乎已在郁达夫视野之外。那么,能否据此认为郁达夫视《洪水》重于《创造月刊》呢?如果以笔误理解郁达夫的日记,事情仿佛也正是这样,起码写日记时的郁达夫心中没有过多牵挂《创造月刊》。此前,郁达夫似乎一直是以《创造月刊》为重的,共发行5期的《创造月刊》,郁达夫一人就编辑了3期,仅创刊号就有5篇文字; 而自《洪水》创刊至郁达夫回沪恢复出版为止,郁达夫只在第1卷第8期和第2卷第13期分别发表了《小说论及其他》和《牢骚五种》两篇文章,和郁达夫此间于创造社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相比少得可怜,与总创作数量相比更是不成比例。在广州时,郁达夫还为成仿吾、王独清催促《洪水》稿件而不高兴。“仿吾、独清两人,为《洪水》续出,时来逼我的稿子,我因为胆小,有许多牢骚不敢发。可怜我也老了,胆量缩小了。”[1]24 郁达夫的牢骚未必针对《洪水》而来,但那时的《洪水》尚不在郁达夫关注的视野中,或者说没有成为他特别重视的对象,由此可见一斑。回到上海的郁达夫只编印了一期《创造月刊》,而《洪水》半月刊却能在几个月时间里都按期出版。虽然《过去》那样的重头作品还是发表在《创造月刊》第6期,却似乎只是按照惯例行事,将篇幅较大的作品放在重创作的《创造月刊》上而已。至于编辑的重心,无疑已从《创造月刊》逐渐转移到了《洪水》上。这种变化与刊物既成特色有关,亦与郁达夫心境变化相吻合。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和革命文学倾向的萌芽等等,都对郁达夫带来了巨大冲击;对革命现实的幻灭感,更激发起他对理想的革命的憧憬,激进的评论显然要比小说的创作更能契合郁达夫此时此境的心理情感需要,所以,带有《语丝》式的风格,泼辣犀利,针对社会现实富有战斗性的《洪水》,自然更能赢得郁达夫的垂青,偏爱的发生是必然的。但这一偏爱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却远远超出郁达夫的预料。
郁达夫对《洪水》半月刊的偏爱,无形中改变了创造社内刊物原有的格局。《洪水》创刊时,并没有得到创造社中心人物相应的支持。《洪水》半月刊创刊号完全没有创造社元老们的文章,第2期上也只有郭沫若一篇《盲肠炎与资本主义》,还是《洪水》周刊上已经发表过的稿子。《创造月刊》、《洪水》与初期创造社的同人、出版部小伙计之间,潜在地存在着分别对应关系。《创造月刊》第1卷共12期刊物,小伙计们无一篇作品发表。高长虹曾为柯仲平抱打不平:“仲平的诗,在上海期间,只在洪水上发表过几首。创造月刊何以不发表他的诗,我常不能明白。”[9] 柯仲平的情况正是众多小伙计们的真实写照。反过来看,《洪水》半月刊从第13期至第25期,小伙计至少有42篇作品发表,郭沫若4篇,成仿吾、郁达夫、 张资平、穆木天、王独清各1篇,即创造社中心人物共有9篇。在这段时期,他们在《创造月刊》(从1926年3月1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1日第5 期)上的发稿情况是:郭沫若5篇,成仿吾5篇,郁达夫13篇,张资平5篇,穆木天6篇,王独清7篇。“至于‘少谈政治,少论主义,保持创造社的作风,常登老作家的作品’这本是我们的规约,我们自当勉力做去。”[10] 从周全平的这段话中可以知道,不是出版部小伙计不愿意刊登创造社中心人物的作品,关键是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稿件。其实,从文章发表的数量与质量也可清楚地知道,王独清和郑伯奇等广州创造社同人的侧重点皆在《创造月刊》,将《创造月刊》视为创造社机关刊物,发表文章的阵地,《洪水》的地位显然不能与《创造月刊》相比。
刊物间的界线可以移动,刊物的风格亦可有所变化。都是一个阵营中战斗着的同人,皆是出版部发行的刊物,若在一般情况下,社内某些刊物格局的改变,本来无关大局。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下,郁达夫的选择却具有了超出个人偏爱以上的意义。郁达夫继承的是《洪水》以往犀利的批评风格,《语丝》式的批评意味着与社会现实的不和谐,意味着郁达夫选择了一条质疑与挑战之路。他的话语方式不是简单地区分敌我,而是首先追问其合理性,在其现实好与坏的表现中给出自己的价值判断。郁达夫编辑的《洪水》,发表了一些对当时革命现状质疑的文章,这直接使参加革命实践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觉得不安。在后来的文章中,郭沫若甚至因此而将郁达夫划入反革命的阵营当中。奇妙的是,郭、成二人只是在政治层面上批评郁达夫,至于“怠工”,则出现于郑伯奇和王独清的言论中。简单地说,郁达夫偏爱《洪水》,以敏锐的批评意识编辑这份半月刊,得罪的虽然几乎是全部的创造社同人,尤其是时在广州的同人,但是得罪的对象却并非一致,他们反对郁达夫的原因,其实有着细微然而却至关重要的差异。郑、王二人虽也认为郁达夫招惹其他同人反对的原因包含政治因素,但在他们的言说中,提到政治因素时很明显地都是在使用“他者”的话语,也就是说,对于政治方面的分歧,他们其实并不很关注,他们关注的是另一个层面,那也就是“怠工”问题所显示出来的内涵。
《创造月刊》创刊后,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当属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中期创造社三诗人的出场。《创造月刊》创刊号发表了穆木天和王独清著名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与《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两篇文章,可是负编辑责任的郁达夫,显然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仿佛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将其作为同人稿件发表了事,在编辑者言中不但丝毫未曾提及,却还说本期没有好文章,对于向来在编辑者言中自负自夸的创造社同人来说,这显然不是和谐的音符。但是,无论怎样,王独清他们那些富有象征意味的诗歌,都占据了《创造月刊》最初几期的半壁江山。《创造月刊》曾是带有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诗歌的最佳阵地,然而,长达6 个月之久的停刊状态,使正处于朝气蓬勃发展状态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受到某些影响。负编辑责任的郁达夫不努力于此却转而去搞重在批评的《洪水》,对郑、王等同人来说,努力显然是弄错了方向;当回到上海的王独清取代郁达夫成为月刊编者,革命文学的潮流又将富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诗歌创作淹没,《创造月刊》创刊时的大好时机已经一去不返。期待与被期待的偏离,郁达夫也就背上了“怠工”的罪名,起码在郑、王二人的眼中是如此。创造社革命文学转向以后,郑、王二人虽多龃龉,但在当时共同面对郁达夫时,他们的态度大体是一致的。1926年9月创造社广州大会后,王独清成为唯一在创造社所有重要机构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的同人。至于郁达夫,时在北京探亲未归,待他回到广州后,感受到的只有更多的失落。像郑伯奇说的那样,王独清与郁达夫之间或多或少存在明争暗斗,“那时候(指1926年在广州),他(指王独清)在和郁达夫暗斗。处处都要和达夫较量。”[3]50 人事变换为的都是“争夺出版部的控制权”[4],就是王独清提出的观点,这里面多少也包含了他自己的一些心声。王独清虽成为创造社内迅速升起的一颗闪亮新星,但编辑实权却还掌握在郁达夫手中,大革命失败以前,创造社中心人物忙于革命实践,出版部事务已少有人问津,回沪清理出版部实际成为一块鸡肋。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版部的位置成了创造社同人唯一的战斗阵地,地位立刻变得重要起来。当时,从广州、武昌等革命前线回沪的同人中,郑、王二人是最早的两位。既然王独清在广州时就与郁达夫暗斗,来到上海后自然也难免会延续,当时尚为王独清密友的郑伯奇自然会站在王独清一边。从这个方面来说,“怠工”其实是一道裂缝,显示了当时反对郁达夫的创造社其他同人虽然出发点并非一致,却正是他们共同将郁达夫挤出刊物的编辑之列,至于成仿吾和郭沫若,只是在郁达夫离开的过程中添加了政治的色彩而已。明乎这一阶段创造社内部政治与非政治各种取向的复杂并存,理解各取所需而针对的目标又皆指向郁达夫,才能洞晓郁达夫的离开创造社出版部既是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又是各种力量合谋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离开后的创造社仍旧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先是成仿吾的离开,接着是张资平、王独清……一直持续到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查封。其实,自从有了出版部这一营业实体,创造社实际上就已逐渐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名利场,起码与前期创造社相比,这一倾向是愈来愈明显。
[收稿日期]2006—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