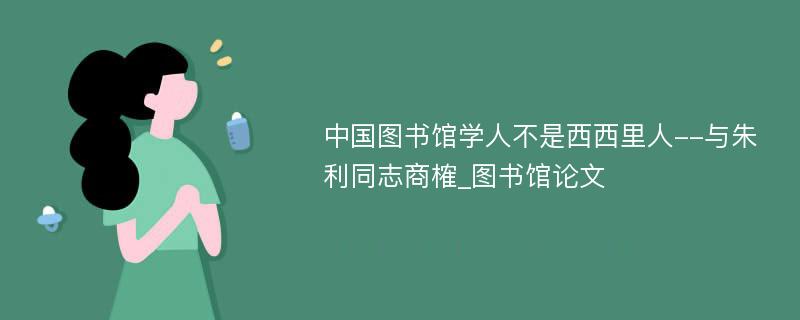
中国图书馆学人不是西西福斯——与祝力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中国论文,福斯论文,图书馆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与情报》杂志1999年第1 期刊登了祝力同志的文章《中国图书馆学的西西福斯巨石》,拜读后有些不同看法,在此提出,与祝力同志商榷。
首先,用西西福斯巨石比喻图书馆学研究是不恰切的。众所周知,西西福斯推巨石周而复始、永劳无逸,是一种被惩罚的现象。西西福斯因罪孽深重而受到宙斯神的重罚,西西福斯绝对无法把巨石推到山顶,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是被宙斯神冥冥之中操纵着的,是一种被控制的徒劳行为,注定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祝力同志用西西福斯现象比喻图书馆学研究,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就象一块无法达顶的巨石,而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则是在无数个没有结果的回合中艰难跋涉的西西福斯”,这种论断无疑是缺乏客观性、科学性的。图书馆学研究起始于十九世纪初,至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从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最初定义“图书馆学”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提出“资源说”,图书馆学象社会科学中任何一门学科一样,随着社会的运动、进步、发展,经历了各种学派、各种体系、各种方法论、各种认识论的发展阶段。也出现了从高峰到低谷,从表象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从恒态到动态,几经曲折、迂回的状态。这些发展变化起承转合、峰回路转,波浪型前进,符合学科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是很正常的。图书馆学经历了一百多年、几代学人的艰辛努力、不懈追求,研究发展生生不息、兴旺蓬勃,说明了图书馆学研究具有深广的研究层面和对图书馆工作实践指导意义的价值。我们不否认从图书馆学初期表象的具体的认知,到深入的整体的认识阶段,再到对其本质规律的认识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憾,如整体研究水平不高、理论与实践出现脱节现象、有美化、虚化的成分等等。但瑕不掩瑜,不乏真知灼见。几代图书馆人的探索与研究功不可没。祝力同志牵强的评判,以偏概全、妄自菲薄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图书馆学研究起始于十九世纪初,从那时起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大都局限在图书馆的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或某几个浅显的要点上,局限到可以感觉到的具体的图书馆工作方面。这个阶段停留在表象的具体的认识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整理说”、“技术说”和“管理说”。“整理说”的观点认为:图书馆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并据此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整理”,主题内容是图书馆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整理说”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乎可以说,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就是图书馆整理,特别是目录学的历史。“技术说”的特点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是从最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能轻而易举的分类、排列并指出架上的图书、小册子,目录里的卡片、剪贴的零星资料和札记,以便及时对这些文献进行标引。”“管理说”则以“管理”为主线去阐明问题,我国早期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中,占主流的是有关图书馆管理的观点。以上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图书馆工作中起了很大的归纳、指导作用,但都未能反映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全貌,只反映了图书馆学的某一部分,或是图书馆学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萌芽,从单方面来说是对的,为全面地反映图书馆的本质、职能、特征、动力、发展规律作了前期准备。在图书馆学发展的初期,首先感知和认识到技术方法、工作和管理等要素是必要的、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从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到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准备。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已具备了全面突破的绝大部分条件。列宁、巴特勒、阮冈纳赞、杜定友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几乎是同时开始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他们认为:图书馆技术固然重要,但作为社会产物的图书馆对社会的反馈——为读者服务——更重要,图书馆正是在与社会大系统发生输入——输出交换的同时,才能形成一个发展的有机体。这些观点形成了该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上升为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提出了“图书馆有书、人、法三个要素”即“要素说”,刘国钧先生继而又提出了“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的“四要素说”,并在1957年发表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再发展为“读者、图书、领导与干部、工作方法、建筑与设备”的“五要素说”。“要素说”是我国图书馆学家对图书馆学研究的贡献,旨在探讨图书馆整体发展规律。整体认识阶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完成了使图书馆学成为科学的使命,它所启动的学科建设工程至今还在组建,这项工程或许还要几代图书馆学人的努力。从表象的具体的认识上升到整体的抽象的认识,图书馆学研究前进了一大步。但该阶段的认识只是在认识的广度和科学性方面进展较大,而在认识深度的挖掘方面,即对图书馆本质规律的认识方面还未能进一步取得突破。祝力同志对‘要素说’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事实上,“要素说”确实是建立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一个经验体系,而不是一个逻辑体系,其概念体系是由实际工作概念所拼成的,而不是由理念概念所构成。因此它缺乏的是逻辑力量,绝不能称之为科学”。根据最简单的逻辑推理:对图书馆这种社会现象,由于它具有自己特有的矛盾性,因而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五十年代就对否定图书馆学成为学科研究对象的理论提出质问:“人们不否认一条蚯蚓、一片树叶以及吃饭睡觉都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为什么要否认客观存在着上千年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的图书馆可以成为科学研究对象呢?”笔者认为刘国钧先生讲的很有道理。
图书馆学研究发展到本质规律的认识阶段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技术论”重又成为本阶段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但此时的“技术论”已非彼时的“技术论”,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技术决定论”。新的“技术决定论”由“交流说”、“矛盾说”和“新技术论”组成。“交流说”在我国的发展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相对封闭的阶段,这种封闭导致了“矛盾说”的出现,这也是我国国情下的我国图书馆学的独有认识。“矛盾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武汉大学教授黄宗忠,他提出了“藏与用”是图书馆学的特殊矛盾的观点。“矛盾说”试图通过图书馆的特殊矛盾来探索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律性认识。我国的“交流说”大致又可分为“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和“文献信息交流说”。“文献交流说”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教授周文骏,他认为:文献“首先是一种情报交流的工具。图书馆利用文献进行工作,所以说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利用文献这个情报交流工具的经验的结晶”。“知识交流说”以宓浩等人编著的《图书馆学原理》为主要代表作,观点是:图书馆是通过对文献的收集、处理、贮存、传递来保证和促进社会知识交流的社会机构。“文献信息交流说”则以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集体编写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为主要代表作,观点是:文献信息交流是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进行文献信息交流和方法的学科。
“新技术说”在九十年代随着“虚拟图书馆”概念和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盛行之势,在英、美及我国的一些图书馆学教育单位,计算机技术类课程的比例已超过了传统图书馆学课程的比例,这也是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一种间接表现。同时,“新技术说”还顺着时间轴的方向将图书馆学引向未来,并开辟了未来图书馆学这一新领域。本质认识阶段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深化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如果说表象认识阶段局限于图书馆的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整体认识阶段局限于图书馆结构及外部联系的展开,那么本质认识阶段则深入到了图书馆内部的文献、知识和文献信息层面,从图书馆——文献——文献信息的认识顺序,正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于这个图书馆本质认识阶段的认识,祝力同志仍是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称:“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说”和“文献交流论”历尽苦难(为什么不说历尽艰辛呢?),终于搭成了《图书馆学原理》、《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和《文献信息引论》的框架,可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三种不同的“学说”由不同起点出发,却搭成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依稀有着传统图书馆学的集大成《图书馆学基础》面貌的框架,尽管言词新颖、却是新瓶陈酒,西西福斯又一次失败了”。笔者认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两个或更多的研究者,分别地几乎是同时地宣布相同的发现,这并不是单纯地相似,而是符合同一时期学科发展需要的一种不谋而合。历史有时就会出现惊人的巧合,就象当年列宁、巴特勒、阮冈纳赞、杜定友等人几乎同时开始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推动了图书馆学认识阶段的进步一样。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认识问题,追根寻源,汇总到一个出发点上来,是一个很正常的学术研究现象。祝力同志的评判是一种笼统、简单的否定,缺乏客观、细致的辨析。
一九九二年九月,国家科委为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决定将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随后一些院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系科也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或其它类似名称。学科更名现象本不是图书馆学科的独有现象,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边缘学科、相关学科、分支学科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里,学科更名已不鲜见。祝力同志对图书馆学更名现象认为是“无论这一切出于多少种理由,都掩饰不住其中的无奈。它无疑在向人们展示,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正在动摇。”实际上,更名并未影响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发展,回顾一下:在全国有多少图书馆更名为“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图书馆虽较早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牌子仍在原位。国家图书馆还是原名。上海图书馆虽与上海科技情报所合并,但新馆大楼上仍挂有“上海图书馆”的牌子。从图书馆学科命名到图书馆改情报信息中心,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关键在实,而不在其名。长期喋喋不休、津津乐道、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在这上面作文章,无休止地争论这些东西,实在有些劳心费神、大可不必。
收稿日期:1999—05—25
责任编辑注:祝力同志的文章《中国图书馆学的西西福斯巨石》复印刊登在本专题1999年7期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