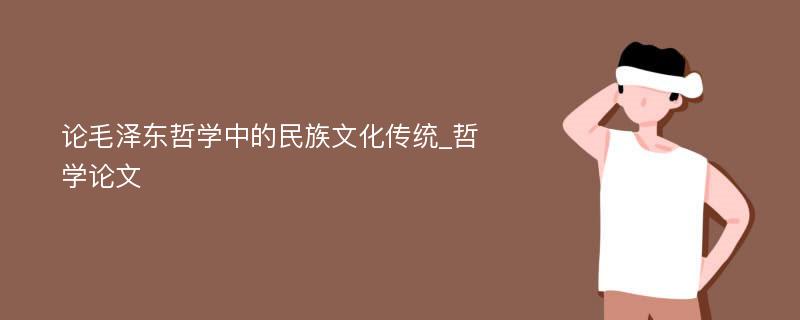
论毛泽东哲学中的民族文化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4-0039-06 民族哲学只有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并通过提炼文化传统的精华,才能为其自立于世界哲学之林奠基,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找到自我认同的根基。这一点,对于曾经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毛泽东哲学,同样如此。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完成,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为标志的。还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探索。如同在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既反对一概拒绝的排外主义,又反对盲目搬用的崇洋主义,而强调“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1083,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1]1083一样,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看到“中国古老的、不易改变的思想方式是中国进步的障碍,但他并不主张用‘全盘西化’来作为一种补救方法”[2],而是既反对一概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盲目推崇的历史复古主义,强调“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1]1083,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统一。因此,必须既批判“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3]707,又“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707。毛泽东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吸取传统文化精华的强调,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而非抛弃的科学态度,又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价值。 然而,由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儒家学说有过某些偏激言论和否定结论,一些人据此断言毛泽东全盘反对传统,其哲学谈不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从晚年毛泽东将中国文化传统,划分为“封建主义”与“民主”两类,并视正统儒家为前一类,视墨家、法家、儒学异端为后一类看,表明了他所认同的传统文化具体内容、文化价值取向的改变,即由正统的儒家思想转向了非正统的思想。这种改变,虽然与毛泽东在现实政治中的需要相吻合,并不表明他放弃了传统文化,更不表明他是“全盘反传统”的,不过是他试图“以新的立场观点去重释传统,重构传统”[4]而已。因此,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哲学与传统儒家学说之间,因属于两种意识形态而似无共同点,然而,“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5],却是不争的事实。通观毛泽东哲学,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是之学”、伦理化认识论的“知行之辩”、“大同社会”的价值理想、“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民本主义的“仁政”观念,都曾对毛泽东哲学产生过影响;毛泽东哲学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吸取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命题、范畴、义理,使其哲学无论在致思趋向①、基本精神②,还是在理论内容③、表达形式④上,都充分体现出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联系,从而鲜明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这里的“民族文化传统”,指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想。而毛泽东哲学的致思趋向、理论内容乃至表达方式,无不体现出上述民族文化传统。 一、毛泽东哲学中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重要动力。它要求面对外辱、强权,在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存亡的关头,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的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从岳飞、文天祥在金戈铁马危难时刻的视死如归,到苏武、顾炎武在长期压抑中矢志忠于家国故土,再到近代西方列强破开国门之际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每到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头,总有无数中华儿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浴血奋战、舍生忘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使肝脑涂地,也不辱国恩,不负民愿。这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至上原则的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求存图强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至于近代中国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潮,其实质仍然是被西方列强野蛮侵略所激活的传统爱国主义。只是这种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情结的爱国主义,其“主流是弱小民族追求解放的民族自救”[6]13。 传统爱国主义在毛泽东哲学中,不仅体现为其哲学的价值指向,解答“中国向何处去”、民族怎样独立、人民如何获得解放,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还体现在对传统哲学经世致用“求实之学”的新解,对传统伦理化认识论“知行之辩”的改造上。这种“新解”,是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中,运用中国传统术语“实事求是”,去概括和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求真务实学风,改造为本体论与方法论、自然观与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相统一的哲学理论,在充分体现传统哲学的实践理性特质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强烈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这种“改造”,是毛泽东的认识论,在扎根于传统哲学知行观土壤的同时,既批判了程朱理学“重知轻行”唯心论,又扬弃了颜李学派⑤“重行轻知”经验论,将辩证法引入知行关系,在知与行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揭示其辩证关系,得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7],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关键和根本原则的结论。“新解”和“改造”,既为中国人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的社会、民众、历史、传统,如何将这种认识付诸行动,提供了理论引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对传统哲学文化的致思趋向、基本精神、理论方式的传承,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毛泽东哲学在理论内涵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血脉渊源关系。由此,毛泽东哲学从认识论、方法论的层面,传承和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 二、毛泽东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表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礼记·礼运》)。从孔子的“均无贫”政治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理念(《论语·季氏将伐颛臾》),到陶渊明田园诗似的“世外桃源”……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又富有崇高道德的社会,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梦想。这种理想主义到了近代,则表现为中国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愿景。实现这一具有浓郁而古朴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需要坚定信念。因此,这种理想主义,通过提倡为“道义”献身的精神体现出来: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的“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到张载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都是对这种理想主义的呼唤。这种理想主义,通过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体现出来:从屈原的“上下求索”而“九死未悔”(屈原《离骚》),到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从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到孙中山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越挫越奋,再接再厉”……中华民族崇敬勇往直前的猛士,蔑视萎靡不振的懦夫,颂扬居安思危的担当,鄙弃行尸走肉的恶行。成则再接再厉,挫则卧薪尝胆。追求理想、壮怀激烈,既是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的具体诠释。到了近代,康有为依据进化论写了《大同书》,将理想社会定位于未来而非远古,则无疑是对传统文化中,以天命观为理论基础的复古理想主义的反叛,是理想主义的近代表达。至于近代中国以“冲决罗网”(谭嗣同)、“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彻底革命”⑥为核心的激进主义思潮,以及以“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热衷“积极自由”、向往平等为宗旨的自由主义思潮,则都可以视为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这种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情结的理想主义,虽然也具有准宗教性的对世界整体的关注情怀,但更多出于改变国家命运、民族民生的现实需要。 传统理想主义在毛泽东哲学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相联系,从价值哲学的层面,表达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憧憬和豪情。财产公有、男女平等、幼有所养、老有所依,这一被誉为具有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价值目标,既是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企盼,也是伴随毛泽东一生的理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哲学,则通过既高扬共产主义的理想价值,强调“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3]686,宣告“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1]1059,又深刻理解中国百姓内心深处对“大同社会”的憧憬向往,并通过比较中国传统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指出两者具有体现“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苦、丰衣足食”社会愿望的共性[8]。于是,从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同社会”观念的巧妙结合,通过二种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共产主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通过“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革命实践和“一大二公”的建设实践⑦,毛泽东哲学从价值观层面,传承和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理想主义传统。 三、毛泽东哲学中的道德主义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的“存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张载的“大其心”以“烛万象之理、体天下之物”(张载《正蒙·大心》)、儒家的“修齐治平”等以道为己任的传统文化,将锤炼陶冶主体道德人格,视为认识与和实践的根本前提,它在对主体道德人格的高扬中所彰显的传统哲学伦理本位主义。这种道德主义,还通过强调和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的形式体现出来。它要求当个人、局部的利益与整体、全局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以后者为重。而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将“利”归属于个体感性欲望,“义”指向于整体理性精神,强调“义”重于“利”,“利”从属于“义”,要求将“义”作为规范主体的道德行为、维护整体利益的标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便是这种义利观的明确表达。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体,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在抹杀个性自由、人权,从而具有明显历史局限性的同时,又因提倡个人为了民族大义应当不惜牺牲自我,而对发展社会共同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于近代中国以大同团结、戮力同心、为国民谋幸福等为行为准则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其无论以民族主义,还是以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为底蕴的思想,都不过是国家民族民众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的一种变形,是民族文化传统中道德主义的体现。只是这种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道德主义,更为强调关注整体利益应当胜于关注个性人格和个体价值。 传统道德主义在毛泽东哲学中,表现为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伦理观,被改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的“大一统”价值取向,被改造为“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传统文化“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的弘道传统和“苟利社稷,生死已以之”(《左传·绍公四年》)的爱国情怀,被改造为“五爱”和“尊重社会公德”的道德规范;传统文化“贵人、尽性、无类”的教育观念[9],被改造为“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的道德教育理念;传统文化“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推己及人等自我道德修养,以及“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观,被改造为提高自觉能动性、改造主观世界、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提高个人的道德境界,做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的道德实践。这样,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理论有效融合,通过系统阐释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实践等理论,毛泽东哲学从伦理学层面,传承和体现了民族文化的道德主义传统。 四、毛泽东哲学中的民本主义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通过强调与民同乐、以民为本体现出来。这种民本正义,强调“国”非抽象符号,而是百姓组构的实体;“国”不仅是君子的“家天下”,更是民众生存的家园,因此,“爱民”即是“爱国”,“爱国”体现在“爱民”上。这种“民本”思想,奉劝当权者不要沉溺于一己利益追求,而应以天下万民利益为重,因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从老子“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认知(《老子》第四十九章),到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仁政”,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求诉,到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告诫,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屈原《离骚》),到黄宗羲“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感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传统文化中重民心向背、顺民意施政、问民生苦乐的理论,既是有良知知识分子恒久的精神追求,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的充分体现。至于近代中国以平等博爱与个性解放相结合⑧,将“互助友爱上升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6]39;在批判封建道德观念的同时,将个性主义与博爱主义相结合⑨等自由主义思潮,不过是在继承传统人本主义文化遗产的同时,又为它赋予了近代西方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所结出的思想果实,因而此时的这种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人本主义,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对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及其道德观,更多地具有了否定性色彩。 在毛泽东哲学中,群众史观、人民主权思想是其民本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但他的这一思想,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主义有着天然联系。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政治家,毛泽东认同几千年民众抗争社会不公之史;作为一个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家,毛泽东深知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之理;作为一个志在人民解放事业的实践者,毛泽东熟知将人民利益置于何处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哲学家,毛泽东深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道。于是,传统文化为民、惠民的民本意识在毛泽东哲学中,体现为要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党的理论宗旨和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传统文化的乐民、忧民的民心思想在毛泽东哲学中,体现为要以“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作为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的基点;传统哲学爱民、亲民的平民观念在毛泽东哲学中,体现为“一刻也不脱离群众”[1]1094、“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10]1128的责任意识,体现为警惕“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10]1438的滋长,强调共产党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3]522等反官僚主义的执政意识;传统文化重民、贵民的治国理念在毛泽东哲学中,体现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031的历史主体观,体现为将人民群众视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建设主体、一切政治权威的终极源泉等价值理念和实践主张;传统文化的仁民、信民的策略方法在毛泽东哲学中,体现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信任人民”、“依靠人民”、爱护人民、尊重人民,以及要善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71等一整套群众路线的理论。由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人民主权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结合,通过全面论述共产党的理论宗旨、路线策略、执政理念、主体动力、群众路线等理论,毛泽东哲学在政治哲学层面,从历史观、方法论、认识论等维度,传承和阐释了民族文化的民本主义传统。 五、简单的结论 上述毛泽东哲学中显示的民族文化传统,只是其诸多内容的有限方面。事实上,在毛泽东哲学中,通过吸取中国哲学的“实事观”⑩,而在本体论上对传统唯物论的传承;通过吸取中国哲学的“知行观”(11),在认识论上对传统认识论思想的传承;通过吸取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一分为二”、“相反相成”,在方法论上对传统辩证法的传承;通过吸取中国文化的“荣辱观”(12),在历史观上对古代朴素唯物史观因素的传承,可谓比比皆是。鉴于学界既有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成果着墨甚多,在此不再赘述。 尽管如此,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由于政治环境、时代局限、传统影响、主体认知等原因,毛泽东哲学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存在着诸多缺憾和不足。例如,以“实事求是”所传承“经世致用”文化传统,因过于强调实用性,使其爱国主义的民族文化传统,隐含着强烈的功利化色彩;以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现实运动所传承的“大同社会”文化传统,因对主观意志和主体能动性的过于强调和夸大,使其理想主义的民族文化传统,渗透着农民社会主义的空想意识;以“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传承的“知行合一”文化传统,因过于强调以共产主义道德人格的塑造(13)代替实践之“行”,使其道德哲学中体现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消知归行”片面性(14),同时,又因为以是否投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作为实践的唯一内容,使其道德哲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贬低知识文化价值的极端性(15);以人民主权思想传承的“民本思想”文化传统,因其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混淆了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官僚主义,而使其政治哲学中体现的民族精神,有着崇尚“大民主”式民众集体造反形式和走向“反资产阶级法权”等偏激性,同时,又因其对现代人民主权理论与传统民本思想之间界限理解上的含混,使其在“惠民、护民”中突出的民众民主和致力于培养“清官”的政治实践,难免存在德治、人治的影响和危险。 我们不应隐讳毛泽东哲学中传承的民族文化传统,存在的缺憾与不足。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和承认,毛泽东哲学对中国哲学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却是其主流。更重要的是,这种传承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即提炼百姓丰富生活经验,用中国百姓所了解、熟知、喜欢的典故、成语、俗语、俚语等语言方式,阐释和表达了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将中国哲学文化的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贯通、结合,将深奥的哲理转换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为民众能够乐于接受的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毛泽东哲学中“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所在。 收稿日期:2015-04-20 注释: ①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自然本体论的思辨,没有多少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性抽象,思域专注于“经邦纬国、济世安民”的政治伦理哲学。毛泽东哲学延续了这一哲学传统,只是其哲学思考的对象,由传统的政治伦理哲学转变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 ②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单纯的本体论,而是奉行本体论与方法论对接的“体用合一”原则。毛泽东哲学延续了这一基本精神,强调并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③中国传统哲学不热衷逻辑抽象思辨,注重实践理性,主张主体的“躬行践履”。毛泽东哲学延续了这一类似经验论的理论方式,将实事求是、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视为最为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内容。 ④中国传统哲学善于借助生动、形象、比喻、寓意等形式,用语录、格言等言简意赅的方式,在表达对人生、社会的体验中阐释哲理。毛泽东哲学直接传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风格,其随处可见的历史典故、成语、谚语、俚语,不仅使玄妙深奥的哲理变得通俗易懂,而且让百姓喜闻乐见。 ⑤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创立。 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 ⑦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人民公社”到“大寨模式”,毛泽东推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举措,无不显露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色彩。 ⑧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到邹容、孙中山等,莫不如此。 ⑨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 ⑩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疾虚妄”、范缜的“神不灭”批判,张载的“气一元论”等等,都体现出这种“实事观”。 (11)《尚书·说命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程颐、朱熹、陆九渊的“知先行后”,以及后人的“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之争、“知行合一”论等等,都说明了此。 (12)以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最具代表性。 (13)为了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道德观,必须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4)这在晚年毛泽东思想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 (15)这一点,从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文化批判运动,如文艺界的批《武训传》,批胡适、胡风、丁陈集团,哲学界的批“合二为一”运动中,皆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