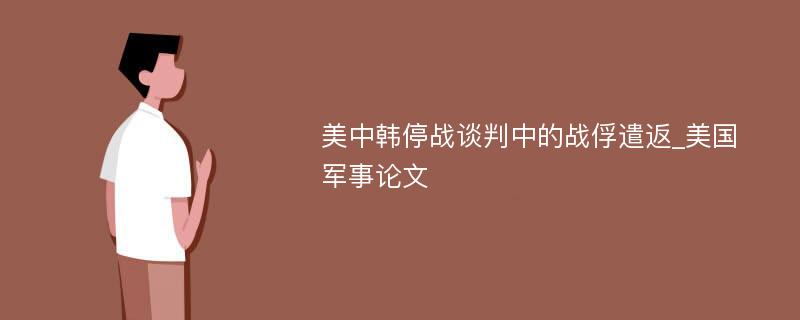
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战俘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3,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5)01-0062-13 战俘遣返问题是朝鲜停战谈判中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朝中方面根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主张停战后双方全部战俘应立即予以遣返。但是,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无理地提出了所谓“一对一遣返”和“自愿遣返”的要求,企图强行扣留朝中战俘,致使停战谈判屡屡陷入僵局,濒于破裂。国外主要是美英史学界对此研究较多,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①但是,西方学者的著述大都是基于美方或西方材料,对中朝方面有关该问题政策的发展变化论述不详,甚至出现了不少谬误。比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1953年5月中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之所以做出让步乃是美国的核威胁使然。还有俄罗斯学者称,是中国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政策,为的是不断地从苏联获取武器援助,担心一旦战争很快结束这种援助就会减少或终止。②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已展开,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特别是对中美双方政策变化的互动还缺乏细致、系统的梳理。③ 1951年12月11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开始就战俘遣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有朝鲜籍战俘11.2万人,中国籍战俘2.08万人;而中朝方面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双方数字相差较大的部分原因是中朝在战争期间释放了部分战俘。中国领导人曾估计,因有日内瓦公约,在这一问题上不难达成协议,主张有多少交换多少。甚至在此问题谈判已经进行一个半月后,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仍乐观地表示,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斯大林也表示,“你们在交换战俘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这是敌人很难反对的”。④事实证明,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态度非常强硬,谈判几度濒临破裂的边缘。 早在1951年7月,美国陆军部心理作战处处长罗伯特·麦克卢尔就首先明确提出了是否将中朝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认为这些中朝战俘一旦被遣返回去,很可能受到“严厉惩罚”或“遭到监禁”,全部遣返将对未来的美国心理战行动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他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把那些主动投诚的士兵送到台湾去,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做并不违反日内瓦公约。⑤这一建议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成,理由是这些战俘回去之后“极有可能被判刑或去服苦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些战俘不应被强迫遣返”。军方强调,美国应保证那些投降士兵的安全和庇护,这对未来美国的心理战是非常有利的,今后美国的心理战也可以通过采取这一行动得到加强。同时军方也承认,此举可能会为以后的战争确立一个不完全遣返的先例,并为共产党方面提供进行政治宣传的借口,共产党方面很可能会以此为理由,在停战协议签署后破坏和平谈判,并重开战火。⑥ 实际上,国务卿艾奇逊最初也倾向于应严格依照国际公约行事,立即遣返所有战俘,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强调,在停战谈判转入战俘遣返问题后,首要考虑的应是如何立即遣返被中朝所收押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战俘,担心军方所提建议会妨碍这些战俘的全部遣返。⑦国防部长洛维特、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等也倾向于接受中国的全部遣返方案,认为中朝不可能同意达成对等交换协议。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的斯泰勒、负责公众舆论事务的官员巴雷特以及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克森等人都反对自愿遣返的主张。他们批评说,这样做不仅违反了日内瓦协议,使美国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一旦谈判破裂或延长几个月,将导致另外数千人的伤亡。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应更多地考虑美国战俘的生命安全,美国的公众舆论不会支持“自愿遣返”的政策。⑧ 但是,美国最高决策者的态度却非常强硬。1951年10月底,杜鲁门总统在与副国务卿韦布谈话时强调,全部遣返战俘是“不公正的”,他不希望将那些与美军“合作”的战俘送回去,不会同意任何以全部遣返为基础的交换方案,除非美国可以从对方获得以其他方式不可能获得的一些重大让步。⑨鉴于此,艾奇逊、洛维特等人也开始转变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态度。1952年1月中旬,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召开联席会议。陆军部、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大都倾向于坚持战俘的“自愿遣返”,即使这可能导致谈判中断,“让步”将会严重削弱心理战的整个基础。艾奇逊在2月8日致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任何强迫遣返战俘的协定“都将严重危及美国旨在反对共产党的心理战作用的发挥”,并且是与美国最基本的“道义”和“人道”原则相悖的。⑩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坦承,美国的“自愿遣返”原则既不是出于人道和正义,也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国民党和南朝鲜军队,而是让人了解“共产党士兵一落到我们手里就可以逃亡”,这对共产党“是有威胁作用的”。实际上,美国政府之所以不顾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拒绝遣返全部战俘,并不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完全是出于冷战的需要,认为朝鲜战争只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场“前哨战”,如果把战俘都送回“铁幕”去,将来发生大战时便无人投降。(11)同时,在战俘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内反对派对政府的指责。的确,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杜鲁门还担心战争很快结束会影响美国重整军备的计划。(12)战俘已经成为美国冷战政策和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952年2月4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通过了题为《关于自愿遣返朝鲜境内战俘的最后立场》的备忘录,称“为了对抗共产主义极权世界,美国在道义和心理战上的立场要求我们不接受任何需要美国强制向共产党人遣返战俘的行动。这些战俘强烈反对这种形式的遣返,而且他们一旦返回,很可能会遭到报复”。备忘录同时提出,在实施这一政策时,应尽可能地减少“联合国军”战俘的危险,并最大限度地获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28日,这一备忘录获得杜鲁门、艾奇逊、洛维特等人的赞成,确定“自愿遣返”为美国的“最终立场”。(13)4月28日,美方提出所谓“一揽子方案”,继续坚持“自愿遣返”原则,提出遣返朝中7万战俘,并称其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能改变的”,要求中朝方面全盘接受。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方的这一提案“完全是有意拖延并企图破裂谈判,完全不是谈判的态度,而是施行威胁”。(14) 美国的盟国对“自愿遣返”政策表示不满。加拿大政府建议遣返所有的中国战俘,而将北朝鲜战俘留下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表示,如果是在继续进行战争与“武力遣返”之间做出选择,他将“毫不犹豫”选择后者。(15)英国政府认为是美国在拖延谈判,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使英国被俘人员早日获释。1952年1月29日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使用国民党对中国战俘进行“灌输”以使他们加入国民党军队,致使谈判一再陷入僵局。备忘录强调,英国不想为了加强国民党军队而让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战俘遭受更多的痛苦,只希望使其尽快得到遣返。(16)负责朝鲜事务的英国外交部官员阿迪斯表示,由于美国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政策多变,并在对方做出让步后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就使得朝中方面确信,美国人并不想真的谋求达成停火。在他看来,战俘问题不应该成为签署停战协定的障碍,美国的政策太情绪化。阿迪斯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为了尽早达成协议,应对一些中国战俘实施强制遣返,这令美国方面大为不满。美国国务院照会英方,强调自愿遣返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则问题”。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提醒外交部,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美国最高决策者态度非常坚决。鉴于美国态度强硬,艾登致函艾奇逊称,“在我看来,使用武力遣返那些战俘是与西方自由世界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尽管如此,双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依然矛盾重重。(17) 杜鲁门对于谈判进展缓慢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他认为在战俘问题上美国必须“立场坚定”,公开称美国不准备在它的“基本道义”与“人道原则”问题上做出妥协,“强迫遣返战俘是不可想象的”,“将使美国与联合国蒙受耻辱”。(18)在他看来,中朝之所以同意停战谈判,旨在为进一步发动进攻争取机会和时间,应该给苏联下一个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所有中国军队应撤离朝鲜,苏联应停止向中国供应任何军需物资,否则,美国就将采取一切措施摧毁中国东北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封锁从朝鲜半岛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海岸,如有必要将不惜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到那时,莫斯科、圣彼得堡、海参崴、斯大林格勒、奥德萨、北京、上海、沈阳、旅顺、大连等中国与苏联的所有工厂都将被夷为平地,这是苏联政府决定它是否愿意生存的唯一机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是想结束在朝鲜的冲突还是准备让中国和西伯利亚被毁掉?他们必须两者选择其一,非此即彼;苏联或者结束在朝鲜的冲突,接受美国的停火协议,“或者被彻底摧毁”。(19)为了打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和谈判桌上的僵持局面,迫使中朝方面接受美国的停战方案,美国远东空军从1952年5月至7月出动大批飞机对朝鲜北部的水电站、机场、铁路、公路、桥梁以及包括平壤在内的主要城市等目标展开大规模的轰炸,并中断谈判。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公开宣称,打破谈判僵局的最好办法就是“从空中把他们撕碎”,“狠狠地打击他们”。国防部长洛维特、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以及“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等认为,轰炸战略可以大大削弱中朝方面进行战争的能力,并给其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20) 但是,恐吓改变不了战场的局势。此时,战局对美国来说越来越不利。中朝兵力已近百万,且构筑了坚固、纵深的坑道工事。在美国国内,由于总统大选在即,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急于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以利民主党竞选获胜。7月25日,艾奇逊致电美国驻苏大使凯南,指示他与苏联方面秘密接洽,通过苏联来软化中朝立场,推动停战谈判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打破板门店的僵局。艾奇逊说,这类接触从性质上来讲,既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刺激,旨在促使苏联对中朝施加影响。他建议,如有可能争取见到斯大林,会谈时应“避免给人以我方过分热情或软弱的印象”,要让苏联知道,美国政府的谈判立场正在向灵活方面转变。艾奇逊强调,会谈应当使美国的“自愿遣返”原则得到苏方的充分理解,并询问“苏联是否愿意利用其对中朝的影响,采取积极措施解决战俘问题,以便尽快签署停战协议”,同时要转告苏方,朝鲜不停战,“便没有希望实际解决困扰着我们两国政府的世界上的其他问题”。(21) 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无理态度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只有坚持坚定立场才能逼对方转弯,让战争拖下去,对中朝方面确实不利,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对方则有内外不可克服的困难,最后总要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怕拖,也不怕战,但也不宣告破裂。毛泽东电告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应“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22)基于美方的谈判态度,中国领导人估计,战争可能要长期拖延下去,决定对谈判“作拖过今年的准备,并决心坚守已经巩固起来的现时朝鲜前线阵地,加修第二条坚固工事,准备应付夏秋两季可能到来的敌人新的攻势”。(23)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对战争形势做了认真分析后得出结论,停战协议在短期内很难达成。由于美国在军事上、政治上困难很多,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力量较前有了很大增强,美方长期中断谈判或进行大打的可能性也很小,朝鲜战场将是拖的局面;在拖的过程中,不断的战术性的小打和个别的战术性的局部攻势都可能出现。总之,朝鲜战争可能长期下去,暂时还不能结束。(24) 1952年5月底,中国领导人将对战局的估计及对策致电斯大林,指出最近一个多月来,可能“由于我们在中立国问题上让步太快使敌人误以为我们在遣俘问题上仍可做更多让步,加上敌人在其国内外的不利形势下需要继续制造紧张局势,故从4月下旬起,敌人态度转坏,谈判形成僵局”。关于战俘遣返,电报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要求对方遣返朝中战俘10万人左右,而决不能是7万人,朝中方面准备遣返现时所有的1.2万名战俘。二是将战俘遣返问题留待停战协议签字以后再行解决,以接触对方目前的任何借口,但这种方案是否合适“尚在考虑中”。中国领导人表示,应继续坚持原则,准备克服任何方面的困难,“以逼使敌人放弃其无理主张”。否则,如果在所谓“自愿遣返”实际是“强迫扣留”的问题上让步,不仅在停战中开一恶例,而且在全世界和平运动中发生不良影响。他们估计,美方如在6月中尚不欲达成协议,则7月以后忙于国内选举,有可能将谈判拖延过11月大选再进行解决。为了在朝鲜进行充分的准备,中方“迫切需要”苏联政府继续提供炮兵和空军装备、弹药及器材。(25) 7月初,美方代表在停战谈判会议上首先表示愿意“诚意地觅求停战,以终止朝鲜流血”,承认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在合理的程度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中国领导人随后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指出“对方的发言明显是在转弯”,“这是两个月来新的变化”,“估计敌人由于其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可能想从协商中与我们求得一个在遣俘问题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停战”,要求对其现有态度应表示欢迎,并“应明快而主动地表明我方态度”。(26)7月3日和6日,中朝方面提出建议:“双方所俘获的外国武装人员即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应全部遣返回家;双方所俘获的朝鲜武装人员即南朝鲜军或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其家在原属于一方地区者应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收容一方地区者,可以许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据此,中朝方面收容对方战俘12000余人,准备全部予以遣返;对方称有中朝战俘11.6万人,至少应遣返9万人左右,“这个数目虽然还不是全部遣返,但已经是绝大部分遣返”,“我们准备与其达成协议,而将其余两万多人保留到停战后继续解决”。(27)朝中方面在战俘问题上已经让步,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争取“绝大部分”遣返。但是,这一建议遭到美方拒绝。7月13日,美方提出一个新方案,将遣返人数由7万人增加到8.3万人,其中朝鲜人民军7.66万人,占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志愿军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并称这是最后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朝中谈判代表团倾向于接受美方的新方案。主持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数字比我们估计高,离我们9万上下的底盘不远”,对方答应遣返的人民军大体上好的分子皆已回来,不回来的可能大部分是那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新参军的人,至于志愿军方面国民党特务是做了长期的工作的,这是对方扣留的重点。朝鲜方面也赞成接受美方提案,认为美方这一方案较前有了“很大进步”,即使继续争论,估计对方也不会增加数字,因而“提议不放弃敌方此次让步之机会”,以便尽快实现停战。(28) 接到美方新方案第二天,毛泽东便否决了朝中代表团的意见,并指出“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谈判不在数字之争,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情况下的停战。据此,周恩来起草了以毛泽东名义致金日成和李克农的电报,认为在目前接受对方这一“挑拨性引诱性的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并在对方狂轰乱炸之后接受,“显然对我极为不利”。电报认为,不接受美方提案的害处只有一条,那就是朝鲜人民和志愿军继续遭受损失,但战争既已打响,中国既已援朝,朝鲜人民已站在保卫世界和平阵营的前线,其牺牲的代价已换来三八线附近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使朝中人民尤其是武装力量得到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战的锻炼,并愈战愈强,使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得到了反对侵略战争的鼓舞并推动了世界的和平运动,使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世界和平堡垒苏联加强建设并影响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切伟大的成绩的造就,使朝鲜人民再不是孤立的了。电报说,中国愿尽一切可能保证解决朝鲜人民的困难,“并请您不再客气地提出朝鲜急需解决的一切问题”,如果超过中国力之所及,当与朝方一起请求斯大林予以帮助。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接受美方提案的害处甚多,朝中将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敌人必将利用我方这一弱点,继续采取攻势,并启其扩大挑衅之念”。届时朝中已处被动,即令转取攻势,损失反会更大,就连上面所说的各种好处,也会同受影响,“这就是一着错满盘输的道理”。电报最后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继续拖延,我坚决不退,敌人仍有让步可能;“如不让或破裂,我应决心与敌人战下去,从敌人不得解决的战争中再转变目前的形势”。(29) 同日,毛泽东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电告斯大林,指出美方宣布的遣返人民军和志愿军战俘的数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毛泽东认为,绝不应接受对方“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毛泽东表示,“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得到了斯大林的赞成和支持。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30)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朝中谈判代表拒绝了美方提出的8.3万人的遣返数字,指出这个数字与最初的11.6万人的数字相差甚远。在克拉克看来,此举表明共产党方面对达成停战协定缺乏诚意,因而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他在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电报中称,“目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避免一切让共产党人认为我们立场削弱的行动,避免让共产党人认为实现朝鲜停战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行动”。他建议,美国有必要在战场上立场坚定,不断空袭北朝鲜军事目标,在板门店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31)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表示赞成,指示他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不要向对方提出任何新的提议,并且除了一星期一次会议之外,不要多开会议,如有必要就单方面休会,同时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空中力量,打击北朝鲜的所有军事目标,加大对中朝的军事压力。 1952年8月中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与苏联领导人就朝鲜战争和国际局势交换了看法。关于谈判方案,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同意美方的方案,这是立场问题。他提出了谈判的三个步骤:中朝方被俘人员以11.6万人计算,如果美方扣留30%,中朝方同样可以扣留战俘13%,促使对方改变态度;第二步可先实行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双方战俘遣返问题;第三步是可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交由中立国代管,然后由当事国进行征询,并陆续接回。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表示,“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他强调,朝中方面应继续坚持全面交换战俘,对美国必须强硬。(32) 在对北朝鲜进行狂轰乱炸的同时,美国的谈判立场变得更为强硬。尽管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建议应基于日内瓦公约首先实现停火,抓住一切机会交换战俘,尔后再处理那些未被遣返的战俘,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认为,美国必须坚持战俘的“自愿遣返”原则,决不能让步,必要时应宣布单方面无限期休会。军方的考虑是,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双管齐下,通过不断增加军事和政治压力,以促使朝中方面“接受我们目前的观点,或提出一个与我们非强制性遣返立场相一致的方案”,任何其他做法只能被人视为“示弱”,并因此而失去目前通过增加军事压力而获得的优势。(33)杜鲁门也致函新任“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指示“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的提案应“措辞强硬”,“不留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对方不接受,就宣布无限期休会,最重要的是“不能减少军事压力”。(34)根据华盛顿的指示,美方代表团于9月28日提出三项任择其一的建议,仍将战俘分为愿意遣返和“拒绝遣返”两类,主张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一是将所有战俘带至非军事区交换地点,由战俘选择何去何从,如战俘声称愿回曾拘留他的一方,应立即准许,并给以平民身份;二是迅速交换愿意遣返的战俘,将反对遣返的战俘分批送至非军事区,由中立国征询战俘的去向;三是迅速交换愿遣返的战俘,将反对遣返的战俘分批送至非军事区,不加征询或甄别,任其自由前往所选择的一方。美方再次声称这一方案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更改的”。(35)很显然,美方建议的实质仍然是坚持“自愿遣返”原则,朝中方面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周恩来电告谈判代表团,要揭露美方提案的目的是企图以形式上的若干微小的变动来掩盖其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的实质,以欺骗世界舆论,并借此逃避其拖延谈判的责任。电报强调,“根据多次经验,我们如在此时稍一松口,敌人又会发生错觉,气焰嚣张,转使谈判再陷停顿”。因而,“我们必须首先揭露敌人提案的欺骗性,予以坚决拒绝,然后再提出可以诱使敌人走下一步的我方对案”。(36) 10月8日,中朝方面就战俘遣返问题提出新的建议,主张在停战后将战俘一律送至非军事区交由对方接管,然后对战俘进行问询,按国家、地区进行分类和遣返。但美方对此并不理会,并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致使停战谈判中断了达半年多之久。29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苏联方案”,建议交战双方在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立即完全停火,即双方停止一切陆上、海上及空中的军事行动,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则交给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北朝鲜和南朝鲜组成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这一提案是经过中、苏、朝三国政府密切磋商而制定的。中国方面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苏联的提议,认为这是立即结束朝鲜战争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合理途径。(37)但是,该提案于11月29日遭到联大政治委员会的拒绝。 11月17日,朝鲜停战谈判出现了新的转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印度外长梅农向联合国提交了印度政府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梅农方案”,建议为使交战双方的战俘问题得以迅速解决,应该成立一个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等4国代表组成的战俘遣返委员会,或由战争双方各指定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外、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由4国组成停战协定草案所规定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具体负责战俘的遣返问题。“梅农方案”得到了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大力支持,认为这是一个打破战俘问题僵局的好办法。英国国防大臣劳埃德向艾奇逊表示,英国政府感到,如有可能,通过印度倡议是非常可取的。艾登也告诉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说,他本人及英国大多数公众都感到印度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38)在随后召开的美、英、法、加四国外长会议上,艾登进一步强调,印度的提案“绝大部分符合西方国家的看法,而且能够在联合国大会赢得广泛的支持”。(39) 美国对印度的提案表示反对,理由是它没有明确提到“自愿遣返”原则。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告诉梅农,美国不愿陷入在停战后还不得不谈判战俘遣返的局势之中。(40)艾奇逊则把“梅农方案”斥之为一个“危险的想法”,竭力迫使印度修改其方案,并向英国施加压力,促其与美国保持一致。他向杜鲁门报告说,“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与梅农打交道”,而是与英国、加拿大等国打交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在他看来,印度的提案意味着“那些同意回国的战俘将被遣返,而那些不同意回国的战俘将被一直关押,直至他们同意被遣返为止”,这是美国绝不可能同意的。他威胁说,倘若西欧在战俘问题上不能同美国保持一致,那将会严重危及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他甚至称,如果英国支持印度,“北约将不复存在,英美友谊将不复存在”。(41)但是,英国政府并不放弃,认为印度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亚洲影响很大,西方的强硬态度只会把其推向苏联一边,并造成英联邦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在艾登看来,美国政府此时似乎是害怕达成协议。(42)迫于美国的压力,印度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修改意见。在实质上,印度的方案就变成了美国的提案。 正当西方国家对“梅农方案”展开争论之时,苏联方面却以明确的态度表示,这一方案是“略为改头换面的美国计划,它是违反禁止甄别、禁止扣留战俘的日内瓦战俘公约的”。11月24日,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严厉抨击了“梅农方案”,同时也提出了苏联的建议:立即完全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将战俘遣返问题交由美、英、法、中、苏等国组成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来处理。中朝方面也随即表示,拒绝接受印度的方案。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声明这个决议案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是以美国一贯坚持的“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为核心内容的,是“非法的”、“无效的”,要求取消这一决议,立即责成美国恢复板门店谈判,并根据苏联提案达成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43)当印度驻华大使询问中方是否愿意考虑印度提案的一项休整草案时,毛泽东指示“不宜再和印度谈此事,除非印度从联合国撤回原提案,方有资格再谈此事”。(44)由于1952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处于内外交困的杜鲁门不可能采取什么大的举措来结束战争,战俘遣返问题依然处于僵局之中。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若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中朝方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因而,尽管中国领导人希望能打破谈判桌上的僵局,及早结束战争,但还是决定让现状拖下去,直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45) 1953年初,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在停战前先行交换病伤战俘。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在政治上、宣传上取得有利地位,决定率先行动。2月底,“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奉命致函朝中方面,主动提出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中国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有意恢复板门店谈判而发出的试探信号。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美方是否有诚意恢复谈判持怀疑态度,分析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此时战场形势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利,如果再打几个月,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上有所松动。实际上,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立场恰与斯大林的看法相吻合。2月28日,斯大林在与苏联其他领导人讨论朝鲜形势时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和朝鲜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仍应“争到底”。(46) 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11日,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进行会谈。苏共新的领导层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决议,并致函毛泽东和金日成,阐述了苏联政府对停战谈判和战俘遣返问题的看法,强调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苏联新的领导层要求中国、朝鲜不仅要对美方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呼吁做出肯定的回答,使这一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定和缔结和约的障碍。(47) 3月1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克拉克要求双方先交换伤病战俘的问题“我方尚未回答”,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乔冠华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毛泽东认为,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他要求周恩来就此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21日,周恩来再次与苏联领导人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磋商,并将商谈情况电告毛泽东:“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首先由金日成、彭德怀出面答复克拉克的提议,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病伤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分别发表声明,表明对交换病伤战俘的积极态度,指出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已经到来,建议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采取必要行动,以支持和推动上述方针政策的实施。毛泽东在复电中对此表示赞成,并说这一方案实际上是1952年9月上旬向斯大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后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蛮横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48)他同时电告彭德怀,指出美方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其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我方准备同意此事”,但此事要等周恩来回国后商议对策,故“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面透露”。(49) 3月26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与苏联领导人讨论朝鲜停战问题的情况,就此拟定了中国方面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次日,毛泽东致电朝鲜方面,指出现拟以金日成、彭德怀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再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50)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克拉克,表示同意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并提出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以使朝鲜停战得以早日实现。30日,周恩来就朝鲜停战谈判发表声明,指出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有关战俘遣返的原则,也不是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而采取的新的步骤,以保证战俘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而不致因此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他表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美方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话,“我方这个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51)对于中国方面的这一新方针,周恩来在4月3日的政务院会议上做出这样的解释:停战谈判进行快两年了,美方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政策,凡是对其有利的就谈,不利的就拖;而我们在全部谈判中一贯坚持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因为美方蛮横无理地坚持其“自愿遣返”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能与其妥协。当他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决地顶回去。我们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是也不能老僵持着,因此在时间上让了一步,分成两个步骤来实现。我们提出的这个遣返方案,与美国方案和印度方案不同,我们这个方案是将战俘交中立国。在这种情况下,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52) 周恩来的这一新建议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获得了世界舆论的普遍支持和赞赏,认为它打破了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僵局,为朝鲜停战消除了最后的障碍,显示了中朝谋求和平的诚意。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都发表讲话,表示支持中朝在战俘问题上的“崇高举动”,支持“关于恢复谈判,以达成交换病伤战俘和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协议,并从而解决朝鲜停战和缔结停战协定问题的建议”。(53)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讲话称,周恩来的声明“提供了一个可以据以有益地恢复停战谈判的基础”。外交大臣艾登致函杜勒斯,敦促美国抓住机会,奉行灵活的谈判政策,而不应仅仅限于商讨病伤战俘交换事宜。(54)联合国大会也通过决议,希望病伤战俘的交换迅速完成,并希望在板门店的进一步谈判能导致早日实现朝鲜停战。3月31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彭德怀,同意朝中方面的建议,提出双方派联络官在板门店举行会议,商讨交换病伤战俘和恢复谈判事宜。4月6日,双方联络小组恢复接触。到11日,签订了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20日,双方正式开始移交伤病战俘。朝中方面至4月26日停战谈判复会时遣返完毕,共有684名美方病伤战俘遣返。美方至5月3日遣返完毕,遣返朝中方面病伤被俘人员6670人。 对于中国提出的遣返战俘的新建议,美方心存疑虑,要求中方进一步做出阐述。4月9日,周恩来在以南日名义致美方代表的信中就此做了如下说明:停战后双方战俘应予全部遣返,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鉴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朝中方面的建议对于遣返战俘的步骤、时间和方法,做了明显的让步,主张将战俘的遣返分两个步骤来进行,即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公正解决;朝中方面的让步绝不是放弃了战俘全部遣返的原则,坚持拘留方应保证不得对所收容的所有的战俘采用任何强制手段来阻挠他们回家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应保证将未直接遣返的战俘释放出来转交中立国,使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主张将一部分因遭受恐吓和压迫而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朝中方面被俘人员转交中立国,经过解释使他们逐步解除疑惧,从而在遣返问题上得到公正解决。(55) 为了更好地进行谈判,争取取得成功,周恩来主持拟定了“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该方案实际上包含第一、第二两套方案。朝鲜方面对此表示完全同意。4月24日,毛泽东将两套方案电告乔冠华,要求其“邀请朝中双方负责同志加以研究”。这两套方案实际上围绕着三个问题:未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交给中立国,是送到中立国去,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接收和看管;这批战俘在中立国管理下的时间上有无限制;这批战俘经过有关方面解释后,仍未解决的如何安排。对这三个问题的第一方案是: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几个亚洲的中立国去(如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有关中立国当局即指定地区加以收容和看管,在规定的时间内(譬如半年或者三个月),朝中方面派人前往解释,使战俘由于心存疑惧而不敢回家的顾虑得以解除,然后由有关中立国当局负责将其遣返;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第二方案与第一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转移到经双方协议的南朝鲜的一个岛上,交给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4个中立国委员会接收和看管。其余与第一方案完全相同。毛泽东认为,第二方案较第一方案简便易行,且易为中立国所接受,同时与美方所提办法在某些方面也大体相同。他指示,为了在谈判桌上有进退余地,在谈判恢复后,先提出第一方案,以取得谈判主动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估计对方接受这个方案的可能性较小;如对方坚持不肯将战俘送到中立国去,而要求中立国到朝鲜接收和看管,在弄清对方全部意图后,可准备以第二方案与之妥协。(56)4月26日,中断半年之久的板门店停战谈判正式恢复。 停战谈判恢复后,双方在解决战俘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朝中方面提出如下6点具体方案:(1)在停战生效后两个月内,应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遣返,不得阻挠,送交给战俘所属一方;(2)直接遣返的战俘遣返完成之后的一个月内,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送到一个由双方协商决定的中立国家去,由该中立国当局指定地点加以接收和看管;(3)在6个月的期限内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前往中立国对战俘进行解释,消除他们的顾虑;(4)经解释后,凡是要求遣返的一切战俘应由中立国协助遣返;(5)6个月期满后仍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交由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6)战俘在中立国家的一切费用,应由战俘所属国家负担。周恩来指示李克农,为推动谈判的开展,引导对方进入具体协商,在发言稿中应强调,中朝方面所提6点方案已经考虑了对方的建议,如规定战俘在中立国接收、释放的期限及最后处理办法,双方在谈判中对于对方的建议应该仔细考虑,并寻求妥协,而不应该抹杀一切、完全否定,这对于以协商精神促成朝鲜停战是不利的。但美方认为6点方案是不能接受的,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出朝鲜境外,主张将其送至非军事区内由中立国接管,同时提出6个月的解释时间太长,要求缩短至2个月,并建议瑞士为临时接收、管理非直接遣返战俘的中立国。关于战俘的最后处理,主张在解释期满后交由政治会议处理,30天后仍未遣返的战俘应予释放或交由联合国大会处理。(57)经过10多天的交涉,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5月7日,为使战俘遣返问题顺利解决,中朝方面再次做出妥协,提出了第二方案,建议成立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留在原地,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安排,并由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进行4个月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经过解释后,凡是要求遣返的战俘,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应负责协助他们迅速返回祖国;解释期满后仍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应交政治会议协商解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此之前曾通过印度驻华使馆参赞将朝中方面的第二方案通报印度政府,并指出,朝中方面提出新方案后,仍保留原来的方案;如果美方对新方案态度恶劣,“我方仍然回到老方案上”。中国领导人认为,在提出新方案的同时仍保留第一套方案,“使我们更处于主动,以利与对方进行谈判斗争”。15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时再次强调,这一方案是“我们在战俘问题上最大限度的让步”,不仅包括了印度原提案的基本内容,而且也采纳了联合国决议的合理部分。(58) 朝中这一方案的提出使双方的立场更为接近,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声明,主张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谈判基础,并赞成召开大国最高会议讨论和平问题。缅甸政府也发表声明赞成以朝中建议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就连艾森豪威尔也承认,中朝方的建议构成了“可以接受的停火协议的谈判基础”。但是,由于南朝鲜方面坚决反对将朝鲜籍战俘交由其他国家看管,美国政府遂又改变政策,提出了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就地释放”的反建议,并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看管和协助遣返战俘的工作,以及战俘所属国向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进行的解释工作,提出了种种限制。朝中方面对美方立场的倒退进行了严厉谴责,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美国在战俘问题上的出尔反尔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西欧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艾森豪威尔并不能控制美国政府,他本人越来越屈从于来自共和党极端分子的压力。因而,他们决定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议会讲话时公开批评了美国在谈判中的消极立场,认为是美国在蓄意拖延停战协议的达成。他呼吁立即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尽快解决朝鲜问题。6月初,他致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表示愿意与苏联合作,缓和紧张的世界局势,并认为如果朝鲜战俘问题能够很好地得到解决,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加拿大政府对美国政策的多变感到不满。皮尔逊总理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僵硬立场,认为中朝5月7日的方案已经在战俘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美国没有理由再拖延谈判。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意大利、印度等也对美国谈判政策的倒退表示“忧虑和担心”。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艾伦于5月19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西欧盟国普遍对美国“不妥协”的谈判政策表示不满,并对美国未与其磋商就贸然做出重大决定的做法表示严重关注。他建议政府在谈判中尽可能采取灵活的态度,而不是使和谈归于破裂。美国心理战委员会也明确提出,在西欧盟国中,公众对美国谈判立场的支持正“令人遗憾地下降”,因为在他们看来,一种“反共歇斯底里”情绪在主导着美国的政策。副国务卿史密斯警告艾森豪威尔,朝鲜停战谈判正处于危机之中,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日益恶化”,支持美国战俘遣返立场的人越来越少。(59)艾森豪威尔也承认,此时的美英关系降到了战后的最低点。(60) 5月25日,美国方面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规定所有非遣返者,都应移交给中立国委员会接管;印度在该委员会中担任主席;在经过120天的解释后仍未遣返者或是释放为平民,或由联合国召开政治会议来解决。实际上,美方的这一方案与中朝的方案已基本接近。美国政府指示谈判代表团向中朝方申明,美国的这一立场是“最后的”,并建议休会一星期,以便使对方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这一建议,倘若遭到拒绝,则终止谈判。(61)美国还敦促苏联向中朝施加影响,促使中朝方接受美国方案。国务院指示驻苏大使波伦,要他转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最近提出的谈判建议是美方的最后立场,具有“极大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美国已为弥合双方之间的分歧“尽了最大努力,走到了极限”,倘若未能在这一“最后谈判条件”上达成一致,那将会导致“美国想极力避免的局势的产生”。国务院还提醒波伦,在向莫洛托夫重申美国的立场时,切不要给人以最后通牒之嫌。(62) 中国领导人对美方的新建议予以高度重视。5月27日、6月5日和7日,周恩来几次接见印度驻华大使,阐明了中国对美方5月25日新方案的意见,认为这一方案“和方5月7日方案的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增加。5月30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讨论了朝鲜谈判问题。会后,他致电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对方的新方案,只在各项条文中作若干必要的和技术上修改”。(63)同时,他将朝中方面准备提出的“关于遣返问题的协议草案”电告李克农。6月8日,谈判双方均做出适当让步,终于就拖延近一年半的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消除了朝鲜停战的最后一个障碍。美方接受了中朝方面提出的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予以直接遣返,不直接遣返的将交由中立国委员会接管的新方案。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全部议程都达成协议。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该协议“使朝鲜停战接近实现,从而打开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这个协议的签订,无疑地是目前国际形势中头等重要的事件”。(64)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结论:第一,谈判双方之所以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争执不下,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而非军事上的考虑。美国最高决策者从冷战对抗需要出发,置国际公约于不顾,试图强行扣留朝中战俘,将其作为推行冷战政策的工具,这些战俘自然也就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较量的牺牲品。正因为如此,自1951年底以后,战俘遣返问题成为朝鲜停战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最大也是唯一的一个障碍。换言之,如果美国也遵照相关的国际公约行事,则战争很有可能会在1952年上半年就结束了。因而,战争拖延的责任完全在于美国。第二,战俘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曾多次宣称,是由于美国的核威胁迫使朝中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签署停战协定。一些西方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事实表明,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1953年3月底和5月初,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朝中方面在战俘问题上两次主动做出较大让步,都发生在美国发出所谓的核威胁之前。即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酝酿扩大战争之时,为配合谈判,朝中军队几次发起较大规模的攻势,给美国决策者以很大压力,并促使美方缓和其强硬立场。通过谈判,美方放弃了“一对一遣返”等无理要求,中朝方面也不再坚持“全部遣返”。第三,在谈判过程中,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其谈判政策都受到了各自盟国的影响。由于英国等国家的反对,使得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不能一意孤行。应当说,在促使美国尽快达成停战协议、结束冲突方面,美国的盟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就中国而言,1953年3月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政策的转变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速了中国的谈判步伐。第四,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是,一旦交战双方在战场上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则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谋求问题的解决。同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再一次表明,实力是谈判的基础。 注释: ①相关著述请参见Rosemary Foot,A Substitute for Victory: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at the Korean Armistice Talk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Pingchao Zhu,American and Chinese at the Korean War Cease-fire Negotiations,Lewiston:Edwin Mellon Press,2001; Elizabeth Stanley,Paths to Peace:Domestic Coalition Shifts,War Termination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②Robert D.Schulzinger,A Companion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Malden:Blackwell,2003,p.285;A·沃洛霍娃:《朝鲜停战谈判(1951-1953年):据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12期,第36页。 ③中文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程来仪:《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朝鲜战争战俘之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贺明:《见证: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王玉强:《周恩来与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徐友珍:《英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宋晓芹:《试析朝鲜战俘遣返谈判中的苏联因素》,《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周琇环:《韩战期间志愿遣返原则之议定》,台北《国史馆馆刊》2010年第24期。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0-251页;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144页。 ⑤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1,Vol.7,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600; Walter Herms,Truce Tent and Fighting Front,Washington,D.C.:US Arm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1966,p.136. ⑥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1,Vol.7,pp.492-493 ; James Schnabel and Robert Watson,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51-1953,Washington,D.C.:Office of Joint History,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1998,pp.60-61. ⑦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1,Vol.7,pp.857-859. ⑧Charles S.Young,"POWs :The Hidden Reason for Forgetting Kore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3,No.2,2010,p.329. ⑨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1,Vol.7,p.1073. ⑩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p.44-45. (11)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下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559、589页。 (12)William Stueck,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162. (13)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p.67-68.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1页。 (15)Callum Macdonald,Korea:The War Before Vietnam,London:MacMillan,1986,p.145. (16)Michael Dockrill and John Young,eds.,British Foreign Policy,1945-1956,London:MacMillan,1989,p.135; Macdonald,Korea,p.144. (17)Cotton and Neary,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107. (18)Foot,A Substitute for Victory,p.108;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549-550页。 (19)Robert Ferrell,Off the Record: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Truma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0,p.251. (20)Matthew Moten,ed.,Between War and Peace:.How America Ends Its Wars,New York:Free Press,2011,pp.243-249. (21)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p.423-426.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548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2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 (25)《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57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91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9页。 (28)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474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89-290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9-250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279-280页。 (31)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p.427-429. (32)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 (33)Stanley,Paths to Peace,p.161; Schnabel and Watson,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51-1953,pp.176-177. (34)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55; Herms,Truce Tent and Fighting Front,p.280. (35)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p.546-547.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610页;张民、张秀娟:《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5-486页。 (3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014-1016页。 (38)Roger Bullen,"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ian Armistice Resolution on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No.1,1984,p.30. (39)James Cotton and Ian Neary,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110. (40)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p.630-632. (41)Burton Kaufman,The Korean War,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p.298;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298-299. (42)Victor Kaufman,Confronting Communism:U.S.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1,p.59. (4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第1012、1014-1016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15页。 (45)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255-256页。 (46)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下册,张慕良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37页。 (47)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第1295-1297页;Kathryn Weathersby,"New Russian Documents on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Winter 1995-1996,p.80. (4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1-182页;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8-119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66-6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48-149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91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314-317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92-293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295页。 (5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第1117-1120页。 (54)Kaufman,The Korean War,p.307. (5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第386-387页。 (5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第387-388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589-590页。 (5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第38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97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92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298、299页。 (59)Foot,A Substitute for Victory,pp.171-172; Denis Stairs,The Diplomacy of Constraint:Canada,the Korean War,and the United State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4,pp.276-277. (60)Kaufman,The Korean War,p.316. (61)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p.1082-1086. (62)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5,pp.1103-1100.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04页。 (64)《打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