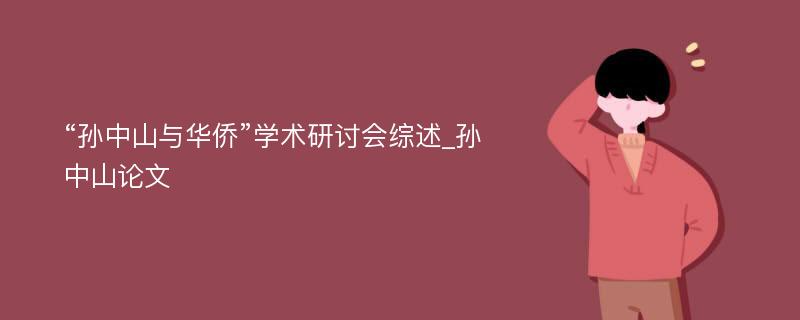
“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外华人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上海中山学社主办的“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5月20-23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北京、广东、福建、上海、台湾,以及新加坡、美国的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围绕着:孙中山与海外华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在经济、政治、教科文方面的发展;全球华人如何迎接亚太世纪的来临等三大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把讨论与争鸣的问题与热点综述于下:
一、孙中山与海外华侨的联系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海外度过。宣传、发动华侨始终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昌福教授的《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一文分析了致公党前身--海外洪门致公堂以及致公党的前期历史,认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不仅改造了海外洪门会党,把它纳入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教育了整整一代华侨,而且为中国致公党在海外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准备。
有的学者认为,陈文为孙中山与华侨的研究提供了新内容,也为孙中山与会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但是要使文章更有说服力和理论深度,作者除了还要进一步发掘史料外(如用可靠的资料有说服力地证明孙中山“天下为公”与致公堂“致力为公”之间的渊源关系),在理论上至少还有两个问题有待深入:一是海外洪门与国内洪门究竟有何异同,是不是由于这种同与不同,孙中山对海外洪门的教育才起了作用;二是孙中山在争取海外会党的同时,保皇党也并没有放松对海外会党的争取,革命派与保皇派,对海外洪门以及致公党的变化究竟有什么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对孙中山争取、利用会党不能简单地看待。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致函孙中山,谈及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孙中山对此答复为,“革命是革命,会党是会党”。这里反映出孙中山对会党的态度和真实思想,是很值得人们回味的。
针对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引发了对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讨论。美国学者戴鸿超认为,辛亥之前,海外华侨在政治上较为保守,还说不上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如何发动、促使他们参加革命,需要有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就是孙中山的世界观。他把孙中山的世界观归结为民族主义(后来为世界主义所代替)、实业计划和道德观。他认为,孙中山如果只是停留在前两者,停留在主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不去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观,他就不会受到海内外华人如此普遍和持久的尊敬。另一位美国学者郑竹园则把孙中山世界观概括为“开明的民族主义,进步的国际主义,理想的大同主义”。他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孙中山思想的基本精神都没有过时。林金枝教授在《辛亥革命、南洋华侨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中充分肯定了孙中山思想在海外的广泛影响。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其革命思想,鼓舞和推动了东南亚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使得东南亚人民在20世纪初的民族独立斗争更加发展起来。
针对众多学者在会议发言及讨论中大多着眼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唐振常教授提出了应该加强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的观点。他认为,历史造就了孙中山这样的杰出人物,这同中华文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联。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领悟,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与儒家文化有区别,搞清中华文化的内涵可以从研究孙中山思想开始。这种把研究孙中山文化思想置于阐明中华文化内涵的高度来理解的观点,令不少与会者有耳目一新之感。
新加坡曾是孙中山海外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柯木林向大会报告了孙中山在新加坡重要革命场所--晚晴园的情况。他在报告中披露的一些重要史实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海外华侨人数众多,东南亚占有相当比重。马克烈的《南洋华人植根于当地社会的历史基础》一文,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几次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他认为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华人聚居的国家,华人作为一个民族将长期存在,并融合在一个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社会框架之中。
孙中山与海外华侨的联系不限于政治活动中,在经济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杨立强、戴鞍钢先生的《孙中山与华侨国内投资》一文,论述了孙中山鼓励华侨投资国内经济建设的主张,赞扬了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为宣传他的经济主张、倡导其建设方案的努力和贡献。他们强调,孙中山“合华侨之财之智以发祖国利源”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沈祖炜研究员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一般都认为孙中山经济思想一贯是强调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而杨、戴认为孙中山对吸引海外大私人资本回国投资持积极态度,这与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的基本思想似乎在学理上有说不通之处。对此质问,论文作者认为,对孙中山的“资本”思想可以从现实和长远两个角度来理解。从现实的角度看,孙中山确实曾主张吸收海外华侨私人资本回国投资,因为这有利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从长远的历史趋势看,孙中山的基本思想还是“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
二、“海外华人”、“华人经济”及“华人经济圈”
在全球重视经济发展的今天,海外华人及海外华人经济自然成为这次会议讨论和争鸣的又一热点。何谓海外华人?过去西方学者往往把大陆以外的华人都包括在海外华人这一概念之中。会上,一些学者也沿用了这种观念,并且把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在内的经济数据作为衡量海外华人经济实力及发展的依据。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港澳台所处地区与其他华人所在国不同,它们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居住在港澳台的华人,不能视之为海外华人。新加坡学者崔贵强更以新加坡为例,提出即使同为海外华人,也不能将其视为没有区别的一个整体。各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教育程度,决定了海外华人也是由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所构成的。
何谓华人经济?储玉坤研究员认为,华人经济是在中国大陆同港澳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大量引进海外华人的资金和技术而形成的一种经济组合。它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而“海外华人经济”,则应该与“海外华人”这一概念相联系。李明欢认为,“海外华人经济”应指那些业已移居中国本土之外,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们所从事的经济事业。杨小佛研究员则更明确地提出华人经济应区分为:台湾经济、港澳经济、大陆经济以及海外华人经济。
在海外华人经济中,东南亚华人经济无疑占有重要地位。丁日初教授的《东南亚华人财团的发展与成功浅说》一文,论述若干入了居住国籍的华人家族,凭借血缘关系,团结协作,积极发展企业,使它们成长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他们同当地的政界权势人物关系密切,甚至合资合营企业,使企业的发展得到可靠的保证。
会上,不少学者还剖析了海外华人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李明欢提出,二战后,不同国家的华人经济由于它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独特发展过程,从而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郑竹园指出,东南亚华人经济多为资源开发,故其发展迅速,在当地经济中有相当实力;而欧美华人经济多经营餐饮业等。其经济实力在本地经济中就显得弱小。
对于华人经济的整体实力,与会者较普遍地认为,一方面,华人经济,特别是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经济确有相当实力,但在过去的研究以及不少报刊文章上,对于这种华人经济的实力以及它们在居住国整体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估计过高,这不仅不符实际情况,而且还会给海外华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至于海外华人经济与居住国整体经济的关系,与会者的看法则较为一致,认为从历史发展看,海外华人经济已越来越融合于居住国当地经济,并且日益成为所在国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华人经济”讨论的延伸,与会者还对郑竹园提出的“大中华经济圈”或“大中华共同市场”展开十分热烈的争鸣。有学者以为,如能建立一个包容中国大陆、港台、海外华人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圈”,对中华民族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这种提法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有些过于理想化。俞新天研究员指出,当前的亚太现实是,东南亚将有自己的自由贸易圈,台湾也有其自身的国际经贸策略,各国各地区皆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规划自己的国际经贸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建立上述经济圈,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值得考虑。崔贵强认为,在新加坡提“中华经济圈”,社会各界反应敏感。当地原著居民会误以为海外华人将把他们的主要财力投向中国大陆,而不是用来发展居住国经济。
三、以“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全球性的海外华人“认同”问题
由于海外华人的根在中国大陆,因此,在以往的海外华人研究中,人们所注重的多是海外华人本身的亲和及凝聚。林其锬研究员的《五缘文化与华商经贸网络》即其典型。他认为,二战以后,在海外华人中,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为纽带的五缘文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为发展。海外华人社团的经济化、国际化现象日益明显,其主要表现就是开放性的世界华商经济网络的形成。不少学者则与此意见相左。丁凤麟提出,讲“五缘文化”,考虑的是民族的向心力及凝聚力。既为“缘”,就应该有共同的联系点,而“五缘”中的“神缘”,是否意味海外华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这似与历史实际不甚相合。崔贵强也认为,“五缘”中的“物缘”,内容到底是什么,不好理解。“亲缘”、“地缘”等确实曾是历史上海外华人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不过这种结构对海外华人并不完全是正面影响的,有利也有弊。而在今日的海外华人社会中,地缘、乡缘的社会功能正在丧失,传统社团组织日趋式微,青年一代对此已兴趣索然。现在新加坡的华人社团,主要工作只是集中力量推广华人文化。关于建立世界华人经济网络问题,崔贵强认为,从东南亚各国的实际看,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华人内部都存在各种矛盾和分歧。要把全世界华人团结和统一在一起,有许多困难。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与着眼于海外华人内部的亲和力相反,近年来在海外华人、华侨研究中提出的“认同”问题,也是会议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所谓海外华人的“认同”,指的是居住在祖籍国以外的华人对自己归属的确认问题。它可以分成政治上的“认同”与文化上的“认同”。政治上的认同是海外华人对自己国籍归属的确认问题,它是当今海外华人“认同”的核心。
崔贵强的《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变》一文详尽分析了当地华人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化过程,认为1950年前,新加坡华人的国家意识是倾向中国的;1950-1959年,华人的国家认同开始转向;1959年新加坡独立后,华人对居住国的认同越来越浓烈。在此过程中,新加坡当局为培植移民对本国的归属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地华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过程,其中新加坡处理最好。针对与会者提出的“认同程度与移民代数”的关系,崔贵强以自身经历为例,指出移民代数无疑与他们对居住国的认同程度成正比关系。
相对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无疑更为缓慢和复杂。美国学者凌渝郎在报告中提出了美国华人传统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的隔阂与共存问题。他认为,美国文化重个人,中国文化重人际。由于两种文化背景的不同,美国华人难以和当地美国人交往,而只能在华人圈子里打交道,社交方面显得相对封闭,从而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安全感,有一种身在美国而不在美国的感觉。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强调参政的国家,而华人所具有的文化背景又决定了他们对政治兴趣甚少,因此他们往往不能较好地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姜义华教授的《论文化的摩擦、适应与再创造-美国华人文化变迁试析》一文,不同意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他回顾了美国华人文化与美国本土的西方文化,从“摩擦”走向“适应”,再走向“多元共生中进行再创造”的变迁历史。认为不同的文化会有摩擦和冲突,但同时也会有融合和同化。应该注意和强调的是,文化本身并不是构成冲突的原因,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以及经济利益的不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对话、发展、共存可以为构建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发挥作用。汪熙教授表示同意姜义华的结论。认为评估海外华人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应该注意到文化的差异不是不同文化本身的差异,而是文化水平的差异。而所谓的摩擦和冲突,说到底还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文化差异既不是冲突的根本原因,也不是冲突的结果,用文化来解释冲突,无论从原因和结果上看都是讲不通的。也有些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唐振常提出,姜在论及“冲突”时,过分强调了政治、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文化背景的作用。从中外历史看,不同的文化会阻碍人们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从而产生冲突。不能仅靠举例来论证。戴鸿超认为,用在美华人的历史例子来反驳亨廷顿,实际上是用美国内部的文化冲突来反驳亨氏的国际文化冲突理论。并且指出姜在论述历史上美国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冲突时,过分强调了这种冲突的严重程度,以致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也有学者指出,在亨氏的“文明冲突”理论中,讲的是“文明的摩擦和冲突”,而姜说的是“文化”的摩擦和冲突。不论在中文还是英文中,“文明”与“文化”都是具有不同涵义的两个概念,对此应有明确的区分和说明。
四、亚太世纪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在未来的世界发展及政治、经济格局中,亚太地区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下个世纪能不能成为亚太世纪,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杨小佛认为,当今世界,亚洲世纪正在形成,只是当今亚洲还面临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集团化的挑战。今后,随着北美贸易圈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亚洲也迫切需要各国之间的互相合作,建立区域的经济组织,以确保本地区经济的正常发展。他分析了亚洲迟迟未能建立统一经济合作组织的五大原因,认为应该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找出变通和妥协的办法,使亚洲团结起来。对此,戴鸿超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亚洲要趋于一体化,就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作为前提条件,但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很大。尽管亚太地区没有自己的实体性组织,地区间的经济活动将会受到外来经济活动的影响和阻碍。汪熙也认为,就太平洋地区而言,各个大国本身的利益并不一致,决定了建立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困难。60年代,日本提出过类似设想,但美国对此反应冷淡;以后,美国有兴趣了,日本却不起劲了。
展望亚太地区的发展前景,与会者大多持乐观态度。俞新天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及中国的作用》中指出,亚太地区发展至今已形成了自身特点,具有广阔前景。亚太地区已是当今世界上三足鼎立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下个世纪,欧美已不能主宰世纪,亚太地区的崛起将成为新世纪的新标志。她也认为,未来亚洲国家与欧美的经济摩擦会加剧,为反对欧美的经济遏制战略,亚洲国家必须有所准备。戴鸿超不同意俞新天关于“三足鼎立”的看法。他认为,因为亚太地区一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地区内的条约或共同组织,二是亚太地区也缺乏共同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谈三足鼎立是不现实的。
对于中国在未来的亚太世纪中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王志平研究员认为,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穷国”,具有双重经济地位的亚洲国家。中国有很大的国际、国内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应扩大活动空间,全面、广泛地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俞新天则认为,未来的中国首先不应该定位于世界大国,而应该定位于地区大国,即亚洲大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中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比较多的与会者认为,中国在未来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1.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它标志着中国的革命性转变。如果成功,将意味着中国创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对于发展中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深远影响,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为世界作贡献。2.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反对大国的霸权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
会议期间,美国、新加坡学者还向与会者介绍了海外中山学社以及海外学者的孙中山研究。郑竹园并代表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海外中山学社”向上海中山学社赠送了镌有“弘扬中山思想”的匾额。台湾中山学社也为会议发来了贺电。四天的会议,与会者各抒己见,争鸣热烈。限于会期,尚有不少问题未能进一步展开讨论。他们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陆与海外华人的交往会更加频繁,对于孙中山及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也必定会越来越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课题。
标签:孙中山论文; 海外华人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加坡华人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华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