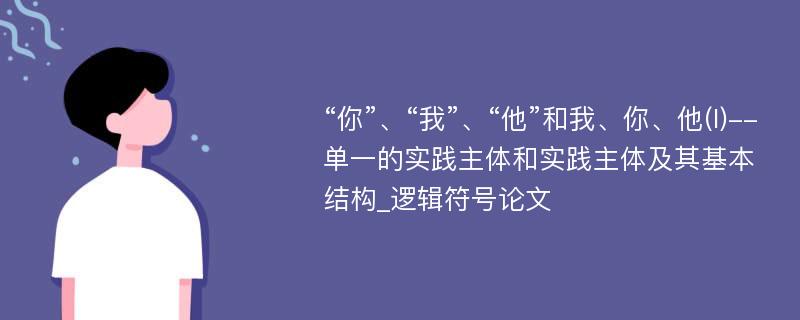
“你”、“我”、“他”和我、你、他(上)——单数的实践主词与实践主体及其基本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词论文,和我论文,单数论文,主体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实践主词、实践主体和自由本体——从“我”说起》(《现代哲学》2010年第4期)一文中,我采用了“循名责实”的分析方法,从“我”说起,看看“我”在实际的使用中究竟意指什么,以及它与其所意指的对象究竟是何关系,并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拟进一步分析“你”、“我”、“他”这三个单数实践主词及其关系,并分析由它们所指代的我、你、他这三种单数实践主体及其关系,最后再分析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而完成对单数的实践主词和实践主体及其基本结构的分析任务。 “你”、“我”、“他” 1.实践指的人称结构 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论文中,我循“我”对我的本指而得自由本体,只是一种自证。本文将表明,“我”对我的指是由“你”对我的指和“他”对我的指相配合而共证的。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通过“我”、“你”、“他”三个人称代词的共同指代而得到人际直观认定的。这三种指代构成了对实践主体的人称指代结构。 前文已述及,“我”是实践逻辑专名。如是,“我”对我的指代属于一阶指。当“我”指代我时,“我”是实践主词,指代我这个实践主体。这种对实践主体的指代可称为实践指。实践指跟表纯粹认知的一阶指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实践指包含一个三位一体的指代结构,即由“你”、“我”、“他”这三个人称代词所构成的人称指代结构,而纯粹认知性的一阶指则可以用指示代词“这”或“那”一指了之。 设想有人指着我桌上的一件物品问我:“这是什么?”我答:“这是一个充电器。”其间,问答双方都用同一个“这”来指代这件物品,并且不会发生任何指代不清的问题。把“这”改成“那”也一样。可是,当朋友问我“你在做什么”时,我却答“我在写东西”。其间,问答双方对我的指代用了两个不同的词语,即“你”和“我”。也就是说,在对方的问话中,我是被“你”指代的,而在我的答话中,我是被“我”指代的。如果这时有人向朋友打听我在做什么,朋友很可能说:“他在写东西。”在这句话中,我又成了“他”的指代对象。尽管在这三句话中,我被三个不同的词语指代,但交谈的各方并不觉得淆乱。相反,如果各方都用同一个词语来指代我,反而会让大家莫名其妙。 这种情况表明,我作为实践主体的存在是由三种目光交叉锁定的,而我桌上的充电器作为一个纯粹认知对象的存在则只靠一种目光即可锁定。换句话说,桌上那个充电器通过“这”或“那”的亲指即可认定其有,而我则总是要通过“你”、“我”、“他”的交叉指代来共证其在。 每一个我都要由“你”、“我”、“他”三个人称代词来指代,这不是任意的。“我”是第一人称代词,其对我的指代是本指,这种指代既显示我作为实践主体已然存在,又开启我的自我认识。“你”是第二人称代词,其对我的指代是对指,这种指代表明跟我正在发生实践关系的对方对我作为实践主体的存在的认定与承认。“他”是第三人称代词,其对我的指代是旁指,这种指代表明当下跟我没有实践关系的第三方对我作为实践主体的存在的认定与承认。 不仅“我”指代我这个实践主体,“你”和“他”也指代我这个实践主体。正因为“我”、“你”、“他”都指代我这个实践主体,即一个可以发出行为的个别实体,所以它们都是实践逻辑专名。所不同的只是:“我”这个实践逻辑专名在充当主词时跟它所指代的作为实践主体的我统一于同一个自由本体,因而是本位的实践主词;而“你”所指代的虽是我这个实践主体,但发出这个指代行为的却是我这个实践主体的对方,主词“你”和它所指代的我并不统一于同一个自由本体,就此而言,“你”可以称为对位的实践主词;“他”指代我这个实践主体,但发出这个指代行为的自由本体却身处我的实践关系的旁边或边缘——既不在其中又相距不远,如是,“他”就是旁位的实践主词。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你”和“他”也被叫作实践主词,但它们之为实践主词不是自立的,更不是跟“我”平等的,而是依附于“我”的——只有“我”才是本原的、绝对的实践主词,包括“你”、“他”在内的其他实践主词都是派生的、相对的实践主词。 用“我”来指代我的是我,用“你”来指代我的是你,用“他”来指代我的是他——当你不以我为对方时,你对我而言就变成了他;反之,当他把我作为对方时,他对我而言就变成了你。这种指代关系不仅呈现了自由本体绝对多元性的事实,而且显示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先验性质的结构。也就是说,自由本体的多元性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由实践逻辑专名的指代结构来加以规范的。这种结构就是实践指的人称结构。 历史上各种关于我的哲学分析之所以陷入唯我论的泥淖,就是因为这些分析没有看到实践指的人称结构及其重要意义。 2.“你”的优先性 在实践指的人称结构中,对位实践主词“你”对我的指代其实比本位实践主词“我”对我的指代更具优先性。 当我聚精会神写作时,若无朋友问“你在做什么”,我不会说“我在写东西”。在这个例子中,朋友用“你”指代我在先,我用“我”指代自己在后,并且“我”是被“你”引导出来的。即使把我和朋友的位置调换过来也一样。假设是我打电话给朋友,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回答“我在写东西”,那么,情况同样是:我用“你”指他在先,他用“我”指他自己在后,他所说的“我”是被我所说的“你”引导出来的。扩展开来看,在日常生活中,两个人相见首先都说“你好”或类似的话,然后再说“我如何如何”。虽然这时的“你”指代对方,“我”指代自己,但“你”的出场同样先于“我”的出场,“我”是由“你”引导出来的。当然,这里所要集中探讨的是对作为实践主体的我的指代问题,其他相关问题留待后文去处理。 在对我的指代结构中,“你”之所以优先于“我”,在于“你”表对指,其指向是正向朝外的,相应的直观可称为对观;而“我”表本指,其指向是反向朝内的,相应的直观可称为本观。不仅如此,对观也是以你为对象的直观,而本观则是对于对观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对观是意识行为的主题,而本观则是意识行为的副题。因此,在意识关系上,对观优先于本观,基于对观的对指优先于基于本观的本指。平常两个人在一起,总是把对方看得最清楚。生活中每个人最熟悉的形象都不是自己的,而是最亲近的人的。就算没有人对着我说“你”,我也可以在镜子里对着直观中的自己说“你”。 我被称作“你”,一方面表明我被承认为一个实践主体,另一方面表明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实践主体正在跟我发生人际关系。如果没有那个对我说“你”的实践主体的存在,我也不会表现为由“我”所指代的实践主体。可见,“你”既是“我”的引导词,也是两个相互对待的实践主体之存在的索引词。 称我为“你”的人也被我称为“你”。就此而言,用“你”对指我的那个实践主体不是别人,就是你。你用“你”对指我,表明我的存在已在你的对观之中。即使你只是跟我通电话,我的声音作为我的整体的一个方面也完全在你的直观把握之中。就算你我素昧平生,仅以书信交往,你称我为“你”也至少表明你相信我的存在,或预设了我的存在。对你而言,我的存在意味着或者我是你正在对观的,或者已经对观过的,或者可以对观的。更重要的是,你称我为“你”,原本包含着对我的回应的预期,亦即我会相应地称你为“你”。只有实际构成了回应关系,“你”的对指才是完全的。或者说,只要得到了我的回应,“你”的对指行为就算最终完成了——即使我不在你的对观之中,你也可以通过我的回应而确认我的存在。 “我”对我的本指存在间距,但这种间距不超过自我意识的视域。“你”对我的对指也存在间距,但这种间距却会突破你对我的直观视域。“你”原本是没有传输辅助手段的语音符号,当你用它来对指我时,我一定在你的直观视域内,或至少我的回应要出现在你的直观视域内。可是,在有了书写符号后,“你”对我的对指和你对我的对观就脱节了——我可以不在你的直观视域内。比如,靠鸿雁传书的我和你就只有对指而没有对观。现代传媒利用语音、文字、图片和视频等远距传输技术,既极大地扩展了你我的对指间距,又保证了彼此间尽可能多的对观联系,使对指间距的情况复杂化。 不管怎样,通常情况下,在“你”对我的指代中,我的存在不会成为问题。只有在网络虚拟世界,由于我把本体隐藏在符号之中,“你”对我的指代才发生存在问题。 3.“他”的必要性 三人行,除了你、我必有他。你称我为“你”,我称我为“我”,他称我为“他”。 “他”为第三人称代词,可以充当旁位的实践主词。汉字“他”可拆为“人”和“也”,颇多“望文生义”的空间——指代任何虽不是你和我但也是人的存在单元。现代汉语发明一个“她”字,用来专指女性,而把原本统指“也是人”的“他”限定为男性及不明性别者的人称代词,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一定要“接轨”西方语言,让人称代词体现性别,那也应该同时多发明一个字来指代男性,而不要让男性独占原本男女共享的“他”字。出于这种理由,本文把“他”用作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不分性别。 凡用“他”称我的人,我也用“他”相称。他用“他”来指代我,表明他跟我不是当下实践关系的双方,或者说我已旁落到他的实践关系的边缘,成了他与其对方之外的第三方。如是,“他”所充当的主词就是旁位实践主词,其对我的指代就是旁指,相应的直观就是旁观。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因之而旁落于我的实践关系的边缘,成为我的实践关系的第三方。 我只要存在,只要有本指的能力和行为,就一定是实践主体。这个道理对他来说也同样适用。尽管如此,只要他没有用“你”称我,就表明他是把我置于其当下实践关系的边缘的,同时也是把他自己置于我的当下实践关系的边缘的,从而我和他各自当下的实践关系就是互为边缘的。 不过,他称我为“他”,表明他毕竟是意识到我的存在并承认我的实践主体地位的;他发出对我的旁指行为,也表明他同样是一个实践主体。虽然我和他都是实践主体,但我和他却互为彼此实践关系的外人。这既是自由本体绝对多元性的体现,也是实践关系复杂性的体现——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我被称为“他”和被称为“你”是可以转换的。朋友本来称我为“你”,这时,我是其实践关系的对方;可他转头跟另外一个人说话,就把我称为“他”,于是,我就成了其新的实践关系的第三方了。也可设想相反的情况:朋友本来是在跟另外一个人说话,其间称我为“他”,我是其实践关系的第三方;可他转过来跟我说话,就称我为“你”,我又变成了其实践关系的对方。我从被称为“你”到被称为“他”的变化是边缘化或去中心化,而从被称为“他”到被称为“你”的变化则是中心化或去边缘化。只要是三人行,每一方就一定都免不了一会儿被称为“你”,一会儿被称为“他”,亦即在被中心化和被边缘化之间循环。 “他”的必要性在于,一方面,我因被称为“他”而拥有了跟无数实践主体的潜在实践关系,另一方面,“他”也给我提供了从他人的实践关系中退出的机制。当我外在于某一实践关系时,只要我被称为“他”,我就有了被称为“你”的可能,就有了进入这一实践关系的可能,亦即有了去边缘化的可能。称我为“他”的人越多,我的实践关系的可能性空间就越大。当我既在某一实践关系中时,一旦我被称为“他”,我立马就旁落到这一实践关系的边缘。再从他人的角度看,“他”的必要性还在于,那些外在于我的实践关系的个人因称我为“他”而有了称我为“你”的可能,从而有了成为我的实践关系之对方的机会。 除了你和我,谁都可以称我为“他”。称我为“我”的人无论如何只有一个,称我为“你”的人在我的实践关系的每一单元中只有一个,称我为“他”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有无数个。我被称为“他”,预设了复数的他人的存在。 跟本指和对指一样,旁位实践主词“他”对我的旁指也存在间距。不同的是,相比本指和对指,旁指的间距最大。称我为“他”的人可以就在我的身旁,此时,旁指伴随着旁观,我的存在不超出旁观者的直观视域,间距相对较小。通常所谓“旁观者清”,大概在这个时候最能成立。不过,旁指也可以不伴随旁观。比如,当朋友放下电话跟别人说起我时,我并不在其直观视域内,他们旁观不到我。有时,旁指甚至恰恰需要脱离旁观。比如,别人当着面不便说我的话,可以等我从其直观视域中消失后再说。更为重要的是,旁指可以在完全且永远缺乏旁观的情况下进行。比如,那些跟我今生今世也无缘晤面的人,同样可以称我为“他”;即使哪天我不在人世了,只要别人愿意,也可以旁指我,尽管其指之所至皆为虚无。 本指间距不管有多大,都不至于使我的存在脱离我的本观而让我不知“我”之所指。对指间距虽大于本指间距,但由于对指要求我的回应,因而只要我的回应出现在你的对观中,我的存在对于你的对指来说就不会成为问题。相比之下,旁指无需回应,不必在直观中落实,既可以“旁观者清”,也可以张冠李戴,甚至捕风捉影,这样一来,由“他”所旁指的我就变得最为可疑——那么多的“他”所指的我真的是我吗?对此,他并不在乎,而我也无从知晓。 4.实践指的剩余——无指、无观和其他 据说全球目前约有70亿人,而迄今总共有过800多亿人。在所有这些人中,用“我”指我的人始终只有我一个;用“你”指我的人就算日增一个,终我一生也只能以万计;至于用“他”指我的人,尽管无从测度,也不过在所有用“你”指我的人外再加上那些跟他们一道谈论我的人而已。即使那些超级名人,也同样只有其各自才可以用“我”指其自身,而用“你”指他们的人也不见得就比用“你”指普通人的人更多,唯有用“他”去指他们的人可能会比用“他”去指普通人的人多出若干个数量级——尽管这相对于总人口而言仍然十分有限。 “你”、“我”、“他”对我的指代显示了我的指代者的范围。这个范围的人加上那些被我用“你”和“他”去指代的人,就构成了我的实践指的全部范围。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你”、“我”、“他”才会发挥切实的指代作用,才可能具有实践意义。超出这个范围,既没有人用“你”和“他”指代我,也没有人被我用“你”和“他”去指代,相对于那些人来说,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互为边缘还要远,已经到了完全相互外在的程度。 凡是我的实践指所不能指达的人,对我而言都是实践指的剩余。这些剩余的人分属两大区域。较近的区域是我日常置身其中的茫茫人海。单就对我的指代来说,这茫茫人海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直观到我,却既不用“你”指我,也不用“他”指我,而是把我视若无物,漠然以对——他们对我可谓有观而无指;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则对我甚至连一瞥也不会有,他们即使看到过把我卷入其中的某片人潮,也不会把我作为存在单元加以观照——他们对我可谓既无观也无指。 所有人都存在于这同一个世界,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实践指的范围。如果把每个实践指的范围都看作一个实践的格局,那么,每个人就都是自己实践格局的当局者,而对于其他人的实践格局来说,就或者是其局中人,或者是其局外人。局外人也就是特定实践格局的剩余者。不同的实践格局之间或者互有交叠,或者互不搭界,局内局外的边界也处于不断流变之中。没有人可以同时存在于所有人的实践格局之中,也没有人可以做到不让任何人成为自己实践格局的剩余者。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可以做永远的当局者,所有的实践格局都有破局的时候。 5.“你”、“我”、“他”的共同替代符号——普通专名 实践指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包括本位实践主词“我”的本指、对位实践主词“你”的对指和旁位实践主词“他”的旁指,以及这三者所指代的我这个实践主体。这个结构是绝对的。但是,“你”、“我”、“他”作为实践逻辑专名属于个别词,当它们共同指代我时,可以用普通专名即我的姓名统一地加以替换。 比如,有人打电话来,说:“喂,请问你是徐某人吗?”我答:“是的,我是徐某人。”电话那头称我为“你”,电话这头则称我为“我”,但都以“徐某人”为替换符号。假设通话之后,对方向第三方介绍情况,说:“我刚才给徐某人打了电话。”第三方问:“他说什么?”这时,我又变成了“他”的指代对象。虽然如此,用来替换“他”的符号仍然是“徐某人”。可见,在对我的指代结构中,三个实践逻辑专名都可以由“徐某人”这一个普通专名来替换。 假设正在写这些东西的不是徐某人,而是另外某个人,上述对话也能成立,但用来替换“你”、“我”、“他”的普通专名就不会再是“徐某人”了,而只会是别的姓名,如“张三”、“李四”。由此可见,“你”、“我”、“他”虽然可以用来指代任何实践主体,但它们在每一次运用中都特指某一个实践主体,因此,如果要将这些不同的实践主体区分开来,就不能靠这三个实践逻辑专名,而只能靠“张三”、“李四”这种普通专名。也就是说,实践指内在蕴涵着普通专名和实践逻辑专名之间的可替换性。 这种替换现象表明:一方面,我作为实践主体是个别的存在,我的姓名就是这种个别性的表达,用来指代我的“你”、“我”、“他”不过是这种个别性的三个指代维度;另一方面,我的个别性又不是一种孤绝的状态,而是一种内在蕴涵了人际性的状态,表现为我的姓名不仅可以反过来由实践逻辑专名替换,而且可以由“你”、“我”、“他”三个实践逻辑专名来替换。 这样一来,我作为自由本体就不仅仅是“我”这个实践主词和它所指代的我这个实践主体的统一体,而且是“我”这个实践主词连带其对位主词“你”及旁位主词“他”和它们所共同指代的我这个实践主体的统一体。我的姓名这个普通专名就是这个统一体的专用符号。 我、你、他 1.实践主体的人际结构 当我用“我”指代我时,我的实践关系的对方是用“你”来指代我的,而我的实践关系的第三方则是用“他”来指代我的,这种情况下,“我”、“你”、“他”都以我为指代对象。这是站在我的立场上并以我为指代对象所看到的实践指的人称结构,亦即实践主词的指代结构。 可是,我不仅是被指代的对象,也是发出指代行为的主体。这不仅表现在我已经用“我”指代我自己了,而且表现在我还可以用“你”指代我的实践关系的对方,用“他”指代我的实践关系的第三方。我用“我”所指代的对象是我,我用“你”所指代的对象是你,我用“他”所指代的对象是他。这样一来,站在我的立场上,我就有三个指代对象:我、你、他。“我”是本位实践主词,我用“我”指代我,表明我是本位实践主体;“你”是对位实践主词,我用“你”指代你,表明我承认你也是实践主体,只不过是相对于我而言的对位实践主体;“他”是旁位实践主词,我用“他”指代他,表明我承认他也是实践主体,只不过对我而言是旁位实践主体。 我承认你和他都是实践主体,意味着我知道你和他跟我一样都可以由“你”、“我”、“他”共同指代。从我的角度去看,所不同的是:我用“我”指代我自己,因而我的主体性是由我建立的;你用“我”指代你自己,因而你的主体性只能由你建立,而不能由我建立;他用“我”指代他自己,因而他的主体性也只能由他建立,而不能由我建立。我只能承认你和他的主体性,而不能建立你和他的主体性,因而你和他的主体性对我来说是对位的和旁位的。 反过来,尽管我无法超出我自身而站到你和他的立场去发出指代行为,但我根据你、我、他的谈话可以推知:跟我一样,你也把你自己看作本位实践主体,而把我看作对位实践主体,把他看作旁位实践主体;他也把他自己看作本位实践主体,而把他的实践关系的对方看作对位实践主体,把我和你看作旁位实践主体。也就是说,尽管你、我、他都是实践主体,但三者并不是直接互等的,不仅各自被指代时的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其发出指代行为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其间的关系比通常所谓的主体间关系要复杂得多。 有我,有你,有他——这就是由实践指的人称结构所彰显出来的实践主体的人际结构。 “你”、“我”、“他”是用以指代的符号,是实践主词;你、我、他是被指代的对象,是实践主体。“你”、“我”、“他”既可以共同指代你、我、他中的任何一方,也可以分别指代你、我、他中的各方。反过来说,你、我、他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被“你”、“我”、“他”共同指代,其中的各方也可以被“你”、“我”、“他”分别指代。 2.你——对位实践主体 我是本位实践主体。我只有已然存在,才能直观到你的存在,并用“你”去指代你,从而把你把握为我的实践关系的对方。就此而言,尽管在意识关系上,对位实践主词“你”优先于本位实践主词“我”,但在实践关系上,作为本位实践主体的我却优先于作为对位实践主体的你。 我称你为“你”,表明我或者已经对观到你,或者已经设定了你的存在。 说我对观到你,并不是说我只是感知到了一个物质形体,而是说我用我的整个直观机能把握到了一个对位实践主体的存在,而这个主体不仅能够领会我用“你”所发出的对指行为,而且能够用“你”对指我,以作为对我的对指的回应。我称你为“你”,蕴涵了我对于你的回应的预期,即你也会称我为“你”。或者,因为你已经称我为“你”了,所以我才作出回应,称你为“你”。可见,你的存在不是我用我的感知一点一滴复合出来的,更不是我用对你的形体的感知加上对你的心灵的推导而复合出来的,而是在我把你作为我的实践关系的对方加以对观的过程中直接意识到的。 可以先有对观再有对指,也可以先有对指再有对观。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当我发出对指行为时,我一定相信你的存在,也就是说,我相信你是可以被对观到的,或者你的回应至少会出现在我的对观中。我之所以相信你存在,是因为我直观到某些迹象,并由此推定它们是由一个实践主体造成的;我之所以对指你,是因为我希望借此得到你的回应,即便这种回应仅仅表现为某些新的迹象。只有在我的对指无所回应的情况下——包括你和你的任何回应迹象都没有出现在我的对观之中,你的存在对我来说才会成为悬疑。这就是说,缺乏对观的对指透支了关于你的存在的信念,而这种透支是必须偿还的,否则信念就会破灭。 本指和本观若即若离、不即不离,这是本指间距的特点。与之不同,对指和对观既可以如影随形,也可以相隔天渊。对指间距的这种特点为实践指带来充满张力的空间。你在我眼前时,我可以当面说“你”;你不在我眼前时,我也可以通过各种传输媒介来说“你”。我可以为了回应你的对指而说“你”,也可以为了得到你的回应而说“你”,甚至即使你永不回应我也依然说“你”。对指间距的这种张力状况表明,我不能对所有的你等量齐观,而必须对不同的你进行存在信度的区分。具有最高存在信度的你是出现在我的对观中的你,我不会对这样一个你是否存在产生怀疑,这种对指属于亲指。具有最低存在信度的你是既未出现在我的对观中也不对我的对指有任何回应的你,这种对指属于虚指。具有中间信度的你是虽未出现在我的对观中但对我的对指有所回应的你,我可以确认存在着回应者,但不能确认回应者是哪一个你,以及是否为同一个你,这种对指属于一阶指的混合类型。 正因为对指和对观之间存在巨大的间距,所以信仰才有了可能。信仰的对象不必在我的对观中,却可以用“你”去对指,其存在仅仅系于我的相信。就此而言,我完全可以把天、地、鬼、神都称作“你”。不过,相信你存在和对观到你存在毕竟不是一回事,对指终究还得以对观为根据。天、地可观却无言,不会反过来称我为“你”;鬼、神既无言又不可观,同样不会反过来称我为“你”。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说明天、地并不是我的对位实践主体。我敬鬼、神而远之,也是因为它们从不回应我的对指,也从不现身于我的对观之中。如是,我对天、地、鬼、神唯有心存敬畏,即使对指它们,也不会把这种对指跟对我身边的人的对指混为一谈——我对我身边的人的对指,可以由我的对观来认定;可我对天、地、鬼、神的对指,却无法由我的对观来认定。 3.他——旁位实践主体 当我跟你谈起另一个人时,这个人就成了他——不仅我称之为“他”,你也称之为“他”;不仅我和你称之为“他”,他也称我和你为“他”。我和你称他为“他”,意味着我和你已经承认他也是人;他称我和你为“他”,表明他也在发出一个指代行为,也是一个实践主体。但是,我作为实践主体是自我透明的——我对自己的符号指谓具有自我意识,你和我作为实践主体是互相半透明的——我和你在彼此应和中互相开放符号意识,而他作为实践主体则对我和你都是不透明的,或至少是不直接透明的——他既不是我和你,也不必跟我和你相应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本位实践主体,你是我的对位实践主体,而他则是我和你的旁位实践主体。 我对旁位实践主体的指代叫旁指,这是实践指中间距最大的指代。他作为旁指的对象是否存在,必须通过旁观来认定。凡是旁观范围内的旁指都不易出问题,而凡是超出旁观范围的旁指都容易出问题。 在我所有的旁指行为中,只有少数行为伴随着旁观。只要跟我在一起的人不止一个,我就必定用到旁指,并且具有相应的旁观,也就是说,就必定有人被我称为“他”,并且他还可以被我旁观到。我所说的“他”是否确有所指,是否指得其人,以及其后的述谓是否属实,都以我对他的旁观为基础。不过,他不可能始终保持在我的旁观之中。当其脱离我的旁观范围时,我依然可以旁指他。有时,正因为他不在我的旁观范围,我才可以更方便地旁指他。有的人可能只被我旁观过一次,却可以被我千百次地旁指。在不被旁观的情况下,他的专名可以充当替身而作为我旁指的对象。比如,如果他在场,我可以用手指着他说“他”;而当他不在场时,我就必须先说出他的姓名,再用“他”加以旁指。不管怎样,只要我对他有过旁观,他的存在对我的指代来说就至少不会成为问题。 在我旁指过的所有人中,只有少数人被我旁观过,而大多数人都在我旁观所及的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对我而言的旁位可以近在咫尺,也可以远在天涯;可以是同时性的,也可以是异时性的。对于不在我旁观范围内的他,我只能旁指其姓名,并设定该姓名对应着一个实践主体,而不能直接把他把握为一个存在的单元。他超出我的旁观范围越远,其存在对我来说就越成问题。就算我确信他的存在,我也无法对他形成旁观所特有的那种明证感。正因为如此,具有存在设定的历史人物往往不如没有存在设定的小说人物真切——关于存在的信念毕竟不是对于存在的直观。 伴随旁观的旁指属于亲指,曾有旁观的旁指属于忆指,从无旁观的旁指属于闻指或虚指。可见,不同的旁指因间距不同而有着意识品质上的差异,或者说,并非所有的他都具有相同的存在信度。 4.剩余实践主体——在我、你、他之外 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只有一个我,却有许多你,还有更多的他。我、你、他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所发出的实践指的作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我的实践指就无能为力了。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你、他,还有大量其他人。虽然我的指代无法达及他们,但我知道他们无不是实践主体。这种不在我、你、他范围的实践主体不妨称为剩余实践主体,他们构成了我的实践指范围的外部社会环境。 依据跟我的关系的远近,剩余实践主体可分为内、中、外三大圈。内圈是我对之有观而无指的那部分剩余实践主体。如大街、车站、广场、商场等场合的人流,我直观到它,甚至卷入其中,却不对其中的诸个体分别指代。中圈是我对之既无观又无指却有实际影响的那部分剩余实践主体。如那些读我的作品而跟我素不相识的读者,我无缘见到他们,也无从招呼他们,却不经意扰动了他们的生活。外圈是我对之既无观又无指亦无实际影响的那部分剩余实践主体。如那些遥不可及时空领域中的人们,我跟他们天悬地隔,即使设想也漫无头绪。 对于剩余实践主体,我无以指代,更无从述谓,因而不可能把他们作为各自独立的实践主体纳入我的计虑考量之中,但我的实践却有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我的对位实践主体和我的旁位实践主体是我的实践格局的内在构成因素,而我的剩余实践主体则是我的实践格局的外部环境。对位实践主体和旁位实践主体不可能变成剩余实践主体,但剩余实践主体却可以变成旁位实践主体乃至对位实践主体。 5.实践主体的专用指代符号——普通专名 我、你、他都是实践主体,但在实践关系中的角色不同。站在我的立场,自称“我”的是我,被称为“你”的是你,被称为“他”的是他。可是,站在你的立场,自称“我”的是你,被称为“你”的是我,被称为“他”的是他;站在他的立场,自称“我”的是他,被称为“你”的也许是别人,而我和你则都被称为“他”。也就是说,我、你、他作为三种实践主体的相互关系是由“你”、“我”、“他”三个实践逻辑专名先验确定的,但我、你、他究竟是谁,究竟对应哪一个存在单元,却无法仅凭这三个实践逻辑专名来确定。这种情况下,作为各个实践主体的专用指代符号的普通专名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一个实践主体都有自己的普通专名,即一张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单元的标签。正是借助这张标签,不同的实践主体得以相互区别开来,并在此前提下形成我、你、他的人际结构。也就是说,每一个实践主体都是以各自的名义来相互指代的。 对我来说,你不是某个特定的个人,而是实践关系中与我相对待的一个位格。一个人只有占据这个位格才是你,否则就不是你;而可能占据这个位格的人是难以计数的。因此,在跟你打交道时,我不会满足于用实践逻辑专名指代你,还要知道你的普通专名。同理,他也是实践关系中的一个位格,可以占据该位格的人也难以计数。因此,我也只有通过不同的普通专名才能把不同的他区分开来。至于我自己,由于只有一个,因而不必靠普通专名来进行自我区分。不过,我毕竟有普通专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样可以帮助别人把我跟其他人区分开来。 我不必时时念叨自己的普通专名,你可以不告诉我你的普通专名,他的普通专名我可能无从打听到——尽管如此,我、你、他毕竟都有各自的普通专名,它们都是用来替换实践逻辑专名的,都是不同实践主体的专用指代符号。(待续) (本文为作者《拯救实践》第二卷第一章稿本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