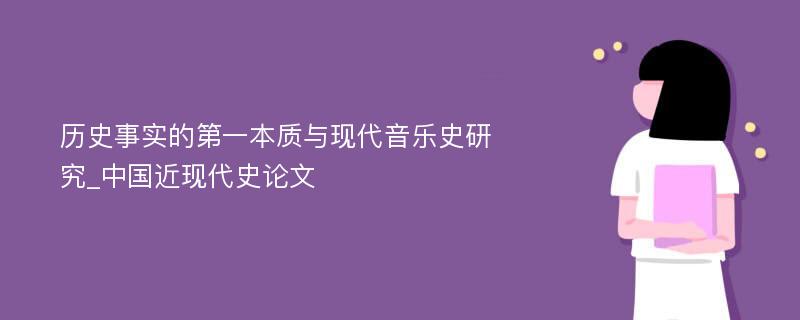
“史实第一性”与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近现代论文,史研究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在编纂《萧友梅生平纪年》过程中,发现了萧友梅先生在抗战初期所写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养成班理由及办法》(下简称“理由及办法”)等一批珍贵历史文献。为此,《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在部分刊载这些文献的同时,配发了一组文章,初步阐发了这一发现对于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戴鹏海教授在他的《事实胜于雄辩》一文中,结合自身的研究实践,对于文献、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文虽不长,但言简意赅,读之感触良多、受益匪浅,从而引发出我对“史实第一性”问题的几点思考。现在把它们写出来,以求教于史学前辈与同行。
史实、史料、史作辨伪及搜寻
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在过去年代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和种种历史现象本身,即“本真的历史”,我称之为“史实”;一种是时人及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叙和描述,即“对历史的第一度解读”,我称之为“史料”;一种是今日史家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对这段历史的再记叙和再描述,即“对历史的第二度解读”,我称之为“史作”。鉴于历史研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因此,前人的“史作”,就是我们今天的“史料”,今人的“史作”,又将成为后世史学家的“史料”。
我在《新音乐史家与现代音乐思潮研究》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说过:
史实囊括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所有具有史学价值的事实,是历史现象的原生态,它以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而令人惊异,成为一切史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矿藏;它之难以企及和不可穷尽,使得作为史学研究个体的史家必须永远怀抱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忠实地匍匐在它的脚下,而无法仰视其全貌。
对这一段话,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史实不仅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而且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是衡量一切成说和观点的试金石。在铁一般的史实面前,任何雄辩和看似雄辩的诡辩都将变得软弱无力。例如单单贾湖骨笛的出土,就修正了五千年的成说而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延伸到八千年前。这就是铁一般史实的力量。新近发现的萧友梅“理由及办法”等一批珍贵历史文献,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推倒了以往加在所谓“学院派”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同样也充分证明了史实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史料的涵盖面虽不如史实那样宏富,但情形也相当复杂。在某些情况下,它与史实是重合的,例如音乐史上的音乐作品(包括音响、乐谱及演出的影视和图片)、思潮批评与论战的文本文献,以及当时的重要文件、会议简报与发言记录等等,它们既是史实,同时也是史料。然而在更多情况下,则是时人和前人对于历史事实的某种记载、报道、评论、描述以及他们的史学成果——史作,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新音乐史家来说,都是典型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料或受制于当时的现实环境,或因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它们在反映史实的真实度上并不相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其中有疑团,也有陷阱。新音乐史家对这些史料若不花一番艰苦扎实的分析、考证和辨伪的工夫,就会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史料面前迷失方向,甚至有可能上当受骗、误入陷阱。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关于汉代竹简的误读就是一个严重教训。这个教训,相关当事人以及每一个史学家都应当牢牢记取。其实,在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类似的例子也并非绝无仅有。戴鹏海先生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个案研究中,就曾经举出过这样的实例。前几年,我本人参与的关于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作者的争论,也牵涉到如何对待史料的问题:《当代中国音乐》根据公开可见的史料,将作者记写为杨嘉仁;而赵沨同志及其他一些同志则根据黎英海先生证词和蔡余文先生自述判定作者为蔡余文。现在看来,上述两种意见都不够准确——根据论战中已经披露的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最大可能是蔡余文改编于前而杨嘉仁修改于后,因此较为妥当的解决办法是蔡、杨联署。
我举这些例子旨在说明,音乐史家对于手中的史料一定要持审慎的科学分析态度,切不可听见风就是雨,拿来就用;也要在研究和写作实践中不断发掘新史料,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史料积累,为史学研究之逐步接近史实提供充足可靠的论据;当然更要有史家胸怀,一旦新发现的史料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失误,就要服膺史实,及时修正,而不能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而抱残守缺、坚持不改。特别是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实在是史料蕴藏极为丰厚的“富矿”区,只要我们肯于下苦工夫,新史料的不断被发现,较之古代音乐史研究有着更多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是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者一个极大幸运,新史料的层出不穷也常常因其有助于史学界对历史真相的认识逐步趋于准确和全面而给我们带来极大惊喜。
我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古代音乐史的新史料发掘是“大海捞针”,而近现代音乐史的新史料发掘则应“竭泽而渔”。现在看来,此事知易而行难。就以这次萧友梅一批珍贵史料的发掘为例——南京第二档案馆就在我工作单位附近,而这批史料却偏偏不是我和南京的同行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者发现的。作为近现代音乐史一位后来的研究者,我对此在惊喜之余也感到羞愧,并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这件事警示我们,史学研究者是不能以任何理由(例如年事高、工作忙、经费少之类)在史料发掘方面偷懒的,不能坐等史料送到手边,而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主动去把那些沉睡在历史尘封中的史料搜寻出来,让它们为解开近现代音乐史上一系列历史谜团提供新的确凿证明和论据。
“史实第一性”: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许多史学家都声称,他们的历史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就使我们关于史实和史料的讨论有了一个对话和沟通的共同基础。事实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学说中,“史实第一性”却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有许多精辟论述和经典范例,恕不一一征引了。
当然,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除了唯物史观之外,还有其他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但无论它们的历史哲学和方法与唯物史观有多少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史实第一性”原则。试问: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严肃的史学流派,会从根本上撼动、否认、反对“史实第一性”原则么?汉代司马迁不可能掌握唯物史观和方法论,但他在史学巨著《史记》中所倡导、施行并成为中华史学传统伟大精神支柱的“秉笔直书”原则,其核心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史实第一性”。在20世纪50-60年代曾被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为“唯心史观”的所谓“考据派”和“索隐派”,它们所坚持和强调的,也正是这个“史实第一性”原则。
因此,“史实第一性”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的史学研究和写作,便不成其为严肃的历史科学,因为它的记叙和结论,经不住史实的检验。
从事的当代史研究,在接近、认识和把握史实方面较之古代史同行有着更多的便利和更直接的途径,但新音乐史家对史实的认识和掌握依然是永无止境的,依然要把一步步接近史实、力争把握史实的主要脉络和基本面貌放在第一位,当作一切研究的起点和基本功,要在史学研究中牢固树立“史实第一性”的观念。只有最大限度地接近和尊重史实,认真地倾听作品、掌握事实,尽可能地了解和熟悉自己所记叙的人物、事件的真实面貌,以夯实我们的史实基础。唯其如此,我们的史学成果——史作才在把握史实这个根本点上获得学术刚性,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才有科学性可言,才能经得起史实的检验。
因此,必须从历史哲学和历史观的高度上来认识“史实第一性”原则,特别是那些公开声言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历史哲学的学者,更要对这一原则身体力行,贯彻始终。我本人对唯物史观了解不多,从事史学研究的根底也浅,但我服膺这个历史哲学,愿在研究、写作和教学中努力贯彻“史实第一性”原则。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表白,是为了与前辈及同行们共同避免“言不行、行不果”的学风,一起把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推向一个新境界。
最不该原谅的,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明明对当时所做的那些事、所说的那些话、所开的那些会、所发的那些文件、所写的那些文章,知根知底、一清二楚,到了后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则开始打起了小九九,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不说,还要利用年轻学子的幼稚、浮躁及其他不健康心态,提供伪证,制造假象,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得真假难辨,企图在搅浑水之余,逃脱历史对其灵魂的追问。然而,史实就是史实,史料就是史料,史料可以造假,史实却是铁一般的存在。任何涂抹历史真相的企图和做法,在无情史实面前,迟早要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
“史实第一性”: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从方法论层面看,“史实第一性”原则同时也是音乐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虽然,对于特定的研究者来说,即便终其一生也很难穷尽一个历史时代的全部真相,或许只能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专题上做到史料占有的竭泽而渔并力求使我们的研究接近史实的原貌,但对于同样是“史实”的一系列对象,例如具体的音乐作品研究、音乐家研究、音乐思潮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对乐谱、音响、图片、演出节目单,当时的会议简报、文件、发言记录及理论批评文本等等的竭泽而渔,研究者必须直接面对这些史实载体,亲耳聆听它们,仔细研读它们,通过与这些史实的“零距离接触”来亲身感受当年的时代风云及其变幻,由此才能获得对这部分历史史实的真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某一作品、某一人物、某一事件或某一思潮争鸣的梳理、认识、评价和判断,才是有根有据的和言之成理的,因为我们对与之有关的所有重要史实、史料已经悉数占有并经过一番分析、体验、研究和消化过程,才能在历史写作过程中保持科学冷静的态度,使我们的历史描述最大程度地接近史实,并在扬抑褒贬之际、遣词用语之间,把握分寸感,驾驭张弛度,美其当美,刺其当刺,而不至于发生背离史实、扭曲真相之类根本性错误,也可有效避免较明显的美刺无节、褒贬失度等偏颇。
在史学研究方法论中实行“史实第一性”原则,看起来很费事也很笨拙,但这种方法非常实用也非常有效。可惜,现在有一些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只看其费事的一面而无视其有效的一面,总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既不费事又很有效的方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是否确有如此神奇的方法存在,倒是因无视“史实第一性”方法而走入歧途的例子见过不少。
例如,一些学者常常分不清史料与史实的联系和区别,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误把史料当史实,以为尽可能地占有史料,我们的研究也就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了。其实不然。你研究50-60年代的音乐作品评论,仅仅把当时的批评文本当作论文的主要史料和立论依据来加以引述和评述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其实是颠倒了史实和史料的关系。因为,这些当时的批评文本只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而且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即便作者对这些文献的搜集已然“竭泽而渔”,也无法改变它们的史料性质。真正的史实是这些被评论的音乐作品本身和隐藏在这些作品及其评论后面的深层文化环境。因此,只有千方百计地将当时的音乐作品的乐谱和音响找来认真听一听、仔细分析一番,联系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并对照当时的评论文本来加以综合梳理、研究和评价,才有可能真正接近史实本相。
再如,最近有一篇博士论文,在谈到关于 50年代中期音乐界对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讨论时说,吕骥同志没有组织《人民音乐》开展这个讨论,而且批评编辑部将贺绿汀与胡风相联系的做法。作者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对伍雍谊同志的采访笔录。且不说伍雍谊同志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单就作者仅仅根据一个当事人的回忆就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做出这一结论的做法本身而言,显然在处理史实与史料的关系上较为轻率。因为,伍雍谊只是当事人的一方,是否应该听一听当事人另一方提供的说法,以便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再说,当事各方的回忆都是史料而非史实,都要接受史实的严格检验;严肃的治史态度还应该遍寻当时的原始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及简报、内部讲话记录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甄别和辨伪,作者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接近于史实的原貌。这个例子也说明,新一辈史学研究者之缺乏科学史观和方法的训练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史实第一性”原则对他们几乎是全然陌生的。因此,关键是他们的导师首先要牢固树立“史实第一性”的观念和方法,乃是当前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当务之急。
因此,当代人写当代史,一定要在史实和史料方面狠下苦功。只有把史实和史料的基础夯实,我们写出的史作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史实,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史实第一性”:历史解读的唯一依据
同历史研究及写作一样,历史解读也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实际上,一种历史写作成果的出炉,也就提供了一种历史解读的范式和方法。对于同一段历史有不同的解读,不仅允许而且极为正常,因为它符合人类对历史现象和历史本质的认识论规律。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伟大史家敢于说他已经把某一历史时代的所有史实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这样说,并不是在提倡“不可知论”或所谓“历史解读相对论”。历史研究和历史解读并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和判断的标准巍然耸立于其间,这就是史实,就是历史真相本身。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其奥秘正在于“史实唯一”的伟力和魅力之中。只要我们在历史解读中坚持“史实第一性”这个标准,把它确立为历史解读的唯一依据,任何视角和方法的历史解读都无法逃脱它的无情检验。某一种解读之是否可信、之能否成立,只要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用相关史实和史料进行综合考察与检验便可真相大白;即便我们这一辈学者都不在了,即便某一历史谜团直到今天仍是难以拆解的悬案,后世学者或后世的后世学者也一定会借助不断发现的新史实和新史料而给出公正和科学的评判。所以,从事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们切莫忘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句话,我们的成果、我们学生的成果,一旦发表出来,就是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存在,其立论可信度和学术含量如何,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是存不得任何侥幸心理的。
当然,有一些因不同解读而发生的争论,是大可不必留给后世学者来解决的,因为现今已经公开的史实和史料已经给出了答案。
仍以吕骥同志在批判贺绿汀问题上的表现为例:那篇博士论文给出一种解释,它的根据是伍雍谊同志的访谈笔录,其合理性和可信度如何,我们已在前面分析过了。我还可以提供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即吕骥同志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策动者和领导者。我提出的直接证据有三条,间接证据有两条。直接证据之一是吕骥同志1955年3月在中国音协党组的一次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明确地将贺绿汀与胡风联系起来,说贺绿汀“虽然没有像胡风那样写30万字,但也是系统地对各项重大的音乐问题都发表了意见……贺绿汀同志和胡风,在文艺思想上所发生的问题,实质上是一致的”①;直接证据之二是《人民音乐》 1955年第3期发表的一篇措词强硬的未署名社论,这篇社论公然说贺绿汀“和胡风思想本质相同而形态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曾长期盘踞在我们音乐领域内而没有受到深刻的揭发和尖锐的批判”,对问题性质的表述及其遣词用语与吕骥讲话如出一辙;直接证据之三是该期封底下发表的在北京音乐界动员开展联系音乐界实际批判胡风的一则报道,这个动员报告的内容也完全体现了吕骥上述讲话的精神。间接证据之一是陈毅1956年3月10日上午在中国音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明确批评吕骥和中国音协“违反组织原则的事要好好检查。批判贺的做法,不是党内正常做法,不好,有宗派情绪,造成思想混乱”;间接证据之二是周扬1956年3月13日上午在中国音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同样批评吕骥和中国音协“发动对贺的批评……把他与胡风相提并论,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②。这三条直接证据、两条间接证据既是史料,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实,它们起码可以证明我提出的解释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敢确证自己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定论,仍然呼吁这个事件的当事者、见证人及其他同行能够拿出足以证明另一种解释的确凿史实和史料来,以便把这个根本算不上复杂的历史真相彻底弄清楚,而不要回避当代史家的学术责任,把它当作历史悬案留给后人去解决。
总之,明确史实和史料的联系与区别及史料辨伪的重要性,在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中牢固确立“史实第一性”原则,响亮地提出“回到史实中去”的口号,使得“史实第一性”原则成为历史哲学的核心、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历史解读的唯一依据,这几点正是我从“新见萧友梅珍贵文献”这个事实中所获得的启示。所说不一定正确,敬请前辈和同行们批评指正。
注释:
①吕骥1955年3月在中国音协党组会议上的讲话 (夏白整理),由中国音协印发。
②陈毅讲话记录稿(摘录)和周扬讲话记录稿(全文)见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附录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11月版。
